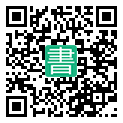第二十三章
他當然不會告訴她東宮一切盡在他掌握,只是對他們如此明目張胆感到不悅。
丞相漫應道:「這是臣份內。」然後轉頭眺望蒼穹,太陽升起來了,天那麼藍,如果沒有昨晚的變故,今天一定是個臨湖觀景的好天氣。
丞相腦中混亂,也想不起來再要盤詰些什麼,撫著額頭道:「孤要小憩一會兒,你且回去吧。」搖搖晃晃走了兩步忽然頓住腳,回過身一臉困頓地問他,「陛下昨夜和你說了很多話么?都說了些什麼?」
她不肯妥協,執拗道:「我不過想請太后寬懷,太后這些年不易,況且她為人如何,相父不知道么?」
「黃門不知情,臣卻知情,陛下難道不覺得不妥嗎?」他滿臉的恨鐵不成鋼,「只要再耐兩個月而已,他自然就入禁中了,這之前倘或被人拆穿了身份,事情可大可小,這種事還需臣提點陛下?」
她的人生,大概真的還需要修鍊,別人能夠輕慢忽略,唯有太后不能夠。
扶微徇私起來雖顯得執迷不悟,但她不莽撞,懂得權衡利弊,能讓她全心維護的,必然是最值得維護的。
太后緩緩點頭,沉默良久方開口:「陛下,莫使親者痛,仇者快。」
她懂得她話里的深意,在她試圖打破朝堂上看不見的勢力同盟時,他們也在盤算著如何剪斷她的羽翼。梁氏再不濟,有太后這層關係,還有些許能夠為她所用的人。如果連太后都折進去了,將來遇事無詔可奉,那麼想親政,路只會走得愈發艱難。
靈均在他的訓斥里低下頭去,窘得滿面通紅,「學生只是……不放心陛下。」
「那個韓嫣,要不是為了留活口,早就該梟首棄市了。」他語氣淡淡的,可是又有隱約的切齒之恨,從字裡行間透露出來,連他自己都沒有發現。
丞相的頭痛又發作了,「不放心?不放心便胡作非為么?那是禁廷,和尋常人家不一樣,翻牆入戶是死罪,你懂不懂!孤知道你們小兒女,又快要成親了,你心裏惦念她……或許將來處得好,日久生情也未可知。」他仰起臉,心頭五味雜陳,「可是靈均,孤同你說過,不要將她當成普通人。她是九五之尊,是大殷天子,別人可以縱性胡來,帝后不能。前朝孝昭皇后,六歲封后尚且可以母儀天下,你竟連六歲孩子的謀划都沒有么?」
她拿出全部修為來,努力不讓自己失態,裝作不經意的樣子問:「相父為什麼生氣?」
「孤當初向陛下舉薦你,是看你素來持重老成,沒想到你如此荒誕!禁中是什麼地方?你知道有多少眼睛在盯著?陛下遇襲的事剛出,你就迫不及待送上門,不怕被人拿住了當刺客正法?退一步說,即便留你的命,你是個男人,朝中原本就風言風語不斷,此事再一出,陛下的名聲豈不徹底毀了?」
她咽了口唾沫,「相父怎麼知道?」
他總是這樣,你同他抒發|情懷,他卻要同你談政事。扶微黯然道:「衛士再多,不能洞穿人心。刺客臉上又沒刺字,誰知道哪個受命於人。」當然警備還是要加強的,不過她有自己的打算罷了。侍中和中常侍必要是親信,如果連這個都由別人安排,那才是真正一輩子受制於人。
攔路的人面無表情道:「永安宮與行刺案有牽連,在尚未洗清嫌疑之前,陛下不應該與太后見面。」
「斷罪量刑,目下就擬定……太急進了。」他煩躁地揮了揮手,命輜車走動起來。城中的直道寬闊平坦,道旁栽著林蔭,也不覺得曬人。只是車轂沒有緩衝,地面上小小的一點坑窪,震蕩便直接傳輸進脖頸上來。他不得不扶住了頭,忽然想起聶靈
m.hetubook.com.com均,半睜開眼問家丞,「少君可來府里?」當初他收養的遺孤是一對姐弟,計劃里本就是要將聶靈均送進宮的,恰好他有個阿姐打掩護,對外便稱姐姐是養女,弟弟收入門下,當了他的學生。後來聶女早夭,靈均一人頂了兩個名頭,出入相府也不必忌諱,用他本來的身份就可以。
丞相直皺眉,看著那細細的傷痕上滲出血來,她自己又看不見,只得抽出汗巾,摁在她臉上。
丞相揖拜,抬起頭時,她人已經在夾道那頭了。
丞相道:「陛下寬心,臣定會保大典如常舉行。」
一君一臣誰也不說話,這泱泱的直道,總有走到頭的時候。
她心裏暗暗感到失望,直說吃醋多好,直說後悔促成多好。難道臉上那點怒容,真的只是怪聶靈均唐突嗎?有時候她在他嘴裏,簡直就是個傻子,他除了搬出忠臣和長輩的姿態來訓誡她,還會什麼?
伴君如伴虎嘛,雖然沒有性命之虞,但丞相一直都準備著,迎面她那些刁鑽古怪的衝擊。前段時間的驚濤駭浪還在眼前,忽然之間歸於沉寂,居然也會讓人感到惶惑。不知為什麼,她的話裡帶上了傷感的味道,是因為他沒有鬆口赦免上官照,還是因為昨晚上的遇襲?
她聽后不過平靜地點頭,「他很好,我要多謝相父把他送到我身邊,至少寂寞的時候有個人說說話,我心境也能開闊些。」
太后忌憚有外人在場,只是緊緊抓住了扶微的手,視線在她受傷的左臉上巡視了一遍又一遍,「傷得可深么?這幾日不要沾水,結了痂就不要緊了。」
說了句大實話,心頭驀地一陣輕鬆。在他看來這已經是最好的讚美了,能入宮充當女御的都是百里挑一,說她艷冠群芳,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他繁複斟酌了下,「其實陛下長得不難看,如果拿禁中的姑娘來比,恐怕尚沒有人能比得上陛下。」
太后哭得厲害,這是真話。長御打起珠簾迎她進內卧,她停在入口處的雲母屏風前回稟:「母親,臣來了。」太后沒有像往常一樣賜她玉幾就坐,內寢一陣匆忙的腳步聲傳來,太后已經繞過屏風,那倉惶的模樣和哭紅的雙眼,叫她無端一陣揪心。
靈均點頭,「只有這些。」
他越是這麼說,越是激起她的逆反心理,「難道相父也覺得幕後主使是太后嗎?太后和我親厚,宮掖里來去從來不受限制,如果想害我,任何時候都可以,何必非要找人來行刺我?多個人知道便多一份危險,真有這樣喜歡多此一舉的愚人么?」
君心難測,丞相百思不得其解。從中東門上出宮時還在納罕,少帝一夕變了那許多,究竟是自己平時沒有看透她,還是她受了刺|激,昨晚打傷了腦子?
在就好,想必是昨晚先斬後奏,今天想明白了,來給他告罪了。孩子就是孩子,一時興起便什麼都不顧不上,少帝的狗脾氣他不抱多大希望,靈均自小在他門下,居然也這樣孟浪,真是砸了他的招牌!
她那麼不留情面,誰還能把她和前幾日那個言笑晏晏的人聯繫在一起?她是君王,心思深沉,甚至有些薄情寡恩。她從來不做無用功,一舉一動都有她的目的。如果之前只是為了拉攏,那麼現在呢?他尚且沒有入套,她就堅持不住,原形畢露了?
她耷拉著嘴角看了他一眼,「一再碰壁,換了相父也高興不起來吧!我的心肝又不是鐵打的,還不許我失望嗎?」如果他現在有點什麼表示,說不定她就縱過去抱住他了。可是他沒有,眼神閃躲著,最後終於調開了視線。她灰心之餘自嘲m.hetubook•com•com地一笑,一面繼續前行,一面喃喃道,「我一直在想,如果身邊有人,就不會讓我戰得那麼狼狽。我曾經說過的,我的那點拳腳功夫,根本不值一提。昨晚上是僥倖,想必韓嫣這一年來疏於練習了。如果換一個力壯氣猛的……」她揚袖指了指高高的白虎闕,「那裡應當已經掛起了白幡,丞相今天穿的也不是縉帛,而是緦麻了。」
若說向著她,自然是的。往光明處想,母子情深,太后護衛先帝獨子,是為保大殷江山永固;往私心上想,她們的榮辱都系在一處。太后無子無孫,換個人來當皇帝,或者退回皇后位,或者去當太皇太后,兩條路皆不會比現在更好走,所以何必挑起爭端,為他人做嫁衣裳。
天太熱,即便有帷蓋遮擋,丞相依舊覺得心浮氣躁,十分的不爽利。昨晚一夜沒合眼,今天眼皮發沉,然而腦子靜不下來,就像餓極了的人餓過了勁兒,反倒不覺得餓了。
從永安宮出來,扶微依舊心事重重。腳下茫然,走了一段路后漸行漸緩,偏頭問:「離大婚還有兩個月,這期間若不能斷案,連大典辦起來都束手束腳。到時候諸事紛雜,萬一又有刺客混進承辦的宮人中,我有幾條命,也經不得那樣消耗。」
丞相向太後行禮,口中領命,心裏卻再三回味。一口一個「我等」,這是將眾人都包涵進去了,這其中當然也有他。捉拿嫌犯不單是為穩固社稷,也是在為自己洗清嫌疑。這宮廷之中有哪個人是簡單的呢,就連一向不聲不響的皇太后,也不是好相與的。
家丞道有,「長史已代君侯查收了,還有武陵案斷罪量刑的陳條,一併送至君侯下處了。」
丞相擺手打發他自便,轉過身時撇了下唇,既然相談甚歡,怎麼可能僅僅如此。看來他真的上年紀了,以至於這些年輕孩子都把他當成老糊塗了……
扶微心頭突地一跳,果然什麼事都瞞不住他,那個無用的建業在廊下守了一夜,居然還不及丞相耳聰目明。
太后聽了她這番話,才略微安定下來,臉上的焦躁慢慢褪去,輕舒了口氣道:「才也罷,德也罷,這宮門之內,活的是帝心。只要陛下信我,旁人毀我、謗我,都動搖不了我。」說罷望向丞相,「君王在禁中遇襲,執金吾和光祿勛難逃干係。刺客是從掖庭出去的,北宮宿衛得撤換,這些都要勞君侯費心。永安宮侍御和此事有關,實在是我始料未及,也請君侯一查到底,絕不要姑息。若有辭供要盤問老身的,隨時可以遣人來永安宮,主謀一日未伏法,我等便一日有嫌疑。君侯既然承先帝遺命,盡可放開手腳,我等亦不敢有悖。」
她不可思議地望向他,「所以在你心裏,只有自己最重要,是么?我身邊已經沒有親人了,只剩這位阿母,雖然不是親生的,但我幼年曾經得過她的拂照。這些年你們打壓外戚,梁氏族親里,官位最高的不過是個少府。至於我的外家樓氏,連一個在朝為官的都沒有,不就是為了讓我無力可借嗎。我沒有膀臂,我是孤家寡人,這些我都能忍,現在連太后也不放過,丞相,你究竟想幹什麼?」
她兩手捧起來,喪氣地捋了一把臉,「我剛才太焦躁了,相父恕罪……」竟忘了頰上的傷,用力刮過去,痛得倒吸了口涼氣。
她負氣,哂笑一聲道:「有相父為我善後,我一點都不擔心。我本來還想感激相父把靈均教導得這麼好,誰知相父竟然怪罪他,這卻叫我難辦了。我的皇后,不忍我獨自住在空蕩蕩的寢宮裡,有錯么?相父既不肯留下陪我,難道還不許他來和圖書?」
他自稱臣,把靈均嚇著了,惶惶然打拱長揖:「學生有不到之處,老師罵也使得,打也使得,萬萬不要這樣。」邊說邊偷眼覷他,「老師怎麼了?是在為學生貿然入宮生氣么?」
丞相終於抬起眼,飛揚的偃月壓著驚鴻,那眼眸如深不見底的寒淵,透出晦澀不明的況味來。
帝王家的威儀,無論如何都不能丟,尤其是當著外臣的時候。梁太后斂容,矜持地向他頷首,吩咐長御:「賜燕相國座。」
皇城距離閭里有一段路,煩亂之餘靠著圍欄打盹,睡不著,卻把以前的記憶又拿出來翻炒了一遍。先前她說梁太后不容易,可是認真論,不容易的其實是她。她五歲登基,因為視朝時間太長,常常憋不住尿。御前的黃門就給她準備一個便桶放在御座后,有時臣僚奏事奏到中途,她忽然大喊一聲「卿且稍待」,然後跳下御座到後面自己小解,滿朝文武在一片咻咻的聲浪裏面面相覷,那個場景,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可笑。後來她長到八歲,開始掉牙,拖著鼻涕搖頭晃腦念書,念到高興處狗竇大開,那缺了兩顆牙的尊容,實在是沒法細看。丞相覺得這一輩子盡記得她的醜樣子了,所以太熟的人,又是長輩……唉!
「我自己來……不礙的……」真是奇怪,習慣了他愛搭不理的樣子,偶爾心血來潮表示一下關心,自己居然不能適應了。她一手捂住臉,一面匆匆轉身,「武陵案又牽扯了燕荊二王,相父不要顧此失彼,忘了那件最要緊的案子。不知韓嫣與源珩等有沒有關係,她開不了口,就從劉媼那裡下手深挖吧,但凡親族中有牽扯的,不論遠近,一個都不能放過。」
其實丞相何等聰明,不會猜不透她的想法。她要集權了,很多計劃開始有條不紊地展開,他不見得沒有察覺。但她遲遲不鬆口,再也不像十年前那樣好拿捏,他想控制她,須得費些周章。
他的話似乎沒有什麼錯漏,可卻讓扶微如此強烈的感受到,這是個多麼冷酷無情的人。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利害,沒有親情,更沒有愛情。當時她要救上官照,他可以大義凜然地拒絕,現在連她想去看望太后,他也橫加阻攔。她知道忠君事主是他冠冕堂皇的借口,他關心的並不是她的安危,而是她背後的大殷江山。
這是她這麼多年來,唯一一次對他大動肝火。以往再惱,相父還是掛在嘴上的,這次居然直呼他的官職,可見是真的氣急了。
怎麼責罰?這是要當皇后的人了!丞相垂眼打量他,那窄窄的脊背輕輕顫動,彷彿是懼怕已極的模樣,可是深衣下的心呢?或者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十四歲,並不是什麼都不懂的年紀了,接近權力的最巔峰,慾望和野心一旦膨脹,誰知道將來會怎麼樣。但願他的棋沒有下錯,否則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那一世英名可真的全完了。
「那朕就下令丞相了,兩個月內務必查明真相。」她抬起手,小心翼翼掖了掖臉,「這一劍不能白挨,傷在手腳上都猶可,偏偏傷在臉上……我在相父眼裡本就是個醜八怪,這下子好了,相父更有理由來堵我的嘴了。」
扶微斷然揮袖,「我聽了太多這樣的話,口口聲聲為我好,卻將我一步步逼入絕境,都是你!」
但好好的一句話,因為他的那句「不難看」,恰恰起了反效果。連夸人都誇得那麼不走心,丞相辦事不容情的臭名,還真是實至名歸。
扶微大覺狼狽,怎麼連一頭睡了這種事他都知道!又想不出話來周旋,便敷衍道:「聶卿是相父高足,利害他自己知道。反正昨夜章德殿沒有一個黃門https://www.hetubook.com.com發現他,我想應該不會出紕漏的。」
「就這些?」
她還記得八年前,定城侯借保護幼主為由,堂而皇之要求入朝宿衛。定城侯是文帝幼子,一度與臨淄王爭權,爭得人盡皆知。礙於他的出身,三位輔政大臣都無權阻攔他,那時是太後站出來,在司馬門上厲聲呵斥他,才將他趕回了封邑。
家丞扶車應道:「仆出門時,正遇見少君來給君侯請安。仆說君侯暫且不在,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府,少君說無妨,料現在應當還在府里。」
靈均無地自容,泥首伏拜下去,「是學生的錯,學生不顧大局險些釀禍,請老師責罰。」
「陛下……」她欲上前,忽然看見丞相隔簾向她行禮,滿心的話霎時就堵在嗓子眼裡,什麼都說不出來了。
丞相謝過了,靜靜跽坐在簾外,少帝與太后的對話輪不到他插嘴,他只需當個旁聽者就好。
她回頭看他,語氣沮喪,「我三歲喪母,一直把太后視作自己的親生母親。雖然這十多年來我不能和她親近,但只要她還在,我就覺得不孤單。」
「臣一切都是為了陛下……」
丞相道是,「陛下仍舊執意去永安宮?」
用不著過多的話,單單這幾句她就知道主使不會是太后。她心裏酸楚,卻不可外露,低聲道:「臣記住了。這陣子委屈母親留在永安宮內,待案子水落石出,臣即刻撤了宮禁。」
他握起雙拳,略頓了一會兒才放鬆下來,垂手在他肩上虛扶一把,換了個溫和的語氣道:「孤不是怪你,是怕你欠思量,不計後果害了陛下。孤是信得過你的,普天之下最大的秘密孤都告訴你了,可見孤對你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只願你每踏出一步都三思而後行,為江山社稷保護好陛下,便不負孤對你的囑託了。」
一起便一起吧,至少目前他還不會對太后不利。她錯身出了樂城門,面前筆直的一條大道,直通天際似的。禁中的道路都是先秦留下的直道,寬敞,一目了然。路面上鋪著工整的青磚,前夜雨勢再大,今天也不會污了足上鞋履。
她說得模稜兩可,並沒有正面給他答覆。心裏有些怔忡,支起耳朵等他反應,結果又是半晌無語。在她將要鬆懈的時候乍然聽見他問了一句:「昨夜聶君入東宮了?」
丞相沉默,隔了一會兒才道:「陛下御前不必添置衛士嗎?多些人手,陛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丞相搖頭,「臣不需要知道,臣只想提醒陛下,既然身在九五,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比什麼都重要。孝宗時期諸侯割據,哪個宗親不是血胤?結果又怎麼樣?兄弟間尚且為嗣位鬧得你死我活,何況一個本就不相干的人。」
扶微踏進樂城門,建業和不害迎了上來。她回首一顧,寥寥道:「相父忙了整夜,快回府里歇息去吧。」
是不是?好像是的。於是丞相把對少帝說過的那通大道理搬出來,重又對靈均複述了一遍。
家丞上來接應,擎著傘把他送上輜車。他坐定后勉強穩住了心緒,「今早可有簡牘送進府里?」
他聲線涼涼的,「主公近來似乎心緒不佳,怎麼總說些喪氣話?」
靈均有些茫然,細想一下,少帝登床不久就睡著了,確實什麼都未說。然而如實回稟,只怕這位多疑的丞相不能相信,他只得含糊支應:「陛下和學生說了遇刺的經過。」
君臣一前一後慢慢前行,雨後天色空濛,空氣是清冽的,混著泥土與青草的味道,有點像卻非殿里常燃的青桂香。扶微深深吐納,「我已經很久沒和相父一齊走走了,這次還是託了韓嫣的福。」
終究是女孩子,再狠的心,做不到男人那樣絕情。他和圖書略頓了下道好,「陛下不宜單獨前往,臣陪陛下一起去。」
丞相點了點頭,「夜宿章德殿了?」
不求他安慰,也不向他撒嬌,如今的少帝行為很正常,卻又好像少了點什麼。丞相心裏空落落的,「再等幾日吧,靈均就快入宮了。」
扶微側身回望,深黑玄端壓不住她的憂慮,憂慮中又悄悄開出了希望的花……他好像確實很不高興,有什麼道理不高興?終究還是有些在乎她的吧!
心情不好,不知是一樁接一樁的案子鬧的,還是因熒惑守心的緣故。車到府門前時他才睜開眼,睜眼便見靈均在車旁站著。他從木階上下來,他很快上前攙扶,輕聲道:「老師一夜辛苦。」
丞相隱隱感覺怒火升騰,幸好他早就知道她的把戲,從來沒有把她朝堂之外的話當真。如今她興緻索然了,可以沖他發火,他卻不能。他只有盡量克制自己,告誡自己一言一行,都必須合乎一位宰相的風範。
丞相眼睫低垂,冷冷道:「若是陛下決意除掉一個人,會親自動手么?這世上多的是亡命之徒,金尊玉貴的人,誰願意雙手沾滿血腥?皇統為先,親統為後,在臣眼裡,只有陛下的安危最重要。至於其他的,即便是皇太后,亦不在臣的考量之中。」
扶微發了一通火,漸次冷靜下來。自己反思一下,好像確實有些糊塗了。他的最後幾句話,總算是站在她的立場上。退一萬步,假如太后脫不了干係,她要留她活命,影響當然越小越好。
他以為她會趁機又讓他補缺,讓他這兩個月留下陪她,誰知並沒有。
丞相面色不豫,進門遣開了仆婢才道:「臣怎及君辛苦,半夜裡來去禁中,冒著雨,又要躲避禁衛,可見比臣忙多了。」
前面即是永安宮了,她一拂袖邁進宮門,連辯駁的機會都沒留給他。丞相心裏百般滋味,無奈看著她走遠,不得不跟了上去。
他向她拱起了手,「臣還有事回稟陛下,掖庭共有采女二百四十六人,臣等俱已一一審問,沒有發現任何疑點。韓嫣傷重,暫且開不了口,獄醫正為她治傷,如果她挺得過去,或者還能從她口中盤問出些線索。依臣之見,此事不宜宣揚,陛下可以欽點幾位大臣暗中查辦,不管是韓嫣也好,劉媼也好,甚至是太后……朝中參与的人越少,將來迴旋的餘地便越大。」
她不由蹙眉,「相父這是什麼意思?」
扶微不語,聞見他袖籠中飄出的淡淡香氣,不知怎麼,彷彿怒氣一瞬消散,忽然變得無措起來。
「臣會……保母親無事的。」她咬了咬牙,「臣心裏都知道,沒有母親,便沒有臣的今日。」
丞相嘴角微沉,明明一臉陰雲,語氣卻一點都不違心,「臣沒有生氣,聶君與陛下相處得好,臣葉感到欣慰。帝后本就一體,同塌而眠亦是人倫,任何人無權置喙。只不過聶君過於縱性,讓臣后怕,現在是非常時期,萬一哪裡出了紕漏……」
扶微擠出個乾乾的笑,「多謝相父誇獎,我還有件事打算命人去辦,先同相父通個氣。掖庭里的家人子,趁著這次的好時機,全都放出宮去吧。我要這些女御幹什麼,讓她們在深宮裡一天天枯萎嗎?女孩子的青春多重要啊,十八九歲,花兒似的……不知我十八九歲時是什麼樣子,長不出鬍子和喉結的話,是不是應當把御座再升高一點,好讓文武百官看不清我的臉……」
靈均站起身,羞愧道:「敬諾。昨夜是學生魯莽了,今後再不會發生這樣的事,請老師放心。」
靈均道是,「不過逗留的時間不長,四更天便出宮了。」
原本這倒是個增進感情的好時機,可惜她心境不佳,提不起興緻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