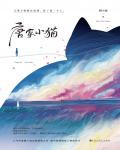第四章 四壁有僧衣,心事照佛面
他幾乎是佩服起蘇小貓的直覺來了。她並不懂一些東西,卻能感受到真相的面貌,這是天性的力量。做記者,她非常合格。
即便以專業性的眼光來看,蘇小貓也不得不承認,台上的這一位傅公子,已是相當具備某種頂尖生意人才會有的特質。懂得寸步不讓的進攻,也懂得適可而止的退讓;懂得笑容可掬的攬客,也懂得冷若冰霜的拒絕。這是一個已經經歷了成功、還未嘗過失敗滋味的年輕人,在他這一個年紀,能有這樣的成績,是可以被允許自傲的。此時的傅絳正握著麥克風,聲音透過話筒穿透到了全場每一個角落,宣布一個驚人的數字:「截至今日零點,『遙鄉』基金會管理規模正式突破一百億!」
「見笑,話題扯遠了。」
蘇小貓放下手裡的白棋,在這個深夜終於直面了一些問題。
年輕的男人長身直立,在夜色中,神情玩味。
「我說呢,誰的眼力這麼好,能看出那副畫的真偽。我差點忘記了,那年那場拍賣會,你也在。哦對了,你在那場拍賣會上拍下了全場最高價,拍走了鍾家大小姐鍾文姜一生死守的祖宅,聽說鍾文姜後來找過你求過情,你心軟了?真是處處風流。」
「我認識的那個?」
這樣子一個唐勁,如何去對她質問?
他仰頭一口飲盡一杯威士忌,「啪」地一聲放在了吧台上,「唐家的二公子,和傳聞中一樣,說話痛快。」
他似乎意猶未盡,「你不喜歡嗎?昨晚你的聲音,可不是這個意思哦。」
蘇小貓把這事從頭到尾想了兩天。
「當然不。」他意猶未盡地看著他:「我只是好奇,蘇小貓那麼精明的一個人,怎麼會被你騙過去了。」
人總是會老,模樣總是會變,她明白這個道理,但仍是不願接受。傅衡正招呼眾人,一件羊毛背心穿在他身上,穿久了都起了毛邊。今日四方來者甚多,政府要員、資本集團、福利機構,傅衡身為創始人、一院之長,這一天忙得脫不了身。
全場嘩然。
昨晚在浴室里對她問了關於宋彥庭的質問之後,蘇小貓也只是笑盈盈地反問一句「你要聽嗎?」,他忽然生起氣來,對她,也對自己,就此放任了一回情緒,講了一句「不要聽」,就將人壓在牆壁上。
傅衡是在庭院里找到蘇小貓的。
邵其軒曾經對唐勁有過一個非常微妙的評價:直覺太好。
「呵。」
主會議室前,五星級酒店的安保流程嚴格有序。蘇小貓遞上邀請函和名片,又在登記卡上簽字,工作人員核對無誤后,一位侍者上前,將她引進會場。近千人的會場座無虛席,數盞水晶燈投下華麗的暗影,蘇小貓就是在這人聲鼎沸中,對上了傅衡的視線。
傅絳剛應酬完晚宴,開車來這裏接他回家。車子停在不遠處,似乎是停了好一會兒了,這會兒他才下了車,走了過來。
她舉步離開,頭也不回地留給他一句話:「只不過,傅院一生的心血,你不要給我把它搞砸了。」
唐勁笑笑,一臉無辜,「我又怎麼了?」
最後,他給了個模稜兩可的答案:「還好。」
唐勁偏頭一笑,「到時候,我們看一看,是你的閑言碎語厲害,還是我們唐家要解決一個人的決心厲害。」
「怎麼會,傅院。這裏變得更好了,是好事啊。」
唐勁微微一笑,沒有否認。
蘇小貓徑直去了這次採訪所在的酒店。
侍者在一旁手法熟練地切好片皮鴨,又由另一位侍者擺盆上桌,笑容可掬地說:「二位,請慢用。」蘇小貓如蒙大赦,第一次覺得這服務真到位,終於來了個聲音打破了沉默。蘇小貓一塊一塊地夾給傅衡,說來說去就那麼幾句,「傅院多吃點」、「傅院再吃點」。
「你哪裡來的自信,敢和唐家比?」
這裡是老貓的埋葬之處,是她的老貓的安息之所,也是她從稚子成為獨檔一面的成年人的地方。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世間萬頃風浪,她仍是找得到這一個地方。這不是人的直覺,這是獸的本能,她身體里流淌著天性的原始獸|性,只待蘇醒。
唐勁笑笑,將冰水置於吧台,等它化開,聲音和冰水一樣冷,「傅院長一生的心血,你不珍惜,拿它來講故事,締造你想要的金融帝國。可惜你的帝國尚未建成,骨子裡各方面的窘態已經漸漸顯露。但你有一天忽然發現,你已經被纏進去了,身不由己。金融就像雪球,一旦滾下去就停不下來,只會越滾越大,你的雪球不是實心的,是空心的,最後撐不住重量,毀滅就是一瞬間的事。你那過百億的帝國裏面,有多少槓桿,有多少槓桿中的槓桿?一旦沒有新的資金進去,後果會怎麼樣,你比誰都清楚。」
「哦?那很巧啊,說不定是同一個人呢。」
他有講不清道不明的薄怒,當即以深吻封住了她想要說出口的反抗,抱起她的腿令她除了承受之外別無出路。她被迫仰起頭,發出一聲喘息,終於明白眼前這個男人一旦放任自流她遠遠不是他的對手。
蘇小貓關於「遙鄉」的特稿經過頭版頭條的運作,一夜佔據輿論高峰。
「這麼快?」傅絳挺意外,轉而一問:「爸爸,小貓介紹過他給你認識嗎?」
蘇小貓離開公司的時候,丁延對她耳提面命:「不該你管的事,不要管;不該你查的事,不要查。聽到了沒有?」
「我不好這個。」唐勁拒絕得輕描淡寫,話鋒一轉,話中帶味:「何況,你是客人嗎?」
她每次回來這兒,都會在隔夜裡給自己準備好一條洗得乾乾淨淨的牛仔褲,一塵不染的白T恤。還有她那一雙被踩得黑黑的球鞋,也被她洗得乾淨極了,此刻正穿在她腳上,襯得她朝氣蓬勃的,活脫脫一個大學生模樣。
「呵,我了解你,不必瞞我。」
當唐勁的車穩穩地滑入夜色中的時候,傅衡身後響起了一個熟悉的聲音:「爸爸?」
唐勁端著玻璃水杯,慢悠悠地喝水,「3.2億的真品名畫,被你一擲千金拍走了,就那樣掛在父親創立的『遙鄉』門口,任它毀壞。你在見證什麼,諷刺什麼?你在看著它和『遙鄉』一同被毀滅,是不是?」
「你還說,」蘇小貓眼睛一瞪,瞪得圓溜溜的,耳根卻不自覺地紅了:「肩上都被你咬疼了。」
「那麼,你需要我做什麼?」
一口氣說了這麼多話,他似乎有些累,沒來由地咳了起來。蘇小貓立刻叫來服務員端來一杯清水,給他喝了一口。又見他伸手去包里拿了兩片葯,就著水喝了下去。蘇小貓看著她的老院長,私情浩浩蕩蕩地就起來了。這些年她心裏不講理的念頭一個個地來一個個地滅,但從來沒有一個念頭像此刻起來的這一個,似刀一樣扎在她心裏流血了,她也不拔了,誓了死要成全它。
「小貓,」他拍了拍她的肩,衷心地:「謝謝你能體諒。」
傅衡沒有說謊。然而也正是這一句「不知道」,令他彷彿一夜老了二十年。
「這麼巧,竟然姓唐……」
蘇小貓「哦」了一聲,沒有聽出他的深意。她的心思暫時不在他身上,「坦白講,我並不排斥金融。但『遙鄉』是不一樣的,『遙鄉』不適合這個。可是如今,它身上金融的氣息太重了,我很擔心。」
「被我害的?害成什麼樣了?」
蘇小貓支支吾吾地含糊過去。
她一愣,頗為不贊同:那豈不就是強人www.hetubook.com.com政治?
唐勁笑了。
「……」
唐勁看著,動作忽然停了下來。
「這就要走?」
唐勁眼色漸深。
兩個人沉默許久,直到蘇小貓開口,打破沉默。
很難說蘇小貓的價值觀是否就此成型,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在的蘇小貓顯然已經變成了傅衡所期待的那樣。蘇小貓曾聽過一句話,一個人的前二十年在哪兒,他的故鄉就在哪兒。對於蘇小貓而言,這裏就是她的根,她的家,這裏就是將她生命中所有的溫柔都留住的地方。
他應該是已經等很久了,進入七月,天氣漸熱,戶外站一會兒,烤得人從上到下的悶。蘇小貓看著她的老院長,後背襯衫被汗水浸濕了一片,蘇小貓都聽得見她的一個心,軟軟地一聲癱下去的聲音。
唐勁笑笑,「他怎麼訛你了?」
他把調子起得那麼鄭重,蘇小貓都快不知如何是好了。眼前這人是她的救命恩人,對她有養育之恩,說「幫一幫」都生分了,她和他的關係就是那一種「讓她去死她絕不苟活」的關係。
這是一個動不動就拿真心撩她的男人,也不嫌她會笑他。蘇小貓常常覺得,當初她救他一命的那點恩情真經用,以至於那以後她對他的傷害、忽視、甚至是不夠愛,都消耗不完它。
蘇小貓臉色紅一陣,白一陣,倒吸一口氣簡直想以暴制暴了。唐勁大笑,終於放下她,不再招惹她了。
蘇小貓趴著沒有動。
「所以啊,我來找你幫忙。」
這一晚,蘇小貓同自己對弈,想起那個男人,連落子的動作都停頓了下。
「如果明天它就會發生呢?」
她「哈哈」了一聲,不好意思再問下去。記者癮上來了,要做到適可而止才行,這個道理她太懂了。
傅衡不知滋味地吃了一會兒,放下筷,認真地看著她,終於道:「小貓,有個事,我想請你幫一幫。」
她似乎從來沒有認真了解過他是幹什麼的,做什麼工作的,只隱約在他接電話時聽出他似乎在做投資業務,但具體投什麼小貓也從來沒問過。第一次見到他的樣子實在給小貓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後來幾乎都快成了個心理陰影,她總覺得他活著就很不容易了,被追殺、被欺凌、被壓迫,怎麼好意思再去問他賺多少錢呢。那次在賀四爺的郵輪上,她倒是看見了他的名片,看了一眼那上面寫的「浙江小西村商品城營銷經理」,蘇小貓頓時就瀑布汗了,真有傳銷組織的既視感。
唐勁細細看了一會兒。
「我不知道,我只是預感,很不好的預感。你信不信記者會有『直覺』這回事?風平浪靜之下的東西,往往都不太好。」
兩人坐下,蘇小貓給傅衡倒茶。傅衡一看就是有事要說,剛開口說了句「我……」,又住了口,拿起茶杯喝了一杯,意思是「先不說了」。於是蘇小貓只能一杯杯地給他倒茶,傅衡一杯杯地喝,喝得很沉默,很孤獨,弄得蘇小貓也不敢出一聲大氣,悶聲不吭。
拿起一旁的餐巾,唐勁擦了擦手。他有些潔癖,不太能聞腥味,起身去洗手,再出來時他手上已經沒有任何腥味。他望了一眼滿桌的螃蟹,臉上沒什麼表情,舉步走去了卧室。打開門,一眼就看見了床上正趴著的人,趴得毫無生氣,整張臉都埋在天鵝絨的被子里,一動不動。
「你擔心什麼呢?」
那三人立刻腳步一頓,為首的人轉身,神色加深,似有話問。
這一天,她在公司被叫去了會議室談話。
唐勁摸著她的後腦,指尖在她的長發穿梭,一下又一下,聲音低沉,「我不喜歡你這樣。」
她停了停,沒回頭,放緩了腳步,意思是她在聽,有話就快講。
「不,我是問來接她的那個人。」
丁延放下稿子,抬手在其上敲了敲,忍不住一句腹誹:「這麼會挑角度,挑這麼一張照片。蘇小貓,你有心偏私起來可真是了不得……」
天生地養的小孩子,除了自己堅強一點之外是沒有其他任何辦法的。
餐桌上放著已經煮好的咖啡,鮮榨的橙汁。他在美國很多年,習慣了精緻又簡易的西式料理,蘇小貓倒是無所謂。八十年代的福利院資源有限,一日三餐的標準是「飽」而不是「好」,在蘇小貓那單薄的營養價值觀里,每天一個白煮蛋就能保證她一天的營養。事實上,這些年,蘇小貓確實體現出了「好養」的強烈個人特色,飢一頓飽一頓的,竟也能常年保持活蹦亂跳,體力和意志永遠處於一個巔峰的狀態。倒是某一天,她嘗過一次唐勁做的奶味燕麥粥之後,就再也戒不掉了。唐勁的奶味燕麥粥很有些功夫,恰到好處的奶香,又剛剛好不會膩,這是常年在國外一個人生活時用好耐心練出來的,蘇小貓對此毫無抵抗力。當然,唐勁也不是省油的燈,往往抓住機會就擅加利用,所以兩人之間一到晚上常常會出現這種情況——
一句恭維,真心卻深不見底,辨不清真假。
蘇小貓深吸一口氣,壓下了私人感情,打開電腦開始做事。
傅衡卻是知道的。
蘇小貓朝椅子上一靠,眼睛輪流在這三人臉上轉了一圈,打開天窗說亮話:「警方?還是監管層的督察組?」
「好吧。」他難得的妥協,不再與她糾纏:「這稿子過了,我一個字都不會改。」
蘇小貓當真是餓了,吃得飛快,喝完兩碗粥又要了一碗,唐勁端給她第三碗的時候抬手擦了擦她的唇角,將沾上嘴角的米粒放入她口中。蘇小貓一時不察,順勢吮吸了一下他的手指,回過神來猛地發現自己又被調戲了。蘇小貓終於受不了了,拍拍桌子抗議,「你夠了哦!」
唐勁將她抱緊,又擔心她動作幅度太大會不小心燙到,語氣終於軟了下來,「好了好了,我不對,不說了。」
這一晚,跟了唐勁很多年的保姆任姨得了他的吩咐,特地來這兒做了一頓螃蟹宴。清蒸帝王蟹,酒香大閘蟹,還有熬制許久的蟹粥。蘇小貓對螃蟹完全沒有一點抵抗力,唐勁曾見過她吃螃蟹的樣子,肉都吃光了蟹黃都沒有了她還捧著個蟹殼翻來覆去地舔,把唐勁心疼得不行,覺得這孩子實在是太慘了,這是幾輩子沒吃過螃蟹了?任姨跟著他在唐家很多年,這些年她老了,唐勁不太勞煩她,但事關蘇小貓,他仍是會請她過來一展廚藝。任姨老了,心卻沒有老,明白唐勁的心思,準備好了晚餐就離開了,給他和小貓獨處的時間。
傅絳喝了一口威士忌,森冷地盯著他,「唐勁,你不怕我把你的底細告訴蘇小貓?」
「一點小忙,都不肯幫?我的事,總比不得你們唐家來得更恐怖。」
男人緩緩放下茶杯,眼底清明。
談話進行了整整四個小時。
「可是你的預感並沒有發生,不是嗎?」
「傅絳很厲害,很聰明,甚至可以說,比當今這個社會上絕大部分人都厲害,」蘇小貓拋開私心,安撫她的老院長:「我明白,要支撐這裏,有多麼不容易。尤其在越來越市場化的今天,沒有錢,沒有利益,只談『善』,是談不了的。傅絳的選擇,是對的。」
「你這兒的酒,都是上品,都可以。」
他想起很多事,恍然間這才記起,他也不是全然無辜的。
那人面色不善地瞪了她一眼,警告意味甚濃,轉身立刻走了。丁延神色不明地盯了她一眼,往她額頭敲了https://www.hetubook.com.com一下,告誡她:「這種時候還耍手段套話,你嫌命大?」
唐勁居高臨下盯著他,眼底有些譏誚,「怎麼,不僅有槓桿斷裂的危機,還有更嚴重的問題?錢洗得太多,洗不幹凈了?」
「我知道的那位,可絕不是什麼營銷經理……」
一直以來,她都明白,他們兩個是有別於普通夫妻的相處的。
「你還有我。」
「……」
蘇小貓耳垂都紅了,一把推開他,「討厭,放開我。」
比如,唐勁在做什麼。
他的目光停在了一張照片上,「遙鄉」的正門櫥窗里,除了孩子們的各種活動照片外,還掛上了一幅畫,畫中一個變形的世界以扭曲的姿態正展現在一個孩子的面前。這幅畫似乎是裝飾品,櫥窗常年風吹雨淋,沒有太好的保護,這幅畫掛在上面,也被弄得有些破了。
傅絳看了她一眼,沒有喊名字,一看就是熟人了。
身後傳來一聲冷淡的聲音,「蘇小貓。」
比如,唐勁是什麼人。
唐勁放下水杯,聲音很淡,「傅先生如果對這些有興趣,可以去《華夏周刊》娛樂新聞部,那裡更適合你。來我這裏,你走錯地方了。」
傅絳扯了扯嘴角,扯出一個比較難看的笑容。
那天以後,蘇小貓卻沉默了不少。
蘇小貓徹底明白了。
這條罪狀太具分量了,壓得蘇小貓當場良心覺醒。她在他腿上翻了個身,摟住了他的腰。
踏進酒店大廳,一眼就望見了氣勢恢宏的指示牌:會議主廳,「遙鄉」基金年度股東會新聞發布專場。
一夜纏綿,蘇小貓睡得沉,唐勁一夜無眠。
「好,」唐勁答應:「可以,到時候我會去接你。」
傅絳大笑。
「是小貓啊。」
也因為這樣,他和她之間的相處非常大而化之。她又是頗有些江湖氣的女孩子,不愛刨根問底,也不愛將生命的重量掛到一個男人身上去,以至於他們兩個之間說過愛、上過床、交過心、結過婚,也從沒有一個人率先問一句「你過去是怎樣的?」。
唐勁從冰桶中抽出一瓶威士忌,給他倒了一杯,把酒瓶放在吧台,轉身給自己倒了杯清水,連冰塊都不放。
唐勁只要一這樣子,她就不行了。她這二十多年的人生從沒有被什麼人用力對待過,以至於撞上他的一腔深情,她下意識就會衡量她得拿什麼才能回報他。此時唐勁的手正從她的薄唇游移下去,在她睡衣領口問了問路,蘇小貓明白他的意思,他想要她了。每當這時她就開始思考應該如何禮貌地拒絕一下以示矜持,她因焦慮而扭了扭身體,殊不知這一個動作將他的手滑得更深了。他順勢握住她胸前的肌膚,俯下身喚了聲「小貓」,就這樣用力覆上了她,開始做一個男人拒絕不了、也不容拒絕的事。
傅絳氣定神閑地撐著下巴,言歸正傳,「唐勁,我今天,還真是非來找你不可。」
蘇小貓沖他一笑,揮了揮手,意思是「我到了,不用招呼我」,傅衡卻仍是過來了。
她曾經的「遙鄉」已經不復存在,宿舍、教室、食堂、操場,都沒有了。樓塌了,平地起,舊的過去,新的開始。蘇小貓明白,傷感不由人,歷史總是浩浩蕩蕩地往前走,不為任何一個人停留,但她仍是有一瞬間的失落,彷彿她的家沒有了,她又成了二十多年前那一個被人遺棄的孩子。
「哦哦,這樣。」
「說到這個,你不是比我更擅長嗎?」
蘇小貓是不可以這樣的。
這個男人,溫柔、不爭,常常會令她忘記了,他到底還是一個男人,且是從唐家出來的,本性中的暴力與佔有慾始終存在著,他只是有意壓制著,不輕易讓之蘇醒。一旦見了光,對手是她,一樣開殺戒。
「嗯?」他轉身,見是傅絳:「怎麼了?」
周四,蘇小貓背著單肩包,胸前掛著一台相機,一身清爽地去了S市。
「傅絳把這裏變成這樣,你不高興了吧?」
蘇小貓那重重點下去的頭,忽然靜止不動了。
他是從唐家出來的,唐勁對很多「不是好事」的事都有本能的警覺性,被唐勁暗示過的,十有八九都成了壞事。
「話不能這麼說,這是犯法,」傅絳笑笑:「我檯面上的,可都是合法的。」
唐勁點點頭,「我知道,怎麼了?」
蘇小貓想了想,又想不出什麼頭緒來,索性不想了,飛快地再扒了兩口粥,洗好碗就興緻高昂地上班去了。
「當然。你很有名,有名到連我都不得不在意你。」
唐勁:「我也累死了,心累。」
小貓吃得快,講話也很快,「本來這個採訪不是我負責的,但有感情嘛,總不想讓別人做,所以就找丁總把這事攬下來了。然後吧,我就被丁總訛上了。」
唐勁緩步走過去,伸手朝她腰間一摟,用力一抱,將她抱了起來。蘇小貓就這麼趴在了他的腿上,連聲哼哼都沒有,軟趴趴的,一個病貓。
蘇小貓站在大廳指示牌前,定定地看了一會兒。笑容可掬的酒店侍者過來問,是否需要領路,蘇小貓有些冷淡地回應了聲「不用」,將侍者打發了。
「3.2億的真品,就這麼掛在門口蹂躪,你在對誰諷刺?」
然而這一晚,卻是連蘇小貓最愛的螃蟹也引不起她臉上的笑容了。她心不在焉地喝了一碗蟹粥,又意思意思地啃了兩隻蟹腳,蘇小貓的眼神和聲音都是飄的,吃完洗手,晃晃蕩盪地就飄去了卧室一頭趴下再也沒起來。
蘇小貓一愣,張了張嘴,抬眼看住他。
「不。只不過,我恰巧知道,有一個地方,也有一個人叫這個名字……」
蘇小貓心中震動。
「晚上你得過來接我一趟,」小貓也不跟他客氣了,這種時候還客氣她是不是傻:「活動採訪要到晚上八點結束,郊區交通不方便,我還要回來寫稿,所以你要來接我才行。」
傅絳神色未變,「我還沒開口,你怎麼知道我要你幫什麼?」
他將手裡的蟹腿剝完,完整無缺的蟹肉抽條而出。男人將它擱在了一旁,沒有吃。他不好這個,很多時候他其實沒什麼愛好,直到遇到蘇小貓。她有很多的愛好,每一種都耗費了她巨大的感情投入。他覺得有意思,所以後來常常做的,就是將她的愛好當成他自己的愛好。
「我沒有特別喜歡,也沒有特別不喜歡,發展和改變,永遠是一個時代避免不了的趨勢。」
「哦?」唐勁一笑,反問:「只有肩上么?應該不止才對。」
蘇小貓悄無聲息地走進廚房,一把趴在唐勁的後背上,以精神上的居高臨下對他道:「今天要多吃一碗,被你害的。」
唐勁看在眼裡,沒有點破。她是成年人了,成年人可以被允許有自己的不快樂,他並不介意,儘管沒有活力的她讓他也感到了些許的不愉快,但唐勁仍是保持了禮貌的不打擾,他知道,蘇小貓的不快樂是需要時間一點一點去釋放的。
再比如,唐勁在傅絳的這件事里,扮演著怎樣一個角色?
他沒有想要對她攤牌歷史的打算,對這一類問題也總是避而不談,如今迎面撞上了,唐勁頗有些自己給自己挖了個坑不得不跳的惆悵。
唐勁還是一貫的溫和,「我不忙。」
蘇小貓暗自查了幾天,天羅地網,憑她一介平凡人的力量,離真相很遠。但有時命運就是這麼微妙,架不住真相自己上門找她。這一個傍晚,蘇小貓背著個單m.hetubook.com.com肩包走出公司的時候,一眼就看到了正站在廣場台階下等著她的傅衡。
「工作上的事,傅絳這些年從不同我說。他以前不是這樣的,總是喜歡等我回家,和我說一說……大概是從他母親過世之後,他就不再同我說了。連這一次也是一樣,不斷有人上門找他,說是情況越來越不好了。我問他究竟是什麼情況不好了,他也不同我講。直到前幾天,我見他開車回來,車裡放著唐勁的名片,我才知道,他去找過唐勁。問他為什麼去找人家,他也只是笑,說人家又不肯幫,問這麼多幹什麼。」
「周四我去趟S市,有個採訪,關於『遙鄉』福利院的,」頓了頓,她又補充道:「我就是在那兒長大的。」
「沒有啦,我沒有特別要瞞你的意思,只是不知道該怎麼講。」她抓了抓腦袋,事實上,她沒有說謊,她被自己的情緒困住了,而這一種情緒她並不太能用語言表達。整理了許久的思路,蘇小貓沒頭沒腦地問了一句:「你懂金融嗎?」
唐勁忽然記起了蘇小貓之前說過的一句話:「遙鄉正門有一幅畫,傅絳掛上去的,說是裝飾。傅衡院長本想給櫥窗套個玻璃罩,保護一下,傅絳說不用了,反正只是仿冒品,便宜貨,傅院也就沒再管。那副畫好看是好看,但總讓我看了不詳。」。
「壓榨啊,強迫加班啊,喪盡天良啊,」小貓很唏噓,一股勞苦大眾的味道:「有些採訪記者只負責『采』,不負責『寫』,一環扣一環,都有明確分工的。丁總就訛上我了,從採訪到成稿再到送審,一條龍服務都要我包了,我拿一份工資,干一個團隊的活。嘖嘖,真會做生意,做新聞真是虧了他了。」
她很喜歡和唐勁下圍棋。和他結婚這半年裡,常常一到晚上兩人就開工下棋,彷彿兩個老年人,揮霍半生終於遇到了生命中能吃掉自己半個子的對手。這會兒蘇小貓一個人下,室內沉靜得聽得見抬手落子的聲音,蘇小貓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她喜歡和唐勁下。因為唐勁不止在陪她下棋,更在陪她「談」。
每每這種情況,最後都以唐勁含情帶笑的一句「成交」以及隨之而來的壓倒性佔有而結束。
這是人性,她過不了這關,情有可原。
蘇小貓深吸一口氣。
唐勁正在廚房煮粥。
蘇小貓抱著腦袋,官大一級壓死人,她又拿出她那不值錢的人格亂保證,「以人格擔保,真的知道了。」
他露出了無恥的一面,並且自認為這並不算是一種無恥。這隻是,一種手段。
她起身,拍了拍腿上沾上的塵土,轉身笑了。
「唐家聲名赫赫的二少爺,唐家令人退避三舍的資金鏈和風控體系,都是你曾經一手締造的奇迹。只要你肯,伸手幫我一把,我這點問題,絕對不會是問題。唐家那麼恐怖的體量,你都能擺平得乾乾淨淨,何況我這一點點的量?」
聽到聲音,蘇小貓一愣。
「這是我和她之間的事。怎麼,我房裡的人和事,你也有興趣插手?」
吃著飯,蘇小貓像是忽然想到了什麼,對他道:「周四你有空嗎?」
蘇小貓興緻不高的時候,通常都不大理會人,閑閑應了一句:「你忙,我就不打擾了。」
小貓:「不要,今天累死了。」
傅絳笑了。
蘇小貓唇角一翹:她的唐勁,君子守時。
對於這種腦筋拎不清的人,唐勁連勸都不想勸了,打開天窗說亮話:「唐家後面的世界,有的是什麼,有的是哪些人,且不說是你,就算是我,直到今天,也沒有弄清楚過。那樣的世界才配得起另一種生存之道,那種法則不是適用你我這裏的。你把這點都搞錯了,還指望誰可以幫你。」
蘇小貓不說話了。她的力氣有限,都用在腦子的飛速思考上了。半晌,她問了一句:「傅絳……到底出了什麼事?」
負責談話的為首人員對她道:「蘇小姐,我們問什麼,你答什麼。其他的,你不要多事,明白嗎?」
「佔有慾這麼強……受不了。」
蘇小貓沒有用餐,收拾好了背包徑直走了出去,迎面就和傅絳來了個狹路相逢。
蘇小貓離開的時候,傅衡送她到了門口。夜色中,一輛黑色幻影低調地停在路旁的香樟樹下,車頂落了些白色的小香花,令人明白它已停了許久。
到底是獨生子,妻子又早已過世,父子相依,他終究忍不住動了私心,拜託她:「可以的話,幫一幫傅絳。我沒有力氣了,也沒有能力了,已經幫不了他了。」
比如在最初的日子里,他拜託了私交甚好的曹叔,設了一點不好不壞的局,將她誘入局。再比如,在她一開始的拒絕里,他表面坦蕩,對她講「沒關係,不喜歡也不要緊」,實則步步緊逼,對她調查詳盡,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在遇到她之前,他做過惡,但從未對女孩子做過惡,在遇到她之後,他做了一生最大的惡:用深情,也用陰謀,將她佔為己有。
蘇小貓腹誹了一句,撐著手坐起來,撿起地上的衣服慢吞吞地穿好。
他給她拿來了會議室的點心和水,拍了拍她的肩,交代道:「從公司到我這兒,估計又沒時間吃飯吧?快吃點,照顧好自己最重要。」
本以為他會避而不談,誰想他卻沒有,抬手落子時總結成了一句話:唐家是一個,由一個人說了算,萬千人認同他說了算從而赴死達成目的的地方。
四十八層的高層辦公室,傅絳在落地窗前站定,遙望窗外這一城天下,給出評價:「好地方。唐家二少爺的品味,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蘇小貓去了趟「遙鄉」。
據說,審核那晚,丁延拿著她的稿子,意味不明地笑了笑,評價道:「蘇小貓,新聞人有心偏私起來,可是了不得的作惡。」
蘇小貓看著他,一絲不亂的颱風,筆挺的襯衫西服,面帶謙虛而又相當享受的笑容,一邊上台一邊朝台下偉人似地揮手,蘇小貓就明白:這是一個極具野心的年輕男人。這一刻,她是相當困惑的。為什麼傅衡那樣的質樸天性,帶出來的獨生子,卻會有這樣一副精明強悍的模樣。
傅絳是在各方掌聲中踏著步子上台的。
蘇小貓醒來的時候,全身酸痛。
他走過來,眼中帶笑。蘇小貓抬眼就見到了傅衡已白透了的鬢邊,她心裏一軟,內心某個角落迅速塌陷。蘇小貓不是一個念舊的人,這樣的人一旦念起舊來,才是真正的生死不顧。傅衡對她而言就是這樣一個存在,在她的老院長面前,蘇小貓的心哪能叫心,根本就是一個爛柿子,經不起一絲舊情的蹂躪。
傅絳淡漠地問了一句:「你不喜歡我對『遙鄉』做的這些事吧?」
所以她喜歡唐勁。
蘇小貓呼出一口氣,關上門走了出去。
她趴在床上,頭埋在枕間,微微睜眼,就看見肩頭一道深色痕迹,那是被人用力咬出來的。她記起了昨晚唐勁是怎樣不容她反抗地佔有她,記起了他最後朝她肩頭咬了一口時她對他喊「痛死了啊」他也沒有放開她反而用力將她抱得更緊。
傅衡抿了抿唇,字字千斤重,「傅絳出了點事,希望唐勁出手,幫一幫他。」
她的「遙鄉」,她的家,已經今非昔比;身價難以估量,令她震撼。
「傅絳,你找我,找錯人了。」
令蘇小貓心下一沉的是:她不知道,這些人的最終目標是「遙鄉」後面的誰。傅衡,傅絳?
這傢和圖書伙,一看就是很會玩的類型,區別只在於他想不想玩而已。蘇小貓不再理他,埋頭捧碗吃飯。以前她真是眼瞎了,怎麼會認為他無害,怎麼會認為他溫和甚至還很好欺負?
他淡淡道:「心裏有事,對旁人,不肯說;對我,也迴避。蘇小貓,你都不知道我會擔心你的嗎?」
「我不知道。」
丁延掃了她一眼。
書房有上好的檀香,黑暗中燃著清幽之味。皓月當空,眾響漸寂,好似四壁有僧衣,心事也可照佛面。唐勁跪坐于茶桌前,手勢柔涼,借茶道寄心事,他需要靜一靜。在唐家這些年,他練就一身靜定的不壞之身,就是憑這一身靜定,得以走過了地獄。
「好久不見,您身體可好?」唐勁伸手,謙敬而有禮,同傅衡交握:「今日有勞您照顧她,改日我一定登門拜訪謝過。」
唐勁俯下身,拿起相機。帶上房門關了燈,男人徑直去了書房。坐在書房的沙發上,唐勁按下鍵,打開了相機。蘇小貓是拍照片的好手,近五百張現場照,無一不清。他明白,她是帶了私心、動了感情在做事,拍很多的照片,寫很美的文字,權當在回報當年之恩。
自目睹蘇小貓和宋彥庭在酒店談話的那一幕之後,唐勁就落了心事。
兩人你來我往了一番,蘇小貓找了個借口,「還有事,先走了。」背著單肩包舉步就走。
蘇小貓一笑,「這麼多人圍著你不放,怎麼,你還缺我一個?」
傅衡含笑,與他握手、應答。這個男人握手的力度、開口的風度、站立的形狀,都令傅衡明白:這是一個已經有過某種故事性、經歷過風浪的男人。
唐勁不趕時間,慢條斯理地回房間換了套襯衫,扣手腕處的扣子時手機響了,唐勁接起來聽了下。
被她耍了。
小貓:「why?!」
幾乎沒有旁人可以理解他的這句話,嚴格說來這根本不像求婚的話,倒像是認親。但蘇小貓卻懂,她幾乎是下一秒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她被他的話中話而感動,彷彿只用了一瞬間,這就是她的親人了。
她沒有父母,他也是;她沒有家,他也是。唐勁在向她求婚時,說過一句話:我一直在等,等一個我不需要有太多自卑和自信,就有勇氣擁有的親人。
傅絳問得很突兀,也很直接:「剛才那個人是?」
越和這男人相處,她就越發現,唐勁在某些方面其實是沒有底線的。他輕易不表現,尋常人沒有太多機會見到,往往會以為他不會,但其實,他很擅長。比方說,欺負女孩子。
唐勁看了她一眼,收回目光。
「唔。」
「酒,謝謝。」
傅衡有些奇怪地看著他,「怎麼,你認識他?」
唐勁一張張照片翻過去,心中微動。昔年一飯之恩,當毀容盤發以報,這麼古老的故事,現代人中竟還有一個蘇小貓在做,他被她震動。
兩人隔了一段距離,傅絳的聲音聽上去沒有感情,公事公辦地告訴她:「可是我很喜歡。」
雖然淡,卻很暖。他是明白的,如今的這一個蘇小貓不止是他一手帶大的小貓,更是業內聲名赫赫的記者,她的態度就是《華夏周刊》的態度,她說傅絳「好」,就可以引領輿論風向令旁人也覺得傅絳「好」。
蘇小貓沒有回頭,也沒有說話,腳步卻停了下來,沉默以對。
「連陪客人,都不賞臉喝一杯?」
三言兩語說完,他又被人叫走了,走了幾步還不忘回頭叮囑她:「快吃。」蘇小貓就在這兩個字里犯了酸。這世間,只有她的老院長,會一生一世將她當成孩子,永遠揣在心上疼一疼。
蘇小貓抬手,一下一下戳著他的胸口,「你、這、個、流、氓。」
整場發布會持續數小時,又在媒體提問環節耗費了相當長的時間,時近傍晚,發布會才正式結束。主辦方準備了精緻的自助晚宴,地點位於高層觀景台,餐后還為每一位參會人員準備了伴手禮,禮盒中除了奢侈品禮物之外,還有一個分量不輕的紅包,傅絳擺平場面的功夫可見一斑。
負責對她談話的不是丁延,不是公司任何一位領導,而是不明身份的三個人。三人穿著便衣,一人負責把守會議室門口,連丁延都不允許被進來,一人拿著錄音筆全程錄她的話,一人負責問話兼記錄。她進去的時候,丁延拍了拍她的背讓她放鬆,像聊天那樣談話就好了。蘇小貓一坐下,見這陣勢,心中腹誹,這天還真聊不起來。
很快地,蘇小貓嗅到了一絲不尋常的氣息。
唐勁抱她去洗澡的時候,蘇小貓已經筋疲力盡,由他照顧了。唐勁將她弄乾凈,抱她重新躺好,自己洗完澡出來的時候,蘇小貓已經拖著條被子呼呼大睡了。唐勁唇角一翹,真是沒心事的一個貓,即便有心事,也心事不過夜。
她抬頭,一臉不解,「誰?」
蘇小貓緩緩接上三個字:「……出事了?」
失眠的夜晚,男人撿起掉落在地的襯衫穿好,輕輕帶上卧室門,去了書房。
唐勁當時就笑了,他並不反對她的看法,只是立場不同,對她道:強人政治沒有什麼不對,在歷史上,秦漢到隋唐之間,也常有強人政治出現,甚至於有些新的朝代,也是由強人主導篡取天下而得;放到現在來看,唐家所謂的強人政治,不及歷史的萬分之一。
傅衡眼中有笑意。
自那年開始,傅衡就沒有太多力氣管理「遙鄉」了,所有的事都交給了傅絳。也就是從那一年開始,「遙鄉」脫胎換骨,從一個小型福利院轉型成為公司制管理。不僅如此,傅絳更是乘勝追擊,一舉成立了「遙鄉」基金會,進而在隨後的兩年裡以基金的名義成立了私立小學、圖書館等等數類實體,成為了今日以「善」為名的一方資本巨頭。大刀闊斧、一夜成名,傅絳的手筆令人不敢小覷。
唐勁不答,反問:「你有什麼事嗎?」
蘇小貓帶著她的老院長去了附近的一家精緻粵菜館。「精緻」二字不是人人用得起的,用得起的都是絕對的好地方,店內小橋流水,每一個位置旁都盛開著百合和鈴蘭。傅衡一邊走一邊躊躇,只說「隨便吃點就好了」。蘇小貓怎麼肯,她平時一日三頓確實都是「隨便吃吃」或者「乾脆不吃」,和傅衡在一起她就不肯了,這會兒走得虎虎生風,一臉「老子現在可闊了!」的擺闊樣。
「好,您放心,我會的。」
對於原生家庭不健全的人而言,結婚、與另一個人結合,會本能地帶著敬畏之心去審視對方的原生家庭。蘇小貓有過太多這樣的經驗。去同事家做客,同事的父母、兄妹,出來迎接,將她接待得禮貌、周到,蘇小貓往往會很無措,因為她明白,她沒有辦法回饋這一份禮貌、周到,她沒有親人可以為她做到這一份回饋,她只有自己。
事實上,傅衡帶給她的,不止是童年,還有整個人生的價值觀。傅衡從小對她講,女孩子天性會愛漂亮,這很好,但比這更重要的,是一種「氣度」,乾淨的氣度、洒脫的氣度;天性是人人都會有的,後面的這一些,卻是努力后也不一定會有的。
他目送這個男人單手摟過蘇小貓的肩,與她並肩離開的背影。
「……」
一百億,這不是一個小數目。資管規模達到百億級別體量的產品,在國內屈指可數。撇開銀行、公募基金這一類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大型個體不談,在其他個體中,一百億,絕對hetubook.com.com是一個十分驚人的體量。蘇小貓幾乎是天性般的直覺猛然有些驚醒:她的「遙鄉」,她質樸的老院長一手帶大的人間凈地,什麼時候開始,竟也被拖進了兇猛異常的金融世界?
「仿冒品?」
電話是跟了他很多年的尹皓書打來的,唐勁聽了幾分鐘,聽懂了意思,聲音清冷地朝那邊下了吩咐:「周四的談判會議替我推掉,推不掉的話就往後延。對方要等就等,不想等就告訴他們,不和我合作,可以,那麼我就只能想辦法吃掉這一塊了。做不成朋友,那就只能是我們之間留一個,你讓他們考慮好。對我而言,無論是哪一個決定,我都沒有問題。」
小貓:「……好吧。」
四個小時后,會議室的門被重新打開,一行人收拾好記錄本、錄音筆,準備離開。蘇小貓站起來,聲音幽幽地忽然說了兩個字:「傅絳……」
車門打開,他下了車。一地月色,一身風流;立身行道,始終如一。蘇小貓在夜色中看著他迎面走近,她在不自知中已有笑意漾開了眼底。
唐勁動作一頓,笑了下。反手將她拖至眼前,單手摟腰將她一手抱了起來。
她正圍著一株玫瑰,東轉轉,西轉轉,看這枝花看了很久,最後蹲下了身,伸手拍了拍根部的土,旁人見了,也不知她在搞什麼鬼。
傅絳一愣,沉默半晌之後,突然笑了。
小貓高興了一會兒,喝了幾口粥又回神了,懷疑地看著他問:「工作日你都不忙的嗎?」
客觀地來講,「遙鄉」這些年的變革,幾乎稱得上是一個「模板」。近些年資本崛起,四處獵尋,「遙鄉」以長久的歷史、良好的口碑借力踏上了這股東風,成了各方資本眾星捧月的對象。資本做事是需要「故事」的,傅衡悲天憫人的情懷和宗旨給了「遙鄉」最好的故事性,這幾乎如同「本原」一般的存在,令各方資本為之興奮、激動,這其中,就包括了傅衡拒絕所有資本也拒絕不了的一個人——他的獨生子,傅絳。
蘇小貓站在他面前,背挺得筆筆直,不知哪來的膽量,忽地生出一團勇氣,把話擋了回去:「不是偏私,是立場。我記得,新聞人是可以有自己的立場的。」
他也不放開她,就這麼一手抱著她,一手端著粥走了出去。將粥放在餐桌上的時候,唐勁興緻不減地壓低聲音又問了句:「昨晚我那樣對你,你其實不討厭,對吧?」
唐勁像是沒料到她會問這個,一時還真被問住了。
丁延獨自坐在辦公室,再次拿起桌上那份成稿。文字相當漂亮,但最漂亮的卻不是這個,而是蘇小貓配稿的一張照片。照片上,會議結束,傅絳正端著一份精緻的自助晚餐給父親,他自己則接過父親手裡尚未吃完的餅乾,幾口將它吃完,那是在會議期間被人剩下的茶水點心,傅衡捨不得,傅絳替他捨不得,於是他將父親的捨不得都解決了。一個年輕的男人,身價剛剛過百億,下了聚光燈,仍是父子相依,沒有比這更動人的瞬間了。
傅絳有些興趣,追著她不放,「方才在提問環節,也沒看見你舉手。蘇小貓,你這是在給《華夏周刊》消極怠工啊。」
唐勁的手指描摹著她的唇線,「我一定會保護你的,你明白嗎?」
他拿出兩個杯子,走到辦公室的吧台邊,問得隨意:「喝什麼?」
沒等她再問什麼,他已經看著她,悠悠反問:你是在把我當成摸底對象,調查我嗎?
「是嗎。」
有一次她問他,唐家是什麼地方?
蘇小貓重重點頭,「嗯,您說。」
蘇小貓面色不動,她是見慣了場面的,當真有心應付起來,各種情況都游刃一二,「謝謝,我當這是一種鼓勵。」
真的是傅絳,出事了。
傅絳拿過威士忌酒杯,若有所思地盯了他一眼。
內容詳細得就像慣犯落網,把身家性命都全盤托出。從出身情況、家庭人口、撫養經歷、社會關係,一直問到收入來源、工作經歷等等。談話的人很有技巧,也很有隱蔽性,什麼都問,什麼都查,令蘇小貓找不到重點。但對方始終忽略了蘇小貓的記者天性,她也是一個盤問人的好手,他們用慣的技巧,也是她用慣的。蘇小貓沉著應對,談足四個小時,心裏明白了:這些人,是為了「遙鄉」來的。他們要從她嘴裏,聽到「遙鄉」的一些真相。
「唐勁。」
豁然地,他唇角一翹,懂了。
蘇小貓空頭支票亂開,「知道了,知道了。」
「什麼酒?」
「簡單介紹過。結婚前,特地帶他過來看過我,」傅衡不疑有他,回憶道:「他姓唐,叫唐勁,當時給了我一張名片,是私企的營銷經理。」
她的眼神落在了這一座恢弘的大廳里。在五星級酒店的主廳會議室發布新聞會,這裏面宣告的意思,蘇小貓懂。
男人不置可否,走向冰桶從裏面拿出一杯冰塊,放了幾顆在水杯里,應聲拒絕,「你要我幫的事,我幫不了你。」
傅絳坐在吧台邊,自己給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眼風一挑,「蘇小貓還不知道你的來歷吧?」
這兩天唐勁出差,家裡沒人管她,她又活成了一條單身狗,自在得很。洗完澡,蘇小貓趴在卧室的地毯上,旁邊有一副圍棋,棋盤上面擺著一個殘局,是唐勁出差前和她沒有下完的。蘇小貓看了它一會兒,拖過棋盤,自己和自己下。
這是一條天性靈動的性命,鐵打的一具身體、打不死的一腔熱情,絕不能這麼瘟。
「嗯。」
丁延朝她後腦勺就是一頓打,「注意態度!你聽進去了沒有?」
「OK,吃早餐吧,我不說了。」
「您放心,」她給出承諾:「我一定會想辦法,讓唐勁幫他的。」
唐勁:「好吧,那明天的奶味燕麥粥就沒有了。」
這是蘇小貓採訪「遙鄉」的相機,自那天回來后,她經常抱著看,似乎竭力想看清一些事,卻不得答案,最終鬱郁地放棄了。
她玩味地看著他:你是因為不認同這一位強人,所以才走的?
他看著他,奉送一句話:「自首吧。或者,向監管層坦白真相。或許,你還有重新再來的一天。」
唐勁陪她談的事很多。
「請便。你動蘇小貓,我就動你。」
唐勁看見扔在床邊的一台相機。
兩年前開始,傅衡的身體就不太好了,常常是中藥不離手,蘇小貓每次見他,都聞得到他身上不散的中藥味。這是累病的,被「遙鄉」累病的,她是從「遙鄉」走出來的,這裏面的責任也有她的一份。於是每當見了他,蘇小貓就喜歡塞錢給他,常常出其不意往他抽屜里、口袋裡、包里,一把塞進去,動作熟練得一看就是個慣犯,她是在用別人偷錢的手速在給傅衡塞錢。不這樣做,傅衡根本不肯收,蘇小貓塞出去了就絕不肯收回來,兩個人都倔,最後當然是傅衡倔不過蘇小貓,以一句「好吧,就當我幫你存著」收尾。
唐勁給她倒了杯橙汁。
唐勁一笑,不緊不慢地喝水。
或者說,她根本喜歡不了別人。因為只有唐勁,和她是同一類人,是真正能懂她的人。
所以當傅絳不請自來、登門拜訪的時候,唐勁吩咐了特助「讓他進來」,並未有太多意外。
他有些老了。
「那是她的先生,半年前,小貓結婚了。」
他答得很快,是那一種只有發自真心才會有的本能反應:不,我認同他,我只是不適合,所以才走。
唐勁:「寶貝,我想親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