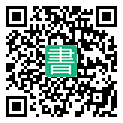第二十一章 椒結子兮
「當初說了不唱,現在為何要唱?」他抬頭望著屋檐上的我,搖晃樹梢的夜風悄悄停了,時間彷彿在我們彼此交纏的視線中凝固。
「無恤前些日子說要去代國,現在怎麼又不去了?」我輕聲問道。
「秋蘭兮青青,椒結子兮灼灼,羅生滿堂兮君欣……吉日良辰兮……」我對著空中一輪殘月,一字一句吟唱著賀子的祝歌。夫郎,我的夫郎,我願你的庭院枝繁葉茂,我願你的膝下兒女成群,我願你此後年年歲歲喜如今朝……悲戚的歌聲從耳邊拂過,滾燙的淚水滑落面頰,抽噎著抹一把濕漉漉的臉,一首唱斷了的祝歌又要從頭開始唱。
我與無恤本不該再見面,見了面,空了的地方、碎了的地方難免是要痛的。可趙鞅病著,我們又幾乎日日都要見面。一間屋子裡,眼神撞上了,以前是竊竊的歡喜,如今卻只有剜心的痛。
沒有三個,一個也不會有了。
伯魯帶著我邁進趙府的大門,沒走幾步就撞上了姬鑿和于安。
盛大的祭禮結束后,太子姬鑿與趙鞅談了許久的話。智瑤也領著一幫宗親來找他商討宋鄭之事。我遠遠地看著神采飛揚的趙鞅,心中浮現的卻是晦暗的天光下,他木然地看著銅鏡,任女婢在他萎縮的灰白色雙唇上點上花汁的一幕。
我順著他的視線望去,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一身黑色禮服的無恤。
伯魯停下腳步,蹙眉道:「阿拾,我走了之後,卿父的病就要託付給你了。我本也不想走,可府里最近閑言碎語太多,我留在這裏幫不上忙,還給紅雲兒添亂,實在有愧。」
「去哪裡?」我驚愕抬頭。
提到醫塵,伯魯一臉愁苦:「君上要將醫塵留在宮中,我們能有什麼法子?」
姬鑿一走,伯魯忙問于安道:「小舒,太子祭禮完了不回宮,來這裏做什麼?」
我在自己的肚子里挖了一個空空的洞,他的心就跟著碎了。
周王四十四年暮夏,無恤計劃著讓伯魯、明夷帶我一起離開新絳。
「你高興嗎?害怕嗎?」無恤在我耳邊低語。
「放心,有我。」從狂喜中平復下來的男人小心翼翼地捧著我的臉,他隱含淚光的眼神猶如冬日晴空里最溫暖的陽光。
「去求求太史吧,他興許有辦法。」
今年春,晉侯大疾,祭祀東方青帝的祭禮並未舉行。諸侯之祭,礿而不禘。往年,晉侯只祭春,不祭夏。但今年國君、正卿皆患重疾,而夏日又主祭掌管醫藥的神農氏,所以此番祭夏之禮籌備得格外隆重。正當所有人都以為主祭之人是太子姬鑿,姬鑿身後必是亞卿智瑤時,久病的趙鞅卻突然「康復」了。
「那告辭。」無恤冷冷一聲別,墨色的衣袂在我眼前一晃,人已經往前去了。
一個小小的生命出現在了最不恰當的時間,但它的出現卻給了絕望中的我戰勝一切磨難的勇氣。在秦國寒冷的冬夜裡,我的母親總是瑟瑟發抖地抱著我,她被寒冷、飢餓摧殘得面目全非,可她看我的眼神卻始終溫暖,因為只要這一刻我還在她懷裡活著,只要我的明天還有一線生機,她便可以無視命運給予她的所有苦難,無懼死亡如影隨形的威脅,這便是母親,這便是一個母親對孩子最深沉的愛。如今,我亦如是。
「唱得這樣難聽,還要再唱一遍嗎?」冷月下,燭海中,無恤一襲青衣走進小院。我透過閃著hetubook•com.com橘紅色光斑的淚水痴望,只擔心眼前的人影只是自己心中的一抹幻影。
晉國,我已經不能再待下去了。
分別就在眼前,但失而復得的喜悅佔據了我們所有的情緒。無恤每夜潛進我的寢幄都會像孩子守著蜜糖一般盯著我的肚子,時而抿唇傻笑,時而神情凝重,有時來了死活要纏著我說許多的話,有時來了卻只握著我的頭髮在榻旁靜靜坐上一夜。我笑他孩子氣,他卻極認真地說:「我不是孩子氣,我是太歡喜。」
我驚慌失措,無恤卻高興得像是發了瘋。他緊閉著嘴巴在屋裡又跑又跳,甚至將剛進屋的阿魚打橫抱起猛轉了好幾個圈。毫不知情的阿魚大概從沒想到自己這一生居然還會被人這樣抱著轉圈,所以被放下來時一臉發矇。
我擔憂地看著他,他朝我連連擺手:「沒事的……」
「你們呀。」伯魯沉沉一嘆,擔憂道,「阿拾,我和明夷下月就要走了。」
「所以你就把自己扯碎了?你以為這樣就可以離開我?」
「敬諾。」于安拱手。
暮春的庭院,桐花落盡,綠蔭濃重。自脫了春衣換了夏衣,天氣一日熱過一日,素紋鏡中的容顏也一日憔悴過一日。後悔嗎?那三個月里,其實無時無刻不是後悔的。可葯,我依舊是吃了。如今被他知道,不過是在日日蝕骨的後悔上再添上一份內疚、一份哀傷和一份無望。
我怕伯魯一時心急泄露了趙鞅的病情,忙笑著截過話道:「卿相腿疾痊癒是因為府里巫醫善製藥,小巫可不敢居功。雖說小巫治體傷也有小技,但君上之疾在心,療心之術,小巫實不及師父九牛一毛。」
至死方休……何苦呢……
「今日南郊祭禮,你站在高台之上,智瑤的眼神沒有一刻離開過你。他那樣的眼神,我從前見過一次,那是在晉侯的園囿里,他一箭射死了一隻雌鹿,興緻起,當場脫衣卸袍,剝下鹿皮呈給君上。今日,你站在那裡,他就那麼赤|裸裸、血淋淋地像個剝皮人一樣看著你。然後我才明白……」
「當年你勸我別養老虎,別養豬,如今居然來勸我養鳥?不過這個主意實在好,雲夢冬日多雨,一下雨,明夷那小子就喊無趣。去歲,他養了只野兔解悶,就嫌它不會說話。這回我備上十隻竹籠,讓他自己到楚國逮鳥去!」伯魯說完哈哈大笑。我想起他過去的院子,又想著他和明夷將來掛滿鳥籠的院子,也忍不住笑出了聲。
孩子出生后的第七日,姮雅派人找我給她的兒子唱祝歌。她會這麼做,不奇怪;她會說那麼多尖酸刻薄的話來打擊刺|激我,也不奇怪。她產子的那一晚,無恤和我在一起,至於我們是在屋頂上傷心難過了一夜,還是在床榻上恩愛纏綿了一宿,對她來說都是一樣的。
家族是什麼?天下是什麼?大家在拚命守住的又是什麼?
「族裡的那些人也不知是受了誰的挑唆,非說紅雲兒娶妻五年未得一子,是因為出身低微不堪世子重任,所以上天才叫他膝下無子,嫡妻無出。這簡直就是胡言亂語!他們這種時候硬推著我坐那個位置,不知是何居心!」
「兄長何事相召?」無恤問。
近月來齊、宋、鄭、衛局勢微妙,智瑤為控制軍隊一直摩拳擦掌想要領軍出征樹立軍威,順便撤換軍中趙氏將領。而趙鞅絕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他要借這次南郊祭禮,給智瑤一個訊號,給滿朝大夫一個訊號。
「夫郎,生兒育女吧,放了我吧!」我抹了淚,看著自己深愛卻不能愛的男人。
我和-圖-書忙揚起嘴角沖他笑道:「我沒傷心。這回去了楚國,記得讓明夷給你多做幾頓炙肉,阿兄不變成胖子,可別回來。」
「為什麼要燒庭燎?發生什麼事了?」我逮住一個往火盆里添柴的小僕問道。
伯魯的大子趙周在無恤「嫡子」出生后的第三天被無恤悄悄送走了。送去了哪裡?沒有人知道。府里好奇的人很多,可誰也猜不透自家世子的心思。如果要維護新生子的地位,那該被送走的,或者說該被處理掉的,也應該是長媳荀姬生的兒子。趙周,一個庶妾生的兒子,活著或是死了,又有什麼區別?
「紅雲兒,我本就是個貪生怕死、自私卑劣的女人。我不值得你真心待我。」
我請于安到後院接了四兒早些回府,自己跟著伯魯去查看趙鞅的情況。
姮雅恨我,她滿腔的恨意,即便不開口,我也能感覺得到。可讓我奇怪的卻是她屋裡的那一碗魚湯。肥美鮮嫩的河魚浸在奶白色的湯水裡,切得細細的金黃色的薑絲掛在河魚淡青色的脊背上。湯剛從陶釜里盛出來,咕嘟咕嘟還冒著白煙。端湯的小婢站在我身旁,絮絮地說著湯是趙鞅賞的,巫醫橋又吩咐了些什麼。姮雅愛聽這些話,機靈的小婢也知道她愛聽,所以說得特別仔細。我站在那裡,魚湯蒸涌的白氣一波波地噴在我臉上。這是一種從未有過的噁心感覺,我腹中酸澀之物幾乎來不及翻湧就直接衝上了喉頭。
「這麼快……禘禮剛過。」
「是捨不得呢……」我看著陽光下伯魯永遠溫柔的眉眼,心裏既替他高興,又難免因離別而哀傷。
「稟巫士,世子婦今夜喜得貴子,老家主令全府上下舉燭同賀呢!」小僕喜氣洋洋地說完,背起地上一大捆的柴薪匆匆離去。
「不外乎是因為荀姬有子吧。」我微微一笑,說出了我們都心知肚明的原因。趙鞅病重,伯魯體弱,而身為智瑤之妹的荀姬膝下卻有一子。智瑤處心積慮要在這時候將無恤趕下世子位,估計是盼著趙鞅一死,伯魯再跟著去了,這有著智氏一半血脈的小嫡孫就能繼了趙氏的宗位,叫他從此高枕無憂吧。
我不語,因為他說的是對的。即便我當初看了他寫給我的信,即便我知道姮雅的孩子不是他的,我依舊是趙稷的女兒、他們趙氏除之而後快的邯鄲餘孽。我不可能成為他趙無恤的妻子;若我對復讎無用,我的父親也不會管我的死活。這世上只有愛剝皮的智瑤會一直惦記我,因為他還等著有朝一日將我剖腹取子,助他一朝永壽,獨吞晉國。這樣的情形下,我怎麼能有自己的孩子?我若保護不了自己的孩子,就寧可不讓他來到這世上。
「你和紅雲兒怎麼了?一早上都沒見你們說話。」伯魯不知何時走到了我身邊。
趙府的院牆裡,一團團瘋狂燃燒的火焰將頭頂墨色的天空映得緋紅,我光著腳爬上屋頂,遙望著遠處人聲鼎沸的院落,想象著那裡的熱鬧與歡欣,想象著他此刻將嬰孩抱在懷裡時嘴角的笑。多好啊,我的紅雲兒終於做阿爹了。
一時間,新絳城裡傳言紛起,朝堂上的「牆頭草們」紛紛立正,持觀望之態。
「你說快,明夷可嫌我慢呢!你知道他向來不喜歡新絳。這回要走的事,我原本打算早點兒告訴你,可就怕你太傷心捨不得我們。」
在無盡的深淵里,在絕望的飽浸淚水的土地里,有一顆小小的種子發芽了,它來得悄無聲息,但註定將帶來滾滾風雲。
「我不辛苦,只是辛苦了四兒每日這樣來回跑。」我心中納悶,難道于安還不知道趙鞅的和圖書病情,四兒沒告訴他?
「她是狄族族長之女,趙氏娶她,有趙氏的考量;她入趙氏為婦,亦有她狄族不可告人的目的。多年無子,我不急,她等不了了。她要送我一個現成的嫡子替我堵住叔伯們的口,我何樂而不為?」
可是傳言畢竟是傳言。趙鞅這一次是真的病入膏肓了,不管我如何替他施藥調養,他的身體始終一日比一日虛弱。南郊禘禮就在今天。當所有知情人都為趙鞅的身體擔憂時,他卻屏退了侍從,密召女婢入室。
「我不怨他,是他在怨我。」自我吞下那些藥丸,所有嫉恨都隨著腹中冰涼的觸感消失了。我已不是個完整的女人,現在要換他來恨我了,恨我毀了他的夢,恨我這般決絕地斬斷了自己與他的未來。如今,在無恤心裏,我該是個多麼狠心惡毒的女人。
因「卷耳子」之事,我信不過趙府中的僕役、婢子,但一個人又實在無法兼顧所有的事,於是便請四兒入府相助。可董石年幼,夜裡不能離開母親,所以四兒只能每日清晨來,黃昏歸。這一個多月,著實累壞了她。
「自然是來看望卿相的。卿相能痊癒真是太好了,智瑤今日回府怕是要氣瘋了。阿拾,辛苦你了。」于安看著我笑道。
「我學醫不精,卿相的病最好還是請醫塵來看看。」趙鞅入睡后,我和伯魯退了出來。
「阿拾,你這一生無子無女,我趙無恤此生便也無子無女。待我百年之後,我會把趙氏還給兄長。」
喜得貴子……她終於給了他一個孩子。
我日漸憔悴消瘦,人人道是辛勞;他那裡頹廢枯萎,也只有我知道是心傷。
「明白什麼?」我心中劇痛,眼中淚水再盈。
「明白你吃『息子丸』的原因。」無恤蹙著眉,好似用盡了全身的力氣才說出了那三個字,「你不是因為誤會狄女懷了我的孩子才吃下『息子丸』來懲罰我,你是怕自己會成為第二個你娘,怕我將來也保護不了你,保護不了我們的孩子……」無恤的視線落在我的小腹上,他知道那裡已冰冷一片,再也無法孕育他心中那些溫馨美好的夢。
在姮雅疑惑的目光中,我捂著嘴衝出門去,在院中嘔得滿臉通紅。
匆匆又是半月,新絳入了仲夏,一輪熾日天天頂頭曬著,即使入了夜也依舊悶熱得叫人睡不著覺。這一夜,我脫了寢袍只留了一件細麻小衣躺在床上,手心、腳心一陣陣地發燙,坐起來看窗外,煙灰色的殘月已下了中天,夜風裡卻仍舊裹著暖暖的濕氣,一吹,叫人從頭到腳都黏糊糊的。
「巫士謙遜了。」太子鑿微微一笑,也沒再多說什麼,只回頭對於安道:「今日你且留下,陪卿相說說話,明日再入宮來見我。」
「祭禮之上吟著頌歌要怎麼說話?」我微笑回道。
「自然是去雲夢澤,明夷連馬車都雇好了。」
「我們好不好,你就別操心了。多關心關心自己的身子,夜裡搬回自己院里睡吧。」伯魯這一個半月衣不解帶地侍奉著趙鞅,人瘦了,臉黃了,面容比起他的父親更顯憔悴。
深更半夜裡燒柴堆,是嫌今夜還不夠熱嗎?
祭禮冗長,祭禮之後又被人拖著聊了許久,趙鞅此刻已虛脫卧床。
阿魚什麼時候走的我不知道,無恤輕輕抱住我時,我聽到了自己發顫的呼吸聲。
我望著奪目的火光、紛飛的火星,失神呆立。
這是那一日黎明無恤在我耳邊呢喃的話,一句話就將他畢生守護的東西拱手讓出,這天下沒有比這更甜蜜、更荒唐的謊言。權力、榮耀,世間父子相殺,兄弟相殘,男人www•hetubook.com.com們拚死爭的不就是那一點點血脈嗎?他沾了一身的血,才得了這個位置,怎麼捨得把一切讓給別人的兒子?可無恤卻說:「阿拾,除了你,這世上沒什麼是我捨不得的;除了趙氏的存亡,沒什麼是我放不下的。」
我有孕了!醫塵騙了我,他身為醫者,居然給我配了假藥!
這一路,我們聊著雲夢澤的雲霧,聊著楚國秋日的蘆花盪,很快就到了趙府門外。
伯魯一聽太子鑿要召我入宮,立馬就急了:「太子容稟,卿父——」
「你當初為什麼不看我給你寫的信?我早就告訴過你,今夜出生的不是我的大子,你無須替他流淚吟祝。」
太史府的神子在趙府住了一個半月,身染重疾的趙鞅已經可以參加太子主持的南郊祭禮了——街頭巷尾的傳聞一天一變,但只有這一條被人足足傳了半個多月。
「可那是你的嫡子,將來是要承你宗主之位的!」
我有孩子了。
「我就是這麼個老樣子,過段時間吃好睡好,就都好了。」伯魯說完,不爭氣地又悶咳了兩聲。
「你既這麼關心他,怎麼不自己去問?」伯魯放下捂嘴的帕子,轉頭往身後瞟了一眼。
伯魯停下腳步,沖無恤招了招手。無恤幾步走過來,沖伯魯頷首一禮,抬頭時墨玉般的眼睛瞬間就對上了我的眼睛。我心中一顫,倉皇低頭。
「你師父那裡……」
「唉,幸而紅雲兒不疑我,否則叫我如何自處?我只盼狄女這次真的能為紅雲兒生下一子,斷了那些人的妄念。阿拾,他是趙世子,成婚五年了,總該有個孩子。你可不能怨他。」
「紅雲兒,你有你的命運,我也有我的。落星湖一別,我們本就該分開,可我們卻非要強扭著命運纏在一起。如今纏得緊了要想再分開,總要連皮帶肉扯碎點兒什麼——」
暮春的庭院,桐花落盡,綠蔭濃重。自脫了春衣換了夏衣,天氣一日熱過一日,素紋鏡中的容顏也一日憔悴過一日。後悔嗎?那三個月里,其實無時無刻不是後悔的。
「不,是我讓你失望了,是我錯了,很久很久之前就錯了。」無恤起身跪在我面前,抬手捧住我的臉,「阿拾,我知道現在的一切都讓你覺得很糟糕,可我求你信我,這不會是永遠,一切痛苦都會過去。只要你我真心不變,我們的將來還會和當年想象的一樣美好。有你,有我,有家。」
「我們可以生三個孩子,四個太傷身了,我怕你會吃不消,三個就剛剛好……」
姮雅扶著門框看著我,亦滿臉漲紅。
「因為……不一樣了。」我哽咽,將臉深深地埋進自己的膝蓋。我已不可能成為一個母親,如何還有資格指責他成為一個父親?
「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伯魯揮退侍從和我並肩擠進了城門,「這一個半月你們在府中天天見面,可搭上的話總共也沒個十句。那天夜裡見你們在屋外頭碰頭說話,我還以為你們已經好了。」
好事之人裝了一籮筐的閑言碎語去找伯魯。伯魯亦不知道自己的兒子被無恤送去了哪裡,他只知道紅雲兒要做的事,就是他要全力支持的事。
「你要問我什麼?」無恤低沉喑啞的聲音一下撞進我心裏。
這麼熱的夜,睡不著就容易胡思亂想,胡思亂想了,就真的睡不著了。我起身到水瓮里打了一盆涼水擦了身子,剛重新躺下,就看到院子里亮起了一片火光。熱浪帶著煙塵一波波湧進原本就悶熱不堪的房間,我剛剛擦凈的後背,即刻又滲出了一層膩膩的汗珠。
「不是我找你https://m.hetubook.com.com,是子黯有話要問你。」伯魯笑著將我往身前一扯。
「讓無恤去吧,我走不開。」自那日竹林一別,我再也沒有見過史墨,見了也不知該如何與他相處。
姮雅需要一個兒子,她知道無恤也急需一個兒子。所以,她費盡心機生下了一個「尊貴」的嫡子。她是興奮的,或許她覺得這樣便能抓住無恤的心,便能將自己的族人與趙氏牢牢捆在一起。無論她心裏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始終相信她是深愛無恤的,只是,她也許從來就沒有真正看清過自己愛上的男人。
這一夜,無恤的話很多,我的話很少,依稀記得在我閉上眼睛的那一刻,緋紅色的天空已恢復了往日黎明的模樣。
我按著自己平坦的小腹,喜悅、恐懼、迷茫,一個人可以擁有的所有情緒似乎一下子全都湧進了心裏。它們交織著,纏繞著,繼而變成一片空白。
「雲夢澤呀,什麼都好,就是冬天多雨,住久了會悶。若兄長真悶了,我那間木屋東面的漆樹林里有種黑羽紅嘴的鳥,能作人聲,教什麼話,就說什麼話。你和明夷養個十隻,保准天天都跟逛市集一樣熱鬧。」
見禮后,太子鑿對我道:「巫士果真醫術精妙,絲毫不遜令師。如今,正卿痊癒,巫士打算何時再入宮為君父診治啊?」
「哈哈哈,好,我一定告訴他。」
「對不起」三個字,我在心裏說了無數遍。可無恤心裏的哭聲太響,他再也聽不見我心裏的聲音。
我瘋狂地點頭。
「哎呀,怎麼還真傷心了?快給阿兄笑一笑。」伯魯避開人群將我拉至街旁。
「無事。」我低頭看著自己的鞋尖。
「你做夢!南有樛木,葛藟縈之。這是成婚第二日你唱給我聽的歌。藤纏樹,樹纏藤,此生此世,我趙無恤與你至死方休!」
「息子丸」,兌卦女樂們最熟悉的葯,我吃了三個多月的「息子丸」,子嗣於我早已成空。可無恤的心裏還藏著一個美夢,夢想著有朝一日塵埃落定,我還能為他生兒育女。
「不是你的兒子?姮雅待你一片赤誠……怎麼會?」我愕然抬頭,無恤已坐在我身旁。
「應該的。」于安含笑道。
「我知道,但現在這個不重要。」無恤伸手擦去我掛在腮旁的淚水,「今日我看到智瑤看你的眼神了。」
「你是說宗親里又有人要推你做世子的事?」伯魯仁孝,趙鞅卧榻之時,他衣不解帶日夜隨侍在側。如今趙鞅病體未愈,他卻突然說要離開,我還以為是明夷強逼他去楚國養病,沒想到竟是為了有人要重推他做世子的事。
「智瑤?」我迷惑不解,他此時為何會提起智瑤?
薄施粉,淺描眉,染唇色,女婢手巧,一番巧妝之後,這位久病的老人看上去竟真的恢復了往日奕奕的神采。一個掌控晉國朝政幾十年的男人,一個駕長車、持利劍、叱吒風雲了幾十年的梟雄,在暮年來臨時,為了震懾蠢蠢欲動的敵人,為了守護自己的家族,竟將黛粉、紅膏也變成了手中的武器。
五年了,趙家的世子婦終於有了自己的孩子,也許有人覺得這寬額大鼻的孩子長得像一個人——一個隨姮雅從北方嫁來的狄族奴隸,可誰也不敢說,因為那奴隸已經死了半年,他墳頭的青草早已將他的存在抹去。
我趿鞋推開房門,一股灼人的熱氣帶著飛揚的火星撲面而來。
伯魯雖然覺得我和史墨有些奇怪,但依舊點了頭。
趙府上下只有我知道,趙周被無恤派人秘密送去了魯國,他將拜入孔門,奉端木賜、卜商為師,學習治國治家之道;而後,會被送往齊國,同高氏子弟一道研習劍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