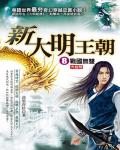第八章 英國來使
「陛下又有宏論了,不過禮儀關於大義,只怕眾臣未必能如陛下之願。倒是臣的梁國在何處,今日倒要向陛下問個清楚明白才是。」
「臣等亦請陛下封爵而不授土。」
「爾等不必如此,這兩個小兒年紀尚幼,有何福德承受大禮。雖然身分不同,卻也不必老是跪來跪去。再過上幾年,我必定廢了這跪拜之禮,凡軍民人等,均不許跪拜才是。」
在十七世紀,與謝高清所記錄的時代不過數十年間,其間英國的種種民用生活設施已經開始有了質的轉變。一慣野蠻和落後的蠻人漸漸恢復其祖先在古羅馬時的文明和榮光。而在此時的中國,種種愚昧落後的生活習俗卻漸漸深入民間,直到二十世紀,中國民間仍有洗澡影像傷元氣之說。而直至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大部分農村,還使用不了馬桶和自來水。
何斌接後方才明白,原本張偉因天下已定,除民爵外乃大封貴族。首封便是當年從他齊至臺灣,一共白手創業的何斌、施琅、陳永華、周全斌等人。他因功受封公爵,倒並不稀奇,奇就奇在封了他一個翼州做為封地,允准他收取賦稅,建立衛隊保護領土,這乃是中國千年來未有之事。
張偉先令各人站起,繼而向呂唯風問道:「唯風,你在呂宋時,最難為之事為何?」
「唯風,你受封侯爵,你之侯國便在西班牙人所謂棉蘭島之上,其島為呂宋離島,土人勢力甚強,漢軍駐軍不過數百,只有一州,三縣,漢人不過數千。你的侯國方圓數百里,可比六合一縣,只憑著當地官府,彈壓得住,保有得住的?我為你選的,乃是有著各種珍奇異產,山林魚產豐富的上佳好地,就這麼放給土人糟蹋?」
張偉聽得他吹牛,卻也懶得理會,卻只聽到法國與西政牙展開大戰的消息。自此之後,西班牙與葡萄牙越發衰落,早期殖民的力量消耗怠盡,成為歐洲的二流小國。
各人此時亦都看到,俱是奇怪,卻見他憋紅了臉,扭捏著答道:「前幾天在宮門處遇著理藩部的郎中吳應箕,他向臣道:諸公都是從龍勛舊,在陛下為布衣時便相隨左右,最受寵信。然則有利則有弊,因受信重,難免放浪形駭,常有違制越禮之處。時間久了,難免有禍。臣聽了之後,覺得很有道理,是以陛下雖然賜座,卻並不敢放肆坐實,緣故就在於此。」
「多謝太師閣下的關心,使團一切都好。出脫了船上貨物,我們很有盈餘,一切生活用具都很充足。貴國物資豐茂,百姓生活富足,環境優美怡人,生活在這裡,並沒有什麼不便之處。」
一時間,不但南京城內冠蓋雲集,欣喜若狂,全國各處,製服造冠者亦是甚多。中國古制,帝冠十二梁,王九、公七,侯伯下皆五,自授爵那日起,南京內外珠光寶氣,冠蓋輝煌,自張偉攻下南京後稱帝日起,此時方算是真正的有了新朝氣象。
與從龍勛舊的喜氣洋洋不同,前明降臣受爵者甚少,除了首降的鄭煊被封伯爵之外,其餘雖然可能位至閣部,地方巡撫,但是因其功勞不著,降附時間很短,並不能與臺灣勛舊相比。倒是前明降將,因投降後大多立下軍功,漢朝軍功比之文官政績強過許多,不但那些早降者有不少受爵者,就是吳三桂這樣的新降之人,亦因在朝鮮遼東有功,受封伯爵。
因都是從龍勛舊,立刻准見。眾人一路迤邐而行,隨著禁宮侍衛直至乾清宮內,卻見張偉膝下一左一右,一男一女兩個小娃兒正在嬉戲。
見何斌點頭應諾,張偉向他點頭笑道:「有一件事,本來是要過來親口和你說。既這麼著,你在府裡等消息就是。」
張偉橫他一眼,又向殿內諸人掃視一周,冷笑道:「漢高祖當年封爵時,諸臣私下議論紛紛,唯恐天子不公,對不住自己的功勞。不成想我新漢的諸公都是如此高風亮節,推讓不受,這真是讓朕喜歡死了!」
鄭煊乃是前明舊臣中投降最早,最得重用,亦是受封伯爵。此時一眾儒臣不敢公然與張偉唱對臺戲,亦不能攻擊何斌等臺灣系的重臣,只得將火力對準了鄭煊,每日攻訐不止。
「各國可依具體情形自立律法,然不得與中央法律相牴觸,各國除了田賦外,其餘各稅與中央依例分成,中央多而地方少;各國官員,亦編入中央體制,可與中央互調用。此確實中央權威,比之唐朝藩鎮,中央無財權、政權、軍權絕然不同。
「我國之內,凡有港口者,皆可通商。只是不論到何處卸貨,皆需交納關稅,貨物要由海關檢定,其餘不論。」
他退後一步,跪將下去,鄭重道:「臣請陛下收回成命,只封爵而不授土。」
因沉著臉向羅汝才喝道:「你要麼現在就滾將出去,再也不准陛見,要麼就給我坐實了!」
此時大殿內早有宮內尚功局的諸宮女雜役搬上座和-圖-書椅,張偉命各人坐下,正欲說話,突見羅汝才歪斜著屁股,只有三分之一坐在椅子上,扭來扭去好不難看。因奇道:「汝才,做這怪模樣是為什麼?」
張偉心中怒極,心道:「這些混帳和兩百年後的子孫倒是一點沒有區別,想的就是利用別國的好意和寬容將自己國家的利益最大化。這些早期的西方冒險者,均是蹬鼻子上臉,一點好臉子都不能給才是。」因冷冷答道:「英人行商,均需遵守吾國法律,犯罪者,雖公侯而不赦。傳教者,我已將在中國的教士成立主教聯席會議,在中國選舉大主教,署理教事。自此以後,凡入中國之教士,一律受中國教會的統管。其餘諸事,一概不准。」
他心中激動,卻並不敢表露半分,只又向張偉道:「雖然封藩可以鎮壓地方,亦可使臣等尊榮富貴。然則葉伯巨前言猶然在耳,臣等不敢因私廢公。請陛下多置官府,多設流官,數十年後,呂宋自安。」
他只管說的得意洋洋,卻不顧張何二人神色由愉悅轉為不悅。韋德爾等人看在眼裡,心中著急,禁不住都在心中大罵:「這個蠢才!人家不過是客氣一問,你倒是當真,若是惹翻了他們,把你拖出去塞在馬桶裡才好!」
他不敢再反抗,只得隨著眾人一起跪下,向著張偉一叩頭了事。待禮畢起身,卻聽張偉向何斌道:「英倫國王自成一國,豈有向朕行禮的道理。此類話,你下次不要說,亦不准人說。天朝雖是上邦,卻亦不能以大凌小,強壓別人。」
周、江二人追擊滿人已至黑龍江之北,聽得信息,均是感激之極,行軍打仗越發用心。而他二人屬下中,亦有不少受封為伯、子、男者,均是各有封地賞賜,全軍上下接令之時,當真是歡聲雷動,直入雲霄。與此兩衛相同,在草原剿擊蒙古的劉國軒與孔有德,駐防北京的張鼐,深入甘寧的張瑞與契力何必諸人,或前或後均是收到恩旨,各封侯伯,領受封地。
待這些使團先行回國,面稟國王之際,那查理一世卻甚是鬱悶,向他們道:「既然這中國如此強大,擁有這麼多的戰艦,那麼遼闊的領土,運轉高效的政府,卻為什麼不在海外佔有殖民地,奪取金銀?嘿,還說他會英文,這必定是你們沒有到達,胡編了來騙我。」
他咂咂嘴,搖頭道:「我雖是商人,亦知道天下事不可以論語治之。偏這些老先生們,枉讀了一肚皮的文章,卻只是食古不化。三王之治都是好的,人心不古,道德淪喪,聽起來好生令人惱火,卻只是拿他們沒有辦法就是了。」
見陳永華一陣愕然,他又笑道:「復甫兄莫要小瞧了它。其土地膏潤肥沃,上有銅礦。除了不能鑄錢,你鑄成銅器出賣,每年要賺多少?」
「國王陛下身體安康,一切均好。」
亂了幾日後,見張偉全無動靜,亦無解釋,何斌等人按捺不住,當即彙集在京諸受爵的大臣,一同進宮求見。
「封國不得在內陸,封地止在海外。在海外為官時,不得臨其國。在中央為官者,亦不可臨其國。待咱們子孫輩時,勢必在朝,在地方時,由公侯國組成會議,決斷地方大事。凡地方稅務、法律、軍務,均由公侯會議決斷而行。如此,可以集思廣議,可以由地方總督、巡撫監視公侯,亦可由公侯會議防備督、撫權勢過大,或是為害地方。」
張偉一番話說將下來,乾清殿內立時氣溫升高。一眾老夥計和伴當們自然不會將心中所思完全浮現在臉上,不過皇帝如此仗義念舊,分封給諸人這麼大的土地,這可無論如何都讓眾人感動不已。
何斌原本就是家資萬貫,前些年為政府墊付的銀錢已多半交還,而臺灣多半的工石礦山都有他的股分,日進斗金已不足形容其富。他又有船隊奔行海上,是以世間無論是何珍奇之物,只要他何太師想要,自然沒有得不到的。他的官位又是太師、閣部大臣,位極人臣之首,無法再有寸進。到得此時,一頂公爵的帽子又落在他頭上,看陳永華的封地如此,料想自己的更勝過他。財富什麼的,倒也罷了,只是以他一個閩省走私商人,成為一個新朝公爵,將來包茅封圭,建宗立廟,追祀祖先,如此榮耀之事,卻又是比發財難得得很了。
張偉雖然心中不悅,卻知道此人所言是實。倫敦雖然此時仍然是石頭城一個,比之中國城市的富麗繁華相差甚遠。直到十八世紀,有中國人至英國時,還是說此城死氣沉沉,沒有活力。然而據十八世紀中國商人謝清高的記錄,英國所有的城市系統都有自來水設施。
封建制度雖然歷朝都有,卻都是錫封而率土,明朝諸王很是尊榮,百官不得抗禮,卻亦是有兵而無名,不得干預政治。張偉此封,除了受封的各國不設正式的政府外,卻是與當真周朝的封建制度一般無二了。而這翼州乃是古和圖書稱,國在何處亦是不得而知,卻當真是讓漢朝新任公爵大人一頭霧水。
張偉卻不管他如何在肚裡暗罵,悠閒捧起蓋碗,向他問道:「爾國國王可好?」
「高傑為什麼還沒有動靜,這該死的狗東西!」
聽得張偉迅問,他便傲然答道:「自有《大憲章》後,吾國貴族對國王的權力開始有了約束。權力有了約束,將國王關入籠子之內,乃是英國獨一無二的成就,亦是對人類民主進程的最大貢獻!」
也不理會諸人詫異,張偉站起身來,向何斌道:「使團之事,交由理藩部的寧完我處置,讓他好生接待,與人家簽定正式條約之後,咱們也派遣使團往英國,記得讓他大辦,派軍艦和大船過去,讓洋鬼子見識一下天朝上邦的禮儀規制。」
何斌見他默然不語,一時間房內冷場,便湊上來問道:「尊使一路過來,在中國生活可習慣麼,有何不妥或是需著什麼東西,盡可開口。」
一眾功臣受封之後,倒也並無別話。然則朝議紛然,所有的儒臣皆是群情激憤,以為張偉恢復舊制,錫土分茅,必為後世致亂之由。
而在明朝末年,在中國強大之時,皇宮內院都經常有外國人行走傳教,天啟帝就差點兒成為教徒。各國的傳教士拜見中國官員亦是有下跪者,更別提見皇帝了。一眾英人一聽得帝國皇帝駕臨,早已是心慌意亂,被何斌一喝,也不等正使吩咐,自副使斯當東爵士以下,各人立時亂七八糟跪了一地。
這些事原是英國內政,韋德爾卻不曾料想張偉亦是知曉。他是下層貴族,對王室的橫徵暴斂極是反感,此次雖然被英王任用,卻並不能使他在政治上改變立場。
「以法輪激水上行,以大錫管接注通流,藏於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以,俱無煩挑運。以各小銅管接於道旁錫管,藏於牆間,別用小法輪激之,使注於器。」
南京夏日酷熱,冬季卻亦是陰冷濕寒,眾英人自外面冰呵呵進來,此時房內有鎏金銅爐燃炭取暖,其中埋以寸香,房內馨香溫潤,各人只覺得一股異香和著暖氣在臉上身上浮動,當真是舒服異常。待看到房內檀木桌椅,四面閣窗木架上皆是精奇珍玩古董,當中條案上供奉一面玉佛,其側放置著一枚黃玉如意,都是上好玉質,所價不菲。一眾英人看得眼花撩亂,也顧不上佛像是偶像崇拜,褻瀆天主,只想著抱將下來,好生把玩。
呂唯風不知他意,因掂掇半晌,方答道:「為難之事甚多,難則最難者,在於土人刁頑,平素目無法紀,嘯聚為盜。大軍一至,則星散而逃。現下呂宋漢人不過二十餘萬,且多半居住在衝要城池中,土人人數約莫兩百餘萬,雖然定居耕作的已服王化,學漢語,寫漢軍,衣冠髮飾漸從漢人,然則居於草野水澤的土蠻野人最是難治。官府諸多繁雜事物,甚難將全力用於剿平匪亂。此事,為呂宋治平最難矣。」
何斌見他生氣,忙上前圓場道:「吳、呂諸公都是為了陛下身後千百年計,陛下不可縱性使氣,涼了眾人的心才好。」
也不理會羅汝才苦著臉又坐將進去,自己只管侃侃而言,將封授海外土地的利弊一一向諸人解說,只說了半個時辰,方才解說清楚。
張偉仍欲斥責,卻見何楷從容上前,奏答道:「陛下,趨福避禍,此人之常情也。若是有人反亂,或是不利於陛下,臣等身為虀粉,亦不敢稍退半步。而現今是太平時節,臣等憂懼清議,一則愛護己身,二則為陛下弭謗,陛下又何怒之有呢?」
自陳永華以下,各勛臣皆欲在向張偉行禮後再向這兩個小兒行禮。張偉雖然錫封,眾人卻都覺得一者是長公主,一者是皇太子,此事不必張偉宣示天下,已然是定論無疑。
張偉吹開浮在上面的茶葉,突然向那韋德爾問道:「聽說貴國的上層王公和貴族對國王並不心服,前次與荷蘭交戰,因要加稅一事,貴族與國王鬧了生分,直鬧騰了大半年,可有這事?」
此時的英國國王查理一世便是第一位登上斷頭臺的英國國王。他在位期間,曾經多次因徵稅與議會產生衝突。而就在他派出船隊往中國的這一年,英國議會通過法案,取消了國王的終身徵稅權,每次徵稅,便需議會同意方可施行。查理一世本欲解散議會,卻因與荷蘭的戰爭迫在眉睫,只得暫且隱忍,先將錢拿到手再說。
見查理一世仍是若信不信模樣,韋德爾等人不禁齊聲道:「陛下,之前的原因我們並不知道,不過,依我們的觀察,這個東方巨龍出來搶奪殖民地,爭取利益空間的時間,已經到了!」
「公侯諸國可以建立軍隊,然公國不過三千,侯國不過兩千,伯子男只一千,若中央下令,則各國需將軍隊交由各處總督將軍指揮,而平時敉平叛亂,各國亦可向中央求救。強幹弱枝,永為垂制,則不必擔心各國禍亂中央。
這兩人雖然位分並不和_圖_書如吳遂仲等人為內閣大臣一般高高在上,其實在張偉心中,兩人以明朝舉人進士的身分在早期投臺效命,其實遠較吳遂仲等人更受信重。此時雖然話語之中並不客氣,倒也使得他怒氣全消。
因笑道:「兩個老夫子說話,罷了。爾等全部起來,待我講說。」
張偉點頭答道:「這個我自然省得,你放心,我有手段治得這些腐儒。」
見張偉低頭沉思,何斌失笑道:「自朱洪武以八股取士,天下讀者人只管按章讀經,哪管文章出處,把別的都看得輕了。你現下重提六藝,宣揚西學,讀書人都說是百般退讓了,萬萬不可再打什麼主意,使得天下騷然。」
卻聽得使團人有人道:「只是貴國居民早上倒馬桶時,臭味實在太大。成百上千的人從家中出來,將馬桶放在路邊,等著糞夫來收取……倫敦自從在伊莉莎白時代有了沖水馬桶,就已經沒有這種景象了。還有,貴國用水都是水夫挑來,一路上風塵雜物甚多,不很乾淨。而在倫敦,已經全數使用了銅管的自來水管,一扭就開,清水自水管中放出,又方便,又乾淨。」
張偉聽完,只覺哭笑不得。明清之際,任何親貴大臣,在皇帝面前都只能跪,而不能站,尊榮之人,或許有軟墊墊膝罷了。他不但不令人跪著回話,反而恢復前制,大臣與皇帝長時間談話,都有座位。舊明大臣當慣了奴才,跪著習慣,此時屁股下有了座椅,反而萬分的不習慣,甚至有人很是不滿,覺得皇帝不像皇帝,大臣不像大臣,有逾禮制。張偉每常看到那些大臣斜簽著屁股坐在椅子邊上,就會想起阿Q的那句:跪慣了,還是跪著的好。明朝之際,人的思想僵化與奴性之重,當真是令他匪夷所思,難以理解。
何張二人正在得意,江南之繁華富裕,日常物資之充足,街道路面之齊整乾淨,道路之寬敞堅實,這都是他們治下的功勞。
何斌也不理會,只向他笑道:「又有什麼新奇物事?這麼些年,我早習慣,倒是那幫子前明儒臣,聒噪得委實教人難受。志華,前幾日陳復甫來尋我,說是他現下不理官學的事,不過也知道官學內教導國學的趾高氣揚,很不成話。學生們還是重經書,不重西學。這股風不扭過來,想得人才難矣。」
此次大封功臣動靜甚大,凡新朝建立,所有上下的功臣勛舊無一不盼望此事。與諸人期望有所不同的是,不但新朝有明朝公侯伯沒有的子爵與男爵等諸多新爵之外,所有的爵位與春秋時相同,皆是授土分茅。
想到此處,張偉未免有些興致索然。因向一眾使者們道:「十年之後,中國亦是如英國一般行事。至於其餘,則遠強於英國矣。」
呂唯風原是世家子弟,然則家境早已破落,這些年來投效張偉,一直奔波勞祿,俸祿雖高,卻仍不足恢復其祖上家業榮光。此時聽得有可堪比擬內地一縣的如斯上好美地,只需用心加以經營,別說恢復原產,只怕原有的明朝藩王,亦是不如。
他大踏幾步,至得何斌身前,向他道:「廷斌兄初見我時,我正立身於海水之中,四顧無人,幸得鄭老大和廷斌兄打救。後來又與我一同奔赴臺灣,在一塊荒地上做出好大一番事業。廷斌兄為太師,為翼公,都是當之無愧!」
若不是張偉的努力,此次英國使團來訪,看到的必定是街道上擁擠混亂,充斥著小腳和驢馬糞便的中國城市,道路不修,一遇雨水便是滿地泥湯。人民以驢車牛車代步,以流傳兩千年的獨輪小車推運物品,而更過不了多久,連衣冠和髮型亦是改變,拖著豬尾巴和戴著瓜皮小帽,抽著鴉片的中國人,在西方的眼中,所有的輝煌和形象俱是萬劫不復。
又問道:「英荷戰事之外,歐洲各國的混戰如何了?」
張偉哈哈大笑,揮手命保姆將子女帶下去,然後方向陳永華答道:「復甫兄,其實我這幾天,只是在等眾人說話耳。既然話說得差不多了,自然無需再打啞謎。梁國之封,便是呂宋的安南城左近,方圓百里!」
當下各人也不打話,由何斌領頭,眾人一起跪定,向張偉道:「臣等叩謝陛下深恩!」
說畢,他飲茶解渴,向陳永華道:「復甫兄,你說說,雖然或許會有勛爵之後反亂的事,不過是否利大於弊?」
比如施琅,乃是武臣第一,除何斌外就屬他隨張偉時間最長。是以他的封地與何斌類同,皆是呂宋最為膏潤之地,出產甚多。此人一向懼內,又不善經營,家產不足何斌的百分之一,他現下駐節福州,甫一接到恩旨,全家上下皆是感奮之極。因施琅官身在身,現下不能親臨封地,於是立刻由其弟帶著家人先去探勘,待落實地界之後,便可先鑄城募兵,招募無地佃農前往耕作。
陳永華沉吟道:「不錯。依陛下所言,漢晉之際以土地為力量,掌握人中,修繕甲兵,煮鹽鑄錢,力量過大中央難制。而https://m•hetubook•com.com現今,以憲法為制,中央又有絕對的力量,各公侯國除了有衛隊外,不得私設官府、鑄私錢,而且土地為常例,不准兼併。呂宋雖在海外,四十天內消息便可傳到京師,有敢違制者削地剝爵,又可以令各公侯國鎮壓土人,擴大我天朝實力,利大於弊矣。現下又都以火器成軍,所耗甚大,且又力量極強,海上水師亦非任何一公侯國能置者,國家亦不許。如此,凡有叛亂者無可以對抗中央,又有何患?
他想到歐洲在近期內無力顧及其他,所有的力量都用在這後世史稱的「三十年戰爭」之上,在此時兵向南洋,拿下麻六甲、爪哇、滿刺加等處,待歐洲人回過頭來,只怕整個東南亞早已落入漢朝手中了。此前張偉已將水師南調,至臺南、臺北、福州、廣州等港口停泊暫歇。除此之外,早有一支分艦隊在呂宋待命,準備隨時依著南洋局勢變化而發兵。
張偉聽得諸人議論紛紛,知道一者是自己的這些打算確實有理,使得這些跟隨自己多年,腦子並不僵化的重臣們心悅臣服,二來也是重利所在,各人原本就是半推半就,害怕人言耳。此時有了反駁理由,自然個個氣壯如牛,樂意受命了。
「那麼是否可以劃出某地,讓我國駐兵,建造炮壘,保護私產僑民?再有,是否允准英人入內陸自行居住,允許傳教?這些都是吾國國王鄭重交代,希望大皇帝允准。」
見眾人面露豔羨之色,張偉又向各人道:「大夥兒都是在臺灣隨著我打江山來的,現下我成了天子,難道能薄待諸位不成?各人的封地,都各有出產,決計不是無用的荒涼野地!」
何斌老臉微紅,向張偉應諾一聲,便也罷了。韋德爾聽通事翻譯完畢,心中一陣感動,心道:「這位皇帝陛下到比國王陛下好說話得多,一會兒談判起來,卻要好生試探一下。」
何斌心中歉然,忙向張偉道:「志華,你難得有幾天天倫之樂,倒是我們來得孟浪。我原說你怎麼一點消息也沒有,卻原來是在膝下弄子。」
自施琅而下,周全斌、江文瑨等人則受封侯爵,封地略小,出產卻亦是很多。各人都是平常人家出身,得了偌大封地,其中各有特產,只需用心經營,均是百萬數十萬金的收入,一下子富貴至此,人生已是無憾。況且封地之上,除了需遵守中央法度外,各公侯就是國主,比之明朝的虛爵又強過許多。
「不然!這世間利字當前,生死大事尚且不顧,哪裡就能忠忱至此?我自起事日起,就曾有言在先,我張偉用人,一定要使人富貴尊榮,是以這麼些年,從未虧待過諸臣工。今日如此,他們或許有些為後世計的想法,但多半,還是憂讒畏譏,害怕眾臣議論,將來吏筆如勾也罷了,倒是眼前亂蜂蟄頭,很是難過。」
他止住各人的話頭,微笑道:「就這麼著,公國方千里,約等內地一府,侯、伯約等內地一縣,子、男、國士,約等內地數鎮。如廷斌兄的翼國,方圓過千里,已有人口過萬,內有金、銅數礦,還有山林、漁場,弄好了,每年可以白銀過百萬。廷斌兄,你現在諸多公務纏身,你的長子現下不過十歲出頭,不能當家理事。不妨派遣心腹之人,由你設府立縣,派駐官員,編入中央官制,招撫流民赴呂宋為你墾荒。如何料理,想來你必會辦得妥妥貼貼,要不了多久,我大漢子民必可充滿南洋等諸處,南洋諸處,亦必定成為我大漢的囊中之物。」
待英國使團將國書遞上,張偉雙手接過,因見使團上下做出如臨大賓,正式談判的模樣,張偉因失笑道:「我來此地,原是因許久不在南京,來尋太師閒話家常。爾等不必如此,通商一事,我自然是准的。至於細節,自有內閣政府負責,我們只管閒談就是。」
韋德爾一面觀察著房內陳設,看到几案上有一十幾磅重的金蛤蟆,上鑲寶石,直看得嘴裡恨不得流出口水來,聽得張偉說起此時只是閒談,卻又凜然惦記起正事,因屁股一抬,向張偉道:「皇帝陛下,未知貴國願意劃出多少港口用做通商?」
韋德爾臉上一陣尷尬,卻只得閉口不語。他心中只是納悶,卻怎麼也想不通,這個幾千年的古國,在以前的資料中的對外關係要麼是頤指氣使,只顧面子;要麼是大而化之,賞賜蠻夷,卻不想如今這個皇帝在禮節上倒是容忍許多,然而在利益上卻又寸步不讓了。
說罷,向房內諸人略一點頭,便起身離去。何斌出門送他,韋德爾等一眾英人直待靴聲漸遠,聽聞不見,方才敢重新坐下。此後何斌與他們虛與委蛇,好生款待一番。然後交由理藩部尚書寧完我接將過去,細談條約,商訂通商事宜,卻也不必細述。
「自然是英法聯盟這一邊。自擊敗西班牙與荷蘭後,英國的海上實力成為歐洲第一,無有敵手。而法國的國力在紅衣主教黎塞留的治理下,亦是蒸蒸日上,和_圖_書擁有著歐洲最強大的陸軍。我們聯手而戰,哪有不勝的道理?」
張偉見他神色如此,心中頗是納悶,卻因為人家說的是事實,在中國皇權日重,除了帝王都是奴才的時候,人家不但在軍事與經濟上不斷發展,待後來,政治體制與科技文化亦趕超中國,中國自領先世界的領頭羊位置上跌落下來,讓位給了英國。
「由都察院派駐監國御史,可以隨時監視彈劾不法,無懼於後世子孫胡做非為,此亦甚妙。
想到家鄉的鄉鄰父老必定交口稱頌,而老父雖亡,老母卻在,到時候必定喜不自勝。他心中歡喜,卻收斂起嘴角的一抹笑容,向張偉道:「陛下,說臣功高,賜爵封地,臣不敢辭。不過,自西漢七國之亂,晉有八王之亂後,封建之事再未行之。明太祖雖然封藩諸王以為屏衛,卻亦不能裂土而授。臣雖然一定忠於漢朝,卻不敢保後世子孫不貪圖富貴行不軌之事,且封授海外,兼併之事中央或難制止,若是到時候獨立於漢朝之外,爭鬥不止,豈不是負了陛下的深恩厚德?」
這禮儀之爭,在明末清初時還不是大問題,一直到馬戛爾尼時到達高峰。英使堅持不跪,中方官員堅持必須下跪。最後雙方折衷,英使一跪後,改以九次鞠躬,以示敬意。到了清末,中國越發愚昧落後,此時禮節問題已是小事,而以皇帝之尊會見蠻夷,接受國書,已經成了不可想像之事。二次鴉片戰爭,很大的原因便是因為咸豐皇帝覺得外國使者見京是對大清帝國的侮辱,而以皇帝之尊會見洋夷,更是莫大的恥辱。華夏文明發展到那時,已是與非洲土著無異,而清朝諸帝與其先祖順治帝稱湯若望為「瑪法」之比較,更簡直是天差地遠了。
陳永華亦道:「陛下自處死巡城御史事後,每常自悔,不肯輕易罪責大臣,亦絕然不肯以言罪人。民間報紙清議如潮,臣等亦是讀書人出身,擔心身後罵名,是以不肯受封,此亦人情之常,何謂反常?」
他用目光掃向吳遂仲、呂唯風、羅汝才等人,逼問他們道:「子女衣食人所愛之,反常即妖!爾等不欲受爵錫土,難道要我這個位子麼?」
在張偉親赴何府過後三日,由內閣首輔吳遂仲親捧詔書,至得何府,宣讀詔旨:
韋德爾滿心不情願,覺得雙膝跪下太過屈辱,況且何斌話語中有國王亦當下跪之語,甚辱國體。只是當此之時,何斌斥責不說,看到張偉微笑端坐於前,卻亦令他感覺到無與倫比的壓力。
韋德爾大是佩服,忙道:「陛下對歐洲局勢如此清楚,真是令人佩服。嗯,就在年初,法國國王路易十三正式向奧地利和西班牙兩國宣戰。支持法國的有英國、荷蘭、俄國、威尼斯、匈牙利等國。」
見他還要說話,張偉又道:「細節諸事,需與專署衙門商討決定,然後簽訂條約,自此以後,成為兩國交往根本。」
「昔君天下者,必建屏翰。然居位受福,國於一方,並簡在帝心。太師何斌,今命爾為公爵,永鎮翼國,豈易事哉?朕起布衣,與群雄並驅,艱苦百端,志在奉天地,享神祇。張皇師旅,伐罪吊民,時刻弗怠,以成大業。今爾有國,當格敬守禮,祀其宗社山川,謹兵衛,恤下民,必盡其道。體朕訓言,尚其慎之。」
「依你看來,哪邊能得勝?」
此類話最是敏感不過,饒是吳遂仲等人乃是自臺灣相隨的重臣,亦是抵受不住。各人連忙跪定,向張偉泣道:「陛下此言,臣等不敢受。若是陛下相疑,賜臣等死就是。」
何斌見那韋德爾仍然呆立不跪,詫道:「怎地?你為何不行禮?」
於是原本就一直攻訐分封制度不妥的前舊眾臣雖不敢當面反對,卻是唆使門生故舊,或是直言上書,或是在報紙是議論攻擊,將自西周、兩漢、西晉,乃至明朝的分封弊端一股腦端將出來,長篇大論的奏報上去,言語間雖是恭謹,卻又將明太祖處死葉伯巨的舊例提將出來。言下之意,張偉拒不納諫,必蹈明太祖當年分封之覆轍。
還在北伐之前,張偉已經派了高傑往南洋運動,誰料直至現在,仍然是個不成,南洋爪哇島上風平浪靜,巴達維亞一切運轉正常,每常想起來,當真是氣得轉筋。
他口說喜歡,其實臉色已冷將下來。殿內的諸臣都隨他已久,除了何斌等寥寥諸人之外,各人都是被他看得膽顫心驚,唯恐皇帝這股怒火落在自己身上。
無論真心或是假意,各人均立時隨同何斌跪下,一起向張偉同聲道:「若為子孫後代計,中央集權之制最為妥當。」
張偉高興得臉上放光,右手在脣下新留的兩撇小鬍了上摸了一把,爾後將胳膊虛抬,向眾人道:「不必如此,咱們都是從布衣一起打滾出來的,我有今日諸位都是首功之人,又何必如此生分。」
韋德爾當即翻翻白眼,向國王道:「國書與印信俱實,中國的使團隨後便會趕到,到時候真偽分明,陛下自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