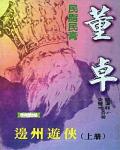第七章 中原煙塵
1.關東群雄興兵來
鄭泰這一番話,剖析深刻,於山東義軍也好,於董卓也罷,可謂切中要害。當然,他的本意是說服董卓不要進擊山東義軍,以免勞師動眾,大喪國本。董卓聽了這些褒獎讚美之詞,也十分得意,立刻轉怒為喜。再加上眾人七嘴八舌一番附議,董卓便決定暫不議論發兵征討關東之事。
轉眼就是年暮。聽從文士的建議,董卓讓獻帝下詔廢除光嘉、昭寧、永漢三個年號,復稱中平六年。
韓馥話音剛落地,治中從事劉子惠挺身作答道:「今興兵為國,何論袁董!」經他一提醒,韓馥不由滿面慚色。劉子惠接著又說:「然兵者、凶事,不可為首,先打探消息,看看它州動靜。冀州兵多人眾,不怕落後,一旦起事,別州搶不了冀州的功勞。」韓馥見劉子惠說得頭頭是道,當即依允,派人打聽各州情況,見反董勢正旺,便致書袁紹,細數董卓的罪惡,並表示要響應他的起事之舉。袁紹得到頂頭上司的贊同,氣也粗了,膽也壯了,把原先的暗中活動公開化,派遣使者四出聯絡,游說同好,相約共同舉義。橋瑁、韓馥自然如約而行。袁紹的從弟、後將軍袁術此時也已潛歸南陰,收到冀州來信,自然樂於從命,便說動南陽太守袁遺一道署名回信。還有孔伷、劉岱、張邈、張超、王匡等地方牧守,均復書袁紹,願同時興兵除暴。
此刻的董卓又怎能不得意呢。
再說驍騎校尉曹操,行刺董卓不成,當夜冒雪潛逃出京,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路過中牟時,正遇亭長沿路巡邏,見曹操帶刀夜行,疑為匪類,便把他攔住,盤問姓名,曹操支支吾吾,不肯如實道出,亭長不由疑上加疑,立即命隸卒拿下,執送縣中,此時,董卓捕拿曹操的移書已行至中牟縣,曹操自料必死無疑。縣廨有一功曹,曾與曹操見過一面,認定他是天下英雄,便向縣令代為求情。縣令處在動亂前夕,也想留條退路,便放了曹操。曹操逃歸陳留,散家財,募義兵,為討董卓作準備,當地孝謙衛茲,也出資幫助他,不過數月,曹操集合起五千兵眾,一聞袁紹起事,立即率兵前往會合。
「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凶,禍加至尊,虐流百姓,百姓哀號,四海瘡痍。今有渤海太守袁紹等,糾合義兵,共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神靈,實共鑒之!」
董卓把本次會議主旨宣說一番,百官皆默然不語,董卓很不高興。忽聽百官中傳出一聲喝語:「夫為政在德,不在燿兵。」董卓一聽是唱反調的,便怒目注視,發言者https://www•hetubook•com•com是尚書鄭泰。董卓厲聲斥問道:「如卿所言,兵為無用之物耶?」
這時的冀州牧是韓馥,他是由董卓推舉擔任這個職位的。到任數月,探得渤海太守袁紹日夕募兵,意有所圖,韓馥心想,渤海隸屬冀州,是自己屬下,應派遣部從加以監督,使袁紹不得妄動,方報董卓的知遇之恩。正要發文接到橋瑁傳來的移文,展閱數遍,狐疑滿腹,何去何從,難下決斷,便召問諸從事道:「方今之世是助袁氏呢?還是助董氏?」
到了此刻,弘農王自知難免一死,便拉住唐姬的手,涕泣作歌以志永訣:「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難延,誓將去汝兮適幽玄!」歌罷,又命唐姬起舞。那唐姬一身縞素,面如梨花春雨,眼似柳煙含蹙,淚如湧泉,且舞且泣,且泣且歌:「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煢獨兮心中哀!」
得到弘農王已死的報告,董卓覺得心頭除去一塊石頭,一下子輕鬆不少,褒獎李儒數語後,便召集百官臣僚速至相府會議,議論發兵征討關東各路人馬之事。
「李將軍乃董相國手下的大紅人,因何造訪寒邸?」李儒到來之前,劉辯正在與王妃唐姬吟詩彈琴,見李儒突然到來,兩人都吃了一驚。然而,今日的劉辯已不是北邙陂下被董卓嚇得發抖的少年天子,幾個月來,腥風血雨和幽居生活,已使他的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自從被董卓拉下皇位,他已不再懼怕那位跋扈將軍,他覺得,恐懼總是與有所求相聯繫。人們想求得財產、名譽、地位,怕丟掉這一切,才會恐懼。他已沒有什麼可丟,也無所求,所以,不用再懼怕了。雖然他還有生命,可是對失去皇位的天子來說生命又值多少錢?於是他又昂起高貴的頭顱,就像在皇宮裡召見廷臣一樣,冷峻而語中帶刺地話問李儒。
各人官職已定,便傳檄告示天下。於是,一紙紙慷慨激昂、怒斥董卓罪惡的檄書便從酸棗飛向全國各地。長沙太守孫堅,承檄起兵,襲殺荊州刺史王睿,直指南陽。前西園假司馬張楊,回籍募兵,道徑上黨,接得檄書,立即集合兵卒千餘人,前往河內報到。一時間,英雄聞風而至,豪傑應聲而集,先後共有十四路人馬。會集在酸棗城內外。但見金鼓振振,旌旗獵獵,聲勢浩大的討董義兵就要開赴洛陽城下,與董卓決一死戰了。
「相國大人,執金吾衙門收到一封緊急文書,請過目。」說話間,跪在董卓面前的府椽把一封加蓋火漆的文書遞給他。
「相爺莫為一紙空文發怒,傳言是否屬
https://www.hetubook.com.com實,還需先行打探再說。」眾人你一言,我一語,總算把董卓的怒火壓下來。當即傳令,派幹吏速往各處打探消息。
打開那份檄書時,董卓驚憤交加,再一看檄書後所附的名字,心裡便有點作慌,怎麼一下子就冒出這麼多反賊來,這太平酒還怎麼喝?一氣便把酒案掀翻:「入娘賊,咱老子一向待爾等不薄,荐舉爾等牧守一方,爾等不思回報,竟要取孤的身家性命,可惡!可惡!」
一年前的今天,他尚在關中莽原上披著鐵甲,飽灌著勁厲的西北風;那時節,他上面不知壓著多少人;眼下的光景是何等榮耀:端坐華堂之上,玉帶蟒袍,笑看歌兒舞|女,金盤玉箸,細啜御封美酒。壓在他上面的人,不是被拋在腳下,就是死了;這一年間,他真可謂翻天覆地,不僅有了富可敵國的財寶,而且有了威震天下的權勢,皇袍加身亦不過是俯拾之間的事。……想想一年來的巨變,怎不令董卓狂喜萬分。
董卓的酒量極好,座中人已醉倒了六成,不少將軍伏在案上發出此起彼伏的鼾聲,他還在與幾位酒量相當的老兄弟劃拳行令,飛觥傳盞。此刻,董卓雖已有八成酒意,可頭腦不糊塗,他之所以不令散席,因為他在等待一個「助興節目」。今日是他秉執朝政以來的第一個新正之日,也是檢驗百官、部下以及外地官守對他態度的一個時刻。眼下,百官已悉數前來朝賀,忠心的部屬們正與他飲酒同樂,只有那些為官一方的牧守們還沒有一點表示。按理說,朝廷改換年號,又值新正之喜,各地牧守早該上書上表,以示祝賀,況且,這是我董卓以相國名義攝政的第一個新年,這幫東西怎麼如此無知無識!送不送禮物權作別論,效忠輸誠的客套話總該說幾句吧?遲遲不見反應,難道對老夫執政心懷不滿?想到這裡,他心裡略生幾許不快之意。
「相國有令,酒為專獻,何得相代?」李儒一把奪下唐姬手中的酒壺,重新放在劉辯面前。
「新春佳節,相國念王爺孤居冷寂,特差小將獻春酒一壺,為王爺上壽。」望著弘農王清瘦哀戚的面龐,李儒動了一點惻隱之心,然而一想到董卓的命令,便趕忙把鴆酒捧至弘農王面前:「請飲此酒,可免災袪惡!」
董卓一面撕去火封,一面想,不知是那位「乖孩子」來搶頭功了。可是他一打開這封文書,臉一下子拉長了。這那是什麼效忠信,分明是一紙討董檄文:
董卓按下火爆脾氣,坐下來仔細研究檄文。檄文裡提到的第一大罪狀,便是擅廢少帝,且號召天下軍民,誅除元凶,復大寶於至尊。這不是明擺著不和*圖*書承認自己擁立的獻帝嗎?好傢伙,他們居然也想打起少帝的這面旗幟來號令天下,要另立山頭。董卓知道這是一著狠棋,天下人對自己廢長立幼極為不滿,假如被廢的少帝落入袁紹之手,重登大寶,自己不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反賊?這少帝雖然已被廢為弘農王,趕出皇宮,但仍留居在京城王府之中,不滅此人,終是後患。事至今日,不如斬草除根,殺了弘農王,從根上斷絕袁紹的胡思亂想。主意一定,董卓令人傳來郎中令李儒。這李儒投奔董卓帳下的時間雖然要比郭汜、李傕、牛輔等人短得多,但為人機警,果斷,而且心狠手辣,執行命令從不打折扣,深得董卓信賴。
前騎尉鮑信,奉何進之命往泰山募兵,回來時,何進已喪命。鮑信見董卓擁強兵佔據洛陽,便帶領招募來的士兵返回泰山故里。鮑信返家後,眼見天下將亂,不但沒有遣散士兵,又招了萬餘名,合得步兵二萬,騎兵七百,輜重五千餘乘,與弟鮑韜督練成軍,往援各州反董義師。
就在這時,從大堂外面跑進一個府椽來,眾人正飲至酒酣,沒注意那府椽,而董卓一直在盼望外地牧守的消息,因此,那府椽剛上堂,他就看見了。
李儒見弘農王道出自己的心機,索性撕下臉皮,硬逼劉辯自己取飲鴆酒。可是弘農王皺著眉頭執意不肯。時間一點點過去了,兩人在僵持著。李儒十分焦急。弘農王凄絕失神的眼睛使他惻隱之心不止一次冒上來,他畢竟是個十五歲的孩子,他有什麼罪過?他和我李儒有何仇隙?非得殺死他不可?咳,李儒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一想到臨行前董卓的叮囑,李儒不得不收起那尚未泯滅的一絲善心,他安慰自己:即使我李儒不殺弘農王,他也難逃一死,肯定會有王儒,趙儒之類的殺手來完成這個任務。還是讓他快點結束,少受痛苦,於己於人都是方便。於是他怒睜雙眼,大喝道:「董相國有令,焉得不從,速飲此酒!」此刻在旁哭成一團的唐姬,突然止住淚,一把搶過酒壺,對李儒哀求道:「賤妾不幸,願代王飲之。」
袁紹接到各地響應書後,立即引軍前往河內,與郡守王匡會合,韓馥留駐鄴城,督運軍糧,袁術屯守魯陽,其餘各軍屯集酸棗。各路首領選了個吉日,設壇祭天,歃血為盟,推選盟主。眾豪傑多歸心於袁紹,大家齊稱,袁家四世三公,袁紹英名卓著,應為領袖。袁紹辭讓再三,大家仍眾口一辭。袁紹說:「恭敬不如從命。非敢為天下先,聊作迎風排頭雁。」於是,袁紹自號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使曹操為奮武將軍。餘者皆「權授」官號。所謂「權授」者,權且自授也。此刻和圖書,天子已為董卓所挾持,袁紹等人無從接受朝廷的誥命,故而權且自封官號,留待日後朝廷追命。
聽罷各路探子報來的消息,董卓坐不穩,笑不出聲了。他本以為,這檄書不過是紙上談兵的袁紹之流虛張聲勢的手段,沒想到竟然真刀實槍地幹起來了。雖然,他並不把袁紹一類的公卿世家子弟放在眼裡,但也不敢低估他們在朝廷內外的號召力。如果海內盡是追隨袁氏,反叛董氏的人,縱有三頭六臂,怕也應顧不暇了。「這如何是好?」無愁將軍董卓也發愁了。
美酒一杯接一杯,部下親朋爭著為他獻酒祝賀,他心情也特別好,只要獻酒者說得中聽,不分尊卑,一律與之同飲,言語若有不得體者,不管職位高低,一律罰酒三碗。不知不覺,太陽偏西,堂上堂下燃起了明晃晃的巨燭,有的人已喝得臉紅脖子粗,滿嘴酒氣,仍爭著為相爺敬酒;有的人傻笑著舉起杯子,一個踉蹌,便連人帶酒跌倒在案上,頓時間,轟笑聲,叫罵聲,杯盤的碎破聲亂成一團。這樣的鬧酒場面,在董卓的軍營裡是司空見慣的,這也正是董卓「寬以待下」的一種舉措。每逢遭遇惡戰,或者打了勝仗,董卓都要與部下一道狂飲大鬧一場,痛苦在這裡發洩,喜悅在這裡分享,生死相許的義氣在這裡加深。這個習慣,起自董卓領著小兄弟從軍征戰時,幾十年來,儘管他的官越做越大,這種與部下同歡共樂的酒會卻被保留下來,沒有任何改變,一如當年,這也是他手下的將士,尤其是跟隨他幾十年的隴西弟兄樂於效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看著屬下僭越儀禮的拜舞,董卓不以為忤,反而笑逐顏開,欣然受納。
下面便是一干人的簽名,數一數竟有十四路之多,領銜者,車騎將軍袁紹,餘下有河內太守王匡,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陰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典軍校尉曹操,後將軍袁術等。
弘農王聞歌哽咽,忍不住失聲相向。李儒在旁連聲催促道:「相國立等回報,豈可一哭了事!」弘農王一把抓起鴆酒,凝視著淚水滿面的唐姬,毅然說道:「卿為王妃,不能再為吏民妻,幸自愛!」唐姬泣不成聲,無法仰視弘農王。
見董卓發怒,鄭泰亦不慌張,從容言道:「泰非謂兵不可用,但以為山東之亂無須發大軍征討。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嫻習軍事。袁紹本公卿子弟,生長京師,曹操乃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只能清談高論,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戰,此輩皆非公之敵。況關東諸軍,雖眾而雜,王命不加,尊卑無序,星分棋散,雁行參差。加之和-圖-書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屢遭羌寇,婦孺皆知挾弓矢而爭鬥,天下所畏者,無過并、涼之人及羌胡義從,而明公收之為爪牙,譬如驅虎豹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明公若以為當議所陳。稍有可採,正不必四出征發,驚動天下,否則棄德恃眾,反損威望,非但無益,且有害也。」
聽董卓下了死命令,李儒絲毫不敢怠慢,立即領了鴆酒匆匆趕往弘農王府。
那幫正在醉鄉裡遨遊的將弁們,先是被「乒乒乓乓」的聲音所驚醒,繼而聽到董卓暴跳如雷的怒罵,以為是他們酒後失態,激起相爺的怒火,皆避席跪伏請罪。倒是那幾位一直陪酒的老弟兄心裡有數,紛紛啟言勸慰。有的說:
越年元旦,又改年號為初平。
不數日,各路消息紛紛傳回相府,十四路人馬討董,並非一紙虛文。董卓聽了,陰沉著臉,命令打探詳細內情。此事的起因,與東郡太守橋瑁有關。橋瑁是已故太尉橋玄的侄兒,做過兗州刺史,吏蹟頗著,及調任東郡太守,正值董卓把持朝政,擅自廢立時,海內豪傑都想起兵討董,只是無人發難,誰也不敢輕易舉事。橋瑁有志討董,又擔心自己勢孤力弱,不足濟事,於是便詐作三公密敕移書州郡,歷陳董卓的罪惡,並稱「遭罹強|暴,無以自救,企望義兵,救國活民」云云。
有的說:「相國大人。龍驥虎步,威震天下,據國家武庫,有猛將雄兵,區區幾路反賊,何足掛齒,大軍一到,還不是灰飛煙滅。」
李儒入了相府,董卓面授密計,要他攜帶鴆酒前往弘農王府邸,乾脆俐落地將劉辯結果掉,事若不成,就提著自己的腦袋回來覆命。
新年伊始,百官都先到相國府拜賀,然後由董卓領著前往宮內朝見獻帝。及至朝班散去,董卓退回府中。堂上已排好盛筵,正等他來開席。與宴者都是部下親朋,人人穿著簇新的朝服,個個臉上掛著志滿意得的笑容,見董卓大搖大擺地坐定在尊貴的南向位上,侍候在兩側的人,便一齊退至堂下,依照朝見天子的儀禮,給董卓行三叩九拜大禮。
「我無病無災,何須飲用此酒?」劉辯生長在帝王之家,對下毒飲鴆一類的事聽說過很多,而且身位罪人,羈居幽邸,需要提防的也正是這類事。他一眼便看出李儒的用心。雖然,他平日裡也想過死,激憤之時,似乎不再怕死,甚至有求死不得的感覺,但真的死亡降臨時,仍然湧上一種難言的悲傷。他語帶哽咽地問話道:「汝欲毒殺小王?」
劉辯叮嚀完,便一仰脖子,飲下鴆酒,不一會兒便跌倒在地,全身抽搐,七孔流血,毒發身亡。這一天是初平元年正月,當時,弘農王還沒有過十五歲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