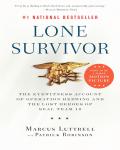第十二章 二二八!這是二二八!
由此,他們推斷有一名海豹隊員在那個村子裡,或者非常靠近那個村子。所以這些人穿過基地組織的封鎖,在我隱藏的地點附近展開了拉網式搜索。而我突然出現了,穿得活像賓.拉登的副手,被幾個阿富汗人架著,像喝醉了酒一樣搖搖晃晃地上了山,還有一個人在身後大喊:「二二八!」
每個人的遺體送回國時都由一名海豹突擊隊的禮兵護送,禮兵身著軍服,為覆蓋著星條旗的棺槨站崗執勤。正如我所說過的,我們絕不丟下任何一個人。
綠色貝雷帽們仍然在執行聯絡任務,告訴飛行員把飛機降在一片剛剛收割過的鴉片田裡。我至今還記得那架直升機旋翼在夜空中發出的淡淡螢光。
那名醫生只是搖了搖頭。他之前已經遇到過許多我這樣的傢伙,知道與這樣的人爭論沒有意義。我猜他明白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如果他們必須把我抬上飛機的話,我還算什麼海豹隊員?不,長官。我絕不同意。
「魯特埃勒先生和魯特埃勒夫人嗎?」
我看到了一張照片,那是在墓地的下葬儀式上拍的。當時邁克的棺槨正在被放入墓穴之中,天上下著瓢潑大雨,每個人都被淋得渾身濕透,表情堅毅的海豹隊員身著禮服莊嚴肅立,在暴雨中紋絲不動。
古拉卜帶我們下山,來到村畔的那塊空地上。我們一面與基地聯絡,一直等待直升機降落。遊騎兵在周圍展開隊形,保護著陸場,以防基地組織孤注一擲。我知道基地組織就在附近,一直目不轉睛的盯著與我們相遇的那座山坡。除了大約二十名陸軍的弟兄,我的周圍還有十幾名村民,因為我的緣故,這些村民從一開始就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是,長官。」我用床單擦乾了眼淚,回答道,「您覺得我能要一個奶酪漢堡嗎?」
警察為送葬行列開道,數以千計的普通人前來向一位為國捐軀的人致敬。但他們並不了解他所有的英雄事跡。除了我之外沒有人知道。
那位護士只喊了一聲「噢,馬庫斯!」,就轉過身去開始抽泣。我拒絕上擔架,強忍疼痛扶著一位醫生向前走。但是他知道我的情況,說道:「來吧,兄弟,讓我們把你放到擔架上吧。」
他是阿富汗特種部隊的成員,之所以舉著槍是因為我穿著阿富汗部落的服裝,跟那些基地武裝分子的衣服一模一樣。接著,兩名美國陸軍的遊騎兵端著槍從他身後的樹叢中跳了出來,為首的是個黑人大個子。這時古拉卜在我身後大喊起來,他喊的是我三叉戟紋身上的海豹基礎水下破壞訓練課程班的編號:「二二八!這是二二八!」
但我的確實現了我的夢想。我以後可能會反覆地問自己,為了這個夢想付出這樣的代價是否值得。而我的回答將永遠跟第一天的回答一樣:
現在他們抬著墨菲走過人群,走過我。突然,我的高級指揮官們走過來告訴我,我應當站在飛機的坡道旁邊。我走上前去,不顧背後的劇痛,盡可能的立正站好。
葬禮上常說的一段話突然湧上我的心頭:「歲月磨不去他們,每當太陽升起,夕陽落下,我們就會想起他們。」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的病床上,我自己為兩位犧牲的兄弟舉行了告別儀式。
我們在那裡休息了一下,同時小心提防基地的狙擊手,但是沒人來。我們周圍的林間都是薩伯拉村的熟悉面孔,他們握緊了AK步槍,準備保護我們。
在古拉卜的帶領下,我們朝村子前進,回到我們躲避暴風雨的那棟房子裡。陸軍的弟兄們在薩伯拉村四周布防,之後把我抬進房間裡。我注意到那隻公雞還在樹上,現在牠終於安靜了,但想到牠之前的所作所為,我仍然想把牠的頭擰下來。
歡樂的叫喊聲迴蕩在東德克薩斯孤寂的高原上,他們告訴我那聲音在五十五英里外的休士頓都能聽到。摩根說那不是平常的叫喊,而是大家一起竭力發出的震耳欲聾的最強音。為媽媽、爸爸和我的家人感到欣慰和喜悅。
我又一次強調我們肯定被包圍了,而他回答道:「收到,馬庫斯。我們會採取相應的措施。」
這是我第一次離開醫院,來到大家面前,每個人看到我都大吃一驚,雖然我衣著整潔,但一點都不像他們記憶中的那個馬庫斯。我還因為接觸了那個該死的百事可樂瓶子而重病纏身。
這種情景讓我難以承受,我也不禁痛哭起來,當我再次打起精神的時候,佩羅中校問我是否需要什麼東西,不管我要什麼,他都能幫我找到。
這個消息像導彈一樣飛遍了全球:從巴格拉姆傳到巴林,再通過衛星傳到科羅納多的海軍特種作戰司令部,最後通過直撥電話傳到我家的農場。
我活下來了,但是我之前並沒有像艾克斯那樣身中五槍。我清楚地記得他最後的位置。我又與搜索隊談了一次,而且海豹突擊隊高層也不會將他留在那裡。他們要再去一次,這次需要盡可能詳盡的情報,更多的搜索人員和更多的當地嚮導。
他們泡了些茶,隨後我們坐下來詳細的介紹情況。現在是中午,圍坐在四周都是陸軍的弟兄,大部分是遊騎兵和綠色貝雷帽。在開始之前,我覺得必須告訴他們我原本希望由海豹隊員來營救我——因為現在我肯定必須忍受他們的許多廢話,告訴我「看到了嗎,海豹遇到了麻煩,然後上級就像以前一樣,派陸軍去把他們弄出來。」
古拉卜又一次做了一個滿不和_圖_書在乎的手勢,我們兩人轉過身,看著基地分子消失在樹林中間。然後古拉卜把我拉起來,又一次帶著我穿過樹林,走下陡崖,一路上他都非常照顧我受傷的左腿,最後我們來到了一條乾涸的河邊。
他們緩慢地,無比莊重的高高抬起棺材,將邁克和丹尼的遺體送往五十碼外的飛機。
我們至少等了四十五分鐘,隨後,在山間的死寂中。又有兩個村民趕到了。他們顯然示意讓我們立刻離開。
是他永不言敗的標誌。
我就這樣自己慢慢地挪下飛機艙口的坡道,下到地面,回到了我的基地。這時我注意到了另外兩名護士也流下了眼淚,記得當時自己心想:感謝基督,媽媽現在還見不到我。
他害怕直升機,在飛往阿薩達巴德途中一直緊緊的抓著我的胳膊。達到目的地後,我們兩人下了飛機,我將前往巴格拉姆,而古拉卜將在阿薩達巴德基地停留一段時間,在他自己的國家為美軍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我與他擁抱道別。這位阿富汗部落的男子冒著生命危險保護我,但卻不願得到任何報酬,我最後一次試圖把我的手錶送給她,但他第五次拒絕了。
「我們有直升機。阿帕契,隨時待命,」隊長說道,「我們有所需要的一切東西,沒問題。」
我的情況看起來糟糕透頂。我的體重減輕了三十七磅,面部再從山崖上滾落時嚴重擦傷,鼻梁骨折,需要復位,腿部嚴重受傷,腕部粉碎性骨折,背部三節脊椎骨裂,劇痛難忍,而且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流了多少血。面部蒼白得簡直像個幽靈,幾乎不能行走。
克里斯軍士長攙著我母親走到電話旁,告訴她不管怎樣,她都必須勇敢面對。一個聲音在電話裡問道:「軍士長,全家人都到齊了嗎?」
不管怎樣,他們找到了艾克斯。在艾克斯重傷垂死的時候,基地分子把整梭子彈傾瀉在了他的臉上。基地分子也是這樣對付邁克的。但是艾克斯並不在我所認為的地點。我知道我們兩個人都被一顆火箭彈從窪地裡炸得飛了出去,我飛下了懸崖,但艾克斯最後的位置比我還要遠幾百碼。沒人知道他是怎麼到達那裡的。
但他們認為操作那部電台的不是阿富汗人,如果一個人完全不清楚信標的作用的話,他肯定不會把它打開並將其指向天空。
現在是星期天了。耶穌啊,能再一次聽到英語真是太好了,那些簡單的話語,美國各地的口音,那種熟悉的味道。如果你在一種敵對而陌生的環境中待過一段時間,無法對任何人說明白任何事情,這時候被自己人——堅強、自信、專業、訓練有素、武裝到牙齒、準備應對任何事情,充滿自信的自己人營救了,那真是莫大的喜悅。但是我不建議你經歷這一刻之前的一切。
我建議他們找薩伯拉村的長者,因為他肯定能夠帶他們找到陣亡的海豹突擊隊員。那時候我才從情報人員那裡得知那位長者原來是搜索範圍內所有三個村莊的總首領,在興都庫什山區廣受尊敬,因為那裡的文化不崇拜年輕、輕浮的電視名星,部落中的人們最重視的是知識、經驗和智慧。
我看了看畫在腿上的地圖上面清楚地標著路線、距離和地形。我指給他們恐怖武裝駐紮的地方,幫助他們標注他們自己的地圖。這裡,這裡,還有這裡,兄弟們,他們就在這兒。事實上,這些混蛋到處都是,就在我們周圍等待機會。我感覺沙馬克可能不願再去正面硬碰美國的優勢火力,畢竟我們四個人在山上就消滅了他一半的部隊。現在我們的人數多得多,所有人都圍在一起,同時特拉維斯則在繼續處理我的傷口。
在我看來他們的人有點少,因為在基地組織的支持下,沙馬克可以很容易的召集一百五十到兩百人。
這些遊騎兵和綠色貝雷帽們也不例外。他們在數百平方英里的山區裡營救了我。但我知道他們並不明白我們當前的處境異常危險。我向他們說明了附近基地武裝分子的數量,在墨菲山嶺上有多少人在跟我們作戰,而且沙馬克和他的部隊就在附近,也許正在監視我們……不,算了吧。他們肯定在監視我們。雖然我們是一支強大的作戰部隊,但是一旦發生衝突,我們人數上將居於絕對劣勢,而且不僅是我,我們全體現在都進入了基地組織的包圍圈。
他們立刻展開行動。一名陸軍上尉命令一個小隊把我帶出森林,到高處去。他們把我抬上山,讓我坐下,隨後醫護兵塔拉維斯立刻開始包紮我的傷口。他解開薩拉瓦包的舊繃帶,重新塗上消炎藥膏,又用新繃帶把傷口包紮起來。
醫生和護士,沒問題。海豹突擊隊的高級指揮官,嗯……好吧,但一切到此為止。其他任何人都沒門。傑夫.德拉彭塔甚至連將軍也擋在門外!告訴他們我正在休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打擾。「長官,讓您進入這間病房是我莫大的榮幸。但是我的醫生下了嚴格的醫囑……」
當火箭彈打中我們的時候,艾克斯還剩下三個手槍彈夾,但當他們找到他的時候,他身上只剩下最後一個彈夾了。這只能說明一件事:艾克斯肯定繼續進行了戰鬥。當他從昏迷中醒來後,再次與那些混蛋作戰,朝他們打了三十多槍。這一定激怒了他們,我猜正是因為如此,當艾克斯最後傷重不支的時候,基地分子才會如m.hetubook.com.com此野蠻地殘害他的遺體。
這時候整座山上一片沸騰,陸軍的弟兄紛紛從樹林裡衝出來,身上的戰鬥服都破破爛爛,渾身都是泥,所有人都幾天沒刮鬍子,看起來髒兮兮的,肯定著實吃了一番苦頭。我想他們從上星期三凌晨就被派出來尋找我的小隊了,事實也正是如此。該死,他們在暴風雨中待了一整夜,難怪看起來這麼狼狽。
我在那裡奔跑、跳躍、托舉、投擲、游泳、掙扎、拼命努力。當別人倒下時我繼續前行。在這片海水沖刷的海灘上,無數人的希望和夢想化為泡影。但我的希望和夢想則在這裡實現。我有一種滑稽的感覺,那個年輕、努力地馬庫斯.魯特埃勒的靈魂會一直在這片海灘上遊蕩,拼命跟上參訓的海豹候選人員。
直升機朝著我們降了下來,他是美國空中力量的象徵,震耳欲聾的轟鳴聲在興都庫什的山峰間迴蕩,打破了周圍的死寂。大地在顫抖,塵土漫天飛揚,旋翼在純淨的山區空氣中發出尖嘯。這是我所聽過的最美妙的聲音。
上級這時候給我指派了一名看護,那就是一級海軍士官傑夫.德拉彭塔(海豹突擊隊第十大隊),他片刻不離我左右。而當時基地裡幾乎所有人都想過來探望我,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但是傑夫不吃這套,他就像一隻德國牧羊犬那樣看守著我的病房,告訴來探望的人我病情嚴重,需要靜養,而他,一級海軍士官傑夫,將保證我能夠安心靜養。
「是的,長官。」
接著那名遊騎兵朝我衝過來,一把把我抱住,我能聞到他身上的汗水、作戰裝備和步槍的氣味,家鄉的氣味,我生活的氣味,美國的氣味。我竭力保持鎮定,控制住自己,主要是因為海豹隊員絕不會在一個遊騎兵面前表現出脆弱。
我站在後排,看著他們小心的把我的兄弟送上返鄉的第一站。無數的記憶浮現在我的眼前,任何參加過墨菲山嶺之戰的人都不會忘記他們的英勇。
克里斯軍士長扶著她走進屋子,來到臥室,電話就裝在臥室裡。這時她看到摩根和我的另一個兄弟斯科提正摟在一起抽泣。所有的人都以為他們清楚部隊的情況,提前來電話只有一個原因——他們已經在山上找到了我的屍體。
當他們把艾克斯的遺體帶回來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七月八日夜,我乘坐一架波音C─一四一運輸機飛往德國。傑夫.德拉彭塔陪著我,寸步不離左右。在德國,我住進了美國駐蘭德斯圖爾空軍基地的地區醫療中心。這個基地靠近法德邊境,在法蘭克福西南方大約五十五英里。
大約七十名海豹隊員、遊騎兵和綠色貝雷帽列隊緩步走上飛機,在棺槨前立正,莊嚴的敬禮,隨後再走下飛機。我一直站在那裡,當最後一人走下飛機之後,我也慢慢地走上坡道,來到棺槨前。
現在我一個人跟這些村民在一起,沒有一個完整的計劃,而且我的腿疼得要命,簡直不敢沾地,只能讓兩個人架著走。來到一條峭壁上鑿出的狹窄通道上時,他們就在我的身後用肩膀把我頂上去。
我望著海豹基礎水下破壞訓練班辦公室門口的那口鐘,望著退訓者留下他們頭盔的地方。很快新的海豹水下破壞訓練班就要開始了,又會有更多的頭盔放在那裡。上次來的時候我穿著禮服,與一群新海豹隊員在一起,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與我一起服役。
飛機裡除了站在棺槨前的海豹突擊隊禮兵之外,還有一位堅強的老戰士,本.桑德斯軍士,他是丹尼最好的朋友,來自西維吉尼亞的山區,是追蹤和攀登專家,對於荒野瞭如指掌。他扶著棺材,悲痛欲絕,泣不成聲。
直升機緩緩降落在離我們幾碼遠的地方。裝卸長跳下了飛機打開了主艙門。人們扶我進了機艙,古拉卜也跟我們一起上了飛機。我們立刻起飛了,沒有人再回望漆黑一片的薩伯拉村。我沒有回頭是因為知道什麼也看不見;古拉卜沒有回頭是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回到村裡。基地組織對他和他的家人的威脅比他所承認的嚴重得多。
我走回第一處營房,旁邊就是「洗消室」,當第一次聽到裡面的設備啟動時,我差點嚇得蹦起來。隨後我來到粉碎機操場旁,當時海豹指揮官就在那裡最終給我戴上了三叉戟徽章,並向我祝福。也是在那裡,我第一次與喬.馬奇奧將軍握手。
我向他們詳細說明了我在戰場上和離開戰場後的行動。在此期間,孩子們不斷地跑進來看我,他們抓著我的胳膊,摟著我的脖子,又叫又笑。村裡的大人也來了,薩拉瓦也重新出現了,古拉卜則一直陪著我。他們救了我的命。
我現在非常擔心艾克斯。他在哪兒?他到底犧牲了嗎?但是人們找不到他,這實在太糟糕了。我已經精確指出了我們兩人待的那塊窪地的位置,基地分子最後就是在那裡把我們兩個炸飛的。
他們走了五分鐘之後,又一起回來了。沙馬克站在那裡瞪了我一會兒,然後就上山回到他的部隊那裡去了。古拉卜下山朝我走來,告訴我沙馬克給了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要麼交出美國人——要麼全家都被幹掉。
在探望親屬的漫長旅途中,作為美國海軍的代表,迎接我們的都是熱情、友誼和感激。我認為探訪遍布全國的那些家庭說明不僅他們的家人會永遠珍藏對烈士的記憶,他們曾經服役過的海軍也永遠https://m.hetubook•com•com不會忘記他們。美國海軍非常重視這項工作。
「是,長官。」
C─一三〇運輸機停在跑道上,機艙的坡道已經放下。參加儀式的大約有兩百名軍人。悍馬吉普車載著兩具覆蓋著美國國旗的棺材抵達了機場,這時雖然沒有口令,但所有人都立正肅立,由海豹突擊隊的禮兵上前抬起他們的弟兄。
我住院的第三天,邁克和丹尼的屍體從山上運了下來,但他們沒能找到艾克斯。我得到了這個消息。當天下午,我穿上襯衫和牛仔褲,讓狄更斯醫生開車送我參加機場的送別儀式,這是海豹最神聖的傳統,我們用這種方式向我們犧牲的兄弟道別。
邁克.墨菲海軍上尉隆重的葬禮在紐約長島舉行。他們封閉了好幾條繁忙的道路,長島高速公路上掛滿了橫幅,紀念一位在打擊基地組織戰鬥中獻身的海豹隊員。
聽到這個消息,媽媽朝著臥室的地板上栽了下去。幸虧斯科提疾步上前抱住了她,媽媽才沒有栽到地上。瓊斯海軍上尉衝到門口,站在門廊上讓大家安靜,隨後他大聲喊道:「他們找到他了。夥計們!馬庫斯得救了。」
那時他是對的,現在他仍然是對的。這的確糟透了。當他們抬著邁克上飛機的時候,我努力要為我最偉大的兄弟想一段墓誌銘,我想起了澳大利亞詩人邦喬.帕特森寫的一首詩。這首詩是邦喬為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寫的,而麥克正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的話引起一陣大笑。儘管如此,我會永遠感激他們,感激他們冒險來營救我。他們都是好樣的,非常專業。首先他們用電台向基地報告已經找到了我,我的情況穩定,但遺憾的是另外三名隊員已經陣亡。我聽到他們向基地確認已經安全的找到了我,但是當地人有可能對我們採取敵對行動,而且我們處於基地組織的包圍之中。要求天一黑就盡快撤離。
當我看著我的隊友的遺體被逐一送回國的時候,我感到無盡的悲傷,覺得自己的一部分也消失了。我這樣做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了找回失去的自我。大部分隊友的葬禮在我回國之前就已經舉行了,我也沒能參加海軍為他們舉行的紀念儀式。
等我安頓下來之後,真正的情況匯報就開始了。我就是在那時才第一次完全了解了洛克海法則的全部含義。之前我只是猜測薩伯拉村的人們可能會為我而戰,但是並不肯定這一點。一名情報軍官告訴了我相關細節,現在我知道薩伯拉村的人們當時確實準備為我戰鬥到最後一人。
丹尼摔下山崖的時候右手大拇指已經被打掉了,但他依然在射擊,一次又一次的射擊。就在我拖著他撤退的時候也依然無所畏懼,挺直身軀向敵人射擊,直至戰鬥到最後一息。現在,他躺在這口光滑的木製棺材裡了。
我跪在棺材旁,向丹尼告別。隨後我轉身抱住邁克的棺材,記得自己當時好像說「對不起,真的對不起。」現在我雖然記不起當時我具體說了些什麼,但我記得自己當時的感受,覺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想著邁克的遺體就要被運走了,很快許多人就會忘記他,另外一些人只會偶爾想起他,而只有幾個人永遠不會忘記他。
但是我們什麼也沒有說。我回家了。而他可能永遠都不能回家了。我們的人生道路突然之間交會到了一起,但現在就要分開了。
我認為,我在興都庫什山脈執行最後一次戰鬥任務時所做的全部事情,他們中的任何人,在任何一天,都會不折不扣的加以完成。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我只是一個德克薩斯的普通鄉下孩子,接受了世界上最嚴格的訓練,跟一群最偉大的同伴一起戰鬥。海豹隊員是戰士,是美國軍隊的一線力量。直到現在,一想到我的使命,我仍然激動萬分。
實際上,我感覺非常痛苦。那針嗎啡還不如村民給我的鴉片。渾身上下沒有一處地方不疼。此時,海豹突擊隊大隊長肯特.佩羅中校也前來正式迎接我,我的醫生卡爾.狄更斯也來了。
在我們離開之前,我問他們是怎麼找到我的。原來是我放在山上小石頭房子窗台上的求救信標起了作用。空勤人員在飛行時收到了求救信號,隨後進行了定位,確定信號是從那個村子裡發出的。他們肯定那部PRC─一四八電台原來的主人是海豹小隊的某個成員,但也考慮到現在電台可能落入了基地手裡。
我們都立刻作出了反應。古拉卜自己沒帶槍,所以抓過我的步槍,並與他的兩名同伴一起翻過石牆,其他的幾名村民飛快的朝山上自己的家中跑去。但古拉卜沒有。他在牆後占領了一個射擊位置,用我的狙擊步槍瞄向山上的敵人。
我站在粉碎機操場上,思緒萬千,而我的背部和腕部又開始隱隱作痛,需要再次手術。我知道我不能再迅捷的奔跑和攀登了,我的身體永遠不可能完全復原,我也永遠不可能恢復之前的作戰水準。可這沒什麼,反正我的身體素質本來就達不到參加奧運會的標準。
就在那時候,我摔倒了。醫生和護士們跑上來幫助我,把我用擔架抬到一輛廂型車上,直接送到醫院的病床上。個人英雄主義的時刻結束了。我經歷了這個該死的國家所能帶給我的一切苦難,又度過了一次地獄週,現在我得救了。
驕傲的高高昂起的頭,
和圖書臨近年底時,我的傷勢有所好轉但尚未痊癒。我被調回科羅拉多,從運輸載具第一大隊轉入海豹第五大隊,並被任命為A排的士官長。像海豹突擊隊中所有的排一樣,這個排有一套精確的管理機制,軍官負總責,軍士長主管,士官長具體管理。他們甚至給我安排了一張辦公桌。第五大隊的指揮官里卡.郎維中校像慈父一般關愛我,一級軍士長皮特.納奇科這位老戰士也一樣。
我跟我的家人通了電話,但是沒有告訴媽媽我的胃部現在感染了某種阿富汗山區的細菌。我向上帝起誓,這肯定是那該死的百事可樂瓶子弄得。那東西簡直可以把興都庫什山區裡的所有人都毒死。這並沒有妨礙我享受我的奶酪漢堡,第一個漢堡真是美味無比。
當然,基地組織傷亡慘重,看起來人人都知道這一點。我想房間裡的每一個人,包括古拉卜在內,都認為基地組織不會再一次冒險正面攻擊美國人。我們就這樣一直等到太陽落山,隨後我向孩子們告別,有幾個孩子留下了眼淚。薩拉瓦則悄悄的離開了,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牧師走上了坡道,當棺材被緩緩抬上飛機的時候,他開始講道。我知道現在不是葬禮,不是遺體送回國內後由其家人參加的正式葬禮。但這是我們的葬禮,我們這些駐外軍人,作為他們的另一個大家庭,將對兩位偉大的戰士作最後的告別。牧師悅耳的聲音在飛機上迴蕩,他讚譽他們的一生,請求上帝給予他們最後的恩典——「讓永恆的光芒照耀著他們」。
我們在黑暗中倚著石牆坐著,注視著陸場,默默等待。晚上十點剛過,我們聽到山嶺上空遠處傳來了一架美軍大型直升機的隆隆聲。
佩羅中校陪我上了廂型車,這位海豹的高級軍官從與我第一次見面開始就清楚的記得我的名字。現在他坐在我的身邊,抓著我的手,問我感覺怎麼樣。我記得當時回答他說,「是的,長官,我很好。」
我們迅速與他取得了連繫,幾天後,這位老人,古拉卜的父親,我的保護人,帶領一支美國的海豹小隊向山區出發了。這支海豹小隊由A排的人員組成,其中有我的許多兄弟,馬里奧、貝克、加瑞特、史蒂夫、西恩、吉姆和詹姆斯(這些都是現役特種作戰人員,所以這裡沒有列出他們的姓氏)。
我一個人走下飛機,狄更斯醫生開車將我送回醫院。我站在病房裡聽到C─一三〇開始起飛,聽著它轟鳴著離開跑道,載著邁克和丹尼向夕陽落下的方向飛去,飛向離天堂更近的地方。
我平安到達巴格拉姆之後,他們就公布了我獲救的新聞。雖然美軍在幾小時前就找到了我,但是我想海軍不願意在我平安返回之前就告訴人們開始慶祝。
至今我們仍未發現邁克、丹尼和艾克斯的屍體。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判讀衛星照片,以便準確指出他們陣亡的地點。陸軍知道一些那場戰鬥的情況,我又對他們做了詳細說明,告訴他們我們怎樣在邁克的指揮下邊打邊撤;艾克斯怎樣憑藉超人的勇氣堅守我們的左翼;丹尼怎樣在多次中彈後仍然堅守右翼,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而基地組織最後又怎樣憑藉人數和火力上的絕對優勢壓垮了我們。
那位長者幾乎不與他們說話。但是他直接把搜索隊帶到馬修.吉恩.埃里克森遺體所在的準確位置。他的面部已經被近距離發射的子彈打爛了,基地分子發現重傷的美國士兵總會這樣做。當我寫到這裡時,如果有人敢向我提《日內瓦公約》,我很可能會控制不住自己。
四名醫生正在等著我,他們向我提供了所需要的全部治療。另外還有幾名護士,其中一名當我在醫院志願服務的時候就認識了。所有人看到我的慘狀都目瞪口呆,那名認識我的護士看到我的時候更是忍不住失聲痛哭。
他們扶著我穿過樹林,登上陡坡。我必須承認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不知道我們正要去哪裡,也不知道接下來我該做什麼,只知道我們不是回村子,而且我真的很不喜歡古拉卜口袋裡那張字條的語氣。
那名遊騎兵的臉上一下子露出了微笑。他看了看我六英尺五英寸的塊頭,突然問道:「美國人?」我剛點了點頭,他就震山動地的大喊起來:「他是馬庫斯,弟兄們!我們找到他了……我們找到他了。」
我自從七年前結束海豹基礎水下破壞課程後就再沒回過科羅拉多,這次重回舊地讓我想起許多往事。我再一次走到當年接受訓練的那片海灘,我就是在那裡第一次懂得了作為一名海豹隊員,應當期望些什麼、忍受些什麼,學會了忍受刺骨的嚴寒和劇痛,學會了絕不遲疑、毫無怨恨的立即執行命令,這都是一些基礎。
我在那裡待了九天,對傷口和背、肩、腕部的骨折進行治療。但是那個百事可樂瓶子上的病菌不願放過我的胃,一直折磨了我很長時間,使我很難恢復原來的體重。
(全書完)
「是的。」媽媽低語道。
現在救援直升機仍然在遠處盤旋,而空軍的飛機終於發動了攻擊,他們呼嘯著掠過漆黑的山谷,用炸彈、火箭彈等各種武器攻擊山坡上的一切生物。山坡上一片火海,沒有人能夠生存下來。
我登上了巨大的C─一三〇運輸機,飛往巴格拉姆基地。晚上十一點,我們降落在主跑道上。邁克、艾克斯、丹尼www•hetubook.com•com和我六天零四個小時之前就是從這裡出發的。當時我們躺在地上,望著遠方被冰雪覆蓋的山頂,笑著,互相開著玩笑,那麼樂觀,絲毫不知我們在遙遠的群山間將經歷怎樣火的考驗。時間到現在過了還不到一週,但在我看來,那似乎已過了千年。
科羅納多已經按照正常規律在當天下午一點鐘左右給農場打了電話,而農場的人們也以為科羅納多四點鐘才會再來電話,告訴他們「沒有消息」。但是三點鐘的時候電話響了,這比預計的時間早。據我的父親說,我的母親幾乎暈倒。在她看來,此時來電話只有一個原因,通知她的小天使(也就是我)已經陣亡。
我認為基地組織顯然是準備要發起最後一搏來把我幹掉。我抓過一部夜視儀,在牆後占領了觀察哨的位置,努力鎖定那些基地分子的位置,好一勞永逸的把他們全幹掉。
我瞪著那片山坡,在黑暗中能都看到有許多白色的光點在迅速移動。「基地,馬庫斯!基地!」我感覺出古拉卜很緊張。我叫過美軍的隊長,告訴他有危險。
這些情況匯報提供了足夠的數據,讓他們能夠精確確定我的同伴們屍體所在的位置。我發現回憶這些對我是一種煎熬,看著兄弟們陣亡地點的照片,我又一次拷問自己,我當時能不能救他們?我能再多做些什麼嗎?那天夜裡,我第一次聽到了邁克的尖叫。
但我還是搖頭。我被注射了一針嗎啡後,試著自己站起身來,轉身直視著那名醫生說道:「我是自己走著來的,我還要自己走著離開,雖然我受了傷,但我還是一名海豹隊員,他們還沒有把我打倒,我要自己走。」
「我們找到他了,媽媽我們找到馬庫斯了。他的情況穩定。」
他消瘦、結實、堅強——就是那種蔑視死亡的人——
周圍一片喜悅,因為所有人都覺得任務完成了。所有的美國軍人都理解這種慶祝的感覺,它說明我們經歷了無數的艱難險阻,一次次面臨絕境,又一次次憑藉過硬的軍事技能化險為夷。
這就是邁克爾.帕崔克.墨菲上尉。你可以相信我。我跟他一同生活,一同訓練,一同戰鬥,一同歡笑,而且幾乎與他一同戰死。這首詩的每一個字都是為他而寫的。
負責通訊的人員開始呼喚空軍,我們知道空軍的飛機就在附近——戰鬥機、轟炸機和直升機,只要基地組織試圖攻擊執行營救任務的直升機,他們立刻就會進行轟炸。
火焰般明亮的眼睛,
當時我聽到他叫了一聲「馬庫斯」,隨後他搖了搖頭,我發現這位無比堅強的人,我上級的上級,也流下了熱淚,我想那是因為我還活著而流下的欣慰的淚水。自從邁克、艾克斯和丹尼戰死以來,這是第一次我同一個真正擔心我生死的人在一起。
他匆匆的腳步中滿含勇氣;
但是邁克的死對我的影響最大。沒有任何人會像我一樣懷念他,感受他的痛苦,聽到他的尖叫。沒有人會像我一樣在凌晨的噩夢中見到他,永遠熱愛他,懷疑自己是否已經為他竭盡全力。
與他告別對我來說非常痛苦,因為我沒法用他的語言來表示我的感謝。雖然我永遠也不會知道,但是如果他能找到合適的英語詞彙的話,也許他會對我說些什麼。可能是一些非常溫暖或者令人感動的話,例如「大叫大嚷的東西,走起路來簡直像頭象,不知感激的雜種。」或者是「我的最好的羊奶有什麼問題嗎?混蛋?」
我盡可能詳盡地向他們介紹了情況,首先說明我的同伴邁克、艾克斯和丹尼都已經陣亡了。我發現這真的難以啟齒,因為之前我從未告訴過任何人他們已經陣亡了。我找不到人匯報這一情況,而且也沒有人會知道那三名隊友對我意味著什麼,他們將在我的生命中永遠留下一個缺口。
另外還有來自E排的一個搜索小隊。他們整日都在崎嶇的山路上奔波,而且攜帶了更多的水和食物,準備進行長期搜索,決心不找到艾克斯絕不回來。不,長官。我們絕不丟下任何人。
另一口棺材裡是麥克.墨菲,我們的指揮官,他走入烈火風暴之中,去打最後一個電話,冒著生命危險爭取一個營救我們的機會。當時基地分子的子彈正中他的後背,他倒在地上,血如泉湧,手機也掉到了地上,但是他又把手機撿了起來。「收到,長官。謝謝你。」還有什麼人比那更勇敢嗎?記得當時我滿懷敬畏的看著他又站起身朝我走來,回到自己的位置,重新投入戰鬥。「馬庫斯,這真是糟透了。」
「嗨,兄弟,」我說,「見到你太好了。」
我問遊騎兵的隊長他們有多少人,他回答說:「我們沒問題。有二十個。」
我看到直升機遠遠地離開「基地」組織大部分駐紮的山坡,在空中不停地盤旋。突然,古拉卜抓住我的胳膊:「馬庫斯,馬庫斯,基地!」
興都庫什山脈中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逐漸消失,美軍的空中打擊結束了。著陸區域已經被清理乾淨,安全了。這時,救援直升機從南面疾速飛來。
我第一個上了峭壁,結果迎面碰上了一名全副武裝的阿富汗戰士,這個人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他拿著一支AK四七,隨時準備射擊,一看到我就把槍端了起來。我看看他帽子上別的徽章,上面的一行英文差點讓我心臟停跳——支持布希當選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