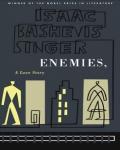第二章
二
「我也答應過自己,可是除了肉沒有別的菜。上帝自己都吃肉——人肉。沒有蔬菜,一點也沒有。如果你看到我看到過的一切,你就會明白上帝是贊成殺戮的。」
「你又來了。我並沒有真的睡著,只是覺得臉上好像蓋了一道帷幕,腦子裡一片空白。但願你不會這樣。什麼味兒?什麼東西燒糊了?」
「誰知道呢?我根本不知道你睡著了,」瑪莎說。「她在屋裡走來走去,腳步輕得跟耗子似的。這兒真的有耗子,我都講不出她和耗子有什麼區別。她整夜在屋裡閒逛,甚至連燈都不開。總有一天你會在黑暗中摔斷腿。記住我的話。」
「郵票?那倒挺有用的。裡面有郵票嗎?有的。我有一百來封信要寫,但是幾個星期過去了,我好像拿不起筆。我給自己找的藉口是家裡沒有郵票。現在我可沒有藉口了。謝謝,親愛的,謝謝。你真不該花這筆錢。嗯,咱們吃飯吧。我給你做了你喜歡的菜——燉肉和麥片。」
「你答應過我不再做肉菜的。」
「在她屋裡。她一會兒就會出來的。坐吧。」
「你接下來還要給我編些什麼?想當初,我躺在盧布林的一家醫院裡,眼看就要嚥氣了。我終於要安息了。突然她來了,把我從另一個世界裡叫了回來。你這麼不斷造我的謠,那你還要我幹什麼呢?不如死了好,倒是件樂事。嘗過死亡滋味的人不再喜愛生活。我原以為她也死了。可是我突然發現她還活著,而且找我來了。她前一天找到我,第二天就跟我頂嘴,拿話刺我,就像拿成千的鋼針刺我。假如我把一切情況都講出來,聽的人都會認為我神經不正常。m.hetubook.com.com」
希弗拉.普厄和瑪莎住在一幢房子的三樓,這幢樓的底層空著,門廊壞了,窗戶全都釘著木板和白鐵皮。門口的臺階踩上去搖搖晃晃。
「我對你做了些什麼,女兒,你要這麼說我?就是在那時你也身體健康——但願你沒有遭到別人的毒眼——而我快要死了。我坦白地告訴她,『我不想活了,我活夠了。』可是她狂怒地把我這條命拖回來。你可以用憤怒斷送人的命,但也可以用憤怒救人的命。你幹嘛還需要我呢?為了適合她的幻想:要有一個母親,就是這樣。她的丈夫里昂,一開始我就不喜歡。我看了他一眼,就對她說:『女兒啊,他是個騙子。』據說,一切都在人的額頭上寫明著,只要你會看。那些最難懂的書我女兒能讀懂,可是碰到人,她可一竅不通。眼下,她給撇在這兒坐著,一個被拋棄的妻子,一個終生跟丈夫分居的女人。」
「你是不正常,媽,你是不正常。要描寫我帶她離開波蘭時她的境況,那需要一大桶墨水。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憑良心說:沒有哪一個人像她那樣折磨我。」
「沒有,媽,什麼也沒燒糊。我媽有個怪毛病——她總是把自己做的事怪到我的頭上。她隨便做什麼飯菜都要燒糊,所以只要我做點兒什麼,她總是聞到燒糊的味兒。她給自己倒一杯牛奶,總是倒得溢出來,可是她卻警告我要小心。這一定是一種希特勒症。在我們集中營裡有一個女人,她告發其他的人,可是她告發他們的事情恰恰都是她自己幹的。這是病理變態,也很有趣。瘋子是沒有的,瘋子和*圖*書只是假裝瘋狂。」
赫爾曼向左拐到瑪莎和希弗拉.普厄住的那條街上。那裡只有幾所房子,被長滿了雜草的空地隔開著。有一個舊倉庫,窗戶已用磚砌死,大門總是關著。在一間傾圮的房子裡,有一個木匠正在做他出售的「半成品」家具。有一間空房子上懸掛著一塊「待售」的招牌,房子的窗戶已被砸掉。赫爾曼覺得,這條街似乎也下不了決心,究竟是成為這一帶的一部分呢,還是乾脆認命,聽憑消失。
列車停了,赫爾曼一下竄出車門。他奔下鐵扶梯,向前走進一個公園。公園裡草木叢生,就好像長在一片田野的中央似的;鳥兒在樹枝間跳躍、啼鳴。到傍晚,公園的長凳上就會坐滿人,但現在長凳上只坐著幾個上了年紀的人。有一個老頭正透過一副藍色的眼鏡和一個放大鏡在看一張意第緒語報。另一個老頭把褲腿捲到膝蓋上,正在暖和他那患風濕病的腿。一個老婦人在用粗劣的灰毛線編織茄克。
赫爾曼敲了敲廚房的門,瑪莎立即打開門。她長得並不高,但是她身材的苗條和昂著頭的姿勢給人一種印象:她的個兒很高。她的頭髮黑裡泛紅。赫爾曼愛把它說成是火和瀝青。她的皮膚白得耀眼,一雙淡藍色的眼睛裡閃著綠斑;她的鼻子瘦削,下巴尖尖的。她的顴骨很高、雙頰下陷。豐|滿的嘴唇間叼著一支香菸。從她的臉上可以看出那些在危險中熬出頭來的人的那股力量。瑪莎現在體重一百一十磅,但是在戰爭剛結束那會兒,她只有七十二磅。
不難看出,她曾經是個很強健的女人。邁耶.布洛克愛過她,還寫希伯來情和-圖-書歌送給她。但是集中營和疾病把她毀了。希弗拉.普厄總是穿黑衣服。她仍在哀悼她的丈夫、雙親和兄弟姐妹們,他們都死在猶太人居住區和集中營裡了。這會兒她像一個突然從黑暗裡來到光亮處的人那樣眯起眼睛看著。她舉起手指修長的小手,似乎想捋捋頭髮,然後說道:「啊,赫爾曼?我幾乎認不出你了。我已養成了這種習慣:坐下就睡著。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到天亮都睡不著,胡思亂想。到了白天我的眼睛老打瞌睡。我睡了好久了嗎?」
走了兩截樓梯後,赫爾曼停住了腳——不是因為累而是因為他需要時間完成他的幻想。如果地球在布朗克斯和布魯克林中間裂成兩半,會發生什麼事呢?他將不得不留在這兒。雅德維珈住的那半個地球會被另一顆星球帶進一個不同的星座。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如果尼采關於永恆復歸的理論是真實的,也許這種情況早在十萬億年前就已發生過。斯賓諾莎在哪裡寫過,上帝做一切祂能做到的事情。
另外一間房間的門開了,希弗拉.普厄走了出來。她的個兒比瑪莎高,皮膚微黑,一雙烏黑的眼睛,黑裡夾灰的頭髮向後梳成一個圓髻,尖鼻子,兩道眉毛長得連在了一起。她的上嘴唇上有顆痣;下巴上有好些汗毛。她的左臉頰上有一塊傷疤,這是在希特勒入侵後的第一個星期裡讓納粹的刺刀給戳的。
「看,我給你帶來了一件禮物。」赫爾曼遞給她一包東西。
車廂裡的人漸漸稀少起來;現在火車行駛在地面上空的高架鐵道上。從工廠的窗外望進去,赫爾曼看見白人和黑人婦女們在機器周圍起勁地轉來轉www.hetubook•com.com去。在一間有很低的金屬天花板的大廳裡,半裸著的年輕人正在玩落袋彈子戲。在一個平臺上,一個穿泳衣的姑娘躺在折疊帆布床上,在夕陽下作日光浴。一隻鳥兒掠過蔚藍色的天空。儘管各種建築物並不古老,但是整個城市籠罩著一種年久衰敗的氣氛。一層金色和火紅色的塵霧飄浮在一切東西上面,好像是地球進入了彗星尾。
「人人都神志正常——只有你媽是瘋子,」希弗拉.普厄嘟噥著。
「你媽在哪兒?」赫爾曼問。
「你不一定非得做上帝想要做的一切。」
「如果我想結婚,根本不必先跟他離婚。」
「一個裝郵票的盒子。」
「逾越節吃麵包跟這有什麼相干?行行好吧,媽,你坐下吧。看你那麼站著我實在受不了。她老是搖搖晃晃,我想像她隨時都會摔倒。而且她真的摔倒。沒有一天她不摔倒。」
「我不是那個意思,媽。別把這些話硬加到我頭上來。坐吧,赫爾曼,坐吧。他帶給我一個裝郵票的小盒。這下我不得不寫信了。今天我本該打掃你的房間,赫爾曼,可是我陷在其他許多事情中了。我告訴過你,做個跟其他寄宿者一樣的寄宿者——如果你不要求保持房間乾淨整潔,那你就住在灰塵堆裡。長期以來都是納粹強迫我工作,因此我無法自覺自願地去工作。如果我要做某件事,我就得想像有一個德國人正端著槍站在我身旁。在美國這兒,我終於明白:歸根結柢奴役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悲劇——要叫人工作,沒有比鞭子更好的工具了。」
「什麼?我們還是猶太人,不是異教徒。燉肉怎麼了?燉肉得在火上燒多久?肉都要燒化了m.hetubook.com.com。讓我去看看。啊,我的上帝!鍋裡的水都燒乾了。啊,你不能依靠她!我聞著是燒糊了。他們把我的腿整壞了,那些惡魔,不過味兒我還聞得出。你眼睛到哪兒去了?那些可笑的書你讀得太多了,願上帝憐憫我!」
「你得這麼做,你得這麼做。」
「聽她往下說。問問她在說些什麼,」希弗拉.普厄抱怨說。「她在說反話,就是這麼回事。這是她從她父親——他該在伊甸園裡安息了——的家庭裡繼承下來的。他們都喜歡辯論。我父親——願他安息吧——你的外祖父曾經說過:『他們關於猶太教法典的爭論是精采的,但是不知怎麼的,他們結果證明人在逾越節是允許吃麵包的。』」
「一件禮物?你不必老是給我帶禮物來。這是什麼?」
赫爾曼離開拉比的辦公室,乘地鐵去布朗克斯。夏日炎炎,人們擠來擠去,匆忙地走著。在開往布朗克斯的快車上,座位上都坐滿了人。赫爾曼緊緊抓住一根皮帶。在他的腦袋上方,一隻風扇呼呼地響著,但是扇出來的風並不涼快。他沒買下午版的報紙,於是他看起廣告來——襪子、巧克力、罐頭湯以及「莊嚴的」葬禮。火車駛進一條很窄的隧道。車廂內明亮的燈光也無法驅走那一片岩石似的黑暗。每到一站,一群群新的乘客湧入車廂。空氣中混合著香水和汗臭的氣味。婦女們臉上抹的化妝品融化了;她們的睫毛油都黏在一起,結成硬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