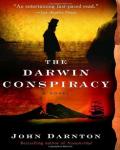第三章
「基本上算是。」
「終於受不了啦,啊?」拉烏爾提高嗓門壓過引擎的轟鳴聲說。
「我感覺自己有點陷入了絕境,」她說,「所以我來到這兒,真的,想安安靜靜思考一下。」
「因此少年時候你生活中沒有女性。」
她俯身看了一眼高高的絕壁下的大海,然後坐回身,挑起眉毛,裝出一副驚嚇的樣子。現在正是滿潮時刻,浪頭湧上礁石鑽到懸崖底下就不見了。一秒鐘後,潮水又直直的衝出來。整個小島就像是一個抽水艙。洋流湍急的遠處,浪波相激,爆裂成一頂頂白色的帽子。
「有點吧。」
「那是你父親撫養你的了?」
「我不想把那些痛苦的事情抖落出來。」
「去哪兒?」
他們談論小島、研究,然後第一次談到私人話題。他問起她的情況——以及她來島上的原因。她盤腿坐著,雙肘撐在大腿內側。
「很可能。」
第二天早上,她準備乘坐打電話叫來接她的船離開。奈傑爾也要走。他解釋說,在這種時候,他更不能離開她;如果她同意,他還會陪她回明尼亞波利斯去參加葬禮。她在帳篷裡給她父親打電話。休和奈傑爾聽見她一邊說話一邊嚶嚶的哭聲。他們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只有奈傑爾。」
「你幹什麼了?」
他哥哥不只是比他大四歲,而且在什麼方面都比他速度快,幹得好。他總是比他跑得快,跳得遠,跑的距離長。他是一個完美無缺的兒子,在學校總是得高分,在初中就當班長,每週給當地的報紙寫一篇專欄文章。在休的眼裡,他是一個永遠無法企及的標準——高大,帥氣,健壯。在棒球場上,他是無可爭議的隊長。當他一個平直球把球打到外場,圍著球壘飛奔時,休會微微側過頭去看父親那雙如饑似渴的眼睛。
「他們沒要我。後來我又申請了一次,但沒上,結果只好去了密西根大學。」
第四天,他們出去游泳,從迎客門氈跳水下去。她把袒肩露背的上裝脫下來放到石頭上。休忍住不去看她的乳|房,但她自己卻似乎渾然不覺有什麼,也不理會奈傑爾的粗言穢語。
「結了,三年前。」
「我們不能這樣,」她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說。「奈傑爾。」
「在上面時,我差點打退堂鼓了。」她說。他知道她是說著玩的。
她凝望著大海。休看著她擱在岩石架上的手,距他的手很近。她的存在是那麼真切,幾乎使得空氣都在顫抖。
他「嗯」了一聲,算作回答。
「你當時是什麼感覺?」
從遠處望去,它顯得很小,顏色暗黑,像一個燃盡了的火山獨自坐在大海中央。
「聽起來好像是他讓你失望了。真奇怪,小孩總喜歡責怪自己,似乎什麼責任都是他們造成的。」
願意,他說——隔了一會兒,他又覺得自己回答得太快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願意與人分享那個地方。
他突然間有種衝動,想要摟住她,親她。看得出來,她也有這樣的一種衝動。但她止住了他。
「他話總是那麼多,是吧?」她搖了搖頭。www•hetubook.com.com「我丈夫的確患有抑鬱症。但我們離婚並不只是他的錯,我們都有錯。」
休點燃油燈,重新生起火,並煮了些咖啡。當他把咖啡給她端去時,她淚水盈盈地抬頭望著他,說她媽媽去世了——是心臟病。她喝了咖啡,兩頰通紅,神情有些恍惚。
那天夜裡,躺在睡袋裡,他回想著白天沒有講的那諸多事情。他略去了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他哥哥是他的一切,是他那個太陽系的中心。他不僅僅是他崇拜的對象,而且是他生存的動力。母親離去後的多少漫漫長夜,把老頭子從椅子抬到床上去:你抬腿,我抬背。有時父子兩人去接晚上參加籃球訓練的哥哥。汽車在公路上一路穿梭,他常常在後排座上埋著頭,祈禱不要撞車。到了那裡,剛剛學著開車的哥哥接過方向盤,眼睛盯著往來奔馳的車輛,以每小時十五英里的速度往家裡開去。他終於放了心,突然感到有一種暖乎乎的安全感。
「我……」她的話像猜謎語一樣。「想想該從哪兒開始呢?」她向他講起在美國中西部地區成長的經歷。開始時她非常喜歡那裡,但上學後,她逐漸感到自己越來越不適應那個地方,自己就像是一個被社會遺棄了的人。最後,她去了哈佛,也是她們班上唯一一個上哈佛的學生。畢業後,她又到劍橋攻讀進化生物學研究生學位,然後在倫敦工作了一段時間。但她煩厭了那裡的生活,於是報名參加了這個項目。如今,不知不覺地,就已經是「奔三」的人了。
下來後,她靠著岩石坐在他旁邊,抹了髮箍上的頭髮,笑了。
「我不該談自己談得這樣多,」她最後說,「我很遺憾奈傑爾告訴你這麼多事。」
「你父母呢?」
他們又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她握住他的手。
「我曾經有一個兄弟,一個哥哥,但死了——在一次事故中。」
當船轟鳴著遠去的時候,他回頭看著辛農布雷島。海鳥在它上空盤旋,牠們的翅膀在陽光下閃耀,像銀色和灰色的小點在陽光下旋轉。他意識到,自己雖然在島上生活了這麼一段時間,對上面的每一塊石頭和每一個岩縫的形狀都瞭如指掌,但卻並不清楚小島的模樣。現在他才注意到它是那麼對稱——兩側坡度均勻,他覺得很像一個蟻丘。
「對。」
他心裡亂哄哄的,哪裡說得清自己到底想做什麼呢?或許他能從這次磨練中學到些什麼,能彌補過去的損失和擺脫沉重的挫敗感。但他聽到自己的回答,禁不住也吃了一驚。
他想換個話題,但又決定不換。他深吸了一口氣。
「上帝!對不起。是怎麼回事?」
他的聲音聽起來很年輕,是美國口音。
「別那麼肯定。」
「島太小了,」她回答說,「藏不了祕密。」
海鷗循著熱氣流在頭頂飛翔——在這死寂的下午,除了熱氣流,好像就沒什麼在動的了。他們走過那兩塊巨石,來到懸崖邊。他攀著岩壁往下爬。她雙手叉腰站在上面仔細地看著他手腳的hetubook•com.com位置,然後同樣一個個攀著小坑爬下去,身子在他正上方五英尺的位置。足足用了好幾分鐘才到達那個岩石架,他以前從沒注意到爬下去竟然這樣費勁。
「沒關係的。」
「真不忍心在這種情況下離開你,」奈傑爾說,「多保重,我敢肯定項目組很快就會派人來接替你的,放心吧。」
「是的。」
西蒙斯說他會的,答應了。
「沒有。」
「但你並不相信。」
「肯定很難過吧。」
「很迷惑。我對自己說,是報應。」
「沒關係,是我想知道。它們說明了很多問題。」
「是游泳事故,說來話長。」他停了一下。「換個時間給你說,現在不行。」
「你離開這裡,高興嗎?」
一個小時後,他用那部衛星電話給項目總部打了個電話,找彼得.西蒙斯。
「他是這樣,但人不錯。」
「可是……你怎麼發現的?」他問道。
「沒錯,我結過婚,在英國。真是一個錯誤。一開始我就非常清楚。我想盡量努力維持良好關係,但沒用。正如他們所說,我們湊合不到一塊兒。我們也曾有過一些快樂的時光,但卻總是夾雜著些不愉快的事兒。後來這些問題愈演愈烈,發生得也越來越頻繁。」
她轉換了話題,問起他的童年,以及這二十八年來的情況。
「緊急線路急線,」他用研究者的行話說。其中一個要求是:立即撤離——沒問為什麼,或者至少說提問很少。但西蒙斯的確提了一個問題:你打算做什麼?
「我想沒什麼好說的。我是在康乃狄克州的菲爾德縣的一個小城鎮裡長大的。小時候我特別喜歡周圍的郊區——到林子裡去野營,參加少年棒球俱樂部,到沙灘上去遊玩,如此等等。後來我到安多佛去上預科學校,開始成績還不錯,後來掉了下來。臨畢業大約一個月時,我被開除了……」
休終於進了球隊,但大多數時候都只能坐冷板凳。偶爾會安排他打右外場。他孤零零地站在偌大的草坪上,每次投球前他都要摸一摸他辟邪的兔後腳:上帝,千萬別讓它往我這邊來。如果投過來,如果必須要過來,求祢保佑我接住。有一次,他答應幫哥哥送報。但袋子裡的報紙太重了,一騎上去就倒了。他試圖把報紙塞在車座下和車軸四周,但仍不管用。球賽就要開始了。他感到很慌,就把車丟在灌木叢裡,最後把它忘得一乾二淨。「感覺怎樣?」哥哥問。休一臉驚惶。後來他們摸黑找到了車子。父親搖著頭開車送他們去把報紙投送了。這類的事情已不止一次了——他感到心情糟糕透了。
他還談到他的父母。他父親是紐約一位頗有成就的律師;母親愛上了另一個人,在他十四歲時就走了。
「英格蘭。」
「我得走了,」她說,「馬上。明天。」
貝絲帶了一大疊書來。她選了一本給他,是W.G.辛巴達的小說。天
hetubook.com.com太熱不上班時,他就帶著書到那裡去消磨漫長的下午時光。微風起時,他這裡還能吹到。有時,他一面讀書,一面思索,還不時地抬頭望著寬廣的大海和雲朵在水面灑落的巨大影子——形成大片大片移動著的暗綠、深藍和黑色水域,他的心境幾乎臻於一種平和狀態。「哈佛那邊呢?」
他心裡想,還有好多好多事情呢。
「我想,開始是這樣吧。她走了兩年後就死了。她和那個男人住在一起,正打算結婚,突然就這樣死了,是動脈瘤。剛還坐在床上梳頭,一轉眼就死了。」
「我能理解——嘈雜,汙穢,還有人太多。」
「是的。」
第三個星期的第一天早上,貝絲問休是否願意帶她到他的「藏身之處」去。
「聽說你結過婚。」他說。
「我打算去攻個學位,」他說,「不是野外考察,而是做研究,也許是達爾文吧。當然得靠你的幫助——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也是。」
他們很信守諾言,派了一對渴求知識的學生來,一男一女,都才二十出頭。休帶著他們看了所有他認為他們有必要知道的東西。起程的早上,他來到小島北端,在那塊岩石架上靜靜地坐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然後草草地打理行裝——只有一個帆布袋,裡面基本上裝的都是書。兩個學生送他走下小路,從門氈把袋子遞給他,揮手與他告別,看上去很高興能單獨留在島上。
「因此你就去上預科學校了,」她說。
接下來的整個上午,他們都在一起工作,查看鳥蛋。她把細繩拴在樁上,在泥地裡圍出一塊方地,再用篩網把泥土打理了一遍,然後對照一本手冊對鳥蛋進行鑑別,最後把它們擺在一張白布上。旁邊的休則在日誌上作記錄。工作中,他們很少說話——像一對老夫婦,他默不作聲地在屋後園子裡忙來忙去。太陽越來越熱了,像一片火直撲而下。汗水使得他的軀體非常光滑。他用拇指在腰間一搔,就留下一條濕漉漉的泥土的痕跡。貝絲站起身,伸了個懶腰,又背對著他蹲了下去。她的短褲褲腰繃開,他能看見汗水順著她的背溝流了下去。在火一般的太陽下,他聽到血液在他腦中汩汩地流動聲。
研究項目進展的速度也快些了。他們兩人一輪,一個捕鳥和測量,另一個人負責記錄。貝絲很善於和地雀打交道,她沉著的舉止似乎對牠們很有吸引力。牠們在她的手裡一點也不掙扎,有些甚至在她鬆開手指時仍然不飛,還站在她的手心前搖後晃地以保持平衡。奈傑爾開始叫她為「聖弗朗西娜」。
「相信肯定會的。」休回答說。但是他關心的根本不是這個事。
「你到這兒來的原因——茫茫大海中的一個孤島,隻身一人——至少在我們來之前是這樣。」
她嚇了一跳,盯著他的眼睛。「奈傑爾跟你說的。」
十點的時候,船來了。她俯身在休臉上吻了一下,悲傷地笑了笑。他擁抱了她一下,然後幫她把設備沿著小路搬下去。在迎客門氈,他和奈傑爾握手告別。似乎幾分鐘的工夫,他和圖書們就消失了,連頭也不曾回。跟著船出去的海鷗飛了回來,又盤旋在小島四周,尋找魚蝦。
「是的。」
「我就乘火車回去了——那是我人生中走過的最漫長的一次路途。當我灰頭土臉到了家,我父親幾乎看都不看我一眼。」
「回到文明社會前,要修鬍子嗎?」
在島上接下來的幾天裡,他們的生活走上了正軌。他們對日常雜事和野外作業都進行了分工。休不得不承認,多了兩個人,擔子輕鬆多了。他們輪流做飯——結果證明,奈傑爾最擅長此道,最會擺弄各種調味料——以及洗公用物品。第二天輪到了休,他把一小捆衣物提到門氈。他沒有用洗滌劑而是直接用海水浸泡,然後再在塑膠盆中用清水清洗。讓他覺得很好玩的是,裡面居然有兩條白色女內褲,又小又薄,棉質的襠部非常狹窄。晾曬衣服時,他把兩條內褲放到最高的一塊石頭上,在太陽的照射下,白光閃耀。
午飯後,他們出發了。奈傑爾待在他的帳篷裡做清潔工作。他曾做了一個用電池帶動的小風扇。他把收音機調到英國的BBC電臺——收音機裡播放著恐怖主義、政治和非洲的愛滋病等新聞——好似來自另一個世界。
「你的到來令我很高興。」
「他後來結婚了嗎?」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
衛星電話一個勁地響起來,真煩人。他好一陣子才從沉迷的思緒中回過神來,拿起電話。過了好半天,對方才傳出一個微弱的聲音。「請找貝絲.達爾西默。對不起,這麼晚給您打電話,找她有急事。」
「說來聽聽。」
這是一個陳述句,不是問句。真奇怪——以前他從沒想到這些。
大多時候,休都只穿一條短褲和旅遊鞋。他身上的肌肉柔韌有力,皮膚呈古銅色。奈傑爾則穿著百慕達短褲和薄質的白色T恤。汗水很快就浸濕了他的衣服,顯出他肉紅的大肚囊,他體形龐大,走在亂石間,樣子很難看。晚飯後的傍晚時分,他最喜歡的莫過於坐在火堆旁閒聊了。休看著貝絲,不確定她到底在想什麼。有一天夜裡起來撒尿,他抬頭看見她在奈傑爾的帳篷裡。油燈下,他們的影子映在帳篷上。他看見他們蠕動起伏的曲線側影,他趕緊轉身走了。
「他們還在明尼亞波利斯,都是教師。我們一直都有連繫——至少在我到這兒之前。我們關係很親近。」
孤身一人,讓人覺得怪怪的——既奇怪又熟悉。但他沒有恢復往常的工作程序——甚至連捕鳥網也沒有架,而是坐在他那塊石頭上,遙望著大海。獨居的安寧被打破了,而且他知道永遠打破了。他不可能再若無其事地過下去了。
「你說過嘛,他話很多。」
「這就是你躲避現實的地方了?」她說。
他想了想這個問題。這是最難回答的。「他非常慈愛,但有一點疏遠,我想。他以前經常酗酒,現在已經戒了——但……我也不知道,他大部分https://m•hetubook•com•com時間都一個人待在自己的房間——夜裡,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我從來沒法與他坦誠地交談,從來不能給他講我的感受。我覺得自己總是讓他失望,讓他臉上無光。」
休迅速穿上短褲,拿著手機,越過營火,光著腳在石頭間往前摸。營火的餘燼還在閃爍。他掀開她的帳篷簾子,低頭進去。她馬上醒了,睡眼惺忪地從睡袋裡坐起來,看著他,先是一驚,接著淺淺地一笑,顯然是誤會了他的意圖。他作了解釋,把電話遞給她,然後走了出去。他能聽到她的說話——聲音富有情感而緊張——接著聽到她哭了起來。奈傑爾從黑暗中衝過來,鑽進帳篷問道:「怎麼回事?怎麼了?」
「來啊休,我們來玩接球。」後院中那青草修剪過的味兒,夏日黃昏越來越暗的影子,蟬悠揚的鳴唱。他們來回地投球:滾地球,小騰空球,擦線球。「來一個難度大點的,扔過我的頭。」他起身飛跑,轉過身,扭頭看著球,然後一個衝接球。每次球都穩穩地落在繫在他手上的皮套裡。「第九局後半局,滿壘,開始投球……長傳騰空球……他能接住嗎?……退……退……接住了!美國佬全勝。側面退場!」
奈傑爾火氣越來越大。如果實在看不下去了,休就閒逛到島嶼的北邊去。他把那看作是世界的盡頭——在那裡,他能逃離紛擾,獨得一隅。那地方是他四個月前追一隻狡猾的地雀時發現的。他順著一邊是乾枯的灌木叢、一邊是枯萎的仙人掌的小路一直追趕。路的盡頭有兩塊巨石,前方是一條通向懸崖下面的天然小徑。他仔細地查看小徑上可以立足的地方,發現居然能夠下得去。他下行了約莫三十米,到了一個大約兩碼寬的岩石架上,下面是一面絕壁。高高的絕壁下面是波濤澎湃的大海,波浪在岩石間激盪著洶湧的浪花。
「我想到其他地方去。」
「奈傑爾說你丈夫有抑鬱症。」
「老兄,氣色不錯呢。」
他們打算回去了。在崖頂上,他伸手把她拉上來,說:「歡迎回到現實中來。」
「你跟你父親關係好嗎?」
她瞟了他一眼,微微皺了一下眉。
聽到這話,他吃了一驚。他也驚訝地感到自己心中升起了一絲希望。在島上的日子還不算白費,也沒什麼感到恥辱的——不管怎麼說,當其他人都放棄了的時候,他卻堅持了下來,是他讓這個研究項目保持了下來。
他身子忍不住顫了一下。「沒」——就一個字。
「有兄弟姐妹嗎?」她問道。
早上,雖然奈傑爾忙著做了些甜餅,但她吃得很少。她面色蒼白,看上去很憔悴。但休卻覺得——雖然有種強烈的罪過感,她悲傷時顯得越發漂亮了。
「我覺得你心裡憋著太多的不幸。」她說。
「沒啥大不了的。學校有一個什麼五大規章。一個週末,為祝賀自己考上了哈佛,我全給趕上了——擅自離校,酗酒。他們還逮住我撒謊,因為我簽字說自己回寢室了。最齷齪的是第五條——行為有失紳士作風——他們給我強安的罪名。我提出了異議,但沒什麼結果。」
「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