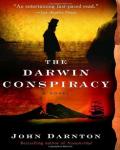第十七章
一八七一年八月六日
我的手開始顫抖。我瞧準機會瞧了一眼爸爸,他並沒有注意到我的焦灼之態——他正在給他的書做關於人與動物的面部描述的筆記。我又看了一眼爸爸的素描像,還有另外一個人站在一棵樹邊。那個人是麥考密克先生。現在我已經抓住了此畫的重要意義所在了——若是他能在審訊中作為呈堂證供的話,它會推翻被告當時不在場的托詞,從而為其定罪。
我唯一可以袒露心事的人是瑪麗.安.艾文思。但是,唉,我已經好幾個月沒見她人了。並且,即使是對她,我也不會說出他的身分。
一八七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X闖進我的生活已經有一個月了,是艾蒂在韋奇伍德遇上他並把他邀請到唐豪斯來做客的。我與他如此相像,我們對於人的本質和進步政治都持相同觀點。像他一樣,我支持改革法案,因為我相信擴充選民是維護民主、清除階級間不平等的唯一途徑。我贊成他對一個烏托邦式的未來的遠見。我可以一直聽他談論幾個小時。雖然我不認識他擁護的所有思想家,比如托馬斯.休斯和弗農.盧士頓,但我讀了約翰.羅斯金的著作。X跟他很熟。在政治觀點上,X比我更激進。不過,我確信我多學點知識也會把自己提升到他那種水準。他對法國正發生的事情表示同情;它承認巴黎公社已經發展到難以控制的地步,最終以「流血週」的悲劇收場,但他說工人們的起義並沒有白白付出。我想他真是聰明絕頂,令人欽佩。
一根樹枝橫在路上,這可是個大障礙,他先跳了過去,然後轉身握起我的手,幫我跳過去。然後他沒有鬆手,一直緊緊地抓著我的手。我感到了他的手指的力量,一股難以承受的愛慕之情深深地打動了我,很快他鬆開我的手,把手滑向我的腰部,把我攬得更靠近他。散著步,我感到他的腿總是碰著我的腿。這一切都在默默無言中進行。如此平靜,就像是世界上再普通不過的事情。然而,我不覺得平凡,我內心深處上下起伏,難以呼吸。
我立刻想起另外一番關於華萊士先生的對話,那也是幾年前偷聽來的。他知道些什麼呢?——居然威脅說要抖出來——重要到要用錢來堵住他的嘴?
爸爸的病情不會成為社會的恥辱。因為近幾年來,他不僅不再是社會的棄兒,而且成了大眾崇拜的對象。他聲名鵲起,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他的自然選擇學說(現在叫進化論)已經被人們接受。最明顯的變化是來自教會的攻擊也逐漸減弱。一年前牛津大學授予他最高榮譽,郵差每天都給他送來一疊疊來自世界各地的信件。總之,他現在成了富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甚至為那些反對他的人所敬重。也許是因為他已經六十二歲,德高望重,又或許他和他的圈子為了宣傳他的學說進行了有效的活動,反正他已經成了國家的知名人士了。
有一段時間我不願意說話。查普曼醫生說我是「精神疲勞」。於是我被送往歐洲大陸,希望換個環境能有助於我的康復,因為那時我已經病得很重了。自然,就像我以前提到的,我不能說出我病倒的真正原因——那就是,我開始懷疑爸爸並不是我們平常所見的那麼一個人。我去了德國,住在巴登─巴登。那裡清新的山谷之氣和輔以治療的山泉水使我的心漸漸地恢復了寧靜。我在那兒待了將近三個月,直到喬治來把我接回唐豪斯,大家為我的回家而歡慶,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帕斯洛最為感動,幾乎流下淚來),我也裝作一副享受的樣子。在國外的時候,我已經做了一個決定,並且告訴了我的家人:我要重新開始,不再用莉齊這個名字,取而代之的是貝西。他們對此有些困惑,也花了一些時間來適應我的決定。傭人們是最先叫我的新名字的,然後是媽媽和我的兄弟們,最後是艾蒂和爸爸。
https://m.hetubook.com.com
我們很快發現自己已經走進了林子裡。樹木給小路遮上了陰涼,他問我冷不冷。雖然不冷,我還是回答了「是」,他溫柔地脫下夾克,披在我肩上,輕輕地觸摸它們,我覺得自己的血液都沸騰了。我們走進樹林深處,雖然都是很高的橡樹,出於某種原因,我總是想起果樹,還有小妖精的叫賣聲:「來買我們的果子,來買!來買!」
我戀愛了。天啊,我陷入情網了。我滿腦子都是他,整天都想跟他單獨相處,夢裡也盡是他的身影。不論我走到哪裡,我都能看到他矯捷的身影,英俊的面容,還有那雙充滿柔情的棕色眼眸。我能聽得到他溫柔低沉的聲音,感覺到他在看著我。這一切讓我的臉一直紅到耳根。我多想終其一生,陪他白頭到老,而他好像並不知道我已為他神魂顛倒。
一八七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儘管我發誓不再這麼做了,但我還是沒有完全放棄弄清楚《乘小獵犬號環球航行》發生的事,還有讓爸爸痛苦的潛在原因。我沒有特意去尋找答案,但一旦它們進入我的視野,我會馬上抓住它們展開調查。我想生活就是這樣的:當一個人準備放棄努力的時候,他往往就會實現一個目標,我的偵察就是這樣。
生活是多麼不可捉摸!命運總是與我們開玩笑!
「他的做法很顯而易見,」赫胥黎先生說,「直截了當地說吧,如果得不到這筆錢,他就要說出一切。」
要離開時,他在門廳裡輕輕地碰了碰我。我不知道這是他故意的還是只是一個巧合。他的手碰了碰我的胳膊內側,一股觸電的感覺頓時傳遍我的全身。我確信他注意到我那時有多麼慌張。我的臉頰一下子變得通紅。他吻我和艾蒂的手時說他會再來的,我看到媽媽站在他背後露出會意的微笑。
多麼巧啊!僅僅是兩天前我還寫到線索總是在不經意間到來,今天下午我就發現了一條最為重要的線索。
爸爸的身體還是沒有什麼起色。他一直在用約翰.查普曼的冰敷療法;他一天幾次把冷水袋紮起來放到脊背下部,凍得牙齒咯吱咯吱響。他看起來那麼滑稽可笑,像隻大笨熊一樣在房子裡走來走去,要不就躺在床上哼哼,那療法也沒起什麼作用。
不再寫了,這麼做只會讓我心情更加憋悶。我袒露了自己的心扉,這麼做了。
將近六年不寫日記了(這是多麼令人不快和失望的六年啊!)現在又重新拾起來,還真有些奇怪呢。我本不必再這麼做,尤其是放棄了這麼久後,但強烈的感情就像旋風一樣猛烈地席捲我的心靈。痛苦與快樂並存,使我備受折磨。有時我都覺得自己的心已經承載不了這麼多了,它就要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而我則不堪重負,摔倒在地,讓所有人猜想:這個可憐的少女怎麼了?是什麼讓她在如花的年齡就此凋謝了?我有種抑制不住的衝動,要袒露心扉,把我內心深處最隱秘的想法和欲念都說出來,那麼就可以如釋重負了。但是,天哪,沒有人,沒有任何人可以做我的傾聽者,我找不到一個可以傾吐祕密的人。
晚上我失眠了,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安睡。有時我覺得從花園裡吹進的暖風讓我大汗淋漓,那風裡帶著金銀花的香味。我不想承認,我有一些奇怪的想法,還做了一些特別精采的夢。最近我總是在睡覺前讀《妖精市場》。這使我升起一種難以言喻的情緒。那個長相醜陋的小妖精所反覆吟唱的「來買我們的果子,來買,來買」總是縈繞在我的夢中。夢裡還有熟透了的柑橘、草莓和梨子,全都滴著果汁。
分手時,他提議明天我們老地方再見,再在一塊兒「散步」。他那樣看著我,毫不掩飾別有用心的企圖。我當然答應了。他一直凝視著我的臉,弄得我滿臉通紅。我形容不出他以後的眼神,看起來不像是愛情的流露——相反的,它讓我感到難受。
啊!——我都說出來了,把我的祕密付諸筆端了。可這並沒有給我https://m.hetubook.com.com帶來如釋重負的感覺。就是在日記裡,我也得小心翼翼,不敢寫出他的名字,更不敢透露他的身分。命運把我們聚在了一起,就像蓋茨凱爾夫人的小說中的戀人一樣,我多想寫下他的名字,哪怕只是首字母也好啊,這樣我就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閱讀,玩味,可是我不敢,唯恐落到什麼人手裡去了。我就叫他X吧。甜心X,最最親愛的X,我全身心地愛著你。這些措辭看起來多麼老套——噢,比起心中的熱望與激|情,語言是多麼蒼白無力!
為了傳播他的學說,他的做法很聰明。他從來不和對手直接對抗,而是採取迂迴戰術,自己擺出一副通情達理的姿態先來消除敵意,而後發動同盟團去說服對方。他措辭靈活,比如,他經常打個比方來化解爭辯。如果有對手嘲笑他居然認為我們的祖先是猴子,他會堅決否認,說他只不過認為人類和猴子有一個共同的祖先。然後他會解釋何為「生命之樹」。他是這樣描述的,最簡單的生物位於最底層,而最複雜的動物位於最高層。物種不斷變化,形成不同分支,差異最大的離得最遠,就這樣,他理論的精華直擊問題的要害。
X並沒有停止,他又一次吻我。這一次我回應了他,手搭到他的脖子上,讓他的臉更近些。他的手在撫摸我,我不知該怎麼辦。他又吻我,如此長久,我都快暈過去了。他的手又游離到我身上來了,不肯拿開。最後,我還是把他推開了。他臉上露出很奇怪的神情——幾乎是憤怒,要是我那時碰巧遇上他,幾乎都認不出他了。他讓我躺下休息一會兒,但我拒絕了。過了一會兒,我們開始聊天,東拉西扯些瑣碎的小事——我記不起都聊了些什麼,我的思維一片混亂——而我們兩人都裝作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
今天早上當我獨自出去散步,走過一片陽光照耀的草地時,看到一個男人正穿過一片小樹叢,神情若有所失。當時我是多麼驚訝!越走越近時,那身影看起來多麼熟悉。當我認出那是誰時,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是我的X!在我認出他的那一刻,他也看見了我,同樣驚訝的表情——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還有一些高興。他很快跟我走到一起,並肩而談,我才知道我們的邂逅不是巧合,他早知道我們家要到格拉斯米爾度假,所以就在附近的村舍也安排了一個住處。那一刻,我感覺幸福得要死,但我還是小心地藏起了自己的狂喜,低著頭。他問我其他人什麼時候來,我告訴他後天。這時他抬頭看了看湛藍的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幾乎像在嘆息。
我從沒向她吐露我向無神論的轉變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對爸爸的感覺。我總懷疑在《乘小獵犬號環球航行》中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也許就在大火之夜——這個想法使我堅信他因做了什麼錯事而內疚,那種感覺使他脾氣古怪,也越來越痛苦。當看到爸爸對菲茨洛伊之死的反應時,我的疑慮更加深了;他似乎不覺得傷心,而好像卸下了一副重擔似的。葬禮一結束我就看到赫胥黎先生拍了拍他的背,並偷聽到赫胥黎說:「好的,整個悲劇告一段落了,我也不用再付薪水給那個氣象員了。」我覺得這是我聽過的最殘忍的一句話。
幾年前,我聽說赫胥黎先生創辦了一個祕密俱樂部,叫「X俱樂部」(之後,一聽到這個名字,我就想起我的X先生)。俱樂部有幾個著名的科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比如胡克,斯賓塞,盧伯克,布希先生。就我所知,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深入到皇室和科學界的當權派裡,為爸爸的思想傳播建立一個灘頭陣地。昨天,四位俱樂部成員來唐豪斯過週末。聽他們飯後的商談時,我吃驚地發現,他們來的一個原因是為可憐的阿爾弗雷德.魯塞爾.華萊士先生籌錢,他時常陷入財務困境。我知道他們正在向政府施壓,希望能讓華萊士先生得到二百英鎊的撫恤金,現在看起來華萊士先生正在索要這筆錢。
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二日
和圖書
一八七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今天下午三∶十五過來拜訪我們了,從倫敦一路騎馬過來的。我們正忙著接待客人(雷維特恩夫人,一個煩人的傢伙)時,他留下了一張卡片,放在門廳的桌子上。我偷著跑去瞥了一眼,心怦怦亂跳。讓我高興的是,他揭開了一角,上面標示他是來拜訪我們幾個女兒的,而不僅僅是媽媽。沒見到他我有點難過,但至少為他不用陪雷維特恩夫人苦著臉一直坐著而慶幸。
他建議我們停下來休息一會兒,我點點頭。令我吃驚的是,他自己開出來了一條路。我們又握起了手,除了跟著他,我別無選擇。真的是這樣,在那時,我變得毫無主見,只願跟他走下去,不論到哪裡。我們低著頭在樹枝下前行,走了一小段路,我們來到了一塊房子大的空地上,四周由高大的樹木圍起來。中間的草地上有片陽光灑下來。他從我肩上拿下茄克,鋪到地上,叫我坐下,我照做了。很快他在我身邊坐下來,在我還沒反應過來時,他突然轉身抱住我,貼著我的唇,給了我一個深深的吻。我頓時渾身癱軟。我想推開他,卻並沒認真用力。他也似乎看出我的反抗是裝出來的。事實上我並不想讓他停下來。那一刻一種很奇怪的念頭闖進我的腦海——我記起多年前在乾樹杈上吻盧伯克男孩時的情形。我覺得像那時一樣,我熱血沸騰了。
《物種起源》很快就出了第六版,這讓約翰.默里著實高興了一下。這本書差不多已經被譯成了歐洲所有的語種。但爸爸對法語版的譯文不太滿意,他覺得那裡面把他和拉馬克拉得太近了。在過去的兩年裡,他一直在寫他的「人之書」——《人類的起源》。這本書終於在上個月出版了。書中把人與動物間的進化鏈分析得更清晰,這是他以前不敢做的。艾蒂幫他校訂手稿,在頁邊空白處寫上她的建議。像以往一樣,她的修改讓結論變得含蓄,也刪減了不合適的地方,她就像一個老女僕那樣工作和思考。
我不敢說X對我的感情有所回報,但我有時候覺得他是喜歡我的。昨天晚上他來唐豪斯吃晚飯,飯後大家來到客廳,他彈琴,我為他翻琴譜。這時我感覺他正從眼角看著我,接著他朝我笑了笑,這弄得我簡直滿面通紅,耳根發燙。我的心怦怦猛跳著,真怕音樂一停下來他就會聽到,那我的心思就敗露了。他充滿激|情地彈奏著——我可以看到他的手指彈壓琴鍵時,那隆起的肌肉。然後他又拉起了手風琴,唱起了牧歌,艾蒂彈著鋼琴為他伴奏。
爸爸正準備寫個自傳,讓我幫他準備,於是在他的允許下,我看了他的研究中的一疊稿紙。爸爸坐在房間另一側的皮椅中,想想看,當一張素描自《乘小獵犬號環球航行》的資料中掉出來時,我是多麼的驚訝吧!那是康拉德.馬頓斯畫的,他是船上的畫家。看著畫,我立刻被畫面上的一個錯誤給驚呆了——剎那間,這幅素描揭穿了爸爸所說的關於那次致命的《乘小獵犬號環球航行》的一切都是個謊言。
明天一早我將帶著霍普一起出發。
我的生活,我是指表面上的,還像我上次合上日記時那麼平淡無奈,沒有變化。我現在二十二歲了。氣象室裡那件令人震驚的事件和菲茨洛伊那令人恐怖的死亡對我影響至深。我總覺得這事我也難辭其咎,我們的面談傷了他。為此,我的健康急速下滑,我垮掉了。幾個星期來接連不斷地痙攣,我食欲全無,瘦弱蒼白,連緊身胸衣也不需要了(雖然我並不想出去逛,絕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
我成功了!但為什麼我不為此而欣喜,反而覺得內心很空虛呢?答案不難猜:現在我已經弄清楚了那臭名昭著的「大火之夜」發生了什麼了——爸爸是一個冒名頂替的偽君子。他偽裝的本事可比我強多了。真可恥!我現在可以了解這些年
www.hetubook.com.com來嚴重損害他健康的那種負罪感了。之後,我和艾蒂都有點神魂顛倒。我們談起他,她說喜歡他那棕色的大鬍子,她微笑著說他在很多方面都使她想起爸爸,不僅僅因為他對工作的熱忱和他的理想。我不敢談論他太久,因為怕我顫抖的聲音會出賣自己。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一日
一八七一年八月八日
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五日
為什麼在證實了自己的懷疑後,我感到如此地傷心呢?我知道在一定程度上我希望自己的猜疑都是錯的。在我內心深處,我多麼希望爸爸就是世人所公認的那樣,是一個偉人,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是一個把自己的名譽建立在流沙之上的騙子。呸!我真不知道我該怎樣看著他而不流露出厭惡的情緒——用這個詞來形容我現在對他的感受一點兒也不過分。
後來我查了他的賬本,在「家庭雜用開支」一欄中他記下了當月的總數,以前他總是討厭使用這一欄的。
多麼令人愉快的一天!我與X一起度過了整個星期天。他為工人大學組織了一次短程旅行,去肯德林屯村周圍的郊區呼吸新鮮空氣。他邀請我和艾蒂同去。我們度過了最愉快的一個早晨,在小路和山間小路間穿行,中午在一間客棧吃了午飯。在回程的火車上,我們一首接一首地唱歌——X有一副低沉的男中音——這讓我們喧鬧而又快樂。還有一個人會把手放在嘴邊,發出鳥叫的聲音,還會吹口哨,這讓大家開心極了。
我們全家決定要去湖區待一段時間,那兒已準備好了一棟村舍。我以幫霍普.韋奇伍德收拾村舍為由,提前五天到了那兒。只有我們倆,再加上幾個傭人,那麼,我早上溜出去跑到北邊去拜訪R.M.一家就是輕而易舉的事了。我知道R.M.是揭開整件事的關鍵所在。我是上星期聽到他的名字和華萊士先生的名字被一起提及的(就在聽到華萊士敲詐案的同一場對話中)。我在爸爸的舊紙堆裡找到了這家人的地址,在去之前給他們先寫了封信,當然沒有說出拜訪的真正目的。我請他們把回信寄到格拉斯米爾的村舍裡而不是家裡。我記得爸爸曾批評我是個「間諜」,不過他還不了解我幹這個是多麼內行。
雖然未經允許,我還是讀完了手稿。爸爸的「性別選擇」理論引起了我的注意:它解釋了個性特徵的持續性決定了人和動物怎樣選擇他們的配偶,還講述了種族之間的差異性以及為什麼在歐洲我們是最先進的。他聲明男人在智力上要優於女性。有一點令我不安的是:他認為在最文明進步的社會中,是男人選擇女人,而不是女人選擇男人。我覺得這很令人沮喪——這種觀念把女人當成了一種沒有意願,沒有思想的被動的容器。我已經聽到有許多女人私下裡在談論這一點,想搞清楚這種斷言到底有多大說服力。而我在與我的朋友瑪麗.安.艾文思聊天的時候,也就此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如果爸爸能夠讀懂我的心,如果他能看到當X走進房間時(當然我早就候在那兒了)我心中那激|情澎湃的愛戀之情,他肯定會轉變他的觀點的。
素描畫又一次激發了我的好奇心,促使我再一次展開調查。我策劃了一個大膽的計劃,這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一定要把這個祕密徹底地挖掘出來。真是不可思議,事情好像正在朝我設計的方向發展,我堅信命運之神站在我這一邊——也許天神們最終決定要把四十年前的那個黑幕揭開。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機會正向我展開笑顏。只有這次我們才能單獨待在一起。在他身畔而沒有其他人在場,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而這可不是我故意安排的,除了散步,我再不想其他,只有好運來做我們的嚮導。而我可愛的天使甚至密謀把霍普留在了村舍。雖然有些亂七八糟的想法,但我知道我不能久留。我應該做一個禮貌性的問候,然後立即返回村舍——這個念頭,不知為什麼,使我們的相遇更hetubook.com.com為刺|激。
音樂停止後,他和爸爸討論起了性別選擇說。X的話讓爸爸非常興奮——他說他經常思索動物何以會以歌聲來追求異性。可以看得出爸爸把這些都默默記在心裡以備日後之用。X還說他覺得人類也是如此。他這麼說時,我總覺得他在朝我看著。
最後俱樂部成員達成了一致意見。爸爸自己說他要跟華萊士先生談一談,措辭小心地告訴他無論如何不能「謀殺了我們的嬰兒」。
一八七一年六月十日
我知道我該做些什麼。就像藏我的日記一樣,我用了同樣的手法——藏在最普通的地方。這在我童年時玩的捉迷藏遊戲中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我要把它藏在房子的中心部位。那兒有塊鬆散的木板,沒人知道的,是個藏東西的好地方。
一八七一年八月二日
回程車上,我神思恍惚。現在該怎麼辦?在我發現了父親的劣跡後,我還能面對他嗎?
但心情一點也沒有放鬆。
但事情終歸是發生了,我想我永遠也不會再是以前的那個我了。但我甘之如飴,如夢如幻。
祕密其實並不難揭示。R.M.一家回信說歡迎我光臨。雖然他們表示對我此行的動機很好奇。在肯德爾轉了一次火車,只用了兩小時多一點我就到了他們家。他們住在鎮子中心的一座小房子裡。女主人兩年前去世了,享年七十五歲。R.M.在國外未歸,房子就被兩個遠房親戚接管了。雖然他們都是同一個姓,但他們之間以及和R.M.的關係我一直沒搞明白。他們熱情地接待了我,還給我端上茶和點心。我表明了自己的來意——我是奔著他們的親戚來的,想問問他是不是給他們留下了什麼文件或紀念品之類的東西——他們對我的要求很是熱心,一個到閣樓上去翻了半個小時,回來時拿著一疊用黃絲帶紮起的泛黃的信件。他說R.M.一家一直保存著他從國外寄回的信。幾十年了,他很高興能找出來供我細讀。這對表親看起來對R.M.的小獵犬冒險之旅極不感興趣。我發現他們從沒讀過這些信,而且他們實際上並不了解和關心他。他們也不了解我父親的研究,因為他們沒有問我任何關於他的問題。在當今的社會背景下,這是很不正常的。他們當然也不知道其中有封信包含著至關重要的信息。我自然不會告訴他們,也沒有在讀到它時表露出任何吃驚的表情,就像看了一張白紙一樣,把信還回去,然後看著那個表親又把它塞回信劄裡繫好。
現在是晚上了,我躺在床上寫下這些,今天一整天我都處於迷惑與興奮的矛盾心理中。我愛他,相信他也愛我。我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但我敢確定一件事:不管發生什麼,不管我的激|情讓我做出什麼,我絕不會做將來會令我後悔的事。
我們離開了那片空地。這次他把手搭在我身上,我感到很自然。他開始興高采烈地高談闊論,還親熱地叫我安琪兒。我喜歡這個稱呼,雖然那不是很常用,但我當時真覺得自己就是個天使。
我也不再去教堂了,成了個無神論者。這讓媽媽甚為苦惱,她不停地催我去參加禮拜,又為我祈禱,希望我能追隨「上帝的恩典」。我第一次為拒絕堅信禮而跟她發生爭吵時,她氣得掉下淚來,她讓我說出緣由,而我忘乎所以,大聲嚷嚷,說我不相信三位一體,不要洗禮,更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她當時被我嚇得啞口無言,急轉身回房大哭去了,我想她覺得我們家現在出了兩個無神論者,另一個當然就是爸爸了。
我飛快地把素描夾在兩張空白紙中間,再把他們偷偷夾到一本書裡。然後我告訴爸爸我想休息一會兒——這個藉口他總是會很快答應的——接著我離開了去研究這個重要線索。我回到臥室,把書放在床下,那不是個藏東西的好地方,女僕肯定會發現的。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