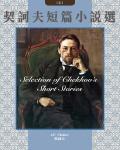05、藝術家的妻子
——譯自葡萄牙文
「您有什麼事?」他問她說。
津扎加堵上耳朵,像瘋子一樣逃出第一百零一號房間。他回到自己房間裡,卻看見一幅扣人心弦的畫面。他的阿瑪蘭達靠桌子坐著,在謄清他的中篇小說。她的大眼睛裡淌下大顆淚珠,滴在草稿本上。
卡羅麗娜搖著手,在房間裡跑來跑去,彷彿深怕人家硬要剝光她的衣服似的。
「我氣壞了!」布特隆察叫道,「您設身處地替我想一想!您知道,我已經聽從巴拉班達.阿里蒙達伯爵的建議,著手畫一張大幅的畫。——伯爵要求我畫《舊約》的蘇薩娜。——我求她,喏,就是這個日耳曼胖女人,脫|光衣服,做我的模特兒,我從大清早起就求她,時而跪在她面前,時而發脾氣,可她就是不肯!您設身處地替我想一想吧!沒有模特兒,我能畫嗎?」
「她對巴拉班達.阿里蒙達伯爵的出版工作,對阿爾豐索.津扎加的勞動成果,多麼不尊重!而他卻給了她津扎加這個光榮的姓!」
「可是你今天早晨臨走時對我說,你今天在《里斯本省新聞報》的主編那兒吃飯,不是嗎?」
椅子喀嚓一響。津扎加站起來,開始走來走去……他走一忽兒,思索一陣,生出極其強烈的願望,打算無論如何要叫自己相信饑餓是懦弱的表現,人生在世是要跟自然搏鬥,不單單是用麵包填飽肚子,誰不挨餓誰就算不得藝術家,等等。他本來也許真就說服自己了,可是偏巧他在思考中想起隔壁的鄰居,「毒天鵝」第一百四十八號房間裡的義大利風俗畫家福蘭切斯科.布特隆察,一個有才能而且有點小名氣的人,想起他有每天弄到飯吃的本領,這種本領在人世間絕不能說不重要,可是津扎加卻從沒學會過。
「我們沒計算氣體,因為科學還不能確切地規定我們所需要的氣體數量。坦涅爾勝利了,然而為時不久。在婚後生活的第四年,有個想法開始煎熬他,那就是坦涅爾太太所吃的蛋白質營養品太多了。他就越發出力訓練她,要不是他覺得不再愛他的妻子,他也許就會達到目的,把五喱縮減為一喱或者零了。他是個愛美的人,因而不能不厭惡他的妻子。坦涅爾太太非但沒有直到老死仍然是美國的美人兒,反而無緣無故,異想天開,變成美國木柴之類的東西,失去原有的姿色和智力,這表明,她雖然還適合於進一步訓練,可是已經完全不適合過夫婦生活了。坦涅爾醫師要求離婚。於是有學問的專家紛紛來到他家,從各方面考察坦涅爾太太,勸她到礦泉地去療養,做體操,給她開食譜,認為他們可敬的同行的要求完全合法。坦涅爾醫師送給同行兼專家們每人一枚金元,招待他們吃了一頓豐盛的早飯,於是……從那時候起,醫師住在一個地方,他的妻子住在另一個地方了。可悲的故事!
「後來你就睡著了?說呀!後來你就睡著了?」
「我到我母親家裡去借錢來著。」
津扎加趁阿瑪蘭達穿衣服的時候,對她講起他打算寫個故事,順便還提到,他寫這個震動身心的故事也要求她作出點犧牲。
她深長地嘆口氣,然而沒醒過來。他就拍她的肩膀,伸出手指頭去敲她那大理石般的額頭,碰她的皮鞋,扯她的連衣裙,打了個滿旅館都聽得見的噴嚏,然而她……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我需要這樣嘛!我打算畫的女人是在月光底下!月光照在她胸脯上……非利士人一起跑來,舉著火把,火光照在她背上……五彩繽紛啊!我不能不這樣畫!」
布特隆察朝女人那邊伸伸左腳。卡羅麗娜哭了。
「是嗎?」
「要是你想睡覺,你自管睡好了!」
津扎加走進第一百四十八號房間裡,看見一個場面,使得身為長篇小說作家的他頗為欣賞,同時又使得身為餓漢的他心裡發緊。長篇小說作家在許多鏡框、畫布框、缺胳膊的人體模型、畫架和掛滿不同種類和不同時代的褪色服裝的椅子當中瞧見了他的朋友福蘭切斯科.布特隆察,這時候他要同朋友共進晚餐的希望卻化為泡影了……原來福蘭切斯科.布特隆察學萬.笛克的樣子歪戴著帽子,穿著彼得.阿敏斯吉樣式的服裝,站在凳子上,發瘋般搖著繪畫用的支腕杆,哇哇地叫。他的樣子可怕極了。他一隻腳踏在凳子上,一隻腳踩在桌子上。他臉色通紅,眼睛炯炯有光,下巴上的鬍子發顫,頭髮直豎起來,似乎隨時都會把帽子頂到空中去。牆角上放著阿波羅的塑像,缺胳膊,沒鼻子,胸部有一塊三角形大裂口。福蘭切斯科.布特隆察正大發脾氣,他的妻子緊挨那尊塑像站著。她叫卡羅麗娜,是個日耳曼女人,戰兢兢地看著燈。她臉色蒼白,渾身發抖。和*圖*書
卡羅麗娜站起來。她身子底下果然有一塊新調好顏料的調色板……啊,上帝!為什麼我不是畫家?如果我是畫家,我就會獻給葡萄牙一幅偉大的畫!津扎加搖一下手,溜出第一百四十八號房間,慶幸他自己不是畫家,同時又痛心,因為他雖是個長篇小說作家,卻沒能在畫家那兒吃到飯。
「嗯……」
「不,你今天聽吧。明天我沒工夫。俄國作家捷爾查文到里斯本來了,明天早晨我得去拜訪他。跟他一塊兒來的,還有你所喜愛的——說來令人遺憾,——還有你所喜愛的維克多.雨果。」
舊報紙收藏在她本來裝糖果用的白鐵盒裡,跟裝過香水的小空瓶放在一起。舊報紙上除了廣告、電訊、政治、時事以及其他各項人間事務以外,還有一顆珍珠,也就是報紙上所謂的雜俎欄。雜俎欄裡有幾篇故事,有的描寫一個美國人怎樣施展巧計賺了另一個美國人,有的描寫著名歌唱家杜巴多拉.斯維斯特小姐怎樣吃光一大桶牡蠣,沒有沾溼靴子就翻過了安地斯山,另外還有一個小故事,非常適合於安慰阿瑪蘭達和其他藝術家的妻子。現在我把這個故事照抄如下:「請葡萄牙人和他們的女兒注意。在克里斯多福.哥倫布這個精力極其充沛而且極其勇敢的人所發現的美洲一個城市裡,住著醫師坦涅爾。這個坦涅爾與其說是科學家,不如說是別具一格的藝術家,因此,他在地球上和葡萄牙就不是以科學家,而是以別具一格的藝術家聞名。他是美國人,同時又是普通人,既是普通人,早晚就必然會戀愛,有一回他果然這樣做了。他愛上個美麗的美國女人,而且愛得神魂顛倒,不下於藝術家,愛到了有一次開藥方,該寫aquae distillatae而竟寫成agentum nitricum了,後來他求婚,終於結婚了。起初他同美麗的美國女人生活得非常幸福,結果違反蜜月的本質,把蜜月延長,不是一個月而是六個月。毫無疑問,坦涅爾是有學問的人,因而是最容易相處的人,要不是他在妻子身上發現一種可怕的惡習,他倆原會幸福地生活到死。坦涅爾太太的惡習就是她像一般人那樣要吃東西。妻子這個惡習使坦涅爾感到痛心。『我要重新教育她!』他給自己提出這個任務,而且開始啟發坦涅爾太太。起初他教她不吃早飯和晚飯,其次教她不喝茶。婚後一年,坦涅爾太太準備出來的午飯,已經不是四道菜,而是只有一道。成親以後過了兩年,她所吃的已經只限於少得出奇的一點點食物。她一晝夜吃下和喝下的營養品的分量開列如下:
未來的皇家劇院演員的妻子還沒來得及從他面前走開,他就看見第一百零一號房間的女房客來到他面前,她的丈夫是小歌劇的歌唱演員,又是葡萄牙未來的奧芬巴哈,大提琴和長笛的演奏者費爾吉南達.拉依。
真的,還不如這樣好!
津扎加瞪大眼睛搖躺和圖書椅。一本書從阿瑪蘭達身上慢慢滑下來,書頁沙沙地響,拍的一聲掉在地板上。長篇小說作家拾起這本書來,翻開一看,頓時臉色發白。這並不是別的書,也絕不是隨隨便便的一本書,卻是他最近寫成後由伯爵唐.巴拉班達.阿里蒙達出錢印行的長篇小說,書名是《聖莫斯科四十四名娶二十個妻子的男人的車裂之刑》。這本長篇小說,讀者諸君明白,所描寫的是俄國生活,因而是最有趣的生活,不料忽然之間……「她居然讀著我的長篇小說睡著了!?!」津扎加嘟噥道。
「俾斯麥提出辭呈。男主人公不願意再隱姓埋名,就說出他的姓名阿爾豐索.宗祖加,非常痛苦地死了。安靜的天使把他安靜的靈魂送上藍天……」等到時鐘敲七下,津扎加才算講完。
「啊……嗯!我明白了。拿點東西來給我吃!」
「對,是我!……你睡著了?你……睡著了?……」阿爾豐索嘟噥說,在一把東倒西歪的椅子上坐下,「你睡著以前做什麼事來著?」
「那叫我上哪兒去?」卡羅麗娜驚叫道,「你先給我錢,讓我回到當初你把我帶出來的柏林去,然後再跟我離婚!」
「不過現在已經是夜間了……現在,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睡覺的時候了……」
她一直睡到阿爾豐索.津扎加餓得不得了,跑來叫她,才醒過來。
幸福的津扎加就在不幸的阿瑪蘭達面前跪下,吻她的額頭……諸位女讀者,事情就是這樣!
「別說了,阿爾豐索!你的長篇小說我讀得津津有味……你這本長篇小說使我入了迷。我……我……我特別被一個場面所感動,就是青年作家阿爾豐索.旬節加開槍自殺……」
「沒有……」
「便宜,很便宜,太太。」
「書名我記不得,不過男主人公的名字我倒記得……這個名字我記得很牢,因為它一連有四個『爾』字……真是個荒唐的名字……卡爾爾爾爾羅!」
「該怎麼跟你說好呢?我覺得好像已經在什麼地方遇到過你這個男主人公,只是不記得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女人啊,你們常常成為偉人的災難根源。女人啊,偉人身後往往缺乏子嗣,這豈不是你們的罪過?葡萄牙人啊,你們的良心負著一項責任,就是教育你們的女兒!不要把你們的女兒培養成破壞安樂家庭的人!!我講完了。明天適逢主編誕辰,本報停刊一日。葡萄牙人啊!你們誰沒有交足訂報費,要趕快補交!」
「好,」阿瑪蘭達低聲說,臉色煞白,往一本破爛的、老是丟在一旁沒人理會的、蓋滿塵土的百科詞典上倒下去,昏迷不醒了……「這些女人可真是怪!」津扎加叫道,「我說的對,我在《一千把火》裡說過:女人這種生物對人類來說永遠是個謎,永遠使人驚奇!只要有一點點喜事,就能把她樂得暈倒在地!哎,女人的脾氣呀!」
京城里斯本最自由的公民阿爾豐索.津扎加是個年青的長篇小說作家,不過論名氣,卻只有他一個人知道;論遠大的前途,也只有他一個人這樣指望而已。有一次,他一整天在各處人行道上奔走,在各編輯部裡進進出出,累得筋疲力盡,餓得不亞於一條最餓的狗,回到家裡。他住在一家旅館的第一百四十七號房間裡,這家旅館在他的一本長篇小說裡化名為「毒天鵝」。他走進第一百四十七號房間,對他那狹小而不高的住所看了一眼,皺起鼻子,點上蠟燭,這以後就有一幅扣人心弦的畫面展現在他眼前。原來在一大堆紙張、書籍、去年的報紙、破舊的椅子、皮靴、睡衣、短刀和帽子中間,他那漂亮的妻子阿瑪蘭達躺在一張蒙著灰藍色套子的小躺椅上,睡熟了。溫情脈脈的津扎加走到她跟前,沉吟一忽兒,拉了拉她的手。她沒醒過來。他又拉她另一隻手。
「不過您累了,拉依先生!您這是在練習什麼歌?」
「對,對,對,就是那本書裡。我們的文學作品你記得多麼清楚!就是那本書裡……你的男主人公很像卡爾爾爾爾羅,不過,當然,你寫的人物聰明得多。你怎麼了,阿爾豐索?」
津扎加在阿瑪蘭達對面坐下,把頭往後一仰,講起來:「情節發生的地點是全世界……葡萄牙、西班牙、法國、俄國、巴西等。男主人公在里斯本的報紙上讀到女主人公在紐約遭到不幸。他去了。他被海盜捉住,而那些海盜是由俾斯麥的暗探買通的。女主人公是法國暗探。報紙上的暗示……英國人。奧地利的波蘭派和印度的吉普賽。陰謀。男主人公下獄。人家打算收買他。聽明白了嗎?下面……」津扎加講得動人而熱烈,搖著手,眼睛放光……他講了很久很久……長得要命!
「祝您健康!」津扎加說著,鞠個躬和*圖*書。
「哼……這還用問?!一點吃的都沒有嗎?」
「我的女朋友索菲雅.費爾德拉班捷羅.涅拉克魯茨.羅茲加,也就是你的朋友雕塑家的妻子,把她丈夫已經塑好、準備獻給巴拉班達.阿里蒙達伯爵的塑像碰碎了……她看到丈夫悲傷,受不了……就吞下火柴自盡了!」
「這種藥水多少錢一瓶?」
「那我到他那兒去!」津扎加決定道,就出去找這個鄰居。
「如何?」他問阿瑪蘭達,「你說怎麼樣?你認為阿爾豐索和瑪麗亞之間那個場面書報檢查機關通得過嗎?啊?」
「他快死了!這可怎麼辦?」
「可憐的坦涅爾太太!」阿瑪蘭達看完這個小故事,輕聲說,「可憐的女人!她多麼不幸!啊,跟她相比,我多麼幸福!我多麼幸福啊!」
「我想吃東西!」津扎加說,「穿上衣服,我親愛的,到你的madre那兒去要錢。不過,propos:我給你賠罪,我說得不對。剛才我去拜訪俄國作家捷爾查文,他是跟另一個俄國作家萊蒙託夫一塊兒來的。據捷爾查文說,有兩本長篇小說用同一個書名《大海中的女夢遊者》,可是內容完全不同。去吧,我的朋友!」
阿瑪蘭達臉紅了。
拉依唱得接不上氣了,這才停住嘴,呆呆地望著津扎加。
鹽 1喱
「為了藝術,太太,」津扎加說,「您不但得忘掉羞恥,而且得忘掉一切……感情!……」
「餓了。」
「我得一直唱到明天上午十點鐘。睡覺對我們沒有什麼好處。誰喜歡睡覺,就讓誰去睡,我呢,為葡萄牙的福利,也許還為全世界的福利,不應當睡覺。」
「可是我受不了,津扎加先生!我不能站到窗前去給大家看!」
「酣酸鹽,太太。」
「後來呢?」
「既是這樣,那您就到藥房裡去一趟,買酣酸鹽藥水。這種藥水治傷口很靈驗。」
阿瑪蘭達深深地嘆口氣,睜開黑眼睛,微微一笑。
「他練習從上邊往下跳,不料一頭撞在箱子上。」
「可是這關您什麼事?」
「去找大夫,太太!」
「犧牲不大,我的朋友!」他說,「你得憑我的口述把我的描寫記下來,這至多破費你七八個鐘頭,然後你再把它謄清。順便,把你對我所有作品的看法捎帶著寫在一張紙上。——你是女人,而我的大多數讀者是女人……」津扎加說了點謊。並不是他的大多數讀者都是女人,而是他的全部讀者只有一個女人,因為阿瑪蘭達並不是「許多女人」,只是「一個女人」而已。
阿瑪蘭達暗自慶幸這個世界上還有人比她更加不幸,就小心地把報紙疊好,放回盒子裡,然後,想到她不是坦涅爾太太而心裡高興,就脫掉衣服,躺下睡覺了。
「講新的長篇小說提綱嗎?」阿瑪蘭達小聲問道。
津扎加向歌劇演員兼樂師的妻子伸過一條胳膊去,由她挽住,往第一百零一號房間走去。第一百零一號房間裡有張大床占去一半地方,有隻搖籃占去四分之一地方,大床和搖籃之間立著一個樂譜架。樂譜架上放著顏色發黃的樂譜,葡萄牙未來的奧芬巴哈正看著樂譜唱歌。他究竟在唱些什麼,一時間是很難聽明白的。只有憑他那冒汗的紅臉,憑他對自己和別人的耳朵所發生的影響,才能推斷他唱得很差,費力,像發瘋一樣。看來,他唱歌是活受罪。他用右腳和右拳打拍子,同時把胳膊和腿舉得高高的,老是碰掉樂譜架上的樂譜。他伸長脖子,眯細眼睛,歪著嘴,伸出拳頭捶肚子……搖籃裡躺著個小小的活人,又喊又嗥,尖聲怪叫,給他的聲嘶力竭的爸爸伴奏。
「拉依先生,現在您該休息了吧?」津扎加又問一遍。
「可是,我的朋友,」他的妻子插嘴說,「我和我們的孩子要睡覺!你這麼大聲地嚷,慢說別人不能睡覺,就連在這個房間裡坐著也不行!」
「你幹什麼?!」布特隆察大吼一聲,「你坐在我的調色板上了!!」
「我辦不到,太太。我買下三令紙,把錢花得一個也不剩了。」
「我不是生氣,而是覺得痛心:你這麼漫不經心地對待我的工作,這種工作即使還沒有給我名望,以後也一定會給!你是因為讀我的長篇小說才睡著的!我就是這樣理解你睡著的原因的!」
「和-圖-書那就再見!」
「沒有。」
「不,那個場面很動人!」
「野蠻人!」布特隆察吼道,「你們不愛藝術,扼殺藝術,見你們的鬼!我怎麼會跟你這個冷血的日耳曼女人結婚的?!我這個傻子,原是一個像風那樣自由的人,一頭鷹,一隻羚羊,總之一個藝術家,怎麼會跟這樣一小塊由偏見和淺薄凝成的冰結合在一起……diabolo!!!你就是冰!你就是一塊木石般的牛肉!你……你這蠢貨!哭吧,你這倒霉的、煮爛了的德國臘腸!你丈夫是藝術家,可不是什麼小商人!哭吧,你這啤酒瓶!津扎加,是您嗎?您別走!等一等!您來了,我很高興……您瞧這個女人!」
「您有什麼事?」他問。
脂肪 2喱
「獻給巴拉班達.阿里蒙達伯爵大人的頌歌。然而這關您什麼事?」
阿瑪蘭達嘆了口氣,可是沒有哭,也沒有當場昏倒。她知道阿爾豐索.津扎加不管生多大的氣,總會回到第一百四十七號房間裡來……對這個長篇小說作家說來,永遠離開第一百四十七號房間就無異於開始在葡萄牙蔚藍色天空下生活,因而就得在里斯本人行道上寫作,還得找個不要報酬的女謄寫員。這一點阿瑪蘭達是知道的,因而她丈夫走後,她倒不大擔心。她只是嘆口氣,開始安慰自己。照例,在夫婦之間這種常有的口角以後,她總是讀一張舊報紙來安慰自己。
「我睏極了!要知道我昨天一夜沒睡覺。你那麼可愛,通宵給我朗誦你那本優秀的新長篇小說,我總不能只顧睡覺,不聽你朗誦,放棄這種快樂啊……」
「我明天早晨聽你講豈不更好,我的朋友?早晨腦子多少清楚點……」
「他淹死的時候還為子爵夫人克塞尼雅.彼得羅芙娜祝福……我心裡很感動……」
「我?哦……我……也就是說……現在您該休息了吧?」
阿爾豐索跳起來。
「睡得好香啊!」津扎加暗想,「這是怎麼搞的?莫非她服毒了?我最近那本長篇小說的失敗可能對她起了強烈的影響……」
「是嗎?那麼這本長篇小說裡是哪個場面打動我的心呢?哦,對了……我讀到俄國侯爵伊凡.伊凡諾維奇從窗口跳出去,掉進河裡……河裡……伏爾加河裡的時候,我就哭了。」
「真的。我在一本長篇小說裡遇到過你的男主人公,而且應當說,那是一本無聊透頂的長篇小說!當初我讀那本長篇小說,心裡就納悶,這類荒唐的東西怎麼會出版呢。我把它讀完,就斷定作者至少一定蠢得像木頭……荒唐的東西倒印出來了,你的作品卻很少印出來。真是怪事!」
「啊唉……嘿!」
「沒有,我的朋友!我母親光叫我吃了一頓飯,沒給我錢。」
「讀你的長篇小說。」
「可是他不願意找大夫!他不信醫學,再說……他在所有的大夫那兒都欠著債。」
「是你嗎,阿爾豐索?」她對他伸出手去,說。
「您看見沒有?看見沒有?這也算是理由,見她的鬼!」
「總的說來,這篇小說好嗎?你說實話。你是女人,而我的大多數讀者都是女人,所以我非知道你的意見不可。」
「你同意嗎?」
津扎加向妻子投過去輕蔑的一瞥,把帽子低低地拉到眼睛上,走出第一百四十七號房間,砰的一聲關上門。
「可憐的阿爾豐索!那你沒有錢嗎?」
「後來就睡著了……咦,你生什麼氣呢,阿爾豐索?」
拉依沒聽見。
共計 16 1/23喱
匈牙利葡萄酒 11/23喱
「我給他洗畫筆,洗調色板,洗抹布,我的衣服給他的畫弄得髒兮兮,我為養活他而出去當家教,我給他縫衣服,我忍受大麻籽油的氣味,我一連多少天站著給他做模特兒,我樣樣事情都做了,可是……如今叫我赤身露體?赤身露體?那我辦不到!!!」
「那個場面不在這本小說裡,而是在《一千把火》裡!」
「哎呀,津扎加先生!我們闖了禍!這可怎麼辦?我的彼得受傷了!」
「這真不走運!自從我做你妻子那天起,我就滿心痛恨那些編輯!那你餓了吧?」
「我辦不到!說實在的,我辦不到!他叫我脫|光衣服,而且還要站在窗前……」
阿瑪蘭達睡著兩次,醒來兩次,街上的路燈熄滅,太陽升上來了,可是他仍舊在講。時鐘敲過六下,阿瑪蘭達胃裡不好受,想喝早茶,可是他仍舊講個不停。
「拉依先生,現在您該休息了吧?」津扎加走進門來,問拉依說。
m.hetubook.com.com「怎麼受傷的?」
「是啊,我原以為我的詩會在《新聞報》上發表,見它的鬼!」
「算了!」津扎加開口說,「您吵什麼,布特隆察先生?布特隆察太太有什麼對不起您的地方?為什麼您氣得她掉眼淚呢?要記住您偉大的祖國,布特隆察先生,您的祖國是把對美的崇拜同對女人的崇拜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國家!您要記住!」
「難道你還沒吃飯?」
水(蒸餾過的) 7喱
「不幸的……塑像呀!哎,這些妻子,巴不得叫鬼抓了你們去,順帶把你們那些碰翻一切東西的長衣裾也抓走才好!她服毒自盡了?見鬼,這倒是長篇小說的題材呢!!!不過,這個題材沒有多大意思!……在這個世界上,人人都要死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後天,你的女朋友反正也得死……你把眼淚擦乾吧,你與其哭,還不如聽我講的好……」
「不是的,我不是為你的主人公哭……」
「如果你真感動,那怎麼會睡著呢?」
「你至少總該記得那本長篇小說的名字吧?」
「把他抱走!」拉依唱著,同時把下巴朝搖籃那邊揚一下。
「女人啊!」津扎加放開他那葡萄牙人的喉嚨大叫一聲,舉起拳頭捶躺椅的邊緣。
「那你為什麼哭呢?」大失所望的津扎加問。
「我要跟你離婚,紅頭髮的潑婦!」布特隆察叫道。
「倒霉的人啊!」
「莫非是在《大海中的女夢遊者》那本書裡嗎?」
「這樣說來,我的長篇小說,我的作品,無聊透頂?」他嚷得那麼響,連阿瑪蘭達的嗓子都覺得痛了,「哼,你這沒腦筋的鴨子!原來您,夫人,就是這樣看待我的作品嗎?原來就是這樣,母驢?您無意中說出了真話吧?從今以後您休想再見到我!再見!哼……呸……白癡!我的長篇小說無聊透頂?!巴拉班達.阿里蒙達伯爵明白他出版的是什麼書?」
「您怎麼了?」津扎加問她。
說完這話,拉依就用腳打拍子,唱起來。
「您在練習什麼歌?」津扎加大聲問道,竭力要蓋過拉依的聲音,「您在練什麼歌?」
「阿瑪蘭達!」他抓住妻子的手,叫道,「難道我這可憐的中篇小說裡那可憐的主人公居然把你感動得流淚嗎?是這樣嗎,阿瑪蘭達?」
「我辦不到!」卡羅麗娜哭著說,「要知道這不像樣子!」
「謝謝您。您永遠是我的彼得的好朋友!我們還剩下一點錢,那是他在巴拉班達.阿里蒙達伯爵家演堂會戲掙來的……我不知道這點錢夠不夠。您……您能借給我一點錢去買那種醬酸鹽嗎?」
「這不可能!」
「莫非他們沒發表?」
與其住在「毒天鵝」最好的房間裡,得到巴拉班達.阿里蒙達伯爵最好的庇護,姑娘們和寡婦們啊,還不如住在隨便哪家賣菸草的小店裡,或者索性在市上賣鵝的好。
「遵命,太太!」
「津扎加先生,」歌劇演員兼樂師的妻子絞著兩隻手說,「請您費心,去管管我那個胡鬧的傢伙!您是他的朋友……也許您能夠制止他。這個不要臉的人大清早起就扯開嗓門哇哇地唱,唱得我都沒法活了!小孩子沒法睡覺,我呢,簡直讓他那哇哇叫的男中音撕得粉碎!看在上帝面上,津扎加先生!都因為他,我甚至不好意思見鄰居的面了……您信不信?連鄰居的孩子們都託他的福,沒法睡覺。勞駕,您跟我走一趟!也許,您好歹能夠管住他。」
「《大海中的女夢遊者》就是我寫的長篇小說!!!」他叫道。
「是的……那你就聽我講吧!」
「好吧!我畫完蘇薩娜,就把你打發到你的普魯士去,打發到那個滿是蟑螂、臭臘腸、旋毛蟲的國家去!」布特隆察叫道,無意間胳膊肘撞著她的胸脯,「要是你不能為藝術犧牲自己,你就不配做我的妻子!野……蠻人……魔鬼!」
「給大家看……不錯,我們不妨認為,布特隆察太太,您是害怕人群的眼睛,其實所謂的人群,如果加以考察的話……。藝術和理性的觀點,太太……是這樣的,那就是……」津扎加說了些聰明人沒法在嘴上說出來而且沒法在筆下寫出來的話,也就是十分正派而又極其難懂的話。
在第一百四十七號房間門口他遇到個臉色慘白、神色慌張、渾身發抖的女人。她是第一百十三號房間的房客,未來的皇家劇院演員彼得.彼得魯千察.彼得魯利奧的妻子。
「我們不久就還給您。」
卡羅麗娜放聲大哭,抱住頭,在椅子上坐下。
你們要知道,姑娘們和寡婦們,這些藝術家你們萬萬嫁不得!烏克蘭佬說的好:「求主保佑,叫那些藝術家滾蛋吧!」
「對了……」
蛋白質 5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