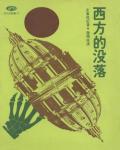第二部 世界歷史的透視
第十三章 城市與民族
這才是「民族」這一字眼唯一的涵義。所謂統一的語言,或生理的家世,都不具決定性的意義。使一民族有別於一堆人口、使一民族高出於一堆人口,而後來有一天,又使一民族回復到一堆人口的層次,這一直是族類精神的內在生命經驗使然。這一族類感受越是深刻,則這一民族的生命力越是強盛。世上有強悍的、也有溫馴的、有早天的、也有不減的,各形各式的民族。這些民族可以改換語言、名稱、種族、及土地,但是,只要它們民族的靈魂尚在,它們仍可收集、並轉變任何地方、任何起源的人類素材。漢尼拔時代的羅馬人,即是一個民族,而圖拉真時代的羅馬人,不過是一堆人口罷了。
在把要待傳達的意思,置入句子之時,先天地,便涉及到種族的特徵了。塔西陀的句子與拿破崙的迥不相同,西塞羅的句子和尼采的判然有別,而英國人驅遣字句的方式,與德國人的方式,也自有其差異。無論在原始的、古典的、中國的、及西方的語言社群中,決定句子單元的型式,以及單字對句子的機械關係的,都不是「觀念」或「思想」,而是思考的過程,生命的類型,而是血液。文法(grammar)與造句法(syntax)的界限,應該置於機械的語言終止,而有機的語言開始的那一點上——有機的語言,是指一個人所用以表達他自己的方式、習慣,以及觀相。另一界限,則在於單字的機械結構,轉入為聲音形成及表達時的有機要素之際。英國的移民,即使是小孩,也常可以由英文「th」的發音,而辨認出來——這便是土地的種族特徵。我們對於很熟悉的人,可以不必看到他,而僅由他的發音,便認識出來。不惟如此,即使一個人能操完全正確的德語,若他是一個外國人,我們仍是可以辨認出來。
例如,若狗需要什麼東西時,牠便搖他的尾巴,等牠無法忍耐他主人的蠢笨,竟不瞭解牠如此清楚明白的「語言」時,牠再加上聲音的表示——牠吠叫一番,而最後,牠還加上姿態的表示:扮怪相或作手勢,至此,在狗的眼中,人實是個蠢物,不懂語言之道。
在最早的時候,只有「風景」的形像,統治著人類的眼睛。風景賦予人的靈魂以大致的形式,並產生迴響。自然的感受與叢林的呼哨,互相交溶,一起脈動;草原與沼澤,都適應著風景的形態、歷程、甚至外表而存在。村落之中寂靜的、山丘形的屋頂,黃昏的炊煙,井穽、籬笆、牲畜,都完全溶合、並嵌入於風景之中。至於鄉村的小鎮,則鞏固了鄉村的本身,故而是鄉村圖像的一種強化表現。只有文化後期的城市,首次否定了土地,城市的剪影,在線條上與自然格格不入,否定了一切的自然。城市,一直是想要成為一種不同於自然、並超乎自然之上的事物。那些高聳入雲的屋頂角牆、那些巴洛克的圓頂建築、塔頂、尖塔,與自然毫不相干,也根本不想與自然發|生|關|系。然後,出現的便是巨大的國際都會、世界都會,它不能容忍其他的事物,存在於自己近畔,故而著手滅絕了鄉村的圖像。在從前某一段時間,城市曾一度謙遜地置身於風景的圖像之中,安份守己,如今卻堅持要自行其是,睥睨自如。於是,郊野、大道、森林、草原,變成了只是一個公園的景物,山嶺變成了旅遊者觀光的所在;而花園造成了一種仿製的自然,噴泉取代了泉源,花床、人造水塘和修剪齊整的籬笆,取代了草地、池澤、和叢林。在村落中,茅草蓋成的屋頂,仍然像小丘一樣的形狀,而街道也只是兩片地域之間的田埂;但是在大城市中,則高大、石砌的房屋之間,所呈現的圖像,猶如深邃而漫長的峽谷,彼此隔絕,房屋充瀰著彩色的塵埃、和奇異的喧囂,人們居住在這種屋子裏,簡直不可思議。人們的習俗,甚至面貌,都必須適應這種石頭的背景。白天,街道的交通,充滿了奇怪的色彩和音調,夜晚,新造的霓虹燈光,比月亮還要閃亮。鄉下的農夫,無助無告地站在路上,茫無所措,也無人瞭解,只是被當作滑稽劇中的一個常用的典型,以及這個世界的日常食糧的供應者而已。
由於人類此種自我與對方溝通的工具,甚為圓熟,故而在動物性的感覺瞭解之外,塑出了一套文字思想系統,來取代了感覺。於是精巧的思想,得以保存於文字意涉之中,寖假而遂致別的語言,皆告淘汰,只剩下了文字的語言。又由於語言本身之完美自足,乃使得語言終與人類整個的生命習慣,截然有異,語言與口語嚴格而不幸地分了家,致使以口語來統涵整個的真相,成為不可能,這在文字的符號系統中,尤其造成了影響深鉅的結果。抽象的思考之得以存在,是靠一套有限的文字網絡的應用,人們企圖在這文字網絡之中,由抽象思想,來掌握生命那完整而無限的內涵。於是,抽象概念殺死了生命存有(Being),並欺騙了覺醒存有(Waking-Being)。很久以前,在語言史的春天時節,理解必須掙扎努力,以求與感覺共存,那時,抽象思考的機械化作用,對生命全無重要性可言。可是現在,人已從很少思想的生物,一變而為思想的生物,而自古以來,每一思想系統的最高理想,便是要迫使生命屈服於心智(intellect)的統轄之下。在理論上,這已由下列方法達成:認定只有「已知事物」才是真實,並把實際事象硬指為虛幻和悠謬。在事實上,這一理想的達成,乃是強迫血液的聲音,在「普遍的倫理原則」之前沉默。
代表各個文化的風格的民族,我們稱之為「國家」(Nations),這一字眼本身,便有別於在其之前,及在其之後的各民族形式。不但在國家之中,有一強烈的族類感受,鍛鑄了所有主要部份中,最關重要的內在統一;而且在國家之下,實有一文化理念潛存著。這一集體的生命之流,具有一種對命運、對時間、及對歷史的深刻關係,這一關係,各有不同,並由它決定了人類素材對種族、語言、土地、國邦、及宗教的關係。正因為古中國文化與古典文化的民族風格相異,故而它們的歷史風格,也便有所異趣。
「世界都會」,真如石砌的巨像,碰立在每一偉大文化的生命歷程的終點。世界都會的意象,出現於人眼的光線世界中,極盡宏偉壯麗之能事,它包含了已經確定的、已經生成的事物,所表現的整個莊嚴肅穆的死亡象徵。在西方,經過了千百年的風格演化,哥德式建築中,那種瀰漫無限精神的石頭,已經變成了鬼域似的石砌沙漠中,毫無靈魂的死物質,正反映出這一死亡的象徵。
埃及筆之書的文字,約在西元前三千年左右,已處於文法急劇解體的狀態,蘇美人的文字,亦與此相彷。中國的文字,即使在現存方古的典籍中,也已完全看不出演變的痕跡,直到晚近的漢學研究,才確定了中文曾有文法演變的事實(譯按:此點似有問題)。印歐的系統,對我們而言,也已是有完全破解的狀態中。對於古梵文(西元前一五〇〇)文法中的「格」(case),一千年後的古典語言中,已只保留了一些殘片賸簡;而從亞歷山大大帝時代起,文字上性別的差界,已隨一般希臘文的衰微而消失,被動語態也已完全絕跡於文法結構之中。西方的語言,雖然起源糅雜,簡直匪夷所思——從出自原始的日耳曼系,到出自高度文明的羅馬語系——可是也向同一方向修正。羅馬文中的「格」已減為一,而英文在宗教改革之後,減為零。日常用的德文,從十九世紀初葉起,已明確地消去了所有格,現在正進而要取消間接受格。只有在嘗試將一篇艱澀而繁複的文章——例如塔西陀或毛姆森(Mommsen)的東西——「譯回」於某一富於文法變化的遠古文字時,我們才能體認到:符號的技巧,當時是如何地蒸發而成思想的技巧。而這些簡潔明瞭,但含義豐富的符記,如今已有如遊戲中所用的籌碼一般,習焉而不察。事實上,也只有特定的語言社群中的肇始人,方會明白其含義。故而,中國的經典,對西歐人而言,必然永遠是根本「不可接觸」之書;其他文化的語言中的原始字語,也是如此——希臘文的「道」與「力」,梵文的「梵天」(Atman)和「婆羅門」(Brahman)——皆是各該文化的世界展望之指標,非生長於此等文化之人,絕不能夠了解其中精義。
所有這一切的形式,都表示覺醒意識如今已極度過量,不受自然宇宙的脈動所緩和及限制,呈現出純粹的心智和擴張的現象。但也正因此故,它們能夠作有力的投出,它們最後鼓動的光芒,伸展並疊壓了幾乎整個的地球。中國文明中,一些形式的片斷,可能在斯坎地那維亞半島的木製建築中發現,巴比倫的度量術,可能在南海發現www.hetubook.com.com,古典的貨幣可以出現於南非,而埃及與印度的影響,也及於南美洲印加文化的土地上。
種族自有其根柢。種族與風景互相隸屬,一株樹生根的地方,也即是它死亡的處所。毫無疑義地,我們確實可以從一個種族身上,追溯到它的「老家」(home)。但是,尤其重要的是,我們要瞭解:種族的某些最最精粹的性格,無論屬於形體的或是屬於靈魂的,都永遠依附在這一「老家」之中。如果在這老家中,如今已找不到此一種族,這即表示,此一種族已不復存在。種族本身,絕不遷移,遷移的只是「人」;這些移民的後代子孫,生長在不斷變化的風景之上,而風景對於他們身中的「植物天性」(plant-nature),施以一種神秘的力量,終於,使得種族表徵完全變形,舊的已告消絕,新的開始出現。英國人和德國人,作為種族來看,並未遷移至美國,所遷移的,只是作為人類一份子的英國人和德國人,而他們的後裔,在那裏便寖假而成為美國人。長久以來,我們明顯地看到:印地安人的土地,已烙印在這些人身上,一代復一代,他們變得越來越肖似於被他們所滅絕的印地安人了。顧爾德(Gould)與巴克斯塔(Baxter)兩位學者,曾指出:所有種族的白人、印地安人、和黑人,在平均身材及成熟時間上,已完全一致,——而愛爾蘭的移民,抵達美國時尚很年青,發展也甚緩慢,可是卻也快速地在同一世代內,受到了這一風景的力量的影響。學者波埃斯(Boas)也指出:美國出生的孩童中,長頭的西西里種、與短頭的日耳曼猶太種,已很快地達成了同樣的頭型。這不是一個特例,而是普通的現象,故而我們在處理那些歷史上的移民之時,要格外小心,因為我們除了略諳一些流浪族群的名稱、及若干語言的遺跡之外〔諸如:丹奈語(Danai)、依特拉斯坎人(Etruscans)、皮拉斯基語(Pelasgi)、亞該亞人(Achaeans)、多力安人(Dorians)等〕,其餘便一無所知了。故而,對於這些「民族」之中的種族情貌,我們當然無從得出什麼結論。至於泛濫於南歐土地上的哥德人、倫巴人、汪達爾人等,名目固然紛歧散亂,但本身其實是一個種族,則略無疑義。然而在文藝復興時代,它自身實已完全溶入於南歐的普拉汶斯、加斯提里、以及塔斯肯等地的泥土,所特有的基本性徵之中去了。
農人,是永恆的人類,獨立於各大文化之外。真正的農人,其虔誠信仰,要較基督教的信仰更為古遠,他的神祇,甚至較諸高級宗教的任何神祇尤為古老。世界歷史,其實祇是城市的歷史。當然,有的時候,鄉野地域也會蒙受到高級文化的某一程度的影響,而不再只是一堆不具歷史的素材。
文字記載之事,首與人的身份有關,尤其是古代僧侶的特權。農夫沒有歷史,故而也無文字。不惟如此,在人類種族的天性之中,還對文字書寫,天生有一種含糊不得的嫌惡之情。我想,筆跡學(graphology)中有一項極端重要的事實,即是:握筆者越具有種族(血液)的特性,則他寫出來的文字越是豪暢淋漓,而他也越是會想以個人的線條圖樣,來取代正規的文字寫法。只有僧侶之輩,才對文字的適當形式,端持一份敬謹之意,並不自覺地,不斷努力複製文字形式。這就是行動人(man of action)與書齋學者之間的差別所在:前者創造歷史,後者只是把歷史筆之於紙,使之「永恆化」而已。在所有的文化中,文字記載皆由僧侶階層在予保管,當然,還要加上詩人與學者。貴族統治階層,則根本蔑視文字記載,它只要令人為它而寫即可。從邃古時代起,文字記載即與智識份子或僧侶階級,息息相關。不受時間限制的所謂「真理」之所以成為真理,並非透過言談而來,而只有在筆之於書時,才告成立。於此,我們又一次遇到「城堡對教堂」(castle and cathedral)之對立:究竟誰能持久,事實或是真理?檔案的史料,保留了事實,而宗教的典籍,記載著真理。編年史記及文獻,對前者的意義,正和經籍詮釋及藏書,對後者的意義一樣。
最後,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是在於:當狗已用盡了其他一切方法,來瞭解牠主人的各種語言之後,他突然人立而起,他的眼睛直注入人的眼睛中。這時,便發生了深奧神秘的現象——「自我」(Ego)與「對方」(Tu)的直接接觸。目光脫離了覺醒意識的限刻,生命存有(Being)瞭解了自己本身,不需任何的符記。在此,狗變成了人的「裁判者」,以眼睛直視牠的對方,並超越了語言,掌握了說話者的真意。
雖然並不自覺到這一事實,可是,我們習慣上常使用此等「語言」。嬰孩早在學會第一個字之前很久,便已能說話了;而成人在談話時,也常使用一些自己根本不曾考慮其正常意義的字語——在此等情形中,是聲音形式(sound-form)在表達語言,而不是字句在綴成語言,此等「語言」,也自有其語群和對話,也可以被人學習、駕御、或誤解。對於我們那字句綴成的語言而言,這些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我們想要以字句語言來獨撐一切,而全不借助於「音調語言」(tone-language)和「姿態語言」(gesture-language),則字句語言必定造反。甚至我們的文字,本是訴諸眼睛的「字句語言」,可是若無以標點符號的形式,所表現的「姿態語言」之助,也幾乎無法為人理解。
自然科學全然不曾意會到:種族與落地生根物固不相同,與活潑動彈的動物,也自迥然有別。種族所表現的,乃是出自生命的內在宇宙一面的,某些嶄新的特徵,而這些嶄新的特徵,對動物的世界而言,實頗具其決定性的意義。自然科學尤其不曾覺察到,當種族這個詞眼,指謂整個「人類」中的某一部分時,更具有一種完全與眾不同的重要意蘊。當自然科學處理到所謂「適應」(adaptation)、「承繼」(inheritance)等等之時,它只是在浮面的性徵上,設定了一套毫無靈魂的因果關聯,而抹去了事實真相:——在種族中,展現自我的,一方面是血液(blood),另方面則是覆蓋於血液之上的土地的力量。這等奧秘,是不能檢視,也無法度量的,只能經由活生生的經驗與感受,而以心傳心。那些自然科學家本身,對於他們的這些浮面性徵的相對屬次,即頓不能一致。
再進而言之,只要我們能擺脫達爾文時代的重大陰影的影響,而自行發現出一套基準,則泥土的神秘力量,自會立即展現於每一件活生生的事物之上。羅馬人曾把葡萄樹從南義大利移植至萊因河,而葡萄確實並不曾有什麼可見的——即:植物學上的——改變,可是,在此例中,「種族」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決定。生長泥土的不同,不但使南歐與北歐的酒,使萊因河與莫索河的酒判然有別,而且即連每一不同的山際、每一片不同的位置,所產生的產品,滋味皆自有差異。這在其他的高級植物「種族」,如茶葉和煙草上,也一樣可以感覺出來。與此相類的,也只有感覺最敏銳的人,才能覺察到:自有一種相似的元素,一種幽邈闇暗的特殊風味,以高級文化的各種各樣的形式,聯繫了伊特拉斯坎人和塔斯肯地方的文藝復興人們;聯繫了蘇美人(Sumerians)、西元前五世紀的波斯人和底格里斯河上伊斯蘭教的波斯人,因為,他們分別屬於同一的種族。
而以文法的結構,逐漸取代實體或聲調上的姿態,實是句子形成過程中,決定性的因素。但此一過程,是永遠不會完全完成的。世上沒有純粹的音符語言,當以單字來說話的動作,越來越趨精細時,透過單字的字音,便會喚起了我們的「認知感受」(significance-feelings),這再轉而透過字句連繫的聲音,而喚起了更深的「關聯感受」(relation-feelings)。故而我們在語言方面的學習,使我們能以簡潔而象徵的方式,不但瞭解到物理事象(light-things)與物理關係(light-relations),而且瞭解到思想事象(thought-things)與思想關係(thought-relations),單字原先只是用以命名,並不絕對確定,故聽者必須感受到說者的意思。由於語言有此一特性,故而姿勢和音調在語言中所佔的角色,遠較研究語言者所承認者為大。而在很多的動物界,也可以發現存有若干的名詞音符,只是絕未有過動詞音符而已。
單字是句子中最小的機械單元。而各個人種所設想出來的,獲致此等單元的方式,皆自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對班圖族黑人(Bantu Negro)而言,他所看到的任何事物,首先,是屬於一大堆的理解範疇之中。故而,與此相應地,他們的單字是包含了一個核心或根柢,然後帶上一大堆的單音節的字首。當他說及一個田野中的女人,他用的字是這樣的:「活的——一個——大的——老的——女的——外面的——人」,這便有了七個音節。諸如此類的理解作用,對我們固嫌陌生疏離,其本身倒也明晰可喻。這一些語言中,單字所涵蓋範圍的廣闊,幾乎不下於句子。和_圖_書
民族與國家
由原始民族及農業土著民族所經歷的生命,只是動物性的起伏昇沉,一種毫無計畫可言的得過且過,既無任何目標,也無在時間中行進的節奏,此類民族,其數孔多,但是,在最終的分析之中,沒有什麼意義可言。唯一的歷史民族,其存在構成了世界歷史的民族,乃是「國家」。
到達此一水平之時,所有的文明,都進入一個歷時數世紀之久的、驚人的人口減少的階段。文化人類所堆成的整個金字塔,乃告消失。它自其頂點開始崩陷,首先是世界都會,然後是鄉野城市,最後,是土地的本身。土地的最佳血液,已經毫無節度地傾注入城市之中,然而只能支撐一會兒的時間。終於,只剩下原始的血液,尚留存著,但也已被剝奪了它最強壯、最有希望的元素。這一剩餘的殘基,便是洪濛混沌的土著農夫(Fellah)的型式。
當然,經常可以把民族與種族相提並論,但此處的「種族」一詞,絕不可以用今日達爾文主義的意義來加以解釋。確實地,我們不能接受,一個民族是僅由生理起源之相同統一,而告結合,而能維持此一統一,達十世代之久的說法。我不憚反覆說明:此類生理起源之說,除了在科學中之外,絕不存在,絕不在「集體潛意識」中存在,也沒有任何民族,曾對此類血統純粹的理想,感到狂熱之情。在種族中,並沒有什麼實質物象存在,有的只是某一古樸自然而具方向性的事物,只是對同一命運的和諧之感,只是對著歷史存有(historical Being)行進的單一節奏。就是此一全然形上的脈動之指向,製造了所謂「種族仇恨」,有如日耳曼人與法蘭西人、及日耳曼人與猶太人之間那種的種族仇恨;但也就是對此一脈動之共鳴,造成了男人與妻子之間的真正愛情——如此接近於仇恨的愛情。沒有種族觀念的人,絕不會瞭解此種危險的愛情。如果如今說著印歐語言的人眾之中,有一部份尚懷抱某一種族理念,則其表現得凸顯的,並不是學者們津津樂道的民族原型之預,而正是此一理念的形上力量和能耐。
種族即風格
現在居於主導地位的,不是命運,而是因果,不是活生生的導向,而是廣延。職是之故,以往文化的每一形式語言,以及它的演進歷史,都黏附在其始源的地點;而如今的文明化的形式,卻能在任何地方隨遇而安,並且,只要它們一出現,就能夠作無限制的擴張。毫無疑問,北俄羅斯的漢沙諸城(Hansa Towns),材料雖出自本土,卻具哥德式的風貌,南美的西班牙式建築,也表現巴洛克的風格。但是,在文明時期之前,即使是哥德式風格歷史中,最微小的部分,也不可能發展至超離西歐的範圍之外,正如阿提克或英國的戲劇、或複句音樂的藝術、或西方路德的與古典奧斐爾的宗教,也絕不可能蕃衍至於其他文化的人們之中,甚至也不可能被其他文化的人們,內在地加以吸納。但古典的亞歷山大城主義、及我們的浪漫主義的本質,卻是屬於一切的都城人們的,並不因文化而異。浪漫主義標示了:歌德以其廣擴的視野,所揭出的「世界文學」的開端。——「世界文學」,就是居於領導地位的世界都會中的文學,與之相反的,便是鄉野的文學,淳樸天真,屬於土地,但卻易被忽視。這種鄉野文學,只能艱困地四處掙扎,以求維持自己的存在。而另外,就政體而言,威尼斯的體制、腓特烈大帝的體制、或是英國議會的體系,都不能在其他文化中複製,但是所謂「現代憲政」,卻可以被「介紹」到任何的非洲或亞洲的國家,這和古典的城邦(Poleis),也可以在奴米提人(Numidians)及古代布立頓人(Britons)之中設立,情形是一樣的。從而,在一切的文明之中,其「現代」都市的型式,越來越具有統一的樣態。我們無論走到那裏,都可以看到柏林、倫敦、及紐約之類的都會,正如羅馬的旅者,可以在帕邁耳(Palmyra)、或特瑞耳(Trier)、或迪姆加德(Timgad)、或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及鹹海的諸希臘式城市中,發現到他自己城中那種的圓柱建築、列有雕像的公共議壇、以及神廟一樣。但是,如此散播出去的,已不再是一種「風格」,而只是一種「風味」,不是真正的「習俗」,而只是泛泛的「格調」,不是國家的服飾,而只是時髦的流行。當然,如此一來,遠方的民族,不但可以接受那文明所賦的「永久」賜予,而且還甚至可以以一種獨立的形式,來予以反射了。像這一類的「反射文明」(「moonlight」civilization),可見於中國南部,尤其是日本(它約在西元二二〇年,漢朝尾聲時,即已首度漢化);另外,爪哇是婆羅門文明的接替者,而迦太基則自巴比倫文明中,獲得了自己的形式。
兩種靈魂
事實上,人類頭部的種族表徵,實與任何一種可感知的腦殼形式無關,具有決定性的要素,並不是骨頭,而是肉體、是外觀、是形體的表現。自從浪漫主義時代以來,我們總在說什麼「印歐」種族(Indogermanic)。但是,是否有所謂的阿利安種(Aryan)的腦殼、或閃米族型(Semitic)的腦殼存在?我們是否能夠區別出賽爾特族(Celtic)的及法蘭克族(Frankish)的腦殼?或是波爾族(Boer)的及卡富爾族(Kaffir)的腦殼?在考古上,對史前時代的頭骨,著名的發現,從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到奧理格奈新人《Aurignacian),對於種族的特徵,及原始人們的種族漂移實況,都不能證明什麼。除了從其顎骨的形式,能對他們所吃的食物作出某些的結論之外,這些考古發現,祇能顯示發現地點,基本土地形式而已。
原始民族的豐富生命力,是一種自然的現象,甚至沒有人去思索這一事實,更少去判斷到它的用途及其他了。當有關生命的問題,必須藉理智來為之解決時,生命的本身,就成了問題。到了此際,便開始了對生育的謹慎節制。原始的婦女,農家的婦女,天生就是母親,從孩提時代起,她所渴切盼望的整個天職,都包括在「母親」一詞之中。但是現在,出現了易卜生筆下的女人,出現了從北歐戲劇到巴黎小說,所呈現的整個大都市文學中的女志士、女英雄。她沒有孩子,她有的是靈魂的衝突;婚姻只是她為了獲得「相互瞭解」,所啟用的工藝。這種反對孩子的情形,無論如美國婦女那樣,是為了不願錯失遊樂的光陰;如巴黎女人那樣,是為了恐怕她的情人離她而去;抑如易卜生筆下的女英雄那樣,只為了她「屬於她自己」,其實本質都一樣——她們全都只屬於自己,也全都沒有豐沃的生命力。與此相同的事實,配合上與此相同的理由,可以在亞歷山大城、在羅馬、事實上,在每一個其他文明社會中發現到——尤其明顯地,是在佛教發展的地方,更是如此。在希臘主義時代、在十九世紀、以及在中國的老子時代、在印度的耆那教時代,都存在有一種反對生育、只重理智的倫理,也都擁有一些有關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及左拉筆下的「娜娜」之類內在衝突的文學。
於是,我們可以在這些文明的每一處,發現那些早期階段的鄉野城市,然後,便是代表演進終點的巨大都會,空洞地矗立著,在它們的石堆中,藏匿著少量的農人。他們庇託在廢墟中,一如石器時代的人們,庇託在洞穴和土堆中那般。例如:撒馬拉城,在第十世紀被人放棄;印度阿蘇卡王朝的首都——佩特里巴特,當中國的高僧玄奘,於西元六三五年尋訪到時,已只剩下一片龐大而完全無人居住的廢屋;在柯特基的時代,甚多偉大的馬雅城市,必定也已處於同樣的狀態。從波里比亞斯以降,一長系列的古典著作家筆下,我們讀到那些古老而有名的城邦,街道已成為空盪的行列、散碎的破片,牛群在公共會所和體育館內大吃嫩草,而競技場已成為一片農田,偶而點綴著一些雕像和殘書。在十五世紀時,羅馬的人口只有一個村落這麼多,而它帝國時代的官殿,仍舊空留在那裏。而這,便是城市歷史的結論:從最初的交易中心發展起,到了文化城市,而最後,直到世界都會;為了它那巍峨莊嚴的演進歷程的需要,它首先犧牲了它創造者的血液和靈魂,然後,為了適應文明的精神,它也牲了該一發m.hetubook.com.com展的最終花朵——於是,命定的,它趨向於最後的自我毀滅。
「文明」的形式語言
而各大文化的春天時節的藝術史,應即是由文字開始的,草體的文字甚至還先於正式的著作。於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純粹的哥德式風格、或馬日型風格的精華。沒有任何其他的裝飾藝術,能具有字跡形式或原稿尺頁所表現的內在精神。回教寺廟牆上的可蘭經文,即是最完美最純粹的阿拉伯式藝術,然後,方輪到早期的偉大藝術,如牆邊圖像的建築、寺廟頂端的雕塑等。以古夫(Kufi)文字書下的可蘭經,每一頁都有一件阿拉伯風格的繡氈所具的藝術效染;而一本哥德式的福音書,也即是一座小小的教堂。至於古典藝術,則為一非常重要的例外,它不曾以筆法來美化它的文字及書卷——此一例外,是基於古典文化一貫憎恨一切持久之事,並輕視任何堅持不甘僅作為技巧的技巧。無論在希臘或是印度,我們都不能如在埃及那般,發現任何具有紀念性的文稿。古典文化的任何人,都不曾以為柏拉圖的一頁手稿,是什麼藝術遺跡,或以為索福克利斯劇本的精美版本,應珍藏於雅典的衛城。
城市那種以石頭砌成的景貌,已在光線世界中,與市民本身的人性結成一體。像市民的本性一樣,這些石砌市景,表現出全然的冷酷和理智——它們表達的形式語言,何其明顯特出?與風景泥土的質樸鄉音,何其背道而馳?我們且看那大都市的掠影:它的天花板與大煙囟,與那遠及地平線的高塔與穹頂!在一瞥之下,奈恩堡或佛羅倫斯、大馬士革或莫斯科、北京或班奈瑞斯(Benares),這些城市給予我們的衝擊,是何等強烈!我們若不知道古典的城市,在南歐的正午之下、在早晨的雲朵之中、在午夜的星光之下,所呈現的壯觀景象,我們對這些城市,又所知幾何?此外,街道的通衢,有直有曲、有寬有狹;城中的房屋,有低有高,有亮有暗,而在所有的西方都市中,房屋都以正面轉向街道,在所有東方都市中,則以房屋的背部、空白的圍牆和欄柵,面對街道。還有,方場與街角、死巷與城景、噴泉與山巒、教堂或廟宇或寺院、古代的競技場與現代的火車站、百貨商店與市民大廳,這一切的景物,所透示的精神,又是何等刺目!另外,市郊有整潔的花園別墅,也有雜亂的平房小屋;有垃圾堆,也有分配站;有時髦的社區,也有貧民的聚所,真是五色雜呈,形形色|色。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古代羅馬的郊區與今日巴黎的「福堡區」(Faubourg),古代的拜爾(Baiae)城與現代的尼斯(Nice)城,像布路爵斯(Bruges)及羅森堡(Rothenburg)那樣的小城風光;以及如巴比倫、提諾契特蘭、羅馬、及倫敦那樣的房多似海!所有這一切,都有(has)歷史,也都是(is)歷史。只要一項重大的政治事件——城市的面貌,就會隨之改觀。拿破崙曾使波本王朝的巴黎、俾斯麥也使本無足觀的柏林,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風采。
但是正當這一展延的過程,超越了一切界線時,文明的內在形式的進展,也已以深刻的統一密度,完成了自身的發展。有三個階段,可以明晰地分辨出來:——首先,文明自文化中解脫出來;然後,優雅精緻的文明形式的製造;最後,文明的僵化。對我們而言,這樣的發展已在進行之中。風格,在文化中,一直是自我實現過程的韻律,可是,文明的風格——如果我們尚可用「風格」一詞——卻呈示為完成狀態的一種表達。它達到——尤以埃及與中國為然——一種輝煌壯麗的完滿狀態,然後,將這一完滿情狀,驅入於生命的內在、不可移易的一切表現之中,驅入於儀禮和風采,以及藝術表現的精緻細微、深思熟慮的形式之中。而後,便是終結。
城市代表了心智與金錢;相形之下,鄉村是質樸野曠的所在。可是最後,城市的本身,無論其為大城或小城,若與「世界都會」比較之下,也都只變成了鄉野區域而已。〕
最後,便產生了巨大怪異的象徵、完全解放的心智之容器——「世界都會」,而世界歷史的過程,便以此為中心,而開始扭曲變形。一切世界都會中,最早的兩個,是巴比倫,和埃及新王國的底比斯。古典文化之前,克里特的米諾世界,雖然也極燦爛壯觀,可是相形之下,只能算是埃及的「鄉野」。古典文化的第一個世界都會,是亞歷山大城,它使得古老的希臘,一下子縮回到鄉野的水平,甚至羅馬、甚至重建的迦太基、甚至拜占庭,都不能壓倒亞歷山大城的地位。在印度,巨大的城市,如烏贊(Ujjain)、甘那基(Kanauj)、尤其是佩特里巴特(Pataliputra),即使在中國及爪哇,都很出名;至於阿拉伯,西方每個人都熟知巴格達和格拉那達(Granada)的神話傳奇,所帶來的聲譽。
文字語言的內在歷史,顯示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已快速發展,然而尚無文字的溝通語言(communication-language)之中,出現了最初的一些「名稱」(nouns)——一些新的瞭解事物的單元。此時,世界的秘密展現了,宗教的思想開始萌芽。在第二階段,完整的溝通語言,逐漸轉形為文法的架構,姿態變成了句子;而句子將第一階段的「名稱」,轉形成為字語(words)。尤有甚者,句子培養了理解(understanding),用以對抗感覺(sensation)。而對句子機構內的關係,與時俱增的精妙感受,也開啟了無限豐富的句型曲折演變,這些抽象關係,尤與名詞及動詞——即空間文字(space-word)及時間文字(time word)——密切相關。這是文法的開花時節,這一段時期,我們也許可定為埃及文化及巴比倫文化誕生前的二千年。第三階段,特徵是句型演變的快速消蝕,同時由造句法來取代了文法。人的覺醒意識,已進展至極度的理性化,不再需要句型演變之類的「感覺支柱」(sense-props),也拋棄了文字形式的舊日光輝,而只以慣用語法的細微的差異(前置詞、字的位置、節奏),來揮洒自如地溝通意見。藉著文字之助,理解已達臻了超越覺醒意識的目標,如今,更進一步,理解要從可感名詞的機構的限制中,解脫出來,而向純粹心智的機構邁進。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已只以心智,而不以感覺。
這種語言史上的第三階段,雖發生於生物層面,卻只屬於人類所有。高級文化的歷史,至此,乃介入了一種全新的語言,「距離的語言」(speech of distance)——書寫(writing)。這確是一種內在必然的發明,促使文字語言的歷史,突然有了決定性的改變。
真正能洞透語言的精髓的人,會摒開了所有語言學家的儀器,而直接去觀察一個獵人,如何對他的狗說話:且看,狗遵循著他伸出的手指指示。牠緊張地傾聽主人的語音,然後牠搖頭——表示無法了解這一種人語。然後,牠弄出一兩個句子,來表達牠的觀念:牠立定,並吠叫,這在牠的語言中,包含了一個問句:「這是不是主人您的意思呢?」然後,若牠發現牠對了,他仍以狗的「語言」,來表達他的高興。若是兩個人確實沒有一句共通的話可以溝通,則他們必也是以與此相同的方式,來瞭解對方的意思。當一個鄉村牧師,要對一個農婦表達某一意思時,他會銳利而不自覺地凝視著她,把她無法從一個教區牧師的方式,所瞭解到的事物,注入在他的眼中。今日的語言,毫無例外,還是只能與其他的達意方式聯接起來,才能完全使人理解,——語言的本身,從來不能獨立勝任達意的作用。
在早期古典時代,曾把鄉土人口逐漸吸收到城市中去,以此而造成了波利斯衛城(Polis)型式的那種雜居狀態,到了最後,又以荒謬的形式再次出現:每一個人,都想住在城市的中央,住在最稠密的核心地區,否則,他就好似不像一個都市人物了。所有這一些城市,都只是密集的內城。新的雜居主義,不再形成市區的地段,而是造成了一種「高樓的世界」(the world of upper floors)。例如在西元七十四年的羅馬城,雖然擁有龐多的人口,可是其周界之小,實令人可笑,——只有十九又二分之一公里(十二哩)。因此之故,這些城市一般的擴展,不是向寬度方面著手,而是越來越高,向上發展。羅馬的市區公寓,例如有名的「英蘇拉.福利古拉」(Insula Feliculae)區,街道寬度,僅及和圖書三至五公尺,可是其高度,卻是西歐絕難一見的,只有美國的一些城市,差堪比擬。靠近主城處,屋頂天花板,已經高達於山凹的水平處。
而語言則不然。語言的「老家」(home),只是語言形成的過程中,一處偶然的地方,這地方與它內在的形式無關。語言可藉舟車的傳承,由一個族群,傳播至另一族群,尤有甚者,語言可以互相交換——事實上,在研究早期種族的歷史時,我們可以、甚至必須毫不猶豫地,認定此等語言變換的現象之存在。我所要重複強調的是:當語言替換時,所涉及的乃是形式的內涵,而不只是語言的腔調。而初民一旦取用某一語言的形式內涵之後,便理所當然地將之用作其自身的形式語言中的要素了。在遠初時代,只要某一民族的力量比較強大、或是語言比較有效,便足以導致其他的民族,放棄自己的語言,而以真正宗教式的敬畏,來取用此一語言。我們不妨研循一下諾曼人(Normans)的語言變遷:他們散處在諾曼地、英格蘭、西西里及君士坦丁堡諸處,而各地的語言皆自不同,不惟如此,這些語言之間還一再地互相遞換。其實,對「母語」(mother tongue)的虔敬,只是後期西方靈魂的特徵,而「母語」這一詞眼,固然深具倫理力量,可也正是我們那不斷重演的、不同語言之間的戰爭痛苦的根源。其他文化的人們,對此幾乎毫無所知,原始的初民,更完全不曾注意及此。
在被西班牙人征服之後,一段極短的時間內,馬雅的人口離奇地消失了,他們那些巨大的空城,被原始叢林重行吞沒。這個事實,並不只是證明了征服者的殘暴獸|性——因為,若是面對一個年青而豐沃的文化人類,其自我再生的力量,會使這種獸行,完全無能為力——而且更證明了一種起自文明內部的滅絕過程,無疑久已在進行之中。如果我們轉而注意義們自己的文明,我們會發現:在絕大多數的情形中,法國貴族階級的古老家族,並不是滅亡於法國大革命期間,而是自一八一五年以來,就已漸漸消滅,他們這種生命荒瘠不孕的情形,也傳播於中產階級之間,而自一八七〇年後,且已傳至那個大革命時代,幾乎重建起來的農人階級之中。
但是,與此大異其趣的是,我們又在每一文化中,很快發現到了「首邑城市」(capital city)的類型存在。在本質上,古典的公共會所,和西方的報紙刊物,即是此類主導城市的心智引擎。有了這類事物,故在這些時期內,任何能真正瞭解政治的意義的鄉村居民,都感到自己和城市中人已處在同一水平,從而,縱使他的身體,未曾移居於城市,可是在精神上,確已進入了城市之中。農人所在的鄉野地區,一般的情緒和公眾的意見——如果還能存在的話——都被城市的報刊和言論所指引和領導。這些首邑大城,在埃及,是底比斯(Thebes);在古典世界,是羅馬;在伊斯蘭,是巴格達;在法國,就是巴黎。
語言的外在歷史中,最重要的部份,也一樣地失落湮沒了。語言發展史的速度,迅快無儔,僅祇一個世紀,就已會有絕大的改觀。我可以提出美洲印地安人的姿態語言為例,因為部落中語言的快速改換,逐使得此等姿態語言,十分必要,不可或缺,否則部落之間的互相了解,便成為不可能。另外,不妨比較一下最近發現的羅馬廣場上的拉丁銘文(約西元前五〇〇年),與普勞特斯(Plautus)的拉丁文(約二〇〇年),以及西塞羅的拉丁文(約五〇年),三者之間的差別若干?如果我們假定最古的梵文典籍,保存了西元前一二〇〇年間的語言狀態,則西元前二千年的語言,與此等典籍所示間的差異,必遠非任何印歐考古學家,以後天的方法,所能推測者,可比擬於萬一。但當能夠持續的語言——書寫——於不同的時代,介入、束縛、並固定了語言系統之後,語言變遷的速度已立即由快轉慢。因此,語言的演進遂顯得曖昧不明,難以究詰。而我們所持有的,又只是已筆之於書的語言遺跡。關於埃及與巴比倫的語言世界,我們固然擁有遠溯至西元前三千年的原始文記,可是最古的印歐語言遺跡,已只是抄本,而抄本上的語言狀態,遠較其內容為晚出。
而我認為:此處的事實,導致了完全相反的結論,這是一項具有決定性重要意義的發現。事實儼然,不容置疑,各大文化才是主體、是始因、是起源,各大文化是由最深沉的精神基礎上崛起,而文化外殼涵蓋下的民族,無論就其內在形式或整體展現而論,皆是文化的產物,而非文化的作者。各個握持並塑造人性的民族形態,所具有的風格或風格史,皆無以異於藝術的種類或思想的模式。雅典的民族,其為一象徵表記,實無異於多力克神廟,而英國人本身,也只如「現代物理學」一樣,是文化的產物及象徵。世上有阿波羅型、馬日型、及浮士德型的各個民族。阿拉伯文化不是由「阿拉伯人」創造的——恰恰相反,因為馬日文化起自於基督時代,而阿拉伯人只代表了其最後的偉大成就:一個由伊斯蘭教義結合而成的社會。正如在此之前,也是由教義結合的猶太社群及波斯社群一樣,同只是馬日文化的產物。世界歷史,是各大文化的歷史,而民族只是具有象徵性的形式和容器,在民族之中,各大文化的人們,完成了他們的命運。
在我看來,「民族」(people)是一個靈魂的單位。歷史上的偉大事件,事實上不是由民族完成的,而是這些事件的本身,創造了民族。每一項行動,都會改變了行動者的靈魂。即使這事件是由某一集團所執行的、或是在某一名字的涵蓋下進行的,但事實上,在這名字的聲望之下,所凸顯的,實在是一個民族,而不只是某一集團,這不是事件的條件,而無寧乃是其結果。東哥德人和鄂斯曼人,其所以成為他們日後的樣子,本是他們遷移時的幸運所致。並非是「美國人」由歐洲遷往美國;這一由佛羅倫斯的地理學家亞美利哥(Amerigo Vespucci)所定的名稱「亞美利加」,今日不僅是一塊大陸,而且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民族,它的民族特性,已在一七七五年的獨立運動,尤是一八六一至六五年的南北內戰,所昂現的精神提昇中,宣告誕生。
民族既不是語言單位,也不是政治單位,也不是動物學上的單元,而是精神的單位。而這隨即進而導致了文化之前、文化之中、及文化之後的民族,有所不同。在各個時代中,均可深刻地感受到一項事實,即是:文化民族(Culture-people)在特性上,遠較其他民族為特出卓絕。文化民族的先人,我稱之為原始民族,這是與時俱逝、雜湊駢形的人群組合,它們形成、解消,無一定之律則可循。直到最後,在即將誕生的文化之預兆時期(例如:先荷馬時代、先基督時代、及日耳曼時代),它們的樣態,逐漸變成更為明確的典型,它們集合了一堆人類素材,而成為族群,雖然在整個時間中,個人的形像並無、或絕少改變,但民族確在形成。就是此等樣態之疊合,使辛伯里人(Cimbri)及條頓人,經過了馬庫曼尼人(Marcomanni)及哥德人,而達到了法蘭克人、倫巴人及撒克遜人的形像。
〔房屋對於農人的意義,是一種「安定」的象徵,城市對於文化人類的意義,也即是如此。城市本如植物一般,它的發展,本與繫著在風景之上的高級文化形式的發展,沒有甚麼不同。但是,「文明」時代的巨型城市,則剝除了這一靈魂的根柢,使城市不再植基於風景的泥土中。城市的剪影,所表達的語言,是屬於它自己的靈魂的。城市與鄉野,各有不同的靈魂;在一個文化的各大時期中,城市之間,自有其不同的特色。當然,不同的文化,其城市也必然有所差異。
然而,最重要的一點是:如果我們不能理解到,逐漸自鄉村的最終破產之中脫穎而出的城市,實在是高級歷史所普遍遵行的歷程和意義,我們便根本不可能瞭解人類的政治史和經濟史。故而,世界歷史,即是城市的歷史。
如今,以哥德式的教堂、廳宅、高牆市街,以及古老的圍牆、尖塔、門柵為核心的西方成熟的古城,已被巴洛克時代成長起來的,那些更為輝煌、更為龐巨的貴族庭宅、宮殿、教會聽堂所環繞,並開始泛溢於四方,成為一堆無形式可言的建築體裁,以不斷增殖的兵營式公寓、和只供實用的房舍,蠶食了日漸衰沒的鄉村;而且,經由清除和重建,而摧毀了古老時代的莊嚴高貴的景觀。我們若從一個古塔上,向下眺望那房屋的汪洋,我們便可從這歷史存有的僵化形象中,感受到這正是一個終結的時期,正標示了有機生長的結束、無機過程的開始,因而,才出現了這種漫無節制的凝聚沉滯的程序。另外,如今也出現了那種人工的、數學的,完全與土地隔離的產物,所謂「都市建築」規劃出來的城市,純粹只是一種心智的滿足。在所有的文明之中,這些城市,都發展成棋盤似的整齊形式,這根本是靈魂消逝的象徵。巴比倫的規則的長方形建築,便曾令希羅多德大吃一驚,提諾契特蘭的同型建築,也使柯特玆(Cortez)訝異不已。在古典世界中,一系列的此類「抽象」城市,是始自特瑞城(Thurii),這是米萊特斯的希波戴馬斯(Hippodamus),於西元前四四一年所「規劃」的。普瑞恩城(Priene)的棋盤型體制,完全忽略了地基的起伏,羅德島與亞歷山大城的建築繼此而來,並成為「帝國時代」無數的鄉野城邦的典範。阿拉伯世界中,伊斯蘭的建築師,自西元七六二年起,開始設計巴格達城,一世紀之後,另一巨城撒馬拉(Samarra)也按照計畫,建築成功。在西歐與美國世界內,一七九一年所設計的華盛頓,便是第一個此類的著例。毫無疑問地,中國的漢朝、和印度的摩里亞王朝的世界都會,也都具有這樣同型的幾何模式。當然,直至今天,西方文明的世界都會,距離到達其發展的頂點尚遠,我看,在西元二千年之後,設計的城市將有一兩千萬的居民,這些城市,散布在龐大的鄉野之間,這些城市中的建築物,將會使今日最大的建築黯然失色。那時候,交通及傳播的景象,我們今天的人們,將會認為光怪陸離,不可思議,近乎瘋狂。
hetubook.com.com促使世界都會中的人們,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而只能以這種矯揉彆扭的狀態,生存下去,其原委所在,就是個人生命中的自然宇宙之脈動,已越來越微弱,而覺醒意識中的張力,卻越來越危險。在此,必須能回憶到:在內在宇宙之中,是動物的、覺醒的一面,凌越了植物的、存有的一面,而不能反其道而行。脈動與張力、血液與心智、命運與因果,彼此之間的關係,就好似繁花遍開的鄉野,對石頭砌堆的城市一樣;就好似自由的存在,對拘束的存在一樣。是以,沒有宇宙悸動在推驅的張力,只合轉入於虛無之中,而文明無他,只是張力而已。文明時代所有傑出的人們,其頭部都只被那種極端的張力所主導,所謂「理智」,只是在高度張力之下,所能瞭解的能力,在每一文化之中,這一類的頭腦,是只有在其最後世代的人們身上,才能發現的典型。我們只須在農人偶而出現於大都市的街道人叢的漩渦中時,把他們的頭部,和文明人的頭部比較一下,便可知道其中差異所在。另外,農人的智慧,是「柔弱的」、母性的機智和直覺,這和其他動物的一樣,是基於生命的感覺脈動。由這種智慧,經過城市的精神,而進步至「大都會的理智」——這一詞眼,恰可尖銳地透露出古老的自然宇宙基礎之消逝——可以描述為命運感受的一種穩定持續的減弱,而隨因果運作而生的需要,則漫無節制地增長。理智是以思想的演練,取代了潛意識的生命,它是君臨一切的,但是,沒有血色,貧瘠無力。理智的面貌,在一切種族中都是一樣的,——而在這些種族中,不斷退步的,正是血液本身。
我們不該忘卻,所謂「鄉野」一詞,最初是羅馬人給予西西里的一個基本指謂;而事實上,西西里的被征服,正是代表了:一度領先顯赫一時的文化風景,竟可以很快淪為純粹而簡單的征服目標,最先的一個例子。西那庫斯,是古典世界的第一個真正的大城,當羅馬仍只是一個毫不重要的鄉間小城時,西那庫斯即已輝煌不可一世,可是不旋踵間,與羅馬相比之下,它只成為一個鄉野之邦。與此相同,哈布斯王朝的馬德里,與教皇駐蹕的羅馬,本是十七世紀歐洲的領袖諸邦的大城,可是從十八世紀開始時起,已被巴黎和倫敦等國際都會,壓抑到了鄉野的水平。而美國在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間南北內戰時,紐約的崛起至世界都會的地位,也許可證明是十九世紀中,最具深長意味的事件。
邏輯和倫理,都只對心智而言,才是絕對而永恆的真理,故而對歷史而言,並非真理。無論在思想的領域中,內在之眼如何壓服了外在,在現實的領域中,對永恆真理的信仰,只是一齣卑瑣而荒謬的戲劇,只能存在於個人的大腦之中。真正的思想系統,實際上不可能存在,因為沒有任何的符號,可以取代真實。深思而誠懇的思想家:永遠都只能達到一個結論,即:所有的認知,先天地,都被它自己的形式所限制,而永不能夠達到文字所作的紙上談兵——只除了在技術的情形中。但在技術上,概念只是工具,其本身並不目的。像這種「神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ignoabimus)的情形,也與每一位真正的聖哲的直觀智慧相一致,即是:生命的抽象原則,只能當作文字構成的圖像、日常使用的箴言來接受,在此之下,生命仍在流動:永遠地流動。終極而言,血液畢竟強於語言,故而事實上,有名的思想家和有名的思想系統,相形之下,對人生產生影響的,還是作為人格的思想家,而不是變動不居的系統。
在西曆紀元六世紀,浮士德靈魂突然覺醒,並以無可計數的形態,顯現了自己。在這些形態之中,與建築及裝飾並駕齊驅的,即是一性徵明晰的「民族」形式,於加羅林帝國的諸民族形態——撒克遜人、斯華比人(Swabians)、法蘭克人、西哥德人、倫巴人——之中,突地,崛起了日耳曼人、法蘭西人、西班牙人、義大利人。迄今為止,有意無意間,歷史研究一致認定:這些文化民族是主體、是始因,而認為文化本身,是其從屬,是其產物。
顯而易見的,人類形體的整體展示中,那複雜混沌的情形,一直絕少為人認知。例如:對中國人而言,嗅覺是一最具特性的種族標誌。而語言、歌唱、尤其是發笑的聲調,也能使我們正確地感覺出,科學方法所無能為力的深刻差異。除此之外,展現在人們眼前的意象之繁複豐富,委實令人目不暇接,有些是實際可見的,有些則訴諸內在的視野。若想把這一切全勾勒於少數的觀點之下,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企圖。而所有這一切,全是整個圖像的一面,這一切的特徵,構成了整個的圖像,而彼此又互相獨立,各有自身的歷史。例如,在有些情形中,人的骨骼結構(尤其是腦殼形式)完全改變,而肉體部份——臉部——卻毫無改觀。學者布魯曼巴哈(Blumenbach)、彌勒(Muller)及赫胥黎(Huxley)皆曾斷言:同一家庭中的兄弟姊妹,也許會表現出各種的差異,可是他們活生生的種族表徵之一致,卻是任何看到他們的人,都會一目了然的。除了血液的力量,世代以來一再印鑄出相同的生命形象,成為「家族」(family)的特徵;以及泥土的力量,明顯彰著地烙印在人的身上之外,在相近的人們之間,尚有著一種神秘的原始力量之共振。懷孕的婦女,有所謂的「胎教」(Versehen),這邊只是種族與生俱來的,一種非常深刻而有力的「定形原則」(formative-principle)運作的一特例,還不算十分重要的例子。此一生命脈動的定形力量,此等對個人自我型式之長成,所具的強烈而內在的感受,實在是無待贅言的。就是此等族類精神,滋衍了種族(Comradeship breeds races)。法蘭西的貴族世家(noblesse)及普魯士的閱閥士紳(Landadel),便是真正的種族典型。而歐洲的猶太人典型、及其數千年的聚落生活,也是由此等碩大無朋的族類精神滋生而成的。當一群人已以共同的精神,屹立於天壤間甚久,並在其共同的命運之前,結合起來,則此一族類精神,便將這些人熔冶為一種族。於是,一個種族理念(rece-ideal)出現了,至高無上,戛戛獨絕,出現在文化的早期——如吠陀時代、荷馬時代、荷享斯多芬的騎士時代——其時,統治階級對此一理念的熱切期整,其意志的專注執著,皆朝向於實現此一理念而進行,以迄終致達成了此一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