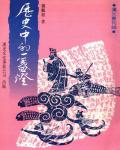二輯
關於烏納穆諾的「生命的悲劇意識」
當笛卡兒的方法論(Discurs sur la m'ethodc)以理智掛帥時,巴斯卡卻要求理智須要謙卑:「心靈自有理智所無法了解的理由」。這是十七世紀的事了,從此以降,歐洲思潮的持續型態中,這兩大|波濤卽衝擊抗衡不絕。一方面實證主義分析方法等層出不窮,而另一方面在文學和哲學上卻也有強烈抵制理智的波潮。十七世紀古典主義時期,學者對心理探索的持續興趣卽已和基督教哲學相滙合,以爲人類所帶給世界的,正是他對罪惡的智慧和墮落。到了十九世紀末期,與烏納穆諾同時的法國大文學家梵樂希(Paul Val'ery,1871-1945)與烏氏探索同樣的難題:人類幸福和解放之道。梵樂希所提出的「在全有中存有個體,而在個體上存在全有」(ll y a de tous dans' chacun et de cha cun dans tous)和烏氏所說的宇宙意識也極爲類似。以悲劇爲起點地確認人和掙扎中的尊嚴,並由此激生出改良人類和社會最終能力的信仰,是烏氏和這批法國作家的共同特徵。不但如此,烏氏狂亂而痛苦的文字;對騷擾、擺盪甚至極端痛苦的心境描寫;對心靈的探索表現於苛峻的顫慄和扭動之中;對人類複雜心態的裸|露遠超過邏輯的理念……在在與法國莫里亞克(Marcriac)、馬羅(Malraux)等人相似。這是理智與科學泛濫之後,從魔魘中驚醒時的呼吶,隔地相通,傳達的是人類文化究竟應何去何從的問題。
烏納穆諾(Miguelde Unamuno,1864-1933)這位西班牙哲學家的哲學思考,原先只想極力闡釋西班牙的靈魂與精神,說明十九世紀以來,在歐洲的悲喜劇激盪中,西班牙自處與自行之道。但因他堅信「所有人類靈魂都是兄弟般的靈魂」(第三九八頁),是以他所思考與探索的問題也指向全人類生命和人性的底層;西班牙天主教的宗教意識,固然是全書所致力勾劃的主題,但他所呈現與揭露的,卻是那些深深震撼我們的存在問題。他說:「不是爲了要思索存在,而是要去生活我們的存在」(第二一四頁)。就烏納穆諾而言,人類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生命的悲劇意識。經由他那扭曲顫動、弔詭激|情的表述形式,它幫助我們去了解和忍受人類之噩夢——那是一個遠比他作品本身更混淆而矛盾的存在,那就是:人生。
現在,且讓我們走入西方哲學的傳統裏予以省察。
歐陽竟無『熊子眞唯識概論序』說:「菩提心爲因,大悲爲根本。菩提心者,大悲之等流也。悲之所至,智之所至。若使無悲,是無法界;若使無悲,是無功德;滅種焦芽,沉沉曷極?!無悲而學,是爲阿世曲學;若使爲己,是爲斷滅學hetubook.com•com。君子由之而無結帶。大悲者清淨之等流也,民衆生百十一苦而起大悲。苦且不知,觀於何起?世聞法救世,悲起於有情,緣有人我國界強弱等故;宗教家救世,悲起於法,緣有神我種種法等故」。烏氏所說,雖爲宗教義,不離世界法,聊以此序爲烏氏全書之總贊。
希臘哲學的上帝觀與早期神話思想中的宙斯神等,有密切的關係;至柏拉圖(Plato)、亞理斯多德(Aristotle)時,卽發展成一種思辨的上帝觀。就柏亞二氏的哲學來說,人安身立命之道,在於人能本此理智以觀照——永恒的眞理,而非如猶太宗教思想影響下,以人之最後安頓,在於皈依——超越於人之上的上帝。猶太宗教這個超越、外在於人而又非人所能企及的神靈,非人之理性所能了解;與上帝的溝通或肯認,並不來自思辨,而是皈依。匐匍哭泣而順服在天主的脚下,用自己的淚水洗淨自己的罪愆。從這裏看來,後代依希臘哲學而建立的基督神學。在本質上卽與猶太教精神了不相應。中古基督教神學家對此不加辨別地綰合爲一,並視之爲宇宙人生的究竟眞理,在基本上卽存在著日後分離的根源。因爲人的理性活動與信仰本無必然的聯鎖,理性逐步發展,人卽逐步與上帝疏離。在傳統神學理論動搖及新興科學思想盛行之下,傳統宗教信仰面臨嚴重的考驗,人心也被科學所展示的理想所吸引,霍德林(Holderlin)所說的「上帝退隱」或尼采(Nietzsche)所說的「上帝死亡」都是此一意識下的產物。康德(Kant)爲了解釋疏通此一疑難,轉而從批判傳統形上學入手,其目的也在解決傳統形上學不能肯定上帝存在的問題。……總括地說,自文藝復興、理性主義興起以後,理性與信仰之間的爭衡,主要表現在:①以神爲宗教信仰的對象,在人的理性中得不到肯定;且上帝既是一超越神靈,則在人内在的修持裏亦不能見到。②如此則上帝超越外在於人而獨立存在,與人沒有什麼關係,上帝卽本質地與人疏離。這是西方哲學與神學發展中的大事。烏納穆諾此書卽是針對這兩點提出新的詮解與肯認。
當然,哲學上的比附與牽合,極爲危險。烏納穆諾的理論所帶來的意義和價值,並不在於它是否可與我國相通。當烏氏以〔①肯定宗教精神和信仰爲一切理性之基礎,不可廢棄。②上帝爲非實質意義之存在,是人藉著生命而彰顯的内在的無限投影〕爲兩大支柱構建他的理論時,我們所要探討的是:這種現象何以會產生?而它所代表的意義又是什麼?
從本書最後一章「唐吉訶德與近代歐洲的悲喜劇」裏,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烏納穆諾對人類心靈、慾望的探索,以及在生、死、宇宙和眞理之間界定人的地位;www.hetubook.com.com宗教智慧的重新提出,並宣稱知識、理智和科學的畸型發展有其嚴重缺憾;……等等,無不涵應着一個大時代的主題,那就是自從文藝復興以後,由理性和科學所帶來的「精神危機」(La Crse de I Esiprit)如何突破這種危機?如何消解知識文明所帶來的威脅?烏納穆諾和他同期的哲人一樣,爲此憂心不已。
在烏氏的理論裏,他從本質上確認理智與生命、哲學與宗教之間永無協調之可能;人類思想的悲劇性歷史,根本就是理智和生命之間衝突的歷史。烏氏承認理智與生命一樣,有其獨特而迫切的需要(第一〇九頁),但因它無法解決生命問題,是以它有其存在上的限制,須要宗教予以彌救。他以此解決了天主教長期徘徊在理性主義和神秘主義之間的困境;也說明了人固然不得不借助於理性或邏輯,但有關生命的安頓,仍須在宗教中獲得。但弔詭的是:烏納穆諾所說的宗教與上帝,涵義和中古以前以神爲本的觀念並不一致,我們可以說他是經由對人高尚精神的認識來說明相應於此一精神的上帝或宗教精神,是經由對人的肯定而肯定上帝。這種由人至神的路向,顯然與西方傳統神學觀不同,所以他說:「在教會的神父當中仍有一批人還不瞭解上帝自身的非實質性意義(雖然對我們來說,這已經是非常清晰而且確定的觀念)」(第九二頁)。從這個意義上看,烏納穆諾已完成了上帝與人之新關係的探索,這種探索固然有強烈反理性主義的色彩,但他和笛卡兒(Descartes)等人也有相似之處:深入思考宗教與理智科學之間的衝突,而建立了以「人」爲主體的哲學世界。
在說明生命悲劇意識的宗教消解之道以前,我們有必要對他「永恆生命的渴望」有所瞭解:面對著理性主義與「爲知識而知識、爲眞理而眞理」的科學觀和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狂潮,烏氏不斷地駁詰:「沒有自我意識、沒有人格,純粹的思想會有可能嗎?」一個哲學家在投入思考之前,他必須先是一個人;而人堅持自己無限存在的努力,就是我們眞正的本質,也是一切哲學的內在起點和一切知識的情感基礎。這種對個人能無限存在的渴望和努力其實是碰觸到「死亡」這個問題時才會產生的。人生大事,不過生死兩端,而生存又是爲死亡而作準備。豈僅生存如此?蘇格拉底不也說哲學的定義就是「死亡的準備」嗎?對個體生命有限性的沈思,必將引發我們極度痛苦的意識,但從這裏我們才能省視到:生命固已長逝不留,但人類對生命的狂戀與執著,卻是可以無限延伸的,人們常用這份不朽的渴望,驅散死亡的陰霾與悚慄,毫無畏縮地面對肉身的消逝,並從此得到慰藉:「從悲慘的深淵裏可以躍
https://www.hetubook.com.com現出新的生命,並且也只有飲盡精神的悲愁,我們才能嚐生命杯底的甜蜜」(第七十八頁)。矛盾?是的,生命的悲劇源於理智和心靈的衝突,烏納穆諾既肯認哲學是來自我們對生命本身的覺知,則他必得不斷地強調心和意志的需求,並尋求情感與意志的上帝:「第一個上帝(理性的上帝)是人類自身藉著定義而顯現的外在的無限投影,祂是抽象的、非人的人的上帝。另外一個上帝(情感與意志的上帝)則是人類自身藉著生命而彰顯的内在的無限投影,祂是實實在在的人,有骨有肉的人的上帝」(第五頁)。理性,並不是可以全然捨棄的;但烏納穆諾無寧是更要強調:知識和理性必須爲生命的本質服務,它才具有意義,僅僅爲了知識而知識,只是一種生命的拋擲,一種陰鬱淒涼的乞求而已。一個哲學家並不止用理智來從事思考;更須以他全幅靈魂與肉體作整體的投入。因爲「以有涯逐無涯,殆已!」所以,他所追求的是永恆的生命,而非永恆的知識;如果我們斲喪了生命的本質,我們的理性也將沈淪棄喪(但,生命悲感的根源就在這裏:凡屬於生命的事物,都是反理性的)「這一份對永恆生命的渴求,在宗教信仰的淵泉裏才能得到平緩」(第七十八頁)。
他說:「對於人格的與精神的上帝信仰,根基於我們對自身的人格與精神的信仰」(第二〇六頁)。爲此,我仍然相信他的理論和佛學有可以銜契之處。
或許我們可以說烏納穆諾種種辯說,都只在喚起人的自覺,經由這份自覺驅策着我們以宗教情懷來履現我們自身所擔負的職責,將自我投入羣體,帶著無限的愛與慈悲,和別人溝通,並藉此抖落自我的怠惰和貪婪。——烏氏以此作爲矯治當時社會秩序的靈藥。因爲他是個活生生的人,他的思考卽面對着他所生存的社會,是以他這套看來扭曲而驚悸的學說也是爲了處理當時西班牙政治與社會狀況而產生的。烏氏渴望一種和平忍讓的統一,因此他強烈抨擊無政府主義和逃世的僧侶,也譴責社會集體的罪惡汚染;他歌頌的是自由、倫理以及那些眞正關懷他周遭人物的人。他努力地嚐試將這種社會的天主教精神透過明確的方式予以表達,作爲他對文化理想所能提供的最大貢獻。對他而言,西班牙天主教的宗教意識就是唐吉訶德式的意識(一種不屈服於科技性邏輯的典型)。
正因每個人所需要的上帝不同,所以人們就依照著自己的形像去塑造衪,並使自己成爲上帝。烏納穆諾說:「宗教的渴望是希望能夠握有上帝,而不是讓自己被祂掌握」(第二九四頁),「如果此生我們把希望寄託給基督,那我們將是所有人類中最悲慘的了」(第五四頁),他這種對上帝(神)的見解和堅稱https://www.hetubook.com.com「對我自己而言,我就是一切」的態度,使我想起了中國佛教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氣魄和逕爽無畏的肯認;禪宗呵佛駡祖、佛在心中坐……的精神,在此彷彿也有一番接應。上帝非實質的意義、和自我主體性的追求,在我國哲學(包括佛教)裏,原是素所習知的觀念,烏納穆諾在經過一番慘烈而詭譎的剖析之後,重新提契這種精神,是很值得玩味的。
烏納穆諾本身是位文學兼哲學家,但他狂暴易怒、懷疑矛盾而又酷愛震盪刺|激的性格,卻深深影響着他思考的型態和表達方式,充滿着內在的矛盾。跳躍而夾纏、扭曲而又冗長。有時一整段文字只是一句,有時又在一個短句中作了三四次的否定與肯定。不但如此,這本書雖然看來結構也很完密,但其實只是種即興作品的形式,由他的筆記摘錄而成。讀來份外艱苦。對這樣的作家、這樣的作品而言,翻譯,尤覺艱辛。
(全書完)
蔡英俊翻譯的烏納穆諾「生命的悲劇意識」已經出版了。烏納穆諾自己說這是一册不著邊際而又急切反映生命悲劇意識的論文,像一則永無結局的冗長故事,狂熱、而又充滿了内在的矛盾。——是的,在理性與信仰之間,生命的存在,原本卽是個茫無止憩的矛盾與撕扯。從「邏輯的上帝」(至高的理性)到「生命的上帝」(至高的愛)烏納穆諾企圖揭示一幅充溢著慈悲、愛、希望和悲憫的世界,並藉此來擁抱那對生命永存不朽的渴望。
此書是根據英譯本再予迻譯的,蔡英俊先生翻譯此書,功力極爲深穩,態度也極嚴謹。他不但把原文詰屈顫動的文字以中文語法清新優美地譯出,對烏氏本身理路的轉折也有着充份的瞭解和掌握。這一位受過思考訓練的翻譯者,熟於原文豐富的引申義、典故、雙關語及多義性等,透過文字上的再創造而予以新的綜合,以此保存原著的全貌,令人激賞。他那含有註解、補充及批判性等多種作用的譯註幾乎可以和原著相媲美。譯註豐富而多趣,帶着溫潤的情感和生命眞誠的體證,審視着這位愁苦激切的西班牙詩人。其中最精彩的幾段,都表現在比較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悲劇精神宗教意識上,簡潔而深入。可惜蔡先生未續此專力發揮,否則必然更有意義。因爲在介譯西方著作時,以自我文化爲立場作批判性的接納和溝通,是當前所急需的。我們對西方學術固已不甚瞭解,對我國固有文化亦荒疏得可怕,有人朝這方面努力,總是值得喝彩的。
科學、追求實用、崇信鬪爭、迷於進化……構建了一個非哲學的工業時代,它深受短視的專門化和歷史唯物論所影響,脫離了神、也背離了人,而墮入物化的樊籠:「科學把人格貶爲只是一種在時間裏不斷流動的www.hetubook.com.com複合,藉而摧毀了人格的概念,也摧毀了精神與情感生命的基礎」(第一五〇頁)。面對這種境況,烏納穆諾和那些思考人類命運的志士一樣,期盼從與理智相對的精神裏重新肯認人的價值,因而「上帝」的宗教意識遂被重新提出,在此,我願借史賓格勒一段精闢的言論作爲當時普遍意識的說明,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西方的沒落」第十六章:「清敎運動與理性主義之後兩世紀,機械的世界觀已達其顯極,成爲代表時代的有力『宗教』除去了體驗與沉思的視景,而代之以機械性的觀點。這時的信仰,無非是力與物質而已,『知識便是力量』。……我們今日在歐美世界中,人們對哥德式或後期古典、或中國道教的崇拜,不過是希望能填補自我內在的空虛罷了。但這類虛擬宗教之所以能出現,無疑預示了一種新起而眞正的追尋精神即將出現。它最初雖是沉寂無聲,但不久以後,便已在文明化的覺醒意識中公然而強烈地喧嚷開來。這一階段,我稱之爲『第二度宗教狂熱』(Second Religiousness)這第二度的狂熱開始於理性主義因無助而萎褪,然後,文化春天的形式重趨明顯,終於,整個原始宗教的世界,本已退居塵世信仰的巨大形式之後,如今又以流行的融合型宗教的姿態,重新回到前景之上」。烏納穆諾的宣言,無疑是人們內在虛渴時,宗教意識復甦下的產物。湯恩比(Toynbee)所說文化生長中必須跨過「佩劍的救世主」、「用時間機器的救世主」、「哲人皇帝式救世主」而到達「上帝化身的救世主」(The God incarnate in a man)才能征服文化的死亡。意義與烏氏相同,同樣指陳一樁事實:文化的命運有待決於精神力量。透過受苦與慈悲,人們用愛結合而努力。
烏納穆諾會說基督教導源於希臘與猶太兩大精神潮流(第七九頁)。是的,從這種結合型態上,我們即可看出信仰必與理性離異的基因,這是它内存的矛盾,猶如人生。
死亡、就是死亡!透過死亡的摧折與揉傷,人們在這層不可宣釋的苦難中,因受苦而產生了悲憫、產生了愛。死亡,是一切生機洋溢的泉源,而愛則是它的孿生兄弟、也是唯一能對治它的靈藥。愛,是相互的感通與結合,也是一種了無牽絆的關懷。當我們從自我意識的執著開始,逐漸逼向自然世界的同情與關切時,「宇宙性的愛」於焉展開。在此時,我們將會發現全體萬有和宇宙同樣是具有意識的人。這種將它所愛的每一件事物人格化的宇宙的意識,烏氏把它稱做「上帝」,他激切而堅定地宣稱:「信仰上帝就是創造祂」(第二一三頁)——就這種宗教觀而言神之所以存在,是因爲我們希望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