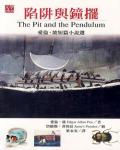與木乃伊一席談
沒多久,我們與公爵之間的談話就變得極其熱絡。令我們頗為好奇的是,他雖然是個木乃伊,但臉上的表情卻相當活潑。
我們極為焦慮地看著伯爵,等待回答,但他卻始終不說話,只是漲紅了臉和低垂著頭。沒有一個勝利比這個勝利更極致的了,也沒有一個失敗,比他這個失敗更不優雅的了。事實上,公爵的樣子窘得讓我不忍心繼續看下去。我拿起帽子,向他硬繃繃地一鞠躬,就告辭了。
我大喊一聲,其他人聞聲望向木乃伊,同時看到了這現象。
「你在經歷防腐程序時,」白金漢先生說,「想必被瀝青包裹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我不知道要怎樣把話接下去,就提高嗓門,指出埃及人對蒸汽動力一無所知。
「我猜,」格列登先生說,「聖甲蟲乃是古埃及的眾神明之一。」
「哈,我就知道——知道這是一個充滿無知的可憐時代!我現在無法把防腐程序的細節一一說明。你們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在古埃及,防腐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動物性的功能保存住。我是在最寬廣的意義下使用『動物性』這個字眼的,換言之,它除了指人的生理功能以外,還指生命功能。我重覆一遍,防腐的原則是要把人的一切動物性功能懸擱起來。簡言之,一個人在接受防腐程序時不管處於何種狀態,防腐程序都會把他當時的所有狀態保存下來。幸運的是,我是聖甲蟲的血裔,所以我是活著被防腐的,這也是現在我能夠坐在你們面前說話的原因。」
在篷諾納爾醫生家裡,早已聚集了一小群神情熱切的夥伴。他們等我已等得相當不耐煩;木乃伊就橫放在長餐桌上。我一到達,開驗的工作就告展開。
我這時問公爵,他對我們的鐵路有何感想。
篷諾納爾醫生把話重覆了一遍,而且為了讓這位外國人明白他的意思,又加上了很多附加的解釋。聽罷以後,公爵沉吟了好一會兒,才說道:
「你入土的時間,距今已有五千多年,」醫生說,「那麼,很明顯的是,你們時代上距天地的創造,大約只有十個世紀左右。」
「毫無疑問是這樣。」
在木乃伊的脖子上,有一個用玻璃珠子綴成的圓柱形領圈。玻璃珠子以不同的顏色組成各種形象,有神明的形象,也有聖甲蟲的形象。在木乃伊的腰部,繫著一條形式與領圈類似的腰帶。
聽了這話,白金漢先生的身體微微動了一下,並將插在左嘴角的右手拇指抽出——但與此同時,卻把左手拇指插入到右嘴角去。
吃過一頓這樣的便宜飯以後,我就戴上睡帽,抱著把它戴到第二天中午的期望,把頭放到枕頭上面去。由於一向問心無愧,我馬上就熟睡了。
「這是毋庸置疑的。」公爵答道,「所有生前就進行防腐的聖甲蟲族裔,是至今還活著的。有些生前蓄意接受防腐程序的人,有可能因為受託人的疏忽,至今仍留在墓穴裡。」
「格列登先生,你的話真讓我訝異萬分。」公爵說,再次坐到了椅子上,「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民族,是承認世界有超過一個以上的神明的。不管是聖甲蟲還是聖䴉,對我們來說都是唯一神的象徵。這個唯一神威嚴得我們無法逼視,只能透過一些中介物來敬拜祂。」
「你為什麼不說話呢,白金漢先生?你有聽到我問你的話嗎?你可以把拇指從嘴巴裡抽出來嗎?」
這讓我們恢復了自信。接著,醫生帶著極莊嚴的神情向公爵探身,說他希望對方能以一個紳士的榮譽感,真誠地回答以下的問題:古埃及人——不管哪個時期的——懂得製造篷諾納爾錠或布蘭德雷斯藥丸嗎?
「樂意之至,」他說,「我們那時候的平均壽命,大約是八百歲。很少人會在六百歲以前死掉,除非是碰上了特別嚴重的意外。也有少數人可以活到一千兩百歲的。不過,八百歲應該是一個平均值。自從發現了防腐的方法以後,我們的哲學家就想到,如果能把我們的自然壽命分成幾段來活,不但可以滿足我們對未來的好奇心,而且可以讓科學大大獲益。以歷史學為例,經驗證明,這種分段活的方法是不可少的。因此,當一個史學家在五百歲時寫成一部大部頭的史書,他就會讓自己接受防腐程序,然後留下指示給受託人,要後者在五或六百年後讓他活過來。活過來之後,他幾乎必然會發現,他所寫過的史書,已被後人以注釋或校訂的名義,任意割裂、增刪、扭曲,變得面目全非。因此,他必須把史書重寫一遍。這種不斷重寫史書的方法,可以讓我們的歷史不致淪為完全的虛構。」
「哦,這個。一般來說,古埃及人在對屍體進行防腐以前,都會先把腦和腸子取出。但聖甲蟲家族的人卻不實行這一套。如果我不是聖甲和-圖-書蟲的血裔,那我的腦和腸子就會被取出。而沒有這兩種東西,我就不可能活過來。」
由於在屍身上找不到開口,篷諾納爾醫生就打算準備解剖器具去。不過,這時候,大家看到時間已過了午夜兩點,就決議把解剖木乃伊的工作,延至明天傍晚再進行。然而,大家正要散去的時候,卻有人提議,何不用伏打電堆對木乃伊做個實驗。
我們都大為尷尬,決定把話題轉到時人對形上學的攻擊。我們拿出一本叫《日晷》的書,唸了一兩章給他聽。這本書,內容儘管不是那麼清楚,卻是被當時的波士頓人稱為「偉大的進步運動」的表表者。
「瀝青。」
想要打開棺蓋而不破壞其完整性相當困難,但我們終於還是做到了。棺蓋打開後,就出現第二層棺材。這一次是棺材形狀的,體積要比第一層棺材少上許多,但在其他方面,都跟第一層棺材一模一樣。在第一、二層棺材的空隙間塞滿了樹脂,這讓第二層棺材的顏色多少受到了磨損。
「被什麼包裹?」公爵說。
我於是又問公爵,他們時代的人懂不懂製造凸透鏡以致玻璃。不過,我話還沒有說完,剛剛那個同伴就用手肘輕輕撞我一下,低聲求我看在老天的份上,先看看迪奧多羅斯的著作,再問這方面的問題。至於公爵本人,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而是反問我:現代人是不是有精細得足以切割埃及人那種多彩浮雕寶石的顯微鏡?就在我琢磨該怎樣回答時,篷諾納爾醫生以非常不尋常的方式介入了談話。
接著我提到鋼鐵。不過,公爵只是仰起了頭,問我,難道鋼鐵有辦法刻出像方尖碑上那麼尖細銳利的圖案嗎?而古埃及人單靠銅製的鋒利器具就足以把它們刻出來。
「嗯,我想我大概知道你說的是什麼。不過。我那個時代很少會用二氯化汞之外的東西為木乃伊防腐。」
「為什麼?」公爵回答說,看來頗為驚訝,「我死的時候才不過七百歲多一點點!我父親就活了一千歲,而且死時一點老態也沒有。」
「聖甲蟲的血裔!」篷諾納爾醫生驚呼說。
「古埃及人壽命綿長,加上可以把一生分開幾段來活,這對知識的累積發展來說,必然有極大的助益。然而,古埃及的各門科學為什麼又會遠遜於現代人,又特別是美國人呢?據我推斷,原因應該是埃及人的頭骨太硬的關係。」
他聽得津津有味,看來似乎饒感興趣。等我們把話說完,他就表示,在很久很久以前,埃及也出現過類似的制度。當時,埃及有十三個省份一起從王國中獨立出來,組成聯盟,決心要為其他人類提供一個完美國家的典範。他們集合了一批聰明才智之士,制定了一部人類所能想像最完美的憲法。有過一段時間,他們把這部憲法執行得很成功(唯一美中不足是喜歡自誇)。然而,當後來另外十五省份加入到這個聯盟以後,一切就變了,最後,從這個聯盟,竟誕生出一個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可憎和最不得人心的獨裁政權。
我們全部人一起火速往外跑,心想這一回肯定要為可憐的篷諾納爾醫生收屍了。沒想到,樓梯才下到一半,我們就欣見他一切無恙地往樓梯上跑,速度快得難以形容。他的神情極為熱切,比先前還要肯定我們進行電擊實驗的必要性。
「先生,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公爵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他回答說。他說我們的鐵路不結實、設計差勁而造工粗糙,說它們根本不能和古埃及那些寬闊、平直、鑲了鐵溝槽的大驛道相比:靠著這些大驛道,埃及人可以運送一整座神廟和高達一百五十呎的方尖碑。
至於我本人,也深信沒有什麼是不妥的,唯一的反應只是站開了幾步,退到木乃伊拳頭搆得著的範圍外。篷諾納爾醫生雙手插在褲子的後口袋裡,怔怔望著木乃伊,臉色漲得通紅。格列登先生撫摸自己的髭鬚,並把衣領翻了起來。白金漢先生則低下頭,把右手拇指插在嘴角。
撕去木乃伊身上的紙草紙後,我們發現屍身的肌肉保存得異常良好,一點腐臭味都沒有,膚色尚帶微紅。肌膚僵硬、滑順而有光澤。頭髮和牙齒也狀況良好。眼睛看起來是挖去了,植入了玻璃珠子,非常漂亮,而且神奇般就像是有生氣的。不過,它那種目不轉睛的瞪視卻讓人不自在。木乃伊的手指甲和腳趾甲都塗了鮮豔的金色。
「樂意之至!」公爵回答
和圖書說。回答之前,他先從他的單框眼鏡打量了我一下,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膽敢直接問他問題。這具木乃伊,是薩布雷塔舒上尉(醫生的一個堂兄弟)數年前從埃及帶回來的兩具木乃伊之一。它們出土於厄拉提雅斯附近一個古墓。厄拉提雅斯位於利比亞山脈,離尼羅河的底比斯城有相當一段距離。在這個地點所發現的古墓,其壯觀雖不如底比斯城,卻更引人入勝,因為它提供了更多有關古埃及人私生活面的資料。我們眼前的木乃伊所從出的那個古墓,據說牆壁上密佈著溼壁畫和淺浮雕,而且有雕像、花瓶和式樣繁富的馬賽克畫,在在顯示出墓主人生前的富有。
毫無疑問,聽到木乃伊竟然開口說話,我們最自然的反應理應只有三個:奪門而出,不然就是歇斯底里地狂叫,再不就是馬上昏厥在地。這三個都是很合理的反應,沒有什麼好笑話的。話雖如此,但不知出於什麼理由,我們沒有一個人表現出上述三種反應的任一項。不過,真正的理由可能在於時代的精神使然,因為我們的時代是把矛盾律奉為圭臬的,認定一切吊詭或不可能的事情,都一定有一個解釋。另外,我們沒有方寸大亂,也許也是因為木乃伊的說話態度使然。他說話的時候,一副自自然然、氣定神閒的樣子,讓他給人的恐怖感大大減低。不過,不管理由是什麼,反正我們的成員裡就是沒有人表現出特別的悸懼,或者看來認為眼前的情景有什麼特別異乎尋常的。
木乃伊就在第三層的棺材裡,我們把它挪了出來。我們本來預期,它會像大多數的木乃伊一樣,是用亞麻布條包裹著。不過,我們沒看到亞麻布,只看到一層鞘狀的紙草紙,上塗一層灰泥,灰泥上又漆著厚厚的金漆和彩繪畫。圖畫中畫的是各種靈魂被認為應盡的義務和靈魂面見各個神明的情景。另外還有一些肖像,不過,它們畫的可能是同一個人:死者。木乃伊從頭到腳書寫著一行垂直的銘文,以表音的象形文字書寫,記載的是死者及其親屬的名字與頭銜。
篷諾納爾上
我不能說這個現象讓我感到震驚,因為「震驚」這個字眼尤不足以形容我當時的心情。不過,也有可能,我這樣神經質的反應,只是晚餐時喝多了黑啤酒所致。至於我的其他同伴,卻一點都不打算掩飾自己的害怕:篷諾納爾醫生全身簌簌發抖,任誰看到都會心生憐憫;格列登先生不知變了麼戲法,一下子就不見了人影;白金漢先生則是手腳並用地爬到了桌子底下。
「我明白了,」白金漢先生說,「這麼說來,已出土的所有木乃伊中,但凡包含著內臟的,都是屬於聖甲蟲家族的了。」
聽罷以後,公爵給我們說了幾則軼事,而這些軼事在在說明了,古埃及也一度流行過與加爾和施普爾茨海姆提出的顱相學相類似的學問,不過後來卻慢慢式微,最後甚至沒有人記得有過這麼一回事。
「請你原諒,」篷諾納爾醫生說,一手輕按在公爵的手臂上,「但不知你是否容我打個岔?」
「古埃及的什麼之一?」公爵高聲說,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不管你在忙什麼,一收到這信就盡可能過來一趟吧,我的好朋友。過來幫我們的忙和跟我們一起慶祝吧。因為,經過長久鍥而不捨的折衝,我終於獲得市立博物館館長的首肯,對木乃伊——你知道我說的是哪一具——進行開棺檢查的工作。只有幾個朋友會一起參與此事——其中當然包括你。木乃伊現在就在我家裡,我們準備在今晚十一點把它打開來。
格列登先生回答得又長又棒,用的也是古埃及語只可惜美國的印刷廠沒有埃及象形文字的字體,以致我在這裡無法把他的卓越雄辯原文照錄。
「我不得不再次承認,」公爵文縐縐地說,「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可否請你說明,你的這個說法,是以哪一門科學為根據的呢?」
握手禮結束後,我們馬上動手修補我們在木乃伊身上弄出來的傷口:縫好太陽穴的肌肉,給右腳拇趾包紮繃帶,給他的鼻尖塗上一平方吋的黑灰泥。
「但這跟你現在還活著有什麼關係呢?」
在他的建議下,我們選定電擊的下一個部位是鼻尖。等篷諾納爾醫生用顫抖的手把木乃伊鼻尖的皮膚切開一點以後,我們就把電線插上去。
格列登先生從木乃伊的微紅色表皮推斷,用來對它進行防腐的物質是瀝青。不過,當我們用器具從皮膚上刮出若干粉末,投到火裡去的時候,卻聞到樟腦和其他帶甜味的樹膠氣味。
我們費了好些勁才把木乃伊太陽穴的肉給刮去一點,因為這個部分的肉比身上其他部位都要硬。然後,我們就對準它的太陽穴施以電擊。不過,一如所料的,木乃伊一點反應都沒有。這個結果,看來說明了一切,所以,大家就一面笑自己的荒唐,一面互道晚安,準備離開。。然而,要轉身以前,我卻不經意看了木m.hetubook.com•com乃伊一眼,而且馬上愣住了。雖然只是簡短一瞥,我卻清楚看到,先前木乃伊那兩顆被認為是玻璃珠的眼珠子,還有它那個目不轉睛的瞪視,現在都被眼瞼大部分遮住了。換言之,它的眼睛已幾乎閉了起來,只有一小部分的眼珠子可以看得見。
看來,我們已經處於全盤皆墨的邊沿。幸而,就在這個緊要關頭,篷諾納爾醫生伸出了援手。他問公爵:難道埃及人真的認為他們在衣著上可以與現代人匹敵嗎?
我注意到,公爵的身體有點微微顫抖(公爵似乎就是這個叫阿拉米斯塔奇奧的木乃伊的頭銜),這毫無疑問是因為冷。有鑑於此,醫生馬上前往臥室,從衣櫥裡帶回來一些衣物,包括黑色大衣、格子呢的天青色燈籠褲、粉紅色的方格外套、錦緞寬鬆背心、白色襯衫、一根有勾狀把手的枴杖、一頂無邊帽、一雙漆皮靴、一雙稻草色小羊皮手套、一副單框眼鏡和一個波浪狀的領結。由於木乃伊的塊頭要比醫生來得大,幾乎是二比一,所以要穿上醫生的衣服,頗費一番工夫。不過,最後他還是穿好了,算得上是衣冠楚楚。格列登先生挽著他手臂,把他帶到壁爐旁的一張舒服椅子坐下。醫生則搖鈴把僕役叫來,吩咐送上雪茄和葡萄酒。
由於從白金漢先生那裡得不到答話,木乃伊就帶怒氣地把臉轉向格列登先生,並用咄咄逼人的語氣問他,我們這樣對他,究竟有何居心。
接下來,我們談到了民主制度的重要性與優越性,並不憚其煩去形容生活在一個有投票權而沒有國王的地方是多麼愉快的事,一心想打動公爵。
對一具有三、四千年歷史的木乃伊施行電擊,儘管不能說是十分正常的主意,卻相當有原創性,我們馬上就被吸引住了,我們帶著好玩多於嚴肅的心理,在醫生的書房裡準備了一個伏打電堆,對木乃伊通電。
「如果我當時真的是死了的話,」公爵回答說,「那大概我現在就還是死的。從你們使用的伏打電堆,我就看得出來,你們仍然生活在知識的襁褓階段,對很多我們古代人來說稀鬆平常的知識一無所知。事實上,我並不是死了才被製成木乃伊的。我那時只是得了強直性昏厥,而我的好朋友卻以為我死了,於是馬上為我進行防腐程序。我想,你們對防腐程序的主要原則應該略有所知吧?」
他這話引起了大家極大的興趣,隨即問了他一連串的問題,而從他的回答,我們得知,一直以來,這具木乃伊的古老性都被大大低估了:公爵被埋在厄拉提雅斯的古墓,已有五千零五十多年之久。
不過,最初的駭然過後,我們恢復了鎮定,並如理所當然那樣把實驗繼續下去。這一次,大夥決定要對木乃伊右腳的拇趾進行電擊。我們在拇趾的表皮畫了一道口子,直達它的外展肌根部,然後把電線對準其中的交感神經。一通電,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就發生了:木乃伊的右腿先是屈起,幾乎觸及腹部,繼而不知憑著從那裡來的驅力,往前一伸,狠狠踢向篷諾納爾醫生——後者隨即像支從十字弓射出的箭一樣,飛出窗外,掉落到街上。
「可否勞駕解釋一下,」我說,「你所謂的『蓄意接受防腐程序』是什麼意思呢?」
「神明之一。」格列登先生答道。
「看看我們的建築!」他對著那個無緣無故一拳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的外國人高聲喊道,顯得義憤填膺。
我問那個奪權的暴君叫什麼名字。公爵說就他記得,好像是叫暴民。
「但最讓我們不解的是,」篷諾納爾醫生說,「你既然已在五千多年前死於埃及,現在又怎麼會活過來,而且一副精神奕奕的樣子。」
對於格列登先生最後的提議,阿拉米斯塔奇奧顯得有所顧慮,至於顧慮的是什麼,我並不是十分清楚。不過,他對格列登先生的道歉表示滿意。然後,他從桌子上跨了下來,跟在場的每個人一一握手。
讀到篷諾納爾醫生的簽名時,我已睡意全消,清醒得不亞於任何醒著的人。我興奮地從床上一躍而起,一面動作一面脫去身上的睡衣,再以驚人的速度穿上外出服,然後全速朝醫生家奔去。
走近餐桌的時候,我看到的是一個很大的盒子或箱子,有近七呎長、大概三呎寛、兩呎半深。它不是棺材的形狀,而是橢圓形的。起初,我們都以為它的材料是西克莫槭的木頭,然而,用刀子在上面戳了戳以後,我們卻發現它的質地很像硬紙板,更精確地說,是用紙草紙製成的。棺蓋上裝飾著用厚厚顏料畫成的許多圖畫,內容包括喪禮的情景和其他哀傷的主題。而在這些圖畫之間,或縱或橫的寫著同一組的象形文字——無疑就是死者的名字。我們運氣很好,因為精通古埃及文的格列登先生就是我們中間的一員。他毫不費力就把那一組象形文字翻譯了出來:阿拉米斯塔奇奥。
聽罷此言,在和*圖*書座各人不約而同聳了聳肩,其中一兩個神色凝重地以手觸額。此時,白金漢先生瞄了瞄公爵頭顱的枕部和前頂,然後說出以下一番話:
接下來是一陣鴉雀無聲。最後打破沉默的人是篷諾納爾醫生。
回家以後,我看了看鐘,已是凌晨四點,我馬上就寢。而現在,已經是早上十點。我七點就起了床,把昨晚與木乃伊的一席對談紀錄下來,因為我認為,這個紀錄,將會為我的家人以及全人類帶來裨益。但對於前者,我已不留戀什麼。我老婆是個潑婦。我已經由衷對自己的人生乃至於十九世紀倒胃,深信每一件事情都不對勁。另外,我也渴望知道誰會是二〇四五年的美國總統。因此,一等我刮鬍子和大口喝掉咖啡,就會馬上過去找篷諾納爾醫生,請他幫我進行防腐程序,讓我可以靜靜躺上兩百年。
我吃的當然是一項清淡的晚餐。我對威爾斯乳酪一向情有獨鍾。不過,一次吃一整磅,卻並不是每次都相宜的。當然,你要吃兩磅,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而吃過兩磅,兩磅和三磅就只是個數字上的差別了。結果我吃了四磅。但如果你問我太太,她準會說我吃了五磅,這是因為她混淆了兩件很不同的事情。我必須承認,五只是一個抽象數字,因為具體來說,它指的是五瓶黑啤酒:威爾斯乳酪不配著黑啤酒吃,就會很費嚼勁。
打開第二層的棺材蓋以後(這一次倒是相當容易),我們就看到了第三層棺材。它也是棺材形狀的,與第二層無顯著不同,唯一區別是它的材料為杉木,尚散發著杉木那種特有的芬芳氣息。第二、三層棺材間沒有空隙,兩者接合無間。
他說,我們的機械工具固然有些用,但又問我,靠著這些機械工具,我們能把哪怕像凱爾奈克那麼小的神廟裡面的拱墩搬到過樑上面去嗎?
「完全不知道。」
「看看紐約的布林格陵噴泉!」他繼續以極大的激|情喊道,「如果說它大得你無法想像,那就請你看看華盛頓的國會山莊!」接下來,醫生極其精細地描述了他所提的兩座建築的結構比例,指出單是國會山莊的柱廊,就用了不亞於四乘二十根石柱來裝飾,每根直徑五呎,柱與柱間距離十呎。
「我必須說,各位先生,諸位的行徑讓人既驚又窘。當然,以篷諾納爾醫生這樣一個又胖又矮又無知的人,會做出這種事,自不讓人意外,所以我同情他並原諒他。但你們兩位,格列登先生和白金漢先生,你們都是在埃及旅居過的,對那裡熟悉得有如土生土長,而你們的古埃及語,也流利得和母語無異。因此,我一向都認為,你們是木乃伊最堅定的朋友。然則,你們又怎麼會對別人施加於我的這種不體面對待,袖手旁觀呢?又怎麼會容許別人在這種冷得要命的天氣,把我挪出棺材和撕去我身上的衣服?對於你們幫助可憐的白癡篷諾納爾醫生對我的鼻頭施以電擊,我又要作何感想呢?」
但公爵卻回答說,他此刻最遺憾的是記不起來阿斯納克城任何一座主建築的精確面積,在他入土的時候,這個城市的遺跡仍然存在於底比斯城以西的一個浩瀚平原上。不過,談到柱廊,他倒是記得,有一間叫凱爾奈克的小神廟,其柱廊包含著一百四十四根大石柱,每根有三十七呎粗,柱與柱之間相距二十五呎。在尼羅河岸與這個柱廊之間,有一條兩哩長的大道相連接,沿途佈滿獅身人面像、石像與方尖碑,那些方尖碑有二十呎高的,有六十呎高的,也有一百呎高的。神廟本身縱深兩哩,周長也許有七哩,牆壁裡外都佈滿帶象形文字的繪畫。如果擠一擠的話,這神廟說不定可以容得下兩三百座篷諾納爾醫生所說的國會山莊。儘管如此,凱爾奈克神廟在古埃及只算是等而下之的建築。不過,公爵又表示,聽了篷諾納爾醫生對布林格陵噴泉的描述後,他仍然不得不承認,那是一座有獨創性的雄偉建築,類似的東西不管是在古埃及或別的地方,都是未之見的。
我也應該藉這個機會指出,木乃伊所說的話,都是用古埃及語說出來的,而我們又是靠著格列登和白金漢兩位先生的翻譯,才聽得懂。這兩位紳士能夠把木乃伊的母語說得極其流暢和優美。不過,我也注意到,他們偶爾也需要靠著形象性的方法,才能讓木乃伊聽明白他們的話(這主要是在他們提到一些非常現代的概念時)。例如,格列登先生為了讓木乃伊明白「政治」一詞的意思,最後只好用一根筆在牆上畫了一幅圖畫:畫的是一個紅鼻頭的矮老頭,站在樹樁上,左臂高舉,拳頭緊握,兩眼瞪著天空,嘴巴張開成九十度角。同樣地,白金漢先生也無法讓木乃伊明白什麼叫「假髮」,最後,在篷諾納爾醫生的建議下,臉色煞白地把自己頭上那頂假髮拿下來。
但公爵只是淡然地說,偉大的思想運動在他們時代極為稀鬆平常,至於進步嘛,這觀念雖然一度被喊得震天價響,但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聽你這樣說,」他說,「在尼羅河一帶的墓穴裡,不就仍然可能存在著和-圖-書其他聖甲蟲族裔的木乃伊——也就是仍然有生命力的木乃伊?」
聽了這個問題,公爵低頭去看它的燈籠褲上的條紋,又拿起他大衣其中一邊的後下襬,端詳了幾分鐘。最後,他的嘴巴慢慢展開成一個大笑容;但我卻不記得他有說過什麼。
我裝作沒聽到他的問題,繼續問他古埃及人懂不懂鑿自流井。但公爵只是揚起雙眉。這時,格列登先生對我猛使眼色,然後低聲對我說,最近才有一些工程師在埃及的大綠洲發現古代的自流井遺跡。
公爵以相當吃驚的神情看著我,卻沒有回答。這時,那位沉默寡言的紳士用手肘在我肋上狠狠一撞,低聲說我怎麼又來自曝其短了,難道我竟然不知道現代的蒸汽引擎是透過德科的媒介,從希羅的發明衍生出來的嗎?
木乃伊以嚴厲的表情瞪了白金漢先生幾分鐘,最後嗤笑了一聲,說道:
「無任歡迎,先生。」公爵回答說,坐直了身體。
但人類的希望又有什麼時候是實現過的呢?我第三下鼻鼾聲還沒有扯完,大門上就傳來了鈴聲,然後是一陣不耐煩的叩擊門環聲。我馬上醒了過來。一分鐘以後,我還在揉眼睛之際,我太太把一張紙條塞到我面前。便條是我的老朋友篷諾納爾醫生遣人送過來的,上面這樣寫道:
我提到巨大的機械工具。
這讓我有點惱怒,開始問他有關天文學知識的問題。不過,公爵還沒有回答,一個一直沒有開口的同伴卻向我耳語,說是我最好讀一讀托勒密的著作和普魯塔克的〈論月亮的臉〉一文。
「我得承認,你提到的這個觀念,是我聞所未聞的。在我的時代,我從沒聽誰主張過,天地是有一個開始的。我記得,有一次(僅僅一次),我是聽到過一個喜歡玄思的人隱約談到了人類起源的問題,而且像你一樣,提到了亞當(即紅土)這個名稱。然而,他卻是在類屬的意義下使用這個字的,指的是五大群人從腐土裡自生而成的過程(就像數以千計的低等生物是自生而成那樣)。這五大群人,是同一時間突然出現的,他們分布的範圍,幾乎各佔世界的五分之一。」
我這時問公爵,他那時代的人是否懂得計算日月蝕。他露出一個相當不屑的笑容,說他們當然懂。
上面提到格列登先生那篇精彩回答,其內容主要是向公爵陳述,對木乃伊進行剖驗,會對科學會帶來多巨大的裨益。不過,他又表示,如果因為我們這種做法對他帶來任何困擾,我們願意致上十二萬分歉意。在結束雄辯前,格列登先生又暗示(應該說比暗示還多些),木乃伊既然聽過這個解釋,那原定的檢驗似乎就應該繼續下去。這時,篷諾納爾醫生的解剖工具都已準備就緒。
我們仔細搜屍身,想找出通常用來取出內臟的開口,但出乎我們意料,竟沒有找到。我們當時還不知道,這種連同內臟一起防腐的木乃伊,並不是不常見的。一般來說,木乃伊的腦部都會透過鼻孔取出,內臟會透過在身體側邊開的一道口子取出。然後,屍體會剃去毛髮、清洗、鹽醃,再擱置幾星期,再進行所謂的防腐程序。
昨晚的宴飲對我的神經而言稍嫌刺|激了一點。它讓我第二天頭痛欲裂,整個人昏昏沉沉。所以今天黃昏,我沒有如預定計畫般出外消遣。我知道,最明智之舉莫過於只吃一點點晚餐,然後馬上就寢。
「看得出來,」白金漢先生說,「你是相當高壽才過世的。」
「對,聖甲蟲是一個很傑出和很顯赫的貴族世家的家徽。所以『聖甲蟲的血裔』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意思是我是這個以聖甲蟲為家徽的世家的一員。」
木乃伊擱在博物館的這段日子,保存狀況和薩布雷塔舒上尉挖掘出來時並無二致,也就是說,棺木從未被打開過。有八年時間,它都是直立著,只供人參觀其棺蓋上的銘文圖畫。再說,一具未被開棺檢驗過的木乃伊,在我國是很罕見的。因此,現在有一具木乃伊就放在面前,任由我們處置,我們焉能不歡欣鼓舞。
電擊帶來的效果讓人目瞪口呆。木乃伊首先是張開了眼睛,快速地不斷眨了幾分鐘;接著,他打了個噴嚏;接著,他坐了起來;接著,他一拳打在篷諾納爾醫生臉上;接著,他把臉轉向格列登和白金漢兩位先生,用字正腔圓的古埃及語說道:
在座各人紛紛你一言我一語,把顱相學的假設詳細說給公爵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