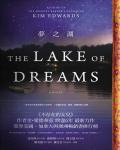第一章
「還沒,已經在我的考慮名單裡了。」
待我轉過身去,吉隆已經站在門口了。他的頭髮蓬亂,身上穿著舊T恤和跑步穿的短褲。吉隆有張溫暖和善的臉。他對藤本太太微微一鞠躬,藤本太太也回禮,然後飛快對他說了一連串的日語。藤本先生是吉隆父親以前同校的同學,我們的房子就是跟他們租的。吉隆的父母偶爾從倫敦回來時,就住藤本夫婦另一戶在街角的公寓。吉隆的母親是英國人。
這就是我對爸爸說的最後一句話。幾個鐘頭後,我在陽光和眾人慌亂的說話聲中醒來,跑下樓:穿過沾滿朝露的草坪,來到湖邊,看到已被大家拉上岸的爸爸。媽媽跪倒在淺水窪裡,伸手用指尖撫摸他的臉頰。他的嘴唇和皮膚都泛青,嘴角掛著白沫,眼瞼閃耀著奇異斑斕的色澤。我心想,就像魚一樣。浮現這個念頭真是瘋了,但這樣至少暫時摀住了其他想法,其他更糟的、此後縈繞不散的想法:要是我去了就好了。要是我在場就好了。要是我當時答應他就好了。
「不要,吉隆,我真的不想再拖了,一直閒著沒事做,我覺得我有點快瘋了。」
一開始,想避免我們的關係升溫並不難,因為時常飛來飛去的人總免不了的短暫戀曲和遠距戀情,我實在受夠了。但接著,雨季開始了。那年的雨季比往年早,且雨下得異常暴烈,這座城市的開放式渠道不堪暴雨,水全淹到路面上。雅加達大部分地區地勢低窪,原本就容易淹水,加上全市各處大肆開發,樹木和綠地少了,能吸納雨水的地方就更少。水勢上升,再上升;有天早上我起床,發現淹水的草坪上竟有魚在游,到了中午,客廳裡已經積了五吋深的水。我和室友一直密切注意電視新聞,新聞報導洪水沖走了無數汽車、捲走建築物門面,還把一個一百四十三人的村落完全淹沒。
接著一切戛然而止,四下頓時靜得詭異。遠方,水滴進池子的聲音清楚可聞。吉隆的呼吸聲徐緩均勻。
我笑了,但吉隆是認真的。他的眼睛是瑪瑙的顏色,如湖底般幽黑,直直注視著我。我屏住呼吸,想起前一晚,他的手輕撫過我的肌膚,那時他也是這樣凝視著我,眼睛眨也不眨。吉隆的工作常需要出差,他是工程師,在一家跨國企業工作,負責設計橋樑。這次出差,只是又一次離開我身邊。但現在這個公務竟成了我們在國外相聚的機會,多諷刺。
我把信讀了兩次,想像媽媽不知怎地受傷了,自己坐在那張孤獨的餐桌旁;我感覺自己又被拉回爸爸死後的那個夏天。我這麼想,其實並不公平,畢竟已經過了將近十年,我們都邁向新的生活了,至少表面是如此。爸死後的那個夏天,我們每天都做著尋常的事,盡可能維持著一個脆弱的秩序,即使吃不下飯,仍照樣煮三餐。我們在走道上擦身而過時避不交談。媽媽開始睡在樓下的空房裡,並且把二樓關上,一個房間一個房間逐一鎖上。整楝房子寂然無聲,圍繞著媽媽的哀慟,而我們就繞著她的哀慟,小心安靜地移動。如果我放任自己哭泣,放任自己憤怒,一切或許就會崩解碎裂;我只能靜止不動。即便到了現在,我每年回家時,仍會感到自己又掉進當時的氛圍,回到那個為失落所囿的世界。
吉隆坐在桌前,語氣輕快地說:「嗯,這倒是真的。」
我出了溫泉池,穿好衣服,但吉隆還沒出來,我便獨自沿著一條石子小徑,漫無目的地走。石子路沿著小溪築成,末端開闊,接在一個池塘邊,池塘圓如瓢盆,讓月光映成了一片亮銀色。我在池邊停下腳步,黑暗中,湖的另一邊有不知名的東西騷動。
吉隆正在剝一顆橘子,十分有技巧,剝下的橘子皮幾乎完整無缺,像一只空的燈籠;他沒抬頭看我。
我別過頭去,吃驚地眨眨眼,因為我眼眶裡不知怎地,竟已泛滿淚水。
隔天結束後,吉隆載我回家,這時陰霾的天終於透出些許陽光。我下了車,狂奔到門口,一邊找鑰匙,結果不小心滑了一下,趕緊抓住旁邊一株芒果樹,以免跌倒,一陣碎枝殘葉隨之落下,灑了我滿頭滿身的種子、花粉和枯枝;原本大掃除就已經把我弄得夠狼狽了。吉隆一把攙住我手臂,我倆忙亂地進到屋裡。他說,妳在發抖,過來。淋浴的水放著,氤氳蒸騰,我們把濕衣服褪在地上。吉隆說:眼睛閉起來。他站到我背後,溫熱的水從我倆頭上灑落,他的雙手探入我髮間按摩,用m.hetubook•com.com洗髮精洗潤每縷髮絲,愛撫我的頭皮,按摩我的肩膀,水流沖去寒意和髒污,也沖去我的緊繃和猶疑。我的雙臂在吉的撫觸下緩緩放鬆,他捧住我的乳|房,宛若捧著花朵。我轉過身去。
海浪拍擊岸邊,屋子隨之輕晃,隨即靜止。我在矮桌旁坐下,啜飲手裡的茶,讓思緒漫遊到新的一天,以及我們計畫許久的山中之旅。在印尼,那個遙遠的國度,我和吉隆也討論過結婚,甚至想過生小孩的事,但在那些飄渺的幻想裡頭,我是有一份好工作的,或者會樂意學日文、學插花,樂意獨自一人到野外走上大半天。當時我並不了解,失業會讓人感覺如此與世隔絕,也沒料想到吉隆會投入這麼多時間在他的工作裡。近來我們處得不太好,常為無足輕重的小事爭吵。在此之前,我也從未意識到,一旦生活的步調慢了下來,逝去的過往竟會如此縈繞不去,沉甸甸地把我往下拉。在日本無所事事過了三個月後,我教起英文,為的是打發日子,至少能聽聽除了自己以外的人聲。我帶著年紀輕輕的學生去散步,在海邊停下來,教他們一些具體的名詞:石頭,水,海浪,心裡懷念起過去工作時,自己曾多麼游刃有餘地把這些字掛在嘴邊。有時我說的話近似囈語,他們想必不能了解。這水恐龍也喝過,你知道嗎?水會永遠不停循環,小朋友,有一天,你的孫子說不定會喝到你的眼淚。
只有這個世界存在。頭一年,和第二年,我們都過得幸福極了。然後,我倆在雅加達的工作合約期滿。我還沒找到新工作,吉隆已應徵到一個當時看來似乎是他夢寐以求的工程師職位,我們便搬到日本。後來我們才發現,這是個截然不同的國家。
震動停了。屋裡傳來一個孩子說話的聲音,似乎在詢問什麼。藤本太太深呼吸,然後往後退,向我鞠了個躬,把掃把從地上撿了起來,她臉上前一秒還惶無掩飾的表情,又恢復了原本的距離感。我獨自站在磨得圓滑的鵝卵石上。
吉隆嘆了口氣,我感覺他似乎有些疲憊。「我不知道,可能是很小的地震吧。」桌上的花瓶倒了,還有幾本書掉在地上。我把水擦乾,拾起散落的花瓣,一起身,四周突然猛烈一震,強度之大,連吉隆都即時做出反應,立刻把我拉到玄關,我倆在門口站了好幾分鐘,對腳下的大地滿懷警戒,注意著它變幻莫測、顫動的生命。我實在倦極了。我害怕眼前將來的夜,怕那些地震,那些夢,我也害怕新的一天,害怕又要為了無足輕重的小事爭吵,害怕吉隆出差後,那股寂靜又將重壓在我身上。我想起那兩隻池畔鷺鳥揮動深色羽翼的景象。
我從廚房窗戶望出去,看著隔壁房子的牆面。
樹葉搖晃不休,地上一灘水窪裡的水也在顫動;藤本家廚房的窗戶下震出一道細縫,呈之字型向下,一路裂到地基。我握著藤本太太的手,一動也不動,心裡想起媽媽發生的意外,想到事發那一刻,她意識到自己沒辦法阻止那輛車朝她迎面撞來,一如她無法改變月亮的陰晴圓缺。
而現在,走過這麼多個日子,我們來到千里之外的這裡。吉隆的談笑聲從溫泉池牆壁另一端飄來。我往下滑,浸得更深,頭枕在濕漉漉的石子上,四肢在水裡漂著,肌膚隱隱透著光,蒸汽冉冉而上。對面的女人仍低聲聊著,我心想,她們該是母女吧,或者是相差多歲的姊妹,因為她們的身形如此相像,舉手投足間十分神似。我又想起媽媽,想起她獨自一人坐在家中的景象。
派對辦在一棟很大的房子裡,裡頭充滿轟轟的音樂和笑聲。我穿了一件暗藍色的緊身絲質洋裝,是訂做的,剪裁非常合身,和我眼睛的顏色也搭。我在屋裡四處走動,笑著,聊著。然後我經過一個幽靜的陽台,臨時起意,便走出去呼吸新鮮空氣。吉隆靠在陽台欄杆上,眼睛凝視著下方的河。看到他,我猶豫了一下,因為他的姿態讓我不想打擾。但他轉過身來,露出他特有的笑容:吉隆笑的時候,整張臉便會亮起來,溫暖友善。他問我要不要一起看河。
我走進蒸氣繚繞的水裡,想像著地底供應這些溫泉的河流,我想到萬事萬物如此相互連結,也想到我和吉隆現在的生活,竟是因為我兩年多前一個無心的決定。那時我剛到雅加達沒幾個禮拜,去探勘一個渠道系統,為期一週的實地勘查結束,我回到家,把行李https://www•hetubook•com.com扔在冰涼的大理石地板上,一心只想沖個澡,來盤印尼炒飯,喝點東西,其餘的什麼也不想。我的室友在愛爾蘭大使館工作,她那時正要出門參加一個派對,邀我一起去,跟我保證那裡東西絕對好吃,放的音樂也比家裡好聽。我剛開始拒絕了,但最後一刻又改變了心意。如果那天我沒去,我和吉隆永遠不會相遇。
現在,又是好幾個禮拜過去了,我開始想,這會不會成為我真正的生活,而不只是理想人生中的一段短暫插曲?
「露西,妳為什麼不休息一下,去看看妳媽呢?等我去雅加達出差完,也可以去找妳,我很想去,我想見妳媽。」
「噢,怎麼會這樣?妳要去看她嗎?」
「喔,關了!」我說,「我瓦斯已經關了!」這是我們常有的對話,是我少數能說得流利的日語之一。
我回答:「不是。」我說的是實話。我拿起橘子皮,揣在手心上,感覺十分輕巧。「只是時間點不對啊,而且我媽的情況又不嚴重,這不是什麼緊急狀況。」
這一整天地震接二連三,我不禁再次屏住呼吸。一隻大藍鷺佇立在暗影中,雙翼收攏在身體的兩側。接著池塘又平靜了下來,如雲母般粼粼閃爍。那隻藍鷺旁還有另一隻體型較小的鷺鳥,這時也騷動起來。我想起溫泉裡的那兩名女子,彷彿她們出了溫泉,來到這池邊,化成了這兩隻謐靜絕美的飛鳥。這時吉隆叫了我的名字,兩隻鷺鳥便展開寬闊的翅飛走了,姿態緩慢優雅,在水面上投下暗影,最後消失在林裡。
「妳下個禮拜、下個月,都還可以找工作啊。」
我們走到一座戶外的博物館,博物館上方是幾棵雪松生成的綠蔭。後來走到一個死火山旁邊的山村吃午餐。一路上,我倆的對話恰然自在,就像以前最快樂的時候;走到那座露天風呂時,已經接近傍晚了。露天風呂就是室外的溫泉。我和吉隆在入口分開。更衣室裡,只見色澤純淨的松木結構,還有淙淙流動的水,恬謐而撫慰人心,幾乎沒什麼人。我把全身上下仔細擦洗過,用溫暖的水沖淨身體,全身赤|裸走到石砌的水池。空氣微涼,靛青色的天空中,月亮已經升起了。兩個女人倚在光滑的石頭上談天,她們的皮膚襯在濕黑的石頭前顯得雪白,白皙的身子隱沒在池水中,腰部以下全看不見。她們的交談聲融合成一股輕柔的聲音,溫泉涓流的水聲也同樣徐緩,再過去一點,牆的另一頭傳來男人潑水和說話的聲音。
「是海嗎?」我問。
我倒了杯茶,拿著茶走到客廳,拉開百葉窗和窗戶,夜裡的空氣便這麼流淌進來,乾淨而微涼。天色仍黑,但附近人家卻已經動了起來,遠近都有潑水聲和碗盤發出的聲響;窄巷對面的鄰居在輕聲交談,一來一往。
我的名字叫露西.賈瑞特。對於這位窗邊少女,我曾經一無所知,那時我還沒回到故居,還沒有在無意之間掘出真相的碎片,還沒試著拼出完整的故事。那時我住在日本一個濱海的小鎮。那是一個小地震不斷的春天,那一夜,我做了個夢,乍然驚醒。外頭,鵝卵石鋪成的小巷間,有腳步聲漸漸遠去,遠方火車轟隆駛過,我側耳,聽見了海潮湧起的聲音,但除此之外什麼也沒聽見。吉隆的一隻手輕輕枕在我臀上,好像我們還在跳舞似的。那天晚上,我們才在昏暗的廚房裡相擁而舞,收音機流洩出輕柔的旋律,我們的舞步漸慢,最後徹底停了下來,在飄著茉莉馨香的空氣中,站著親吻彼此。
吉隆盯著我,眼神就彷彿是他能將我全然看透,直入心底。這樣的神情曾令我深深為之吸引,如今卻讓我感覺喘不過氣。
吉隆把一瓣橘子遞給我。這些小巧的蜜柑長在附近的小山坡上,成熟的蜜柑看起來就像色澤鮮豔的裝飾品。那些蜜柑樹是我們去年秋天去那附近玩的時候發現的,那時吉隆才剛得到這份工作,一切彷彿都還充滿可能。
「寶貝。」吉隆摸著我的手,指尖微黏。「露西,對不起,好不好?我們不要想這些了,去爬山吧,照原本的計畫。」
躺在榻榻米上,吉隆在我身旁嘆了口氣,身體動了一下,手從我臀上滑落。月光照在地板上,映成一塊方形,遠方的浪花拍擊著海岸,風吹不止,窗簾沙沙作響。接著震動愈來愈強烈,過程幾近不知不覺,剛開始震得並不明顯,就像早先那列火車隆隆駛過的微顫。但接著,我排在地上的西藏頌缽開https://m.hetubook.com.com始發出低沉的嗡嗡聲,平時蒐集的石頭紛紛從書架上掉下來,打在墊子上,發出下雨般的聲音。樓下傳來東西摔破、摔碎的聲音。我屏住呼吸,彷彿把自己停住,便能停住整個世界。但四周震得愈來愈厲害,愈來愈嚴重。書架突然猛地一震,幾本書掉到地上,接著是一連串的震顫,牆搖地動,彷彿是一隻龐然巨獸驚醒了,翻身了,彷彿大地是活的,地表只是牠的皮膚,隨時要起伏晃動。
我便走了過去。我走過鋪著磁磚的地板,跟他一起站在欄杆旁。起初我們沒說什麼話;底下的水流湍急渾濁,把我們給迷住了。後來我們才開始聊天,一聊之下,發現彼此有許多共通之處,不只工作性質相近,同樣熱愛旅行,我們兩個還同年,也同樣對啤酒過敏。我們滔滔不絕地暢談,對身旁來去的人渾然不覺,沒注意酒杯空了,也沒發現天色變了。季風雨瞬時傾瀉而下,熱帶地區的雨總是來勢洶洶,令人措手不及。下雨的那一刻,我們彼此相視,接著開始大笑。雨水大把大把地從天而降,吉隆把雙手高高舉向天空。我們已經淋得濕透了,這時再進屋裡似乎也沒意義,我們便繼續留在陽台上聊天,直到雨又戛然而止,就和落下時一樣突然。吉隆陪我走回家,我們一起走過沿途幽黑潮濕的街道。到了我家門前,吉隆用雙手抹去我頰上的雨水,然後親吻我。
這時已近黎明,我站起身走到窗邊。外頭,地上鵝卵石的顏色已明亮起來,成了淺灰色,一棟棟木造建築也從夜色中浮現。對街傳來盆子輕輕碰撞的聲音,把我從思緒中拉出來,接著又傳來沖水的聲音。是藤本太太出來掃門前的人行道了。我走到外面的露台,點頭向她問早。藤本太太掃地的勁道強而有力,發出唰、唰、唰的聲響,因此直到她停下動作,我才發現腳下的地又開始隆隆作響了。剛開始聽起來沒什麼異樣,像是有一股大浪衝上海岸,或卡車駛過街道的聲音——但不是。我和藤森太太四目相接;搖晃沒止住,反倒愈晃愈厲害。藤本太太一把抓住我的手。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這個嘛,地震要不就會停,要不就不停,反正我們都無能為力啊。再說,妳看,」他又指著我想當然耳看不懂的報紙說,「頭版新聞:海底要形成一座新的島了,之後狀況就會好轉,現在只是在釋放能量而已。」
「嗯,那之前那個顧問工作呢,中國要在湄公河蓋水壩的案子?妳繼續問了嗎?」
「地震嗎?」吉隆喃喃地說。
「我的意思是,最近妳感覺很悲傷,很寂寞,就這樣。」
「妳又不是要走回去。」
我躺回床上,往吉隆溫暖的身軀蜷縮。剛剛我夢到自己回到那個伴我長大的湖,夢裡的我並不想,卻還是回去了。夢中的天空十分陰霾,還有那棟油漆顏色已褪去的綠色小屋。這屋子我見過不只一次,只在夢裡。小屋滿是霉味,上頭樹枝蔓生,破窗的玻璃上覆著沙塵和雪,灰濛濛的。夢裡的我走過小屋,來到湖畔,走到結冰的湖面上,湖面的冰厚而透明。我走著走著,看到了那些人。好多好多人,都在那底下度過他們的一生,我一眼瞥見他們,便屈膝跪下,掌心按在玻璃般的湖面上——湖冰好厚,好透明,凍徹心扉。是我把他們留在這裡的,我心裡知道,是我把他們一直扔在這裡。他們的髮隨著湖裡的水流漂動,眼睛對上我的視線時,便充臆著渴盼,和我的渴盼同樣深切。
「沒關係啊。」我說著,跟著吉隆走到廚房,途中順便拿起我喝完的茶杯。「我也很怕地震,你怎麼可以這麼冷靜?」
「怎麼了?她還好嗎?」
我的筆記型電腦在房間另一頭閃爍著微小的燈光。我起身去收電子郵件,電腦螢幕的光把我的雙手映成一片蒼白的藍。總共有十六封新信,大部分是垃圾郵件,兩封是斯里蘭卡的朋友寄來的,還有三封是之前在雅加達的同事寄的,他們一起去叢林健行,傳來了旅行的照片。我匆匆瀏覽過這些信件,想起之前我們曾和這些朋友一起沿著河旅行,還記得當時河岸上蔥蘢蒼鬱,我們把睡蓮摺成帽子,戴在頭上抵擋烈日。那樣的生活,我和吉隆已經遠離了,而我心裡多麼渴慕。
「露西,」吉隆又叫道,「我們動作快一點,可以搭到下一班火車。」
「喔,她跟我說一九二〇年代的關東大地震,她那時候死了一些親人,可能是這樣,才會連小地震都這麼怕
m•hetubook.com.com,她很怕火災。她還說她握住妳的手嚇到妳了,跟妳說不好意思。」
這時我深呼吸,沒立刻答話。這次郊遊的行程,我們已經期待了好幾個禮拜,我不想在這個時候吵架。最後我終於回答:「我還在查那家公司的資料。」我努力提醒自己,不過幾個小時前,我們才在同樣的地方相擁而舞,周遭一片昏暗,馥郁幽香。
水開始退了以後,吉隆和兩個同事一起策劃替一家育幼院大掃除。他開著一台借來的老舊日產貨車來載我;車程中,只見整個雅加達全泡在水裡,已然面目全非。育幼院地上浸滿泥漿,滿是碎片,裡裡外外惡臭難耐。我們從早清理到晚,隔天又清了一整天,這兩天當中,吉隆四處穿梭,一會兒剷污泥,一會兒指揮志工。中間有一度,他經過一個小男孩身邊,男孩穿著一件破爛的紅衣,站在爛泥裡哭著,吉隆一把抱起小男孩,把他抱進屋裡。
「對,很大,樓下有東西摔破了。」
「吉隆,」我開口說,「我想我還是回去看看家人吧。」
他抬起頭來看著我。
於是我們出發了。在海邊時天氣十分悶熱,但隨著火車逐漸蜿蜒上山,天空也越顯開闊明亮,陽光明媚。之前初春時,這裡四處盛開著梅花和櫻花,襯著整片山野,給大地覆上一層瑩白的花瓣,當時我學的生字就像詩一樣:樹,花,落下,花瓣,雪。現在已是季節尾聲,海濱的水田裡,稻穗早已探出頭來,但山林裡的春天卻仍逗留著。繡球花才正開始綻放,花瓣成簇,從極淺的綠暈染成豔紫碧藍,生得十分濃密,挨在火車窗邊。
溫泉池裡的女人一個接一個起身走了,水滴在石頭上,池水輕晃。我想起之前作的夢,那些湖冰底下的面孔。以前爸爸常說故事給我聽,故事的女主角總是我,結局永遠幸福美滿;我從未經歷苦痛,面對他突如其來的死,我全無準備。根據驗屍結果,爸爸當時是失足,頭一把撞在船上,整個人跌落水裡,那是一場怪誕得難以解釋的意外,也沒辦法逆轉。幾天後,有人在沼澤邊發現了爸爸的釣魚竿,被成叢的蘆荻纏著。
我家人一連寄了三封信。第一封信竟是媽媽寄的,我很驚訝。我們滿常聯絡,這些年來我也盡量一年回國一次,就算能待的時間不長也會回去,但我媽使用網路的程度,就像爺爺奶奶那輩打長途電話的情形是一樣的,也就是鮮少使用,即便用了,也總是長話短說,有重要的事情才用。我和媽媽通常用電話聯絡,或寄薄薄的藍色國際航空郵件,我的游牧生活把我領到哪裡,媽媽的信就寄到哪裡,而我寄的信則永遠投遞到同一棟房子的信箱。這棟格局蓋得有些凌亂的房子就是我成長的地方,位於一個小鎮——「夢湖」。
下一封信果真是布雷克寄的,讓我有些緊張。布雷克夏天都住在他的遊艇上,他的工作是駕駛夢湖碼頭的渡輪,每兩小時一班;冬天就到聖克魯斯島,做的事情大同小異。他常用Skype即時通訊軟體和我聊天,還飛越大半個地球來找過我兩次,但他不太用電子郵件,幾乎沒寫過信給我。布雷克告訴我媽媽發生意外的細節:媽媽開車經過停車再開的標誌時,有人硬闖過去。他說媽媽的車全毀了。但我不覺得他看起來顯得過度保護,只是擔憂罷了。下一封我堂妹柔伊寄來的信感覺才真是有些失控了,但她本來就是這樣。柔伊出生時,我已經快十四歲,她和大家實在差太多歲,因此有時會覺得她跟我們似乎不是在同個家族長大的。柔伊的哥哥阿約和我年齡相仿,他繼承家族的名字,也繼承了家族的財產。我和阿約從小就不合,但柔伊呢,她現在十五歲了,熱愛上網,在她心目中,我的生活無比精彩,充滿異國情調,她經常寫電子郵件給我,轉播她學校裡種種戲劇化的事,但我很少回信。
吉隆聳聳肩,又從鈷藍色的盆子裡拿了一顆橘子。「有時寂寞就是緊急狀況啊;露西。」
「不是地震嗎?」
「妳瓦斯關了嗎?」她問。
「出車禍,不嚴重,應該吧,或者車禍滿嚴重的,但她人沒事。大家的說法都不一樣。」
我轉過身去搖搖他的肩。他緩緩睜開眼。這些小地震他完全不當一回事,雖然那個春天發生了幾百次地震,有時甚至一天不下十數次,有的輕微得只有地震儀能察覺,但有的就像這次,強得能把我們從睡夢中搖醒。
房裡窗簾一陣顫動,我www.hetubook.com.com不禁緊繃起來,懸在不停歇的地震和那個夢之間。但那其實只是遠方的一列火車,正往山裡開去。這個星期以來,每天晚上,我都做著同樣的夢,擾醒逝去的過往,又時而被挪移的大地擾醒。這夢把我帶回到多年前的一個夜晚。那年我十七歲,正是浮躁不羈的年紀。那晚,我側身滑下奇岡.弗爾的摩托車,我們頭頂上綻放著一朵朵的蘋果花,瑩白如星子。我把手攤開,撫在他胸膛上,然後他驅車離去,引擎聲劃破靜夜。我轉過身去,看到爸爸在花園裡,他的短髮在月光映照下,顯出縷縷銀絲,他手上的菸點燃,舉起,又落下。黑暗中,紫丁香和開得早的玫瑰正飄送陣陣芬芳。爸爸說:妳回來啦。我對他說:對不起讓你擔心了。然後是一陣靜默,空氣中聞得到湖水和堆肥的氣味,還有黑土中冒出嫩綠幼苗的氣息。接著爸爸問:露西,要跟我去釣魚嗎?想不想?很久沒一起釣魚了。他說的話聽起來十分傷感,我也還記得小時候,我常天還沒亮就起床跟爸爸集合,吃力地拎著釣具箱,跟著他一起穿過草坪,走到船邊。我想答應爸爸的邀約,和他一起去釣魚,但我更想上樓想著奇岡.弗爾。因此我轉過身去,語氣尖銳得像碎貝殼似地說:爸,拜託,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露西,我出了點意外,但不要緊,妳千萬別擔心,如果妳弟布雷克說了什麼,請妳聽聽就好。他當然是好意,不過也太過份保護了,我真有些受不了。我很確定手腕沒有骨折,只是扭傷而已,醫生說實際情況等X光報告出來就會知道,妳不必特別回家一趟。
吉隆終於又對藤本太太鞠了個躬,走進屋裡,我問他:「你們在說什麼?」吉隆從小就講兩種語言,能在語言間轉換自如,這點讓我又羨又妒。
「可能吧。」
「妳的考慮名單——露西,妳的考慮名單有多長啊?」
最近妳感覺很悲傷,很寂寞。這句話仍讓我感覺刺痛,但我不得不去想,這話是不是真的。爸爸死後沒幾個禮拜,我就離家上大學了,那時我全然麻木,但決心要逃離家裡籠罩的那股黑魔法似的冥寂;奇岡.弗爾一次又一次試圖打破那股靜默,但我總冷酷地打發他,兩次,三次,最後他終於不再打來。那之後的歲歲年年,我不停換到新的地方,從大學到研究所,從好工作換到更好的工作,歷經一段又一段戀情,將所有的悲痛拋在腦後,從不讓自己放慢腳步。直到現在,在日本失了業,我終於停了下來。
「難道妳都不想帶我去見妳媽嗎?」吉隆不放過我。
他閉上眼,伸手把我摟過去,很快又恢復了深沉規律的呼吸。我從半掩的窗戶望出去,看到對街房子的屋頂後面,疏疏落落閃著星光。「吉隆?」我喚他,但他沒回答,我便起身,走到樓下去。
「真的嗎?嗯,現在停了,靜下來了不是嗎?睡覺吧。」
我語氣生硬地回他:「我很努力在找了,你根本不知道。」
「可是好遠。」
我沒立刻回答。吉隆希望我去嗎?這樣對他算是解脫嗎?過了好一會兒,我才說:「應該不會,她說她沒事,而且我要找工作。」
種在廚房窗台上的那盆蘆薈掉在地上,盆子已經摔得粉碎。我煮了一些水,然後把散落一地的沙土、玻璃和斷裂的莖葉掃起來。這時街頭巷尾的日本主婦,應該都做著相同的事吧,一想到這點,我不禁感到不是滋味,心裡有些酸溜溜的——我確實已經失業太久了。我不喜歡像這樣沒有收入,除了家事以外,沒有一份有意義的工作,只能依賴吉隆。我的專長是水文學,專門研究水在地表和地表下流動的情形。我認識吉隆之前,已在幾家跨國企業旗下做了四五年的研究工作。我們在雅加達相識,瘋狂墜入愛河,一如所有的異國戀人,和自己熟知的人事物割離了,因此我們所居住的國度,其實是自己創出的,是一個隨我們所欲的國度。那時,吉隆會一邊用手拂過我的身體,一邊說,只有這塊大陸最重要。
「很好,聽了還真放心耶。」我看著吉隆沖水到茶裡,動作從容純熟。「吉隆,我媽發生意外了。」我說。
隨著海拔漸低,熱氣又逐漸襲來,火車窗外的繡球花也益發凋朽憔悴,彷彿原本徐緩漸進的時序全壓縮進短短的一小時了。待我們抵達海濱這一站,已經完全不見花的蹤影,舉目只見蠟滑光亮的枝葉。我和吉隆沿著窄窄的鋪石路走回家,蟋蟀唧唧低鳴,腳下的地隨著拍打的浪潮微微顫動,我兩度停下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