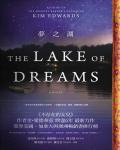第五章
隔天早晨,我們很早就起床。我用媽媽買好的大容量氦氣桶灌氣球,然後把灌好的氣球在草坪、門廊欄杆和樹枝上四處繫著;氣球飄在空中,宛如脫離軌道的小小行星。因為我十點要到教堂和奇岡碰面,我和媽媽便提前出發到市區去。我送媽媽上班後,把雪佛蘭停好,在車裡坐了幾分鐘,用手機收電子郵件。吉隆寄信告訴我他印尼之旅的日期,列出了幾個時間,問我什麼時候飛來美國比較好。我回信給吉隆,但按了幾個鈕之後,或許是因為過去兩天被這麼多料想不到的前塵往事撼動,我突然很想聽到他的聲音,找回當下生活的定位,所以我決定直接打給他。響了第二聲,吉隆就把電話接了起來;聽到吉隆和緩而熟悉的嗓音,一股安心的感覺倏地湧上,我發現自己竟如此渴望見到他。
我謝過喬安娜,然後在沙發上坐下來,把文件夾打開,灰塵的氣息和霉味撲鼻而來。我翻閱這疊印刷華麗的證書,每張證書上都繪有一隻白翼鴿,是輪廓畫,畫工細緻,鴿子的頭上有一圈光環,正從一個殼狀物凌空飛下。有些證書上沾了水漬,有些則泛黃了。一個個舊時代的名字在我眼前閃過:葛羅麗亞。赫伯特。埃文。洛伊德。史都華。蘇珊娜。諾曼。堊爾。艾薇。伯莎。荷馬。葛蕾蒂斯。奧斯卡。葛瑞絲。我沒找到賈瑞特家族的人,但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姓氏或中間名,這些家族有的至今仍住在夢湖,有的則在我小時候曾住在這裡,後來才搬走了——這些人是我同學的祖先。我試著想像,在一九一〇年的時候住在夢湖,生活會是什麼面貌。那時世界大戰還沒發生,後勤基地還沒興建,湖畔地帶仍未開發,夢湖旁邊緊連著一片片原始的曠野。那時想必還沒有柏油鋪成的路,我眼前看到的這些名竽,這些人小時候上的想必是那種只有一個教室的學校;這些孩子用水要從水井裡汲,夜晚照明要打油燈。
我沒回答,因為牆上成排的教區牧師盯著我,令我不禁神經緊繃。但奇岡笑了,彷彿這樣的對話他們已經進行了許多次,他已感到稀鬆平常。他回答:「謝謝,不過我不喜歡制式化的宗教,希望沒有冒犯到妳。我比較喜歡自己禱告。」
「我幾乎可以確定。」
領洗日期:主後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的確。」
我走過幾個掛滿禮袍的櫥櫃,到了轉角一轉身,不禁愣在原地,這道玻璃花窗之大、之美,讓我震懾不已。花窗懸掛在一大片透明窗戶上,外頭就是夢湖,因此整個鉛框鑲成的彩繪玻璃花窗溢滿光線,彩光斜照而下,落在我的雙臂、身子和地板上。花窗裡有一片深藍的天,鳥兒飛翔其間;下方是色澤暗些的海,斑斕的魚兒在裡頭悠游;花窗四邊爬滿藤蔓,綻放的花朵色澤明豔。花草間有形形色|色的動物,斑馬、蜥蜴、野兔和象,四周環繞著蓊鬱綠樹,樹上色彩斑駁的葉彷彿在顫動。花窗裡也有人形。人像樹、像花,都從紅褐色的大地長出來,這些形體看得出是人,但無法分辨男女。他們站著,雙臂高舉,手掌幻化成葉,葉子又長成許多不知名的字母。花窗底邊正是那道我已看得眼熟的藤蔓綴圓月,而交扣的月亮上方寫了一句話,由透光的金色字母拼成。
「而且我猜也和教堂有關聯。」
「那你工作室裡的那道窗呢?那道約瑟窗?」
四下空氣全然靜止。我在印度和日本時,也曾到過和這裡一樣無限寧靜的寺廟,那樣的緘默使人靜下來,專注聆聽。在印尼,禮拜的廣播定時在粼粼閃爍的空氣中迴響,一日五次。儘管如此,我卻已多年不曾接觸自己的宗教傳統;這座教堂讓我感覺既熟悉又陌生。前方的聖堂比從前明亮了,一扇扇的窗子也比從前更鮮豔奪目。我往中間走道的另一端走去。在教堂最前方,最靠近洗禮池的窗子旁邊有一道鷹架,窗邊地上攤著一塊帆布,上頭散落著各種工具,那道窗上裝著一塊透明玻璃。不一會兒後,奇岡從風琴後的窄門走出來,一邊輕輕吹著口哨。
我同意,但感覺又不止如此。想到家族裡有我從沒聽過的故事,我心裡就感到一陣悸動。這個看待過去的觀點,可能會打破我對一切的認知,這想來振奮人心,也有些懾人心魄,誘惑極了。
「這道窗也有我說的那種飾邊嗎?」
「沒問題,」蘇希站在門口笑著說,「還有,奇岡,也歡迎你星期天來參加禮拜。露西,也歡迎妳來。」
喬安娜嘆了口氣。「想到這些就會起雞皮疙瘩對不對?看著這些表格,白紙黑字,都好好歸檔在盒子裡,然後想想這些人曾經也都在這裡,或許曾經站在我們現在站的地方,在這裡交談和_圖_書,過著他們的生活。」
「這個圖案實在太特別了,我相信這其中一定有關聯。」我說。
「沒問題。」她把洗禮證書擱在影印機的玻璃板上,然後闔上蓋子。「我今天不會再到檔案室,可能明天也不會,不過妳可以把妳的電話號碼留給我,我之後可以再打電話跟妳說。妳也可以去查查墓園那邊的紀錄,或是結婚紀錄之類的,或者是舊報紙的檔案庫。」
主,請賜給我們恩典,我們將祢的僕人馬汀交付給祢……我們排隊逐一上前領聖餐,教堂裡迴盪著移動腳步、蒙住咳嗽、清嗓子的聲音。我們在圍攔前跪下,我的一邊是媽媽,另一邊是布雷克;領餅和酒中間的短暫空檔,我聽著他們兩個人輕微的呼吸聲,胸中的悲傷和渴求大到彷彿要將我撕裂。牧師在木欄杆後移動身子,先給聖餅,接著給聖餐杯,一一湊在我們唇上。這是聖體;這是救恩的杯。我其實並不相信聖餐那一套,因為從邏輯的觀點來說根本不合理,然而在這個儀式中,在這個地方,我卻經常有一種神秘的感受,一股渴求,並感到自己的渴求被回應。
「在廚房,喝點東西,處理一些文書工作。」
我往後退,讓蘇希走進壁龕。她走過來,動作不禁停住,有些目瞪口呆,和我剛剛一樣。玻璃和光線構成的圖案美得令人屏息。
父母:喬治.以撒.溫德姆(歿)、玫瑰.賈瑞特.溫德姆
她往前站了一步,用手觸摸玻璃上的人形,這些人形高舉的手指變成了枝葉,然後又化成了語言。
「噢,奇岡。我不曉得這裡有人。」她說。
樓梯間傳來一陣腳步聲。喬安娜回來了,看起來有些上氣不接下氣。
「噢,我也希望。」
「嗨。」
「嗯,找不到什麼紀錄,」她說,「不然就是我一時找不到,但我有時間的話,會再仔細找一遍。那座禮拜堂是一九三〇年代晚期落成的,隸屬這座教堂的一部份,這記載在教堂歷史裡;動工的時間是一九三八年四月。我也有印象那座禮拜堂是一個匿名的人捐錢蓋的,可是在樓下找不到相關資料,只找到這張收據,這上面有做那些花窗的藝術家的名字。」
「對,沒錯,好像是。我找到她的名字了,她叫做玫瑰.賈瑞特。」我想起穹頂閣樓裡找到的那疊紙,提到愛麗絲要被送走的那封信裡,寄信人的署名是R,這一定是她沒錯——玫瑰(Rose)。這時我心裡感到一股急遽的興奮,彷彿這個在一百年前活過、夢想過、也受苦過的女人走進了這間辦公室。「她一定就是我曾祖父的姊姊或妹妹。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關於她的事,可是顯然一九一一年的時候,真的有她這個人,她是個寡婦,有一個女兒。」
「這是希伯來文。『特黑拉』(Tehillah),就是『讚美』的意思。還有『亞當瑪』(Adamah)。」
「沒有,有飾邊的花窗都還放在後勤基地的禮拜堂,除了最大的那一扇以外;那扇已經請人清乾淨了,現在在這裡展示一段時間。妳想看嗎?」
蘇希露出笑容。「我想知道,你都怎麼禱告?」
「我剛在想那句引言有什麼含意。」我說。
「我們只是在看這道花窗。」我向她解釋。
「能再看到妳真的很好,露西,真的很好。妳找到什麼再告訴我,好嗎?我也會打聽一下能不能去看放在禮拜堂裡的那些花窗,還有,祝妳尋寶順利。」
傍晚時,媽媽搭著一部淺綠色的豐田汽車回家。她邊笑邊用沒受傷的手勾起幾個薄薄的塑膠袋,車倒退出去時,她因為一隻手戴著護臂,另一手又拎滿了東西,便站在原地朝車子的方向微笑。開車的人對她揮揮手,把頭伸出窗外跟她說再見;他的臉型有稜有角,相貌十分和善,頭髮已有些花白。媽媽站在車道上,待男人的車消失在視線裡,才轉身進屋。
「不用客氣。感覺這是一道很吸引人的謎對不對?」
「很了不起,不是嗎?另一道窗,就是那道約瑟窗,如果整理好了,一定也很壯觀,禮拜堂的其他花窗我也等不及想看了。這道窗是創世記的故事,不過沒有呈現整個故事。我第一次看到這道窗的時候,玻璃髒到我根本看不出上面有什麼圖案。妳看到這些紋路了嗎?」他一面問,一面指著圖案上面及四周交織的漩渦,一縷縷的漩渦都透著亮光。「那些都是風,我後來才看懂的。剛開始因為玻璃很髒,我還以為可能是有些玻璃已經碎了,被重新換過,但後來發現上面都是原本的玻璃,是原始的設計。」
我們又稍微聊了一下,講他的行程。待我掛上電話,周圍的空氣顯得純淨空曠,似乎煥然一新了。
「這個我就不知
和_圖_書道了,禮拜堂目前還是管制得很嚴格,但我會去了解一下。」「亞當和夏娃的亞當嗎?」奇岡問。
教父母:珂拉.史都華.埃文斯頓、華特.杰西.埃文斯頓
「那就真的很了不起了。聖經裡的女性意象和暗喻,以前大部分都會被忽略,最近這些年來,各界開始對這些東西有興趣,可是一九三〇或四〇年代的時候並不時興這些,我沒想到會在那個時期的藝術作品裡面看到這類元素。所以我對這道窗實在太好奇了,實在很有趣。」
露西,我媽低聲喚著,勾住我的手臂。露西,寶貝。她往走道走了一步,我跟著她。
奇岡微笑,又凝視我一會兒。我有種奇異的感覺,彷彿時間已然散去,而此刻和我倆從前無拘無束、自在相處的日子是連在一起的。我很努力才忍住不去牽他的手;十七歲時,我牽他的手多麼輕鬆自然。
「啊,我整個禮拜都不在這裡,還沒看過呢,我看一下吧?」
因她是神的力量所吹動的氣息……她令萬物燦然一新。
我在辦公室裡頭等著,凝視拱形窗外面的景色,一株銀杏樹的枝葉婆娑晃動,扇狀的葉子讓微風吹起陣陣漣漪。我心裡既煩悶又興奮,十分焦躁,令我回想起在印尼剛開始和吉隆交往的時光,那時生活很明顯要轉變了,一切都要不同了,顯得精神奕奕。最近發現的這些東西,布料、信件、花窗,如果單獨來看,都只是一時新奇,很快就會成為過眼雲煙,但合在一起看,卻讓我對自己的過去產生了疑問,而先前我始終以為過往早成定局。這一切儼然如地震,顛簸人心,令人措手不及,一如大地的顫動。
「可能是一九三〇或四〇年代的作品。」
「真的嗎?照理說應該會鎖啊。妳等我一下。」
「喂,你在哪?」我問。
「露西,找到有趣的東西了嗎?」喬安娜正要到影印機那邊,她中途停下來,從我後面看我手上的東西。
「謝謝,這個很有幫助。」我說。
奇岡咧嘴笑了。「這個嘛,我會划船出去,坐在水面上,想想生活中不順的事,想想我怎麼做會更好;然後我會想想生活中美好的事,一件一件地想,我就會覺得很感恩。」
出生日期:主後一九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嗨,牧師。」奇岡微笑對她說;我看得出來奇岡應該滿喜歡這個人。「這位是我的老朋友露西.賈瑞特;以前我們曾經瘋狂愛著彼此,很久很久以前。」
這張發票開立的日期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六日,上面列了三個品項。
「對,這件作品一定是別人委託製作的。這是一件很好的彩繪玻璃花窗,」他補充,「有受到蒂芙尼或拉法吉影響的痕跡,不過不是他們的作品,可是做得實在非常非常好。不管做這道窗的人是誰,他一定是很傑出的工匠,很優秀的藝術家,至於訂製的人,絕對非常有錢。」
「清得很乾淨對吧?」
我說:「這個嘛,我也覺得很有趣,可是老實說,我的理由跟妳不一樣。」我向蘇希提起飾邊圖案的事,並告訴她那塊布料和我在閣樓裡找到那疊紙的事。「我看到這道窗上也有一樣的圖案,真的大吃一驚。其實我就好像在瞎子摸象,我對這個人完全不了解,我只知道不管她是誰,一定和我的家族有關聯。」
她遞給我一張紙,紙上有很正式的標頭,以及一道道淡藍色的線,上頭的字跡工整嚴謹,一邊的欄位中記著一筆筆價格。這讓我想起小時候看到夢大師開的收據、放發票的灰色金屬箱,還有記著採購物品的表冊,全是整整齊齊手寫而成的,還有薄透的複寫紙,夾在發票之間。
「從門進來,門沒鎖。」
蘇希點點頭說:「對,不過『亞當瑪』其實是『人耕地』的意思,但英文大致可譯成『人』的意思,我想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些人形會從土裡長出來。」她湊近細看。「所以這道窗大概是『人讚美神』的意思。你說這道窗的年代是什麼時候?」
奇岡用鑰匙開了門,然後讓我先進到小房間裡,他才進來。小房間格局畸零,每一道牆邊都排滿了櫥櫃和架子。
「跟妳說,露西,以前捐贈的金主,常會請藝術家把他們愛的人、甚至是他www.hetubook.com.com們自己畫進聖經故事裡。我在想,約瑟窗裡的那些女人,她們看起來像誰嗎?」
8道彩色鑲嵌玻璃窗250美元/道
我便跟他去了。奇岡的一切都如此熟悉,他耳朵的輪廓、手臂擺動的方式,而且他仍像從前一樣,用深藍色橡皮筋綁頭髮,幾綹髮絲自髮圈散落。我跟著他走過狹窄的走道,爬了三階,進到一個房間裡。這一路上我好想問他,你還記得嗎?那些夜晚,我們划船到夢湖裡,看月亮升起,在湖水中隨波逐流,你還記得嗎?
「叫我蘇希就好了。」她說。
她站直了身子,一臉沉思。「真的嗎?但這個意象看起來非常現代,意象和引用的話都是。」
這裡的走廊全是拜占庭式的設計,一段接一段環環加蓋,但我走到教堂辦公室的途中,一點也沒有迷失方向。教堂秘書喬安娜是個身材矮壯結實的女人,髮長及肩,整頭都是金色挑染。我和她聊了幾分鐘,才發現原來她是以前學校裡大我一屆的學姊,以前上西班牙文課的時候坐在我旁邊。她現在已經結婚,有兩個小孩,先生在郡政府做事。我把之前跟蘇希講過的故事告訴她,包括布料和花窗的飾邊,還有我找到的那幾張字條。她在一個檔案櫃裡東翻西找了幾分鐘,但毫無斬獲。她對我說:「我去檔案室裡看一下。」她站起身理理裙子,接著說:「這是好聽的講法啦,意思就是我要去翻地下室的東西了。應該不會花太久的時間。」
他一看到我,便露出微笑說:「嗨。」他的聲音在教堂裡迴盪。
接著爸爸便溺水死了。在他的告別式上,我坐在平常坐的那張長椅上,爸爸的靈柩擺在前面,上頭堆滿鮮花。
「沒想到這道窗這麼美。」我輕聲說。
在我小時候,教堂裡女人能扮演的正規角色,就只有打理祭壇布,以及唱詩,但即使那些故事似乎都將我摒除在外,我仍深受這裡某種不能言說的力量所吸引,或許是這股深沉的寂靜,又或許是因為這股寂靜所召喚的神秘感受。我甚至到了十幾歲,已和奇岡.弗爾四處奔馳狂飆的年紀,仍持續上教堂。後來,教會終於改變規定,終止數十年來的激烈爭議,首度讓女孩子擔任輔祭員,我便是首批擔任輔祭員的女孩之一。我仍記得當時套上白棉袍,柔軟衣摺落在腳踝的感覺;我在腰際繫上繩帶,拿起沉甸甸的銅鑄十字架,帶著唱詩班慢慢走過教堂中間的走道。當時的我感到既喜悅,又帶點挑釁;那是離家前的最後一個春天,我把頭髮剪得極短,飄動的禮袍下穿的是牛仔短褲。
「對啊,我想跟你一起在黑暗中跳舞。」
「沒關係啊,我很喜歡炫耀那道花窗。花窗就在另一個房間,就是放禮袍啊、聖餅和聖餐酒的地方。跟我來。」
她笑了,握住我的手說:「我是蘇希.威爾斯。」
「我想啊,可是我怕會打擾你工作。」
「我不知道,這個想法很有趣,不過我之前都沒把注意力放在人的臉上,我要再仔細看看。不過總之用臉來判斷還是不夠,我想知道名字,還有故事。奇岡,我可以去禮拜堂看其他花窗嗎?」
奇岡露出笑容。「對啊,他們已經警告過我了,說那根管子是直通大地啊,『只能倒聖餐酒,不能洗刷子』。」
「『的確很有趣』還是『的確很神聖』?」
我們走到大廳,大廳其中一面牆上是成排的窗戶,另一面牆上是歷任教區牧師的裝框黑白照,年代最早可追溯到一八三五年。
紐約州羅徹斯特市
「真不敢相信,之前看起來那麼黑。」
「妳怎麼進來的?」
聖路加聖公會教會
大衛.普萊斯卡特 牧師簽名
大衛.普萊斯卡特 牧師簽名
我說:「有可能。」我心裡感到一股詭異的寬慰。這樣的故事縱然悲傷,但至少我能得到一個解答。「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家族的人從來沒提過她們兩個的事。」但這時我想起了另一張提到要把愛麗絲送走的紙條。儘管如此,我還是請喬安娜幫我查查看下葬紀錄。
他小跑步到走道盡頭。過了一陣子,他走回來,指著那道透明玻璃窗說:「這裡原本的窗戶拿下來修復了,今天下午就會送回來,我現在先把舊的填縫劑清掉,方便等下把窗戶裝回去。」
她笑著走回放禮袍的房間。奇岡說他可以帶我到教堂辦公室,但我說我知道怎麼走。
「在廚房啊。」我重複了他的話。「真希望我們現在可以一起跳舞。」
「太好了,我就想可能會有用,我幫妳影印一份。還有,我剛剛聽完妳說的事以後,腦力激盪了一下,我想我到樓下和-圖-書跟老鼠為伍的時候,可以把一九一〇到一九二〇年之間的受洗紀錄調出來,就是可以看一下。幾年前這裡淹過水,所以有些紀錄已經不在了,但我想妳可能還是會想看看這些資料,喏,給妳。」
「這些字是什麼意思呢?」
我退到最後面,用手機拍了幾張照。手機拍照的畫質不清晰,要是我今天想到要帶相機就好了。
我把雙眼闔上片刻,回憶從前。小時候,我每個星期都來這裡兩次,一天是唱詩班的練習,一天則參加冗長的主日崇拜。我和布雷克總在長椅間蠢蠢欲動,在奉獻的信封袋背後寫字或畫畫,兩人傳來傳去的,爸媽總要投以責備的眼神。我還記得那些久立、站起、跪下的例行動作,記得大家齊聲吟誦公禱,每週都唸一樣的禱詞。公禱完便是默禱,也就是不與人說的秘願。當時我總不甚自然地跪下,耳邊注意著四周的呼吸聲。那些歲月中,上帝彷彿和我爸爸一樣沉默寡言,和我伯伯一樣不以為然,也和我家進門處的曾祖父肖像一樣遙不可及;我閉上眼,感覺到的就是他們的目光,因此總感到忐忑不安。儘管如此,我八歲、十歲、十二歲時,依然盡我所能,為生活中的尋常小事禱告,不管是課業成績,或者是暗戀對象,甚至是一隻從鳥巢摔落地面的山雀雛鳥,牠小小的生命,曾在我手心發顫。七年級時,我因為污染問題感到憂心忡忡,還竭力為河流和湖泊祈禱。
這位蘇希博士兼牧師笑出聲來。「嗯,這我就沒話說了。不過哪天還是可以來看看,我想你會覺得很驚喜。」
弗蘭克.魏斯卓姆工匠
一塊塊鮮明繽紛的光投在我身上,豔藍、翠綠、鮮黃。我想起那塊有同樣飾邊的布料。寫那些字條的人,或許就是織那塊布的人,說不定她也就是製作這些花窗的人,或至少參與了設計。但這位神秘莫測的R,她是誰呢?她究竟是什麼身分?
此證
我們吃了簡單的晚餐:法國麵包、去籽黑橄欖、煙燻布里乾酪、生菜沙拉。我們在廚房吧檯上吃,一邊分享白天發生的事。媽媽講到今天去銀行辦事的人,一些我可能有印象的人;我則告訴她夢湖四處改變多大。她去年春天去過奇岡的玻璃藝品工作室,在那裡買了個玻璃盤,她拿出來給我看。盤身是亮黃色的,有著波浪狀的邊緣。吃完飯後,我們把少少的幾個碗盤洗了,然後又倒了些酒,一起到外面的露台去。我幫忙掛裝飾品,替媽媽的夏至派對佈置,她則在一旁監工;我把成串小燈泡繞在樹叢和花草上,連蔓生的牡丹花叢也掛上大把大把的燈串;這些牡丹是媽媽從前設計月花園時種的。我一面佈置,一面想起爸爸。我上一次參加家裡的夏至派對,就是爸死前的那年夏天;那時他在水邊掛滿燈籠,還搭了一座營火,燒了整晚。我從樹上採了幾枝花,放進白色籃子裡,在樹枝上繫緞帶,還調整了傢俱擺設的位置。
「我滿不想這麼說的,」喬安娜邊說,邊把剛剛那張收據的影本遞給我,「不過如果妳想的話,我可以查查下葬紀錄。那個年代很多小孩都很小就死了;當年流行性感冒大傳染時,她應該還很小。」
「這張出生證明可以也印一份給我嗎?」
吉隆笑了,我感覺得出來,他覺得喜孜孜的。
那是我最後一次進這座教堂。
「對啊。」我接過文件,對喬安娜說:「真的。」
我點點頭,想起那塊布,布料用一層層的紙裹著,藏在曾祖父行李箱的內裡後面。或許布料是為愛麗絲織的,或許是一件嬰兒用的毛毯;想想也合理,尺寸確實剛好,質地又細緻,而且織得那麼用心。但那塊布為什麼會被藏起來?「不知道她後來——她們兩個後來怎麼了?」
茲證明愛麗絲.賈瑞特.溫德姆
奇岡稍微想了一下。「我本來要說的是『的確很有趣』,不過其實兩個都對吧。來吧,來看花窗,就掛在角落的壁龕裡。」
1道彩色鑲嵌玻璃窗650美元/道
我翻到一九一一年五月的紀錄時,有一個眼熟的名字閃過,我翻回去看,心裡升起一股興奮。這張洗禮證書是厚紙製的,只有右上角有污跡,其餘部分都完好無缺:
遠處的聖堂有腳步聲在迴盪,接著來到走道,然後愈來愈近,我們轉過身,看到一個女人走進房間。她身材頗高,只比我嬌小一些,頸間戴著牧師的硬質白色衣領,看起來大約比我年長十歲左右,一頭金髮在肩際擺盪。
「謝謝妳囉。」
總金額2,650美元/道
她自嘲地笑笑,然後往後退,說:「好和_圖_書吧,對我來說很有趣,因為我是牧師,也是學者,不過對你們兩個人來說可能沒這麼有趣啦。」
「這花窗年代很久嗎?看起來感覺很久了。」
奉主耶穌基督的指示,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施以洗禮
「那是同一個年代的,也是同一個藝術家的作品,我幾乎可以確定。這兩道窗很有可能是同一批委製的作品,還有禮拜堂的其他花窗也是。我不知道他們當初為什麼沒把約瑟窗裝到牆上。」
因此我跪在那裡等著,一邊是媽媽,她紅著眼眶、銀髮肅穆地攏在腦後,而另一邊是布雷克,他身上西裝的袖口已經短了幾公釐。我等著,但當我站起身,讓酒甜苦交雜的滋味充臆口中,並沿著狹窄的走道繞著風琴走一圈,回到聖堂後,我並未感覺悲慟被療癒,整個世界也沒有煥然一新。我在教堂前面暫停下來,看著一排排的長椅,座位間全是熟悉的面孔,其中能看到堂哥阿約、伯伯亞特、伯母奧絲汀把柔伊抱在腿上。大家都穿著一身黑,其中有些人在流淚,有些人在擦眼睛。這些人很富有,他們名下有船、有事業,他們曾仰賴我爸爸幫他們開鎖,開啟他們的祕密及寶藏;這些人同時也很窮困,因為他們有過相同的夢想、祕密,也同樣失去過、挫折過。我爸爸離開了,永遠離開了,但不消幾分鐘,我們都會回到自己的生活,我們日常生活的軌道會掩蓋爸爸的離去,如潮水淹沒石子,不留痕跡。
「蘇希博士,蘇希牧師。」奇岡說。
「很有趣,好像大地跟聖餐酒一樣神聖。」
蘇希點點頭,視線仍停留在窗上。「我要查一下才能告訴妳確切的章節,不過這是《智慧篇》裡的一句話,是在讚美智慧女神的每一個優點。有一些傳統會把智慧女神叫做蘇菲(Sophia),你們一定也知道,『蘇菲』就是希臘文的『智慧』。根據經文的記載,上帝創造世界的時候,智慧女神也在場,不對,我修正我說的話,智慧女神不只在場,她也參與了創造世界的工作,而且非常喜悅。大家把智慧女神描述成一個全知全能、賦予生命的力量;我想這就是畫面上這些風想要呈現的。智慧女神也跟聖靈有關,而『靈』這個字來自希伯來文,希伯來文的『靈』(ruah)也是陰性的名詞,是氣息的意思,萬事萬物都有氣息,氣息可以讓萬物燦然一新。」她轉過身去對奇岡說:「你說這是一九三〇年代的作品,你確定嗎?」
「牧師,下禮拜見,等窗戶清理好以後。星期二可以嗎?」奇岡說。
蘇希舉起雙手說道:「我真的不知道,問得好,我只知道後勤基地的禮拜堂是一九三〇年代建的,隸屬這座教堂的一部份,所以年代確實吻合,沒錯吧?不過我只知道這樣,我到夢湖還不夠久。問問喬安娜好了,她是教堂的秘書。」蘇希從口袋裡抽出手機看了一下時間,然後說:「喬安娜應該還沒去吃午餐;她很優秀,而且在這裡待好幾年了,如果真的有相關資料,她一定找得到。」
「對,沒錯。所以我在想,教堂會不會有這些花窗的紀錄?有當初捐贈的相關文件嗎?」
我伸手穿過一道道彩光,碰觸那道飾邊,飾邊上圓月環環交扣、藤蔓和花朵的鉛框錯綜複雜。「又出現了,這個圖案。」
收據底部寫著「匿名捐獻人致贈」,下方蓋了這位藝術家的戳章:
市區裡已漸漸有觀光客湧入,大家都要去公園逛藝術市集。我逆著人潮的方向,走到教堂。教堂的門呈拱形,圓弧的曲線向上收攏成一個尖頂,門板漆成暗紅色,門鉸和五金零件都是舊式的,花紋繁複而華麗,鑰匙孔很深,模仿古代工藝的風格,錯綜複雜的鐵製飾紋襯在酒紅色的門板上,顯得十分醒眼。進到教堂裡,一股謐靜頓時湧上,這樣深沉的寧靜,令我不禁想靜下心來傾聽。空氣中還帶著木頭和蠟的氣息。我在門檻處稍稍駐足,讓自己習慣裡頭的幽靜和昏暗的光線。教堂裡的地板以鏽紅色的陶磚鋪成,長椅是拋光橡木製的。一扇扇玻璃花窗色澤鮮麗,在昏喑的教堂中更顯生動。
「噢,天啊,真的很美,太漂亮了。奇岡,這真的是之前那道窗嗎?」
「我以前都在這間房裡穿禮袍。對了,那個水槽不能用喔。」
「不過還是謝囉,還有謝謝你今天帶我來。」
「這個啊,這道窗走新藝術派的風格沒錯,不過我認為年代其實比較晚,看玻璃質地,可能是一九三〇或四〇年代的作品。花窗玻璃是很古老的技術,但十九世紀開始,大家開始只用顏料著色,有好幾十年都沒人用鉛框。後來二十世紀初,鉛框的古法又開始復興,到現在都還有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