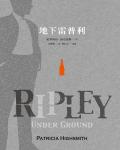十七
「嗯。葛雷斯東?」
他們決定在大使飯店再住一晚,以防萬一星期一晚上該到的護照又有什麼變故。湯姆考慮過要搭星期二凌晨的夜班飛機到希臘,但護照還沒拿到手,暫時還無法決定。另外他還得熟悉護照上自己的簽名。他明白,這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救貝納德一命。湯姆真希望可以跟赫綠思談自己的想法和感覺,但他怕她無法明白。如果她知道偽造假畫的事情,能夠理解嗎?理智上有可能,只要他講得有道理。但赫綠思會說,「為什麼這一切都要由你來承擔?不能讓傑夫和艾德去找他們的朋友嗎?貝納德是他們的生財工具啊。」湯姆沒把這事情告訴她。最好還是單獨行動,就某種意義而言,就是去除不必要的牽絆。別想要找人傾訴感覺,即使是來自家人的柔情。
「任何美國人的名字都行,」湯姆說。「最好是美國護照,英國的也可以。我現在住凡登廣場的麗池飯店……丹尼爾.史蒂文斯。」湯姆把麗池的電話告訴瑞夫斯,以方便連絡,又說屆時他會親自去奧利機場,跟瑞夫斯的信差碰面。
她說是。已經訂好房了,在蒙塔隆貝街的皇家橋飯店。湯姆把她介紹給赫綠思,然後去取車,赫綠思和史耐德小姐則在人行道上等,就離當初湯姆放下莫奇森行李箱的地方不遠。他們一路開到巴黎的皇家橋飯店,然後史耐德小姐說:「我該把東西交給你了。」
「啊,親愛的!別擔心!」湯姆手臂擁著她。「我們來喝點香檳吧!一切都很順利!」
以目前幾乎聽不見的狀況,要解釋也沒什麼用。湯姆設法問出傑夫和艾德都沒接到貝納德的消息。
「噓——」她指的是他的後腦。沒有什麼能逃過赫綠思的眼睛。湯姆心想可以告訴她幾件事,但不能全講。墳墓的事情就太恐怖了。此外,那就讓貝納德變成了凶手,但他不是。電梯服務生堅持要替赫綠思提行李,湯姆賞了他小費。
然後他們上床睡覺,那個奢華的大床上有四個厚厚的枕頭,赫綠思還自願把她的睡衣褲墊在湯姆的頭底下,免得萬一他又流血。赫綠思沒穿衣服,她的皮膚光滑得難以置信,像磨光的大理石,只不過當然她是柔軟的,甚至還是溫暖的。這一夜不宜做|愛,但湯姆覺得好幸福,而且毫不擔心明天——他這樣或許不聰明,但那一夜,他打算放縱自己一下。在黑暗中,他聽到赫綠思啜香檳時,杯中氣泡的嘶嘶聲,還有她把玻璃杯放在床頭几上的叮噹聲。然後他的臉頰抵著她的胸脯。赫綠思,妳是世上唯一會讓我只想到眼前的女人,湯姆想說,但他太累了,而且這句話大概也不重要。
赫綠思想,湯姆很開心。他想像再過大概一個小時,就可以跟赫綠思隔桌對坐,共飲香檳——如果她想喝香檳的話,通常她都會想的。
「啊——打得不嚴重。他情緒正緊張。一點也不嚴重,真的。」
「他發明了行李箱!我才不相信!誰能發明行李箱?太簡單了!真的,湯姆!」
「有貝納德的消息嗎?」
萬一你見到貝納德,請讓他以為我死了。貝納德認為他殺了我。我稍後會再解釋。這封信不要讓任何人看到,我寫這信只是以防萬一你見到貝納德,聽他說他殺了我——請假裝相信他,不要輕舉妄動。先設法拖住他,拜託。和_圖_書
「我今天很忙。」
好吧,莫奇森太太要趕來了,湯姆已經預料到這點。或許她知道那個淺紫色的理論。而《浴缸》賣掉了,賣給誰?另外,貝納德——在哪裡?雅典?他會步上德瓦特的後塵,在希臘的某個小島淹死嗎?湯姆想像自己去希臘。德瓦特死掉的那個小島叫什麼?伊卡利亞?在哪裡?明天找家旅行社問問。
他們很早就上床睡覺。湯姆想勸赫綠思把後腦那些愚蠢的膠帶剪掉,但是沒成功,她還買了一些淡紫色的法國消毒水,沾在包紮的繃帶上。她在麗池已經把他的圍巾洗乾淨,到早上就乾了。快要午夜十二點時,電話響了。瑞夫斯說有個朋友星期一晚上會把他需要的東西帶過去,搭德國航空三一一號班機,夜裡十二點十五分抵達奧利機場。
赫綠思聽不懂。湯姆是用英語講的。
「我明天再解釋吧——或許。」
到了早上,湯姆有很多事情要跟赫綠思解釋,而且他必須解釋得很小心。他說貝納德.塔夫茲因為他那位英國的女朋友而心亂,可能會自殺,所以湯姆想找到他。他可能在雅典,而既然因為莫奇森失蹤,警方就希望能掌握湯姆的去處,所以最好讓警方認為他在巴黎,或許讓他們以為他和朋友在一起。湯姆解釋說,他在等一本護照,最快也得星期一晚上才能拿到。湯姆和赫綠思在床上吃早餐。
「我不懂你為什麼要為這個瘋子費事,他還打了你。」
好,瑞夫斯說,有個朋友可以飛去巴黎。不能是運貨人(或貨主),湯姆堅持,因為他這回,絕對不能去扒別人的口袋,或者偷開別人的行李箱。
湯姆搭了船回到船主居住的密克諾斯島,他隨身帶了行李箱,覺得自己坐立不安、筋疲力盡,而且很挫敗。他決定今晚回到雅典。他坐在一家小吃店,沮喪地喝著一杯甜咖啡。然後湯姆回到碼頭找那個希臘船主,發現他回家吃過晚飯後,又回到船上了。
一切進行得很順利。湯姆和赫綠思在星期一半夜十二點到奧利機場,班機準時抵達,湯姆到樓上的出口等,葛爾妲.史耐德——或者是用這個名字的女人——過來跟他打招呼。
湯姆打電話要了一瓶香檳。他覺得頭暈,好像發燒一樣,但他知道那只是因為疲勞和失血。他檢查過屋裡有沒有血滴嗎?有,他記得臨出門前還上樓一趟,去看看各個地方有沒有血。
他們還在車裡。葛爾妲.史耐德打開她的大手提包,拿出一個厚厚的白色信封。
赫綠思在說什麼膠帶。
「我開車載你去。我想確定你平安無事。」
「對,我們在巴黎,」湯姆說。「很抱歉沒留字條給妳……或許赫綠思夫人明天夜裡晚些會回去,我不確定。」他把話筒又遞給赫綠思。
凌晨的空氣冰冷刺骨。湯姆硬威脅一個計程車司機(動口不動手),載他到雅典的憲法廣場,答應要給他很多錢,來到了大不列塔尼飯店的門口。
「以德國人來說,她算很漂亮了。」赫綠思說。
不過,這個小島,因為曾是德瓦特自殺的地方,對湯姆仍有一種www.hetubook•com•com模糊而微弱的神祕感。在那些黃白色的沙灘上,菲力普.德瓦特曾走過其中一處,走向大海,再也沒有回來。湯姆不太相信有任何伊卡利亞的居民還會記得德瓦特這個名字,但他還是問了那個小吃店的老闆,結果沒成功。德瓦特當年來這裡還不到一個月,湯姆心想,而且那是六年前了。湯姆在一家小餐館吃了一盤番茄羊肉燉飯,恢復了精神,然後去另一家賣酒的餐廳,載他來的那個船主之前告訴過湯姆,說如果要找他的話,他會在那裡待到下午四點。
瑞夫斯聽起來很慌張。老天,這個要求會不會太過分了?一本護照?沒錯,這種基本必備的小東西常有人搞丟,到處都有。湯姆禮貌地問瑞夫斯要多少錢。
湯姆朝希沃里街直走。在這麼晚的時間,四下一片昏暗,商店的櫥窗都拉下鐵柵、拴上鎖鏈,以防有人來偷那些專賣觀光客的垃圾——印著「巴黎」字樣的絲巾,太貴的絲質領帶和襯衫。他考慮叫個計程車到第六區去,在聖傑曼德佩那種最怡人的氣氛中散步,然後去力普小店喝杯啤酒。但他不希望有碰上克里斯的機會。他走回飯店,打了個電話到傑夫的工作室。
這倒是有可能,湯姆這會兒才想到,不過貝納德的東西都已經帶走了。湯姆去檢查過。而且貝納德進不去,除非打破後面的落地窗。「他不在屋裡了。」
她年約三十,金髮,相當健美,一臉聰明相,而且沒化妝,好像她只是用冷水洗過臉,穿上衣服就出門了。「雷普利先生,很榮幸認識你,」她用英語說。「久仰大名了。」
「我們賣掉了《浴缸》……他們問起……德瓦特!湯姆,如果你可以……」
「你好,瑞夫斯。我是湯姆。我在巴黎。你一切都還好吧?……你能不能馬上替我弄本護照?我已經把照片寄給你了。」
「好。」湯姆說,很滿意瑞夫斯其實還沒收到他的照片,就已經搞定了。然後湯姆掛了電話,問赫綠思:「明天晚上要跟我一起去奧利機場嗎?」
那船主大驚小怪,列舉了一大堆困難,但有錢好辦事。途中湯姆睡了一下,就在小小船艙裡的木凳子上,身上綁著安全帶。到了清晨五點左右,他們到達派瑞厄斯港。那個叫安提奴的船長昏頭昏腦的,可能是因為開心或錢或累壞了,也可能是喝多了希臘茴香酒。安提奴說他派瑞厄斯港的朋友看到他一定會很高興。
湯姆和赫綠思舉杯,赫綠思有點猶豫,然後喝了。她非得要檢查他的頭。湯姆屈服了。他脫掉襯衫,彎腰閉上眼睛,讓赫綠思在洗手台上用溼的小毛巾清洗他後腦的傷。他閉上耳朵,或者是試圖閉上,不去聽他預料之中的驚叫聲。
「是一位女士。葛爾妲.史耐德。她知道你長什麼樣子。」
「帳單我來付就是了,」湯姆自信地說。「重點是馬上弄來給我。如果你星期一上午收到我的照片,能不能星期一晚上就弄好?……對,很急。比方說,你會不會有朋友星期一夜裡飛到巴黎?」如果沒有,就設法找一個,湯姆心想。
赫綠思好恨英語,因為她認為裡頭充滿了她永遠搞不清的下流雙關語。「不,只不過這個人發明了一種行李箱。」
貝納和圖書德顯然一定沒回麗影,否則安奈特太太會提起的。
湯姆本來圍了一條墨綠與藍色交錯的圍巾,在脖子上圍得很高,蓋住流血的傷口。這會兒他摘下圍巾。「貝納德打了我。現在先別擔心,親愛的。脫掉鞋子,脫掉衣服,讓妳自己舒服點。要不要喝香檳?」
「很不清楚!」
「是的,史耐德小姐嗎?」
祝 一切順利
「啊,那是什麼——」
「晚安,史蒂文斯太太,」湯姆用法文說。「今天晚上妳是史蒂文斯太太。」湯姆本來想帶她去櫃檯登記,然後又決定不必費事了,於是領著赫綠思轉向電梯。
「朋友嘛,」湯姆說。「現在,親愛的,妳要不要回麗影,跟安奈特太太作伴?或者——我們可以打電話跟她講一聲,妳今天就可以陪著我了,」湯姆講得更開心。「不過我們今天最好換個飯店,只是為了安全起見。」
「好吧!」湯姆回答。「把你的麻煩都告訴我吧。」
湯姆暈過去一會兒,但他沒提。他爬到馬桶邊吐了一下,再用赫綠思的溼毛巾擦擦臉和額頭。然後過了兩分鐘,他站在洗手台前,啜著香檳,同時赫綠思用一條小手帕做成包紮的繃帶。「妳為什麼要帶著膠帶?」湯姆問。
湯姆站在灰色的人行道上,看著眼前圓弧形的凡登廣場。圓圈讓他心煩。他該走哪個方向?往左到歌劇院,還是往右到希沃里街?湯姆比較喜歡以正方形或長方形思考。貝納德人在哪裡?你為什麼想要一本護照?他問自己,當成一張備用的王牌?讓自己更有自由行動的機會?我沒辦法畫得像德瓦特那樣——貝納德今天下午說。——我就是根本沒辦法畫了,就連為自己畫都很難。貝納德此刻正在巴黎的某個飯店,在浴缸裡割破自己的手腕嗎?或者正靠在塞納河上的某座橋,打算趁沒人注意的時候跳下去?
「你們打架了?因為他不肯離開?」
「傷口不大,否則血就會流個不停了。」湯姆說。可是清洗傷口時,血當然又開始流了。「我去拿另一條毛巾——找點東西來擦。」湯姆說,回到臥室,身子一軟倒在地板上。他沒昏迷,所以他又爬回浴室的瓷磚地板上。
「雅典?」
他們換到大使飯店,在第九區的奥斯曼大道上。保守而尊貴。湯姆用威廉.坦尼克與妻子蜜瑞兒的名字登記。湯姆又打了電話給瑞夫斯,常常替他接電話那個德國腔的男人接的,湯姆留了他的新名字、地址、還有電話PRO72-21。
「我真的不知道。或許就在巴黎。」
湯姆從他飯店的房間打電話給赫綠思。她不在,女傭說她跟父母出去吃晚餐了。湯姆又請接線生幫他打去漢堡找瑞夫斯。這回二十分鐘就接通了,找到了瑞夫斯。
湯姆星期三到了那裡。他從密克諾斯島雇來一艘當地的快艇和船主。在湯姆短暫而片刻的樂觀之後,伊卡利亞島令人徹底失望。島上的小城阿門米斯提(或者類似的名字)看起來昏昏欲睡,湯姆沒看到任何西方人,只有一些漁夫在修補魚網,還有坐在小吃店裡的當地人。湯姆從小吃店開始詢問,看是否有人見過一個叫貝納德.
和_圖_書塔夫茲的英國人,說他深色頭髮、瘦瘦的等等。湯姆打了個電話到另一個聖基里克斯島的小鎮詢問,一名旅館主人幫他查了,說他會再去問另一家旅館,再回電給他。結果他沒回電。湯姆放棄了。這是大海撈針,湯姆心想。或許貝納德選了另一個小島。「我要檢查一下你頭上的傷。進來浴室吧,那邊燈光比較亮。」
「貝納德人呢?」赫綠思脫掉鞋子,現在光著兩隻腳。
湯姆笑了起來。
「我是湯姆,我在雅典。」湯姆說。他在床上都快睡著了。
「他的名字呢?」湯姆問。
「葛雷斯東有什麼好笑的?」
「沒有,沒聽說。你去雅典做——」
門上傳來敲擊聲。香檳送來得好快。那個灰髮肥胖的侍者笑咪|咪打開軟木塞,然後把瓶子放進了冰桶。
下午湯姆和赫綠思去看了場電影,六點回到飯店。還沒有瑞夫斯的留話。在湯姆的建議之下,赫綠思打回家給安奈特太太,然後湯姆也跟她講了話。
湯姆告訴她,家裡那輛旅行車還在梅朗火車站。或許她可以找他們家偶爾會雇用的園丁安德烈,跟她一起去把車開回來。
「今天晚上載我回雅典的派瑞厄斯港要多少錢?」湯姆問。湯姆身上還有一些美國的旅行支票。
「那些小島現在情況怎麼樣?」湯姆在一個相當體面的旅館問起,他覺得這旅館的人可能懂一些觀光的事情。湯姆在這裡講法語,不過在其他旅館可以通一點英語,「尤其是伊卡利亞島。」
「什麼?」老天,電話這玩意兒真會逼得人發瘋。大家應該回到用紙和筆和郵船的時代。「我一個字都聽不見!」
「你的頭怎麼了?」
「伊卡利亞?」對方有點驚訝。
湯姆坐在寫字檯前,匆忙寫了一封短信:
「當然要,有何不可?」
到了星期二下午兩點,湯姆來到雅典——比他五、六年前來訪時更多汽車,也更乾淨。湯姆登記住進了大不列塔尼飯店,在面對著憲法廣場的房間裡稍事梳洗,然後出門逛了一圈,去其他幾家飯店詢問是否有一位客人貝納德.塔夫茲。貝納德不太可能住在大不列塔尼,湯姆心想,這是雅典最昂貴的飯店。湯姆甚至有六成的把握,確定貝納德不在雅典,但反正他得先到雅典,再設法去德瓦特的那個小島,或者去哪個小島;即使如此,湯姆還是覺得不去幾家飯店問一下,也未免太笨了。
湯姆停下車,光線有點暗。他拿出那本綠色的美國護照,塞進外套口袋。護照外頭顯然包著好幾張白紙。「謝謝,」湯姆說。「我會再跟瑞夫斯連絡。他還好嗎?……」
幾分鐘之後,湯姆和赫綠思駛向大使飯店。
還沒有不清楚到再讓湯姆試著接通第二次。他繼續:「我不曉得貝納德現在人在哪裡,你有沒有他的消息?」
「今天我們要換個名字。妳想姓什麼?一定要美國姓或英國姓,因為我的關係。妳只是我的法國太太,懂吧?」湯姆用英語說。
「謝謝,先生。」那個侍者說,接過了湯姆的鈔票。
「你為什麼去巴黎?」
有三個人看著他們。她真是他太太嗎?
「用來黏我的指甲。」
湯姆被她的有禮和愉快的口吻逗得笑出聲來。他很驚訝瑞夫斯居然能叫得和*圖*書動這麼有趣的人替他做事。「我跟我太太來的,她在樓下。妳今天晚上要在巴黎過夜嗎?」
親愛的傑夫:
湯姆下樓,跟櫃檯買了七十生丁的郵票,然後把信寄出。傑夫大概要到星期二才會收到。但這種事情他不敢打電報。或者他應該打?——我得躲著貝納德,甚至躲到地下去。不,這樣不夠清楚。他還在思索時,赫綠思進門了。湯姆很高興看到她帶著那個古馳的小旅行箱。
「親愛的——赫綠思——現在我是羅柏了。」湯姆用法語說:「容我告退一下,我得去練習我的簽名了。」
赫綠思靠著衣櫃,望著他。
「湯姆,你好蒼白!」
湯姆要了一個房間,不是他原來住過那間。那個值夜班的服務生很老實地告訴他,那個房間還沒打掃完畢。湯姆把傑夫工作室的電話號碼寫在一張紙上,請那位服務生幫他接到倫敦。
湯姆的說法是,他和一位講好要碰面的朋友貝納德.塔夫茲失聯了。不,他自己的名字不重要,但如果有人問起,湯姆就說是羅柏.馬凱。
「我是湯姆,我在巴黎!你聽得見嗎?」
這時赫綠思已經回到香堤邑的家裡,湯姆跟她通了電話。「對,我在巴黎。妳今天晚上想過來嗎?」
瑞夫斯暫時還說不上來。
怎麼黏?湯姆很納悶。他拿著膠帶讓她剪斷。「粉紅色的膠帶,」湯姆說。「這是種族歧視的標誌。美國的黑人力量應該要抗議並阻止。」
接線生說,這通電話要四十五分鐘才能接通,線路很忙,但結果半個小時就接通了。
回到房間,湯姆檢查了護照一下。看起來很舊,而且為了不要顯得突兀,瑞夫斯也把他的照片磨舊了。名字是羅柏.費德勒.馬凱,三十一歲,生於猶他州鹽湖城,職業工程師,沒有撫養的家眷。簽名字跡高而修長,所有的字母都連在一起,這種字跡讓湯姆聯想到他認識的兩個美國人,很無趣。
「啊,湯姆——」但赫綠思的口氣並不失望,湯姆知道。她喜歡做有點詭詐、保密的事情,雖然有時沒必要保密。她曾告訴湯姆一些她青春期跟女同學的密謀故事,也有男生加入,以逃避父母的監視,精彩程度不輸考克多的虛構創作。
湯姆
那個小島位於相當東邊,是多德卡尼斯群島最北端的島嶼之一。沒有機場。有船,但那個人不曉得多久有一班。
「喂?——巴黎?」傑夫的聲音像是溺水的海豚所發出的。
湯姆把話筒重重摔回話座,又拿起來,準備要跟樓下的接線生發火。但他又放回去。不是接線生的錯。不是任何人的錯,找誰發脾氣也沒用。
然後傑夫說,「他們想找到德瓦特……」(喃喃用英語詛咒。)「老天,如果我根本聽不見你講什麼,我不相信中間的人能聽到什麼……」
電話突然斷線了。
「莫奇森的太太可能……」
然後他上樓到房間,洗了個澡,從頭到尾都留意等著電話鈴聲。到了七點四十五分,電話接通了。
「那為什麼你跑來巴黎?他還在屋裡嗎?」
「湯姆.雷普利嗎?」她微笑著說。
「我要去倫敦了。我是說,今天晚上。準備好那些化裝用品,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