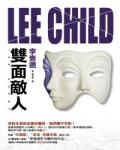12
我們三人陷入沉默中。
我點點頭說:「如果不是為了克拉瑪夫人,我根本應該早早放棄這案子。」
諾頓又閉上眼睛,一開始我以為她很生氣,接著我發現她在回想昨晚軍官俱樂部裡,大家用完餐要拿外套離開時的情景。
「千真萬確。」
在頭二十哩路上我沒做任何事,接著我把車內圓頂燈打開,開始仔細檢查克拉瑪的手提箱。我想應該不會發現什麼,而且也沒出現任何意外。他用的是一本七年前核發的普通護照,護照裡的他看起來比汽車旅館裡的他好一點,但實際上沒差多少。因為常常進出德國與比利時,裡面蓋了很多戳章——兩個國家分別代表著可能的決戰地點以及北大西洋組織總部。除此之外,他沒去過別的地方。他真的是個工作狂,因為過去七年時間裡,他關心的只有一件事:如何為這世界上的最後一個坦克戰場建構完美的指揮架構。
我說:「好,我們上吧。」
我點點頭,不發一語。
「你的新指揮官怎麼說?」
「她知道,卡邦那件事發生後,他跟她談過。」
「你應該聽命於他。」
那本精裝書是中西大學出版的學術論文,主題是一九四三年七月發生的庫斯克戰役。那是納粹在二次大戰期間發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攻擊,而且也是納粹軍隊第一次在戰場上慘敗,那場戰事最後演變成人類史上最大的坦克決戰。而且,除非像克拉瑪這種人抓狂,否則以後也不會再有這種規模的戰事。我對他的閱讀品味一點也不意外,他心裡一定隱隱恐懼著未來有天會發生大戰,所以要深入了解德國的虎式與豹式坦克如何在當年的驕陽與令人窒息的塵土中馳騁,與蘇聯T34坦克對決。
「那她最少必須離開一小時。」
她不發一語。
她說:「解散!」
「在哪裡?」
他搖搖頭,把手提箱放回櫃檯上,「只是猜測。」
「也許你應該相信,他們可是資深軍官。」
我說:「當然。」
她說:「不,我不知道。我還很訝異他們為什麼沒有待在德國。」
「一萬兩千人,可能有一萬兩千把刀。」
我說:「告訴我們昨天的晚宴發生了什麼事。」
她點點頭。
「所以小偷是往北逃。」
「我為什麼要給他們手提箱呢?我跟他們又不熟。」
我說:「大概是吧。」那傢伙用請求允許的神情看著我,然後用兩手把手提箱拿起來,好像鑑賞家在仔細端詳一件珍品似的。他把東西拿到燈光下,從每個角度看看它。
我問她:「這些記號代表什麼?是在基地裡還是不在?」
「我想是瓦特.瑞德醫院把屍體發還國防部,其餘細節由他們處理。」
「上面會有產品號碼,也許有保存期限在上面,類似的東西。也許可以讓我們找到兇手買優格的地方。」然後我頓了一下,說:「而且上面可能會有指紋。」
這個休息區跟美國大部分州際公路休息區一樣,都是把往北與往南的車道分開來,中間形成一大塊凸起的草地,往兩個方向的旅客都可以使用這個休息區。因此建築物兩邊都算入口,沒有後端可言。休息區由磚造建築構成,周圍花床光禿禿的,樹木也沒有葉子。裡面設有加油站,還有一排排斜斜的停車位。時候休息區看起來不算特別熱鬧,但人也不少。假期快結束了,一個個家庭拖著不情願的腳步回家,馬上該上課、上班了。停車位只有三分之一停著車,而且大家停車的方式非常有趣,每個人都是看到有位置就停,並未考慮要離用餐區與廁所近一點,怕有位置不停,等一下會找不到停車位。
「是嗎?為什麼?是件禮物嗎?」
在等待的時間裡,我跟桑瑪一起在辦公室裡看著她列出的清單:在卡邦的死亡時間裡,誰在基地裡、誰不在。她把從電腦跑出來長達一碼的報表紙整齊地摺成一吋厚。紙上每一行都有點陣印表機用淡淡墨水印出的姓名、階級與兵籍號碼,幾乎每個人旁邊都被打上核對記號。
她說:「我不知道該笑還是該哭,我真的被你們搞混了,而且這種說法實在太荒謬!我很驚訝妳居然連這種話都說得出口。」
她說:「在。」
我點頭說「從她那裡我們可以知道什麼?」
「是我怎麼樣?」
整間辦公室都陷入沉默,諾頓看著她的樣子好像她剛才妙語如珠地講了個笑話,但諾頓卻一句也聽不懂。
「調查的職責是發出疑問和-圖-書。」
桑瑪說:「嗯。」她點點頭,又繼續開車。
桑瑪等著車陣出現空檔,然後穿越三條車道,開上用來分隔車道的柔軟草坪。她開下一個斜坡,通過一道排水溝,然後直接把車開到路的另一邊。她暫停後等了一下,然後又左轉開回柏油路,往南馳騁。這種行進路線是悍馬車最擅長的。
「就是她。」
「酒吧在哪裡?」
「所以根據你們的交情,妳知道他們的基地在德國?」
「這裡往南走三十哩的一個汽車旅館。」
「這個基地有十萬畝大。」
她說:「我們來推演一下。昨晚瓦索與庫莫在十點拿著手提箱離開博德堡,他們前往北邊的杜勒斯機場或華府。然後他們拿走議程,把手提箱丟出車窗外。」
她說:「有什麼可以為你效勞的嗎?」
「他們吃飯時心情怎樣?」
她說:「陸軍是個大家庭,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我說:「回去後跟用餐室那傢伙談談,看看當晚是誰跟瓦索與庫莫吃飯。」
「那妳是怎麼認識他們的呢?」
機票時間跟蓋伯說的一樣,從法蘭克福到杜勒斯機場,再從華盛頓機場到洛杉磯國際機場,兩趟都是來回票,都是經濟艙,享有公務人員優惠票價,在出發三天前就訂位了。
「我想我們該跟她談一談。」
他說:「現在是一月,晚上有一點點露珠,冷到恐怕會結冰,而且空氣中鹽分較重,這時候如果東西被擺在路肩,會耗損得很快。這東西看起來很老舊了,但是沒有因為空氣而耗損的跡象。在帆布縫隙裡有些沙礫,但數量不是很多。所以它不是除夕夜那天就被丟在那裡的,至少這點滿可以確定的。我猜它在那裡待了才不到二十四小時。最多不會超過一晚。」
「如果委婉一點就不會侵犯到她。」
我問她:「誰?」
「瓦索與庫莫說沒有。」
我們在軍官俱樂部大廳找到諾頓中校,問她是不是可以移駕回她的辦公室,挪點時間給我們。我可以看出她很困惑,我說這是件機密,她還是很困惑。因為威拉跟她說,卡邦的事情已經結案了,她不了解我們還有什麼要跟她說的。但她還是同意了,跟我們說三十分鐘後見。
桑瑪說:「這些垃圾桶的位置太明顯了,不可能在這裡丟東西。」
我們離開休息區往北走,桑瑪又好像在參加越野賽似的再度穿越分隔草坪,然後掉頭往南開。我找到一個最舒服的姿勢,準備好踏上歸途。左邊的天色已經開始慢慢變暗,隱隱約約可以從西邊看到夕陽。路上濕濕的,桑瑪似乎不擔心路面可能結冰。
「還有,諾頓說我們是個大家庭。」
大家都沉默以對。
「克拉瑪是歐洲裝甲部隊的指揮官,他們又是他的幕僚,難道他們的基地會在夏威夷嗎?」
「說啊!」
「她不知道威拉警告過你。」
那傢伙搖搖頭,但他看著桑瑪,不是我。
我說:「這東西在那裡還不到一個月。」
我說:「除夕夜。」
「我們可以知道議程的下落如何,知道瓦索與庫莫把議程拿回去了。但至少陸軍就可以放心,不會因為記者在垃圾堆裡發現它而搞得輿論嘩然。」
她說:「就跟軍官俱樂部裡的任何一頓飯局一樣。」
「說說看那頓飯怎麼樣?」
「而且,他們會在休息區做這件事,把東西丟在垃圾桶裡比較安全,把手提箱從車裡丟出來太顯眼了。」
桑瑪說:「也許諾頓發現議程,看到了內容,那她就可以跟我們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桑瑪抬頭看著牆上的鐘。
「我們可以問她,瓦索與庫莫是不是跟她約好昨晚要拿手提箱,藉此我們可以證明他們在找東西,克拉瑪夫人就有可能是他們殺的。除此之外呢?」
「他們有提到為何再度造訪博德堡嗎?」
她不發一語。
「是妳把手提箱給他們的。」
「這點倒是挺有吸引力。」
我說:「錯了,他把自己帶過去了。」
「我不相信他們。」
她說:「很輕鬆,好像正在度過平凡無奇的一晚。」
「我們要用不一樣的方式來進行。」
「他們整晚都待在博德堡的酒吧與用餐室裡。」
我往窗外看,下午很快就要溜走了,傍晚即將來臨。整個世界看來又冷又暗。
「在哪裡被拿走的?」
「你們要簽收。」
「他們是克拉瑪將軍的手下。」
「不,我們知道顯然博德堡是個很有吸引力的地方,瓦索與庫莫https://www•hetubook.com.com不斷來這裡,只是我們不知道理由何在。」
「有可能委婉一點嗎?」
我說:「吃晚餐的時候,或者當他們離開時。」
我們往北開,經過克拉瑪投宿的汽車旅館,往東開過交流道後,往北開上九十五號州際公路。十五哩後我們經過一個休息區,然後開始尋找那個警察局。繼續開了十二哩路後,我們找到警局。那是棟單層的低矮磚造樓房,長長的樓房屋頂上插滿高高的天線桿。樓房可能是四十年前蓋的,用的是黯淡的棕褐色磚頭,很難判斷它是本來黃色,但因長久日照而褪色,或者原色是白的,但因沾染了汽車廢氣而變色。整棟樓房上面平均地嵌裝著不鏽鋼製的裝飾藝術風格字母,拼起來構成「北卡羅萊納州警局」。
我說:「不可能。」
「除夕夜她去參加一個派對。」
「在他投宿的地方被偷走。」
「那是有可能的。」
我們停在一道雙扇玻璃門前靠邊,桑瑪把悍馬車的引擎熄掉,我們坐了一會兒才下車,越過一道狹窄的人行道,拉開大門後走進警局。這是個典型的警局,地上鋪了油地氈,不管需不需要,每晚都會清裡一次。冰泥牆面直接塗了好幾層亮光漆。局裡空氣很熱,隱約可以聞到汗味跟咖啡加熱後的味道。
「如果是這樣,又怎麼會發現它呢?」
她問我:「還有別的事嗎?」
我起身後桑瑪也站起來,我拿走放在中間那張椅子上的手提箱,走出辦公室,桑瑪跟在我後面。
她說:「阿靈頓國家公墓,不然還會在哪裡?」
我沒有回話,只是轉身走出門,回到悍馬車上。
她說:「有什麼問題嗎?」
我點點頭——這就是我怕的,我用拇指撥弄整疊紙。
我們開著悍馬車到心戰學校去,停車的車位有可能是別人專用的。那時候已經九點了,桑瑪關掉引擎,我們開門走進外面的冷空氣中。
我們走過鋪著老舊磁磚的迴廊,到了諾頓的辦公室門口,燈開著。我們敲門後走進去,諾頓坐在桌後,先前擺在桌上的那些教科書都已放回架上,眼前也沒看到橫紋筆記本,也沒有鋼筆跟鉛筆。她的桌面完全淨空,桌上只看得到檯燈打在桌面的光影。
「 將近一萬兩千人。」
他說:「我自己把它擺進塑膠袋的,因為我想讓它保持乾淨,不知道過多久才會有人來拿。」
「什麼都沒有。」
他說:「這裡,往北的路肩上,休息區過了一哩後,我們這裡往南十一哩的地方。」
我不發一語。
「他在哪裡投宿?」
我說:「他還帶了藍波刀。」
桑瑪說:「是妳嗎?」
他頓了一下,從桑瑪那個方向把頭轉過來,用厚厚的指甲壓在桌上的記事簿上,往下滑到一行寫著哩數標誌代號的地方,然後轉身再用同一隻手指壓在一張地圖上。那一大幅公路地圖畫著九十五公州際路穿越北卡羅萊納州的部分,地圖又窄又長,就像一道五吋寬的緞帶。地圖從南、北卡羅萊納州交界處的九十五公路開始畫起,結束在公路越過州界,進入維吉尼亞州的地方。那傢伙的手指猶豫了一下,然後很確定地往下滑。
「那他們為什麼大老遠跑來這裡晚餐?」
我搖搖頭。
她揮手示意我們走向三張訪客椅,自己挑一張坐下,桑瑪跟我分別挑中最右邊跟最左邊的一張。我把克拉瑪的手提箱擺在中間那張椅子上,想藉此提醒她,但她連看都沒看一眼。
我又點點頭。說真的,要從一萬兩千人裡找出一個兇手,實際上並不算難,警察查案時,嫌犯人數可能更多。在韓國曾經發生一件案子,結果整個駐韓美軍部隊都成了嫌犯,但是那種案子需要投入無數的人力與物力,而且每個人都必須集體行動。不能有人背著指揮官偷偷行動,像我們兩個一樣。
我沒有回話。
「她們都有不在場證明。」
我看看手錶,已經快十點了。
「你是一一〇特調組的,你想問誰、問什麼都可以。」
我說:「妳再表演一次迴轉,穿越分隔草坪,然後朝著北邊往回走,我想去看看休息區。」
她說:「三十分鐘到了。」
「有辦法知道它被擺在那裡多久了嗎?」
諾頓說:「一只手提箱?」
「克拉瑪將軍的葬禮在昨天中午舉行。」
我問她:「妳知道他們要來嗎?」
「威拉正在監控我。」
她說:「跟瓦索與庫莫一起吃飯的人裡和_圖_書只有一個女的。」
「那真的是世界陸軍史上頭一遭。」
「你是軍官,我也是軍官。」
桑瑪問我:「你相信她嗎?」
「別人說她在那裡,但她有可能那時候已經出去過了。那小夥子說悍馬車是在十一點二十五分開走,所以她還有五分鐘的空檔可以非常從容地突然冒出來,等著跟大家一起倒數計時,派對又進入另一個高潮。」
「如果是她,她會把手提箱拿出來處理乾淨,也許裡面有她的電話、名字或照片,或者日記裡有提到她,她不會希望這件事變成醜聞。東西拿到後,她就不需要其他東西了,當然很樂意在別人的請求下把手提箱交出來。」
「所以東西是跟他們一起吃飯的人給的,我們該查查誰和他們吃飯,也許那張清單裡的某個女軍官也在場。」
我說:「一點也沒有。」
我說:「她是個軍官,妳覺得還會有其他說法嗎?」
「的確。」
「逼急了,她有可能去找威拉。」
桑瑪不發一語。
我說:「昨晚瓦索跟庫莫是帶著手提箱離開的嗎?」
「妳能百分之百確定嗎?」
有個傢伙坐在接待櫃檯後面,因為我們穿著戰鬥服,他又能看到停在外面的悍馬車,所以他很快就想到我們的來意。他沒有要我們出示識別證,也沒有問我們來做什麼,他也沒有懷疑克拉瑪將軍沒有親自現身,只是瞥了我一眼,花了較長時間看看桑瑪,然後屈身拿起在櫃檯下的手提箱。東西裝在一個透明的塑膠袋裡——不是證物袋,只是某種購物用的袋子,上面用紅色字體印著店名。
我說:「六十哩路。那手提箱是在博德堡以北六十哩的地方被發現的,等於是一小時車程。如果是他們,一拿到議程他們就會把行李箱丟了。」
手提箱裡別無他物,只有幾張碎紙條卡在縫隙裡。克拉瑪每次用過手提箱似乎都有清空物品的習慣,甚至可能會把箱子倒過來搖一搖,清理乾淨。我把所有東西都擺回去,把帶子扣好,將箱子擺回腳邊。
桑瑪聳聳肩,然後用手去撥動印表紙邊緣,整疊紙先是變鬆變厚,然後就一邊從每一頁空隙中吹出空氣,一邊漸漸變薄。
她問我:「手提箱裡有東西不見了嗎?」
「你來決定吧。」
「確切時間是什麼時候?」
我說:「他必須把東西丟掉,離現場不能太近,也不能太遠。」
「離汽車旅館三十分鐘車程。」
「你怕他嗎?」
我說:「百分之百相信,如果她之前曾看過那只手提箱,她一定會顯得驚慌失措,而且我當然相信她說自己不會去汽車旅館這件事。如果跟她來段一|夜|情,至少要去麗池酒店開個套房。」
我點點頭,他把櫃檯的記事簿反轉,推過來給我。我右胸的口袋上方印有李奇兩個字,我想他大概沒注意,因為他大部分時間都看著桑瑪。所以我在應該簽名的地方寫上潦草的克拉瑪三個字,然後拿起手提箱後轉身。
「他帶了什麼東西去現場。」
桑瑪幫我開停在外面車道上的悍馬車,因為我們不想再浪費時間去調度場換車。不過悍馬車有點不符合她開車的風格——悍馬這種又大又慢的卡車有很多長處,但在柏油路上行走不是其中之一。她在駕駛座上顯得很嬌小,車子噪音很大,引擎轟隆作響,輪胎也因為摩擦地面而發出聲音。那天的天氣陰沉,才下午四點天色就快黑了。
這個手提箱與克拉瑪的行李袋就各方面看來都讓人覺得是成套的。不管是顏色、設計、使用時間和磨損程度都一樣,上面沒有印他的姓名。我打開後看看裡面,有個皮夾,機票還在,還有護照,三張夾在一起的行程表,以及一本硬殼書。裡面沒有議程。
我把手提箱的位置稍微調整一下,讓它在椅子上站得直挺挺的。
「只是例行性攔檢,那位州警下車後走向他攔下的那輛車,就看到東西被擺在那裡。」
我說:「氣氛,還有你們聊了些什,還有你們的心情怎樣。」
桑瑪說:「沒什麼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有收穫嗎?」
「這圈子有多大,長期的婚外情哪有可能不被知道?」
我的腦海浮現一個畫面:一個男人氣喘吁吁地快步行進著,也許流著汗,右手拿著一把沾血的藍波刀與一支鐵鍬,左手拿著一個空的優格盒子,在黑暗中蹣跚前行。到達一個定點之後,往下看著手裡的盒子,然後丟進矮樹叢。然後把刀插|進口袋裡,把鐵鍬藏在大衣裡和圖書。
我說:「先睡一覺。明天一早,我們要去找那個優格的盒子。」
「我在酒吧裡,他們邀我一起用餐,如果拒絕,那就太失禮了。」
她說:「拜託你饒了我吧!我只想知道你們到底想用一連串胡言亂語表達些什麼,有東西不見嗎?」
他的行程表跟機票完全吻合,還特別指定了座位,他似乎偏好靠走道的座位,也許他的年紀已經到了頻尿的地步。他還預約了爾汶堡來訪軍官寢室的一個單人房,不過他永遠都到不了了。
「我們可以走進去直接問她嗎?」
她說:「他們沒跟我講。」
「有人把一只手提箱交給瓦索跟庫莫。」
我們有好一陣子沒講話。諾頓面露微笑,好像她現在的情緒反應主要是覺得很好笑、沒有憤怒。她閉上雙眼,過沒多久後又打開,像是已經把這段對話從記憶裡消除了。
「瓦索與庫莫怎麼知道要跟誰開口要東西?」
我說:「好,謝啦。」
「他應該是戴著手套。」
她說:「挑個名字出來。」
我說:「所以在現場的有四種東西:他本人、一把藍波刀、一支鈍器,還有一盒優格。那優格是哪裡來的?」
我說:「還真難啟齒,她可能會覺得被人侵犯。」
我們坐在心戰學校外面的那輛悍馬車裡,引擎正空轉著,汽車裡的暖氣帶有柴油味。
「至少有這麼遠吧。」
「他們在爾汶堡訂了餐盒,出席的有二星中將、一星准將,還有幾個上校,整個午餐時間都要用來開會。這可能也是陸軍史上頭一遭。桑瑪,相信我,這個會議很重要。」
「聽起來我們好像要放棄克拉瑪這個案子了。」
我沒說話。
「那在三百哩外。」
那傢伙說:「這小偷還真怪,裡面有張美國運通卡,錢也還在。我們把裡面的東西都列在清單上。」
「什麼晚宴?」
諾頓面無表情地看她——如果她不是真的完全搞不清楚狀況,那她就能拿一座最佳女主角獎。
「卡邦比較重要,我們該先辦他的案子。」
桑瑪不發一語。
諾頓說:「上帝為證,那個人不是我。」
「也許真的沒有議程。」
「多年前,我跟他們見過一兩次面。」
「現在怎麼辦?」
「那妳為什麼跟他們吃飯呢?」
「妳跟幾位來訪的裝甲兵幕僚一起用餐。」
她說:「汽車旅館?我看起來像那種會跟男人在汽車旅館約會的女人嗎?」
我問他:「精確的發現地點在哪裡?」
「那只是編出來的,誰不知道除夕夜的派對都很混亂?」
「午夜那一刻她也在酒吧裡嗎?她是不是也跟人一起手握手唱著〈往日時光〉呢?只要問那些待在她身邊的人就可以確定了。」
我點點頭。問題還是無解。通常我只要打一通電話就可以安排基地裡所有的步兵排成一直線,每個人相隔一碼遠,跪在地上慢慢爬過基地的整個區域,像一把大梳子一樣梳過去,仔細低頭檢查地面,把每一根草撥開來看。這種事可以連續做好幾天,直到其中一人找到東西為止。如果有陸軍這種人力,在乾草堆裡,別說一根針,就是斷成兩半的針也找得出來。就連煞車上掉下的金屬碎屑也不難找到。
我不發一語。
她又點點頭:「這我知道。」
我把手提箱關起來,把它擺在櫃檯上,把箱子邊邊弄齊。我感到失望,但一點也不意外。我問他:「那位州警發現時就是裝在塑膠袋裡嗎?」
她點點頭,「那是瓦索與庫莫。那又怎樣?」
「嗯,就算他們不知道好了,但也許他們知道有這個可能……這也不可能,因為他們以為已經結束了。」
休息站入口處有個半圓形廣場。我可以看見裡面食物攤位上的明亮霓虹燈,外面擺了六個跟門相當接近的垃圾桶。附近有很多人,有的往裡看,有的往外瞧。
「我們可以利用她的處境,趁虛而入。因為這是令她尷尬的事,她不想張揚出去。」
「諾頓中校。」
我沒有回話。
桑瑪點頭說:「我們知道,而且我們保證這整件事不會曝光,但我們必須先確認妳把手提箱給了誰。」
我沉默片刻,想到了克拉瑪的精裝書。這個時刻就像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庫斯克戰役的決戰日,而我們就像蘇聯的亞歷山大.瓦西烈夫斯基將軍。如果我們在此刻發動攻擊,就必須持續到敵人逃走,贏得這場戰爭。如果我們突然卡住不動或者停下歇息,即使只有一秒鐘,我們也會被擊潰。
「他還帶了輪胎和_圖_書扳手或鐵鍬。」
「這我倒是不知道。」
那傢伙說:「今天大概十二點多,中午過後不久。」
我沒接話。
「昨天跟他們吃飯的人裡只有我一個女的。」
我說:「還帶了優格。」
桑瑪換了個坐姿。
他說:「不太可能,我們在公路上的任務不是在路肩上找垃圾,任何東西都有可能在那裡擺了一個月。」
我們回博德堡的時候剛好趕上晚餐,我們跟一群憲兵一起在軍官俱樂部的酒吧裡吃飯。如果裡面有威拉安排的奸細,他們只會看到兩個一臉疲憊的人,什麼事也沒做,只是在吃飯。但是在每一道菜之間,桑瑪都會溜別的地方,回來時都是一副有大新聞的表情。我悠閒地喝咖啡與吃蛋糕,讓別人誤以為我好像沒有急事要處理,然後起身慢慢踱步出去。在冷冷的人行道上等著,桑瑪五分鐘後出來。我對她微笑,因為感覺好像我們兩人在偷情似的。
他有一張維吉尼亞州駕照,儘管他沒辦法住在綠谷鎮,駕照上登記的永久住址還是那裡。裡面有張標準的部隊識別證,皮夾的透明塑膠夾層後面還夾著克拉瑪夫人的照片。照片裡的她跟我在走到地板上看到的死者相較,比較年輕,照片至少是二十年前拍的。她留了一頭赭色長髮,因為照片褪色了,看起來有點像橘色。
「心戰部門那個?」
桑瑪問他:「你確定嗎?」
我指著手提箱說:「這是克拉瑪將軍的手提箱,在除夕夜當晚失蹤,昨天才被發現,我們在追查它被誰拿走了。」
桑瑪不發一語。
「來自他寢室裡的冰箱,也可能是食堂的廚房或自助餐區、營區的雜貨舖、營區外的超市、輕食店或雜貨店。」
「什麼才是不一樣的方式?」
我點點頭,「我在西點軍校待了四年,我早該看清這一切,然後換個名字,再回去從大兵開始幹起。經過三次晉升後,我就可以做到下士,甚至中士。真希望時間可以倒流。」
她說:「妳以為跟克拉瑪將軍上床的人是我?」
我搖頭說:「妳看過人們打開優格的樣子嗎?我從來沒看過有人可以戴著手套打開,因為上面有層薄膜包裝,要從旁邊的一小角拉起來。」
「你是說食物如何嗎?」
我說:「我們該把裝優格的東西找出來。」
我說:「不合理,如果有人知道克拉瑪與諾頓的事,為什麼還有人去搜維吉尼亞的房子?」
沒人講話。我看著諾頓的眼睛,她看著那只手提箱的時間不會超過幾秒鐘。她可能只是一心想,我怎麼會帶個手提箱過來,然後就把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
除此之外,皮夾裡沒有任何東西。沒有發票、沒有餐廳帳單、沒有美國運通卡的簽單收據、沒有電話號碼,也沒有任何紙條。我一點也不意外,因為將軍通常是些井然有序而且生活有組織的傢伙,他們除了需要有打仗的天分,也要有做行政工作的天分。我想克拉瑪的辦公室與辦公桌還有寢室應該都是一樣整齊——裡面擺的東西不會有一件是他不需要的。
「他什麼時候遺失這東西的?」
「葬禮在哪裡舉行?」
「找到會對我們幫助嗎?」
大家都沒說話。
諾頓說:「我不記得有這回事,什麼時候的事?」
她說:「在一個汽車旅館裡。當時他正跟我們基地裡的一位女性上床,一位開著悍馬車的女性。因此我們在找認識克拉瑪、擁有專用悍馬車,而且除夕夜曾離營的女性。還有,她昨天還跟瓦索與庫莫一起用餐。」
「我只怕他利用官位來惡整我們,如果我們都被調去阿拉斯加,那誰來辦這案子?」
「他不要我追這案子,他怕這是個醜聞。」
他的皮夾裡有三十七塊美金和六十七塊馬克,都是面額不等的小額鈔票,美國運通卡是綠色普卡,一年半後就到期了。根據卡上記載,他從一九六四年以來就是運通卡會員。我想他大概是較早拿卡的軍官之一,當時大部分軍人用的都是現金和軍人優惠券。克拉瑪的財務狀況應該挺複雜的。
我問她:「有多少人?」
她說:「沒有,他們兩人都沒拿著手提箱。」
「可是呢?」
桑瑪做了個表情,她說:「你也知道那些派對是怎麼回事,都在鎮上的酒吧裡,幾百個人擠在一起,大家都進進出出的、又吵又亂、又都喝了酒,人們一個接一個離開,她有可能溜掉了。」
我把克拉瑪的手提箱也拿下車。
我沒有回答。
「或者那議程可能真的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