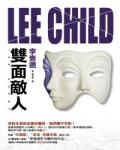14
「他在晚餐後離開,他老婆以為他開車回博德堡了,那沒什麼奇怪的。但那輛車到目前還沒在哪裡出現過,至少哥倫比亞市警局與聯邦調查局還沒發現它。」
「他正要來這裡,似乎是個愛管閒事的傢伙。」
「為什麼?」
我說:「嗯。」
他說:「他被人用槍抵住頭部,因此有殘餘的火藥與煤灰。」
我說:「大概是這樣,但我不認為這次跟錢有關,不過卡邦一定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好處,否則他為什麼要投訴我。」
「有人聽到些什麼嗎?」
「你覺得陸軍裡會有同性戀嗎?」
「現在換妳要保護我?」
「說了些什麼?」
「他們的驗屍官不同意我的判斷,死亡時間不是凌晨三、四點,而是前天晚上的凌晨一點二十三分。」
她把手移開地圖,我走回辦公桌,又坐下來,把人員清單弄成整齊的一疊。
「最好是這樣。殺了布魯貝克,就好像殺了他們的天神。」
「不會那麼久。」
「哥倫比亞市的形象?干他屁事?」
兩份筆跡是一樣的。
「裡面到處都是流鶯與藥頭,城市旅遊手冊裡不會介紹的那種地方。」
他說:「有消息了。」
我問他:「你的直覺是什麼。」
我說:「那我真的要放一百二十個心了。」
「那是個怎樣的暗巷?」
我說:「我們該跟桑切斯確認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在某處發現他的車,問他老婆看看他是不是本來就開車。」
人事參謀點點頭,「謝謝你親自來一趟,這樣比打電話好多了。」
「那三角洲特遣隊那些傢伙就不能怪你了,一點二十三分的時候你在這裡。」
「這妳也查過了?」
「他有喝酒嗎?」
「他為什麼會去那裡?」
「為什麼?」
她說:「我也許做得到,但是沿路的平均時速要維持在八十哩。當然,這要看我開的是哪種車,還有路面是否平整,也取決於路況好不好以及有沒有警察等因素。不過這當然有可能。」
「嗯。怎麼回事?」
我點頭說:「我們要回歸備受重視的傳統調查手法。」
「房裡還有其他人嗎?」
特遣隊那個人事參謀是個混球,但他畢竟是個人。當我把布魯貝克的死訊通知他時,他好像被定格了,接著臉色慘白,顯然不只覺得在行政上有所不便而已。據我所知,布魯貝克是個暴君般的傢伙,嚴肅而且與人疏遠,但他也是特遣隊的大家長,不只是每個隊員都視其如父,「布魯貝克」這四個字簡直是整個特遣隊的代名詞。國防部與國會向來把特種部隊——特別是三角洲特遣隊——視為麻煩。陸軍討厭改變,習慣新事物要花特別久的時間,尤其是要在陸軍裡面養些像流氓、獵人一樣的殺手,從一開始就是個困難重重的計畫,布魯貝克則是計畫的推動者之一,而且從沒放鬆過。他的死,在特種部隊的小圈圈裡,就等於總統去世的國殤。
「_他一定認識那傢伙,沒有其他可能。否則在深夜的暗巷裡,他怎麼可能在別人面前轉身?」
我說:「用的是全金屬彈殼子彈。」
桑瑪說:「怎麼啦?」
「什麼手法?」
「問問她的腳好了沒。」
她量出地圖上的雷利市與哥倫比亞市之間的距離是四點五吋,但是她把距離當作五吋,因為美國一號州際公路的路徑就像蛇一樣蜿蜒,她拿著尺去比對圖例裡面的比例尺。
我說:「你聯絡就好了。我還有其他事要做。」
「他有沒有接到電話或什麼的?」
我說:「未曾謀面。」
我看著他,「為什麼會有關?卡邦的死是因為訓練出意外。」
她說:「瓦索與庫莫,他們離開華府後,在史派瑞維爾偷了鐵鍬,然後闖入綠谷鎮克拉瑪夫人家中。」
三十分鐘後,我們接到電話。但不是桑切斯打來的,也不是跟布魯貝克或卡邦的事有關,而是維吉尼亞州綠谷鎮的克拉克警探來電,有關克拉瑪夫人案件的進展。
她說:「真冷酷,就像背後插|你一刀。」
「沒概念,可能是跟他認識的人有約。」
她說:「只要他有消息,就會打電話給我們。」
我又繼續看著基地人員名單,桑瑪出去後又回來,回來時帶著一張美東地圖。她把它用膠帶黏在時鐘下方的牆壁上,然後用一根紅色圖釘插在我們的所在地博德堡上。接著她把南卡的哥倫比亞市,也就是布魯貝克被發現的地方也用圖釘插https://www.hetubook•com•com著。接著她把他跟老婆一起打高爾夫的地方,北卡的雷利市也標出來。我從桌子抽屜裡拿出一把刻度很清楚的塑膠尺給她,她查看一下地圖的比例尺,然後開始計算時間與距離。
「為什麼?」
「都是些老百姓,能問出什麼?」
「跟道德有關嗎?也許他覺得自己有義務投訴你。」
桑切斯說:「一定有人在搞鬼,我查過了,因為我很好奇,而且全世界有二十幾個像我們這樣的人被調動,調職令全是蓋伯簽署的。但我覺得那筆跡不是真的。」
我站起來,說:「有需要的話,可以打電話給我。如果有我可以幫忙的地方。」
「想知道妳懂不懂拉丁文。」
接著她查看博德堡跟哥倫比亞市之間的距離,結果是一百五十哩路,比我原來猜想的還少。她說:「如果多給點時間,大概三小時車程也可以到了。」然後她看著我,「有可能是同一個傢伙。如果卡邦在九點或十點被殺,同一個傢伙可能在午夜或凌晨一點出現在哥倫比亞市,準備好殺布魯貝克。」她把小拇指擺在插著圖釘的博德堡上面,說:「卡邦。」然後她轉動手指,把食指擺在哥倫比亞市的圖針上面,「布魯貝克,順序一定是這樣的。」
「巴拿馬。」
桑瑪說:「在他們的兵器室裡,擦得一乾二淨,也上了油,裝滿子彈。他們進出時都會檢查武器。他們的機棚裡有個地方,你真該去參觀一下,那就像聖誕老公公發武器的地方。裡面停滿了加裝特殊裝甲的悍馬車,還有卡車、炸藥、榴彈發射器、闊刀式地雷還有夜視鏡。有了那些武器,任何人都可以組支軍隊,去非洲當軍閥。」
她說:「允許同性戀從軍可是一大進步。」
人事參謀說:「卡邦的事已經夠糟了,這件事更是讓人難以置信。他們倆的死有關係嗎?」
「那她沒有報警或做什麼事嗎?」
「舉個例子,像是追查錢的流向?」
「總得有人做這件事。我去過他們那裡,他們快氣瘋了。」
「這種事哪有不困難的?」
「子彈打中他的手錶。」
「十二月二十八日你在哪裡?」
「我想我可以試試。」
還不到一小時,桑瑪就回來了。進辦公室後她給了我一張紙,那是張卡邦上士在四個月前提交的武器申請書副本。他申請的是H&K的P7手槍,也許是因為之前三角洲特遣隊配記發同一家公司的衝鋒槍讓他用得很順手,所以他希望自己能申請一把P7手槍來用。他還要求把槍膛改成可以使甩派拉貝倫型的九毫米制式子彈,並要了個十三發的彈匣,還有三個備用的。這是一份非常標準的武器申請書,要求也都很合理,我很確定申請應該是被核准了。因為這裡面沒有牽涉敏感的政治問題——H&K是一家西德公司,而西德是北約會員國。同時也不會有相容性問題,因為派拉貝倫型的九毫米制式子彈是北約組織的制式子彈,美軍用的也不少,倉庫裡有一堆存貨。如果我們明天開始全面改用十三發彈匣,未來一百萬年也用不完。
我說:「這跟動機永遠是相關的。」
「救護人員猜那傷口是九毫米手槍造成的,週六晚上在那個城區執行了很多急救任務。」
人事參謀點頭說:「他們一起打。」接著他頓了一下,說:「應該說曾經一起打。」接著他不發一語,把頭轉開。
我說:「很有可能。案發時間是凌晨一點二十三分。子彈擊中他的手錶,等於案發時間是在卡邦死後的三個半小時到四個半小時之間。」
我說:「也有可能不是他們。他們剛從機場出來,沒有車子,而且他們沒有打電話給別人,電話紀錄可是妳自己查的。」
她不發一語。
桑切斯說:「他認識的人幹的,像布魯貝克這種特遣隊老鳥,要在暗巷裡偷襲他可沒那麼容易。」
我說:「還有桑瑪中尉。我們在這邊聽著。」
她說:「兩百哩路。所以如果布魯貝克在晚餐後離開雷利市,可能在午夜就到了哥倫比亞市,時間非常充裕,離他死前大概還有一小時左右的時間。」
桑切斯說:「李奇?」
「很多東西都可以用這點來解釋,像是歷史、政治,什麼都可以。」
「雷利市的郊區。」
「非常小心,而且這麼多年來你只被投訴過這麼一次。」
我說:「我和_圖_書們不是鑑識筆跡的專家。」
我點點頭。兩個簽名都是寫C .卡邦,而且他簽的C這個字很特別,簽得很快,而且拉得很長很捲。此外,兩份文件中簽的小寫字母e也很有特色:他先畫出一個小圓圈,然後往頁面右邊拉出1個長長的尾巴,比名字本身更長、更有力。中間的a rb o n幾個字母簽得又快又流暢,幾乎一氣呵成。整體來講這個筆跡展示出大膽、驕傲、容易辨識以及自信等特質,無疑是從多年簽支票、酒吧帳單、租約以及汽車文件等東西練出來的。當然,任何筆跡都可以模仿,但我覺得這筆跡的模仿難度很高。如果說要在午夜到〇八四五這段時間內就完成這個偽造簽名,我會說是不可能的。我說:「嗯,真的是他投訴我。」
「那也是正常的。」
我說:「沒有。」
「所以他看完我跟人打架後在八點離開,一點也不焦躁或擔心?」
我說:「哪一種車?」我想她應該會問。
「難道我們未來幾年都會惡運連連嗎?」
他說:「槍傷是九毫米手槍造成的。被開了兩槍,兩槍都穿過頭部,進入的傷口挺平整的,出口則慘不忍睹。」
「他老婆的說法呢?」
桑瑪走回牆上的那幅地圖前,在史派瑞維爾上面插了個圖釘。因為史派瑞維爾是個小地方,圖釘一插下去,地圖上那點就完全被塑膠的圖釘頭完全遮住了。然後她又插了根圖釘在綠谷鎮上,兩點之間大概相距四分之一吋,兩根圖釘幾乎碰在一起。兩點之間的距離代表了大約十哩路程。
「她以為他接到了電話,只是不知道是幾點。她不敢肯定,她在晚餐前去做了水療,當時他們才剛打完二十七洞。」
「屍體已經冰冷了,皮膚開始有點變綠,屍體也不再僵硬。他們說他已經死了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時。最保險的預估是在前天晚上半夜發生的,也許是凌晨三、四點左右。市政府的垃圾車在進行每週例行垃圾收集時發現他的。」
她沒有回我話。
我心裡想像著布魯貝克的樣子,我跟他未曾謀面,但卻很了解他那種傢伙。前一天他們可能跟人大談要如何裝設闊刀式地雷,裡面的滾珠軸承才能發揮最大效用,把敵人的脊椎炸斷,隔天他們卻可以穿著鱷魚牌淡色襯衫,跟妻子一起打高爾夫,而且當他們坐著小小的高爾夫球車馳騁在球道上時,說不定還手牽著手,面露微笑。我認識很多這種傢伙,我爸就是這種狠角色,不是說他有打高爾夫的習慣,他的興趣是賞鳥,世界各國的鳥他看過的可不少。
她點頭說:「從最早的紀錄開始查起。」
「他那晚吃完大餐後,八點就不見了。他從餐桌離開後就再也沒回去。」
「不在高級住宅區裡。」
她說:「應該說每個人都不是。」
「韓國,你呢?」
我說:「而且他們是癡肥的高級幕僚,就算要他們當賊,也不懂得怎麼偷五金行。」
「誰得到好處?什麼意思?因為投訴而得到好處嗎?」
「憑一只破錶來判斷?不太可靠。」
接著我算了一下還留在名單上的人,在一張紙上寫下九百七十三這個數字,也就是嫌疑犯人數。在我發呆時,電話響了,我拿起話筒,發現又是桑切斯從傑克森堡打來的。
我問他:「你跟威拉碰過面了嗎?」
我把那張上面寫了九百七十三的紙推到她面前,說:「我們的嫌犯有這麼多人。」
我點頭說:「我想我得去,這是尊重的問題,不過妳去幫我通知基地指揮官好嗎?」
我頓了一會兒。我想像不出當時的情景。兩發子彈?被人用搶抵住頭部?所以其中有顆子彈穿進頭部之後,在裡面繞圈圈,然後再鑽出來往下擊中他的手錶?
我回到辦公室,桑瑪不在。我花了一個多小時看她給我的人事資料,然後決定要省點事,於是把病理醫師劃掉,也把桑瑪劃掉,也把諾頓跟所有女人都劃掉——從驗屍結果顯示,從高度與力氣看來_,兇手都不像女人。我也把軍官俱樂部裡的服務人員都拿掉,因為負責的士官說他們都在工作,瓦索與庫莫兩位訪客讓他們忙進忙出的。我也把廚子跟酒吧的服務人員都劃掉,還有門口的憲兵衛兵。我還把目前住院而且不良於行的人劃掉,也把我自己劃掉,最後我把卡邦劃掉,因為他沒自殺。
「他為什麼要投訴我?」
她和-圖-書說:「我說錯話了。」
「哪裡的暗巷?」
「允許黑人從軍也是,還有女性。大家也都曾經對這種事嗤之以鼻、抱怨連天。說什麼會打擊士氣、破壞團結。那些過去的屁話到現在還是有人在講。對不對?可是妳不是還在這裡、工作也都沒問題嗎?」
我起身趨前,看著地圖。史派瑞維爾位於一條蜿蜒道路的彎曲處,那條路往西南走會通往綠谷鎮,繼續走會通往他處。如果往另一個方向走,除了最後會通往華府之外,沿路沒有什麼地方。所以桑瑪也插了根圖釘在華府上面,然後把小指頭的指甲擺在圖釘上,食指則擺在綠谷鎮。
他聽起來很得意,接著開始詳細說明自己做了哪些事,聽起來他用的方法既合理又聰明。他用地圖找出綠谷鎮周圍三百哩範圍內有哪些路可以通往鎮上,然後用電話簿列出這些路上有哪些五金行。他要求手下逐一打電話清查,從中心點開始往外著手。他發現鐵鍬的銷售量在冬天很少,主要的裝修工程都是從春天才開始,有誰想趁天冷時把廚房牆壁打個洞,讓冷風灌進來?三小時後他發現所有的店都沒有賣出鐵鍬,聖誕節後人們買的大多是電鑽與電動的螺絲起子。有些人則是為了幫爐子添柴火而買電鋸,對西部生活充滿幻想的人則是買斧頭。像鐵鍬這種單調乏味的東西是乏人問津的。
我說:「威拉不喜歡醜聞,形象問題會讓他很緊張。」
「你該打電話給她。」
「一瓶啤酒。」
「桑切斯覺得他們對他有所隱瞞,有些事他們知道,但我們不知道。」
「是的,那時候我跟諾頓在一起。」
「你可以自己打電話給她嗎?她一定寧願跟你聊,而不是跟警察。」
我搖頭說:「如果是這樣,我們打架時他會插手。」
「你要去告訴他們這個消息嗎?」
「有人提到他的心情怎麼樣嗎?」
「不是只有天主教徒懂拉丁文。上學的人也懂。」
我說:「據說沒有。他的敵人都是官位比他大的傢伙。」
「他的手正好擺在頭上嗎?」
桑切斯說:「沒有,他待的是特種部隊,結婚那麼多年來,他總是突然消失,一點預警也沒有。有時是飯吃一半、有時是半夜,他有可能消失幾天或幾週,事後也沒辦法告知原因以及去了哪裡,她已經習以為常。」
「問題是,這是他第一次投訴別人。他一定看過更惡劣的事,我只打斷別人的腳跟鼻梁,根本沒什麼大不了的。桑瑪,我們身在陸軍,我想他不會覺得自己參加的是園藝俱樂部。」
「一件事也沒有,有史以來最平靜的一週。」
他陷入沉默。
「你覺得卡邦與布魯貝克兩人的死有關嗎?」
「他們不會相信妳的。」
「那還用說。」
我搖頭說:「拉丁文是我媽教的,她很關心我們的教育,教了我跟我哥喬伊很多事。」
「布魯貝克去飯店做什麼?」
「他在博德堡有敵人嗎?」
「那真奇怪。」
「他們幹嘛調動我們?」
「你是天主教徒嗎?」
「我們可以假設是這樣。」
「人數可不少。」
「哥倫比亞市警局又找上我,就這麼回事。他們一點一點把事情告訴我,而且他們好像在玩弄我似的,卯起來幸災樂禍。」
「三角洲特遣隊員不會透露心情,如果跟一般人一樣,對他們來講就太危險了。」
「你要我在這裡幫你聯絡,還是要他們直接打電話給你?嚴格來講,布魯貝克的事應該歸你管。」
「因為布魯貝克的口袋裡有海洛因、三包少量白粉,還有一大袋現金。他們說那是樁毒品買賣,結果被黑吃黑。」
她說:「嗯。」她走出去用外面中士桌上的電話跟桑切斯聯絡,我則繼續看那份名單。她在十分鐘後才回來。
「有機會就去。」
我點點頭。是因為布魯貝克的事。
「他常去那裡嗎?」
我回想元旦那天在脫衣舞酒吧裡的卡邦。我走進去後看到我認為都是士官的四個人,其中三個被人群擠開,一個則被推向我這邊,所以他們的行進方向都是隨機的。我不知道他們之中誰會走向我,他們也不知道我會出現。我跟其中任何一人都沒見過面,那次與卡邦相遇可說是巧合中的巧合。我打的那一架根本不算什麼,他不知道看過幾千次了,搞不好自己也打過幾百次,可是卻因為那一架而舉發我。如果有哪個軍人說自己沒在酒吧跟m.hetubook.com.com老百姓打過架,那一定是鬼扯。
我說:「妳不在時桑切斯又打電話過來。布魯貝克上校是被人朝後腦勺開槍擊斃,從後面抵住他的頭共開了兩槍。」
「我們早就有了,而且未來還會有更多同性戀從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盟軍有一千四百萬個軍人,用合理的比率來算,裡面至少有一百萬個同性戀。而且我還記得,歷史上記載著我們大獲全勝。」
我說:「你只能做好心理準備,麻煩上門了。」
「他老婆也打高爾夫嗎?」
「妳想知道妳跟怎樣的一個人一起辦案嗎?」
「你覺得是什麼時候?」
我說:「還有什麼事嗎?」
我說:「他們當然生氣。」我想像他們駐紮的那老舊牢房,一開始是設計用來關人,接著被用來擋住外人,現在卻像個壓力鍋一樣,把那群人聚在一起,凝聚力像鍋內的溫度一樣,愈來愈高。我不知道布魯貝克的辦公室在哪裡,但我想像著辦公室裡寂靜而空無一人的樣子。我想像著卡邦的寢室,空盪盪的被晾在那裡。
「妳跟別人聊過了?」
我說:「也許等我有空吧。」
我說:「布魯貝克是開車南下雷利市的嗎?」
「他當了十六年的兵,只投訴過這件事。」
「妳很小心嗎?」
傑克森堡的憲兵執行官是個叫桑切斯的傢伙,我跟他很熟,而且很喜歡他的為人,既聰明又正直。我把電話用擴音器放出來讓桑瑪也能聽到,我們稍微聊了一下有關司法管轄權的問題,但這話題我們不怎麼喜歡。司法管轄權總是有灰色地帶,而且我們知道軍方從一開始就處於劣勢。布魯貝克正在度假,他身穿便服,而且在都市的暗巷中被發現,所以哥倫比亞市警局宣稱這是他們的案子,我們沒有插手餘地。而且哥倫比亞市警局通知了聯邦調查局,因為布魯貝克最後現身的地方是北卡的高爾夫球場飯店,這可能是個跨州的案子,而跨州謀殺案正是聯邦調查局管轄的。而且,嚴格說來,陸軍軍官等同聯邦政府職員,如果謀殺的是聯邦政府職員,而且他們又奇蹟似的抓到兇手,就可以另外在他身上加條罪名。到底這案子是歸各州或者聯邦法院主管?不管是我或桑切斯或桑瑪,都不關心這個問題,但我們心知肚明的是,如果聯邦調查局插手,那我們就管不動這案子。我們都同意,到頭來我們最多只能看到一些相關文件,但都是對方出於客套而給的一般資訊。我把擴音器關掉,把話筒拿起來跟桑切斯單獨對話。
「他試著要他們說出來,但很困難。」
「但可能性不高。」
我說:「切記,不是每個人都跟妳一樣像是個賽車手。」
「雪佛蘭羚羊SS型。」
掛斷電話後,我又繼續看著桑瑪列出的清單。九百七十三人,其中有九百七十二個人是無辜的,一人有罪。是誰呢?
「飯店在哪裡?」
「他比一般特遣部隊成員厲害得多,是個真正的專家。而且他會冷靜思考,只要有機可乘,不管自己有任何優點或對方有任何弱點,只要他發現了,一定會善加利用。」
她又說了一次:「我不知道。」
「不是專家也看得出來,李奇。兩個簽名一樣,相信我。」
我說:「真詭異,這是我的感覺。之前我跟這傢伙沒見過面,我很確定。而且他是個三角洲特遣隊員,不是和平主義者,為什麼我會惹到他?我又不是踹斷他的腿。」
「那些娘娘腔才不會在半夜的暗巷裡暗算別人。」
「那麼我們就需要一個新計畫,克拉克警探現在不會再找鐵鍬了,他要的那把已經被他找到了。」
「但他為什麼被人在後面開槍?」
桑切斯說:「對了,這種事有可能發生在他身上嗎?你認識他嗎?」
我說:「我很確定那是偽造的,布魯貝克死前,你那裡還有出什麼狀況嗎?」
「是陸軍的形象。他不希望布魯貝克這種菁英部隊的上校跟流鶯、藥頭扯上關係。他覺得陸軍會因為蘇聯瓦解而導致人事地震,現在是大搞公共關係的時刻,他以為自己可以看見未來的願景。」
「不,這根據非常有力。他們還做了些其他測驗,如果可以用腐屍上的蟲子來測試,也會有幫助,但這個季節沒什麼蟲子活動。但從胃部殘餘的食物看來,可以看出他晚上大吃一頓後,東西又在胃裡停留了五、六個小時。」
「我只知道這個案子的未來與我和_圖_書無關。難道他有什麼門路可以買通哥倫比亞市警局或聯邦調查局?如果沒有,他來也沒用。」
我說:「但妳這也是猜測。」
我說:「那又怎樣?」,桑瑪說:「你看簽名的筆跡。」她從內側口袋裡拿出卡邦投訴我那份文件的影本,拿給我看。我在桌上把它攤開,放在那份武器申請書旁邊,比對筆跡。
「根據常識判斷,一定有關係,但是我還看不出來如何產生關聯,也看不出為何有關係。我的意思是,他們都是三角洲特遣隊的人,但是卡邦死在這裡,布魯貝克在那裡喪命。而且布魯貝克是個動見觀瞻的大人物,卡邦卻是個行事低調的小角色。也許他覺得這樣才能掩飾自己的身分。」
她說:「他開自己的車。他老婆告訴桑切斯,他們在飯店有兩部車,兩人各一台。他們一直是這樣,因為他總是要趕往某處,她擔心自己沒車可以回家。」
我不發一語。
「因為他喜歡打高爾夫,很早以前他就在布瑞格堡基地附近有間房子,但他不喜歡那裡的高爾夫球場。」
她說:「我不知道。」
「武器呢?」
我說:「我的直覺。」
掛掉電話後,我靜靜坐了一會兒,我估計南卡的哥倫比亞市大概距離博德堡兩百哩。從高速公路往西南邊走,跨越州界不久後,找到二十號州際公路往西再開一會兒就到了,這趟路大概是兩百哩。前天晚上我們發現了卡邦的屍體,我在凌晨兩點離開諾頓中校的辦公室,所以一直到那個時刻她都可以為我提供不在場證明。接著我為了驗屍,七點出現在太平間,病理醫師可以幫我作證。所以我有兩個時間並不相連的不在場證明,但在兩點到七點間還是可能有個空窗期,而布魯貝克的死亡時間就在這段時間裡。只有五小時的時間,我可以在兩地之間來回各開兩百哩路嗎?
「特遣部隊那些傢伙已經把卡邦的死算在我頭上了,現在布魯貝克這筆帳會不會又怪我?五小時內要開四百哩路,妳覺得可能嗎?」
所以他直接跳過這個步驟,打開全國犯罪資料庫查詢。本來他想查詢有關門被破壞與鐵鍬的報案記錄,但他想自己可以設定一個區域,結果在那範圍內找不到任何紀錄。但是就在他的國家犯罪資訊中心的資料庫中,他查到維吉尼亞州史派瑞維爾地區一家小五金行發生了一起竊盜案。那家五金行是間位於死巷裡的偏僻店家,根據老闆的說法,店頭的窗戶在元旦凌晨被人踢破,因為是假日,收銀機裡面沒有留錢。就他所知,唯一遺失的東西是一把鐵鍬。
他不發一語。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讀的是西點軍校,不是憲兵學校。」
桑瑪說:「看看這個。」
桑瑪說:「不是。為什麼這樣問?」
「也許他覺得這是個人恩怨,那胖子是他的朋友。」
「門關著嗎?」
「不,我只是想讓特遣隊那些傢伙知道你沒跟別人結怨,不管是跟別人或卡邦。」
「我會把話放出去。」
桑切斯說:「沒有,哥倫比亞市警局都盤問過了,沒有結果。」
我把文件擺在桌上,桑瑪把它轉向自己,儘管之前已經看過很多次,她又從頭看了一遍。
「這也太準確了吧?」
我說:「我一直覺得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為什麼了。」
「我們必須專注在卡邦的案件上。」
「好車。」
「太棒了。」
我說:「卡邦剛剛領到的P7手槍在哪裡?我在他的寢室裡沒看到。」
「各單位的人。我在這裡打電話,那些人離這裡有遠有近。」
「所以他也認識跟他見面的那傢伙。」
我說:「好,那我問妳,cui bono?」
我的電話又響了,又是我聽過那個溫暖的南方女人口音:傑克森堡發送了一〇三三與一〇一六兩個訊息代碼。我知道後打開擴音器,整個人靠在椅背上等著。整個房間裡響著嗡嗡嗡的電訊聲,然後又傳來一聲喀。
他說:「哥倫比亞市警局剛打電話給我,他們跟我分享資訊。」
桑瑪不發一語。
「李奇,他是被人從後開槍的。從後腦勺打了兩槍,砰!砰!謝謝,晚安。第二槍一定打穿了他的頭,然後擊中手錶。因為彈道是往下的,所以開槍的人是個高個兒。」
「你在查傑克森堡的人嗎?」
她說:「他在酒吧裡一直待到八點,這點我也查過了。他自己離開的,沒有人看到他再回去。」
我問她:「妳是天主教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