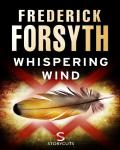第一章
他策馬向位於營地前頭的卡斯特將軍的帳篷走去。其他士兵也跟著跨上了馬。
「有沒有任何規定說我們不能先與她玩一玩,上尉?」布蘭多克中士問。其他戰士發出了一陣贊同的笑聲。阿克頓上尉騎上了馬。
「我們別去打擾他們。他們不是我們要尋找的人。」
偵察兵數了數,共有十四具屍體,橫七豎八地躺在他們倒下的地方。當其中一名士兵遞給他一件戰利品時,他搖搖頭,拖著腳步經過那些帳篷到溪岸邊讓他的戰馬去飲水。
「那麼,中士,」阿克頓說,「這就是你的俘虜。讓我們問問她知道些什麼。」
金礦終於在南達科他州神聖的黑山裡被發現了,淘金者蜂擁而至。但黑山已經永久性地給予了蘇人部族。對此,平原印第安人認為被出賣了,他們怒火萬丈,以襲擊淘金者和列車作為他們的報復。
「她說她沒看見過蘇人。她的家來自於南方,來自於湯格河。有更多的夏廷人與他們在一起,但一星期前他們分手了。高糜喜歡單獨狩獵。」
布蘭多克中士從馬匹上朝克雷格俯身一瞥。
那位夏廷姑娘靜靜地躺在皮繃子上,凝視著正在黑下來的天空。她已經準備死去。克雷格在溪流裡灌了一壺水,拿來給她喝。她用她那雙黑色的大眼睛凝視著他。
克雷格走到最近的那輛炊事車,取了一盤豬肉、硬麵包和扁豆,找到一隻彈藥箱,坐下後吃了起來。他想起了他的母親,十五年之前在昏暗的燈光下把《聖經》讀給他聽。他想起了他的父親,耐心地在流向普賴爾山脈的溪流上淘金。他還想起了老唐納森,老人只有一次憤怒地解下皮帶要抽他,因為他曾經粗暴地對待一頭被捕獲的動物。
唐納森是一位年長的山裡人,他專門設置陷阱捉狼、河狸、熊和狐狸,每年把獵物帶到附近的集貿市場去出售。出於對這個孤兒的同情,老頭子收留了他,把他作為自己的兒子撫養。
他從地上扶起姑娘,只輕輕一抱就把她抱上了雜色矮種馬的背上,又遞給她韁繩,然後他指向那塊開闊的牧草地。
老唐納森在世時常說:「孩子,當我走了時,帶上你所需要的物品。這些東西全歸你了。」於是他帶走了那把鋒利的獵刀,連同以夏廷人方式裝飾的刀鞘、那支一八五二年製造的夏普斯來福槍、兩匹馬、鞍具、毯子以及旅途上要吃的一些牛肉乾和硬麵包。他不需要更多的東西。然後他走出山區到了平原,一路騎馬北上去了埃利斯堡。
是在羅斯伯德溪谷中的第四天強行軍時,前方的一支巡邏隊回來報告了在夏廷人小村莊的一次勝利以及一名俘虜的消息。
「坦率地說,中士,我才不管你想幹什麼呢。」
「那不行,上尉,」他說,「她已經把她所知道的告訴了我。如果蘇人不在我們沿路過來的北邊,而且也不在南邊和西邊,那他們一定是在東邊。你可以這麼告訴將軍。」
下午剛過四點鐘,卡斯特將軍命令停下來紮營。太陽開始落向遠處視線之外的洛磯山脈。軍官們的帳篷很快被搭建起來了。卡斯特和他的知己部下總是使用那座救護帳篷,那是最大的也是最寬敞的帳篷。折疊式營地椅子和桌子支起來了,戰馬到溪邊去飲水了,食物準備妥了,篝火點起來了。
布蘭多克中士沒有詢問偵察兵是怎麼知道的,他只是接受了偵察兵的解釋。他張開嘴打了一個哈欠,噴出一股酒氣,露出了一口黃牙。偵察兵滑下堤岸站了起來。
但白人的西行並沒有停止。
阿克頓上尉凝視著那紮上了繃帶的大腿,俯身向前狠狠地掐了一把。姑娘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但沒有叫出聲來。
但布蘭多克已經隨第七騎兵團在平原上當了三年兵,其間沒有參加過什麼行動。
「五座印第安人棚屋。夏廷的。營地裡只有婦女和兒童。男人們外出去溪流對面打獵了。」
蘇人及其同盟並沒有接受這個警告,他們簡單地不予理睬。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甚至根本
和圖書沒有聽說過這個最後通牒。他們繼續打獵,當冬天過去春天來臨時,他們追尋著他們的傳統獵物:大量的野牛、性情溫和的鹿和羚羊。早春時候,印第安人事務局把這事交給了軍方。其任務是:找到他們、趕攏他們並把他們押送回達科他保留地。沒人知道在十八日那天,克魯克遭遇到由蘇人和夏廷人混合組成的大批人馬並被打得落花流水。他已經折回南方去了。他沒有派騎兵去北方找到和通知他的兄弟部隊,所以,吉本和特里都不知道將沒有來自南方的接防部隊。他們繼續行進。
在湯格河與羅斯伯德溪之間,克雷格有兩個星期的時間來觀察大名赫赫的七團及其偶像般的指揮官,而且他越看心情越沉重。他希望他們不會遇上一大群準備廝殺的蘇人和夏廷人,但又擔心他們也許會遇上。
他從槍套裡拔出他的柯爾特手槍並進行瞄準。蘆葦裡的那個姑娘轉過臉來凝視著他們,那雙空洞的眼睛裡充滿了恐懼。偵察兵伸出手緊緊抓住中士的手腕逼著持槍的那隻手舉向了空中。布蘭多克那張粗糙的、被威士忌薰紅了的臉面因為憤怒而變黑了。
「也許可以給予一個小小的鼓勵。」阿克頓說。布蘭多克中士微笑了。克雷格伸出手去,抓住上尉的手腕,把它推開了。
「喝吧。」他用夏廷語說。她一動也沒動。他把一股清涼的溪水澆到她的嘴上。
從達科他北部的林肯堡開始,阿爾弗雷德.特里將軍將沿著黃石河西行,去那塊狩獵地的北方邊界。從蒙大拿的莎堡,約翰.吉本將軍將南下去埃利斯堡,繼之轉向東方沿黃石河挺進直至與從另一個方向趕過來的特里將軍的部隊會合。
「你看見什麼了?」中士用一種粗啞的耳語問他。
他聽到中士在他身後爬上了溪岸,於是朝身後做手勢讓那人趴下來。然後他身邊出現了那隻繡著三道人字形標誌的藍色制服袖子。
六月初,吉本與特里在湯格河匯入黃石河的地方會師了。他們連一個印第安人的蹤影也沒見到。他們所知道的是至少平原印第安人在他們南方的某處。吉本與特里商定,特里將繼續西行,吉本在與他會合後,也返回西行。於是他們向西進發了。
卡斯特已經把他的團部樂隊留給了特里,所以當他要吹衝鋒號時,號角聲並不是他所鍾愛的《加里歐文》。但在他們的南下溯源路上,掛在流動炊事車兩邊的水壺、鐵鍋和勺子互相碰撞發出了叮叮噹噹的聲音,克雷格不知道卡斯特希望驚奇地聽到的是哪一支印第安人的樂隊。在由三千隻馬蹄形成的噪音和揚起的塵土中,他知道人們可在幾英哩之外見到和聽到他們。
附屬於七團的所有邊防偵察兵,六個白人、一小組克勞人和三十個左右的阿里克拉人,因共同的興趣而形成了一個小組。他們全都了解邊疆以及邊疆的生活方式。
「去吧。」他說。她盯住他看了兩秒鐘時間。他在矮種馬屁股上拍了一下。幾秒鐘之後,牠就走了,那是一匹堅定的、頑強的、未釘上蹄鐵的矮種馬,能在遼闊的牧地上找到自己的道路,直至牠聞到自己親屬的氣味。幾個阿里克拉的偵察兵在五十碼開外的地方好奇地觀察著。
差幾分鐘八點,當夜幕完全籠罩到營地上時,他站起身,把盤子和匙子放回到車上,走回到那張皮繃子。他沒對姑娘說話。他只是把兩根木杆子從那匹雜色矮種馬上卸下,放在了地上。
它們擠在山脊與溪岸之間的狹長地帶裡。這是一個營地,至多五間印第安式的棚屋,一個繁衍擴展的家庭。那種印第安人的圓錐形帳篷表明是北夏廷人。這位偵察兵對印第安人的帳篷很了解。蘇人的圓錐形帳篷又高又窄;夏廷人把他們的圓錐形帳篷的底部建得很寬大,更為矮胖,顯示狩獵戰利品的圖畫和-圖-書裝飾在帳篷的側面,這也是夏廷人的風格。
這時候是上午九點鐘,已經熱得使人喘不過氣來了。他們已經騎行了三個小時。
在母親的熏陶下,本只知道一本書——《聖經》。她曾經大段大段地讀給他聽。
偵察兵趕攏一匹正在到處亂跑的矮種馬。現在只剩下兩匹矮種馬了;五匹已經竄到了遠處。那動物在被繫上韁繩時膽怯地後退著。牠已經聞到了白人的氣息,這種氣味可使一匹雜色矮種馬發狂。反過來也同樣:美國騎兵的戰馬如果聞出平原印第安人的氣味,也會變得難以駕馭。
他獨自單騎走在前頭,領先於十名邊防騎兵巡邏隊二十碼距離。他們在羅斯伯德溪谷的西岸行進著。
吉本還向卡斯特提供由布里斯賓少校領導的三個騎兵連,但被謝絕了。特里向他提供加特林機槍,但他也回絕了這些裝備。當他們溯羅斯伯德溪而上時,七團有十二個連隊、六名白人偵察兵、三十幾名印第安人偵察兵、一個車輛縱列和三位平民,總共六百七十五人。這個總數包括了馬醫、釘馬蹄鐵的鐵匠和趕騾人。
但華盛頓也讓給他們一塊被稱為未割讓的領土。那是蘇人傳統的狩獵地,仍充滿著野牛和鹿。該土地的東部界線是豎向垂直的——北達科他州的西部邊界。其西部界線是一條想像中的南北向直線,在往西一百四十五英哩處,是印第安人所無法想像出來的界線。未割讓土地的北部邊境是流經蒙大拿州進入南北達科他州的黃石河;南部邊境是懷俄明州境內的北普拉特河。在這片土地上,起初印第安人被允許可以打獵。
「那麼蘇人的主要聚居地呢?」
「你發現了什麼,小夥子?嗯,是不是又一條害蟲?而且還活著?」
從南方懷俄明州內的菲特曼堡,喬治.克魯克將軍將向北進軍,跨過瘋女溪源頭,越過湯格河,朝比格霍恩峽谷行進,直至遇上另兩支主力部隊。他們推測,在他們之間的某個地方,他們中的一支部隊將找到蘇人的主體。他們都在三月份出發了。
傳聞一直在說,卡斯特將軍統帥下的部隊在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小比格霍恩的那次大屠殺中,沒有一個戰士存活下來。這話不對,其實有一位倖存者。他是一名邊防偵察兵,年齡二十四歲,名叫本.克雷格。
晚上圍在營火旁,在就寢之前,他們習慣於互相交談。他們談論那些軍官,從卡斯特將軍談起,還有連隊的指揮官。克雷格已經驚奇地發現將軍在其部下中是如何地不受歡迎。他的弟弟湯姆.卡斯特,C連連長,卻深受戰士們喜愛,但軍官中最令人厭惡的是阿克頓上尉。克雷格也有這種同感。阿克頓是一位職業軍人,十年前南北戰爭時參軍,在卡斯特的庇護下在七團裡得到了晉升,他出生於東部一個富裕的家庭。他長得瘦瘦的,有一張刀削臉和一張殘忍的嘴。
「好主意,小夥子。我們把她作為一件禮物帶回去獻給將軍。」
「是在將軍帳篷裡吃飯的時候了,」他說,「我要走了。」他顯然已經失去了對那個俘虜的興致。「中士,到天空完全黑下來以後把她帶到牧草地上幹掉。」
「別打死她。她也許知道一些事情。」偵察兵說。這是唯一的辦法。布蘭多克頓了頓,想了一想後點點頭。
一八七六年四月,他以一名獵人、設陷阱捕獸人和馴馬人在那裡勞作,這時候吉布將軍的部隊騎馬經過了。將軍需要了解黃石河南部土地上情況的偵察兵。提供的待遇很不錯,所以本.克雷格加入了。
他的父親約翰.諾克斯.克雷格是一名蘇格蘭移民。在被一個貪財的地主從他的小農場趕出之後,這位硬漢於一八四二年移民到了美國。在東部的某個地方,他遇上並娶了像他自己那樣有蘇格蘭長老會教徒血統的一個姑娘,在發現城市裡發展機會不多時,西行去了邊疆。到一八五〇年時,他抵達蒙大拿南方,並決定在普賴爾山脈山腳附近的荒野裡嘗hetubook•com.com試淘金發財。
一八七六年那次夏季戰鬥前兩年,這位老人被他所居住著的同一片荒野召喚去了。
這場屠殺只花了五分鐘時間。十名騎兵從山脊上衝殺下去。偵察兵爬上山脊,從上面厭惡地觀察著。
至於他們具體在什麼地方,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找出來。必須派軍隊去蒙大拿把他們找到。所以制訂了一份計劃,要派遣由步兵和騎兵混編的三支大部隊。
在林肯堡的一個漫長而無聊的冬天使他與一個洗衣女工和兼職妓|女生下了一個私生子,但他來到平原上是真正想殺印第安人的,不想卻被勸止。
阿克頓上尉把抓住他手腕的那隻手推開,似乎他的手腕會受到感染。他伸直身體,取出一個銀懷錶看了一眼。
是那位邊防偵察兵靈敏的鼻子首先聞到了它:由草地上的微風吹來的炊煙的那股淡淡的香味。
嘴唇分開了。她嚥了下去。他把水壺留在了她的身邊。
找到他之後,騎兵回去報告了。二十分鐘以後,阿克頓上尉騎馬過來了。陪同他一起來的有布蘭多克中士、一名下士和兩名騎兵。他們跳下馬圍住了那張皮繃子。
這些代理人從華盛頓領到牲畜、玉米、麵粉、毯子和錢,然後分發給他們所管理著的印第安人。許多人大肆騙取印第安人錢財,導致婦女和兒童挨餓,並由此使印第安人做出返回狩獵平原的決定。
「上尉,姑娘說她的名字叫輕風。她是北夏廷人。她的家庭是『高糜』的。今天上午被中士消滅的是她家的棚屋村。村裡有十個男人,包括她的父親,當時他們都去羅斯伯德東岸獵殺鹿和羚羊了。」
這是關於他的故事。
在正在化作一片焦土的圓錐形帳篷旁邊的營地上,有幾個皮繃子。皮繃子由兩根細長而富有彈性的松木杆組成,交叉紮緊後安放在一匹矮種馬背上,叉開的兩頭分得很開,中間放上一張展開的牛皮用以載重。這是一種很舒適的旅行工具,對於一名傷員來說比白人使用的牛車更為安穩,因為牛車遇到路面不平時顛簸得很厲害。
那天的剩餘時間裡,那個夏廷姑娘被留在那張皮繃子上。偵察兵把那匹矮種馬牽到後面,把它的韁繩繫在了一輛行李車上。拖著皮繃子的這匹矮種馬跟在行李車後面快步行走著。由於現在不需要去前方偵察,這位偵察兵留在了附近。剛加入騎兵七團不久,他就覺得不喜歡他在做的事情。他既不喜歡自己的連長也不喜歡連裡的這個中士,而且他認為大名赫赫的卡斯特將軍其實是一個殺人魔王。但這個想法他沒有說出來,他把它留在了心底裡。他的名字是本.克雷格。
完成之後他看著她。她也回視著他。一頭瀑布般的黑髮鬆散地披在她的雙肩上;一雙黑色的大眼睛,籠罩著痛苦和恐懼。在白人的眼裡,並不是所有的印第安女人都很漂亮,但在所有部落人中,夏廷人最為俊美。蘆葦叢中的那個姑娘大概有十六歲,具有驚人的美貌。偵察兵今年二十四歲,是讀《聖經》長大的,從來不曾知道《舊約全書》意義中的一個女人。他感覺到他的心在狂跳著,不得不去看別處。他把她搭上自己的肩膀,走回到被摧毀的營地去了。
他把手槍放進槍套,回去檢查自己的人馬了。偵察兵跳下馬,走進蘆葦叢中去照看那個姑娘。幸好她的傷口很乾淨。當她在逃跑時那顆子彈在短距離內|射穿了她的大腿。槍洞有兩個,一個進口,一個出口,都是又小又圓。偵察兵用他的手帕和清澈的溪水擦洗了傷口並進行了包紮以止住血流。
卡斯特將軍喜歡盡早拔營出發。但偵察兵已經能夠聞到從他旁邊那個人身上散發出來的威士忌的味道。這是一種劣質的邊防威士忌,味道很難聞,比用野山梅、櫻桃和長在羅斯伯德溪岸的漫山遍野的野玫瑰製成的香水的味道還濃。
是與唐納森在一起時,他才遇到了那個夏廷人,那人也是布設陷阱的捕獸者,是唐納森與之在農貿市場上做交易的。和-圖-書是他們教會了他說夏廷人的語言。
當暮色加深時,B連的一名騎兵到營地來找他。
喬治.阿姆斯壯.卡斯特將軍自豪地騎行在他的騎兵大部隊的前邊。他為了急於趕路,不想為了一個俘虜而讓整支部隊停下來。他對布蘭多克中士的到來點點頭,並命令他去自己的連長那裡報到。如那個印第安女人有任何情報,可以留待他們在晚上紮營以後再處理。
那偵察兵沒有轉身即提起他的右手把韁繩勒住了。在他的身後,那位中士和九名騎兵也跟著勒住了馬韁。偵察兵跳下馬,讓牠安詳地去吃草,自己小步跑向騎兵們與溪流之間的一道低低的溪岸。在那裡,他臥倒在地上並爬上岸頂去窺視前方,他的身體仍隱藏在漫長的野草叢中。
卡斯特已經至少有了兩個會講蘇語的偵察兵。一個是黑人戰士,是七團裡唯一的黑人,名叫艾賽亞.多爾曼,曾和蘇人一起生活過。另一個是偵察隊長米奇.波耶爾,是一個法國人和蘇人的混血兒。但雖然人們普遍認為夏廷人是與蘇人血緣最近的和傳統的同盟,但語言卻相差很大。克雷格舉手報名。吉本將軍向他詳細作了交待後讓他加入了七團。
「皮繃子,」他說,「不然她會死去。」
克雷格彎腰俯身於野牛皮上的那個姑娘。他操起了夏廷語,輔之以表示數字的手勢,因為平原印第安人的方言詞彙量很有限,需借助於手勢才能表達清楚意思。
對於這種暴力,白人們做出了狂怒的反應;暗底下的野蠻暴行傳說,常常是虛構的和極度誇大的,更使事情火上加油,白人社區向華盛頓提起了申訴。政府做出的反應是隨意取消拉拉米協定並把平原印第安人限制在一系列貧瘠的保留地上。這只是他們曾經得到過的莊嚴的承諾的一個零頭。這些保留地在南、北達科他州的領土上。
「把她放到一匹矮種馬上。」中士喊道。他又從他的馱袋裡摸出酒瓶開始痛飲了。偵察兵搖搖頭。
她躺在那裡,半隱藏在蘆葦叢中,鮮血汩汩地順著她的一條光腿流下來,剛才在她奔跑時一顆步槍子彈穿透了她的大腿。假如他的動作稍稍再快一點,他肯定會轉過頭去並回到正在燃燒著的帳篷旁邊去。但正在注視著他的布蘭多克看到了他的視線方向,於是策馬跑過來了。
「要讓她活著,小夥子。我們會回來的。」
他是那時候的第一批淘金者之一。在森林的小河旁一座小木棚裡,生活是艱難的,尤其是寒冷的冬天。只有夏天才會顯露田園風光,森林裡到處是野味獵物,溪流裡漫游著鮭魚,草地上開滿了各種野花。一八五二年珍妮生下了他們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兒子。兩年後,一個小女兒在嬰幼期不幸夭折。
偵察兵朝那動物的鼻孔輕輕地吹了一口氣,直至牠安定下來接受了他。十分鐘之後,他已經把那個皮繃子就位了,那位負傷的姑娘躺在野牛皮上,身上裹著一條毯子。巡邏隊整裝出發從原路折返去尋找卡斯特將軍及其領導下的第七騎兵團主力部隊了。這是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軍隊有兩件事情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走出了保留地以及他們在什麼地方。對於第一件事,軍隊受騙了。那些保留地是由印第安人的代理人所管理,他們都是白人,而且許多人是地痞惡棍。
聽到馬蹄聲時,那些正在料理營火和爐灶的印第安女人們試圖召集孩子們跑向河裡,但她們太晚了。在她們抵達水邊之前,騎兵們衝進了她們之中,然後折回去殺向棚屋,射倒任何移動的目標。當事情結束,所有的老人、婦女和兒童都死去後,他們跳下馬去襲擊圓錐形帳篷,尋找能引起他們興趣的戰利品以便帶回家去。當仍然活著的孩子被發現後,棚屋裡又響起了幾聲槍聲。
這支大部隊整天都在騎馬南下,沿著羅斯伯德溪流,但沒有看見更多的印第安人。然而有好幾次,當微風從牧地吹向西方時,騎兵部隊的戰馬似乎受到了驚嚇,甚至驚恐,克雷
hetubook.com.com格確信牠們已經聞到了風中的某種氣味。正在燃燒的圓錐形帳篷不可能長時間不被注意到。牧草地上的沖天煙柱在幾英哩之外就能看見。「把你的名字告訴我,姑娘。不會傷害你的。」
他參加了抵達湯格河河口的行軍和與特里將軍的會師,他還與聯合部隊一起折回騎行,直至他們再次到達羅斯伯德河口。在這裡,卡斯特率領下的第七騎兵團接受了南下去羅斯伯德河源頭的詳細命令。部隊裡開始尋找會說夏廷語的戰士。
其中一名騎兵剛入伍不久,他的騎術是如此之差,以致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其他人實施了屠殺。所有的馬刀都留在了林肯堡,於是他們使用了他們所佩帶的柯爾特左輪槍或者新配發的斯普林菲爾德七三型步槍。
「你會說那種野蠻人的土話?」他接著問克雷格。偵察兵點點頭。「我想知道她是誰、她屬於哪一個族以及可在什麼地方找到蘇人的主體。現在就想知道。」
那年夏天在蒙大拿州南方平原上發生的戰役,其火種可追溯到幾年之前。
一八七五年,蘇人開始走出達科他的保留地,向那塊未割讓的狩獵土地行進。那年下半年,印第安人事務局向他們發出最後通牒:限一月一日之前返回保留地。
這些代理人之所以說謊還有一個原因。如果他們宣稱那些應該留在保留地上的人百分之百地確實留在那裡,他們能夠領到百分之百的津貼。如果那些留守的印第安人的數量下降,那麼分配下來的錢物也會隨之下降,這樣代理人的個人好處也會減少。在一八七六年春天,這些代理人告訴軍隊只有一小撮勇敢的印第安人消失了,越過邊界去了未割讓的土地上打獵。
偵察兵拖著腳步從山脊穿過四百碼距離走到了營地來察看屠殺的情況。當騎兵們點火焚燒帳篷時,那裡似乎沒有什麼東西也沒有什麼活人。其中一名騎兵,其實只是一個大男孩而且剛當兵不久,取出他攜帶著的當早飯的硬麵包和扁豆,靠在馬鞍邊上,以免自己因噁心而嘔吐。布蘭多克中士得意洋洋。他已經獲得了勝利。他已經找到了一頂插著羽毛的頭盔,把它固定到了水壺邊的馬鞍上。
「我叫輕柔說話的風。」她說。騎兵戰士們站在周圍傾聽著。他們一個字也聽不懂,但能明白她的搖頭。最後,克雷格直起腰來。
雖然他讀書寫字並不熟練,但他的腦海裡已經記住了他母親稱之為「好書」中的一篇篇短文。他的父親已經教過他如何淘金,但是唐納森教會了他野外生活的方法、各種鳥的名字、根據動物的嗅跡去實施跟蹤,以及如何騎馬和射擊。
偵察兵估算這個營地能容納二十至二十五個人,但十個男人外出打獵去了。他能夠從矮種馬的數量上猜測出來。牠們只有七匹,在棚屋附近吃草。要搬遷這麼一個營地,讓男女老少騎上去,折疊起圓錐形帳篷連同其他行李一起裝上皮繃子,應該需要二十匹馬。
在捕獵一頭老棕熊時,他錯過了他所做的記號,這頭瘋狂的野獸抓死了他。本.克雷格在林中的那座小木屋附近掩埋了他的繼父,帶上他需要的東西後,用一把火燒了其餘物品。
本.克雷格十歲時,已長成了一個山林和邊疆男孩,這一年,他的父母親死於克勞人的一次交戰中。兩天後,一個名叫唐納森的設陷阱捕獸者遇到了他,當時他坐在被燒成了灰燼的木屋旁,又是飢餓又悲傷。他們一起把約翰.克雷格和珍妮.克雷格埋在水邊的兩支十字架下。約翰.克雷格是否隱藏著一袋金粉將永遠不得而知,因為如果克勞的勇士們發現它時,他們會把這袋黃粉扔掉,認為它只是沙土。
六月二十日,這支聯合部隊抵達了羅斯伯德溪流入黃石河的地點。在這裡,他們決定萬一那些印第安人逗留在羅斯伯德溪上游地區,從林肯堡起一直陪伴特里的第七騎兵團,應拉出去溯羅斯伯德溪而上直至抵達源頭。卡斯特也許能找到那些印第安人,他也許能找到克魯克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