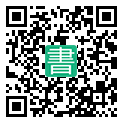(二)
我出門前收拾了一下,打了腮紅撐氣色,但畢竟狀態大減,拾掇到出門不會嚇人的程度,就懶得再修飾下去。既然老朱已經看出來,我便想跟他訴個苦算了;但張一張口,又說不出話來,這麼一轉折,又深深嘆了一口氣。
老朱立刻眉開眼笑,「那肯定呀!長得跟我一樣就完了!」口吻收一收,又低低添了一句:「她像她媽,她媽原來挺漂亮的。」
「之前那麼幾年都等過來了,為啥現在要離婚?」
「看來事情還不小啊!」我一連串的唉聲嘆氣把老朱驚到了,駭笑道:「跟你老公吵架了?」
「哦。可是我問了小天,他說是你跟一個中國女生混在一塊了,因為你跟人合租,怕室友看見之後告訴你女朋友,所以帶著那個女生到他那裡住了幾天,讓他住你宿舍。」
外國剪頭貴,很多男留學生會自備理髮用具,自己剪或是互相剪。女生就簡單一些,頭髮長了就長了,所以很多女留學生都是及腰乃至過腰長發。只是太長了,發梢就會發枯。而我在國內,向來只保持及肩長度,從頭到梢都是漆黑的,有非常健康的光澤。
我感到這話題可能讓老朱有點不是滋味,便收住,又問:「你怎麼想到做尋寶遊戲過生日的?你這個當老爹的,心思還挺靈活。」
老朱這段話,讓我忽然有些感動了。這個男人雖然看著有點兒窩窩囊囊(不然我們女同事也不會跟他產生這麼純粹的友情),但作為一個父親真的是用了心。我開始有點兒羡慕那個未曾謀面的、叫小儀的女孩。在我小的時候,那些幻想、夢想、空想,實現過一次嗎?似乎沒有。人人都知道小孩兒是胡思亂想,人人都不在意,直到小孩變成了大人,終於丟棄了那些想頭。可是小儀還小,如果幫老朱一回,讓這個小女孩擁有一次有意思的經歷,有什麼不好?何況眼下,我覺得自己確實需要一件不一樣的事,來轉移一下長久陷在感情問題中的注意力。
我不語,盯著地上思索。片刻,我說:「我怎麼感覺你在騙我呢。」
「喝不了冰的,給我一瓶常溫的吧。我點個杏鮑菇,一條秋刀魚,就夠了,剩下的你看著點吧。」我把菜單交給他。
「你臉色不大好啊,有點腫腫的,是不是經常熬夜?」老朱把我打量兩眼,「還是有什麼不開心的事?」
我一邊想著,一邊輕輕掀開床單與枕套。是新換的,什麼都沒有。我又走到洗手m.hetubook.com.com間,在下水道進水口面前蹲了下來——女人就是這樣,自欺欺人和心細如髮總是同時并行。為了迎接我的到來,庄小天把房間打掃過,也清理過下水口。但我手指和筷子並用,還是勾出了少許頭髮。我耐心分離掉那些短小的、明顯屬於庄小天的頭髮,在剩下的雜發中,析出了四五根一尺多長、髮根烏黑、發尾略泛黃的青絲。
他忽然住了嘴,眼神從驚詫與激動瞬間跌落,變得無措而狼狽。我默默地盯著他。
如果是別的任何人,我可以把這關係直接扔掉——比如砸了鄭喜的眼鏡,跟他絕交,便了了事。可是庄小天是我的丈夫啊,我們之間有十年感情,十年的共同生活讓他的一部分血肉已經長在了我的體內,我沒辦法一下子把他剝出去。我要做一個巨大的手術才能完成這次分離,無論成功與否,我都必定會元氣大傷。
「是啊,跟你沒有關係。剛才那話是我編的。這才是你被冤枉時真正的反應吧?」
「個子挺高了,現在小孩都長得快。」老朱把手機相冊打開遞給我。我翻了幾張,評論道:「說句實話,你女兒比你好看多了。」
「嗨,她現在這個年紀,不就是好奇心重嘛,不管是在家裡還是出門,看到什麼新鮮的都要刨根問底。玩遊戲也喜歡什麼海盜啊,探險啊,盜寶啊——其實我們小時候不也是一樣?在荒郊野外,看到個兔子洞都要掏一掏,想掏個什麼寶貝出來。我跟你說,有一回我真在土裡挖了個瓶子出來,那種瓷的,白的,粘的全是土跟綠苔。我一看眼睛就亮了,這不古董嗎!跟我一塊玩的小孩還跟我打起來了,兩個人都要爭這個古董。最後被我搶到手,拿回家給大人看,說就是個以前的雪花膏瓶子,我不信,把它泡水裡一洗,果然,還有一塊商標在上面,把我給氣得!」
「我嘆氣了?」我意外,因為自己毫無覺察。
所以那晚,他看到了我歇斯底里精神崩潰的一面。庄小天很厭惡這樣的我,他皺著眉頭說:「聲音能不能小一點,非要搞得鄰居都聽見你才滿意?我已經跟你反覆道歉了,你鬧成這樣要給誰看?」我心如刀絞,眼淚模糊地喊道:「你為什麼這麼殘忍?為什麼不能對我好一點?」
「嗯,還有三個月就回國。」
「任婕,這你就冤枉我了。」鄭喜輕輕晃一晃腦袋,笑容絲毫不減,「我跟和*圖*書小天經常中午晚上一塊吃飯,晚上他一般都在實驗室搞到十點多才回去,周末不是睡覺就是找我打球,他比我過得還無聊,怎麼會有女生到他家裡住?」
「那個『仙女』,你還有別的人選嗎?」我問他。
得到肯定答覆之後,我就出了門,坐地鐵,徑直奔去鄭喜所在的研究所大樓。一路上我有點兒恍惚,因為一天之前,我還在中國,在一片鄉音里趕往機場。一天之後,我就坐在滿車廂的外國人中。這種時空的轉換讓我感到像一場夢。我真的希望我在房間里發現的那些痕迹,都是一場夢。
「我在家裡發現了一些東西,有其他女生來住過。」我慢悠悠地說。
老朱和他前妻離婚挺早,印象中小儀當時還不滿周歲。原因是什麼大家也不清楚,我從來沒問過。不過,總覺得老朱對前妻還是有點情分的,從來沒聽他說過前妻壞話。從這一點來看,老朱倒是挺仗義。
「你值得我對你好嗎?」小天偏過頭,嘴裏咕噥道。
我笑了起來。這是這些天我第一次真心覺得一件事好笑。
最後,我把鄭喜新配的眼鏡砸爛了。因為一想到我在眼鏡店裡煞費苦心選款時的蠢相,就感到噁心。這一砸,自然意味著跟他決裂,也意味著小天肯定會得到消息,我已經知道了。那晚小天回來的時候,我發現,比起他如何面對我,我更不知道我該怎麼面對他。從小到大,我認定一個人可信,就一直信他;我不覺得可信,就不會親近。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一個已經複雜化、變成灰色的關係。
小時候我養過一隻小狗。有一天我跟它出去玩,忽然它不見了。一路回頭找它時,我腦子裡閃過了一萬種可能性:它迷路了;它中毒了;它被打狗的人打走了;它遇到大猛獸,被吞吃了;它掉進了時間隧道;它卡在了樹洞里……那一刻的慌亂是空白的,我只能用各種想象去填補。正在著急時,它忽然又出現了,原來它只是撿到了一點食物,躲進路邊的草叢裡吃。聽到我遠遠地喊它,它便循聲追了過來,重新繞著我的腿轉來轉去,還快樂地搖著尾巴。
「怎麼有點兒皺著眉頭?來看你老公,還不開心呀?」鄭喜笑眯眯地問。
「行,那我演。」
「沒事,要不是你跟我說說話,我更悶呢。」我不想再說自己的事情,便轉了話題:「小儀現在長什麼樣了?給我看看她照片。」
「哎,他弄成這樣https://www•hetubook.com.com,是要離婚,不然以後怎麼過?可是你這幾年又太虧了。要是他沒出國那會兒就出軌了,對你還好一點,你現在有二十——二十幾?」
「你才說幾句話,都嘆了兩回氣了!」
「小儀過生日,她媽也來吧?」
跟老朱的飯局約在第二天晚上,他說要請我吃龍蝦。三月下旬市場上沒幾隻蝦,自然價貴,老朱請我吃蝦,倒是挺有誠意。我其實無所謂吃什麼,到了約定的鐘點,晃晃悠悠打車去了燒烤店。老朱已經點好一大盤紅彤彤的龍蝦送上桌,他的胖臉在龍蝦邊笑容可掬地看著我,和龍蝦相映成輝,彷彿兩隻喜慶的大紅燈籠。
「來,不過,她都是提前來,把孩子接去玩一玩。當天她不來。」老朱笑笑。
鄭喜戴上眼鏡,前後左右瞧了瞧,笑嘻嘻地說:「正好正好。又麻煩你帶東西,真是謝謝你。」
對著毛衣思緒胡涌的那一剎那,我期待著眼前的異常狀況和當初丟失小狗一樣,只是因為某種最簡單、最安全的原因。比如,這就是他一時興起疊的呢?或者曾經有同學來借住,出於感謝幫他疊了衣服?這些可能性並非全沒有。我不能輕易冤枉我的老公。我不能輕易失去了現有的生活。
「沒有沒有,不會的。」他把手搖了搖,「你放心,我給他打包票,不會的。」
「我知道,你跟小天講義氣,不好跟我說,」我有氣無力地說,「但我現在既然發現了,你就實話實說罷,他們兩個好了多久了?」
當時小天那張臉啊。那冰冷的臉頰,陰沉的眼瞼,刻薄地抿起來的嘴角,永遠地刻在了我的記憶中。我沒見過鬼,在我的感受中那樣的面孔就是鬼。那一刻我明白了,男人是不會關心一個嚎啕的女人為何嚎啕的,他們只會覺得,那哭喊的聲音真刺耳,那失態的面孔真難看;所以,我要是夠聰明,就要盡量讓自己避免處於可能會嚎啕的處境中。嚎啕沒有意義,痛苦也沒有意義,除非我是個作家,或有可能把這些一手體驗當成日後的寫作材料,可我並不是,所以,我立刻離開了荷蘭。
何況這次過來不到一天,我還沒有洗頭。
鄭喜尷尬地別過眼神。我看著他的臉,發現這張臉比起初中時變化很多了,雖然乍一看還是那個人,仔細端詳,骨骼,皮膚,眉眼,都不一樣了。初中那會兒,我們還是小孩子,他和我的座位只隔一條過道,我們每天有說有笑,互換課和_圖_書堂筆記,互傳小道消息,考試時互相偷偷報答案,自習時互相提醒老師在窗外。明明是一個可以交換真實的人啊,沒想到如今,真話換來的是假話,假話套出的反而是真相。我心中十分悲哀。
「我們要離婚了。」我擺正腦袋看著他,嚴肅地說。
我多希望鄭喜說的是真的啊,其實到此時此刻,我仍然很願意選擇相信小天和鄭喜。可是,一個不知道從哪冒出來的想法忽然在我的腦子裡顯靈,讓我暗暗轉換了心思,不動聲色地繼續說了下去。
我臨出國不久,鄭喜打球摔破了眼鏡邊。在國外配一副眼鏡也是個麻煩事,他趕緊叫他爸媽找出原來的配鏡記錄,配了一副新的讓我帶過來。款式是我在眼鏡店幫忙選的,畢竟是上臉的東西,我當時很考慮了一會兒,力圖盲選出最適合他的款式。
「蝦我已經點了,你看下菜單,想吃什麼燒烤?——我們來兩條秋刀魚吧,他家秋刀魚不錯,還有那個烤茄子也可以嘗嘗。喝點什麼?來幾瓶青島?今天挺暖和的,喝點冰啤酒,涼快!」雖然一年多沒見,畢竟認識多年,彼此都沒啥隔膜感,老朱自自在在地招呼起來。
「你咋了,怎麼嘆氣?」老朱看看我。
我給鄭喜發消息:「你在辦公室嗎?你爸媽讓我給你帶了東西,我現在送給你。」
鄭喜一怔。他的肩膀猛然挺直,聲調陡然提高,差點破了喉嚨:「怎麼變成我劈腿了?鄭薇薇跟我有什麼關係——」
「怎麼不好搞?」
「其實這也不算生日禮物,過生日那天的蛋糕和禮物還是會準備的,我就是想——怎麼說呢,讓小孩有點不一樣的經歷,讓她覺得,『哎,我還會遇到這麼有意思的事情!』說不定多少年以後她還會記得,『我小時候啊,曾經發現過一張藏寶圖,找到了一個寶藏,寶藏里還有仙女呢!』她自己參与了這麼個遊戲,比去遊樂場、迪士尼都更有意思,你說是不是?」
「啊,不是吧?」鄭喜一抬眉毛,把新眼鏡取了下來,舊眼鏡戴回去,「你看錯了吧。」
我看著老朱,但視線好像並沒有落在他臉上,而是回到了阿姆斯特丹那間淡黃色木板壁的出租小屋裡。一切又回來了。三月十三日上午,我下了飛機,庄小天把我接到住處,就到學校去。我睡了半天休養精神,醒來後庄小天還沒回來,我無事可做,便開始收拾房間,又打開他的衣櫃準備整理。下層收放的當季衣物確實有些雜亂,是www•hetubook.com•com他平常的風格;打開上層櫃門的一瞬間,卻發現他冬季的衣服比往年明顯收放得整齊,不需要我再整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一種異樣的感覺襲上我心頭,讓我把已經合上的櫃門又重新打開。我抽出一件高領毛衫,發現它是用一種我不熟悉的疊法疊起來的,領口和袖口巧妙地拼合在同一個截面,使得整件衣服疊好后是一個完美的長方體。庄小天不可能會這樣疊衣服。
見到鄭喜,我倆走到咖啡間說話。我把他爸媽托我帶來的東西點給他看,「兩件套頭衫,一件羽絨背心;一包干木耳,三包火鍋底料。還有你要的新眼鏡,你戴上試試,看度數是不是一樣。」
「二十九!」我瞪他一眼,「你不要跟我強調我的年紀,我自己還不知道嗎?」
「沒呀!實話說,真不好找——又要扮著像,又要跟我熟、能商量事兒,小儀還不能見過。我認識的女生又不是很多,前幾天想來想去,只想到你一個。」
「離婚?」老朱瞪大了他的小眼睛,「他不是在荷蘭讀博么?應該快讀完了吧?」
「庄小天是不是在這邊劈腿了?」
今天我肯來見老朱,前提就是經過了這些天的緩衝,我已經能控制情緒。我平靜地、扼要地敘說著這些事情,無視老朱一愣一愣的表情。我說到我已經想清楚,等他一回國就辦理離婚,老朱把嘴張了半天,擠出一句:「真不好搞。」
「好好好,不說不說。——怪不得這些天找你總是沒反應,原來真的是有事情。我之前說的那當仙女的活,你要是不想當,就算了。怪我不知道你心情不好,抱歉抱歉。」老朱做了個抱拳的動作,在我面前搖了搖。
「都是小事。」我看著鄭喜露出的一排板牙,有點兒出神。如果庄小天真的和其他女生住在一起,鄭喜知道嗎?
「是嗎?」我隨口道,結果不自禁地又嘆了一口氣。這次自己發現了,我好笑起來。
鄭喜猶豫著,甚至到了這時候,還想幫裝小天掩飾。我明白這對他來說有多麼難堪,可是我不再關心。我緊追不放,像一個嚴厲的判官,只想得到我要的真相。不時有外國同學進出咖啡間,奇怪地看著我們這兩個表情不對的東方人,不明白髮生了什麼。鄭喜跟他們大多都認識,時不時要停下來,用英文和他們敷衍幾句;又盡量控制和我說話的語氣,讓這場對質聽著像聊天。但我一個人也不認識。在這個異國的世界,我是孤軍奮鬥,反而什麼也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