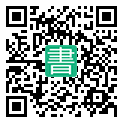一、台灣艱苦的日子
「你要當兵,遲早都要讓她知道的。」許二牛說。
只見那對男女聞聲便放下工作,歡天喜地的走進小屋裡去。望著眼前這一戶家人的溫馨的情景,高弘想起了自己的母親。
「是打架嗎?」
「怎麼啦?」許二牛眨眨眼睛,乘機向他追問:「我們一起當兵好不好?」
「你現在才收隊回來?」高弘惺忪地問。
高弘聽著,轉頭望望身邊的漢子,認出他果然是那天近晚的時候,在老婆陪同下到學校報名當兵的漢子。
他們見到李貴手拿著喇叭筒,從軍餉部走出來。他跳上一個汽油桶上,高聲向排隊領軍餉的士兵宣佈:
高弘縮了縮腳沒有理會牠。牠轉過頭去嗅許二牛那從破褲管中露出來的膝頭。許二牛霍地站起來,猛地舉腳朝老母狗的嘴巴蹴過去,大聲罵道:
「殊——」高弘連忙轉過身來,把食指豎到嘴前,示意許二牛別作聲。
跟著,王排長繼續大聲說:「大家聽著:我重複一遍,在國軍的整編中,我們的番號是第七十師一三九旅二七八團一二五營。我們將駐營在豐原進行積極訓練。我們是正規的國軍,不是散兵游勇。所以,必須嚴守軍紀,如有觸犯軍法、不服從上級命令者,將會馬上槍斃,以儆效尤!明白嗎?」
「再來一次!明白嗎?」
士兵冒著雨,在營地上集合,跟著在附近的山頭作雨中作戰訓練。他們渾身濕漉漉的在泥濘中爬行,在山丘上奔跑……
「我——」高弘遲疑一下說:「我沒有意見,服從中央的決定。」
高弘和許二牛經過學校門口,不期然往裡面望進去,瞥見學校操場的破舊籃球架上,懸掛著幾盞煤油大光燈,燈下擱著一張乒乓球枱。四五個穿著軍服的國民黨兵坐在乒乓球枱前,為幾個排隊報名當兵的人登記。
許二牛站在隊伍的尾部,他不時轉過頭來,伸首望向門外的人群。
杜升被拖行時,乏力的雙腳在沙地上留下長長的、像火車路軌似的痕迹。
翌日。
「嘿——吃飯囉!」
「我寧願我們一起餓死!」婦人摟著漢子嗚咽起來。
十多個國民黨兵扛著刺刀閃亮的長槍,在操場上叱喝著新兵列隊。驟眼看來,不知情的人倒以為操場上站著的是一群俘虜。
許二牛自討了個沒趣,搔搔頭頂的短髮,亦步亦趨地跟在他後面走。
高弘在睡夢中給拖著一身疲憊鑽進營帳來的許二牛驚醒。黝暗裡,高弘聞到許二牛濃郁的汗臭,聽到他低聲嘆氣的聲音。
「日本人無條件投降是事實,不過——」老軍醫說到這裡,突然壓低嗓子說:「我恐怕趕走了外侮,家裡又兄弟鬩牆起來!」
「娘說的話,不相信也得去做。」高弘聳聳肩膊說。說著,他加快腳步回家。許二牛在巷口跟他分手時,還留下步來對他說:
「醫生,你是我們在軍隊裡遇到的最好的人。」高弘肅然起敬說。
「我料他會肯的。」許二牛笑著說:「這醜八怪難得有人肯下嫁他,那寡婦和兩個女兒現在住在旅舍裡,聽說十天內崔麻子再找不到房子的話,婚事就拉倒。」
高弘點點頭。許二牛連忙打岔說:「這是他家的祖屋,他的父母都死了,他是獨子,是唯一的繼承人。」
當高弘向那個負責登記的國民黨兵報上姓名、年齡、籍貫和地址後,那國民黨兵吩咐他三天後中午前來報到,就揮手叫他離開。
那婦人發狂似的追近軍車。她把手中的一張照片遞給這漢子。
「不要忘記我們!」那婦人哽咽著聲音叫道。突然,她絆著一塊石頭,一個踉蹌跌倒在揚起黃塵的地上。人們響起一陣驚叫。
「娘,我回來了!」高弘一邊喊著,一邊走進房子裡。
許二牛咧著大嘴巴,傻愣愣地笑著。
高弘長長嘆息了一聲,點了點頭。
杜升卻一動也不動,嘴裡仍喃喃自語詛咒著,似乎陷入昏迷狀態。
「在和平的日子裡,軍人不用上戰場打仗,老婆怎會做寡婦呢?」杜升大惑不解問。
說到最後,他的聲音哽噎,眼眶紅了。
照片中一個頭髮灰白的老婦人坐著,一個穿花裙子,兩條烏亮的辮子垂在胸前的標致姑娘站在旁邊。
許二牛走到崔麻子和徐夫子面前,向崔麻子打招呼:「崔老闆,你好!」
「甚麼是領袖?」許二牛大惑不解問。
營地旁邊那木製的囚禁室,濕漉漉的像個剛從大海中撈起來的大木棺。高弘走近囚禁室,伸手拍了拍用松樹樹幹拼合而成的、厚厚的門,把嘴湊到門縫上叫道:「老杜,我給你送飯來了!」
「你不是進學校裡報名當兵嗎?」
「當營長多威風!你讀過書,有文化,將來也許有機會升級當長官的。」
他發覺杜升斜坐在囚禁室裡。一動也不動。他不禁大吃一驚,惶惑地問:
路上,許二牛把高弘喪母的事情告訴崔麻子。
「只是甚麼?」
「你娘有你哥哥和嫂子照顧,還惦念甚麼?」
高弘回身走到牆邊的一張破舊的木桌子前,拉開抽屜,伸手往抽屜內翻了一會,終於翻出一張發黃的紙鈔來。
他一時悲慟得嗚咽起來,話說不下去。
高弘身邊的漢子大吃一驚,轉頭向駕車的司機高聲叫道:
李貴用鑰匙開了囚室的門鎖,「咿呀」一聲拉開木門。突然瀉進去的光線使杜升緊閉的眼睛微微動了動。他渾身濕透,面色灰白,像一具剛從河裡撈起來的屍體。
「是我們國軍最高的頭兒。」
高弘娘搖搖頭,想說甚麼,但張開口吸了一口氣又嗆咳起來。
「你們站著!」李貴突然喝住他們。
「娘,那是騙人的,你別相信。」高弘用手指輕輕地替母親揩拭臉上的淚水說。
「排長,他發高熱,看情形可能有生命危險!」他焦慮地對李貴說。
「你需要甚麼條件?」
「毛毛小時候像醜小鴨,沒想到她長大後變成一個漂亮的姑娘!」趙軍醫在高弘、許二牛及杜升三顆腦袋湊在一起,湊著觀看照片的時候,在旁笑著說。
「你認識字較多,可以去瞧瞧佈告嘛!」
「我倒想到了一個辦法。」許二牛說。
「為甚麼?」高弘和許二牛不約而同驚異地問。
王排長面色一沉,再大聲叫道:
「交換甚麼條件?」高弘納罕問。
高弘再回頭望望塵土飛揚的路上,透過薄霧似的黃塵,瞥見那揹著嬰兒的婦人,站在遠處路中央揮動著手。軍車拐了個彎,婦人和嬰兒的身影在視野中消失了。
「沒,沒甚麼。」崔麻子支吾應道,跟著起身走出去。在茶室門外,他見到許二牛抱著雙手,站在路旁等候他。
王排長訓完話,開始指揮新兵們攀上停在操場旁的軍車。軍車魚貫駛出校門。這時節,門外圍觀的親人們情緒開始激動,頻頻高聲叮嚀和揮手道別。
月光照射在高弘娘那灰白如紙的、乾癟的臉上,像鍍上了一層冷冷的寒霜。
「排長,如果不給他醫治,他可能會死的。」高弘連忙追上去對李貴說。
高弘這個動作是故意讓許二牛娘知道,他與許二牛是並肩在一起,互相照應的。
「這房子是你的嗎?」崔麻子向高弘問道。
「崔老闆,我怎敢騙你,以後還要你關照我工作哩!」許二牛睜著眼睛認真地說。
「那麼,三年後退役,你找到工作後快點娶個好媳婦,侍奉你娘吧!」高弘拍拍他的肩膀笑道。
「是報到入營後。」瘦排長望許二牛一眼答道。
「他媽的!」李貴一邊咒罵著一邊回過頭來,向站在一旁張望的許二牛命令:「把他扛到醫療處去!」
「捨不得離開你娘嗎?」高弘笑著問。
崔麻子料想不到許二牛慷他人之慨,又提出給對方一百塊錢紅包,正想開聲反對,高弘已站到他面前,打躬作揖,連聲道謝。他想起自己找房子結婚要緊,也就無奈地答應了。
「好吧!我馬上就去!」高弘不敢忤逆母親的意思,準備往門外走,但仍不放心地回過頭來問:「讓我先把那個剩下來的饅頭蒸軟,給你吃好嗎?」
許二牛目送高弘走遠了,才走進茶室裡去。
「是我們的領袖。」
士兵起了一陣哄動。
「娘想你替我馬上去辦一樁事情。」高弘娘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說。
於是,這簡陋的房子裡燭煙裊裊,唸經和敲木魚的聲音,響徹了這條平日謐靜的小巷。
高弘和許二牛好不容易才把身體癱軟的杜升,從窄小的囚室裡扛出來。另外兩個士兵趨前幫助。四個人跑著步,匆匆把杜升抬進設在營帳裡的醫療處去。
這時候,聽見王排長在台上喊一聲:「稍息!」
高弘和許二牛面面相覷。
「你到那兒去?」許二牛問。
「你憑甚麼討特別人情?」瘦排長蹙了蹙他那稀疏的眉毛。
這時候,只見那婦人爬起身,伸手拍拍身上的塵土。揹在她背後的嬰兒受驚號啕大哭起來。看來她母子倆沒有受傷,人們都暗暗吁了一口氣。
「是在囚室裡病倒的。」高弘答道。
「街上貼了佈告,有許多人在圍觀。」
「只要你換過一扇新的門窗,拆掉舊竈造一個新的,及全屋髹過灰水的話,我擔保你的未過門太太一定會喜歡!」許二牛繼續指指點點地說好話。
高弘和許二牛在營帳外聽到他們的對話,兩人不禁互相交換一下眼色,對老軍醫的正義行為暗暗敬佩。
「快讓他躺下——」老軍醫指了指旁邊的一張鋪上白布的木床,對他們說:「馬上替他脫去身上的濕衣服。」
「你怎麼啦?」崔麻子盯著他問道:「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崔麻子點點頭,眉頭舒緩了。
「我們還是不明白你說的意思。」高弘搖搖頭說。
說完,轉身向酒糟鼻的金營長立正、敬禮,然後退站一旁。
「你哥哥知道嗎?」
一清早崔麻子就帶了仵工,扛了一具棺材和帶來了一大包冥鏹和香燭等祭品。過了一會兒,又來了四個穿灰衣的僧人。
「現在是甚麼年代了!」趙軍醫格格笑起來說:「兒女婚姻大事,還會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些封建俗例嗎?」
「我娘的病一天沒痊癒,我就是不放心。」高弘說完,也不待許二牛再說甚麼,逕自匆匆跑進小巷回家去。
許二牛站在廟的門檻上,瞥見高弘逕自走近神龕,在香案前停下步。他合十雙手,向神龕裡的觀音菩薩像揖拜了三下,略一猶豫後,伸手往香爐裡抓了一把又一把香灰,放進口袋裡。
一九四六年九月,國民黨七十一軍一四零旅的台灣士兵,在台中附近的營區集結整訓。士兵們要在火辣辣的陽光下,或伸手不見五指的黑https://www.hetubook.com.com夜裡進行山地作戰及行軍等等專案訓練。
「這人犯了甚麼大過失,要用槍柄把他打得如此重傷?」老軍醫向李貴問道。
崔麻子不住地點點頭,這時候,他才把目光落在愣愣地站在床邊的高弘的身上。
「從今天開始,你們被編入國軍第七十師、一三九旅部隊,將執行保衛台灣的任務——」
這所謂囚禁室,其實只是一個面積僅一平方公尺,用樹幹釘封,頂部有幾個小孔作透氣的,看起來像一具豎起來的棺材似的小囚牢。人給關在這小囚室裡,就只能站著或屈腿坐著,不能躺下來。
他們待李貴走遠了後,再次鑽進醫療處的營帳去。
這漢子聽了,咧開大嘴巴格格地笑起來。但他忽然又沉下臉,滿懷愁緒地嘆了一口氣,神情有點惘然若失。
「別擔心,總會想到辦法的。」
「我聽人家說過——」高弘娘說著的時候沒有睜開眼睛,只見眼縫裡又滲出一滴老淚來:「用香爐灰澆水洗三次面,就可以百病消除了。」
「難道日本軍隊投降是假的嗎?」高弘搔搔腮幫子問。
此刻,王排長站到台前,一邊大聲吹響哨子,一邊伸手在空間按了按,示意台下各人肅靜,跟著大聲道:
說著,他把照片遞到高弘的面前,然後把自己的臉移後一點,好讓高弘把自己的眼睛跟照片中兒子的眼睛對照一下。
許二牛會意地用手捂著自己的嘴巴,悄聲問:
「因為——」趙軍醫嘆了一口氣:「我不想女兒做年青的寡婦!」
許二牛見他語氣堅決,只好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膊。兩人在河邊的一棵老樹的陰影下坐下來。
「我不是對你說過,我家的房子不賣嗎?」高弘偏過臉,窩他一下白眼。
「這回不是要你賣房子,是去跟崔麻子交換條件。」
高弘聽他怪聲怪氣扮母親的聲音,忍俊不禁笑了起來。
「是真的嗎?」崔麻子驚喜問。
許二牛見他洞悉和回答了自己心裡的話,感到沒趣,於是改變話題向他問道:
「是!排長!」他們轉過身來立正應道。
崔麻子打量一下兩眼紅腫,眼眶裡仍閃著淚光的高弘,指指許二牛向他問道:
金營長輕輕咳嗽一下,慢條斯理地走到台前。他瞪著眼睛,向台下二百多名新兵掃視一遍,然後挺起胸、昂著頭開始他的訓話:
「你有這房子的契約嗎?」崔麻子再問。他想起徐夫子說的話:現在時勢不好,失業人多,騙人的事兒層出不窮。
說完,他蹲低身子,伸手打開門下一扇小活門,把那碗稀飯塞進去。
這當兒,他們背後忽然傳來一陣女人的哭聲。他們回頭一望——一個年約三十三、四歲的女人,揹著嬰兒,一邊哭泣著一邊拉扯著一個漢子的手,不讓他進學校裡去。
高弘連忙扶著她往床前走,用手掌輕輕為她拍著背脊。他小心翼翼地把母親扶上床,讓她躺下來的時候,驀地發覺母親那黃濁的眼睛在望著自己,兩大滴淚水從眼角沿深陷的皺紋滑到耳朵上。
高弘沒有吭聲,他把目光望向排隊人龍的前頭。杜升進入軍餉部已經十多分鐘,仍未見他走出來。
「對,說到『執行保衛台灣省的任務』——」金營長一邊說著,目光一邊在講稿上搜索連接的講詞。然後繼續大聲訓話:「你們是第一批參加本師的本省志願兵,是後來應徵入伍者的倡導者。本師陳頤鼐師長為了獎勵你們的熱忱,將呈請縮短你們的服役年限,使你們能够提前退役,並安排你們獲得就業機會——」
「不可以把它儲蓄起來,將來退伍後做小生意嗎?」
為了發放軍餉,部隊的野地作戰訓練提早收隊。在營裡放下槍桿後,士兵爭先恐後地到軍餉部排隊領取,情緒都顯得非常興奮。
站在他身旁的高弘,此刻給觸動了思念亡母的情懷,鼻腔不禁為之一熱。他把手搭到許二牛的肩膊上,並向許二牛的娘及他的兄嫂揮手。
高弘娘點點頭,闔上眼睛,她似乎感到很疲憊。
在雙方簽署好租約,留下見證人一欄,許二牛向崔麻子收了五十塊錢介紹費,才肯用大拇指蘸了烏亮的黑墨,把指模印到租約上去。
許二牛與高弘交換一下眼色,低聲說:「他媽的!看來那三千塊錢安家費是不發放了!」
「甚麼安家費?」那國民黨兵抬起頭來瞪他一眼。
「是和尚嗎?」許二牛睜大眼睛問。
「你怎麼啦?」在門側停下,崔麻子直瞪著許二牛問:「我甚麼時候答應過用上好的棺木和請僧人做法事?」
「我不全懂上面寫些甚麼,不過,我聽人們看過佈告後說,國民黨招募年青人參加軍隊,有三千塊錢安家費——」
這當兒,突然有一個背著嬰兒的女人從人叢中擠出來,向他們乘的軍車追上來。
高弘點點頭,神情沮喪。
「要是入營後不發放,怎麼辦?」許二牛搔搔腦袋,再打岔怯怯問。
哥哥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膊,點點頭。
「別跟他說話!」有人在他們背後大聲叱喝道。
「不行。」高弘搖搖頭說:「這房子是我爹唯一遺留給娘和我的祖業,我不能在娘剛去世,屍骨未寒就把它賣掉。」
高弘瞪他一眼,問道:「你不把安家費匯給你娘嗎?」
「長官,你還沒有發給三千塊錢安家呢。」高弘問。
「你們以為戰爭已經結束了嗎?」老軍醫望望高弘和許二牛問。
「不錯,每一個當新兵的,按照國家規定都會獲發安家費三千塊錢。」這瘦排長笑著對高弘說:「不過,這安家費不是現在發放的。」
「明白!」新兵們高聲回答。但聲音仍是參差不齊,立正的動作也先後不一。
高弘不期然轉頭往學校內的操場望去,瞥見她的男人站在排隊報名當兵的行列裡。
王排長在台上先鼓掌,引導台下的新兵們又一次熱烈鼓掌。
「日本鬼子不是無條件投降了嗎?」高弘納罕問:「戰爭已結束了,為甚麼剛才你說現在是亂世呢?」
趙軍醫說著的時候,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照片來遞給高弘和許二牛看。
九點鐘的時候,報到的新兵二百多人,集中在學校的操場上。學校的門外麕集送行的親人,他們都依依不捨,守候著不肯離去。
許二牛和杜升在他的身邊互相作了一個鬼臉。趙軍醫看在眼裡,伸手取回照片,然後拍拍高弘的胳膊,半說笑半認真說:
老軍醫閒來無事,便叼著香煙,在拉二胡自娛。高弘不吸煙,把每月發配的香煙都送給他,彼此的感情愈加深厚。
「你心裡打著甚麼主意?難道就此眼巴巴的兩母子一起餓死嗎?」
「甚麼佈告?是有大米派發嗎?」
「你們一齊立正回答我!」王排長精矍的目光往台下一掃,再大聲問:「明白嗎?!」
「招兵的告示裡不是註明,每一個參軍的都有三千塊錢安家費的嗎?」高弘理直氣壯說。
「他受傷很重,要帶他去見軍醫嗎?」高弘惻然,問李貴。
高弘是最後一個領軍餉的人。那戴眼鏡的軍官把雙腳撂在辦公桌上,嘴角叼著香煙,悠閒地監視一個文職人員發放軍餉。
「老頭子,別在發牢騷胡說八道了!」李貴哼了一聲,撥開布帳走了出去。
站在一旁的許二牛貪婪地往這婦人的胸部偷偷窺視了兩眼,回過頭來,發覺身邊的高弘不見了。他舉目四顧,發覺一條身影走進觀音廟去。他連忙追前去察看。
說到這裡,他忘記了講詞,於是用拳頭按著嘴巴,輕咳了一聲來掩飾。而另一隻手連忙往褲兜裡掏了又掏,可是發覺講稿不見了。他急得滿頭大汗,兩頰通紅。惹得台下起了一陣哄笑聲。
「有話你在這兒說好了!」跟著,他又對崔麻子說:「現在時勢不好,失業人多,騙人的事兒層出不窮,凡事小心為佳。」
「你甭說了!」高弘猛搖著頭,斬釘截鐵說:「房子不能賣!」
「嗯。」許二牛點點頭說:「反正你當了兵,房子空著無人居住。」
許二牛點點頭,無奈地笑了笑。
「你們跟他是同鄉嗎?」
「他媽的!」李貴瞪高弘一眼罵道:「死的是他不是你,你在囉嗦甚麼!」
許二牛喊完後低聲問高弘:「蔣委員長是甚麼人?」
金營長見了連忙接過來,吁了一口氣。然後張開講稿瞧了瞧,蹙著眉轉過臉向王排長悄聲問:「我講到那兒?」
他趨前向他問道:「你說有房子出租是真的嗎?」
「就是這樣我才讓你當兵。」許二牛娘放下高弘的手,轉捉住許二牛的手叮囑說:「你千萬要規規矩矩當好兵,待三年後退伍時,讓政府給你介紹一份好工作。娘有你哥哥和嫂子照顧,你不用惦念。」
「林副官?」高弘好奇問:「是日間負責發放軍餉的、戴眼鏡的那個人?」
「崔老闆,你瞧,我沒騙你吧!」許二牛咧著嘴,堆著滿臉笑容說:「這真是個好地方!」
「大娘,你放心好了!」高弘捉住她瘦稜的手笑著說:「阿牛雖然不識字,但他比我機靈,恐怕我還需要他照顧哩!」
「抗戰勝利了,我這把年紀是應該復員回家鄕過安逸的晚年。可是,我卻被從大陸調到台灣來繼續當軍醫,你們細心想想,這是為甚麼?為甚麼?」
這軍官說完話,張目向圍觀的士兵掃視一眼,嘴角牽著一絲冷笑,然後負著雙手慢條斯理地走回軍餉部去。
「現在是甚麼時候了?」高弘再問。
「當真?」高弘眉毛一揚,捉住許二牛的胳臂問。
高弘和許二牛望了一眼。
回到家門,他沒有進去。他坐在門檻上,把頭埋在兩膝之間。煩惱中他把頭髮抓得像一蓬亂草。蒼茫的暮色中,他感到內心和眼前的一切都是同樣的灰暗和紊亂,無法找出一個端緒來。
「那時候她沒有病,而且,假期我也可以從台南回來探望她。」
台下的鼓掌聲停止了。一片肅靜裡,二百多雙眼睛望著台上的金營長。
「老人家百年歸老是件好事嘛!」許二牛辯道。
「為甚麼?」高弘疑惑問。
果然,不久石油公司倒閉了。那個女同事嫁給一個當官的做姨太太……
杜升雙腳一軟,一個踉蹌摔倒在地上。他的臉貼著地面,滿嘴臉是沙土。他掙扎想爬起來,啐了口裡的沙土,正想開口再罵,「篷」的一聲,兩枝槍柄同時重重砸在他的背脊上。
他伸手摸摸杜升的額頭,感到熱得燙手。
「孩子餓了。」漢子望望嬰兒對婦人說。
「阿弘!」當他踱到河邊的時候,一直默默跟在他身旁的許二牛伸手搭著他的肩膊說:「還在為你和_圖_書娘下葬的事發愁嗎?」
「怎麼不行?」許二牛說:「這事情只有你、我及那孝子知道,只要你馬上決定成交,替他辦完喪事,把房子修葺粉飾一番,她怎會知道?」
本來曙色漸現的天空此刻又變得黑沉沉的,突然,雨水瓢潑似的灑下來。空中偶爾間掠過銀蛇般的閃電。
「你回去吧!我收到安家費就馬上匯給你!好好的撫養孩子!」
「他媽的!討吃也不懂得找門路!」
「可是——」崔麻子面有難色。
「是病死的,正如人家常說的甚麼壽終正——」許二牛搔搔腦袋說:「正甚麼的?是福壽全歸吧!崔老闆,你要是住這房子,擔保你長命富貴,金玉滿堂,還有——」
老母狗悶哼了一聲,夾著尾巴倉皇逃跑了。
「娘,你怎麼啦!」高弘錯愕地問,連忙上前攙扶著母親。
「剛才你說到——『安排你們獲得就業機會』。」
「他媽的!不發安家費!他媽的!騙人!」杜升嘴裡仍喃喃咒罵著。
杜升斜坐在小囚室裡,腳伸出門外。李貴動手想關上門,但給杜升伸出來的腳阻住了。他狠狠地朝杜升的腳蹴了一下罵道:
高弘跪在母親的新墳前,母親的話彷彿仍在耳畔縈繞。
陽光從木窗子投進來,落在母親那雙從破被子中露出來的、瘦得皮包骨的腳上。兩三隻蒼蠅在嗡嗡地盤旋著,不時伏在腳趾上。
「你在台南工作的時候,你娘不也是獨個兒留在家裡嗎?」
許二牛轉過臉來望望高弘。他見高弘垂下頭,用手背揩拭著滑落到嘴角的淚水,便伸手拍拍高弘的肩膀安慰他說:
高弘用手肘暗暗撞許二牛一下,阻止他把話說下去。只見杜升無奈地苦笑著說:「要是能够溫飽,有誰願意離鄉別井,離開妻兒?總不能眼巴巴地三個人一起捱餓吧!」
她說到最後,聲音哽咽,噙在眼裡的老淚終於忍不住滑下來。
許二牛躊躇地想了想,俯著身,雙手放到嘴前作喇叭狀,湊近崔麻子的耳邊悄聲說:「有一間房子出租,不能讓徐老頭知道。」
許二牛點點頭,跟著也不管崔麻子是否跟隨,轉身朝著茶室門口走去。
「崔老闆將會粉飾這房子作新房,為了討個吉利,除了出錢替你母親辦喪事外,還準備賞你一個一百塊錢的紅包,你快點向崔大善人叩謝吧!」
「怎麼啦?」杜升推許二牛一下,笑謔問:「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對對,」金營長輕咳了一聲,清了清喉嚨繼續昂頭大聲道:「退伍後將會安排你們獲得就業機會。同時,我們的軍隊像一個大家庭,陳師長保證會使全師的官兵穿得很暖、吃得很飽,身體健康,精神愉快!」
許二牛大喜,領著崔麻子匆匆趕路……
吃過晚飯後,有十多個士兵給李貴召去,進行額外的挖戰壕訓練,許二牛也是其中之一個。
高弘連忙伸手替她輕輕地拍著胸部的氣門位置,好不容易她才停了咳嗽。
「我不是已經決定不去當兵了嗎?」高弘白他一眼說。說完,他加快步子趕路。
李貴突然伸手向站在最前頭的高弘和許二牛一指,跟著又指指躺臥在地上的杜升,對他們說:
「他受傷很重嗎?」許二牛指了指杜升問道。
「真有這回事?」不待他說完,高弘忙不迭打岔問。
王排長瞥見一張稿紙在他掏褲兜的時候飄落地上,連忙上前拾起來,遞給他說:「營長,你是找這個嗎?」
「他們都這麼說的——」許二牛繼續興奮說:「三年後退伍,政府還可以介紹工作哩!」
「老弟,我剛才說的話你們千萬別說出去,有機會就溜走吧!」
杜升並沒有回答他,嘴裡仍說著同樣的話。
「醫生,剛才你說的一句話我不大明白。」高弘吹熄火柴的火苗後說。
「好吧!你帶我去瞧瞧那房子。」崔麻子聽他這麼一說,毅然下了決定:「如果合意的話,我就照你的意思去做。」
「抓一把香爐灰?」高弘疑惑問。
這漢子伸手接過照片。
「快起來!」高弘伸手扯掉他的被子,大聲催促道:「你不是想跟杜升那樣進囚室吧!」
她揹在背脊上的嬰兒這時候給驚醒,蹬動著瘦小的腳,「哇」的一聲哭了。
那漢子停下步來,嘆了一口氣對婦人說:
許二牛見他眉頭緊蹙,連忙走近牆邊,伸手拿起那條繫著天窗的繩子,大力一拉。隨著軋軋的滑輪滾動的聲音,天窗給打開了。陽光驟然瀉入,整間房子登時清爽明朗起來。
高弘鑒貌辨色,知道他在惦念剛分別了的妻兒。為了驅散他的愁緒,高弘向他伸出手,自我介紹:
「大家聽著,因為中央方面還沒有把你們的安家費款項付來,所以,今天只能發放這個月的薪餉二百塊錢,如果誰有意見的站出來跟我說!」
「崔老闆,玩笑倒不敢開,只是——」許二牛欲言又止。
「甚麼好消息?」高弘把抬起準備擲石子的手垂下來,納罕問。
「這廝說些甚麼?」徐夫子好奇地向崔麻子問道,目光在審視著他麻臉上的表情。
像一盆冷水迎頭澆在高弘的腦袋上。他愣愣地踱出學校外,心裡是一片空白。他踽踽地在塵土飛揚的街上,漫無目的走著。
全場肅靜,鴉雀無聲,不見有人站出來。
「長官,我可以討個特別人情,優先發放安家費嗎?」高弘哀求道。
一路上,高弘都沒有跟許二牛說話。他們走近觀音廟的時候,天色已經漸漸黑了。他們發覺觀音廟左鄰的一所小學的操場上,燈火煌亮。學校的門口掛起一條白布橫額,上面寫著「男兒愛國,保衛台灣」八個紅色的大字。旁邊的一根石柱上,還貼了一張寫著「國軍招募處」的紅紙。路上的行人三五成群地在門外觀望。
高弘想到這裡,眼眶裡的淚水終於噙不住,泫然滴下來了。
這漢子抬起頭望望高弘,嘴角泛起笑意說:「他跟我女人像同一個模子鑄出來的。不過,眼睛還是像我,你說是嗎?」
當他站起身,拿著燒著了的紙條,準備走前去點亮擱在木桌上的油燈的時候,在抖動的火光中,他赫然發覺一條人影寂然地掛在窗前。
李貴把小囚室的門上了栓,扣上了大鎖之後,轉身就走。
「娘!」他惶遽地叫起來。他慌忙摸到竈前,伸手到竃旁摸到一條引火的紙條,蹲低身子,把紙條伸進竃膛裡在未熄的灰燼上點燃。
「不是的——」許二牛堆著笑容答道:「我們是來找崔老闆的。」
「老杜,你覺得怎麼樣?」高弘關切地問:「很痛嗎?」
他想從腦袋裡再掏些吉利的話來說,可是他沒讀過書,平日聽回來的東西記不了多少,所以期期艾艾的再說不下去。
「都是同鄉兄弟,以後大家互相照應。」高弘說。
李貴聽了蹙蹙濃眉,伸手拿起撂在門邊的油紙傘,一聲不響往囚室走去。這時候,營裡的士兵都從營帳裡鑽出來,往囚室張望。一些更跟在李貴和高弘後面走,去看個究竟。
一隻瘦骨嶙峋的老母狗,垂著尾巴,擺動著乾癟的乳|房,蹣跚地走到他們面前來覓食。牠俯著頭用鼻子嗅嗅高弘腳上那破舊得露出拇趾的布鞋,黏滿眼屎的紅眼睛怯怯地望望高弘。
高弘想了想,疑慮說:「崔麻子他肯嗎?」
他推開破舊的木門,跨過門檻,發覺家裡黑黝黝的一片,只見竈膛裡未熄的灰燼,隱隱現著紅光。
片晌,只見一個士兵給兩個提槍的衛兵推推撞撞的從軍餉部押出來。
「是光頭的。」
他聽不見母親的應聲,一種不祥的預感在他的心裡升了起來。在黝暗中他撲到母親的床前,伸手往床上一摸,再摸,床上空空如也。
「娘,我要去當兵了。我把房子租給人家,租金是用來安葬你的,相信你和爹都不會責怪我吧!三年後退伍,政府會給我介紹工作,那時候我會勤奮工作,娶一個賢淑的媳婦,為爹娘生一個乖孫子……」
「騙子!他媽的騙子!」
「一點不錯!你兒子的眼睛跟你的眼睛長得一模一樣!」
那時候,石油公司裡有一個長得胖胖白白的女同事,曾經對他表示好感。可惜當時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這家屬於日資的石油公司傳出結束營業的消息,他眼看會遭到失業的命運,再無心談兒女私情了。
他們回到領軍餉的人龍裡去。
「我想到一個好辦法,可以令你安心和我一起去當兵。」
翌日早上,天濛濛亮的時候就下著滂沱大雨。但嘹亮的軍號聲仍透過雨聲傳到營帳裡來。
許二牛偷望高弘一眼,心裡在想:「人家年青夫妻也願意分離了,你還用顧慮嗎?」
許二牛好生奇怪,暗忖:他要香爐灰作啥用途?思量間,見到高弘回身往廟外走出來。
「會復元嗎?」高弘低聲問。
「我叫杜升。」這漢子從迷惘中醒過來,定了定神,與高弘握手。
「你的孩子長得很標致啊!」高弘湊個頭去瞧瞧。
「你以讓他居住你的房子三年,不用交租金的條件,來換取他負責你娘的一切殮葬費用。」許二牛說:「你當兵最少三年後才回來,這三年裡房子反正是空著的。」
那時候,台灣的經濟蕭條,人浮於事,到處是失業的人。高弘到處找工作都碰壁,有一次在街上跟幾個失業漢爭做一份伕力的臨時工發生齟齬,被圍毆致重傷。在飢寒交迫中,高弘母子倆得到好心的鄉親施捨冷飯殘羹,好不容易才把傷養好。每天,高弘仍在街上彷徨地四處找尋工作。傍晚回家的時候,母親聽到木門「嘎吱」一聲被推開,就吃力地用手肘支撐著身體,從病榻上偷偷地望向回家的兒子。當她見到他垂頭喪氣地走進來,知道他找工作又落空了,不禁轉身把面朝向牆上,躲在被窩裡暗暗淌淚……
他們回頭一看,原來李貴跟在後面監視他們。兩人把杜升扶進囚禁室裡,輕輕把他放在地上。
老軍醫欲言又止,最後無奈地嘆息一聲說:
「你們別問我為甚麼,只記著我的話就是了!」老軍醫說完揮揮手叫他們離開。
「崔老闆你爽快,我也爽快,你不用打賞我,就照徐夫子的規矩好了!」
「我叫許二牛——」站在旁邊的許二牛也向他伸出手:「我跟高弘是好兄弟。」
「你們早晚進去瞧瞧,如果發覺那廝死了,就把他的屍體扛到山上埋葬算了!」
「你別管,娘叫你去抓,你就去吧!」高弘娘撥開他的手,背過身去。
這女人聽了,粉團似的胖臉上登時綻開笑容,連忙從櫃枱前走出來,態度變得友善說:「阿崔他就是忙於四出去找房子,你們有房子出賣嗎?房子在哪兒?」
「這https://m•hetubook.com•com個嘛——」許二牛臉上露出為難的表情。
他掀動被子替母親蓋好雙腳,在床前跪下來。他雙手扶著床沿,垂下頭,哽咽著說:
「觀音廟。」高弘淡然答道。
許二牛坐在他身旁,用竹枝輕輕挑著燃燒中的冥鏹,讓它們徹底燒成灰燼;僧人們繞著靈柩,一邊敲著木魚一邊唸經。
「娘,你放心好了!」許二牛微俯著身大聲說:「日本鬼子投降了,戰爭結束了!我們當兵是不會派去打仗的!」
「你說甚麼?」許二牛娘的耳朵有點聾,偏著頭大聲問。
觀音廟裡沒有燈光,只見擱在神龕前的兩盞油燈,那不太明亮的火苗在跳動。香爐上還沒有燒盡的香枝仍在裊裊地冒著灰煙。
「不然,你們會這麼關心他嗎?」老軍醫把杜升的手放回毛氈內,輕輕哼了一聲,淡淡答道。
「阿娘!你保重呀!」
走進來的是李貴。他揮了揮手,示意高弘和許二牛離開。跟著,他向老軍醫問道:「這廝死不了吧!」
這女人見到他們在店門外交頭接耳,望著自己竊竊私語,似乎有點不高興。她把在口裡咀嚼著的甘蔗渣滓往門外一吐,瞅著他們問道:「要買東西嗎?」
「願望倒是這樣。」許二牛輕輕嘆了一口氣,憬然說。
「昨天我聽別班裡的一個四川兵哥說——」許二牛站得無聊,把頭湊近高弘悄聲說:「在鎮裡有一間小旅舍,裡面有幾個漂亮的小妞兒。明天放假,我們兄弟倆去找她們快活快活好嗎?」
這時候,排長李貴聞訊趕到。一個戴著眼鏡的軍官從軍餉部裡走出來,把李貴招到他的身旁。他低聲向李貴說了些甚麼,李貴唯唯諾諾地點頭稱是。
「這才是一個好軍人!」
「那是安家費,你無家可安,自己不去花錢,拿去給誰?」
不過,自己當了兵之後,如果病中的母親有甚麼三長兩短,誰去照顧她呢?
這一天,高弘在街上跑了一個上午,找不到工作,沮喪地坐在河邊,狠狠把石子擲進河裡,發洩憋在心裡的鬱氣時,同村的失業青年——他兒時玩伴許二牛氣喘咻咻的跑過來對他說:「阿弘,好消息!好消息!」
「他媽的!把腳縮回去!」
「你不去,我獨個兒也不去。」許二牛搖搖頭說。
「老杜,你怎麼樣?聽到我說話沒有?」
醫療處那年老的軍醫正坐在一張竹椅上拉二胡,嘴裡哼著京曲。他見到幾個士兵抬著一個人進來,連忙住了口,放下二胡,審視昏迷中的杜升,問道:
「住口!」兩個衛兵向杜升叱喝著,用槍柄狠狠地砸他的腰背。
「阿弘,我家裡的人都答應讓我當兵,你問准了你娘沒有?」
當兵的生活是艱苦的,但他們為了逃避更艱苦的貧困生活而當兵。
李貴沒有理會高弘,只用鼻腔重重哼了一聲,又想舉腳往杜升的腳蹴過去。高弘連忙上前,俯身把杜升伸直的腳屈曲,好讓小囚室的門能掩合關上。
她發覺許二牛說話的時候,目光落在她開敞著衣領,露出來的白皙的脖子上。於是連忙放下手中的葵扇和甘蔗,動手把鬆脫了的衣領鈕扣扣上。跟著,她打量他們一下,蹙著眉問:「你們找他幹啥?」
金營長訓完話,王排長連忙走到台前,高聲喊道:「立正!」
高弘不想讓這些傷感的話說下去,於是連忙把話題岔開……
「停車!快停車!」
「是甚麼時候發放?」一直站在高弘背後的許二牛這時候打岔問。
這當兒,木門「咿呀」一聲給推開了。許二牛領著崔麻子走進來。
仍然沒有聽到杜升的回應。高弘感到事有蹊蹺,也不顧得囚禁室門口有一個水窪,連忙趴下身子,俯臥在污水裡,把頭湊近小活門前,往囚禁室裡面張望。
「那老人家是怎麼死的?」
「他媽的!」李貴氣惱地大聲道:「誰人會知道中央甚麼時候才把安家費發下來?」
高弘把嘴湊到她的耳邊,大聲再說一遍。她聽了,轉過頭來關憐地望站在身旁的許二牛一眼說:「我就是怕他太機靈惹禍!」
這當兒,他們突然聽到一陣哨子聲,只見操場旗杆下的司令台上,站著兩個國民黨軍官。
許二牛聞言惺忪地坐起來。他使勁地搖了搖腦袋,想把滯留在臉上的、濃濃的睡意抖掉。高弘眼看其他人都跑出營帳外去了,一時性急,上前硬生生地把他揪起來。
「娘,你怎麼啦?」高弘見母親神色有異,不禁納罕問。
國軍一三九旅二七八團的新兵到了豐原後,進行了一次整編。把在桃園、苗栗所招的一部份新兵,撥到台中的一四零旅去。目的是不讓太多台灣同一地區招募的新兵編在同一軍團,防範他們聯群違反軍令,甚至叛變。
「我已經告訴了他。」高弘向許二牛仰了仰下巴答道。許二牛連忙對高弘暗暗打個眼色,然後對他說:
「還有,你們要記著:以後每次聽到或說到蔣委員長的名字,都要馬上立正,表示我們對領袖的尊敬。」
「現在請金營長給大家訓話!」
他把額頭擱在床沿,低聲飲泣著。不知經過多少時候,淚乾了,他感到腦海一片空白。
這時候,他們見到那些從軍餉部領完餉銀走出來的士兵們,都在交頭接耳,面露敢怒不敢言的表情。
「他說你要把這房子出租,是嗎?」
他把鈔紙遞給崔麻子,請他過目。崔麻子識字不多,但他見到這張鈔紙跟自己五金店的屋契是同一個模樣,上面蓋著「台灣省政府」的大紅印章,知道它不會假的了。於是,他向高弘問道:
士兵紛紛從席地的床鋪上跳起來。高弘發覺剛躺下睡著不久的許二牛翻了翻身,把被子掀起蒙著頭腦,響著鼻鼾繼續熟睡如故。
「我娘對我說——」許二牛搔著腦袋:「兒呀!你不認識字,性情魯莽,幹甚麼也得找個伴兒。」
「凌晨四點鐘了!」許二牛跟著詛咒道:「他媽的烏龜王八蛋!」
「因為我娘昨晚死了。」高弘傷感地說:「我需要錢作殮葬費用,希望長官格外開恩。」
站在營帳外偷聽的高弘和許二牛慌忙走開。
「她是那天晚上我們去觀音廟的時候,在學校門口碰見的女人。」許二牛把嘴湊到高弘耳邊,悄聲說。
「這女人就是崔麻子要娶的寡婦。」許二牛把嘴湊到高弘的耳邊說。
「你先照顧自己吧!」許二牛打斷他的話說。
「……」崔麻子猶豫著。
李貴瞪著眼睛朝聲音的方向望過去,大聲道:「發問的是誰?站出來!」
高弘離遠瞥見杜升第一個走進軍餉部。許二牛跟在高弘的背後,他也掩不住興奮的心情。咧著嘴向高弘說:
「報告排長,杜升在囚室裡一動也不動,看來病得快要死了!」
「那三千塊錢安家費你如何去花掉?」
「我的肚子還不餓,你快點去吧!往觀音廟的路程不短喲!」高弘娘從被窩裡伸出手來揮了揮,催促地說。
「我是醫生,難道用槍柄打傷的痕迹會看不出來嗎?」老軍醫理直氣壯地說:「我反對濫用職權傷害部下,對待俘虜也該用人道精神,何況是自己人!」
「你聽到了吧!我們當兵的決定是正確的,吃得飽,穿得暖!」
「你怎麼會知道?」許二牛納罕問。
「你想把房子租給我三年,是嗎?」
「……」許二牛抓著耳朵,窘得答不出話來。
「崔老闆,這完全是為你好!」許二牛煞有介事說:「你也該聽過『種善因,得善果』這句話吧?」
「有關遲發安家費問題,你有甚麼意見嗎?」說話的時候,眼鏡玻璃片後的小眼睛直勾勾盯著高弘,等待他的回答。
可是,司機並沒有聽到他的喊聲。或者,聽到了也不理會他,車子繼續啣跟著車龍往前駛,愈來愈快。
「甚麼辦法?」
他們替杜升穿好衣服後,老軍醫把一張灰色的毛氈蓋在杜升的身上。跟著,他用手指撐開杜升的眼皮,用手電筒照照他的眼瞳。然後,他戴上聽診器,微側著頭,聚精會神地細聽他的心跳。
他們見到杜升雙手被反扣在背後,卻不斷回過頭去大聲漫罵:
僧人、仵工和崔麻子都下山了,只有許二牛坐在墓旁野草上陪伴他。暮色悄然而至,這荒塚處處的山頭上籠罩著灰色的蒼茫……
「到觀音廟去占卜問卦,由觀音菩薩指點迷津來決定去不去當兵?對嗎?」許二牛睜大眼睛,好奇問。
「知道!」台下齊聲喊道。
徐夫子在街尾的半爿小店裡,專門替人占卜擇日、寫信及介紹婚姻、職業、房地產買賣等生意。聽說崔麻子那個快要跟他結婚的寡婦,也是徐夫子扯紅線的。
高弘似明非明的點點頭。許二牛卻仍是一臉迷惘。
對岸是一畦畦菜地,兩個頭戴竹帽的男女,在烈日下到河邊挑水澆菜。菜地旁有間用泥磚蓋成的、破舊的小屋,屋頂的煙囪正冒著灰色的炊煙。
同時,每一個排或班,都由一個外省士兵當排長或班長,以他們來管制或監視台灣新兵。
他說著的時候,精矍的眼睛狠狠地瞪許二牛一下。許二牛登時噤若寒蟬,不敢作聲。
「明白!」這回二百多把聲音一齊喊出,聲勢浩大,站在校門外圍觀的人也給這驟然響起的喊聲嚇得一跳。
「只怕是講一套,做一套。」高弘悄聲說。
天上還飄著細雨。高弘脫下軍帽蓋在盛著稀飯的碗上,不讓雨水滲進稀飯裡。
高弘此刻心情平靜。他心底裡感激崔麻子。母親能够獲得這樣的葬禮,在九泉之下應該得到安息了。
高弘搖搖手表示自己不吸煙。他又遞給許二牛,許二牛同樣婉拒了。最後,他把香煙叼在自己的嘴裡。高弘連忙拿起桌上的火柴來為他點燃香煙。
只見他悶哼一聲,整個人稀泥似的癱在地上,嘴角滲出殷紅的血。高弘見狀連忙飛跑過去。
「好啦好啦!就這樣辦吧!」崔麻子急不及待,催促他起行。
「甚麼辦法?」高弘停下步來。
老軍醫正在替杜升注射針藥。
「小弟叫高弘,老兄貴姓大名?」
站在隊伍中的許二牛伸手拍了一下高弘的大腿,喜孜孜地對他說:
金營長停下話來,伸出舌頭來舐一下乾燥的大嘴唇,又掏出手帕來,揭起軍帽,揩拭一下他那光禿得發亮、熱汗涔涔的腦袋。
「我們國軍是軍令如山的,怎會這樣做!」瘦排長正色地大聲道。
高弘瞥見小屋裡走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人來。這老婦人站在門口,把手放到嘴前作喇叭筒,高聲向那兩個挑水澆菜的男女喊道:
「嚴重的內傷,還染了肺炎。」
「為甚麼?」
「你相信嗎?」
「不過,份屬和-圖-書同鄉能互相關心,已經是很難得了!」老軍醫把老花眼鏡扔在桌子上,在椅子上坐下,喟嘆一聲:「在這亂世裡,誰不為自己打算?」
「你罵誰?」
幽幽的月光灑在廟內天井的大石板地台上,予人一種冷清清的、空寞的感覺。
「崔老闆,我們到外面談談好嗎?」
「你——」那國民黨兵面色陡變,霍地站起身,正想跟高弘說些甚麼的時候,坐在他身旁的另一個年約四十歲,樣子瘦削的國民黨兵排長伸手拉了一下。他把滑到嘴邊的話嚥回去。
高弘用白眼窩許二牛一下,一聲不響,站起來推門準備跨進去,不料他赫然發覺母親原來顫巍巍的站在門內,面色蒼白如紙。
「讓我娘跟你娘一起居住,她們不是可以互相照顧嗎?」許二牛說。
他俯低身想伸手扶起杜升,眼前倏地閃過兩道銀光,兩把長槍上的刺刀直刺到他的面前。他給嚇一跳,本能地退了一步。
許二牛乘機打蛇隨棍上,呵諛地笑著說:
「崔麻子一向是住在店子裡,聽說他娶的新娘子是個來自台南的寡婦。」許二牛滔滔地說:「這寡婦帶著兩個與前夫生的女兒,她下嫁崔麻子的條件中,聲明要有一個像樣的家,不要住在堆滿貨物的、亂七八糟的五金店裡。所以,崔麻子最近到處打探租賃房子的事兒。」
「發生了甚麼事?」在排隊士兵面面相覷,七嘴八舌地嚷起來。
崔麻子抬頭望了望,見到站在面前的是常到店子來要求做搬運散工的小夥子,沒待許二牛再開聲,就揮揮手示意他走開,說道:
「我娘說,用香爐灰洗三次臉,她的病就會痊癒了。」
這時候,高弘盯著照片,正看得入神。
「為甚麼要去花掉?」高弘白他一眼,反問道。
「說實在的,你那女人胖胖白白的,老人家說這是好生養的型格,將來一定能够替你生幾個胖嘟嘟的兒子。」
母親葬在父親的墳墓的旁邊,這是她老人家生前閒聊時,常向他提出這個願望:「兒呀,你爹在你三歲的時候去了。在世間有你與我相依為命,你爹在地府孤零零的一定很寂寞。你記著,他日我去世後,你一定要把我和你爹葬在一起……」
「我們該怎麼辦呢?」高弘憂心忡忡問許二牛。
戴眼鏡的軍官聽了點點頭,嘴角牽著一絲冷冷的笑意說:
他們認得其中一個高瘦的,正是報名時見過的瘦排長。高弘聽見過士兵叫他王排長。另外那個身材較矮,臉上長著紅彤彤的酒糟鼻子的軍官,他們沒見過。
許二牛說得咬牙切齒。原來,日間發放軍餉的時候,林副官在試探每一個士兵的態度。凡是對於不發安家費有怨言者,林副官都暗中通知李貴,命令他們晚上進行額外的挖戰壕訓練,以此作為懲罰。
趙軍醫搖搖頭,欲言又止,結果還是顧左右而言他……
老軍醫叫趙正,上海人,本來是上海市的執業醫生。抗日戰爭開始,他和剛從醫學院畢業的兒子毅然參加抗日救國的行列。家裡留下老婆和一個十二歲的女兒。
許二牛心裡暗喜,重新走到高弘面前,裝模作樣地說:
「老弟,雖然你沒有去嫖妓,但你也不是我的東床快婿人選!」
「娘!娘!你為甚麼要這樣做?為甚麼?」
高弘娘搖搖頭,伸出瘦稜得皮包骨、枯枝似的手來捉住兒子的手,噙在眼眶裡的淚水又一次泫然而下。
「你要香爐灰幹甚麼?」
高弘和許二牛聞言連忙把杜升攙扶起來。杜升眼睛半闔,「啊」的一聲,嘴裡吐出一口鮮血。他渾身乏力,雙腳無法提起來,要由高弘和許二牛合力半扛半拉地扶著他,往操場旁邊的囚禁室走去。
「你去當兵,家裡有哥哥及嫂子照顧你娘,我當了兵,誰照顧我娘?」高弘反問道。
高弘輕輕地掩上門,把腳從門檻內縮回來,然後瞪許二牛一眼,怨懟說:
「他怎麼啦?」
一清早,人們就見到四、五輛大卡車停在學校門外。學校門口有兩個背著長槍的國民黨兵在守衛著。到來報到的人,必須出示報名時發給的證明,才獲准放行進校內。
「娘,你甚麼地方不舒服?」高弘俯身關切地問。
「你跑到觀音廟來,就是為了抓幾把香爐灰嗎?」
在高弘和許二牛合力迅速脫去杜升身上的衣服時,老軍醫把一件乾淨的病人衣服扔過來說:「快點給他穿上!」
高弘回到家裡,掩上門,坐到寂然躺在床上的、母親的屍體旁邊。
其實,從照片中並看不清楚他兒子的眼睛是怎樣的。但高弘還是煞有介事地瞧瞧照片,又瞧瞧這漢子,然後附和說:
「經徐夫子辦的事情要不讓別人知道才怪!」許二牛說:「如果你不速戰速決,把那女人娶進門來,難保徐夫子不把她介紹給別人。」
「為甚麼?」許二牛錯愕問:「剛才我們不是說好了一起去當兵的嗎?」
「娘,你餓嗎?」
高弘靦腆地笑了笑。
「為甚麼?」高弘納罕地問。
高弘和許二牛一起來報到。許二牛的娘、哥哥和嫂子到來送行。許二牛的娘拉著高弘的手,老眼閃著淚光說:「阿牛不識字,做事魯莽,希望你處處要指點他。」
「娘,我知道了!」許二牛的眼眶紅了。為了不讓母親發覺自己的表情,他連忙轉過身去,緊握著哥哥的手說:「大哥,娘要你和嫂子照顧了!」
當高弘和許二牛協助把杜升的身體推側,讓老軍醫用聽筒按在他背部診聽的時候,發覺他的背部一片瘀黑,不禁抬起頭來向高弘問道:
李貴雙手按著門框,伸腳往杜升的大腿上蹴了一下,叱喝道:「站起來!」
「你沒聽到金營長說過,退伍後我們將獲得介紹職業嗎?」
「這要看他的運氣了。」老軍醫點點頭說:「我給他注射了針藥,讓他好好地安睡。」
茶客中有人在高談闊論日本投降後的國內政治形勢,有人在談論著一些外國企業倒閉的消息;也有人談論國民黨軍隊招募士兵的情況,和宋美齡已經悄悄從南京乘飛機遠走美國的傳聞。
「到山邊的觀音廟去,替我抓一把香爐灰回來。」高弘娘嚥了一口口水說。
這一天是第一次發軍餉的日子。陸軍最低軍階的二等兵,每月的軍餉是台幣二百元。同時,每名士兵每月可獲發香煙一百五十支,即每日五支。
老軍醫望著他,示意他說出來。
高弘想著、想著,鼻腔一熱,眼前的景物都模糊了。他從對岸那小屋煙囪冒出來的炊煙,想起昨晚從觀音廟回家時,竈膛裡未熄的灰燼。原來母親臨上吊之前,還把那個冷硬的饅頭放到鐵鍋裡蒸軟,以便他回家時果腹……
「甚麼怎麼辦?」
「你的意思是要我把房子賣給崔麻子?」高弘睜大眼睛問。
父子兩人隸屬不同軍團當軍醫,兒子參軍不足一個月,就在一次戰役中犧牲了。趙正從抗日戰爭開始,直到戰爭結束,又給遣派到台灣來,差不多十年了,還沒有回上海見過老妻和女兒。
高弘、許二牛和杜升幸運地給編在同一個排。而高弘和許二牛更湊巧編在同一個班裡。
「趙醫生,這廝曾到小旅舍去嫖妓,可能身染梅毒,千萬別把女兒許配給他!」杜升指著許二牛笑著說。
「你去了當兵,留下我們母子倆,以後生活如何度過?」那婦人哭著說。
高弘伸手去趕走牠們,拂動了在陽光中浮游的塵埃。
「你們把他扛進囚禁室去!」
「營長!」王排長馬上立正答道:「你講到『執行保衛台灣省的任務』——」
「你還沒讓你娘知道?」
崔麻子一進門就四處張望。
可是,裡面一點聲息也沒有。
「沒甚麼,我聽見門外有人說話的聲音,想開門瞧瞧……」高弘娘說到這裡,氣喘得嗆了起來。
「你可不要讓她知道嘛!」
杜升一動也不動,完全沒有反應。高弘也不顧得李貴准不准許,從他的脇下擠進狹小的囚室去。
許二牛瞥見母親和兄嫂站在人群中向他揮手。他見到母親垂下頭,揪著衣袖來揩淚水,登時感觸得眼眶紅了,忍不住揮動手大聲喊道:
王排長說到「蔣委員長」的時候,自己也霍地立正致敬。跟著他又大聲問:「你們知道沒有?」
老軍醫淡然笑了笑。他拿起擺在桌子上的香煙包,拈了一枝遞給高弘。
「我不去當兵了!」高弘嘆了一口氣說。
「你怎麼會知道是用槍柄打的?」李貴嘻皮笑臉問。
從人叢中鑽出來,高弘既喜又愁,腦海裡忽然感到一片紊亂。他暗暗思量:當了兵可以領取三千塊錢安家費,最低限度令母親一年半載不用捱餓。而且,三年後可以有就業機會,這無疑是一條絕處逢生的路。
台上的王排長滿意地點點頭,繼續說下去:
「你先回家等我,先讓我單獨跟崔麻子談好了,才帶他到你家裡去。」
「幹啥用的?」許二牛好奇問。
高弘身旁的漢子惘然地把揮動的手垂下來,低頭瞧著手中的照片。照片中是一對年輕夫婦,女的懷裡抱著一個嬰兒。
金營長抹完腦袋,把手帕放回褲兜後,目光不停在搜索剛才講到甚麼地方。王排長見狀,連忙上前再次悄聲提示他:
許二牛與高弘交換一下眼色。許二牛搶著答:「房子離這兒不遠,待我們見到崔老闆後才詳細談談吧!」
訓練完畢,除了四個負責指揮、身穿雨衣的排長外,其餘的士兵都彷彿一個個泥人似的,筋疲力竭地回到營地來。
「李貴和那個林副官。」
喊聲過了五秒,台下的新兵才相繼地懂得併腿立正身子。
說話間,他們經過學校門口,看見那抱著嬰兒的婦人仍站在那裡。她露出半邊乳|房在餵著懷裡的孩子,她的男人不在她的身邊。
「我知道嫂子對娘不太孝順。」
翌日。高弘一清早就和許二牛跑到「國軍招募處」報名當兵。
二十四歲的高弘本來在台南玉井石頭崎的「日本石油株式會社」工作,因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石油公司倒閉,他就離開台南,回到苗栗老家去與多病的母親相依為命。
吃過午飯,李貴命令高弘把一碗浮著幾片菜葉的稀飯,端給囚禁室裡的杜升。
高弘跨出門檻,掩上破木門。回過身來,他發覺許二牛靠在一堵破牆上,嘴角咬著一根枯草,光著的腳在撥弄著面前的泥土,一副百無聊賴的表情。
「聽到崔老闆你四出託人,急著要找房子的時候,我就到處奔跑打聽,也花了不少時間和勞力,所以——」許二牛裝著傻兮兮的表情說:「希望老闆你事成後,意思意思。」
崔麻子似乎有點猶豫不決。許二牛把握時機慫恿他:
「啥事兒?」崔
和圖書麻子滿是瘢痕的臉上露出疑信參半的表情。這小鎮裡唯一的茶室雖然簡陋,但偌大的地方都坐滿了茶客。那喧嚷的聲浪令人彷彿走進嗡嗡作響的蜂巢裡。
李貴怒目向士兵掃視一遍後,從汽油桶上跳下來,走回軍餉部去。
「你輕聲一點好嗎?」
高弘點點頭。
「他要結婚跟我沒錢下葬我娘是兩碼子事,有甚麼關係?」高弘沒精打彩地說。
高弘瞟他一眼,想了想,說道:
兩人匆匆地來到崔麻子的五金店門前。他們往店內張望,見不到崔麻子,只見一個約莫三十多歲的婦人坐在櫃枱旁,一邊不停地搖動著手中的葵扇,一邊啃著甘蔗。
「你別胡說!」高弘瞪他一眼,沉著面色悄聲說:「小心槍斃你!」
「行嗎?」
崔麻子猶豫著想站起來,徐夫子倏地把長煙斗伸過來按住他,抬起頭來對許二牛說:
「你怕你爹娘在九泉之下責怪你嗎?」許二牛笑了笑說:「你不是把賣房子的錢拿去嫖去賭嘛!」
「老杜得不到治療,一定會——」高弘憂慮說。
士兵興奮的原因,是今天除了領取頭一個月的軍餉外,還可以獲得發放三千元台幣的安家費。
他用手推了推滑到鼻翼上的眼鏡,向剛接過軍餉的高弘問道:
台下響起零星的回應聲。
高弘依稀聽到軍餉部內傳出吵架聲。不旋踵,見到兩個站崗的衛兵匆匆跑進軍餉部去。
許二牛見他不再吭聲,伸手推推他的胳膊說:
「喔!有了!」許二牛突有所悟說,跟著站起來:「我們去找崔麻子談談!」
金營長在台下全體新兵立正行禮致敬中,步下司令台。眾人目送他在兩個馬弁的護衛下,鑽進停在操場旁邊的一輛吉普車裡。
高弘沒有再流淚。他默默地跪在母親靈柩的旁邊,燃燒著一大堆冥鏹。
許二牛聞言登時伸伸舌頭,不敢再作聲。
「崔老闆,聽說那皮細肉白的婦人現在還不是你的女人,要是你十天內還找不到房子,她就帶著兩個女兒回台南去了,對嗎?」許二牛瞅著她說。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他的老婆還年輕,年輕的女人在亂世中容易掙扎求存,不等於我可以離開我年老的娘去當兵。」
「聽說鎮上那五金店的老闆崔麻子要結婚了。」
高弘不理會他,逕自趕路去。走了不久,他聽見背後傳來腳步聲,回頭一看,原來許二牛趕上來了。
崔麻子靠在門上,百無聊賴地看著。後來,他似乎有點不耐煩地離開。過了好一會,他從外面走回來,手中拿著一把木尺。他不時搔著腦袋,用木尺量度這裡、又量度那裡,思量著如何修葺他的新房子。
「為甚麼?」許二牛睜大眼睛問。
在場的人及軍車上的新兵都用驚訝的目光望著她。高弘身旁的一個漢子倏地把身子伸出車外,向那婦人大聲喊道:
「我就是不放心讓娘獨個兒留在家裡。」高弘抬起頭,眼睛紅了。
「崔老闆,這是一個難得的種善積福的機會。」許二牛打斷他的話,繼續游說他:「這樣,你們住在這房子裡,神靈會保佑你家老少平安。而且,假如你錯過這個機會,恐怕你連娶媳婦的機會也失去。」
這女人告訴他們,崔麻子約了朋友在街頭拐彎處那間「福昇茶室」見面。兩人聽罷匆匆往街頭跑去。在茶室門口,許二牛若有所悟地拉停了高弘。對他說:
「你說沒有發放安家費,是真的嗎?」許二牛問。
老軍醫站起身來,分別在高弘和許二牛的膀子上拍了拍,悄聲說:
高弘沒吭聲,雙手抱著小腿,下巴擱在膝蓋上,怔怔地望著那緩緩流向遠處的河水發愣。
高弘回過頭,發覺許二牛在偷望自己,知道他在想著甚麼,於是搖頭嘆了一口氣說:
這時節,通往學校的路上,行人絡繹不絕,都是一些送親人入伍的親屬。學校門外的空地上,人群擠得水洩不通。叮嚀、低泣、擁抱和依依不捨的揮手,構成一幅令人傷感的圖畫。
「不行!」瘦排長冷冷說:「我們當軍人的要服從命令,一視同仁!」說完,他揮了揮手示意高弘走開,讓下一個人報名。
「老杜,你怎麼啦?」高弘大聲問道。
「要是讓我女人知道,她一定不喜歡的。」崔麻子為難地說。
這天是新兵報到的日子。
許二牛搖搖頭:「嫂子很懂得門面功夫,表面上是個孝順的媳婦,暗地裡常欺負娘。」
「崔老闆,這回不是向你求工作。」許二牛咧著嘴笑著說:「是一樁你喜歡聽到的事兒。」
他跌跌撞撞的爬起來,上前把懸在樑上的母親抱下來,他抱著母親往門口跑,把母親的腦袋輕輕地擱在門檻上,大力搖撼著她已經冰冷了的身體,哭喊道:
「不,是——」高弘正想說出杜升受傷原因的時候,瞥見營帳給人撥開,有人走進來,他連忙把滑到唇邊的話卡住。
士兵們又是一陣低聲的議論,沒有人敢再發問。
許二牛認得這個老頭子,他的姓名沒多少人知道,人們都叫他做徐夫子。
高弘見到許二牛在廟門口等候他,不禁好奇問:
「老兄,我雖然跟你不認識,但見你一片孝心,出租房子葬母,所以我為你跟這位崔老闆說了許多好話。崔老闆是個樂善好施的大好人,他完全同意你提出的條件,兩天內替你把母親下葬,用上好的棺木,請僧人做法事,令她老人家風風光光的到另一個樂世界去。而且——」
台下響起了一陣雷似的鼓掌聲。
「娘!」他驚駭地叫起來,扔下紙條,往窗前撲過去。他給一張橫臥在地上的木板櫈絆著,一個踉蹌,整個人裁倒在地上。
坐在旁邊的徐夫子,吸吐著煙,用冷眼瞅著許二牛。
「你怎麼會知道?」崔麻子納罕地問。
「關於房子的事。」許二牛說。
「作白日夢!」高弘啐了一口說。
「那房子剛死了人,怎能用來當結婚的新房子?」崔麻子停下步來,瞪著許二牛。
「這個沒問題。」崔麻子拍拍他的肩膊,笑著說:「事成後我會給你賞錢。」
許二牛說到這裡,崔麻子乍地一手拉著他往門外走,不讓他說下去。
許二牛舉目張望,輕易地找到崔麻子那個半禿的腦袋。他見到崔麻子正在跟一個叼著長煙斗的老頭子在一起。
崔麻子翹起的屁股重新在椅子上坐下,對許二牛說道:「說吧!是甚麼事兒?」
雖然她的眼球微突,舌頭外露,但她的神情仍是安詳的。月色下,高弘清楚見到母親皺紋斑駁的臉上,留下了兩行淚痕……
許二牛沒有吭聲,在默默地抽著煙。煙火驟亮間,可見到他那黧黑的臉上緊蹙著的輪廓。
這時節,母親偶爾的嗆咳聲從門縫中隱約地傳出來。過了一會,他無助地嘆了一口氣,雙手按著膝蓋慵倦地站起來。當他轉身推開門,準備跨進門檻的時候,突然聽到許二牛興沖沖的在背後叫他:
「他是甚麼模樣的?」許二牛好奇問。
「甚麼事?」
高弘重新坐在門檻上,把沉甸甸、彷彿灌滿了鉛的腦袋垂得低低的。
「因為——」瘦排長和顏悅色的對他說:「有許多青年不是真心報國從軍,他們往往是為了騙取安家費還賭債而報名當兵的,所以,安家費一定要入營後才發放。」
許二牛偷偷望高弘一眼,心裡暗忖:原來他說到觀音廟來,其實早知道這裡有招募站,到這裡來報名當兵。想著,他的嘴角不期然泛起笑意。
「老杜,你的女人這麼漂亮,兒子這麼小,你怎麼這般狠心,捨得離開他們?」許二牛向杜升問道。
許二牛望望崔麻子,又望望徐夫子,想了想,然後對崔麻子說:
「唉——」許二牛嘆了一口氣,在他的身邊蹲下來。
許二牛把嘴湊到高弘的耳畔,低聲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地說著,高弘一邊聽,一邊睜大眼睛不停地搖頭,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聽完,他大力拍了拍許二牛的胳膊笑起來說:「你這人詭計多端!」
吉普車噴了一股黑煙,怒吼一聲,朝校門外駛出去。許二牛轉過頭來低聲對高弘說:
他說著的時候偷偷向高弘打眼色。語音甫下,他暗暗伸手推高弘一把。
「嗯。」許二牛悻然說:「他是團部派下來押軍餉的,是個奸險小人!」
「甚麼時候才有安家費發放?」排隊的人龍中有人高聲問道。但說話的人卻不敢站出來。
「那麼你快點帶我去瞧瞧房子!」
「是杜升!」高弘和許二牛異口同聲、驚愕地叫起來。
老軍醫微低著頭,目光從老花眼鏡上的空隙望高弘和許二牛一眼,問道:
「我留下來,一家三口都會餓死。我去當兵,你和孩子有三千塊錢安家費,不用再捱餓。現在的時勢,還有甚麼比這更好的出路?」
「嗯。」
黝暗裡,高弘隱約見到杜升的嘴巴翕動了一下,但似乎沒有氣力說出聲音來。他見狀連忙爬起來,飛快地跑去向李貴報告:
這當兒,人龍突然起了騷動,排隊的士兵都把目光投向龍頭那邊。
許二牛興致勃勃,領著高弘飛快地往大街跑。高弘果然見到路邊那堵灰水剝落的破牆前,站滿圍觀的人。他們從人叢中擠了進去。只見一張蓋了大紅印章的、台灣省政府招募新兵的佈告貼在牆上。高弘仔細讀了一遍,內容跟許二牛所說一樣。
「醫生,他怎麼樣?有生命危險嗎?」高弘趨前望了望杜升,向老軍醫問道。
婦人住了哭,鬆了扣在胸前的、揹帶的結,右手往後一抄,就把嬰兒抱到懷裡來。跟著,她利落地伸手解開鈕扣,敞著一個呈現青筋的乳|房,把黑棗子似的乳|頭往嬰兒的嘴裡一塞,哭聲就停止了。
一時間兩人都緘默了。
與許二牛別過後,高弘心情忡忡在河邊呆了許久,直到太陽在遠山漸漸隱沒,他才怏怏地踱回家。
他想起自己在台南工作的日子,每次放假回家探望母親的時候,她老人家總會嘮嘮叨叨的說個不停,要他早日娶個媳婦回來。
聽許二牛說完,崔麻子搔搔半禿的腦袋,考慮了片晌,最後終於點頭答應了。
「沒有工作給你做!」
台下又響起了一陣哄笑。
高弘想再說話,但給許二牛在旁扯了扯他的衣袖,他把話吞回肚子裡去。
「趙醫生,她許配了人家沒有?」許二牛問。
塵埃在高弘的眼前飛舞。一滴又一滴熱淚從他的眼眶滑下來。
杜升在老軍醫悉心的治療下,病情有了顯著的好轉。高弘和許二牛常溜進醫療處去探問杜升。原來,老軍醫暗中叫杜升繼續裝重病躺在病床上療養。因為,如果一旦被發覺病情好轉的話,每天到來視察的李貴一定會再次把他關進囚室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