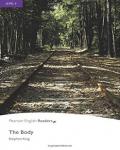Ⅵ
柯里終於說道:「他們會說出去。」
「戈弟,到哪兒去了?」
「戈弟,你呢?」馬瑞爾問道;他輕扯著查理的胳臂,跟經驗老到的馴狗人管著兇狠的惡犬一樣。「你起碼有點像你聰明的哥哥,你叫他們放棄,我讓查理稍稍修理一下那個四眼田雞,然後我們各幹各的。你看如何?」
「沒你那麼想。」柯里說道,他的臉色蒼白得可怕,雙目炯炯有神,彷彿全副生命都已投注在眼睛上。
「快滾!」柯里高聲喊著,一邊舉起手槍。馬瑞爾朝後退。
「是嗎?好,你試試看!」泰迪突然大發威風,他的眼睛在淋濕的鏡片後閃著瘋狂的光芒。「來啊!這一架我替他打!來啊!快啊!大個子!」
我點頭,這樣大概還可以,只要魏恩與泰迪不|穿幫就好。
「好了,現在怎麼樣?」馬瑞爾問。
我們身後的枝葉開始沙沙作響,我猛地一轉身,難道他們真的包抄過來了,但是柯里只是蠻不在意地瞄了一眼,又繼續專心想著布勞爾的屍體。來人是魏恩與泰迪,他們的牛仔褲已浸得濕濕的,緊緊黏在大腿上。兩人都曖昧地笑著。
我們又一言不發地走過另一條街。
我全身發冷,我並沒有像剛才在鐵軌上那樣嚇得尿了一身,不過那一定是因為此刻沒東西好尿。你知道,他說的話可都是當真的;多年來,我對許多事都已改變看法,但這件事是例外。當馬瑞爾說要折斷我兩隻胳臂時,這話絕對當真。
「他們是孬種!」泰迪反唇相譏,「魏恩都告訴我們了!他們根本孬到家了!」他扭曲著臉,模仿嚇得痛哭流涕的查理。「真希望我們沒偷那輛車!真希望我們沒到赫婁路!噢,比利,我們該怎麼辦?噢,比利,好可怕!噢!比利——」
「去他的!我要走過去,如果被火車撞了也好,不必再擔心馬瑞爾那個傢伙了。」
「戈弟說得對,你們只是一票下流的太保!查理跟比利根本不想要他們的優先權,這點你們都知道,否則我們也不會走那麼遠的路到這地方來。而他們只不過在別的地方洩漏了他們的大祕密,讓馬瑞爾替他們想辦法。」可他的聲音轉為聲嘶力竭的高喊,「是你們別想碰他,聽見沒?」
「你們現在聽著,」馬瑞爾說道,他耐著性子說著,好像我們不是站在滂沱大雨中似的。「我們的人數比你們多,塊頭也比你們大,現在我給你們一個滾開的機會,我不管你們到什麼地方去,只管給我乖乖走開。」
29
「當然值得。」我說。
「聽著,」馬瑞爾說道,「你最好在拔腿開溜之前先把那東西放下,我看你連射一隻土撥鼠的膽子也沒有!」他又開始向前走,臉上仍掛著溫柔的微笑。「你們只是一夥裝腔作勢的小渾球,我會叫你把那支他媽的槍吃掉!」
這時我們都已經站起來準備動身了。鳥兒瘋也似地叫著,我想牠們大概對雨、對陽光、對蟲子以及萬事萬物都感到愉快吧!然後我們像被人操縱的傀儡一樣,不約而同地回頭望著布勞爾。
「你走開,」他顫聲說道,「是我們發現的,我們有優先權。」
凸眼蛇憤怒地發出一個模糊的聲音,同時開始向前走來,柯里開槍射擊他前方十呎的水中,水波飛濺。凸眼蛇急忙跳開,嘴裡不停地詛咒。
天啊!這聲音多美妙啊!查理蹦得老高,兩眼直勾勾盯著我的馬瑞爾也倏地轉頭看柯里,一張嘴張大成圓形;凸眼蛇根本是一臉驚愕莫名。
我用食指摩擦拇指。「這是全世界最小的小提琴,演奏的歌曲是『我的心為你排出紫色的尿』。」
柯里的哥哥哈哈笑著,伯考維拍拍馬瑞爾的背,表示欣賞他的聰明才智。
他好像去了好長一段時間,我都開始認定他被躲在林子裡的馬瑞爾或凸眼蛇抓住了。我站在原地,只有布勞爾的屍體陪伴我等待有人——任何人——回來。過了一會兒,柯里回來了。
他們再度走進沼澤地和馬路之間的重重樹林中;柯里與我仍然紋絲不動地佇立原地,也不管不斷打在身上的冰雹,任它打紅我們的皮膚,任它像夏雪一般堆積在我們周圍。我們凝神傾聽著,不久,在冰雹撞擊樹幹的狂亂聲響掩蓋之下,聽見了兩輛汽車的發動聲。
「我們回去吧。」柯里說道。
「好,我不亂講,」柯里說。
「我們該怎麼辦呢?」柯里問道。我覺得心中一陣戰慄,或許他是在對我說話,或許是對……但他仍然低頭望著屍體。
「你說得對。」魏恩應道,可是他的聲音聽來還是不太高興。
魏恩嚥了兩次口水,再也不吭聲了。
大男孩成橫列前進,他們的腳踏過泥沼,濺起水花(由於下大雨,那裡已變成泥水坑)。布勞爾的屍體躺在我們腳旁,像是汲足了水的水桶。我已準備好隨時應戰……就在這時候,柯里發射了從他老頭櫃子裡弄來的手槍。
「他們為了報復,會說任何不利於我們的話。」我告訴他。我的話聽來軟弱無力、而且愚蠢。「他們不惜說任何謊話,你是知道的,他們可以說出任何下三濫的話,到時我們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就像那個牛奶——」
「真的?」
回程我們幾乎是跑的,沒有人說話。我不知道別人的情形如何,但我卻忙著想事情,根本無暇說話;關於布勞爾的屍體,有一些事情令我感到不安——從當時一直到現在仍是如此。
泰迪的媽媽到了第二天晚上開始擔心,於是打電話給魏恩的媽媽,魏恩的媽媽說我們都還待在魏恩的帳篷裡,因為前一天晚上她還看見裡面有光;泰迪的媽又說希望沒有人在帳篷裡抽菸,魏恩的媽說她覺得是手電筒的光,何況她知道魏恩與比利的朋友都不會抽菸。
馬瑞爾漸漸恢復鎮定,臉上的肌肉又緊繃起來,他的嘴抿得緊緊的,而他看柯里的神情,就好像柯里剛剛認真提了個提案——要購併他的公司或處理他的貸款,或射斷他的命|根|子,是一種等待而近乎好奇的神情,令人覺得他若非已了無畏懼,就是掩藏得很好和-圖-書。馬瑞爾重新估計了他被槍擊的或然率,發現並不如原先想像的那麼對他有利,但他還是頗具危險性——或許比過去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後來我發覺這是我生平所見最生澀的一次心靈角力,他們倆都不是在唬人,而是玩真的。
「你有。」
「可是麥洛知道,」我說,「佛羅里達市場那個渾球也知道。」
「聽著,傻蛋,」柯里說道,「如果我們帶他回去,大家都會被關進感化院,就像戈弟說的那樣,那些傢伙可以隨心所欲編造任何謊言,如果他們說是我們殺了他怎麼辦?呃?你喜歡事情變成那樣嗎?」
他又注視柯里片刻,點點頭,然後轉身。「走吧。」他對其他人說道,然後,又轉頭看了柯里和我一眼。「後會有期。」
馬瑞爾的笑容倏然凍結。「我會因為這句話宰了你,沒有人敢損我媽。」
「嘿!幹嘛?」泰迪喊著,真急了,「我要帶他走!」
馬瑞爾詫異不已,嘴巴張成了大圓形——我的話的確太出乎人意料之外,若在其他場合,保準立刻廝殺起來,然而此時所有的人——兩方的人——都瞪眼看著我,說不出話來。
他緩緩地點頭。「我沒想到這些。戈弟,你有看透人心的本領。」
「你們甭想。」我說著,突然對他們感到極度憤恨,竟然在最後一刻就這樣冒出來了;如果我們曾經思考過,應該想到可能會發生這種事……但這一次我們不會讓年長力強的大孩子搶去我們辛苦的成果——不讓他們理所當然地巧取豪奪,彷彿抄捷徑是正確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他們是開車來的——我想這才是令我們最憤怒的地方,他們竟然開著車來。「凸眼蛇,我們有四個人,你給我試試看!」
「你少亂講了。」我說著,想把話說得強硬一些——我想到柯里在森林裡對我說的話:「也許我拿了錢到史老師面前認罪,也許那些錢一文也沒少,不過我還是放了三天假,因為那筆錢一直沒有出現。也許第二個星期史老太婆來上課的時候,身上穿的是一件全新的裙子……」還有當時他眼中的神情。
「我非去不可!你留下。」
「沒什麼,媽。」
我曾想再回去找找看——你會不會覺得我很變態?我曾想過在亮麗的夏天早晨,駕著我的新福特車到赫婁路的盡頭,然後下車走入林子。就我一個人,我的妻子跟小孩則在遠方的另一個世界裡,只要按下電燈開關便能驅走黑暗、迎向光明的世界。我想過情形將是如何。我會拿出背包,把背包擱在車後的保險桿上,同時小心地脫下襯衫扎在腰際,在胸膛與肩膀上塗滿防蟲油,然後穿過森林到那塊低漥的沼澤地,也就是我們發現他的地方。他躺的地方會不會順著身體的形狀長出黃草?當然不會,當然是了無痕跡,不過你還是想知道,這時你就會發覺在理性成年男人的外衣之下——身穿楞條花布西裝、手肘處打著皮補釘的作家內心——仍然懷念著兒時各種古靈精怪的幻想。然後我再攀上如今已長滿雜草的堤防,慢慢地在通往錢伯倫鎮的腐朽鐵軌旁踱步。
「去你的優先權,我們要去報警。」
我們走到了我家那條街的街角,於是兩人停下腳步。時間是六點十五分,我們可看見鎮中心的送報車在泰迪叔叔的文具店前停下,一個身穿牛仔褲與T恤衫的男人丟下一綑報紙,報紙翻了個身摔在地上,露出漫畫版(通常首頁都是白朗黛和狄克崔西漫畫)。不久車子開走,它還有好幾站得跑。我還想對柯里說些話,但不知該如何開口。
但是馬瑞爾卻拍拍他們的肩膀,不讓比利與查理上前。
「嗯,我們就說是麥洛把我們嚇得半死,大家才決定去布列山露營。」
我往左移,過了一兩分鐘,兩枚彈殼都找到了,在剛冒出來的陽光下閃著光。我把彈殼給了柯里,他點點頭,把東西塞進他的褲袋裡。
我脫下襯衫,把它丟在洗衣機後面的塑膠籃裡,然後從洗手臺下拿了一塊乾淨的布往身上擦抹一臉、頸子、腋窩、肚子,然後我拉下褲子的拉鏈,使勁擦我的私處——一直擦到皮膚腫痛為止。儘管吸血蟲留下的紅色痕跡迅即消失,但我總覺得好像永遠擦不乾淨似的,直到現在,那地方還有小小的新月形疤痕,有一回我太太問起,我竟毫不思索地就隨便撒了個謊。
我點頭。又過了五分鐘,沒有人講話,我突然想到——我們總得防患於未然,免得他們真的報了警。我又跳下堤防,到柯里原先站著的地方,然後跪下來,用手指在水草與泥漿中撈著。
「我想在你左邊。」柯里說著用手指了指。
「柯里,就照你的意思做。」
「不過我們會找你算賬。」馬瑞爾說道,他又開始露出微笑,「你不會不知道吧?」
「我才不甩呢!」泰迪怏怏不樂地說,然後又滿懷希望地看著我們,「何況他們可能只會把我們關上一、兩個月,我的意思是再怎麼說我們才十二歲,他們總不會把我們關進蕭山克監獄吧?」
26
「那你一定可以未卜先知了,因為你是第一個跑的。」
「他睡覺時總是把窗戶開得大大的,毛毯也……戈弟,你剛才是不是說了什麼?」
我們都走了過去——或者應該說拖著疲倦的腳步蹣跚而行,沒有火車來。走到垃圾場時,我們翻過柵欄(沒見到麥洛,也沒見到大|波,他們不會那麼早,更何況是星期天),直接走向幫浦。魏恩打水,我們輪流把腦袋伸向冰涼的水流,並且把水拍打全身,一直喝水喝到肚子裝不下為止,然後把上衣穿上,因為早上好像有點涼颼颼的。我們一拐一拐走回鎮上,還在空地前的人行道上逗留片刻,我們望著樹屋,這樣大家才不必互望。
「柯里——」
我們走過一條街,沒有人開口。城堡岩的清晨安靜得可怕,我突然有種近乎神聖的感覺,覺得全身的疲憊皆離我而去。整個世界都在沉睡中,惟獨我們清醒著,我幾乎覺得一轉個彎就會看見我和*圖*書的鹿站在卡賓街角,也是鐵軌穿過工廠卸貨場的地方。
「你會坐牢。」馬瑞爾低聲說道,腳下絲毫不猶疑,臉上仍然掛著微笑。其他人都以既害怕又神往的表情注視他……與泰迪、魏恩和我注視柯里的表情一樣。馬瑞爾是鎮上方圓幾十哩之內最難纏的角色,我想柯里大概唬不了他。馬瑞爾不認為一個十二歲的小鬼會真的開槍打他,我覺得他錯了,我想柯里會在他奪去手槍之前開槍。在那數秒之間,我十分肯定這下麻煩可大了,是我所碰過最大的麻煩,或許會出人命也不一定,而一切都是為了誰對那具屍體有優先處理權。
「戈弟,你說得對,」他說道,「沒有人得到最後的權利,小人到處都是,呃?」
這時風雨又開始轉劇,來勢又急又猛,不過這一回下的是冰雹,而不是雨。森林的輕聲細語變成矯揉造作的二流電影中的叢林鼓聲——大塊大塊的冰雹敲著樹幹叮咚作響,會刺痛人的冰雹開始落在我的肩膀上——好像有某種邪惡力量在投擲這些冰雹似的。最糟的是,冰雹也開始打在布勞爾上仰的臉上,發出可怕的啪啦聲,又提醒我們他的存在,想到他無止境的驚人耐心。
「你給我閉嘴!」柯里對泰迪說道,「剛才你跑得挺快的,真是差勁的孬種!」
「因為我們要把他帶走,」馬瑞爾溫和地笑道(你可以想像,如果他在撞球檯邊正準備瞄準射球時,偏偏有個痞子在旁邊胡言亂語,馬瑞爾把球桿朝他的頭敲下去之前,臉上就掛著同樣微笑),「如果你們離開,我們會把他帶走,如果你們不走,就把你們打得稀爛,然後照樣把他帶走;何況,」他又說道,想替他們巧取豪奪的行逕加添一點冠冕堂皇的理由,「發現他的是查理與比利,所以他們有優先權。」
我和他擊掌。「回頭見。」
我們在星期天清晨五點多回到城堡岩,那天是勞動節前一天。我們走了一整夜,雖然大家的腳都磨出水泡,肚子又餓得嘰呱亂叫,但沒有人抱怨。我的頭痛得厲害,雙腳因為操勞過度而扭傷發熱。我們曾經兩次為了避開火車而躲到堤防下面,其中一輛火車和我們走同一個方向,但車速快得我們來不及跳上去。我們再度來到橫越城堡河的橋上時,天色已濛濛亮,柯里望了望鐵軌,望了望河水,再回頭望了望我們。
「我也是,」魏恩說,「我快睏死了。」
「噢,戈弟,」柯里顫聲說道,「剛剛這一切對他來說,真是太可怕了。」
麥洛也沒有把事情說出去,我猜他左思右想,大概覺得對自己頗為不利,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發誓他叫狗咬我是真有其事。
「柯里,他們可能會報警,再回來抓我們。」
30
「伸出手來?」
「露營」,我說著開始吃了起來,「本來是在魏恩家後面,後來又跑到布列山;魏恩的媽媽說會打電話過來,她沒打嗎?」
我爸問了我一些含糊的問題,都讓我含糊地擋了回去,他看來好像有點困惑不安,然後說改天一塊釣魚去,僅此而已。如果他們有一天聚在一塊兒的話,一切就穿幫了……不過這情形一直都未出現。
愚蠢的幻想!竟然想為了一個二十年前裝野果的罐子而深入森林探險,說不定這罐子早已被丟至森林深處,或是在蓋房子整地時被壓路機碾平了,或是茂密的雜草把它蓋住,根本看不見了。但我敢說罐子一定還在原處未動,就在那條舊鐵軌沿線的某個地方。有時候那股回去找找看的衝動幾乎有點瘋狂,通常這股衝動湧現的時候都是早上,我太太在淋浴,小孩則在看波士頓三十八頻道的《蝙蝠俠》,這時我特別會覺得少年時期的戈弟在我心裡蠢蠢欲動,那個也曾在這世界上昂首闊步,一會兒走路、一會兒說話、一會兒像隻爬蟲似的趴在地上爬行的戈弟。我想著:那孩子就是我,然而隨之而至的念頭卻令我有如被潑了冷水般全身發寒,那就是:你是指哪個孩子?
柯里張嘴望著凸眼蛇,濕淋淋的襯衫仍然紮在他細瘦的腰桿上,背包被雨淋得更形深綠,此刻也仍背在他裸|露的肩胛骨上。
「你們或許辦得到,或許辦不到。」
柯里柔聲說道:「泰迪,如果你有不良紀錄的話,就不能從軍。」
「我是怕冰雹!」泰迪既羞又怒地喊著,「不是怕那些傢伙!柯里,我怕雷雨!我沒辦法!我發誓,我敢跟他們任何一個人打架,可就怕雷雨!這我也沒法子。」他又開始哭,身子還坐在水裡。
喔,我的意思並不是布勞爾的屍體一直沒被找到,確實有人找到了。不過我們雙方人馬都沒落著什麼好處,我想馬瑞爾後來一定覺得匿名電話是最安全的辦法,因為新聞上是這麼報導的。我的意思是,沒有任何人的父母發覺我們那兩天究竟上哪兒露營去了。
他詫異地看著我。
31
二十分鐘之後,柯里爬上堤防坐在我們旁邊。雲層已開始散開,幾線陽光從雲層縫隙中射出,在短短的四十五分鐘之內,樹叢的深綠色已變了三次。柯里全身從頭到腳都是污泥,只有眼白部分是乾淨的。
我狂亂地低頭望著布勞爾,他正以獨眼平靜地望著從天而降的雨水。雷鳴聲依然隆隆不斷,但雨勢已開始減緩。
柯里帶著極懊惱的口吻柔聲說道:「馬瑞爾,你想在什麼部位吃一槍?手臂還是大腿?我不會挑,你替我挑挑看。」
「我們會逮到你的,」馬瑞爾說道,「如果你以為我們會忘掉的話,最好還是死了這條心。」
「他說得對,」我說道,覺得自己簡直是狗屎,「泰迪,他說得對,志願入伍的時候,他們會先調查你過去的紀錄。」
我們都好像給捅了屁股似地驚跳起來,魏恩則驚叫出聲——後來他承認,他以為說話的是布勞爾的屍體。
「當然會,不過不是今天或明天,這你不用擔心,我想起碼會過好久才敢講,也許好幾年。」
「也許是你爸爸m•hetubook•com.com接的。」她說著,悄悄走過我身邊到洗手臺前,像個粉紅色幽靈。日光燈對她並不仁慈,在燈光照射下,她的臉色變得蠟黃。她嘆口氣……幾乎是啜泣。「每天早晨,我總是特別想念丹尼,」她說道,「我都會走進他的房間看一眼,裡面總是空盪盪的,戈弟,空盪盪的。」
「是啊,真他媽的!」
「……毛毯也一直拉到下巴。」她說完後背向我怔怔地望著窗外。我繼續吃我的,全身顫抖。
「好吧,」馬瑞爾聲音柔和地說道,「去揍他們,把那叫戈弟的小鬼留給我,我要把他兩隻手臂折斷!」
「夠了!」查理說著開始走上前,臉上交雜著憤怒與難堪。「小鬼,不管你叫什麼名字,小心我打扁你的鼻子。」
他走開了,臉上仍掛著笑,走得輕鬆而優雅,彷彿他並不像我這樣腳丫滿是水泡,而他的身上也沒有被蚊子及小黑蟲咬得處處紅腫,彷彿他在這個世上了無牽掛,好似他要到一個很棒的地方,而不是待在一個只有三個房間的屋子(說是陋室還更確切些),屋裡不但沒有水龍頭,窗戶也破破爛爛,臨時用塑膠板擋著,還有個哥哥可能正在前院等他回來,準備好好修理他。即使我剛才知道該說什麼,或許也說不出口,我認為過多的言語只會破壞了愛的機能——我猜從一個作家嘴裡說出這種話大概極不可思議,但我相信這是真的。假使你告訴一隻鹿說你對牠毫無惡意,牠只會擺擺尾巴,一溜煙即不見了。多說無益,愛並非像有些混帳詩人所描述的那樣;愛有牙齒、會咬人,而這種傷口永遠也無法癒合,沒有任何言語可以使愛的傷口癒合,可笑的是,恰好相反,若是傷口乾了,言語文字也隨之枯死。相信我,我是靠文字討生活的,我知道事實的確如此。
「他是我們的,我們要把他帶走!」
我僵立原地,簡直無法置信,這就好像關鍵時刻臨時上臺的替角演員,竟說出一句劇本上找不著的臺詞一樣。我順著眼角瞧見柯里已將背上的袋子拿下,一手在裡面急急摸索著,但我不懂他在幹什麼——至少當時不懂。
「好了,」泰迪終於說道,「星期三學校見,我想我會一直睡到那時候。」
「如果我們的家人碰到一起,拆穿了我們的話呢?」魏恩問。
「好了,」柯里說道,本來他想以輕快的語氣說話,然而喉嚨發出的聲音卻又乾又澀,「我們走快點。」
「我們先過橋,」柯里說道,「以後的路不走鐵軌,我們從另一個方向回城堡岩。如果有人問我們到哪了,就說我們在布列山露營,結果迷路了。」
「對,如果你要的話。可是如果那些傢伙——」
「那又怎麼樣?」柯里說道,「我哥哥會修理我,馬瑞爾也許會修理戈弟,另外有人會修理泰迪,可是我們還是成功了。」
「我不管!」他尖叫著,同時掄起拳頭向我迫近,但他一隻腳正好踢到布勞爾的胸膛,屍體因而抖動一下,他一個踉蹌,整個人跌在地上,我等他站起來打我一拳,然而他卻伏倒原地,頭對著堤防,兩手越過頭部,做出跳水家預備跳水的姿態,正與布勞爾被我們發現時的姿勢一樣。我狂亂地望著柯里的腳,好確定他的球鞋還穿在腳上。之後他開始嚎啕痛哭,他的身體在泥漿裡抖動著,雙拳不斷地搥打著泥漿,腦袋扭來扭去。泰迪與魏恩盯著柯里,臉上帶著興奮的神情,因為沒有人看見柯里哭過。過了一會兒,我走回堤防,攀上去,坐在其中一條鐵軌上;泰迪與魏恩也隨後跟來,我們一言不發地坐在雨中,像極了禮品店裡賣的三隻美德猴,總是一副走投無路、瀕臨破產邊緣的樣子。
柯里看著我,「我們做到了,對不對?」他輕聲問道,「很值得,是不是?」
在這塊泥濘地的另一頭又是一大片森林,恰好擋住路的盡頭,馬瑞爾與凸眼蛇站在一起,由於隔著灰色的雨幕,看起來有幾分模糊。他們兩人上身都穿著學校的紅色尼龍夾克,一頭火爆浪子的髮型聽話地貼在後腦勺,雨水混含著髮油順著臉頰滾下,像極了道具眼淚。
「我們都到了,」馬瑞爾咧嘴笑道,「我看你們還是——」
查理更是嘴巴不饒人。「你這小偷窺狂!看我不打得你屁滾尿流才怪!」
我們滿心溫暖地互望了一秒鐘,也許從對方的眼光裡看到了什麼,又一起尷尬地低下頭。突然間一陣恐懼襲來,我從柯里移動雙腳激起的啪啦啪啦水聲得知他也看到了,布勞爾的眼睛已成慘白一片,沒有瞳孔的眼睛瞪著前方,就像希臘雕像在瞧你們似的。我們很快便了解是怎麼回事,不過了解並不能減輕恐懼感。他的眼睛裡滿是圓圓的白色冰雹,此刻已經溶化,正順著他的臉頰流下來,彷彿在為自己離奇的遭遇流淚——他竟然成了兩批蠢孩子爭奪的戰利品。他的衣服上也都是白色冰雹,宛若躺在自己的壽衣中。
魏恩茫然地搖搖頭,仍然震懾於柯里的怒氣。「我以為大家都要跑。」
27
「柯里!」我驚惶地說道。
28
「我在這兒。」
「嘿!」泰迪笨拙地說道,「大家都是哥兒們,不要傷感情,好嗎?」
「他媽的」,泰迪一派不再感興趣的口吻,「你們講話的口氣嚴肅得好像在上政論課似的,饒了我吧。我要回家了,不知道我媽是不是把我列在十大通緝要犯名單上了。」
「他媽的!」凸眼蛇說道,「那是我弟弟!」
我拿出一打雞蛋,炒了六個,等平底鍋裡的蛋成半凝固狀時,我又加了一盤碎鳳梨與半夸脫牛奶。正要坐下來吃時,我媽走進廚房,她的灰髮在腦後挽成髮髻,身穿一件褪色的粉紅色浴袍,嘴裡叼著駱駝牌香菸。https://www.hetubook.com.com
「我們會偷襲你,我們會——」
「很好,你們現在給我走,要幹什麼,改天再說。」
「好啊!」
馬瑞爾停下腳步。
之後泰迪欣喜若狂地喊道:「戈弟!說得好!讓他們嘗一點厲害!過癮!」
「是啊!」魏恩說道,「比利可不會饒我。」
右臉頰嚴重的瘀傷、頭部有劃破的痕跡、鼻子流血,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傷痕——至少看不到其他傷痕;但許多人在酒吧裡鬧事,渾身傷得比他厲害十倍,到頭來還不是照樣大口喝酒。不過火車一定撞到他了,否則他的球鞋怎麼會離腳那麼遠?為什麼火車駕駛沒看見他?會不會火車的撞擊力把他甩得老高,但卻還沒有要了他的命?我想像在適當情況下,不無可能發生這種情形:是不是他想避開火車時,被火車撞到側面,然後一個滾翻,落在那塊低凹的沼澤地上?他會不會神智清醒地躺在那兒顫抖了好幾個鐘頭,然後才死的?死時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和整個世界切斷了聯繫。也許他是死於恐懼。從前有隻尾翼折斷的小鳥,就那樣死在我手裡,牠的身體輕顫微跳著,嘴巴一開一合,黑亮的眼睛仰瞪著我,不久牠的身體不跳了,嘴巴半開著,黑眼睛中光芒不見了,變得毫不在乎,布勞爾的情形也可能如此,他很可能因為覺得這樣活下去太可怕了而死去。
柯里瞪著他,眼神慍怒而狂亂,然後他轉向我。「戈弟,我們幫他弄個擔架。」
「馬瑞爾,你再不站住,我發誓就要開槍了。」
他們冒著漸漸減緩的雨勢朝我們走來。莫傑從口袋裡掏出一把彈簧刀並敲著刀柄,六吋長的刀子隨即彈出,在陰暗的下午光線下閃著灰漾漾的光。魏恩與泰迪突然一左一右閃到我身邊,同時擺起備戰姿態——屈起雙膝,緊握雙拳;泰迪充滿了狂熱,魏恩則是一臉絕望與擔憂。
他不該提丹尼的。我本來想跟他講理,讓馬瑞爾知道魏恩親耳聽見涸比利與查理甘願放棄,因此真正有優先權的人是我們;我要告訴他,魏恩蠶和我為了找這具屍體,幾乎在橋上被火車壓扁,告訴他麥洛與他那隻天不怕地不怕——或者該說愚蠢至極——的狗朋友大|波,還有那些吸血蟲。我想我真正想告訴他的是:算了吧,馬瑞爾,做人要公平一點。但他卻把丹尼扯進來,於是我聽見從我嘴裡吐出來的,不是溫和的說理,而是我的死刑宣判:「去你的!你們這些下流的太保!」
我相信柯里不過在說謊——但這種時候還是不挑明的好。泰迪望著柯里良久,他的嘴唇顫抖著,最後他終於說出話來。「不是臭蓋胡說?」
柯里的爸爸仍然在喝酒,跟柯里的預測沒有兩樣。他媽媽跑到路易斯登的姊姊家裡,每回柯里的爸爸喝酒狂歡時,她總是跑到那兒避難,然後讓凸眼蛇負責照顧年紀較小的弟妹。凸眼蛇不辱媽媽的託付,每天跟馬瑞爾與一群太保朋友四處閒混,留下九歲的南登、五歲的榮莉與兩歲的黛拉自生自滅。
「嘿!柯里,那是爸爸的槍嘛!」他說道,「你想找死啊!——」
「他們嚇壞了,柯里,尤其是泰迪,他害怕沒辦法從軍,不過魏恩也很害怕,他們兩個都會好幾天睡不著覺。我想今年秋天,他們有好幾次差一點脫口而出,但我猜他們不會講,因為……你知道嗎?這話聽起來有點瘋狂,可是……我想他們根本會把整件事情忘掉,好像不曾發生過一樣。」
「我跟你一塊走。」柯里提議道。
他滿懷希望地看著我。
「戈弟,不要走開,」柯里顫聲低語,「別走。」
「喔,你幹嘛不回去跟你媽多親熱親熱?我聽說她挺喜歡的。」
「現在你們坐進車裡,給我乖乖地回城堡岩,以後你們要做什麼,我不管,可是別想碰他。」他抬起一隻淋濕的球鞋輕觸著布勞爾,幾乎帶著尊敬的意味。「懂嗎?」
「你去問戈弟。」
「魏恩!」比利大聲咆哮著,帶著責備的口吻,兩隻拳頭握得緊緊的,還不斷滴水。「你這小渾球原來你躺在走廊下面!你這偷聽別人說話的小鬼!」
柯里吹著不成調的口哨,一句話也沒說。
不過還有一件可疑的事,我想最令我不安的就是這件事。他是動身來採果子的,我好像記得新聞報導上說他還提了個罐子來裝果子。我回家之後曾到圖書館查過報紙,結果證實我沒錯,他的確是出門採果子,手裡還提了個瓶子或罐子之類的東西,但是我們沒有發現這東西。我們發現了他與他的球鞋,看來他一定是在伯倫鎮與他橫死的沼澤地中途把罐子丟了。或許剛開始迷路的時候,他還緊緊抓住那罐子,因為那代表了他與家庭、安全的聯繫,然而後來他越來越害怕,再加上一種完全的孤獨感,他發覺除了靠自己之外,沒有人能救他,這時他從心底湧現一股充滿寒意的真實恐懼,也許就這麼不知不覺地把罐子丟到鐵軌邊的林子裡,連他自己都不曉得是什麼時候丟的。
「我聽說你媽的錢是睡覺睡來的。」柯里向他說道,馬瑞爾的臉開始一陣青一陣白,幾乎快與柯里的臉一樣慘白。柯里又說道:「其實我還聽說她——」
「現在就給我走。」柯里對馬瑞爾說道,他竟然能不露出半點顫聲,實在神奇,他的口氣就好像在教導一個愚笨的嬰兒。
「我們成功了,」他說道,「他們走了。」
「錯了,你不會知道的。」
「不好,」柯里說著,驀地他一臉的疲倦鬱悶都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甜蜜而和煦的笑容,「我們做到了,是不是?我們趕走了那批渾球。」
「那再見了。」他說著,聲音中透著疲倦。
「喔,我們當然會試試看,別擔心。」凸眼蛇說著,他與馬瑞爾身後的樹枝隨即抖動了一下。查理與魏恩的哥哥比利也站了出來,一邊抹掉臉上的雨水,一邊罵著髒話,驀地我覺得心中一沉,等我看見莫傑、迷糊蛋伯考維與溫斯接連出現時,我的心更沉了。
(砰!)
「我們走著瞧!」柯里告訴他。
他又笑了——還是那甜蜜、和煦的笑容。「我會先見到你和圖書的,渾球。」
魏恩哀號一聲,第一個投降,他急急大跨幾步,一溜煙竄上堤防。泰迪逗留了一分鐘,也跟在魏恩後面抱頭鼠竄。至於他們那一邊,溫斯蹣跚後退到附近的樹叢下,伯考維也跟著躲了起來,不過其他人仍站在原地,馬瑞爾又咧嘴笑了。
「那你呢?」柯里轉身問魏恩,「你也怕雷雨?」
魏恩畏縮在一旁。
「這一點你自己去操心吧,」柯里說,「我爸爸反正還是醉得厲害。」
柯里如大夢初醒般抬起頭,嘴唇扭曲著,他朝泰迪大踏步走去,兩手按在泰迪胸前,粗暴地把他向後一推。泰迪踉蹌後退,兩手像風火輪似地猛打著圈想穩住身子,最後坐在一灘泥漿中,兩眼上仰對柯里眨眼,好似一隻驚訝的麝香鼠。魏恩留心地注視柯里,似乎怕他做出什麼瘋狂的舉動,不過或許跟事實相差無幾。
「也許我們聽見的是他的鬼魂,也許他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這樣你爭我奪,對他來說,真是太可怕了,我是說真的。」
「你這小癟三!」凸眼蛇只這麼說道,「你會被修理得很悽慘的!」
後門上了鎖,於是我從門墊下面摸出一把鑰匙,打開門進去。廚房裡沒有人,一片安靜,乾淨得令人不快;我打開電燈開關時,聽見洗手臺上的燈管發出哼聲。我大概有幾百年不曾比我媽早起了,連上一次是什麼時候都不記得。
「我們要把他帶回去,對不對?」泰迪困惑不解地問,「我們會變成英雄,是不是?」他先望著柯里,又望著我,然後目光又回到柯里身上。
因此祕密一直未曾洩漏出去——不過事情並非就此結束。
我們的祕密一直沒有洩漏出去。
「希望如此。」
「那走吧。」魏恩說著朝我們與赫婁路之間的森林望了一眼,好像懷疑警察隨時可能帶著一群惡犬,從樹叢中冒出來。「早走早好。」
「我想他不會知道的——」
「天哪!」
「我們會狠狠修理你,」馬瑞爾微笑道,「打得你全身是傷,我不相信你不知道這點。我們會讓你們全上醫院療傷,我可是說真的。」
「對,兩輛車都走了。」他兩手交叉高舉至頭上,兩手中間夾著手槍,彷彿冠軍揮著手的姿態;然後他放下手,對我微微一笑,我想那是我見過最悲涼、最驚恐的微笑。
「他是我們的。」柯里說,漆黑的眼睛反映著晨光。
他躺在那兒,再度孤零零的。他的手臂張開,因為剛才我們曾幫他翻身朝上,因此這時他呈大字形平躺著,似乎在歡迎陽光出現。頃刻之間,一切彷彿都很好,比殯儀館安排的瞻仰室更自然,然而不久之後,你就看到了他臉上的瘀傷、下巴與嘴上的血塊,以及漸趨腫脹的軀體,也看到了和太陽一起出現的綠頭蒼蠅正繞著屍體打轉,發出擾人的嗡嗡聲,於是你記起那股難聞的腐臭味,就像緊閉的密室中有人放屁的味道一樣。他的年紀與我們相仿,而他卻死了,我不願相信這一切是出於自然,我恐懼莫名地排斥這種想法。
「去他的那些傢伙!」他喊道,「你們都是一群膽小鬼!全部給我滾開,討厭鬼!」
「留在這兒別動。」柯里對我說著,便開始朝泥沼地跨去。
比利與查理並不需要一再邀請,他們一道走過來,魏恩又畏縮了一下——顯然是在想像自己即將挨揍的景象與過去挨揍的情形,儘管他畏畏縮縮,但表面上依然硬撐,因為他是跟朋友在一塊兒,我們一起度過了許多艱險,而不是輕鬆開汽車來的。
「當然!跟童子軍一樣」,他的聲音變得高亢而奇特,「就跟他媽的童子軍一樣。用襯衫和竿子做個擔架,就像手冊裡說的那樣,戈弟,對不對?」
擦完之後,我把破布丟開,上頭真髒。
「好吧,」馬瑞爾柔聲對柯里說道,「可是我知道你會有什麼下場,你這渾蛋。」
啜著手中的熱茶,注視著廚房窗戶斜射入屋的陽光,聽著分別由屋子兩側傳來電視聲音與淋浴聲,我感覺到眼睛的顫動,看來昨晚啤酒喝多了,這時候,我就會覺得回去一定可以找得著那個罐子。我可以看見那個罐子雖已鏽爛,但仍透著金屬的光芒,把夏日陽光反射到我的眼中。我會走到堤防下面,撥開緊緊纏住罐子耳朵的雜草,然後我要……幹嘛?我就是要把它從逝去的時光中拖出來,不斷地在手中把玩著,一邊摸著罐子,一邊想著它的一切,慨嘆著最後一個握住罐子的人,如今已作古多年。裡面會不會有張紙條?寫著:「救救我,我迷路了。」當然不會——小孩子才不會帶著鉛筆和紙去採野果——這不過是假設。我想像自己握著罐子時會是多麼驚駭敬畏,不過我猜我只會這麼想:雙手捧著那罐子,象徵了我的生與他的死,也證明我確實知道死掉的孩子是誰——是我們五個孩子中的哪一個孩子。握著罐子,從鏽跡斑斑與不再光亮的外殼上,讀出它所經歷的歲歲年年;撫摸著它,試圖了解曾經照耀其上的陽光、打落其上的雨水與覆蓋其上的冰雪,也回想著這罐子孤零零地經歷風霜雨雪的同時,我又遭遇了什麼?我在哪裡?在做什麼?在愛誰?過得如何?在什麼地方?我會捧著它、讀它、摸它……望著罐子上反映出的自己的臉孔,你明白嗎?
微笑消失了,我看見他的臉上突然露出恐懼的神情,我想使他害怕的倒不是柯里的話,而是說話的口氣;我心想,這下漏子越捅越大了,如果這真是唬人的把戲,可算是我生平所見最棒的把戲。其他的大男孩也都信以為真,臉孔皺成一團,彷彿有人以火柴點燃了炸藥引信似的。
「你在找什麼?」泰迪問,他也下來了。
「我永遠也無法離開這個鎮,」柯里說著嘆了口氣,「等你上大學放暑假回來,就可以在七點到三點的日班結束後,到酒館來看魏恩、泰迪和我,如果你想的話;不過也許你根本不想。」他的笑令人脊背發涼。
我們都大笑出聲,泰迪又是一臉「我又說什麼啦」的神情,我們和他擊掌,然後他與魏恩兩人便朝家的方向走去,我也應該回家才是……但我猶豫了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