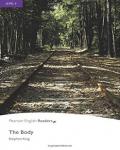Ⅶ
柯里升上初二時選了升學班的課——他和我都知道再等下去就來不及了,因為他永遠也無法趕上。每個人都為他這個決定而大感意外。父母認為他在裝腔作勢,朋友認為他成了好學生,再也不與他為伍,輔導老師認為他的功課一定趕不上。而大部分老師都對這位留著鴨尾巴長髮、穿皮夾克與靴子的學生很不以為然,因為他毫無準備地出現在他們班上,他們認為穿那種靴子與滿是拉鏈皮夾克的人,竟然出現在高尚的幾何、拉丁文與地球科學等高深科目的課堂上,簡直是大不敬,這身打扮只該出現在技藝班才是。柯里坐在那些來自望城山與布列山中產階級家庭、衣著考究、活潑開朗的乖小孩中間,就好像格蘭戴爾一樣,隨時可能對他們發出可怕的吼聲,把他們連同漂亮襯衫、鞋子和所有的一切,全都吞下肚子。
(全書完)
「我們是來找你算賬的,小鬼。」伯考維說道。
她帶我進屋子,給我一塊濕布擦鼻子——這時鼻子已扁成一團——又讓我喝下一杯有藥味的咖啡,好像使我好過多了。她一直對我吼,說要找醫生來,我一概說不用,最後她只好放棄,於是我走回家,走得非常慢。我的寶貝還沒有腫得像罐子那麼大,不過也差不多了。
我們四個人傷痕累累地上學,活像韓戰突擊隊的殘兵敗將,沒有人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不過大家都了解我們跟那些大孩子結了樑子,但每個人都表現得像個男子漢,於是一些謠傳出現了,每種說法都荒誕得離譜。
「是啊。」醫生說道,他對柯里的不滿如克拉森醫生對我的感覺一樣,隨後他掛電話給班警官。
我賣掉了那本小說,片商將它拍成電影,影評人的口碑甚佳,小說本身也大大熱門,這一切都發生於我二十六歲那年。第二本書也拍成電影,第三本亦不例外。我告訴過你——簡直是他媽的荒誕不經,況且我太太好像也並不介意我待在家裡,現在我們已有三個孩子了。在我看來,他們都很完美,大半的時間我都覺得很快樂。
至於我呢?
「我不知道,克拉森醫——」
我們倆在高中時都交過女朋友,但沒有一個女孩能介入我們之中,你會不會覺得我們有點曖昧?我們的老朋友都這麼想,魏恩與泰迪也包括在內,但這只是我們求生的途徑。我們在深水中緊緊攀附著對方;我想柯里那方我已經解釋過了,而我攀附他的理由則比較不是那麼清楚。我想,柯里亟欲逃離城堡和圖書岩與逃離工廠陰影,就是我最好的理由,我不能丟下他一個人逆流而上,如果他沉淪了,我想一部分的我也會隨之沉淪下去。
一九七一年底,柯里到波特蘭一家小吃店吃飯,就在他的面前,有兩個人正在為誰先排在前面而爭執不休,其中一個抽出刀子。柯里是我們之中最善於打圓場的,這時他介入他們中間調停,刀子正好就插|進他的喉嚨。拿刀的這個人曾經在四個不同的監獄裡服刑,事發之前一個星期才從蕭山克州立監獄出來。柯里當場斃命。
正如我說的,現在我是個作家,許多書評人說我寫的東西都是狗屎,我也時常覺得他們說得沒錯……但每回在銀行或醫生辦公室裡填表格填到職業欄,我填上「作家」二字時,都仍然覺得心慌。我的故事太像童話故事了,顯得荒誕不經。
米太太好久好久都不發一語,最後才答應,她沒有多問,柯里也沒有說謊。班警官確實去了他家一趟,不過凸眼蛇並沒有坐牢。
但我曾經說過,寫作不像過去那麼輕鬆、那麼有趣。電話總是不停地響,偶爾我會頭痛欲裂,於是就必須到幽暗的房間裡躺下,直到不再頭痛為止。大夫說我得的並不是真正的偏頭痛,他稱之為「緊張痛」,叫我心情放輕鬆即可痊癒。我偶爾會擔心自己,這種毛病多麼愚蠢啊……可是我卻無法停止頭痛。我想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是否真有任何意義?一個人能以寫作杜撰的小說致富,這是個什麼樣的世界?
「我不認得他們,真的。」
「沒有關係,米太太。」柯里說道,「你看一下我家門口有沒有一輛別克?」那輛別克是柯里媽媽開的,已經開了十年,引擎燒熱的時候,聞起來會有一股焦味。
他蒼白的臉頰開始微微泛紅。「你何必護著那些白癡?你以為他們會因此尊敬你嗎?他們只會說你是笨蛋,然後大笑三聲;他們會說:『啊,那個被我們打得慘兮兮的笨蛋來了,哈哈哈!』」
他在辦公室打電話的同時,柯里緩緩地穿過大廳,將吊腕帶按在胸前,免得它亂晃,這樣斷裂的骨頭才不會互相摩擦;他打電話給米太太。他後來告訴我,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打對方付費的電話,他深怕米太太不肯接電話,還好她接了。
「柯里,對不起,我不能留下來照顧你,因為我正在烘餅——」
爸媽看了我一眼,便一路罵了出來——說實在,我還真有點訝異他們竟然注意到了。「那些小孩是誰?認不認得出來?」我爸問道,他從不錯過那些警匪影集。我說大概無法從一排人中指認出嫌疑犯,又說我累了,其實我想我是過度驚嚇,而且因為喝了喬太太的咖啡——裡面至少摻了百分之六十的VSOP 白蘭地——有點酒醉,我說他們大概不是鎮上和*圖*書的小孩,可能是從路易斯登來的。
那年他有十幾次想要放棄,他的父親尤其拚命打擊他,指責柯里自覺比老爸強,指責柯里想上大學好花光他老子的血汗錢。有一回他用瓶子敲柯里的後腦勺,結果柯里又上了醫院的急診室,縫了四針才把腦殼合起來。他的老朋友們——現在多半整天抽菸鬼混——看到他都極盡訕笑之能事。輔導老師勸他多少修一點技藝課程,才不會全部不及格。當然最糟的是:他荒廢了前七年的教育,如今重拾課業,開始大吃苦頭了。
33
柯里和我漸漸減少上樹屋的次數,過了不久,那地方就變成他們所有了。我記得一九六一年春天,有一次我上了樹屋,注意到裡面充滿一種砲轟過的乾草堆味道,以後我再也沒上去過。漸漸地,泰迪與魏恩變得只是偶爾會在學校碰到的另外兩張面孔,我們見面僅點點頭、說聲嘿而已。這種事隨處可見,有沒有注意到,朋友在你生命中進進出出,好像餐廳中的侍者來來去去一樣。可是每當我想起那場夢、想到那兩具屍體正用力拖我下水的時候,我就覺得這樣也好。有的人會沉淪,如此而已,並不公平,但世事就是這樣,有的人會沉淪下去。
32
我看得出來他好想扳住我的身子把我搖醒,不過他當然沒有這麼做,於是他讓我出了診療室,一邊搖著滿頭白髮,一邊嘴裡還喃喃說什麼不良少年;我想他晚上抽著雪茄、喝著雪利酒的時候,一定會對他的老朋友上帝談起這件事。
馬瑞爾在我臉上重重打了兩拳,一拳打在我的左眼,這一來,那隻眼睛得過四天後才能看清楚,另一拳打破了鼻子,聽來有點像咀嚼脆米花的聲音。這時年老的喬太太從門裡出來,一手拄著拐杖,嘴裡叼著菸,開始對他們大吼:
我注視著他把車子彎進酒館旁邊的骯髒停車場,然後他下車,兩手插在褲袋裡走了進去,我可以想像他開門時裡面飄出的菸味和西部鄉村歌曲的聲音,以及其他常客的歡迎聲,他將那偌大的臀部往凳子上一擱,或許自從他二十一歲以後,除了星期天之外,每天都在這裡消磨三個鐘頭。
發生車禍的地點是赫婁。泰迪的雪佛蘭車上載滿了朋友(其中兩個是泰迪、魏恩從一九六〇年就一起混的朋友),每個人都喝了不少酒。車子撞上電線桿,把電線桿撞成兩半,然後連翻六個觔斗。其中有個女孩還活著,她在醫院的植物區——緬因州綜合醫院的植物人病房——躺了半年,直到後來不知哪個慈悲的幽靈拔掉了她的呼吸器。泰迪死後獲頒年度狗熊獎。
由於經常曠課、遲到與多項成績不及和-圖-書格,泰迪留級一年……不過還是畢業了。他有一輛老舊的雪佛蘭,時常開著到過去馬瑞爾、伯考維時常去的地方鬼混,像彈子房、舞廳、酒館等,最後終於在城堡岩工務局找到一份修補路面的工作。
「有。」她審慎地說道,最好不要跟柯里家有任何瓜葛,一窮二白的愛爾蘭後裔。
魏恩與泰迪也掛了彩,不過沒柯里和我這麼嚴重。比利在魏恩回家的路上修理他,才揮了四五拳,魏恩就失去知覺。魏恩只不過是昏倒了,比利卻深怕他已經死在自己的拳下,不敢再出手。泰迪有一回從樹屋回家的路上,被他們中間的三個逮著,他們把他一拳打飛了過去,砸了他的眼鏡;他要跟他們對打,可是等他們知道他根本是在瞎子摸黑時,就不願意打下去了。
不過我與馬瑞爾重逢的經過倒是挺滑稽的。我的朋友都死了,而馬瑞爾還活著。我看見他在三點鐘的下班哨聲之後,從工廠停車場駕著車出來,那是我上一次帶著孩子回家看爸爸的時候。
等到疤掉了、瘀痕也褪去的時候,魏恩與泰迪離我們越來越遠,他們又找到一群新夥伴,可以讓他們作威作福,其中大部分都是徹頭徹尾的渾球——五年級的小笨驢——但泰迪與魏恩一再把他們帶上樹屋,指揮來指揮去,活像納粹頭子一樣跋扈。
34
車門一一甩開,馬瑞爾與伯考維跨步走了下來。
一九六六年,魏恩葬身於路易斯登的公寓大火中——我相信布魯克林與布朗克斯的人會稱這種公寓為貧民窟。消防隊稱火勢起於凌晨兩點,天亮時,整棟建築物只剩下一堆灰礫。那裡原本在舉行一場大型的喝酒晚會,魏恩亦是座上客,有人在其中一間臥房裡睡著了,卻忘了捻熄香菸;或許是魏恩自己,正在夢想他那一罐子錢幣。他們從牙齒辨認出魏恩與另外四具屍體的身分。
我往左邊一望,越過工廠,我可以看見城堡河的河水仍然在赫婁與城堡岩之間的橋下奔流著,雖然不及過去那麼寬闊,但卻乾淨得多。上流的橋已不復存在,但河水仍繼續奔流著。我也是。
「小鬼,下次別再讓我看到!」馬瑞爾微笑道,然後他們放下我走了。我坐起來,身子前傾著,兩手捧著傷得不輕的命|根|子,心想這下八成活不成了。我仍然哭著,但伯考維開始繞過我時,一看到他那雙緊裹著牛仔褲的腿與他的長靴,我又滿心憤怒,於是我一把抓住他,朝著他的小腿,用盡吃奶的力氣狠狠咬下去。伯考維也開始尖叫,而且用單腳猛跳,竟還氣急敗壞地罵我卑鄙。我正望著他蹦來跳去,馬瑞爾一腳踩住我的左手一用力,兩根指頭斷了,我清楚聽見指頭斷裂的聲音,這回不像脆脆的米花,而像脆餅。hetubook•com.com之後馬瑞爾與伯考維走回車上,馬瑞爾把手插在後褲袋中慢慢走著,伯考維還不忘轉過頭來罵我一大串髒話。我蜷縮起身子哭著,喬太太走下來,還不住生氣地揮舞著手裡的拐杖。她問我要不要去看醫生,我坐起來,勉強止住哭,抽抽嗒嗒地告訴她不需要。
但他終於在高三時被大家接納。我倆都不曾名列前茅,不過我得第七,他也得了個十九。我們都得到緬因大學的入學許可,不過我上的是奧朗諾校區,他則去波特蘭校區念法律。你信不信?得念更多的拉丁文。
「沒有,大夫,真的。」
我們幾乎每天晚上都一起念書,有時候一口氣就足足念六個鐘頭,每次念完,我都精疲力竭,有時候也很害怕——因為他會為過去的荒唐竟然需要付出如此高的代價而大發雷霆。在他學「初級幾何學」之前,得先復習五年級的分數部分,因為當時他正與魏恩、泰迪玩得不亦樂乎呢!看到一個拉丁句子,他還得問清楚主詞、介詞與受詞分別是什麼;在他的英文文法課本裡,工工整整寫著「他媽的動名詞」。他在作文方面的構思與組織都不錯,但文法很差,他不打標點符號的方式彷彿拿霰彈槍亂射一般;他把那本《瓦瑞納英文與作文》翻爛了以後,又在波特蘭買了一本新的,那是他買的第一本精裝書,日後被他奉為《聖經》一樣神聖與珍貴。
「你在撒謊。」
在那個月的月底,有一天我從學校走路回家的時候,一輛黑色的一九五二年福特車停在我面前,就是這輛車,不會錯。車身是幫派分子喜歡的自色,還有流線型車頭和高高隆起的保險槓。後車蓋上畫了兩點和十一點的撲克牌圖案。
「胡說!」她咆哮道——喬太太已經半聾,因此說話都用吼的,「我看見那壞東西打在你什麼地方,哼,我看你的寶貝不腫得跟腌果醬的罐子一樣大才怪!」
我毫不在意馬瑞爾他們究竟是尊敬我或視我為傻瓜,還是根本沒把我放在心上,但我必須為柯里著想。他的哥哥凸眼蛇打得他手臂折斷兩處,臉上又紅又紫,斷裂的手肘必須打鋼釘才接得起來。米太太走在路上時,瞧見柯里懸著無力的胳膊蹣跚而行,兩隻耳朵裡也都流著血,眼睛卻還在看漫畫書,於是她立刻帶他上醫院急診室,柯里告訴醫生,他是在黑暗中跌下地窖樓梯摔傷的。
泰迪則在車禍中喪生,我想是一九七一年,也可能是一九七二年初。我長大那段時間流行一種說法:「如果你一個人出去闖盪,是英雄;帶了人跟你一起,就是狗熊。」泰迪自懂事以來,唯一的願望就是從軍,結果空軍不接納他,徵兵部門將他的體格列為D等。其實任何人只要見了他那對厚鏡片與助聽器,就知道會有這種結果,惟獨泰迪自己不知道。他在高www.hetubook.com.com二時,由於辱罵輔導老師為狗屎而禁止上學三天;學校就業輔導室的老師已經觀察他許久——他幾乎天天上辦公室查看從軍資料,這位老師知道他不是從軍的料,就勸他考慮一下其他職業,於是泰迪就狂怒起來。
我把書包朝人行道上一丟,拔腿就跑,但還沒跑到這條街的盡頭就被他們逮著。馬瑞爾飛身把我一抓,我即刻趴在地上,下巴結實地搗著水泥地,不僅是眼冒金星,簡直看到了整個星系、整個星雲。他們拉我起來時,我已經哭了起來,倒不是因為我的手肘與膝蓋都破皮流血,或因為害怕——而是一股感到無能為力的強烈憤怒;柯里說得對,他原本是我們的。
我又扭又轉,幾乎擺脫了他們,這時伯考維抬起膝蓋,朝我的下部猛力一頂,我感到一陣令人難以置信、無與倫比的強烈疼痛。這種驚人的痛讓人眼界大開,彷彿見識到電影除了普通的寬銀幕,還有全景寬銀幕。我開始尖聲哭叫,看來尖叫是我唯一的機會。
「很好,謝謝。」柯里說。
一九五二年的福特車已變為一九七七年的旅行車,車身上還貼著褪色的「雷根/布希/一九八〇」字樣。他的頭髮推成了小平頭,人也發福不少,原本伶俐、英俊的五官,如今都已陷進滿臉贅肉裡。我把孩子留在爸爸那兒,好進城買份報紙。我正好站在卡賓街的角落等著過街時,他朝我一瞥,這個過去曾打歪我鼻梁的三十二歲男人完全沒有認出我。
「戈弟,是誰幹的?」
「柯里,你還好吧?」她問。
我想:(原來馬瑞爾現在變成這樣。)
「下流的太保,是嗎?」馬瑞爾說道,臉上仍是溫溫的笑,「我媽挺喜歡我的技巧,對嗎?」
「能不能麻煩你走一趟,叫我媽到樓下把地窖燈泡的插頭拔下來,好嗎?」
他們帶我去看克拉森醫生,如今他依然健在,不過當時我就覺得他已經老得可以跟上帝一起促膝談心了。他接好我的手指與鼻梁,又給了我媽止痛藥的處方,之後他藉故要我爸媽走出診療室,然後慢吞吞地走到我面前,好像電影《科學怪人》中的怪物走近伊戈爾一樣。
「柯里,真的,我的餅——」
「請她立刻去拔插頭,」柯里執拗地說道,「否則我哥哥就得坐牢。」
「嘿!你們在幹嘛?不准再打了!警察!警察!」
我是在報紙上看到這個消息的——柯里當時即將結束研究生二年級的學業,而我也已經結婚一年半,正在一所高中教英文,我太太有了身孕,我也正在籌劃寫一本書。當我看到報紙的大標題時——研究生於波特蘭餐廳被刺殞命——就告訴太太我要出去喝點東西。我駕車到郊外,停了車,為他哭泣;我猜我大概哭了將近半個小時,雖然我們夫妻感情甚篤,但我無法在太太面前哭泣,否則就顯得太軟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