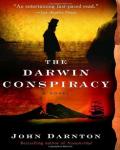第九章
我敢肯定拉斯舅舅也聽到了部分她說的話,因為所有客人離開後,他奇怪地盯著我,說我對他來說一直是個謎——一個「真正的潘朵拉盒子」。他接著的話顯得更傷人,但我敢肯定他並沒那個意思。相反,我把他的話當作是一種恭維。他說他不明白為什麼明明近旁就有同樣的另一個寶貝,我爸爸卻偏愛艾蒂。
今天,我回到唐豪斯的家裡。天正下著瓢潑大雨。我從馬車上跑下來,裙子被雨濕透了。剛一進屋,一條好消息就讓我鬆了一口氣:所有一切都得到了寬恕。媽媽給我倒了一杯茶,之後爸爸停止了跟帕斯洛打撞球,而向我挑戰玩雙陸棋遊戲。我故意輸給了他,他非常得意。我覺得他都沒看穿我的把戲。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三日
接著又引出對《接觸性傳染病法案》的討論。我覺得最讓人憤怒的是,它規定只要發現婦女接近軍事要塞就可予以逮捕。所有的男性都辯護說,消滅這一可怕的傳染病的唯一辦法就是對所有帶有可疑病毒的婦女進行汞處理。
「太有意思了,」他高聲回答說。不過給我的印象是他似乎表現得有些過頭了,是有意在掩蓋某種深藏內心的壓抑和鬱悶。
我發現了一件怪事。很多標本都是些骨架和化石之類的東西,上面的標籤和日期都是爸爸的字體。但有一些上面貼的卻是縮寫字母:「R.M.」。我覺得這很讓人費解,但卻不敢問爸爸那些字的含義。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日
事實上,我們達爾文全家一直都共同承受著早亡的折磨:可憐的瑪麗,不過松鼠那麼大,還不到一歲;小查理.韋爾林也不到兩歲。每個星期天去教堂,我們都要經過他們小小的墓碑。接著是爸爸的父親——我的祖父,去世了。這事給我們帶來了深深的不安,也給爸爸造成了永遠的遺憾。因為他到達什魯斯伯里太遲了,未能參加讓他擁有今天這番成就的父親的葬禮。
一八六五年二月七日
他的話是這樣的:「我想冒昧說一句,自然選擇這個詞雖然從科學的角度來講很精確,但對於大眾來說則可能有誤導性。」
過了一些時候,我問他是在什麼時間、是什麼原因使他失去信仰,變成一個無神論者的。因為我暗自猜想,這是否是安妮夭折所帶來的危機造成的。但他的回答全然出乎我的預料。他久久地拉著我的胳膊,看著我的眼睛回答說:「是很久很久以前,當我年輕時在小獵犬號船上的時候。但至於其他,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我偷偷從舅舅那裡拿了一本在整個倫敦引起一片嘩然的書。看得出來,它為什麼會如此知名。書很薄,裡面只有一首叫做《妖精市場》的詩。有的部分雖然很是嚇人,尤其是對那些恐怖的小男妖的描寫,但我發現它最末部分的寓意卻非常令人振奮。我想,結局好一切都好。我是在拉斯舅舅客廳的紅木桌子上發現這本書的,於是沒經他允許就把它拿到樓上去了。據我所知,他從沒問起過這本書。因此我實在忍不住,就把它藏了起來。書非常的小,我於是把它藏在了安妮的寫字盒裡。
我得說,舅舅在城裡的家是全世界我最喜歡的地方之一。各色有趣和優雅的人物都聚集在他的餐桌旁:邊沁主義者,憲章派人物以及天主教教徒,甚至還有無神論者——總之,形形色|色的自由思想者。葡萄酒慷慨地流溢,他們的談話也酣暢淋漓。不像在唐豪斯,一旦討論進入熱烈狀態(非常稀罕的事),爸爸就不會讓我待在客廳裡。在這裡,他們允許我留下來作為唇槍舌劍的見證。
和圖書
赫胥黎先生有一次說「實際上,他變得非常專橫了」。賴爾先生也贊同他的看法。我完全不知道他們指的到底是誰——有一陣子還擔心說的是親愛的爸爸——直到聽見賴爾先生接著說道:「不該告訴他第二版時他的名字被去掉了。那明顯地讓他很不安,是個錯誤。」顯然,這指的是華萊士先生,因為過去我曾聽說有人批評爸爸在這一版《物種起源》中沒有提到他的競爭對手,並強烈要求他立即予以矯正。科學家對這類事情是非常在意的。
在這整個過程中,我都在思考早先的一個問題,並一直想鼓起勇氣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因為雖然我有幸參加了拉斯舅舅的社交聚會,但我以前從沒有表達過自己的觀點。按照一些不成文的禮節,我保持著沉默,因為我不知道如果我打斷他們的話,舅舅會不會不高興。艾文思小姐注意到我複雜的心緒,於是和藹地拍了拍我的手,對眾人說:「我敢肯定達爾文小姐有話要說。」一時間所有的目光都投到我身上。我別無選擇,只好把自己的觀點說了出來。我說,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群體「生活在枷鎖之下」。「什麼群體?請說來聽聽啊。」卡萊爾先生問道。我感覺自己應該遲疑一下,以接受如此傑出的思想家的質問。但我發現自己幾乎沒來得及思考,兩個字就衝口而出:「婦女。」
「適者生存。」
他和爸爸在商談時很是熱情友好,看上去也非常得體。但我知道,他們間的關係也不乏緊張。爸爸第一次回覆華萊士先生那封勾勒出那一理論的著名信件後,很久都沒有收到回信。而當他終於收到來信時,他非常不安,一個人在書房讀完後,一下把它扔到壁爐裡。我敢這麼肯定,是因為我隨後進去時,看到它正在火裡燃燒。
然而,對童年的回憶卻使我陷入了一種怎麼也無法擺脫的憂傷。我想到自己目前這令人沮喪、好似很遙遠的青春,怎麼也不能把它與我曾經有過的快樂時光連繫起來。回首往事,讓我最為不安的是,我弄不明白是什麼原因導致了自己人生的不幸。但我深信,儘管有過不少的快樂與歡笑,某種導致不幸的東西在我年少時就已經埋下了種子。久久的沉思,使我想到了爸爸的多種病痛以及噩夢般籠罩著我們全家的疾病和死亡氣息。
只要覺得什麼有趣,拉斯舅舅就不會放過。今天早上吃早飯時,他問我小時候什麼時候最快樂。他坐在桌邊望著窗外,神色黯然。從他提問的樣子來看,他顯得很傷感,似乎是在思索自己孤零零的獨身生活。但我只是最膚淺地理解了他的問題,並盡量給他一個恰當的回答。
他的話顯然引起了在座的人的不愉快,因為他的話影射了艾文思小姐。我感覺路易斯先生就要拉開架勢跟他單挑(我本想有好戲看的),不過所幸看在主人的面上,只好作罷了。整個晚上,我hetubook.com•com都覺得艾文思小姐藍灰色的眼睛和圓滾滾的臉都關注著我,讓我沐浴在她溫暖的關照之中。道別的時候,她俯身過來,離我非常近,我感覺到她的一綹頭髮拂在我的臉上。她咬著耳朵對我說,我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女子——她說這是我這類女性的一大榮耀——並說我必須永遠堅守自己的信念。
這一事件在我腦中盤旋了很長一段時間。我不明白,這一詞語怎麼會讓爸爸如此緊張和惱怒?
阿爾弗雷德.魯塞爾.華萊士先生今天到唐豪斯來度週末。像往常一樣,他的來訪總是突然地造成一種危機氣氛。甚至在客人還沒有到來之前,爸爸就開始結巴了——像他經常在華萊士先生面前那樣。我想,這是可以料想到的,因為爸爸對任何社交活動都反應過敏。而在這種情形下,華萊士先生的正當要求——申明自己是自然選擇理論的共同發現者,就更要加重他的病情了。
我的臉簡直紅透了,整個下午都不敢看他們的眼睛——雖然很難說到底是因為我的偷聽行為呢,還是因為與他們身分最不相宜的陰謀。但不管是什麼原因,晚飯前不久,媽媽把我帶到一邊對我說,爸爸對我非常生氣,並說要送我到倫敦的拉斯舅舅家住一段時間,好讓他消消火氣。
一八六五年二月八日
我興奮地講起小時候的事,尤其是當他到唐豪斯來做客的時候,我們這些小孩子就像一群小狗一樣成天跟在他的腳跟後面轉。在我心裡,還珍藏著他帶給我們的那些快樂的回憶。他給我們講他在非洲和印度的冒險經歷,講他用瘦長的手指捉妖怪、猴子和小魔鬼的故事。看到這些話似乎讓他開心了些,我於是又繼續講我們去倫敦看大展的事。實際上,是後來他們給我講的,我只有一點非常模糊的印象了。我只記得自己緊緊地抓住他的手,生怕被人山人海的人群擠掉了。我回憶起我們去逛動物園。我特別喜歡懶洋洋的河馬。我們還到武姆韋爾動物園去觀看穿著童裝的猩猩。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六日
「我建議借用赫伯特.斯賓塞的一個術語,」華萊士先生回答道,「它最能精確地總結這一理論,並且避免了對任何更高級力量的指涉。」
他已經不止一次那樣過分地自責了。幾年前,在媽媽對宗教最虔誠的時候,她曾悄悄給他寫過一封信,表達了一種深藏內心的悲傷:她擔心,如果他不回到上帝身邊,他們就可能無福永生相守。我是碰巧在他書房的書桌裡看到的。他把它藏在書桌裡,經常拿出來看。有一次我碰巧到他房間,但他沒注意到我。我看見他情緒異常地激動,嘴裡叨念著一些自責的話:「要是她明白那原因就好了。要是她明白那原因就好了。」好長時間我都沒明白這話的意思。
這天晚上,托馬斯和簡.卡萊爾都來了,另外還有亨斯利和范妮.韋奇伍德,以及其他三四個知名人物(其中包括說話比寫的新聞報導生動有趣得多的哈麗特.馬蒂諾)。想想我有多驚訝,晚飯結束後居然又有一對夫婦來了,而且他們只是來喝咖啡和白蘭地的。但當我被引見給瑪麗.安.艾https://www.hetubook.com.com文思時,我感到特別窘迫。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我竟與自己最崇敬的人站在一起。她是《弗洛斯河上的磨房》和《織工馬南傳》的作者,但她的筆名喬治.愛略特把我一時弄糊塗了。讓我更尷尬的是,接下來與我說話的是她的情夫喬治.亨利.路易斯。他很鄙視人們對他倆關係的指責。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完美的紳士。我覺得舅舅非常了不起。他竟然為這樣兩個敢於蔑視社會習俗的人物也敞開著大門,尤其是公開與有婦之夫同居的艾文思小姐。
「哎,什麼詞啊?」
可是,我發覺要制服自己的好奇心太難了。今天下午,我決定去查看爸爸從小獵犬號寄回的標本。他從沒明確禁止我們看那些東西。它們被分散存放在家中最為奇奇怪怪的地方。我在溫室的兩個很深的櫃子裡找到整整的一個密窖。溫室是爸爸對會吃昆蟲、氣味極為難聞的茅膏菜進行實驗的地方(他教會了這些植物吞食生肉——它們真是巴不得呢)。
客人們到達的時間早晚不一。康福特為了接他們,可累壞了不少馬。媽媽打發艾蒂、倫納德和我下午到伯祖母薩拉家裡去,免得礙手礙腳的。我們回來時差點沒趕上晚飯。赫胥黎先生對自然科學的大加讚揚使得談話非常活躍。他還宣布說,對於一個沒有接受過關於大自然壯麗景致的教育的人來說,漫步於鄉間那「充滿著瑰麗藝術品的長廊中,十有八九都不過是面壁而立罷了」。
聽到這話,爸爸猛地一挺身坐直,問道:「啊,怎麼會呢?」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四日
我們一家就像是我們那可堪同情的女王。四年前她失去了心愛的艾伯特,但時時還得聽人們談起那事。她至今仍未從傷悲的迷亂中恢復過來,每天都穿著素服,並且每天早上都要重新把他的衣服擺出來。
今天有件事情讓我想起來就害臊。下午早些時候,爸爸在他房裡還沒起來。華萊士先生已經告別去火車站了。赫胥黎先生和賴爾先生在爸爸書房裡開會。他們有一點神祕兮兮的,似乎討論的問題是保密的。這自然地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於是幾分鐘後,我不慢不緊地走進房屋中間的大廳,在門外等著。我的直覺很快就有了回報,因為我偷聽到他們熱烈而令人非常感興趣的談話中的一些隻言片語。
我知道自己聽到的是最為有趣的陰謀。我幾乎不敢呼吸,唯恐聽漏了一個字。於是我往門前靠近了一點。但就在這個時候,偏偏是爸爸下樓來看見了我。我趕緊開溜,雖然我敢肯定他已經看到了我沒有一點女孩樣子的偷聽行為。一點不假,他跟著我走進客廳,抓住我的手腕,質問我在幹什麼。我的申辯沒人會信——也難怪,我本來就被抓了個正著。他突然轉身離開了房間。
「不過,」卡萊爾說,「這一措施並不是針對像您這樣的女士的,而是專門針對下層人的。」
「請你給我們說說好嗎,你用什麼詞來換?」赫胥黎先生問道。
達爾文家所有死去的人中,最讓爸爸傷心的是安妮。我覺得他總認為是自己的錯——她的離去是某種報應https://www.hetubook.com.com。記得艾蒂曾跟我說,爸爸在給安妮寫長篇的紀念文時,她仔細地觀察了爸爸。他寫得很慢,常時不時地輕聲哭泣。她說,至少在她看來,他臉上有著一種負疚感。
讓我們最為悲傷的大概是十四年前可愛的安妮的不幸夭折。老實說,我並不記得安妮了,因為她走的時候我才四歲。不過有時我也能想像出她的樣子——十歲,溫柔可人,一對紅撲撲的嘴唇和一頭金色的鬈髮。他們告訴我說,我們幾個女孩同時患了猩紅熱。她最嚴重,而且再也沒有好過來。她在莫爾文接受水療,在死亡之門一直徘徊了數週之久。爸爸晝夜守候在她的床前。但他沒有去參加她的葬禮,這讓我感到很奇怪。所有這些都是我從伊麗莎白阿姨那裡聽說的。父母從來不說安妮的死,甚至連安妮這個人他們都從不提起。
雖然沒人提起過安妮,但她在我們家裡仍然陰魂不散。幾年前,我在一個箱子底下發現了她的寫字盒。在我一個人的時候,我偶爾還會想起它來。它是用一種漂亮的硬木做成的,裡面放著邊緣為深紅色的乳白色信箋和色彩與之相稱的信封,木柄的鋼質筆尖,兩隻鵝毛筆和一把珍珠母柄的鉛筆刀。另外,在一個小盒子裡還有紅色的封蠟和封箋紙。盒子上面印有一些裝飾性文字:「歡迎我嗎」和「上帝保佑你」。鵝毛筆尖上還有墨漬。以前我常常拿起筆,想像自己就是安妮,像她那樣給筆蘸上墨水,一面苦思冥想地遣詞造句,給這人或者那人寫信。
華萊士先生個子很高,有些兒冷漠超然。他給人一種印象,彷彿在摩鹿加群島和巴布亞新幾內亞島的野蠻人中遊歷八年後,對英國社會已不太適應。我看到他身上有種鋼鐵般堅韌的東西。他讓人很難捉摸,並在我心裡激起了某種隱約的感覺。但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我也沒法解釋,因為他對爸爸和我們全家人總是那麼友善和敬重。艾蒂從他的舉止中看出他出身低賤、庸俗,因此沒什麼了不起。但我卻總覺得,迅疾、狡猾如他的某個標誌性物種,僅憑本能就能占據上風得以存活。
赫胥黎先生說話的語氣似乎非常肯定。他接著說:「他是一隻繞著我們雞舍轉的狐狸。他可能給我們造成無盡的麻煩,損害我們的事業。」對此,賴爾先生提了一個問題:「你認為我們該怎麼辦?」稍稍沉默了一下,接著的回答是:「我這會兒還不是太擔心。他朋友不多,也不是哪個學術團體的成員——我們一直很在意這一點——而且他總是缺錢。那是他最大的弱點。如果我們多點心計,就可以利用他這點。」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五日
聽到這話,滿桌子的人都歡呼起來,弄得我滿臉通紅。不過艾文思小姐解了我的圍。她堅稱我這樣說是有很多證據和理由的。其他人又大笑起來。但她突然提高嗓門宣布說:「我常常有這樣的想法——我非常不願說出來,也因此而壓在心裡沉甸甸的——我寧願自己生下來是一個男孩而不是女孩,因為誰也不能否認,在當今的英國,無論從哪方面來講,男孩的命運就是比女孩好。」
為了這個週末不那麼緊張,爸爸還邀請了其他一些客人,包括賴爾先生和赫胥黎先生。賴爾先生性格有點兒陰鬱,說話聲音很小,必須要豎著耳朵才能聽得清楚。但我最喜歡赫胥黎先生。他最有趣,精力旺盛,而且反應快,表情生動。他是爸爸最忠誠的護衛者,稱自己是m.hetubook.com.com「達爾文的鬥牛犬」(雖然我覺得他更像一隻捕狐犬)。有時我覺得他像一個革命將領,像博物學上的一個拿破崙。他發動了一場旨在反對教會和打著純理論旗號的科學研究的軍事戰役。
接著,他又描述了最近人們對爸爸的理論的攻擊,以及他自己迎擊那些批評的努力。聽他說,他的反擊大獲全勝。他說,在倫敦各大俱樂部的閒談中出現了一個新詞:達爾文主義。當他說到這點時,我忍不住偷偷往華萊士先生的方向瞟了一眼,看他對這話有何反應,因為有時我很想知道他是否會心存嫉妒。但他的臉上只是一副沉靜的表情。過了一會兒,他提出一個建議,說這能確保該理論的任何細節都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難道不是嗎,」她說,「一旦結婚,女人的財產就落入她丈夫的手中?難道不是嗎,一個女人只須被指責為通姦就可以立即休掉?」(在說這話時,艾文思小姐對自己的通姦行為沒有一點愧色)。「而一旦到了法庭,她會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合法權利,不是嗎?」
聽他講(三年前第一次來訪時),當他在劃分摩鹿加群島的濟羅羅島上兩個敵對部落間的無形界限時,他就想到了這個理論。他患了瘧疾,躺在一間茅棚的草蓆上。房屋兩旁長著一排排的棕櫚樹。這一觀點在他腦中突然變得非常清楚。像爸爸一樣,他也受到托馬斯.馬爾薩斯作品的影響。他推想,疾病、戰爭和饑饉往往會制約一個民族,而使這個種族不得不自我提升,「因為每一代人都這樣,弱者必然被消滅光,而強者得以保存下來。」
我們剛剛坐定,談話就變得活躍起來。馬蒂諾小姐一如她的寫作筆鋒,攻擊奴隸制是最「令人憎惡的制度」,並說在所有民族中,美國人最是野蠻。拉斯舅舅——無疑是火上澆油,因為他從未表現過對窮苦人的關心——問她對「戴著鐐銬的人們」的同情是否也推而廣之到英國的勞苦大眾頭上。另一位先生也說,中部地區的挖礦工人所遭受的奴役與美國南方莊園的奴隸並無多大差別。
如果赫胥黎先生沒有一點輕慢就不是赫胥黎了。他對這一提法不屑一顧,一邊喝咖啡一邊對華萊士先生說:「我要說,如果您要的就是這種強烈的反應,那麼您還真找準對象了。」
說到這裡,哈麗特.馬蒂諾頗有感觸地回憶起可憐的卡羅琳.諾頓的故事。她丈夫毆打了她九年,剝奪了她的財產,分居後還惡毒地到法院告她,拒絕讓她見三個兒子。
對此,亨斯利令人非常不愉快地反對說,貧窮者的墮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基督教的問題就在於滋養了罪惡。馬蒂諾小姐表示反對,並從自己的研究中引證了工廠事故的例子。
聽到這詞,爸爸的反應是如此強烈,我想他會中風的。他面如死灰,一手猛地按住胸口,像是心力要衰竭了似的。他顫巍巍地站起來,說了聲對不起,離開桌子回臥室去了,整個晚上都沒再出來。
「這個詞語開啟了誤釋之門,因為它似乎暗示自然的力量——您與我都贊同它們是非人格的,隨意性的——是在某種更高級的意識操控下起作用的。選擇那個詞似乎表明確有某個實體之類的東西在執行著這種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