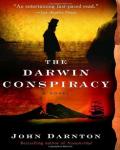第十章
他們又起錨揚帆前行。
「隔離!」查理未及細想,結結巴巴地說道,「但為什麼?這裡有什麼疾病,這麼可怕?」
「我想你知道菲茨洛伊船長偏向你吧,」麥考密克突然說。
於此,兩人都放鬆了下來,開始爭論起猴麵包樹的尺寸來。查理認定它非常高,而麥考密克則肯定說是樹幹的幹圍給人造成的錯覺,使它顯得那麼高的。他們還押了賭。
麥考密克咬著下唇。查理不知道他是憤怒還是傷心。
「絕對沒問題。」
兩人都有些慍怒,有足足一刻鐘都沒有說話。他們一直走到一棵枝葉繁盛的猴麵包樹前。樹幹的直徑有十六英尺,上面刻滿了姓名縮寫字母。他們坐在樹下休息。查理從肩上解下一隻水壺,兩人喝了些水。
第二天早上,他和菲茨洛伊划船去奎爾島。那是一片光禿禿的火山岩。他仔細地察看那裡的地貌結構。他在滋生著大量標本的潮汐形成的水塘裡搜尋,其中還捉到一隻讓他欣喜萬分的會變色的章魚。回到船上,他把一籃子的標本遞到他看見的第一雙手裡,全然沒意識到伸手的竟不是別人,而正是麥考密克。那人接過標本,把它一下扔到甲板上,眼睛死死盯著他。查理正高興著,也沒太在意這些。他忙著把部分戰利品解剖了,另一部分則放到酒精瓶裡寄回國去。
麥考密克嚇了一大跳。
查理心中有一種難以抑制的念頭,他覺得雖然他們身著文明社會的服裝,但一旦有機會,他們就會回返到他們原始的生養之地。
「而且——肯定你也知道,他嚴厲訓斥過我。五天前,他把我叫到一邊,懲戒我不要煩擾你,不要自以為——他的原話——我們在考察方面擁有平等的權利。」
「你是否注意到,」麥考密克接著說,「那個岩層裡的貝殼與海灘上看到的一樣?」
查理非常吃驚,他居然那麼快就轉變了自己的觀點。
查理想了想,沒有回答。他不想答應一件讓自己日後後悔的事。但麥考密克那副悲哀的神情觸動了他悲憫的心腸。他拍了那人肩膀一把,裝著輕快地說:「當然可以——但得提醒你,適可而止。」
「約克壞人,」他說,「他們部落都壞人。」
接著他的臉上被塗上瀝青和油彩。有人用一塊生鏽的鐵環給他「修面」。他覺得有些鬍鬚都被拔了出來。然後隨著一聲信號——肯定是菲茨洛伊發出的——他覺得自己被腳朝天翻轉過來,落在一面裝滿海水的帆裡。有兩個人把他往水裡按,其中一個人動作很粗野。他掙扎著吸了一口氣,又被按了下去,在水裡憋了似乎好幾分鐘。正當他覺得自己要被淹死了時,兩人鬆開了手。他像躍出水面的鯨魚噴出一口水柱。過界儀式結束了。這是他人生中最為可怕的一次經歷。
「是山羊骨頭,我敢保證,」麥考密克說,「附近肯定有大型動物。」
查理也跟著他大笑起來。他是想聞它的味道嗎?有時在這種情況下,他忍不住會問自己,傑米對學習的愛好是一種本能的作用——一種他在他自己的世界裡(在那裡少有得到運用)就基本會利用的東西,還是在文明社會看到各種奇妙之物後才培養出來的。一個人可否牽著任何一位具有天分的野蠻人,像教小孩子一樣教他呢?他又能達到什麼程度呢?他肯定達不到一個十二歲的英國孩子的水準。
小獵犬號向南駛往維德角群島時,船上生活好轉起來。當它進入熱帶的溫暖水域後,起伏的波浪變得平穩了。早晨的陽光像燃燒的箭,從蔚藍的天空直射而下。而到傍晚,太陽又像一個橘紅色的火球沉落在大海裡。月亮在和-圖-書水面灑下一片粼粼波紋。
第二天,他們出發去測量那棵猴麵包樹。菲茨洛伊量了兩次,先用的是小型六分儀,接著又爬到樹頂,從上面放繩進行測量。兩次的結果都一樣:樹遠不及它看上去那樣高。菲茨洛伊畫了一個草圖以證明這一點。麥考密克勝了查理,欣喜若狂,一定要他當場給錢。當查理從褲子口袋裡掏出一枚硬幣遞給他時,他又一次窺見他的敵手臉上那冷酷的表情。
「那還能怎麼解釋?」
「我不得不告訴您,先生,」上尉說,「我認為他堅持不了整個航程。我敢保證,下次靠岸時,我們就將再也見不著他了。」
「我帶你到我的國家。你去見見我們那兒的人。你去和智慧的人談話。很多窺─穴,很多談話,很多。」
有人扔給查理一條毛巾,讓他把身上擦乾。甲板上到處是水、顏料和肥皂泡沫,非常滑,他不得不緊緊抓住索具。他留在那裡觀看其他的人,覺得除了最後一個外,大多數人比他更慘。但相比於最後那個人,他算是被折磨得夠嗆的了。這時他注意到站在齊膝深的船帆裡的兩個惡霸中有一個是麥考密克。他的前臂油亮油亮的,上面全是汗水和海水。
傑米.巴頓緊挨著查理坐在大桌子邊,在看博物學教科書裡的豹子、蛇和其他動物的圖片。每看到一種認識的,他就會興奮得侷促不安地伸出粗短、棕色的小指頭去觸摸。
「但最起碼,你能幫我一個小小的忙吧?」
只有傑米例外。他與另兩個人不同:火地.巴斯克特是一個快樂但智力低下的十一歲小女孩;約克.明尼斯特則是一個性情陰僻、乖戾的年輕人,有二十五六歲。被綁架後,三個人都配了個英語化的名字。傑米.巴頓是被人誘拐的。菲茨洛伊把他從一個駕駛獨木舟的老頭那裡買過來。為了交易公平,他當時一怒之下從緊身短上衣上扯下一顆珍珠母紐扣扔在那人的腳下。
不到一個星期,小獵犬號就到達了聖賈戈河西岸,然後停泊在波多普拉亞灣。當划艇靠近岸邊時,查理感到全身血液奔湧——終於能把腳踏在堅實的大地上了!但奇怪的是,腳踏上陸地時並沒給他多大異樣的感覺。他並沒找到自己長久夢想著的那種輕舒的感覺。或許是他到底已經習慣於乘船了吧。
也許是因為缺少可資研究的標本,達爾文的科學熱情受到挫折,所以他才對三個雅馬納族印第安人特別著迷。儘管自己生了病,但自從遇到傑米後的那個星期,他經常去找他們,觀察他們對船上世界的反應。他們對輪船並不陌生——兩年前回英國的過程中,他們在小獵犬號上就待過八個月——但他們似乎仍對船的運轉很覺神祕。他們用一副昏昏欲睡的眼神來掩飾自己的迷惑。大部分時間裡,他們都躲在甲板下面,只有在風平浪靜時和似乎有著某種神祕意義的日落時分才敢上來。他們是一個怪誕的三人組合——全身上下的英國服飾,把自己打扮得絕頂漂亮,睜大雙眼凝望著沉落天際的橘紅色圓盤。他們黑色的皮膚也像在燃燒。
他比劃了幾個手勢,開始模仿一個動作。他野蠻地笑著,在他的關節上做拉鋸的動作,並張大著嘴巴,用指頭摸嘴。他走後好一會兒,查理才明白他要表達的意思——約克.明尼斯特的部落吃人。
查理豎起耳朵想聽聽船長的反應,但卻沒再聽見什麼。他知道他們在說自己。他的反應很複雜。開始時他發誓一定要讓惠格姆的話落空——他要堅持到航程的終點,因為他最想得到的就是菲茨洛伊的尊重。但轉念一https://www.hetubook•com.com想到陸地上豐富多彩的生活,他又開始動搖了。他覺得自己放棄了這旅途上難熬的艱辛也沒什麼大不了,尤其是他們倆都這麼看了。他們對自己的輕視已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
正在這時,菲茨洛伊走了進來。看見查理,他有些尷尬。這就更證實了查理的懷疑——他們剛才說的是自己。為了掩蓋這種尷尬相,船長說了幾句話以長長他的士氣。
「嗨,你知道明天黎明時我們會到什麼地方嗎?聖克魯斯呢!從錢有所值的角度來說,就再沒有更好的港口城市了。尖頂的建築矗立在白雪覆頂的山峰前面。總之,那一切都是造物主本人的傑作。」
傑米.巴頓就在不遠處。聽到他們的話,他轉過頭去,興奮得臉都扭得變了形。他記得英國人總是傲慢地認為自己國家什麼都強。
「我認得那個。我在我們國家見過的。」他咯咯地傻笑著說。他雙手捧起書,把鴕鳥圖畫舉到面前,離鼻子不過三英寸的位置。
他沉默了一下,想了想又補充道:「而且我敢說,倘若我有幸親自見過那島嶼的話,解釋起來就會更容易。」
那天夜裡躺在吊床上,聽著金的鼾聲,透過天窗看著運轉中的月亮和星斗,查理感到自己既沒有目標,也微不足道。他懷念什魯斯伯里起伏和緩的青山。他從未有過這樣的渴望。他決定:在聖克魯斯下船,讓一切都見鬼去吧。他不適應海上生活——這與意志力毫無關係,是他該死的胃不爭氣。誰也拿它沒辦法。
查理用他的科學儀器來吸引傑米,以供研究。這個印第安人從來對看顯微鏡樂此不疲。他喜歡觀看頭髮節和亞麻絲。有一次,一隻在船艙裡發現的蟲子被放到儀器下面,牠的一條腿動了一下,差點把他的魂給嚇掉。他似乎覺得自己與查理間有著一種特殊的紐帶。這讓那位英國人感覺很有趣。他覺得很是怪異,居然這個原始人認為科學這一概念能把他們倆連結在一起。傑米把它讀成「窺─穴」。不過他是否完全理解這一抽象概念,則不得而知了。
查理不知該怎樣來培養他。他很聰明,但對人有防範心理,有時很自負,有時又一副卑躬屈膝的樣子。他的英語裡夾雜著一些古怪的語句。當一個水手問他的身體怎樣時,他會一臉奴顏地笑著回答:「健壯著呢,先生,沒有更好的了。」而有的時候他又裝著聽不懂。他喜歡欺凌人,對待火地.巴斯克特如低等動物。這讓約克.明尼斯特很氣惱,因為他把她看作自己的妻子。傑米的視力遠比任何英國人都好——即使站在甲板上,他也能比水手們更先看到海平線處的物體——曾有一次,廚師沒多給他一份布丁,他很生氣,並威脅說:「我看見法國船,我不說。」
一天下午,查理斜靠在菲茨洛伊的沙發上讀洪堡的著作。他聽見菲茨洛伊與惠格姆在房艙門的另一端輕聲談話。
第二天早上,小獵犬號在港口下了錨。他走上甲板,呼吸著夾著鹽粒的芬芳空氣,心中充滿了希望。在他面前是一片壯麗的遠景:火山形成的山峰巍然聳立在小城上空,上面點染著片片綠色。房屋都塗成燦爛的白色、黃色和紅色。他能辨認出城市建築上空飄揚的西班牙國旗和沿著碼頭行進的馬車。
查理很感動。他想到和一群赤身裸體的棕色皮膚的男人坐在一起談論更高知識領域的問題,覺得很是好笑。但他沒有表露出來。
艙口開了,下來四個海神的軍士。他們直奔查理,拽住他的肩膀和雙腿,把他上身扒光,然後蒙上眼睛把他帶到上層甲板。聖歌在空中和圖書迴蕩,沉重的舞步震得船板直抖。無數桶水劈頭蓋腦地潑下來,弄得他差點喘不過氣來。他被帶到一塊厚木板前,並強行要求他站在上面。
傑米在專心看著動物圖時,查理則在對他進行研究。他是一個十足的花|花|公|子。即使是在馬上就要刮起西南大風的甲板上,他也戴著白手套,穿著燕尾服。他到處招搖,喜歡照鏡子,而且總是把襯衣領子打理得白晃晃的。倘使發現靴子上有哪怕一點汙跡,他就會怒沖沖地跑回房間去把它擦乾淨。要是誰調笑他像個花|花|公|子,他就會把鼻子昂得高高地說:「好多雲雀啊。」
他抬頭看著麥考密克,心想:這個鄙陋的東西對標本採集的意義的理解比我的獵犬高明不到哪兒去。有誰能讓他明白自然科學的魅力呢?
「你能讓我隨同你的物品寄一些標本回去嗎?很顯然,你搜集到的將是一個巨大的數目。我很難想像你會騰出一丁點空間給我。還沒上船前,我就指望這次航行能給我一個成就的機會,使我成為一名搜集家。」
「得了吧。你和那人一起進餐。你在他房間看書。你陪他出遊。在這種情形下,你想想我能和你競爭嗎?」
「我從未覺得我們在競爭。」
「你可真笨,去碰牠,」麥考密克說。他在近旁,很想過來幫幫忙,但被查理婉言謝絕了。查理把手指放在嘴裡。水母的黏液把他口腔上顎刺得生痛,但他極力不表露出來。
有人曾告訴過查理,傑米與另外兩個來自不同的部落。他們的部落居住在高地,骨骼較小,進化得也好些。他們自認為是文明民族。聽菲茨洛伊說,他剛到小獵犬號船上時,非常可憐,因為另兩個火地島人譏諷和折磨他,並稱他是「亞僕」——很明顯是敵人的意思。而菲茨洛伊雖然對雅馬納人非常感興趣,但他似乎對他們出奇的冷酷。有時他戲稱他們做「雅虎」——《格列佛遊記》裡骯髒的人形獸的名字。
除了一副慘相,查理仍然一無所獲。在過去的十天裡,除葡萄乾和餅乾外,他什麼也吃不了。甚至他與船長的進餐也取消了。他的體重降得很快。他覺得自己就要瘦成皮包骨了。當船路過馬德拉島,距離岸邊只有一臂之遙時,他甚至沒起來看一眼,儘管島上有眾多的同胞在那裡度假。
他們在巴西海岸的聖保羅岩作了短暫停留,儲備了些新鮮食物。菲茨洛伊和查理乘坐一艘尖尾快艇到島上去暢快地玩了一番。那裡的鳥不怕人,水手們徑直走上去就可以用棍子打著。他們甚至徒手都抓到一些。另一艘帶著麥考密克的汽艇也準備上岸去,結果被浪打得遠離了,於是只好開到港口去釣魚。水手們拋出魚線,釣起不少石斑魚。他們揮舞著槳擊退前來掠食的鯊魚。
「現在該我祝賀你了,」查理觸摸了一下帽子說,「毫無疑問,你是正確的。」
幾天後發生的一件事情,給查理造成了從未有過的不安。因為最近的休戰協議,他和麥考密克仍結隊出行。他們穿過一片平如桌面的高地,來到旗杆山——一個以周圍的荒野而聞名的海岬。在山的北邊,他們發現了一條約二百英尺深的狹窄山溝。找了好一段時間,他們終於發現一條通往溝底的陡峭石徑,於是便沿著小路走了下去。
三天後,查理寬宏大量地捐棄前嫌,邀請麥考密克乘牛車一同深入內陸去。讓人吃驚的是麥考密克居然同意了,因為他看著查理晾曬的標本在船尾的上層甲板區占據的位置越來越寬,他嫉恨得要命。
但接下來的一件事讓他更為不安。在回汽艇的路上,麥考密克側身趕到他面前假惺惺地說:「順便說https://www.hetubook.com.com一下,昨天我碰巧去了奎爾島。我看到了你說的那個岩石層。確實有點奇怪,不是嗎?我真的希望你關於其構造的理論是正確的。」
查理不曾注意到。「那又怎麼樣?」他有一點防禦的架勢。
他的話很有氣度,但他心裡卻不是那麼回事。他心想,這傢伙不是個傻瓜,東西學得快,而且還進行了細化和發展。我們可絕不能讓徒弟超過了師父。
他們還沒出發,麥考密克就開始抱怨起天太熱來。為了轉移他的注意力,查理給他描述自己在奎爾島上看到的讓人奇怪的地質構造——一條距離地面約三十英尺的水平白帶從嶙峋的懸崖上穿過,近看時像是一個貝殼和珊瑚的壓縮層。很明顯,它曾位於海底。是什麼使它懸在了半空中呢?他向麥考密克提了一個問題。
「不是這裡,」船長回答說,「是英格蘭。他們怕我們攜帶有霍亂病菌。」
「在我看來,那表明不管是什麼地質運動導致它上升的——比如說地震或者其他地殼運動——其發生的年代必然不會太遠。」
「陸地上升到空中?什麼——像弩炮?比你在劍橋大學的異端邪說更有點嘩眾取寵的味道。」
濕熱的空氣迎面撲來。不知名的昆蟲在他周圍嗡鳴;不知名的花兒絢麗地綻放著。那茂密的植物,那陌生鳥啼的合奏,那果樹與棕櫚與藤蔓的華蓋以及透射下來的束束陽光——那異域的喧騰的一切,讓他如醉如癡。這就是他曾夢寐以求的東西,就像一個盲人夢想著光明。
查理感覺好些了。他開始又充滿了希望,甚至還做點工作。他做了一個四英尺深的浮游生物網,用一根曲棍撐開掛在船尾。才兩個小時,他把網傾倒在甲板上,裡面就捕到各種的海中生物,其中包括一隻水螅和一隻僧帽水母——把他手指給螫了一下。
他們決定搜索一下。查理備好槍,走山谷的一端,麥考密克走另一端。他們正摸索著往中部靠近時,查理突然聽到一個響動。他一轉頭看見麥考密克就在離他不過十英尺的地方,槍口正對著他,臉上一副狡黠冷酷的表情。
「偏向我?我請你說清楚你指的是哪方面?」
他們踏進的那片谷地另有一番天地,裡面到處是繁茂的植被。谷底藤蔓遍布;長於岩石架上的樹上擠滿了各種各樣的昆蟲。受到侵擾的鷹和烏鴉在他們近旁飛騰聒噪,想把他們嚇唬走。一隻樂園鳥從隱蔽的巢中突然飛出來,消失在現已距離他們頭頂很遠的一隙藍天中。
「好啊,我會非常高興的,」他說。
查理表示懷疑。「整個海洋嗎?」他問道,「這些火山島本身似乎也沒那麼老。這個解釋不通。」
最後,小獵犬號到達了赤道。查理自然早就聽過關於那種古老儀式的種種傳說。儀式被稱作「過界」,充滿著小學生的惡作劇味道。但船上的人都講得不具體。恰恰相反,他們故意說得模模糊糊又挺嚇人的樣子來拿他開心。二月十六日,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他和另外三十二個「格里芬」——新來的人——被關在下層的甲板上。艙口被封死,裡面一片漆黑,而且悶熱難受。查理曾看到一眼艏樓,他覺得他們肯定都瘋了:菲茨洛伊扮作海神尼普頓的模樣,身穿一件托加袍,手持三叉戟,坐在上面。下面是一群身上塗著色彩的、半裸的人在和著笛子和鼓聲瘋狂地舞蹈。
查理根據賴爾的觀點提出了自己的理論。他說,山崖的隆起是其底座的劇烈運動導致的,而那個相對平穩的帶狀構造則表明作為其成因的地殼運動是一個漸進和遞增的過程。
從輪船有節奏的起伏裡,查理開始體會到了一種美的感覺。
https://www.hetubook.com.com他很羨慕水手們在索具上攀爬的身影,有時只能透過船帆才能看見他們的一個個影子。夜裡,他喜歡傾聽海浪衝擊船頭的聲音,喜歡聽桅杆上船帆呼啦啦的聲響。船友們給他起了個雅號——阿哲——哲學家的簡稱,以表他對自然科學的熱愛。這個雅號很快就為大家接受了,因為它避開了前一陣子他的地位問題的尷尬:對於一個沒有頭銜的上層平民,這個尊稱再好不過了。他跟隨著菲茨洛伊參加了許多社交活動,會見了葡萄牙總督和美國領事。然後,他在城裡四處走走瞧瞧,看到扛著木製武器的黑人士兵,赤|裸上身的棕色小孩和一欄欄的豬羊。他來到城郊的一個深谷。在這裡,他終於——總算見到了洪堡的熱帶樂園。
船在維德角停留了二十三天。那期間,菲茨洛伊對那些島嶼進行了精確的定位。然後,小獵犬號又揚帆起航了。他們往南航行時,氣溫與日俱增。大部分的時間,查理仍感到噁心。而現在,他又覺得昏沉沉的。用他對金的話來說,那感覺就像是「燜在熔化了的黃油裡」。
「但看看這些東西,雖然牠們在大自然中屬於低等級,然而牠們的體形卻如此纖美,色彩卻如此豐富。」他興奮得聲音都有些顫抖:「如此豐富的美僅僅為了成就如此纖小的目的。難道這不讓人覺得奇妙嗎?」
「看在上帝的份上,喂,」查理看著槍管叫道。
這時,槍管突然往旁邊一揚。查理聽見背後有窸窣的響動和一聲槍響。他轉過頭,看到一道色彩一閃,一隻動物的後腿躍進了一個洞穴|口。他推測那是一隻大型貓科動物。
醫生摘下帽子,擦了擦額頭。他說答案很淺顯。「那兒一度是海底。顯而易見,後來水位下降了嘛。」
麥考密克張開著嘴,瞪著雙眼,轉身走了。
傑米接著說,他們絕不能讓約克.明尼斯特或者火地.巴斯克特跟他們一起去。他從桌邊站起身,向門走去。
一隻小船開過來傳達領事的命令,接著是短暫的商談。菲茨洛伊失望地扭過頭——他不可能輕言細語地向他們講這個消息。他說,如果他們上岸,就必須進行十二天隔離。
當他們走下陰暗的谷底時,查理感到一種難以描述的緊張不安,似乎他們撞入了某種不知名的野獸的巢穴。對於這樣的迷信思想,他從來就滿不在乎,但卻又怎麼也擺脫不了那種感覺。這時,他聽見已到達峽谷谷底的麥考密克大叫了一聲,於是衝了過去。他發現他正盯著一堆各式各樣的骨頭,有些骨頭上面的肉還沒啃乾淨。
「一定。」
查理站在船頭近旁,感受著和風拂面的愜意。他仰望夜空,找到南十字座的位置。突然,他意識到自己不覺間已經做出了一個決定。他決心不放棄此次航行,無論前路如何,也要留在英國皇家海軍艦艇小獵犬號上。他要堅持到終點。在這個地球上,除了這艘裝備有十門炮、九十英尺長的船外,他哪兒也不會去。船上七十四個人的航海勇氣令他欣賞,他們的友愛之情讓他珍惜——除一個人外。
他們趕緊沿小路往上爬。到達開闊地帶後,查理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他覺得自己真是死裡逃生——雖然很難說到底是逃於人之手還是動物之口。
傑米突然合上書,看著查理的眼睛——樣子很不尋常。他好像做出了某種決定,想要談什麼重要事情。
那天夜裡,查理覺得自己已經越過了一條界線。他知道那些水手接納了他,自己成了他們的一員。他曾一槍就把一隻鳥擊落下來,令他們一直羨慕不已。如今,無論什麼時候,當他衝到甲板上去看海豚或者其他海洋生物時,他們都會和善地衝著他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