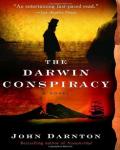第二十四章
貝絲讀完信,又把它小心地放回塑膠信封中封好,以便安全保存,然後又看了一下休的表情。
做好你自己的吧!
「你知道這麼多年以來我一直在寫一部自傳。」我點點頭。但我發現他仍然充滿疑惑地抬頭看著我,於是,我大聲地回答道,「是的,我知道。」以便肯定他能聽到。
「我原以為你這位達爾文研究專家對這兒瞭如指掌呢。」
你永遠都在我心裡。
我現在正以一個把你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人的身分給你寫信。要不是發生了那一連串令人傷心欲絕、難以敘說的不幸之事,我將會比任何活著的人都更珍愛你。當你還是個不足一天大的嬰孩時,你就從我的懷抱中被奪走了。我是在魯莽衝動之中懷上了你——那是一段不可否認的感情,而你便成了私生子。這只能怪我自己。對於這令人傷心的往事以及由此引發的種種後果,我請求你的原諒。我只能祈禱,願你的同情憐憫之心會淡化你對這不光彩事情的評判,因為你的性情特點中一定留有我的痕跡。我祈禱在時機成熟時,即使你不能完全理解我的行為,至少也不會在內心深處那麼憎惡地來看我。
這時,他放開我,倒在枕頭上,聲音之中顯得有些疲憊。「但是,你不知道我省掉了一章,當然我還是寫出來了,只是把它藏了起來以防有人看到。我想,寫下來後可以讓我感到輕鬆些,但是結果並非這樣啊。」我注視著他,不知道說什麼好。他也沉默了一會兒,抬頭看著天花板,似乎還沒有決定要怎麼做,然後嘆了口氣,指示我去取他的一些東西。而讓我驚奇的是,他要我找手杖。
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上個星期二,也就是四月十八日,爸爸開始虛弱了。就在午夜前,他心臟痛得厲害,吵醒了媽媽。她迅速從她臥室跑過來,又趕快去取戊基藥品,但慌亂之中腦子一片混亂,於是又打電話給我。要我過來幫忙。而等到我們找到一些他自己有所研究的藥品並再回到房間時,他已經倒在床上,看上去奄奄一息了。媽媽嚎啕大哭,引來了僕人。我們設法讓他吞下了一些膠囊,嚥下一點白蘭地酒,但很多都溢了出來,順著他的鬍鬚流到了他的睡衣上。但他甦醒過來了,眼睛突然睜開,還往盆裡嘔吐。但他因為顫抖得厲害,不能說話。然後,這個一貫的無神論者做了一件讓我永遠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把媽媽拉到身旁,在她耳邊急切地呻|吟道:去請個牧師。她跳了起來,欣然表示同意。然而爸爸的請求實際上不過是個沒有惡意的計謀,他只是想和我單獨待一會,他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只能講給我一個人聽。
「那你怎麼拿到鑰匙的?」
此刻,貝絲很想與休分享這個戰利品——最後一個謎底,於是她打了個電話,氣喘吁吁地告訴他:「一個小時後,咱們在克里斯特學院見吧。」她的語氣中還帶有和*圖*書那麼點命令的味道。而當他問什麼事時,她卻咯咯地笑著說:「每次淘寶都得善始善終啊。」
「從門房那兒拿的,我求了很多次,他才給我。現在小費也降了,才五鎊。」
「莉齊。但是她一直管自己叫貝西——多久了?差不多四十年了吧,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下面,我來描述一下今天的儀式吧。我希望你讀了它之後,能對外公的尊敬有了一種根基,接下來的任何新發現都不會將它破壞掉。你知道,外公受到廣泛的尊敬。昨天一整天都下著討厭的小雨。四匹馬拉著靈車從唐納村來到西敏,一路上紳士們都脫帽致敬。然後棺材在聖菲斯小禮拜堂昏暗的燈光中,在儀仗隊的護衛下過了一夜。今天早晨,人們又從四面八方趕來,不斷地湧進西敏教堂。雖然女王和首相格萊斯頓沒有來,但是其他的很多名人都擠滿了教堂的左右兩翼,包括穿著喪服的法官,議會成員,許多國家的駐英大使,知名社團的官員等等。在家裡,大家又都去安慰媽媽,她因為太哀傷而沒有參加。我很高興看到很多普通老百姓,包括我們的男管家帕斯洛。他們排滿了教堂中殿的兩邊,以至還要站到外面的臺階上來。中午時分,喪鐘開始鳴響,顯要人物要繞棺材走一圈,棺材上面蓋有黑色絲絨褶綴布,還裝飾小枝白花。唱詩班的人員則以「快樂,就是人們找到了智慧並獲得了理解」開始,唱著選自《聖經箴言》中的聖歌。儀式簡潔,也沒有太過於嚴謹,爸爸應當會覺得這恰到好處。之後,抬棺人——包括阿爾弗雷德.魯塞爾.華萊士,即理論的共同發現者(赫胥黎先生差點都把他給忘了,直到最後一刻才邀請到他)——將棺材抬到教堂中殿的東北角,也就是要下葬的地方。它正好就在艾薩克.牛頓先生的紀念碑下面。
我珍視對爸爸的這份承諾,不到他死後不打開箱子——也就是要到今天從西敏教堂回來後。在裡面,我發現了一個封好的包裹,裡面裝滿了文件,封皮上有爸爸的手跡。那是從他過去很多年前讀過的一本書《失樂園》中引用的。我決定不打開這個包裹了,因為我知道父親的這個祕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現在,通過這種方式。我把他生命中缺失的這一章傳給你,你按照你自己的意願去處理它吧,我相信你會知道在以後的歲月中怎樣安排是最好的。
一段時間後,媽媽和一個爸爸其實並不需要的牧師回來。她沒有看我,但很驚奇地發現了那根手杖,還在爸爸的手中。我覺得沒有必要解釋什麼,於是離開了房間,也沒再回頭看一眼。凌晨二點,醫生來了,父親吃了他的芥子膏後,又吐了。我只聽到他說:「只要我能做的,除了死,做什麼都行啊!」然後他就開始吐血,膚色也變暗了,我們餵了他幾勺威士忌後,他整個晚上和第二天上午都是在昏昏欲睡和疼痛的煎熬中交替度過的。等到下午,他已經失去了意識,發出刺耳的呼吸聲,最後死於四點鐘。那是一八八二年的四月十九日下午。
和*圖*書「是的,我還沒看。我想我們應當一塊兒看吧。我只看了附的那封信。」
「有一個,她兒子,叫班傑明,她女兒就是我母親,你知道,她可是得知自己跟達爾文家族有親戚關係的第一人啊。」
你來自一個高貴的家系,那是因為我的父母,也就是你外公外婆的高貴,他們是第一代表兄妹。達爾文家族一連好幾代都是醫生和學者,韋奇伍德家族則是著名的陶器生產商。你外公的爺爺是達爾文.伊拉茲馬斯,他是個詩人,哲學家,也是第一批信奉現在的進化理論的學者之一,儘管他那時還沒理解它的發生機制。而提供那最關鍵要素的任務就落到了你外公頭上,他就是查理.達爾文,著名的博物學家。你肯定知道,他提出了一個觀點:他認為,有著差別極其細微的各類物種的大自然自身在進行著適者生存的選擇,從而促成新的物種的形成。這個思想為他贏得了相當大的知名度,因為它和《聖經》中上帝創造了每個個體和物種的思想相對立——後者認為一切都在永恆之中保持固定不變。漸漸地,由於他的理論獲得了更多的支持——當然部分是因為少數能說會道的支持者們的努力,使他在英國社會獲得了非常受人尊敬的地位。
休沿著霍布森大街一直往前走,然後轉入五角塔下的地道拱門。一進去,他就發現庭院中央一片綠油油的環行草坪,鮮艷發亮得幾乎都要灼傷他的眼睛,周圍則由平滑的石子鋪成的走道環繞著。學院古老的城牆有三層高,每一面牆都有四個單獨的入口。鑲嵌其中的矩形窗戶,比例上絕對是完美至極,沒得挑的。其中一些還有花盆像瀑布似地垂下,裡面有紅的、白的小花。
「這個家譜中有男的嗎?」
穿過斯賓塞.傑克斯.哈欽森法律公司的層層防衛,貝絲終於來到了內部密室——老傑克斯.阿爾弗雷德本人的木鑲板辦公室。她出示了許多文件,證實了自己的身分後,才最終得到莉齊留下的那個包裹。這個包裹從一八八二年開始,就保存在該公司的保險庫裡。一個人把這像皇家珍寶般的包裹高高舉在手中,遞給了她。
「是的,她從來都沒有得到過。當然她的名字也不叫艾瑪,她的新家給她取名叫菲麗帕,我現在已經知道了這個家譜,她就是我了不起的外婆,一個大家都說是特別堅強的女人。」
也正是在這一天,爸爸(三十四年當中我大多數時間都是這樣叫他的)在西敏教堂永遠安息了,這也是我要寫信給你的一個原因。能在那裡舉行葬禮可不是個小榮耀,特別是對於一個自由思想家而言(實際上,我的一個很好的朋友,瑪麗.安.艾文思,兩年前就沒得到這一殊榮)。爸爸是想埋在我們所住的肯特唐納村聖瑪麗亞教堂。但在他死後,他的這個願望被他圈內的崇拜者否決了(包括他的長期擁護者托瑪斯.亨利.赫胥黎)。赫胥黎認為,埋葬在西敏教堂是他理所應得的,尤其是它還將提升科學的地位。於是他們發起了一場運動,其間那些權威人物都出面和教堂調解,使得他們的請願書在議會上獲得了通過。和*圖*書
「認識——怎麼可能?我從來都沒來過。」
不要責怪自然,她做了她應該做的;
英格蘭
「我明白了,」他說,「這就是他原來的房子。」
「某些時段會有人。」
在一張笨重而髒兮兮的長椅上,他們並排坐了下來。貝絲把手伸進籃子,拿出了一個很重的綠色瓶子和兩支笛子。瓶子上扣有一個盾形的蓋子。她說,這個以後再說吧。然後她又拿出一個小小的公事包,拉開拉鏈,取出包裹,把它舉在手裡。包裹用褪了色的棕色紙包著,還用麻繩緊緊繫著。
「這裡沒人嗎?」
在以後相處的日子裡,我和父親從來都沒有討論過這件事情,直到他死的那個晚上。當媽媽被支開,僕人被打發出了房間後,他把我拉到像剛才離他那麼近的距離,聲音刺耳地說,儘管他根本不是個嚴謹的人,也不相信神,但他確實有必要承認一個錯誤。他說,除了我沒有其他人能夠讓他解開心中的包袱,因為我是唯一知道他祕密的人。這時,我的血液凝固了。他靠近我,用一種我幾乎都不敢相信的力量抓住了我的睡衣邊。
於是我的敘說還得回到以前。長期以來,甚至從孩提時開始,我和爸爸之間的關係就不融洽。這可能源自於我們的個性差異(當然深究沒什麼太多意義),也可能是爸爸在工作方面的一些事情。我有了自己的各種各樣的事實依據,我發現了在五年的小獵犬號航海過程中發生的一些不幸之事的線索。這裡我不想一一作深入說明。只說一點就夠了。那就是在你出生前不久,我有證據表明,從廣度和深度上來說,他都不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思想家,而應屬於相當不同的道德等級。於是,在一封寫自一家蘇黎世診所的信中,我清楚明白地向他提出了這一點。也就是在那個診所,我被迫放棄了你。
肯特,唐納
休環顧四周,感覺這裡像大多數劍橋學生的住所一樣,雖然破舊了點,但還是很雅緻。裡面有一個有大理石壁爐架的磚製壁爐,一個舊窗座和有很多疤痕的紅木牆板。兩根桁條深深地嵌在灰泥中,中間還掛著個小巧的珠狀玻璃吊燈。地板是古橡木的,有如鐵般堅硬。得知達爾文年輕時住過後,休對這個地方有種說不清的感覺。
另外,我還想說說你外公過去的一些情況,希望你能寬容些,耐著性子讓我把它說下去。它或許能幫助你對他形成一個更豐|滿的形象來瞭解他。你外公病了好些年。事實上,他這一生健康狀況都不是很好。這麼說或許會比較合理些,自他從小獵犬號船上回來,他保存的大量日常記錄都可以證明這些。而最後幾年,他則是在幾乎細節上都沒有什麼變化的日常瑣事中舒適地度過的,儘管它們有時候免不了有些混亂。
和圖書「你覺得呢?」他問,「我們現在把它打開嗎?」
艾瑪,你要知道,我因為失去你而懲罰我自己。想想看,要是我能更明智、更正派,你我的生活都會是怎樣的不同啊。這樣的日子可不只是一兩天!然後我又想,不只是在過去那段流逝的歲月中,而是在任何時候,只要我有這種強烈願望的時候我都可以把你緊緊摟在懷裡,那該多好啊!沒有哪一天我不在想像中描繪你的形象,你的習慣,你的相貌,還有你的精神面貌。現在你都快十歲了,離你那重要的生日又只差四天了啊,在我心裡,我可一直把你看得像我一樣健康但遠比我漂亮!
「不,這完全是一種巧合,在他們從律師那兒得到通知之前我已經出生了,你還想瞭解一點悲傷的事情嗎?看看這個。」她把文件夾遞給了休。
她領著他來到離他們較遠的一面牆。入口處寫了個「G」,裡面的樓梯刷成了藍色。他們來到一樓,貝絲拿出鑰匙,打開門的右半部分,然後自己站到一邊,讓休先進去。
他把它放在一隻手上掂量著,像一桿秤一樣上下移動。不太重。
愛你的媽媽莉齊
「看看她是怎麼簽名的吧。」她說。
親愛的艾瑪:
其中有一面牆上刻著盾形紋章和警句:Souvent Me Souvient——他不假思索,立即就把它翻譯成:常常記起我。而恰好就在它下面,貝絲正提著個籃子站在那兒。一看到他,她頑皮地笑了笑,走過來挽著他的胳臂說:「跟我來。」
我去把它取來,然後遞給他時,他一把抓了過去,緊緊地握在一隻手中。隨著一聲抽泣,他說,在他死後——而不要在此之前。打開那個書桌底下上了鎖的箱子,鑰匙就在大書桌最上面的那個抽屜裡。他看著我走過房間中央,打開抽屜,拿出一把保險櫃的鑰匙。而當我充滿疑惑地再回到他身邊時,他仍然抓著那根我很想拿走的手杖,對我說了一句我永生都不會忘記的話:「在所有人當中,只有你知道我是怎樣一個人。」這時,他閉上了眼睛,變得很虛弱,感覺就像身體被淘空了,面色也變得很蒼白。
我這次寫信的目的是想告訴你有關於你的高貴血統,並遺留給你一份特別的文件。當我告訴你它是誰寫的和是在什麼情況下寫的時,你就會很容易理解它的意義所在。我決定不了到底怎麼處理它,總是在兩個反面之間游離不定——看看各自的優缺點,真的不知道是把它公開好,還是立刻把它毀掉好?如果你收到了,我想讓你以後將它保管好。當時間沖淡了激|情,腐蝕了我們對相關人物的記憶後,或許又由於新的大洲、新的時代,這種時空的距離帶給了你更多的智慧,你也將自己作出一個恰當的決定。總之,我現在是在給你一件禮物,同時也是賦予你一個重大的責任。
「不要告訴我你還沒看過它哦!」他說,「你可是經常到處看別人日記的啊!」
「的確是這樣。」和_圖_書
「那這也是她把你取名為伊麗莎白的原因吧?」
「我不知道,我想她肯定背負著沉重的心理負擔。這種情況出現在她這樣一個家庭也沒什麼奇怪的——一個有名氣的父親卻是個偽君子,母親又只一心護著他,一個偽善的姐姐也是每個人眼中的寶貝。」
我現在對你的境況一無所知,只知道你被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好家庭」收養了。這個地方我曾在圖畫書上看到過,也常常想起那猖獗的野蠻印第安人——至少我是這樣覺得的。這自然也讓我很關心你的安全,但我相信我的擔憂是錯的。現在,我對美洲各方面的信息都有一種無法滿足的需求願望,甚至還妄想有一天我會來這個地方參觀,那只是因為我被那種想念你的思緒所吞噬,想要到每一個地方去找尋你,即使知道它註定要失敗。
「還認識這兒嗎?」她問。
「未來的姐夫還要引誘她,使她陷入困境。」
唐豪斯
正說著,她又打開一個塑膠文件夾,取出幾件文具,它們都非常精緻,有如衣蛾的翅膀。「這是莉齊給她女兒的,現在坐好,靜靜地聽吧。」剛開始時,她還是用一種戲謔的語氣來唸,但很快她變得嚴肅了,休想,她好像已經想像著把莉齊的聲音融入自己的聲音了。
休的眼光落到了那個包裹上,他拿起來,看了看引文,是達爾文的筆跡,經過了這麼久了,以致黑色的墨水都褪色剝落了。上面寫著:
我不能肯定這封信是否會到達你手中,我是通過兒童援助協會辦公室寄出去的。它是一家專為你們辦事的機構。儘管我知道他們有政策規定,小孩與放棄撫養權的母親不能連繫——這是為了讓孩子從過去的枷鎖中解放出來,開始全新的生活,也是必要的。但我仍然充滿希望,因為查理.勞瑞.布萊斯先生是我父親的一個熟人,或許能出現例外,這封信也就能最終到達你手中。而協會如果決定不把它交給你,它也將會保存在他們的法律顧問那裡。他們告訴我,他們有權決定怎麼處置它。
八個月前,他深愛的哥哥伊拉茲馬斯去世了,他受到巨大的打擊,陷入了絕望的深淵。他認為自己也是心臟病晚期了。而上個月,具體地說是三月七號,當他一個人沿著郊外一條他喜歡的道路散步時,他又犯病了,勉強回到自己的住所,有好幾天都躺在沙發上。經過一個年輕醫生的好一番勸說,告訴他心臟還很好後,他才終於又精神煥發,甚至還去春意盎然的花園呼吸新鮮空氣。你姑媽,亨麗埃塔來待了幾個星期後又走了。各類的醫生,一共有四個,在不同的時段輪流來,每一個推薦的治療法都有所不同,甚至還有相互矛盾的說法。
「喂,」她揚起了眉毛,說道,「如果需要的話,這就是證據。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多麼殘酷啊!他們曾一直猛烈地揮舞著那古老神聖的清教徒之劍,不是嗎?」
「是啊,這就是那些從小將你養大的人。告訴我,這些年,這信一直都留在某個律師的文件夾中嗎?艾瑪從來都沒有得到過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