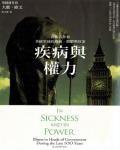第一章 一九〇一至一九五三年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溫斯頓.邱吉爾以六十五歲之年成為英國首相。希特勒終於遇到一位國家元首有決心來對抗他。在這個月的最後五天——同時間敦克爾克大撤退正在進行之中而且成功救援的勝算並不高——邱吉爾所做的正確判斷把全世界從希特勒的手中救了出來。在當時,只有少數幾個人了解那五天發生的事代表了什麼;約翰.魯卡斯(John Lukacs)的描述很出色地重溫了這段關鍵的時光。在五月二十五日這一天,邱吉爾用盡他腦袋裡所有的政治手腕,阻止了外交大臣哈理法克斯回應一份由義大利大使遞交給他的和談倡議。哈理法克斯當時已經確定地站到了綏靖主義的那一邊。支持哈理法克斯接受談判倡議的,還有法國總理保羅.雷諾(Paul Reynaud),當時人也在倫敦。這使得哈理法克斯在白廳裡有點不太誠實地把這份談判倡議稱為「雷諾先生的計畫」。他們兩人都沒能了解到,班尼多.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興戰的決心已經到了什麼程度。墨索里尼在五月十三日告訴他的外長齊亞諾:「在一個月之內我就會宣戰。我將攻擊法國跟英國,從空中以及海上。」二十九日他告知他的軍事將領,在六月五日之後,義大利隨時都可能加入戰爭。
羅斯福在一九四五年的雅爾達會議期間健康有嚴重問題,這一點無可懷疑。亞倫.撒勒里昂(Alen Salerian),美國FBI前任精神科首席顧問,也表示羅斯福在那時候已經罹患醫學意義上的憂鬱症;但是從醫療病歷裡做出這類診斷並不容易。一份於二〇〇五年發表的回溯性的神經心理學研究,透露了他惡化的速度有多快。這份報告主要是研究了羅斯福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在國會發表的最後一場演說。羅斯福坐著發表演講,這在他是很少見的。在許多地方上他失去注意力,跟隨準備好的講稿也有困難,他把雅爾達(Yalta)誤拼為「馬爾他」(Malta),言詞表達頗有瑕疵,而且當他脫稿說話時,所使用的辭彙很貧乏。
一隻明智又年老的貓頭鷹棲在一棵橡樹上。
牠見過的愈多,說的就愈少;
牠說的愈少,聽的就愈多;
為何我們不能學學那隻老貓頭鷹?
牠見過的愈多,說的就愈少;
牠說的愈少,聽的就愈多;
為何我們不能學學那隻老貓頭鷹?
對希特勒精神狀態的研究,只要人們仍然對歷史懷抱興趣,就毫無疑問地會有人繼續下去。但是這類研究如果要免除他邪惡罪行的可問責性,則機率並不大。希特勒傳記作者伊楊.克爾蕭的看法是,一九三六年萊茵河地區的重新佔領讓德國人高興的不能自已,也給希特勒帶來了重要的影響。接近他的人士所看到的改變是:「他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相信自己絕不可能犯錯。他的修辭裡染上了類宗教的象徵色彩……以彌賽亞的模式,他看到神祕的命運把他自己跟德國人民結合在一起。『你們在數以百萬計的人裡找到了我,這是我們時代的奇蹟!而我找到了你們,這是德意志的幸運!』」希特勒成為他自己領袖崇拜的頭號信徒。他的狂妄無法阻擋,而過度的傲慢會招來災難。天譴追上他的時間點,就在一九三六年。
令人驚訝的是,一個帶有憂鬱症焦慮性格、喜好沒有任何事件發生的日子的人,本來應該跟美國總統這個位置八竿子打不著關係才是。確實,某位報導美國總統的頂尖作家給了柯立芝一個標籤,稱他為一個「大謎團」。在他的家裡有一塊刺繡寫成的引言,展示在顯著的地方:
西奧多的弟弟艾略特是一個嚴重的酒精依賴患者,最終在一次癲癇發作中死去。一八九一年年末時,艾略特對一份宣稱他精神不正常的報紙提出法律訴訟,並且發表了一份聲明,否認有任何精神問題。那次事件後西奧多在床上躺了八天,也許是因為應付他弟弟的事情給他帶來壓力。一八九九年春天,還在紐約州州長任內,西奧多公開承認他「有一點點沮喪」;愛德蒙.摩利斯寫道:「這是一個羅斯福風格的委婉用詞,實際上他是掉進了絕望的深淵裡。」因此這裡顯示出了一個清楚的證據,他有臨床意義上的焦慮症以及憂鬱症,這些都影響著他的健康——這個人在四十二歲的時候當上了美國副總統一職,在其他方面被各方認為是精力充沛、健康強壯的。
大多數的政治人物都表現出某種型式的猜疑妄想,只是程度不同。跟醫學臨床上的妄想症不同,政治的猜疑妄想「開始時只是適當的政治反應,但經過變形扭曲,遠遠大過了原有的用意……這個人終會成為失利者,成為猜忌的受害者」。但是政治猜疑是只標籤,它不是一個臨床的診斷。有猜疑妄想的領導人,無論在專制國家還是民主體制,都把自己視為中心,把一切事物都關聯到自己身上。他會容易過度敏感,常常專注於自己而不管他人,還容易嫉妒。
馬克思.艾特肯(Max Akken,他後來成為報社老闆比佛布魯克勛爵〔Lord Beaverbrook〕時較為人知)從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六年是艾敘頓-昂德-萊恩鎮(Ashton-under-Lyne)政治聯合派(Unionist)的議員。他曾隨加拿大部隊在法國作戰,之後加入勞合.喬治的政府,於一九一八年擔任蘭徹斯特公爵領地大臣(Chancellor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 )。一九六三年他出書談勞合.喬治失敗與垮台的過程,但是書中寫到他在戰爭期間擔任首相的表現時不吝溢美之詞:
馬克思(艾特肯)昨天晚上告訴我,如果你回到下議院,無論它遇到任何困難,你打算有餘之年都支持當今政府。我回答他,這完全就是我對我自己的未來規畫,但是每次當我把這個想法透露給你,我這些愛國的表白總是遭到懷疑。你是對的。我覺得要寬容地評判我的繼任者是最困難的事情!公平而不偏頗,這種美德損耗的非常快,我的已經消耗殆盡了。我剛剛給一本書寫了序言,文章裡我對每一個人的批評都是完全公平的。我很高興再次見到你,也很高興見到你看起來狀況相當好,比我經歷類似經驗的時候要好上許多。
在日本攻擊珍珠港之後不久,邱吉爾動身從倫敦前往美國。他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首先搭乘夜班火車到蘇格蘭,次日早晨從古洛克(Gourock)搭乘「約克公爵號」戰艦,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抵達乞沙比克灣(Chesapeake Bay),再飛到華盛頓跟羅斯福總統共進晚餐;他抵達時一副精疲力竭的模樣可想而知。當晚午夜過後,他召來他的私人醫生查爾斯.威爾遜爵士(sir Charles Wilson,後來成為默蘭勛爵〔Lord Moran〕),看看是否可以服用助眠的藥物。邱吉爾太過興奮了,以致無法成眠。威爾遜給了他兩顆紅色的巴比妥酸鹽鎮定劑。
邱吉爾直覺地也很正確地了解到,在這個局面下的任何談判裡,墨索里尼只是一個門面,英國真正的對手是希特勒。在當前戰爭的階段裡,和談的協商一旦開始,第一個議題一定是立即停火,而且英國將無法拒絕。他擔心一旦英國同意停火之後,那麼當希特勒提出令英國曲辱的停戰條件時,他——邱吉爾——就再也沒辦法重起戰火。
溫斯頓.邱吉爾
在一九四四年春天將盡時,他表現出劇烈的情緒動盪,有時展現出爆衝的能量與光彩四射的演出,但全面來說他的情緒是倦怠與憂鬱的。這很大成分是因為他意識到他的對話者——史達林、羅斯福、戴高樂——當中沒有一人會真正去做他想做的事,他心中的無力感日漸擴大,感到無法貫徹他的意志。他走向戰爭勝利時情緒如此低落,遠遠比不上四年前他面對戰敗威脅時的樂觀。
到了上述保守黨總部會議時,這些因素都成為討論的素材,鮑德溫也警告,勞合.喬治「精力充沛的力量」已經分裂了自由黨,也很有可能會分裂保守黨。勞合.喬治具有魅力但又喜歡反對的人格特質,在一封一九二三年九月(已經辭去首相職務)他寫給波那爾.拉奧的信上鮮明地表露出來。他跟拉奧共事的五年合作無間。後來拉奧生了重病,並於一九二一年三月辭去內閣職務,勞合.喬治總統式的領導風格就此失去了最後一道阻礙。她們後來一直維持好朋友的關係,也許是因為當勞合.喬治深陷野心之中的時候,拉奧幾乎已經無法認知野心為何物。這封信如下:
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這一天,麥克當諾簽署的國防政策白皮書發表,其中主張英國的防衛能力有嚴重的缺失,必須增加額外的軍事預算才能夠補救起來。在多大程度上麥克當諾是否真的相信這本白皮書的說法,並不明朗。他從前反對過波爾戰爭與一次世界大戰,因為他覺得英國本身並未陷入危險。在那之後他盡一切努力擁護裁減軍備的政策,所以現在要他相信重新增加軍備的關鍵性與重要性,是很困難的事。如果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權的時候他還年輕、狀況也好的話,有可能他會做出重整軍備確有必要這樣的結論。但是麥克當諾在裁減軍備這個議題上一直是個理想主義者,只有在不得已的狀況下才會面對現實。
一九一九年九月最後一個星期裡,威爾遜右半腦的一條主要動脈上發生栓塞,換言之,他中風了。十月二日他的意識受到影響,這時候他的腦裡已經形成大面積的傷害,左半邊身體完全癱瘓,左半邊視覺也完全喪失。他說話變得虛弱而含糊。威爾遜的病情也發展出一種所謂的「忽略症候群」(Neglect syndrome),使他忽略整個半邊的身體。(在威爾遜的案例裡,他忽略了左半邊的身體,而且他自稱是個「瘸子」,用來辯解他左邊身體並未真正癱瘓。這種對於癱瘓事實的不注意與不在乎常常發生在右半腦重度中風的病人身上,他們甚至因此完全注意不到疾病,或說喪失病識感。結果病人可能用非常古怪的說法來否認疾病或者合理化自己的狀況。)總統否認自己的狀態是病理現象,他的妻子與私人醫生卡瑞.格雷松上校(Admiral Cary Grayson)也否認總統病情,卻沒有醫學上的理由可以解釋。他們對他身體的狀況完全就是在撒謊。格雷松在一九一三年時還只是一個下級軍官;當時他偶然地有機會替總統的姊姊縫合傷口,就因此被任命為威爾遜的醫生。他們自此成了朋友,格雷松在對病人的照料上失去了一切的客觀性。
無論如何,如詹金斯上面的敘述所點明,在戰爭最後的階段,邱吉爾所做的決定都已不再牽動大局。邱吉爾有時給人一種印象,好像他希望聯軍能夠早蘇聯部隊一步攻下柏林。但是這樣傷亡將會非常巨大,我相信他應該會明理地對這個展望感到猶豫。他也一定知道,首當其衝的美國並不覺得在戰略上有必要這麼做。
默:好吧,去年當你剛中風時,馬克思跟康羅斯到查特威爾(Chartwell)來,問我再來會怎麼樣。我告訴他們,這只能用猜的。
歷史家安德羅.羅伯茲(Andrew Roberts)於二〇〇八年出版的《大師與指揮官》(Masters and Commanders)是一本深具說服力的書,書中引用了將近七十位與邱吉爾同時代人物的私人文件,以及此前從未公開過的邱吉爾戰爭內閣會議的逐字紀錄。針對擘畫西方陣線主要戰略的四位關鍵人物,他在書中做出非常重要的結論,也陳述了他們如何在二次大戰期間與史達林過招。書名所指的政治大師是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軍事指揮官則是馬歇爾將軍與亞蘭.布魯克爵士。這四位當中,羅斯福自承對軍事戰略所知最少,然而他卻是「影響戰爭進展最大的人」。
邱:你沒回答我的問題。
當日本極力要求希特勒宣戰時,希特勒要跟日本訂定一個新的協議,而這件事本可以推遲到充分評估俄羅斯反攻的戰況之後。這個新的協定在十二月十一日簽署完成,協定中禁止日本與美國單獨進行和平協議。伊楊.克爾蕭思索著,這宣戰的決定,是否是「一個謎團」,一個誇大妄想瘋狂的「華麗瞬間」?他給自己的回答是:「並沒有什麼謎團。從希特勒的視角來看,這只不過是把反正避不掉的事情提前進行而已。這完全不是不可解釋或令人困惑……如果把他潛藏的價值觀考慮進來,他的決定是相當遵循理性的。」然而這「潛藏的價值觀」的黑暗面馬上就顯現出來了:宣戰後第二天,當希特勒在柏林的帝國總理廳裡對納粹黨首長們進行講話時,就指示他們開始著手將歐洲納粹佔領區內的猶太人予以毀滅。希特勒宣稱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在帝國議會上的演說裡就已經預先提示過可能會需要這麼做。
在高血壓的情形下,動脈裡的收縮壓很高,而舒張壓通常也會上升,反映出心臟的搏動以及被施加在動脈裡的力道。長期的高血壓會改變動脈血管的管壁,使其容易形成凝結或者血管栓塞。在威爾遜的案例裡,早在一九〇六年就有視網膜動脈病變的紀錄。一九一九年,當他參加巴黎和約的會議時,威爾遜不只判斷力已有損害,而且還很容易做出對他來說非常「不自然」的事情。其他人說他已經發展出一種只有單一軌道的心智。到了當年五月時,他無法通過思索來調整他的政治立場,於是變得充滿預設立場、無法達成協議。很顯然他的無法有效溝通是腦部病變,而且他表現出失智的徵兆,這是多次輕微中風的結果。(失智是指心智功能的惡化:六十五歲以上的人約有百分之十,七十五歲以上的人約有百分之二十會發生失智現象。失智是由進行性的腦部病變所造成,可能是血管問題、退化問題或者通常由惡性腫瘤引起。腦的額葉包含了運動皮層以及與行為、人格與學習相關的部分。)人們描述他「越來越自我中心、多疑以及喜歡保密,但是跟人相關的事情卻又比以前更不謹慎」。
羅斯福再次試著用冒險與鍛鍊身體來克服他的憂鬱症。他於一九一三年十月踏上探險之途,去巴西探勘杜伯河(The River of Doubt)。這條河(今天已經冠上他的名字叫作羅斯福河)是亞馬遜河的一條支流,蜿蜒地流過巴西的熱帶雨林,河道長達一千英哩。羅斯福在這裡重獲新生,再度恢復了活力,在探險中還差點喪失了性命。在性命危急之時,他叫他的兒子克爾米特領導探險隊繼續前進,留下他重病的父親跟一小瓶嗎啡;這嗎啡是羅斯福特別為了這樣的狀況而帶上旅程的。克爾米特拒絕了,大腿感染又發著高燒的羅斯福很幸運地存活了下來。一九一四年五月回到紐約港時,他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幾年以後,羅斯福又有點像從前的自己,決定去法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是被威爾遜總統否決。羅斯福的兒子昆丁去了,並戰死在那兒。
儘管如此,有些在他身邊工作的人留下的證言,確實略微透露了他不只有憂鬱面,而且還有躁狂的一面。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的私人祕書奧利維.哈維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的日記中有這樣的紀錄:「首相(即邱吉爾)處在瘋狂的雀躍狀態裡。這戰爭已經鑽進了老先生的腦袋裡。他喝酒的數量之大——香檳、白蘭地、威士忌——真叫人難以置信。」有意思的是,哈維說那鑽進邱吉爾腦袋的,不是酒精,而是戰爭。同樣有意思的是他使用「瘋狂的雀躍狀態」這樣的形容。精神科醫師在診斷躁鬱症時,一定會把這個症狀考慮在內。
他性格的複雜面貌在一本十分出色的書裡有鮮活的描述:《史達林:紅色沙皇的法庭》(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透過信件與回憶錄,這本書對史達林的性格有深刻的洞察,也向讀者展示了何以他既受到崇拜也使人恐懼。到今天許多俄國人仍認為他是他們最偉大的領袖之一。
邱吉爾:身為我的醫生,你會不會覺得我之前就應該辭掉首相?
當亨利.甘貝爾-班納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於一九〇五年於英國就職時(他的前任貝爾福〔A. J. Balfour〕辭職下台),他是史上第一位被官方授予首相頭銜的人,他的前任其頭銜是第一大臣或者財政部第一大臣。他的政府包括了三位未來的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以及溫斯頓.邱吉爾。當甘貝爾-班納曼一九〇六年宣布進行大選時,自由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他自己從一八九八年起就是自由黨黨魁,在波爾戰爭期間在國會中領導自由黨反對此一戰爭;這個立場引發爭議,招致了言詞辱罵的書信,例如其某位教士寫道:「您是一個無賴、懦夫跟殺人兇手,我希望您遭到背叛者跟殺人兇手應有的報應。」他並沒有遭到那麼大的報應,但是隨著他在唐寧街時期的進展,甘貝爾-班納曼生病越來越嚴重。一九〇七年六月,他第二次心肌梗塞,只好讓財政大臣阿斯奎斯漸漸接手他各項職務、最後成為他的幕僚長,才使得政府的運作不至崩解。一年以前他摯愛的妻子逝世,他已經深受打擊。他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心肌梗塞反覆發作了幾次。「他從來不肯自願辭職,臨死前在床上也還堅持自己首相的身分。」直到他的醫生團隊幫他料理一切事情時,他才終於被迫辭去職務。之後他也還是留在首相官邸,三星期後,於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二日過世。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六日,威爾斯人大衛.勞合.喬治成為英國首相。透過複雜的運作,他跟戰時聯合執政內閣裡的保守黨多數成員給阿斯奎斯施加壓力,讓他接受討論過的戰時內閣組織;阿斯奎斯於十二月三日接受了,但是四日就又予以否決,這給自由黨內部造成裂痕,其餘緒到今天也仍然存在。
歐洲方面對威爾遜表現的回應,是後來小布希所引發的文化衝突的一個早期徵兆。(這種衝突給歐洲人帶來了美國恐懼症〔Americophobia〕,小布希所引起的,比威爾遜的規模要大的多)。人們耳語傳著,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說起話來像是耶穌基督,而法國總理喬治.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稱他心智受損,患了「宗教精神官能症」。
透過通信,羅斯福跟史達林建立了一個很有意思的關係;這些信件現在收錄在《我親愛的史達林》(My Dear Mr. Stalin)一書裡。美國大使阿維瑞爾.哈利曼(Averell Harriman)在戰爭最後數年出使蘇聯,他覺得羅斯福故意培養一種能夠影響史達林的能力。波蘭問題的決議被留到雅爾達會議,因為邱吉爾與羅斯福都知道在德黑蘭會議上——當波蘭邊界被用火柴棒劃定的時候——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對波蘭未來的意見衝突,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當安東尼.艾登到莫斯科見史達林時就浮上檯面。更甚者,羅斯福與邱吉爾兩人在內心深處一定很清楚,在邊界變更之後,波蘭是否能有自由與公平的選舉還是個問題。無論史達林在雅爾達簽署了任何協議,事後都很難或根本不可能強制他實現。羅斯福也知道,邱吉爾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在莫斯科跟史達林進行的雙邊會談上,首次做出了戰後歐洲的「強權政治」勢力範圍瓜分圖,目的在於把蘇聯排除在地中海周邊之外。今天再看當年邱吉爾在克里姆林宮裡潦草畫下的那半張紙,當中羅馬尼亞上方壟罩著史達林表示同意所打的巨大的勾——在圖上這個國家百分之九十被劃分給俄國,百分之十留給其他國家——就可以了解領導人的個人權力能決定什麼。難怪邱吉爾會表示他當時對史達林說:「我們看起來像是用漫不經心的方式,來處置這些重大的議題,這可關係到數百萬人的身家性命,難道不會有人認為這樣太背德又不管他人死活嗎?讓我們燒掉這張紙吧!」史達林回答他:「不,你留著吧。」
如果要找出一個關鍵時刻,希特勒的狂妄終於使他遭受天罰,我認為這個轉捩點應該是俄羅斯軍隊在莫斯科周遭對德軍展開反擊,也就是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五日星期五的清晨開始,一直到十二月十一日的下午,當希特勒宣布,根據三國同盟條約(德義日三國於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簽訂),德國與義大利不得不聯合日本「一齊為防衛進行奮鬥,從而維護自身民族與國家的自由與獨立,以免於受到美利堅合眾國與英國的侵害」。
我們一定要在馬克思家裡再來一次聚餐。他昨天晚上興致高昂,講了不少有色笑話。
直到一九一七年真相才公諸於世。一九二八年,治療團隊裡的一位醫生披露了那場手術的細節,而他的腫瘤的性質,在一九八〇年三月才揭曉。克里夫蘭的故事,特別是嚴格保密這個環節,本來是可以跟本書的幾個例子互相呼應。但是十九世紀跟二十世紀的醫學是很不一樣的兩回事,因此從這段歷史所得到的教益並不大,所以本書才把焦點聚集在最近的一百年左右裡。
一九二一年開始時,很少人會反對拉奧的看法:「勞合.喬治如果願意,可以一輩子都當首相。」但是根據比佛布魯克的說法:「一九二一這一年開啟了一段為期兩年的殘酷時光,把所有金色的錦緞與亮片通通撕碎。」儘管比佛布魯克不是最冷靜客觀的,但是當他下筆分析勞合.喬治的時候,他十分了解擁有權力是怎麼回事,他在邱吉爾座下擔任過空軍生產部長(Minister for Air production)、後勤部長(Minister of supply)以及掌璽大臣(Lord Privy seal)。他十分稱讚勞合.喬治戰爭期間的表現,相對於此,他對他戰後首相任期的表現做了沉痛的批判,他意識到勞合.喬治的問題的根源就在於傲慢自大:
並沒有可信的證據足以讓我們認為希特勒心智失常。相反地,我們應該描述他為「政治的惡」的化身;確實這也是最大多數人的看法。關於他的健康的所有文獻探討,你很難找到真正跟他的決策相關之處,也跟他的仇猶心態沒有關係。他之所以仇猶,跟他在維也納度過貧困的少年時期似乎更有關係,那時候的維也納仇猶情緒相當盛行。後來他在第一次大戰打過仗後,住在慕尼黑,這時他才發展出對蘇維埃共產主義的仇恨,以及把德國視為世界強權的憧憬。不管怎麼樣,想把納粹統治所釀的罪惡完全地歸諸於一個領導者的人格之上,這種作法本身是極度錯誤的。在十二年的暴君統治期間裡,希特勒的吸引力並不是僅僅在納粹支持者圈內才存在,而是廣布於一般大眾之間。希特勒的個人魅力與高超的政治宣傳技巧帶給他的權力,不足以讓他把自己的意志凌駕於敵對的、抗拒的人民大眾之上;他所做的是去培養他們的熱情,操作他們的支持,以達成他自己所想要的目的。希特勒從全體德國人民——數以百萬計個別的人——獲得可觀的效力與鼓舞。有些分析因為把焦點完全放在他的人格特質上,常常忽略了這一切。希特勒跟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如何創造出猶太人的「終極解決」?探討這個問題可以讓我們得知許多事。「並沒有一個由上級頒布的犯罪藍圖,也沒有由基層設計出來、層峰只需點頭認可的計畫。一個個的納粹黨人執行著謀殺,並非因為受到粗暴的威脅所強迫。」這是一個集體的事業,業主是成千上萬的德國人;希特勒在開啟俄羅斯戰線的時候,給了這事業一個推動的力量。幸運地,德國也有許多勇敢的男性與女性從第三帝國的內部抵抗納粹主義;他們當中許多人的名字與事蹟,可能永遠也無法完全為世人所知。
儘管書中也對邱吉爾有許多批評,羅伯茲還是持平地寫道(對照現今內閣政府的名存實亡,這些話頗具現代意義):
班尼多.墨索里尼
甘貝爾-班納曼獨特之處,在於他是史上唯一一位在唐寧街十號官邸裡過世的首相;他曾經形容這座官邸為「一間腐爛又老舊的兵營房舍」。然而他不是這一百零六年期間最糟糕的失能者案例。這項殊榮屬於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他雖然沒有死在白宮裡,但是所患的疾病使他失能的程度,是所有就任過的總統中最嚴重的。
溫斯頓的問題是他老是在採取行動。他會堅持掏出他的地圖來。一九一四年時他掏出達達尼爾海峽的地圖來,思考那會把我們帶到哪裡去。在戰後,我還得考慮該怎麼處理他。我要他留在我的內閣,這是一定的,但是在戰爭結束以後,對一個會掏出一堆地圖來的人而言,什麼位子才是最安全的?戰爭部,理所當然。我想,在那邊他會是安全的。但是他以前當戰爭部長安全嗎?我頭還沒回過來,他已經掏出一堆俄羅斯的地圖,然後我們就在內戰裡面扮演一堆傻瓜。
到了一九四一年年底,希特勒滿足了狂妄症候群的所有重要特徵。但是在生命的這個時期裡他並未患有任何醫學上認可的疾病。特別是多到數不清的人試著證明他已有精神疾病,但沒有人找到任何可信的根據。他沒有躁鬱症引起的躁狂現象,也從來沒有十分明顯的憂蠻症或者躁症的發作。
西奧多.羅斯福
阿斯奎斯在首相任內的健康狀況相當不錯,但是他曾於一九一一年四月二日瀕臨暈倒。當時他抱怨三個星期以來都感到暈眩,整個人看上去精疲力竭,因為他當時花了許多冗長的辦公時間處理第一次全國煤礦罷工。他的醫生診斷出他有高血壓,警告他必須大幅降低他的飲酒量(阿斯奎斯主要是在晚餐時間喝葡萄酒與白蘭https://www•hetubook.com•com地)。據稱從那時開始「他似乎牢牢控制住他的喝酒習慣」。但是在為二〇〇九年《腦》期刊的論文|做研究時,我們發現了更多的資訊,足以指出阿斯奎斯在擔任首相期間,從現代的診斷標準看來,已是一個酗酒者。一九一一年十月,在與阿斯奎斯共進午餐之後,他的一位老友康斯坦絲.巴特希(Constance Battersea)在給她的姊妹的信上說:「首相很親切,極其地熱情,但是他的改變真是大呀!滿臉通紅,身材臃腫,跟他過去的樣子非常不同了。他讓我感到震驚。他們全都提到他吃得太多,又飲酒過量。我怕這些說法無疑都是真的。」一九一六年九月,在阿斯奎斯訪問過英軍在法國的指揮總部之後,陸軍元帥道格拉斯.海格(Douglas Haig)寫信給他的妻子說:
這一章將檢視的,是從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五三年之間握有真實權力或影響力的政治領導人物所患的疾病,而下一章則涵蓋一九五三年到二〇〇七年這段期間。在這個略長於一百年的時期裡,國際政治與醫藥科學經歷了巨大的改變。一九一八年美利堅合眾國以世界強權的姿態興起;一九四五年它成為世界實力最強的國家。在第二章裡我們將看到,在一九八九年時,儘管在越南吃過敗仗,美國還是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強權,因為蘇維埃帝國崩解了。儘管如此,在二〇〇六年時美國的力量在伊拉克與阿富汗受到了挑戰,而且中國正在轉變為一個新的世界強權。
在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與二十八日三天裡開了九次困難的會議之後,戰爭內閣終於接受了邱吉爾的看法。(戰爭內閣原本只由五名成員組成,當中三位是保守黨人:首相與他的副手、工黨領袖克理門特.阿特烈〔Clement Attlee〕、前首相張伯倫、外交大臣哈理法克斯勛爵以及工黨副主席亞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在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天的內閣會議後,邱吉爾又讓自由黨議員亞齊鮑德.辛克萊〔Archibald Sinclair〕加入接下來的戰爭內閣會議。辛克萊是邱吉爾可靠的盟友,因為他從來就反對綏靖主義。敦克爾克大撤退是從五月二十七日開始,而一直要到戰爭內閣完成了反對和談的方針之後,這場撤退的奇蹟之處才顯現出來:五月二十七日當天七千人離岸,二十八日一萬七千人,從二十九日到六月一日每天五萬人。敦克爾克撤退跟戰爭內閣會議同時進行的過程,瑟巴-蒙特費悠〔Hugh Sebag-Montefiore〕的《敦克爾克:戰至最後一人》書裡有很好的敘述,書中大量引用了戰爭內閣會議裡的發言。對邱吉爾來說,戰後如果他揭露哈理法克斯願意和談的立場,會給自己造成政治問題,因為哈理法克斯是上議院裡保守黨的領袖。而邱吉爾也寧願保持一種從未考慮過任何和談〔雖然這並不正確〕的厲害形象。)值得大加讚賞地,張伯倫在一開始的兩面觀望之後,支持了邱吉爾而反對哈理法克斯。在此一關鍵的行動上,張伯倫挺身反對自己的老友,因而完全證明了邱吉爾決定,把他留在戰爭內閣裡面是正確的。這也是張伯倫向邱吉爾表達感謝的一種方式,因為先前張伯倫擔任首相時,邱吉爾懂得兩面做人,很少直接而不掩飾地反對他。哈理法克斯與邱吉爾在首相官邸的花園裡一起散步之後——邱吉爾盡力修好與他的關係——也轉而接受了戰爭內閣的多數意見。在戰爭內閣之外,邱吉爾以一場令人振奮的演說,贏得了二十五位有部長大臣職務的同事的支持。戰爭內閣的決議是,在英國贏得戰爭之前,都不可以再提起任何和談的問題。但是對邱吉爾來說,所謂贏得戰爭,指的不只是空戰,最起碼也要包括大西洋的海戰。
到了一九四二年後期時,墨索里尼的精神問題把他困住了。他的體重在數月內減輕了四分之一;這並非全由於他長年的胃潰瘍毛病所致,也因為他憂鬱的症狀已經根深蒂固。所有豪氣干雲的修辭都消失了,他的勇氣或力量已經用盡。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的沮喪非常嚴重,原本與希特勒約定的會面,只好請女婿齊亞諾代替他出席;在聖誕與新年期間他大都躺在床上。一九四三年四月,在前往德國的旅程中,他又遭遇一次緊急狀況——胃痛不止,也無法成眠;這些問題無疑都因為義大利此時明顯將要輸掉戰爭而更加惡化。他開始顯得精神緊張,說話急促,也漸漸失去號令的權威。到了一九四三年七月,他實質上已經被身邊的人囚禁在龐查島(Ponza),之後被轉往薩丁尼亞島(Sardinia)的海軍基地,八月時再送到一個滑雪休憩地。九月義大利投降以後,墨索里尼被一個德國的黨衛隊小組救出,並且用飛機送到慕尼黑。然後德國人把他送回義大利,讓他擔任殘餘的義大利社會共和國(Italian Social Republic)的傀儡獨裁者。義大利共產黨的游擊隊在柯莫(Como)附近逮到了他,並將他射殺。他的屍體在被扔進一輛卡車的車斗後被運回米蘭;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他與情婦兩人的屍體被並排倒吊在米蘭的羅雷托廣場(Piszale Loreto)上;一九四四年八月時十五名共產黨游擊隊員曾在同一地點被槍決。墨索里尼此前已深受死亡恐懼的困擾,然而他害怕的死法與此相去甚遠,而是一種夢幻華麗的死法。他擔心如果被美軍:活逮,他應該會被送到美國,在紐約的麥迪遜廣場受審,「彷彿我是一頭被囚禁在籠子的野獸」。他對現實的逃避在當時已經完全成功了。
在聯合內閣裡,勞合.喬治不只跟自由黨的同事如邱吉爾意見相左,他跟保守黨的下院議員與上院議員也不一致,這使得狀況相當複雜。外交部長庫爾叢勛爵在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一封寫給妻子的信上說:「他要他的外長當個隨侍的男僕,甚至是個奴工,日常的禮貌禮儀他棄之不顧。」一九二二年三月勞合.喬治開除了他的印度事務大臣愛爾文.蒙特古(Erwin Montagu);在劍橋自由黨黨部發言時,蒙特古說:「我們的政府首腦是一位偉大、但也古怪的首相。他要求我們付出的代價——這是每個傑出人物在他權力範圍內會做的要求——是內閣共同責任的政治倫理完全消失。他是一位偉大的天才,但也是一個獨裁者。」勞合.喬治現在是個獨裁領導人,而不是民主政治人物了。
大多數人都認為阿特烈是英國承平時期最優秀的首相之一。他的健康狀況一向良好。只有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因為十二指腸潰瘍而不得不進聖瑪莉醫院(位於倫敦西區)住了一點時間。這使得阿特烈錯過了健康大臣阿紐林.貝凡(Aneurin Bevan)與財政大臣修斯.蓋茲克爾(Hugh Gaitskell)發生衝突的那次關鍵內閣會議。貝凡與其他揚言辭職的閣員到醫院探訪阿特烈,他們帶來的壓力自然無助於他的潰瘍。四月二十三日貝凡辭去了職務,因而導致了工黨在該年十月敗選,邱吉爾於是重返首相的位置。
二〇〇六年相關專家確診柯立芝在白宮任內曾經患有憂鬱症。雖然許多人認為憂鬱症的表現型式是絕望,但是焦慮同樣也是憂鬱症的重要表現特徵,柯立芝的例子就是這樣。在孩童時期他很害羞而敏感,有導致氣喘的過敏症狀;鼻通道的阻塞讓他的聲音有一種獨特的「像鴨子叫的音質」。他使用某種喉嚨噴劑,但是對外從不明說。他終其一生對於鼻子與喉嚨給他帶來的困擾,以及對他的慢性消化不良,都非常敏感。很多人形容他是一位枯燥的律師,「城裡一位古怪的無聊傢伙」,所以每個人都感到不可置信,他娶的新娘是一位活潑、幽默、外向又充滿吸引力的小學老師,這位女孩喜歡他枯燥的機智,忍受他脾氣的發作,能接受他事事不愛明說的保密性格以及他在孤立中的自得其樂。他一天最多可以睡上十一個小時。一位記者曾經寫道:「他所謂的理想的一天,就是在那天裡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墨索里尼決定入侵希臘之後遭到天罰。一九四〇年他在佛羅倫斯與希特勒會面時告訴他,義大利的部隊已經在十月二十八日越過了阿爾巴尼亞的邊境。納粹頭子在先前的入侵行動沒有先知會他,現在這位法西斯頭子也回敬一招。然而這行動看起來貌似獨裁者絕決的壯舉,實際上只是虛有其表的花拳繡腿而已,背後都是一些不成熟的假想、膚淺的觀察、外行的判斷與全無批判能力的評估。這場希臘戰爭成為義大利無以復加的災難,只有靠德軍的救援才得到解脫。
羅斯福在世的時候,關於他的健康狀況一直就有很多的傳言。甚至他的逝世也成為爭議。有些人宣稱他是死於胃癌,另外有些人說他是死於惡性的黑色素瘤。(關於羅斯福所謂的胃病,黛西.薩克菜〔Daisy Suckley〕提出了解釋。她在一九四四年裡與總統見面頻繁在五月二十六日這天在貝特斯達醫院,她記得總統做了一次X光照相,顯示出膽囊中有結石。這些膽結石很可能是羅斯福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德黑蘭會議當天晚上不適的真正原因,當時以為是急性的消化不良;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以及五月一日的兩次急症也很可能是膽結石的問題,當時布魯恩醫師在場,他給的治療是注射可待因。黑色素癌說法的由來,似乎是總統曾開刀移除背上一處尺寸如小難蛋大的皮脂囊腫〔sebaceous cyst〕,當時的稱呼是「疣」。這個皮脂囊腫在他背上已經二十年了,手術是在局部麻醉下進行的。這次手術同時也移除了他眉毛上一處有色素沉澱的傷疤,有些人相信這是一個黑色素瘤。)然而自從一九九五年,羅斯福未婚的表妹黛西.薩克萊的日記公諸於世之後,關於他的死因(由心臟衰竭引起的腦溢血或者腦血管病變)就應該沒有多少懷疑的空間了;日記釐清了他所有戰爭期間的疾病狀況。總統信任黛西的謹慎與保密,並且請她負責整理他私人文件,以便交由他自己的紀念圖書館收藏。羅斯福原有一位暱稱「小姑娘」的超級祕書瑪格麗特.勒罕(Marguerite Le Hand),但是在她的健康崩潰之後,黛西以及羅斯福長年的貼身顧問哈利.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試著填補她留下的無底空缺。「小姑娘」給羅斯福的生活帶來色彩與歡樂,那是他備受尊敬的妻子艾倫娜永遠無法給他的。
於是在這本編年史的開頭處,本書的許多主題已經都呈現了:一個政府首腦——英國首相,因心臟的問題在任內生病,接著需要其他人替他執行任務,以使得政府施政的崩解程度降到最低,但是同時不讓外界得知問題真正的嚴重程度;另一位政府首腦——美國總統,雖然有精神疾病的病史,卻仍然績極地也成功地統治國家。甘貝爾-班納曼的個案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醫生團隊很不尋常地,展現了力量並要求首相辭去職務,相對於此,本書所敘述的幾乎所有其他個案裡,為政府首腦提供意見的醫療諮詢者從沒有發揮過任何類似此案的權威力量。
圍繞在邱吉爾身上的醫學議題是,他是單純只有憂鬱的困擾,還是他的情況其實是帶躁症的憂鬱症,也就是今天所說的躁鬱症?反對者認為,他畢生都沒有無可爭辯的躁症發作病史。他無疑有許多非常古怪的行為,但他們懷疑這是否能夠被歸因於躁症。例如,邱吉爾喜歡在泡在澡缸裡口述指示給祕書,而且他沒意識到自己是裸體的,有人將此事診斷為躁症的表現。但是這種作法在他的社會階層頗為常見,並不能證明什麼。
當羅斯福從一位騎警處獲知前總統麥金萊被射殺的消息時,他正在攀登紐約州境內阿第倫達克山脈(Adirondacks)的最高峰。此時他已經擔任美國總統七年之久,他的焦慮症與氣喘病在這段期間似乎消失了,似乎不影響他作為總統進行決策。「少年時期裡他的攻擊衝動是佔主導地位的,但是成年後,他使自己更為堅強,足以克制這些衝動,像是硬化了的岩漿把火山包夾起來,」在他就任總統一職之前:「三年之久,這道防護都沒有出現過嚴重的裂縫。」在白宮裡,也許是為了擺脫他的攻擊性,他規律地練習拳擊。在一次練習賽裡他的左眼被打瞎了,也無法醫治,但是大眾從來沒有被告知這件事。
浮現出來的明顯事實是,邱吉爾是戰略天才。雖然他偶爾也會端出魯莽的策略,但那不過是他偉大的揮灑當中,無可避免會夾帶的一小部分閃失。如果英國是獨裁體制,那些魯莽策略一定會被付諸實行(希特勒政府就是這個情況),但是因為英國是民主體制,所以這些都被擋了下來、最終歸檔了事,出手把關的通常都是亞蘭.布魯克爵士。
羅依.詹金斯如此描述邱吉爾:
哈定總統死亡的次日,副總統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在家族位於佛蒙特州普利茅斯諾奇村(Plymouth Notch)的農場裡,在深夜一盞煤油燈的燈光下,由他擔任州公證人的父親見證,宣誓就職美國總統。他於一九二四年連任成功,擊潰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約翰.達維斯(John Davis),在總統選舉團選舉中以三百八十二票對一百三十六票贏得壓倒性勝利,代表進步黨的羅伯特.拉.佛葉特(Robert La Follette)只有十三票。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柯立芝宣布他選擇一九二八年不競選連任,所有人都無法置信。有可能他是受到妻子格蕾斯(Grace Coolidge)健康狀況的影響。她「缺少活力,體重在下降當中」;跟柯立芝一樣,她也為了小兒子死於腳趾的敗血症而悲傷,同時還為她母親的病情操心。一九二八年夏天格蕾斯被診斷出有腎臟腫瘤。不過實際上她比先生還活的久。柯立芝是因為自己在兒子死去後開始有的喪親憂鬱症而自願離開白宮。一九二五年他在白宮裡有可能發生過一次心臟麻痺,如果為真,那這更增強了他做出如此決定的理由。
中午時羅斯福與他的副總統亨利.華萊仕(Henry Wallace)會餐,確定他們昨天討論過的聲明,內容主要是讓羅斯福推薦華萊仕。這時總統有點閃躲,並且向華萊仕提到,許多人認為他是共產黨人,甚至比此更差勁。也許羅斯福了解到,由於他的健康狀況,副總統的人選比以前更為重要。當天晚上羅斯福與幾位反對華萊仕再度被提名為副總統的民主黨領袖會餐。他們討論了兩個人選:一個是羅斯福評價很高的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一個是杭涅剛提議的參議員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羅斯福於是在信封上寫著,他很樂意跟這兩人的任何一位一起競選。但是他沒辦法下定決心正式拋棄華萊仕。到了七月二十一日在芝加哥的民主黨代表大會發言台上,杭涅剛與其他民主黨大老才把選票推向杜魯門;前一天晚上大會還因為受到支持華萊仕的基層車隊威脅而暫時休會。幸運地,杜魯門作為總統,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普通人。華萊仕是個夢想家,而美國需要的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也在杜魯門身上找到了。
希臘人描述過一種人:他位高權重,充滿自信,他如此成功,以至於太過強勢讓所有人難以忍受。然後他的德性開始轉變,轉向了衰敗。他犯了傲慢的罪惡。他的自信與成功所建立起來的一切開始傾倒與挫敗。他對抗命運奮力掙扎,但是他的劫數已經注定。這就是勞合.喬治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年裡的情況。之後,一切都結朿了。他所有的計劃,不管好壞,都成落空。他倒下了,之後也沒再站起來。
親近羅斯福總統的圈子很清楚,總統已經無法再應付公務的重擔多久時光。二月八日,會議將要結束時,羅斯福開始有交替脈,也就是一強一弱的脈搏交替出現。這代表心臟有十分危急的狀況——左心室衰竭。幸運地,幾天之後,他的脈搏恢復正常了。就在這個突發事件之前,總統的女兒(當時也在雅爾達)首度被告知關於她父親心臟的狀況。消息來源不是海軍上將麥金泰爾,而是布魯恩大夫,那位年輕的海軍心臟醫師。她於二月五日寫信給丈夫:
對於勞合.喬治在戰後的任期表現,歷史家肯尼特.摩爾根(Kenneth O. Morgan)有個比較平衡的看法,把他無疑應該被視為成就的部分也紀錄了下來:「儘管有很多失敗之處,勞合.喬治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二年間的聯合內閣試著建立政治共識以達到最好的結果,這在和平期間的所有英國政府當中是僅見的。」跟比佛布魯克相反,摩爾根肯定勞合.喬治的社會改革,認為遠遠勝過了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的那些措施;他設置了全面性的國家失業保險,籌畫新預算給退休基金與社會安全機制,設立了衛生部,並且給農業勞動者以及教育改革應有的支持。由於財政部要求節約開支,這些措施因此停滯不前。不過在勞合.喬治的領導風格裡,已經可以察覺出有毀滅的因子:有傾向專制統治的危險……全憑直覺又反覆無常的外交手腕,會面前欠缺事前準備。摩爾根接著描述一九二一年六月勞合.喬治似乎已經放棄希望,這構成了他身體健康的暫時危機。「由於內閣政府所有計畫都強調他個人權威的印記,媒體也就自然地把首相當成他們最重要的靶心。」對此,一個象徵性的事件是:他把內閣召喚到印佛內斯(Inverness,他在離此不遠處療養身體),這突顯了「單人樂團」的形象,「樂團的指揮瘋狂又不依常軌,演奏出違反自然的合音。」
邱吉爾當上首相之後,他少年時期情緒起伏帶來的猛烈衝擊已經得到平息,跟老羅斯福很像。他的女兒描寫邱吉爾抑鬱與深陷挫折感的狀況時,認為:「這抑鬱之感早年太過頻繁地造訪他,以至於他現在不可能不知道這種感覺具有何等力量。但是現在對他來說,穩固的地位與婚姻帶來的幸福已經把那隻『黑狗』關進狗籠裡。」她還說,寫作與繪畫是「對抗他性情中抑鬱成分的絕佳抗體」。但是不管那隻「黑狗」能不能說是被關進了狗籠,邱吉爾還是會陷入憂鬱。他的私人祕書約翰.柯爾維爾(John Colville)一九四四年二月如此描述邱吉爾:「首相看起來衰老、疲倦,而且非常抑鬱。」
到了他第三次總統選舉,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五日時,歐洲正在戰爭中。亟需援助的邱吉爾希望羅斯福能讓美國投入戰爭,以對抗德國。人們很容易認為美國跟德國的戰爭終不可免,但是在美國民意的深處總是不願意在歐洲打一場戰爭。在選戰過程中,羅斯福感到有必要對選民做承諾,他在十月三十日說:「不會把你們的兒子們送去打任何外國戰爭。」羅斯福沒有提供邱吉爾兵力,而是透過租借計畫(Lend-lease scheme)提供資金。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七日的記者會上,他用一個簡單但是多少有點誤導的類比來描述這個租借計畫:就好像把你的花園工作褲借給鄰居,讓他去撲滅他家的失火。同年早些時候,在六月二十二日,德國進攻俄羅斯。在八月的九到十二日之間,羅斯福與邱吉爾在紐芬蘭島的普拉根提亞灣(Placentia Bay, Newfoundland),分別在英國皇家海軍的威爾斯王子號與美國現役軍艦奧古斯塔號上,共同簽署了大西洋憲章。就算在那個時候,邱吉爾還是得等待羅斯福是否表現任何意願來加入戰爭。羅斯福事後給美國媒體做簡報時表示,他們彼此交換了意見,就只是這樣。他還讓媒體間接引述一句話:「沒有更接近戰爭。」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因為共和黨分裂,威爾遜贏得了大選。泰爾寫到這場注定不幸的選舉挑戰:「如果他不能執政,就會崩潰。從前指稱他已經瘋掉的傳言,現在當然又流行起來了。」羅斯福打完選戰敗選之後,儘管他的票數還高過現任總統塔虎脫,他陷入一種「被碰撞過的心情」——他的家人很小心地如此形容。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祕密地問他的醫生亞歷山大.藍博特(Alexander Lambert)能不能過來看看他。羅斯福此時已成為政治上的賤民階級,他向藍博特坦白地說:「我的寂寞簡直無法形容。一個被同類排斥的人會寂寞到什麼地步,你根本不知道。」
然而若比較犯行的性質而非數量,那麼希特勒是兩人中更邪惡的,因為,如同有人說過的,希特勒的敗壞是「在於目的」,而史達林是「在於手段」。希特勒與史達林都使用大量屠殺、流放、勞動改造營以及可怕的剝奪與匱乏,來當作鎮壓的武器。為了在蘇維埃境內維持他的權威,史達林會釋放上述所有力量來對付大批的民族團體,比如一九四四年在格洛茲尼(Grozny)。不過史達林並不是個種族主義者,像下決心根除猶太人的希特勒那樣。蘇維埃的古拉格(Gulag)無疑也是對人權極惡窮兇的攻擊,但是這跟納粹的集中營並無法等同,因為後者的目標是要致人於死。
他主要的煩惱來源都跟鮑德溫首相的健康與精神狀況有關。首相情緒低落,明顯地越來越聾,無法入睡,「神經過於緊繃」。夏天裡他發生了一次徹底崩潰,情況如此嚴重,以至於他的醫生宣布,首相要恢復體力,最少需要三個月的完全休息才有可能。
一九四四年七月的炸彈事件發生之後,希特勒開始習慣性地使用古柯鹼。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時常用棉花棒將百分之十濃度的古柯鹼塗到鼻孔裡,另一種是每日兩次的吸入食用。再加上莫瑞爾醫生開立的藥方,他原先的行為模式更為劇烈了:他比原先更容易暴怒,做決定也更為突然與衝動。一九四五年時,他所做的決定無論在哪裡效力都大不如前,但是這並不等於喪失心智能力。他晚期所做的這些決定,模式跟早在他健康惡化以前是一樣的。這些晚期的決定仍然都是他的責任。
在慕尼黑巨頭會議後,由於逐漸迫近的癌症以及陳年的痛風,張伯倫的表現遠遠及不上應有的水平。(痛風的發生,是血漿裡與身體一些部分中尿酸濃度過高而引起的。尿酸以尿酸結晶體的型式貯存在組織裡,濃度過高會導致關節的腫脹與疼痛。病因仍然未知,但是遺傳扮演了一個角色。四十歲之前很少發病,可能的伴隨症狀是尿結石,尿結石是由尿酸鹽所組成。如果有腎臟疾病的話,長期的預防性治療可以投以安樂普利諾,這會降低血液裡尿酸鹽的濃度。非類固醇的抗發炎藥對疼痛有療效。使痛風惡化的因素是喝酒跟富含動物性成分的食物。)外交部裡傳著的一首五行打油詩,總結了一九三九年時白廳(Whitehall)裡人們對他懷抱的觀感:
阿道夫.希特勒
邱吉爾的病情鮮明地點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在位或即將上任的國家領導人其健康對於大眾的透明度應該怎麼拿捏,特別是必須考慮到維持民眾的信心士氣。如果英國內閣得知邱吉爾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末有心臟病的話,他們可能會十分擔心萬一民眾廣泛知道的話,對大家的士氣會有負面的影響,也可能會造成一些政治揣測,認為邱吉爾可能會因此不得不下台。內閣可能會希望外界知道此事的人愈少愈好,也會籲請邱吉爾悄悄地去休個長假,讓克理門特.阿特烈代為操刀。事實上,後來事態的進展也是如此:當邱吉爾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迦太基(Carthage)生了肺炎與肋膜炎時,內閣請他在馬拉克須(Marrakesh)休養身體,不要急著回來。美國當時已經加入戰爭,而且對戰況有巨大的貢獻,這緩解了任何政治危機或民眾信心危機的發生。如果邱吉爾在一九四三年死去,會是一個打擊;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死去,會有相當損害;但如果在更早死去,就會是個大災難。
史達林的猜忌妄想是起於合理的懷疑,而且他確實有很多值得他懷疑的事情。猜忌妄想也不必然讓一位領導者無法順利工作、理性決策與有效率地行事。史達林能擊敗他的敵人,是由於他沒有善惡之感同時又極其狡猾精明。與希特勒相反,史達林的決策能力在戰爭的過程中不斷改進,到最後他讓將領更自由地指揮戰事。戰爭剛開始的時候,他試著透過共黨書記來控制前線上的大小事務。這種作法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德軍差一點就奪下了莫斯科。幸運地,史達林有足夠清醒的神智,他改變了想法,讓他的指揮官們享有更多的主導權。在這件事以及其他特點上,他證明了他並沒有狂妄症候群。
約瑟夫.史達林
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是一個擁有非比尋常精力的人。他是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當總統時的副總統,麥金萊於一九〇一年九月十四日遭到暗殺。當羅斯福接任總統職位時,時年四十三歲。一九〇四年他再度被選為總統,然後於一九〇九年時下台,時年五十一歲。對很多美國人來說,他的總統表現可以拿來跟林肯與華盛頓的偉大政績相提並論。愛德蒙.摩利斯(Edmund Morris,他為羅斯福所寫的傳記贏得普立茲獎)與法國作家李昂.巴扎傑特(Leon Bazalgette)發表過一篇篇幅不長但是觀察敏銳的散論,當中www.hetubook.com.com解釋羅斯福發熱一般的性格:「他那些顯然具有攻擊性的言行像洪水一樣一波衝過又是一波,一半相當猛烈,一半帶點幽默,這更多顯示出來的是他精力旺盛,而不是嚴肅地思考。這些是羅斯福本性的一部分:他性格裡具有某種飽滿與充盈到自己不能容納的東西。攔水壩必須時常讓一些水溢出來,才能夠讓水壩後方的深水區保持平靜與清澈。」像誇大狂與狂妄症這樣的語詞如果拿來套在羅斯福頭上,非醫學專業的外行人並不會覺得不貼切。作為一個精力旺盛過人、又患有週期性憂鬱症的人,羅斯福在政壇階梯的攀升過程是非比尋常的。
在興登堡總統逝世之後,希特勒就開始慢慢地但毫不留情地拆除內閣政府;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他成功佔領蘇台德地區之後,內閣就完全消失了。國內政治變成希特勒閒暇為之的小娛樂,他的思考與計算專注於對外政策以及抵觸凡爾賽合約,企圖全面重建軍隊,擴張德國邊界——最後這件事他從一九三六年三月佔領萊茵河地區中連接法國邊境的非軍事區域時便已開始。希特勒長期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自從一九三六年七月爆發了西班牙內戰後,在他的構想裡,與蘇維埃政的戰爭無法避免。他宣稱自己的行動是防衛性質的,他的意向是和平的,但他是一個慣性的撒謊者。
改變這個局勢的,是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攻擊美國的珍珠港基地。羅斯福形容「將永遠不忘記這可恥的惡行」,並對日本宣戰。十二月十一日希特勒對美國宣戰。這給邱吉爾減去了心中極大的重擔。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德國最終將被美國與蘇聯的力量擊敗。邱吉爾個人對戰爭勝利的貢獻,將不會再如此刻這般關鍵。
甘貝爾-班納曼最主要的政治遺產是南非和解。他為偉大的自由黨改革鋪好了道路,在英國婦選舉權運動最盛時支持婦女享有投票權。就此而言,雖然他長期生病,他還是成功的首相。
當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張伯倫接替鮑德溫時,英國輿論大眾的反應非常熱烈。他初任首相時活力十足,十分積極,雖然已經是六十八歲的老人。事實上在那之前,他已經做首相的工作很長一段時間了。現在他把握這個機會跳上世界舞台。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在幕尼黑親自協商外交事務兩星期,結果是災難性的。慕尼黑將會以世界史上第一個巨頭會議的地點流傳史冊(會議在該月二十九與三十日),而且將對以後所有的巨頭會議永遠發出一個警告:相信元首間的私人交涉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但是更危險的,是一個政治家的理想主義(與狂妄心態),相信他一人可以給歐洲帶來和平。」很多人都忘記,張伯倫對和平的追求在當時是受到廣大支持的,反對者稱此政策為「姑息政策」。邱吉爾是重建軍備的擁護者,此時被輿論打成不實際的先知,許多評論家認為他已經不再值得重視,其中有一位描述他為「沙灘上擱淺的鯨魚」。但是儘管邱吉爾不同意張伯倫的作法,他一開始並沒有對張伯倫開砲。(當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安東尼.艾登勇敢地辭去外交大臣時,即便這種透過姑息來求取和平的政策被許多人視為已經失敗,邱吉爾仍然很快地在下議院裡支持張伯倫的圓形簽名請願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他在三月十七日上對黨鞭大衛.馬爾格松〔David Margesson〕表示,他跟首相的觀點並沒有出入。艾登的辭職之舉從來沒有發展成讓張伯倫倒台的關鍵因素。)直到十月五日在下議院會議上邱吉爾才讓他的批判充分地傾洩出來,稱慕尼黑協議是一個「徹底而沒有藥救的敗舉」。
在推翻大衛.勞合.喬治這位具有強壯形象的首相之後,繼任的幾位英國首相都受到健康問題的困擾,這有可能也是姑息政策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安卓.波那爾.拉奧(Andrew Bonar Law)從勞合.喬治手上接下首相的職務,當時他已知道自己得了咽喉癌。到了一九二三年四月,他已經無法在下議院發言。同年五月辭職,十月他就過世了。我們不知道他的醫生,湯馬士.霍爾德爵士(sir Thomas Horder,來升為勳爵),是否在第一時間勸阻他不要擔任首相,或者,如果醫生確有勸阻,為什麼拉奧忽略這樣的勸告而且還對他的同僚隱瞞自己真正的健康狀況。史丹利.鮑德溫在拉奧辭職後成為首相;職業生涯中他兩次因先前在位者的健康狀況不佳而升任首相一職,這是件古怪的事。第二次時,那位生病的首相是詹姆士.蘭姆塞.麥克當諾。
你永遠誠摯的朋友勞合.喬治
三個月之前,在五月裡——醫生診斷羅斯福血壓過高,而且嚴重的缺鐵,情況壞到他接受了兩次輸血,而且該月的上半月他完全沒辦法離開臥房。但是並非是總統的健康,而是政治使得美國對戰爭保持距離。希特勒充分地了解這一點。
這種較為寬廣的思考方式——即調整先前的假設或從根本上重新評估策略——已經不再可能,而這正是狂妄症候群的指標特徵。領導者被他的確信與極度自信綁架了,而確信與極度自信最後總是讓人無可挽回地遭受天譴。
耐人尋味的是,邱吉爾在所有戰後書寫、出版的書籍裡,從來不強調讓戰爭內閣拒絕與義大利談判是什麼了不起的功績。在戰爭回憶錄第二冊《最光輝的時刻》(Their Finest Hour)裡邱吉爾寫道:「未來的世代可能會認為這是一件值得記上一筆的事情,那就是,我們在戰爭內閣的議程上從來不曾討論過那個最終極的問題:英國應不應該單獨作戰下去?」這些戰爭內閣的討論彰顯出一個絕佳的範例:在國家遭遇危難時,一個民主的內閣政府如何運作;邱吉爾真正的性格也在其中顯露出來。在這個時點上,他沒有任何沮喪、輕度躁症、狂妄或躁狂行為的跡象。在閱讀這些會議細節時,最令人高興之處,是看到一位完整的政治家,他藉由思路清晰的論據以及一切政治技巧的能耐,在與同僚的公開辯論上,贏得了一場至關重要的政治爭論。
在一九四〇年代初期帕金森氏症並沒有任何有效療法,但是這個病大概並不怎麼影響希特勒最主要的決策,因為他野心過大的戰略目標早就決定好了。很奇怪地,希特勒的顫抖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史陶芬貝格暗殺事件(史陶芬貝格是德國軍官,暗殺計畫的主要人物)後停止了一段時間。當時在希特勒在他的「狼穴」指揮部裡,一個離他不遠的手提公文箱內的炸彈被引爆;這爆炸震破了他的耳鼓,他的平衡感受到損害,但是最重大的影響是心理層面的,希特勒的妄想變得嚴重的多。不過他仍有能力施展他的權威;到了十月底,他全力投入亞耳丁戰役的準備工作,也仍然控制著軍隊。
英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裡的經濟榮景,經過了兩個源起於歐洲的毀滅性戰爭後,喪失了不少元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一點一點地失去了她的帝國統治,其中最劇烈的,最重大的,就是一九四七年准許印度獨立。由於經濟衰弱,英國不得不退出蘇伊士運河以東地區,差不多在一九六七就完全退出。
希特勒是二次大戰的主要設計師,對猶太人進行的種族屠殺也是在他的號召下進行的。德國製造出希特勒,讓他在展望裡看見自己未來。全國如此欣然地伺候著他,不只分享了他的狂妄,也一起分擔他所遭受的天譴。
雖然布魯恩繼續治療總統,設法給他導入了低鹽餐飲與減重計畫,讓他服用苯巴比妥,但是他從未獲得麥金泰爾或總統本人——後者透露更多訊息——的徵詢,總統是否應該在十一月繼續參選。有時候會有一種說法,認為羅斯福不應該「被允許」參加競選,但是誰有這個權力來不允許呢?於是總統決定要繼續參選。(根據布魯恩的紀錄,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時,羅斯福已經有了典型的心絞痛。證實了他先前的診斷,總統的確患有冠狀動脈疾病。麥金泰爾認為這疼痛是「肌肉引起的」。羅斯福本人則是否認他病情的嚴重性,雖然他知道布魯恩是心臟醫師而且他當時血壓非常高。在九月十一曰至十六日在魁北克跟邱吉爾舉行會議時,總統的血壓來到了他所有紀錄的最高點,二四〇/一三〇。疾病可能可以解釋羅斯福一次罕見的判斷閃失:羅斯福支持所謂的摩根陶計畫〔Morgenthau,按照羅斯福的財政部長漢斯.摩根陶而命名〕,內容是將戰後的德國去工業化。這個「計畫的構想是把德國送回一八七〇年之前的農牧水平,把所有可拆卸的機器都運到俄羅斯作為戰爭賠償,以便讓德國工業完全消失」。由於許多顧問的指貴,羅斯福撤回了他的支持。這顯示他仍有能力聽從好的建言。)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一日,在晨間的記者招待會上,羅斯福朗讀一封他寫給鮑伯.杭涅剛(Bob Hannegan)的信,後者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主席。信中表明他將繼續參選總統:「我滿腔的內心都呼喊著要回到我在哈德遜河畔的家,卸下公共的責任……這本來是我的選擇。」但是他聲稱,還有一場戰爭必須打贏,必須確保和平的局勢,國民的經濟必須架構在堅實的基礎上。「因此,雖然心中無奈,但是作為一名勇敢的士兵,我重申一次:如果我們的總司令——美國崇高的人民——的命令是如此的話,那我將接受,並且在職位上繼續服務。」
十月六日,內閣第一次在威爾遜缺席下進行會議,國務卿羅伯特.藍新(Robert Lansing)請格雷松向內閣報告總統的病情。格雷松告訴他們,威爾遜只是因為神經衰弱,消化不良以及神經系統耗弱而身體不適。藍新提到憲法裡規定總統在不能視事的期間可讓副總統擔任職務,格雷松清楚表示他不會簽署任何失能證明,事後還數次強調總統的智能沒有受到損害。實際上威爾遜既不能讀也不能口述;他躺在一個遮住光線的房間裡,一連好幾個星期什麼國事都沒處理。直到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他才能再次主持內閣會議,而這幾乎是他中風後七個月的事情。在這段期間裡,他顯然沒能力做重要決定,他雖然與格雷松討論過辭職的事,但是兩人誰也沒有在積極進行。
你不能用一般的標準來判斷首相:他跟你或我曾經遇過的任何人沒有一點相像之處。他是一大群衝突的集合。他不是處在浪峰上,就是在波谷底;不是對人倍加讚譽,就是酸苦而多責難,不是脾氣好的像天使,就是像地獄般暴怒;如果沒有很快睡著的話,就會變成一座火山。在他的性格組成裡,沒有折衷這回事。他是一個渾然天成的小孩,情緒像四月天一樣的多變。有時他對一位朋友說了殘酷刻薄的話,但一個小時還沒過,因為聽了友好的解釋就忘了這回事,而同樣這些殘酷刻薄的話他在傳電報給遠在數千里之外的朋友時也會說,只是這時一點緩和補救的機會都沒有。對他來說,這兩個情況好像全無差別……
在希特勒的理性表象之上,卻可以看見狂妄症候群大部分的元素。希特勒掌握的權力已經來到一個層級,他的判斷、洞察與認知成了唯一的決策因素。其他人的意見幾乎已經完全無法左右他,而他持續地犯下錯誤,巨大又狂妄的錯誤。希特勒的心智框架在一九三〇年代早期在追求權力的過程中是理性的;即便大權在握以後,直到一九四〇年夏天為止,如果沒有這層狂妄症狀的蒙蔽,他應該會充分考慮莫斯科周邊戰事有全盤翻轉的可能,也應該會了解,先前避免在軍事上挑釁美國的策略有必要維持下去。到了一九四一年年底希特勒對軍事與政治現實採取忽視的態度,因為他完全知道美國輿論界多麼深切地希望能夠避免戰爭。在十二月裡他本來可以返回他先前的願望,向英國提議進行政治談判,以避免美國加入戰爭。如果他能先單方面停止轟炸並且表明與邱吉爾會談的意願,而且如果他能請求羅斯福出面居中斡旋以使他們達成協議,同時公開地與日本可恥的偷襲行動劃清界線,那麼,也許羅斯福就不會對德國宣戰。就算希特勒與美國一戰終不可免,他也可以爭取到幾個月的時間,讓在柏林的每個人都可以專注在他們當時手頭上的任務——如何扭轉德軍在莫斯科周邊的軍事挫敗。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裡這六天對德國的命運關係之重大,就像一九四〇年五月裡的那五天之於英國人民與世界一樣。在這幾天裡,希特勒所做出的重大決定,不可避免也無法扼抑地導致了他一九四五年在柏林的自殺。他在奪取莫斯科失敗的當下,完全沒有必要地向美國發出挑戰。雖然德國外交部給他指出了清晰的法律見解,三國同盟條約裡並沒有任何條款約束德國必須向美國宣戰,因為日本並沒有被美國攻擊;日本在十二月七日對美國珍珠港內的艦隊所發動的是偷襲攻擊,這確保了德國與義大利(對於正式宣戰並不陌生)的人民大眾並不感覺到非得協助日本進行防禦不可,然而希特勒還是做出了對美宣戰的決定。根據某位當事人日記,日本發動偷襲的消息傳來,希特勒第一個反應是「我們絕對輸不起這場仗……我們現在多了一個三千年來沒有被征服過的盟友」。此時德國士兵正在莫斯科周邊遭受到嚴厲的攻勢,十二月八日由康士坦丁.羅科索沃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指揮的蘇維埃第十六軍團從德軍手上奪回了克留果沃(Kryukovo),這是俄國軍團指揮部原先所在地,先前十一月時被德軍攻下。
一個比羅斯福更健康的總統可能會主導更多的決策,且更積極地涉入討論。不過羅斯福事實上已取得了他以及美國所想要的東西,最主要的,就是讓史達林承諾,在歐陸的戰鬥結束後二到三個月之內,加入對抗日本的戰爭。這在當時被認為是關鍵的。人們容易忘記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作戰犧牲了多少美國士兵的生命。邱吉爾關注的焦點是歐洲,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對羅斯福而言,由於日本的因素,史達林也很重要。蘇聯跟中國接壤,而且在海參威有一支艦隊。後來的發展是,在八月裡,史達林在日本投降的前幾天才決定加入對日戰爭。
勞合.喬治住在唐寧街十號期間健康狀況維持地很好;他沒有憂鬱症的紀錄,只有週期性的喉嚨感染,這似乎跟工作壓力大有關。一九一八年九月他得了嚴重的流行感冒達九天之久,之後恢復的過程也十分辛苦。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時一次大戰結束,參戰國公布停戰協定,勞合.喬治恰如其份地被稱為「贏得戰爭的人」。
希特勒的算盤是,他通往權力最佳的路徑是讓這個國家年邁又衰弱的總統興登堡留在位子上。興登堡原是陸軍元帥,他在一次世界大戰中成為戰爭英雄,雖然戰敗但還是獲得晉升。後來他於一九二五年當上德國總統,即便當時他已經年老力衰,對民主共和的政體甚至懷抱疑慮。希特勒看到,他可以利用憲法賦予興登堡的重大權力,來驅使武裝部隊取締反對黨派,並且架空憲法本身。希特勒的策略是利用興登堡對德國陸軍的影響力,讓體力衰老的興登堡在通過合法程序將政權轉移給自己的時候,使軍方也站在支持的一方。
然而,邱吉爾的軍事參謀長哈斯亭.愛斯梅(Hastings Ismay)將軍在一封信上所描繪的人格形象,更大幅度地揭露他非比尋常的性格。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愛斯梅寫給在北非沙漠的克勞德.奧辛列克(Claude Auchinleck)將軍。愛斯梅外號「奧克」(Auk),最近經常成為邱吉爾情緒的出氣筒。信上稱:
一九七三年大英國協加入了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當時原先只有創立會員國六國,此次連同英國,加上丹麥與愛爾蘭,變成有九個會員國。今天的歐洲聯盟由二十七個國家組成,雖然是個獨一無二的嘗試,但風險與成敗仍未定數。
這未被診斷出的癌症對張伯倫作為首相進行決策有沒有任何嚴重的影響,我們沒有明確的證據。但是在一九三九年時,若說這癌症對他毫無影響,那會令人十分驚訝。雖然我們對於癌症早期對人的影響所知還太少,但是有證據指出(部分還未發表),癌症會引發老化的過程,有相當的機率會伴隨著情緒低落,以及常常伴隨著腦與身體機能運作速度的減緩。(癌症意指惡性的腫瘤,不論這腫瘤是從什麼組織生長出來或者它位於身體內的哪個部位。癌細胞可以在身體裡潛伏很多年。例如有人統計過,直徑約二至三公分以小腸癌在被診斷出來之前,癌細胞平均已經在身體裡存在五年之久。流行病學上有為數不少的證據顯示,在重大的持續性工作壓力與之後被診斷出患有癌症之間,統計上有顯著的正相關。也有一些證據——雖然並非決定性的——顯示了生活壓力如何可能成為引發癌症的因素,這是說壓力使免疫細胞能夠快速增生。)在一九三八年時,體力耗竭與壓力兩個因素對張伯倫造成損害。一九三九年三月,當時的外交大臣巴特勒(R. A. Butler,一般稱他「Rab」)描述過,當他得知義大利入侵阿爾巴尼亞的消息,他就到唐寧街十號去,告知首相發生了什麼事。張伯倫在他的書房裡,站在打開的窗前餵鳥兒吃穀子。他對巴特勒的來訪頗為惱怒,還表現出一臉驚訝的模樣,不明白巴特勒為何煩惱:「我很確定墨索里尼已經決定不來攻打我們。」當巴特勒再談到這對巴爾幹半島地區的威脅,張伯倫不讓他說下去,說:「別傻了。回家吧,上床睡覺。」然後繼續餵他的鳥兒吃穀子。這件插曲最讓人擔心的一點是他自我欺瞞的能耐。而這件事的紀錄者是巴特勒,一位支持慕尼黑會議以及綏靖政策的政治人物,這使得這項證詞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張伯倫在他的首相任期裡有可能很早就患上了狂妄症。
沃倫.哈定
默蘭:我有時候真不知道五十年後人們會給我什麼評價。
一開始麥克當諾由於身居首相要職以及他頗受各方矚目的政治形象與地位,是還有一點施展空間的。然而在內閣大臣中只有三位前工黨閣員,下議院中只剩下十三位工黨議員支持他,他開始感覺到孤立無援,因為工黨裡幾乎所有的老同事都跟他劃清界線。如果他還年輕,他的妻子還在世的話,這一切可能比較容易承受。慢慢地,他的健康問題開始損害他的聲望。麥克當諾患了青光眼,接受過一連串的眼部手術,而且到了一九三三年時,更令人憂慮地,他的心智功能開始惡化,他極可能得了輕度的失智症。到了一九三四年、他六十八歲時,他對英國政策的影響變得微乎其微,他差不多已經成了傀儡領袖。國民政府裡的關鍵人物是鮑德溫,重要的決定是由他拍板的。
然後羅斯福於一九四五年二月赴雅爾達與史達林和邱吉爾會談。羅斯福的健康狀況是否成為左右會議結果的重要因素,仍然是個高度爭議性的議題。這次會議決定了東歐未來的面貌,而波蘭議題是特別難解。
勞合.喬治,有些人稱他「威爾斯巫師」、「森林中的大野獸」或「山羊」,是二十世紀裡最具有多方才能的政治家。他的演說口才罕有匹敵,他協調事務的出色天分是罕見的。他是最激進的財政大臣,而且在開頭三年的任期裡,他是最好的英國首相。然而他也是第一位在發展出狂妄症狀之後被推翻的英國首相。從一九二〇年開始,他對阿總統制的政府很快地興起了毫無保留的欽羨心情,先是對老羅斯福政府,然後是對小羅斯福政府。為了對自己有利,後來他甚至對希特勒也讚美過度。他狂妄的性情一直都是有的,但是在一九二一年之前都在民主體制的制約之下。
邱吉爾終其一生,都有短期但反覆發作的重度抑鬱問題,這我們在導論中已經提到過。他父系的家族裡有這樣的病史。威爾遜描述邱吉爾跟他討論他黑色的抑鬱,這問題從他少年時便固定出現,當他結婚之後,在下議院時也持續著;威爾遜也描述了邱吉爾提起他過去的自殺念頭。邱吉爾告訴他,當一列快車穿越車站時,他不喜歡站得太靠近月台的邊緣。如果可能的話,他會選擇讓自己與火車中間隔著一根柱子,否則只要一秒鐘的行動就能結束這一切。他形容這些感覺像是幾個丁點的絕望。
英國首相波那.拉奧、鮑德溫、麥克當諾與張伯倫
憂鬱的症狀並沒有阻礙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二年以三十九歲之齡掌握大權;儘管有些時期他有神經過敏的問題,但他還是統治了二十年之久。墨索里尼一開始統治的基礎,是建立在法西斯黨、教會、商業團體i、軍方以及官僚精英所共同達成的協議。他逐步建立起一種領袖崇拜;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的衣索比亞戰爭勝利之後,這領袖崇拜使他站穩了主導國家大事的位置。許多人將戰爭視為墨索里尼個人不顧冒險的後果,但他從未鼓動國王維克多.伊曼努爾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於一九四〇年投入戰爭,而且許多有力人士都表示反對。然而一九四〇年時義大利確實在墨索里尼一人的掌握之下。他採取的每一個行動都帶有明顯的狂妄症。「法西斯大議會」、「元老院」、「法西斯與工商立法院」以及「部長議會」都是妝點門面的設置,實際上全無份量。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羅斯福死於沃姆斯普林斯(Warm Springs),黛西是他死去之前最後談話的人。跟黛西在一起的還有露西.魯瑟福特(Lucy Rutherford),她曾跟羅斯福有婚外情,但是一九一八年被艾倫娜發現後就已中止。霍華.布魯恩就在不遠處,總統死後不久便前來看他。他擔任羅斯福的醫生,在任內的行為都無懈可擊。他等到一九七〇年才發表了他對羅斯福疾病的解釋,而且選擇的是《內科醫學年報》(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而不是試著利用他病人的病歷來撈錢。布魯恩於一九九五年過世的時候,他的遺孀把他的文件,裡面包括他的醫療日誌,存放到位於紐約海德公圜的羅斯福紀念圖書館裡。
希特勒於戰爭全程對軍事動態都有相當仔細的掌握,但是他似乎把俄軍於十二月五日到八日所發動的攻勢從腦裡一筆勾消。這種等級的軍事考驗會讓所有政治領袖——只除了最狂妄者——重新評估並考量替代選項,以及聽取專家的建議。這些希特勒通通不做。相反地他違反專業的建議,開啟了新的政治與軍事戰線,來對抗世界上力量最強的國家。當然,有人可以說,從他先前的策略看來,他這個決定是無可避免、是有內在邏輯的。但是他本來有另一條路可走。
波倫描述了一九四五年三月末羅斯福總統與歷史家李查.紐時達(Richard Neustadt)進行的一次對話;根據此一描述,總統的思考仍是清晰與專注的。波倫說,總統非常清楚,雅爾達協議是對蘇聯的一個測驗,看蘇聯究竟有多大意願在戰後仍保存三巨頭間的尊重與合作;而且總統感覺到,照當前情況的發展,莫斯科這個測驗是不會通過的了。波倫還相信,如果羅斯福在四月回到華盛頓,他一定會跟邱吉爾聯手拒絕從易北河撤退,絕不回到先前協議好的佔領區裡。而且,既然羅斯福預定在五月前往倫敦,波倫相信,因為這時德國剛投降,一定會召開一個三方的緊急會議,這可以替代後來的波茨坦會議。新受命職掌國務院的是愛德華.史特提尼伍(Edward Stettinius),他遠比前任國務卿科戴爾.霍爾(Cordell Hull)容易操控,這清楚表示羅斯福的構想是要扮演更突出的角色,而不是要淡出。再者,他任命波倫出任私人幕僚,以協助自己鞏固權力,這真的不是一個準備好在幾星期後死去的人會採取的行動。羅斯福的一生,從他患了小兒麻痺以來,就一直是個努力戰勝病痛的人生;就算他的醫生們知道他已經來日無多,在性格上他也還是忽略他的健康問題,繼續往前計畫。有不少有力的理由指出羅斯福不應該在十一月出來再度參選,但是雅爾達會議不是其中之一。
國會投票之前,在三月二十一日上,波茨坦兵營教堂(Postdam Garrison Church)裡舉行了一個意象強烈的官方儀式,作為帝國議會新會期的開幕儀式,納粹黨與陸軍齊聚一堂。老態龍鍾的總統興登堡與年輕的總理希特勒並肩走下教堂的中央走道。希特勒在演說中大力推崇陸軍元帥總統,演說完畢後走到總統身前,彎下上身,握住老人的手。以這樣的姿勢,希特勒演出了超乎事實的恭順:事實是他已經確保了軍隊的效忠,合法地成為政府首腦,踏上了通往絕對權力的道路。
這個「滴答鐘」的情況比我過去所知都更嚴重的多。而且處理這個狀況最難的地方,就是我們不能跟任何人說到這個「滴答鐘」的問題。這實在太令人擔心了,任誰都沒有多少能耐來做點什麼。(你最好把這一段撕下來然後把它毀掉。)
羅斯福的健康狀況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之間日漸惡化,雖然他的私人醫生海軍上將羅斯.麥金泰爾(Ross McIntire)大多都不予承認。只有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在美國海軍醫學中心(Bethesda Hospital),三十九歲的m.hetubook.com•com海軍心臟科醫師霍華.布魯恩(Howard Bruenn)才為羅斯福做了一次完整的全身健康檢查,這是他擔任總統十一年以來的第一次。這是在羅斯福的女兒安娜堅持下進行的,雖然麥金泰爾表示反對。麥金泰爾根本不應該擔任羅斯福的私人醫生。他不具有醫療專業,此外他身為現役的海軍軍官,他的病人同時是他的上級指揮官,這個角色組合持續地帶來壞處。布魯恩發現羅斯福的血壓是一八六/一〇八,胸部的X光照片顯示心臟肥大。布魯恩直截了當地診斷羅斯福患有高血壓、高血壓性心臟病、左心室心臟衰竭以及急性支氣管炎。(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羅斯福總統有過兩次血壓紀錄,分別是一八八/一〇五與一七八/一〇二,兩者都清楚顯示出高血壓,但是麥金泰爾〔醫學專業是耳鼻喉科〕當時說「總統的心血管各項指數都維持在一個良好的水平」〔Ross T. Mclntire, House Physician G.P/Putnam's Sons, 1946, p.139〕。羅斯福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量的血壓指數有可能是良好的,但是麥金泰爾應該定期測量,並且至少設法降低總統血壓,雖然當時可用的治療方式效果都頗有疑問。並沒有紀錄顯示麥金泰爾做了兩件事中的任何一項。)支氣管炎是麥金泰爾唯一正確診斷的病情。布魯恩事後形容總統當時的狀況「真是太嚇人了」。
當然,希特勒有時候確實像一個發作中的瘋子,但是從醫學的角度來看,只有當一個人的精神狀況讓他在某些方面失能時,醫生才可以做出患有精神疾病的診斷。而在希特勒的案例上,不管他整體的精神況狀究竟是怎麼回事,都不可能主張他因此失能,甚至完全相反,他從崛起、掌權、將絕對的權力鞏固於自己一人手上,其政治計算與自我紀律是極其出色與周詳的。
保羅.德沙內爾
然而根據那些親身於一九四五年二月裡在雅爾達的人的說法,羅斯福進行談判時並不像有過度嚴重的失能,雖然他的健康確實很糟糕。許多當時在場的資深外交官與政治家——當中有些全程密切參與三巨頭全部出席的七次會議——提到羅斯福的表現不差,為他的心智能力辯護。查爾斯.波倫(Charles E. Bohlen)是當時美國國務院對白宮的連絡主任,在會議中擔任羅斯福的口譯員。他絕非逢迎奉承的人,然而在一九六九年他如此描述羅斯福在雅爾達的表現:「我不知道總統曾因為健康狀況而對蘇聯方面做過任何讓步。」他還說:「他似乎由他的顧問團緊密地引導著,不曾照自己的意思採取任何一步。」因為口譯員獨特的工作性質,所以也具有諮詢人員的功能,為了協助他們準備,讓他們先知道會哪些主題,為政府領導準備說話材料的官員會事先拿一份副本給口譯員。美國歷史學者亞瑟.史列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曾寫信給史達林的口譯員瓦倫廷.貝瑞茲科夫(Valentin Berezhkov),詢問從蘇維埃方面看來,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會議上的健康狀況如何,特別是相較於先前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德黑蘭會議上的表現。貝瑞茲科夫覆信說:「毫無疑問比在德黑蘭差,但是任何看過他談判的人都說,即便他病容滿面,他的心智能力仍然強大。在感到疲倦之前,他是十分清醒的,反應快速,論述也非常有力。」他還提到「史達林對羅斯福非常的尊敬」。
朗格報告裡對希特勒性變態的界定,是來自潔莉.勞博(Geli Raubal)的敘述,內容講述了她在自殺之前跟希特勒的性經驗。我們不知道希特勒與艾娃.布朗(Eva Braun)——希特勒跟她在地下碉堡裡結婚,之後兩人自殺——的關係裡有沒有性變態的成分。不過不管怎麼說,性變態不是一種疾病。心理學家佛洛姆為希特勒下的總結是最持平的:「我們最多可以說,他的性|欲主要是窺淫式的,跟比他低下的女人時他是肛|門性|虐待者,跟他所崇拜的女人時他則是受虐狂。」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
卡爾文.柯立芝
並沒有多少證據顯示他的心智狀態損害了他擔任總統的表現。他的評論「處理美國國務就像做生意一樣」(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總結了他的態度——政府要精簡,債務要削減。他的憂鬱症焦慮可能是他個人問題,但是如同他的傳記作者所寫:「他跟胡佛、羅斯福、杜魯門甚至跟在他之後的艾森豪一樣,得多馬克熱病最罕見的一型——那種只有總統才會染上的類型;這注定了他無法持平地看待任何有潛力繼任總統的人。」他的憂鬱症在他退休以後以及在他的書信裡表現的更為明顯。柯立芝死於一三三年一月五日,死因是冠狀動脈栓塞。
也有人宣稱——也許不太可能是真的——德沙內爾在接見英國大使德爾比伯爵時幾乎什麼也沒穿,除了他的徽章以外。我向英國外交部查詢過,對於這件傳說,他們沒有任何紀錄。還有一次有人發現德沙內爾衣著整齊地在杭布葉(Rambouillet)的淺水湖中散步。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五日,多家報紙打出「總統的健康崩盤」這樣的標題,報導了總統在諮詢總理的意見之後決定辭職。德沙內爾在同月二十一日自願地執行了他的決定,在位僅七個月。
在此期間,英國在巴勒斯坦、土耳其與美索不達米亞(我們今日稱為伊拉克)的軍事介入造成了嚴重的傷亡,許多下院議員開始在選民之間感覺到一種不安。美國總統威爾遜沒能成功地阻止國會否決凡爾賽條約的第十條——「對聯盟內所有會員國的領土完整及其既存的政治獨立予以尊重,並保護其免於外來的侵略」——這導致美國沒有加入國際聯盟。所有這些都影響了勞合.喬治在國內作為成功的和平奠定者的威望。
現在一般認為德沙內爾除了艾爾比諾症候群之外,還患有額顳葉失智症(Frontotemporal Dementia)。這是一種退化性的腦病變,一開始常常出現無法控制的行為。他於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過世,享年六十七歲,相關人士沒有提到任何腦部病變,也沒有死後的身體檢查。
然而史達林的心智人格組成裡很特出的一點,是他極度的妄想症。關於他妄想的故事多到數不清,一般人聽到還以為他精神失常。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謝爾蓋.基洛夫(Serjei Kirov)遇刺之後,史達林的妄想症變得嚴重了。有一天在克里姆林宮裡,史達林與一位海軍軍官走路經過安全衛兵旁邊;這些衛兵沿著迴廊每隔十碼就設一哨。「你注意到他們是怎樣的嗎?」史達林問這位軍官。「你順著迴廊走下去,想著『會是哪一個呢?』如果是這一個,他會等你轉身時從背後開槍;如果是那一個,他會開槍打你的臉。」另外一個詭異而且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史達林有一個近身侍衛,長筒靴長期以來都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有一天他很不明智地把問題給修理好了,史達林因為沒注意到他靠近被嚇了一跳,就把他槍斃了。
羅斯福從來不是一個對於談判對手的力量與弱點會產生幻覺的人。如他對海軍上將威廉.勒希(William Leahy)說,他知道「此時此刻我為波蘭只能做到這麼多」。他的病痛並沒有使他變成一個容易上當、讓史達林擺佈的美國總統。這一點,從羅斯福在三月十三日的一場對話可以清楚看出。從雅爾達回來兩個星期之後,羅斯福把里昂.漢德森(Leon Henderson)找來辦公室談話,他是羅斯福新政的經濟顧問,羅斯福打算讓他到德國擔任美國經濟首長。羅斯福警告他不要做太多超前計畫的事情,也提醒他一方面法國、德國與美國都將遵守協議,但是蘇聯人會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商定的條款他們雖會遵守,可能敗露的地方他們不會亂來,但是只要可以躲過監督的地方,他們就會自己行動。
邱吉爾的下坡路
撇開脾氣問題,羅斯福在總統任內的政績是十分可觀的。他注意到戰略上在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需要有個捷徑,因而確保了巴拿馬運河的建造。他對門羅主義的詮釋,阻止了外國在加勒比海地區建立基地,並且把介入拉丁美洲事務的獨家權利握在美國手裡。古巴得到解放,美國境內的軍事力量也強化了。他於一九〇五年讓日本與俄國和談,為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國內,他一方面整頓政治,伴隨而來的是殺人事件減少。他的反壟斷法為市場經濟建立了遊戲規則。一九〇六年八月發生布朗斯維爾事件(Brownsville incident),羅斯福在處理黑人士兵的問題上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但他也承認犯錯。。羅斯福在環境政治上也功績顯著。到卸任時為止,他已經創建了五個國家公園,十八個國家紀念建築。他完成這些事情,一半是以哄騙的方式讓國會的威望為他背書,一半則是簽發執行命令。他脾氣火爆,行事帶威權霸氣,沒有耐性,有時甚至好與人爭,但是他也獲得很多的敬愛。
麥金泰爾作風還是一樣,甚至不願意接受布魯恩的判斷,不讓總統服用強心劑。等到麥金泰爾於五月三十、三十一日與四月一日跟三個部門的醫療顧問團開會之後,才不情願地同意施打。這是因為布魯恩揚言,如果不讓總統打強心針的話,他將不再過問此案。對一位年輕的海軍軍官來說,這是非常勇敢的行為。
常常有人拿希特勒跟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做比較,有時是為了判定誰是更大的壞蛋。如果評量的標準是誰造成的無辜死亡人數更大,那麼史達林就脫穎而出,成為比希特勒更黑暗的角色。跟希特勒不同,史達林的罪行數十年來都不為人知。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透過蘇維埃的新聞機構TASS,承認在卡廷森林發生的波蘭軍官大屠殺是蘇聯所為。一九九二年十月葉爾欽公布了一份由史達林以及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y Beria)簽署的政治局決議,批准射殺一萬四千七百名波蘭軍官以及一萬一千名其他被囚的波蘭人。這場大屠殺在當時被錯誤地算在希特勒頭上,因為蘇維埃當局提供了一份假情報。
要把勞合.喬治與阿斯奎斯兩人拿來比較是出了名的困難事。羅依.詹金斯(Roy Jenkins)在一九八七年談到阿斯奎斯時提到,一九六四年他為他編寫傳記時,努力地保持客觀:「他有知識、判斷、洞察力與寬容的心……即便如此,我覺得他在位太久了,他的領導風格無法適應作戰期間對領導人的要求。」
羅斯福並沒有受到國會或輿論的壓力要求對德國宣戰。然而希特勒此時的心態是與美國一戰終不可免,從一項措施就可以看出:他放手行動,於十二月八日到九日之間取消了德國潛水艇不得攻擊美國海運船隻的禁令,用意顯然是在挑釁美國的輿論。希特勒選擇對美國宣戰的當日,十二月九日,蘇維埃軍隊重新奪回了伊斯塔拉(Istra)。希特勒不可能不知道莫斯科周邊的戰況如何。蘇維埃新聞社並未報導十二月五日的反擊行動,但是到了十二月十三日,就努力讓所有報紙都刊出「德軍包圍與攻奪莫斯科的計畫被瓦解」、「德國部隊前進莫斯科途中被擊退」這樣的頭條新聞。十二月十四日史達林下令拆除莫斯科工廠、橋樑與公共建築上所裝置的炸藥藥包。
西奧多.羅斯福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過世,享年六十歲。他的朋友自然學者約翰.波羅夫(John Burroughs)如此描述這位患有週期性憂鬱症與焦慮症、並且可能一生都與躁鬱症奮戰的出類拔萃人物:「他一離開,這世界就更蒼白、更冷清了。我們將再看不到一個像他這樣的人。」
病痛或心智失能都不能作為這兩人減輕罪責的藉口。史達林的健康基本上良好。他能與朋友喝酒喝到半夜,工作時間也很長。在二次世界大戰全程裡他的身體一直都很強壯,而且在德黑蘭、雅爾達與波茨坦三次與盟國進行的關鍵戰時會議上,他都能挺的過來。然而在一九四一年夏天,他見到德軍推進到蘇維埃的心臟地帶,也了解到,他忽視了那些警告他德軍攻擊近在眼前的聲音,這時他似乎精神崩潰而整個人垮掉了。但是他恢復了勇氣,當德軍跨入莫斯科的防衛圈時,他還大膽留在城裡反抗。
希特勒正確地估算,佔領捷克斯洛伐克(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不會導致英國與法國宣戰,但是他知道入侵波蘭則會。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在德軍開進巴黎之後,希特勒在當天清晨巡視巴黎時,他相信自己已經沒有敵手。他無戰不勝,他初期的自大妄想進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九曰在與國防軍參謀總長阿弗瑞德.約德爾將軍(Allfred Jodl)開會時,他決定在一年以內,也就是在一九四一年五月裡,要入侵俄羅斯。兩天以後,他將這個決定告知他的資深軍事將領。到了一九四〇年年底,希特勒認為美國將在一九四二年因為支持英國而加入戰爭。然而他還是十足謹慎地給德國軍方發布了一個特殊的命令,要求他們在那之前避免採取任何會導致美國加入戰爭的行動。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的說法確認了希特勒遲至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四日也還沒改變看法:「美國正式宣戰拖延的愈晚,對我們就更有利。」九月十七日羅斯福總統發表了「勿論」的演說,德國海軍上將艾力希.雷德爾(Erich Raeder)在與希特勒討論過後,下達命令:「領袖要求,在十月中旬以前,攻擊運輸船時要小心避免引發支節。」這顯示了希特勒此時仍然維持這個看法。十二月四日義大利外長加勒阿索.齊亞諾(Galeazzo Ciano)指出把美國捲入是「德軍越來越不樂見」的事。但是他的德國窗口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稍後不久在給他的電話裡對日本攻擊美國(十二月七日,珍珠港)表示高興。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阿道夫.希特勒是個瘋子;這有一部分是由於他的滔天罪行,但這個印象也有可能是得自他的行事風格,或者至少是來自他的演講方式,如同新聞影片中他多次在紐倫堡黨大會演說時所顯示的那樣。他看起來就像個瘋子在那裡嘶吼咆嘯。不過這新聞影片給人的印象是不正確的。事實上他演說的能耐非常可觀,他能夠發表非常平靜、甚至措詞柔軟的演說。希特勒也能十分禮貌,並展現良好的教養。他懂得掩蓋他的暴怒。二〇〇五年在英國上映的《帝國毀滅》(Downfall)是一部由德國拍攝非常寫實的電影,片中描寫了希特勒在柏林地下碉堡裡最後的日子,許多英國人看到電影裡呈現的不是一個怪物,都非常地驚訝。
在後續對雅爾達協議的批評裡,越來越多人忘記蘇聯艱苦對德軍作戰,並且征服了納粹的東歐佔領區,他們付出的傷亡代價非常高,所以想在談判桌上得到回報。有一份研究宣稱英國或美國每死一人,曰本人損失七人,德國損失二十人,蘇聯則死八十五人。各方的數字差別很大,但是另外一項統計稱蘇維埃軍民死亡人數是二千七百萬,相較之下美國人只有四十萬五千。俄國人今天仍然認為,為了推翻納粹政權,他們的犧牲是最大的。這是有道理的。
墨:他們認為你的政治生涯毫無疑問已經結束了。但我從你第一次中風就覺得,你如果退休,撐不下去的可能性還更大。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默:就是不知道到你下次中風之前還有多少時間。他們兩個都說,你再也不會出現在下議院了。我告訴他們,我看過比你癱的更厲害的病人,後來也都過的相當好。我們只能等待,看情況如何。
羅斯福一生中都沒有清楚無誤的、無可爭辯的躁狂症發作紀錄。但還是有些證據指出他有躁狂症的傾向。羅斯福的睡眠非常混亂,但是在一天工作十八小時之後他的短暫睡眠是深沉並且恢復精神的——這是輕度躁狂症的先決條件。然而,外行人描述羅斯福顯現出誇大狂的徵兆,專業醫師則診斷他罹患輕度躁狂症,這兩者間只有細小的區別。一九〇四年選戰勝利後,在冗奮的情緒裡,羅斯福宣布他將追隨華盛頓的典範,一九〇八年將不再競選連任。一九〇八年,他攻擊《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跟《印地安那波里斯新聞報》(Indianapolis News),他認為這兩家報紙誹謗他,這時有人說他是處在一種躁狂的暴怒狀態裡;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在一份送給國會的非常火爆的信函裡(美國政府剛從法國巴拿馬運河公司手中取得巴拿馬運河的所有權,國會中有人聲稱美國政府在交易中有貪污腐敗的行徑,羅斯福的信函是在回應這些說法),他說:「這些說法根本就是粗鄙下流與誹謗,在每一個核心的具體細節上都不符事實。」不止於此,他還攻擊《紐約世界報》的老闆約瑟夫.普立茲(Joseph Pulitzer),因為後者投書給《紐約時報》說:
大衛.勞合.喬治
美國總統格羅弗.克里夫蘭(Grover Cleveland)的口腔癌是政府首腦疾病事件裡最怪異的插曲之一。一八九三年七月一日克里夫蘭因為他的下顎癌症,在極端保密的狀況下接受手術,地點是在紐約港裡的一艘遊艇上。他被用皮帶直立地綁在一張椅子上,固定在這艘歐內達號的桅杆上,先用笑氣麻醉,然後再用乙醚。他的下巴有一大部分被切除。媒體被告知,總統只是有牙痛的困擾。費城一家報紙刊出了船上手術的事情,但是遭到官方否認。克里夫蘭是到目前為止唯一一位先當了一任,然後敗選一次,之後又重新選上當了第二任的美國總統。他於一九〇八年過世,享年七十一歲,死因跟他的口腔癌沒有關聯。
一九三三年四月起,政府機關裡的猶太人被剝奪了職位,司法機構裡以及大學裡的猶太人也遭開除。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這一天,希特勒前去探視已經非常衰老與病弱的興登堡,因為有個危機正在發生:布隆柏格將軍告訴希特勒,有兩百萬兵力的納粹衝鋒隊必須得到控制,如果再沒有其他有效行動的話,那麼總統就準備宣布戒嚴令,讓軍隊來接手政府的統治權。六月二十九日,費迪南.紹爾布齊(Ferdinand Sauerbruch)這位聞名的德國醫生被請來探視興登堡。也就在這一天——這兩件事或許有所關聯——戈林(Hermann Goering)與希特勒很快地採取了行動,他們擔心興登堡即便病倒在床上也可能宣布戒嚴令。當天晚上他們逮捕了衝鋒隊領袖恩斯特.羅姆(Ernst Rohm)以及其他許多人,並予以處決。興登堡感到欣慰——他沒能了解到事情的全部,他在陸軍裡的支持者更是高興。
他開始涉入政治是參加學生會。一九〇六年他勝選進入麻薩諸塞的州議會,並依照當地慣例,一年一任的任期連任兩次後退休。之後他當上諾桑普頓(Northampton)市市長,做了兩任,在那以後擔任公職二十年之久,歷任麻州參議員、麻州州長,之後是美國副總統。在這些時期裡,他一直是個誠實、勝任但也單調無聊的選舉公職人員。然而他始終存在的焦慮讓他對總統一職無法感到興趣。一九二四年他在給父親的一封信上說:「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我不得不被推出來當候選人。」
從那以後,許多國家政府首腦的醫療顧問也經常矇騙或誤導大眾,隱瞞其所照顧的病人的健康問題,把病人的利益置於國家的利益之上。在威爾遜的案例裡,撒謊並不困難,因為格雷松是服役中的海軍軍官,他所照料的病人是他的統帥,他是在順從上級的願望。
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麥克當諾下台,離開了首相的職務,由鮑德溫第三度接任。但他的麻煩不止於此: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大選裡他失去了自己的席次。次年二月,他利用蘇格蘭大學一個非正規的位置返回下議院,並且在內閣裡擔任樞密院議長。一九三七年五月當鮑德溫退休時,他也跟著離開政府職務,同年十一月七日他便死於心臟衰竭。從前的那個麥克當諾,從各方面來看,至此可說都所剩無幾。
莫瑞報告的診斷結果是希特勒患有歇斯底里、妄想、精神分裂、戀母傾向、自我曲辱(self-abasement),以及「梅毒恐懼症」(syphilophobia)——定義為害怕自己的血液在與女性的接觸中遭到污染。朗格的報告,用歷史學者羅伯特.偉特(Robert Waite)的話來形容:「提供了一個意含豐富、充滿暗示性的詮釋,任何認真研究希特勒的人都不會忽略。」報告中使用了精神分析的辭彙,朗格跟他的協同研究者在那時候大致上同意希特勒頗有可能是個有精神官能症的精神病患,距精神分裂只剩一步之遙。今天醫生已經很少使用「有精神官能症的」一詞,而「精神官能症」並不是一種疾病。精神分裂是當時診斷時常使用的病名,而且常常跟有躁狂症狀的憂鬱症混淆(後者今天稱為躁鬱症)。朗格報告作者群的論點是,希特勒的瘋狂,並非一般認知意義下的瘋狂,而是「缺乏適當抑制作用的精神官能症者」。
在他擔任總統的初期,他的健康狀況似乎是極好的。他從來不是一個有官場排頭的政治家;在充滿香菸煙霧的房間裡談事情是他風格之一。一九三六年在總統選戰的後期,在紐約的麥迪遜花圜廣場(Madison Square Garden),他發表一個典型的、自信的、火力十足跟黨性堅強的演說來嘲弄共和黨人:
一九二〇年邱吉爾當戰爭部長時曾經抱怨,首相幾乎完全接手了外交部的運作,而歷史家則寫道,英國某種型式的總統制政府是從這幾年開始的。他們本來是友好的,在英國對愛爾蘭的條約問題上曾同心協力,但現在他們漸行漸遠,比他們長期連繫裡的任何時期都更為疏遠。勞合.喬治甚至到了有點鄙視邱吉爾判斷的地步:
作為一位廣受尊敬但也樹敵甚多的人物,羅斯福卸任後沒辦法安置自己過平靜的生活。他很快就懊悔選擇了霍華德.塔虎脫(Howard Taft)當他的繼任者。塔虎脫政績不彰,而且患有呼吸中止症,這是一種與呼吸問題相關的睡眠障礙。(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才被確定為病症。呼吸中止症指的是睡眠時發生的呼吸中斷,鼻腔流入的空氣量低於正常時的百分之三十以下且持續十秒鐘。此一症狀的判準是,在睡眠中的任何一小時,都發生五次以上這樣的呼吸中斷,因而導致白天嗜睡。治療方式是在夜晚使用連續正壓呼吸輔助器材,而且如果咽喉構造不正常的話,再加上下顎前移止鼾器。打鼾是這種病的特色之一,併發症狀可能導致心臟衰竭與高血壓。">)
邱吉爾的醫生查爾斯.威爾遜觀察到羅斯福的狀況,而且以他豐富的經驗,幾乎不可能看錯那是怎麼回事。二月七日他在日記上寫道:「在一個醫生的眼裡,羅斯福總統像是個病的非常嚴重的人。他有腦部動脈硬化症晚期病人的一切病癥,所以,我推測他最多只能再活幾個月」。
邱:你說用猜的是什麼意思?
我接下來會提到,在這段期間裡政府首長的病歷(他們有的是真的病了,有的是被認為曾生過病)各不相同,醫學上並沒有連貫的線索可以把這些病歷連結起來,我也不嘗試用自創的方式把他們分門別類;讓他們能夠按照年代順序,在各自的時代背景裡被評估,我就很滿意了。這些領導人當中有些是民主人士,有些則是獨裁者或暴君。某種角度看來,這些病歷只是個別病患的簡短醫療紀錄而已。但是以這些病歷資料為基礎,我們和圖書可以得出某些醫學知識,在第八章裡我將試著把這些知識做個總結,並且為未來做出建議。
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繼任者,沃倫.哈定(warren Harding),是一位英俊、看起來非常健康的人,當上總統時才五十五歲。但是實際上好幾年來他已經有心臟方面的問題,還伴隨著呼吸短促的症狀,後來他比失能的威爾遜還早過世。哈定沒有頂尖的形象。他推行的「前廊競選運動」(Front Porch campaign)無甚成效,他本人也缺少鮮明的特色。參議員威廉.麥克阿杜(William MCAdoo)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語言,描述哈定的演說像是「一支由語詞組成的大軍在地平線移動著,找尋一個理念。有時這些散漫的文字部隊還真的找到七零八落的思想,就會像凯旋儀式那樣把它扛起來,作為隊伍中的俘虜,一直到這名俘虜因遭受奴役與過度勞動而死亡為止」。哈定的外表讓人對他的健康與能力產生錯誤的印象。他患上憂鬱症,多年來都有心臟的病症,一九一八年他由於心臟問題而無法在台上完成演說。當上總統後,他從一九二二年開始抱怨胸腔疼痛,而他的血壓上升,看上去也顯得精疲力竭。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哈定死去。他的妻子拒絕做解剖檢查,但是儘管關於他死前的情況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他死於心血管方面的毛病所引起的腦溢血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羅斯福從幼年起就有氣喘與週期性腹瀉的毛病,他的家族稱之為「假性霍亂」(cholera Morbus)。在哈佛的時候一位醫生警告過他,他的心臟機能已經受到他的氣喘以及健美鍛鍊的影響。醫生建議他降低鍛鍊的強度,不然壽命可能減短,但是他拒絕聽從。一八八三年七月,擔任紐約州議員,他有過一次嚴重的氣喘發作併發腹瀉,事後他說那是一場噩夢。一八八四年二月十四日他的母親死於傷寒;十一個小時之後他的妻子愛麗絲.李(Alice Lee)在生下他們第一個孩子後,死於腎衰竭,當時稱為布萊德氏病(Bright's disease)。羅斯福徹底崩潰了。他的日記裡有段黑暗、巨大又痛苦萬分的文字:「我生命中的光消失了。」當時他二十五歲。羅斯福藉由鍛鍊身體的方式尋求逃避,也為了克服那種他稱為「黑色憂慮」的悲傷,他的解釋是,這種黑色憂慮「很少坐在一個騎的夠快的騎士背後」。他在牧場裡度過了一段騎馬與鍛鍊身體的日子,三月底四月初時他的氣喘又發作了兩個星期。然而透過騎馬他獲得了力量;威廉.羅斯可.泰爾(William Roscoe Thayer),一位在哈佛時期就認識他的傳記作家,便預言過:這位令人印象深刻、表彰男性勇氣的奇人「具有如泰坦巨人般的頸子,寬闊的肩膀與鐵打的胸膛」,他的強大的心靈以及同樣強大的身體對他發出了彼此衝突的召喚,終其一生他都將為了調解這樣的衝突而掙扎不已。然而一八八七年九月當他的新任妻子艾笛絲即將臨盆之際,他又經歷一次氣喘的發作。因此,毋庸置疑地,引發他氣喘與腹瀉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焦慮。焦慮是一種情感性精神病,在診斷上可以跟躁鬱症裡的鬱症一樣的嚴重。
在戰爭全程裡邱吉爾的健康狀況都維持的相當不錯。他一直都吃大份量的餐點,抽的雪茄不計其數,飲酒的數量也相當可觀。喝酒似乎從來不曾給邱吉爾造成任何問題,雖然如果晚餐的時間太晚,晚餐之後他又繼續工作到次日清晨的話,則酒精常常使他的注意力鬆散。這時他的思路遊移,他的狀況讓戰時的參謀長們失去耐心。比如國防部的參謀長,陸軍元帥亞蘭.布魯克爵士(Sir Alan Brooke,後來成為亞蘭布魯克勛爵〔Lord Alanbrooke〕)未經刪節的日記裡有一段話說:「這些夜間會議讓我『氣到快死掉』……而且前次會議的臭味還留在我的鼻孔裡還沒散掉!」(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十二年以來這個政府的施政有個困擾,就是它聽不到、看不見也不辦事……他們唯一全體一致的,就是對我的憎恨——而且我歡迎他們的憎恨……我高興聽到人們說在我第一任期內,自私的力量與對權力的慾望遇到了好對手。我高興聽到人們說在我第二任期內,這些力量遇到了它們的主人。
如果希特勒沒有在地下碉堡舉槍自殺,而是被盟軍捕獲、被送到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受審,他應該會得到危害人類罪的判決並且以吊刑處決。就算辯護方主張他精神失常以及心智不健全,出庭作證的醫學專家也不會予以採信。希特勒是一個極端人格,這一點毋庸置疑,跟他出身於功能失常的家庭一樣屬於事實。至於他是否有精神官能症,是不是性變態,或者是否有精神病的傾向——這些主張為真,都不足以在醫學上把他診斷為病患。
興登堡於八月二日逝世,政府立即通過一道法律,宣布總統與總理兩個職位將合而為一,希特勒將成為國家元首以及帝國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這道法律由帕本與布隆柏格以及其他許多人簽署。同一天,德國國防軍全體官兵宣誓效忠,對象不是國家或政府體制,而是德國帝國與人民領袖阿道夫.希特勒。針對這項領袖與帝國總理的職位變更,於八月十九日舉行了一場公民投票,希特勒獲得壓倒性的多數的認可,投票率達百分之九十五點七,其中百分之八十九點九三投下贊成票,也就是總投票人口中百分之八十六點零六贊成希特勒的變革。這支持率如此之高,與興登堡政治遺囑的公布很有關聯——興登堡在遺囑中表達了對希特勒的支持,不過當局沒有公布遺願中興登堡提到他個人希望德國恢復君主體制。即便如此希特勒仍然等了很長的時間,直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才把這項法律付諸實行。這時,在第三帝國最後一次的內閣會議上,他冠上最高統帥的頭雅,此外還授予布隆柏格國防軍統帥的頭銜與職務,並廢除戰爭部長一職。曾經所向無敵的德國國防軍便完全地臣服在希特勒的意志之下,無論是形式上還是實質上。沒有任何因精神疾病而失能的人能夠以如此高超的技巧來行動。
我想我可以宣稱,在過去六個月中,首相用了太陽底下一切的名字來說我,也許唯一還沒用的是「膽小鬼」。但是處在這些語言風暴當中,我非常清楚這些難聽的話準確來說並不表達任何意義,而且,在太陽下山之前,首相又會找我進行一次親近、愉快又友善的談話,來把關係補救一下。
調停者必須處理的是現實,而非「本來可以變成怎樣」。他們試圖解決巨大而困難的問題。民族主義或宗教的非理性激|情要如何抑制,以免產生更多危害?我們怎樣才能防止戰爭?對這些問題,我們現在仍然沒有答案。
提到這些進步,並不是要暗示,疾病及其對政府首腦的影響等等本書所探討的議題,是在一九〇一年忽然間從石頭裡蹦出來的。
在那以後,他對每個人的尊敬越來越少,甚至失去了對國會的尊重。他死於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兩日後在下議院一場極為引人矚目的葬禮演講上,邱吉爾說:「作為一位有行動力、豐富見識跟創造能量的人,在他巔峰的時期裡,再沒有第二人能趕上他。」
邱吉爾也相信英國在中東以及其他地方沒有足夠的地面部隊。對勞合.喬治來說,邱吉爾「腦袋裡有布爾什維克主義」。
麥克當諾是英國第一位工黨首相,在那之前他沒有任何內閣的經驗。那是一九二四年一月的大選,沒有黨派過半,但是工黨獲得最多席次。他擔任這個職務只有九個月之久,然後第二次大選就把鮑德溫送回大位上。麥克當諾在一九二九年第二次當上首相,這次任職到一九三一年。當國民經濟危機發生時,他要命地拒絕了經濟學家凱因斯的建議並且拒絕讓英鎊眨值。經濟危機使得國家必須採取一些艱鉅的經濟措施,但是他的內閣卻扛不起來。麥克當諾在國王喬治五世的施壓之下留在位子上,但是他決定他有義務組一個聯合執政的國民政府。保守黨的貢獻是如此巨大,以至於麥克當諾沒有選擇地成了他們的政治囚犯。
伍德羅.威爾遜
邱吉爾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得了肺炎,當時他正在北非進行拜訪行程。一九四四年三月布魯克的日記上如此記載邱吉爾:「我們覺得他情緒上極端的疲倦,我擔心他會很快地敗下陣來。」真實地寫下日記,布魯克傾吐了他累積的挫折感,也做了過早的判斷。為此布魯克受到了批評。但這些批評是不公平的。日記的重要之處在於——如果是誠實地寫下來的——可以提供我們重要的洞察。布魯克與其他許多戰時日記向我們展示一件事:在重大決策的過程中,疲倦可以成為一個無比關鍵的因素;而在這段期間內,對那些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來說,邱吉爾有時候是多麼地讓人無法忍受。布魯克日記在其他方面也揭露了不少事情。一個精采的例子是:一九四五年三月當邱吉爾訪察英國部隊時,像一個搞笑的男孩一樣,決定要在一次大戰的齊格飛防線上小便。
亨利.甘貝爾-班納曼
首相似乎很喜歡我們的老白蘭地。我在九點半離開餐桌之前,他就喝了好幾杯(那可是大葡萄酒杯!)等我再次看到他時,他顯然又灌下許多杯。這時候他的兩腿已經站不穩,不過他的腦袋還是相當清楚,能夠閱讀地圖,也能跟我討論當前局勢。
史達林的猜疑妄想,可能是源自於他喬治亞共和國的出身。他許多冷酷與殘暴的特質,用「高加索酋長」的形象比較容易解釋,而不像是得自於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在任何正常的民主社會,史達林最後的下場很可能會是在監獄裡。「史達林全無情感的個人磁力,在他生命的每個時期,都會吸引背德者、無節制者以及精神病態者。」他是一九〇七年六月十三日發生在第比利斯(Tbilisi)一樁銀行搶劫案背後的主謀,時年二十九歲。他在蘇維埃共產主義固有的保密氣氛與威權主義裡特別如魚得水;列寧於一九二四年死去之後,他在殘酷無情的鬥爭中爭奪權力,使他的猜忌妄想日漸增長。列寧時代便已開始有系統地謀殺,到了史達林時代獲得了更大力的推動。一九三七年政治局下令實行「紅色恐怖」,各單位有系統地編列配額,逮捕與處決被指認為對蘇維埃領導最有敵意的分子。儘管如此,史達林仍鼓勵各區域的積極分子交出超過配額的成績。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俄國稱之為「偉大的愛國戰爭」,在那期間以及之後,無差別處決都持續進行。戰爭期間的慘酷是巨大的:至少二十萬名紅軍士兵遭到俄國人自己槍決。戰鬥間任何膽怯的表現會當場處決,存活歸來的戰俘也常遭槍殺。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蘇聯在紅場上舉行慶祝戰勝德國的凱旋遊行;在這之前早些時間,史達林發作過一次心臟病,照他女兒的描述,是一次「小中風」。他得到的診斷是動脈硬化症,並且得到了治療。但在那時候,史達林對醫療專業感到厭惡;在「醫生密謀」之後,他讓曾經當過護佐的亞歷山大.波舍克雷比雪夫(Aleksandr Poskrebyshev)擔任非正式的私人醫生,替他管理各種藥片與藥水。他的脾氣越來越壞,猜忌妄想也日漸嚴重。
我親愛的波那爾,
先前在一九四一年八月時,一份心電圖顯示希特勒的冠狀動脈在窄化當中,他顯出衰老的跡象;在這之前除了疑病症與失眠以外,他的健康狀況一直都很好。慢慢地希特勒出現帕金森氏症的症狀,他的左手開始顫抖,演說時變得遲疑——這一點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有紀錄可證。(帕金森氏症是一種與老年相關的退化性疾病,通常在人生命的後半段出現。他的典型病變是基底神經節〔basal ganglia〕——位於腦半球的基底部位,與運動的控制有關——的退化,通常情況下沒有其他的腦部損害。男性發病比女性常見。病症與多巴胺分泌不足有關,病症初期對抑制副交感神經生理作用的藥物如左旋多巴〔levodopa〕反應良好。典型症狀是顫抖與僵硬。顫抖在手或腳靜止時較為明顯,僵硬會使走路變成拖行,使臉部表情喪失變化,以及聲音變得平板。)到了一九四四年時他左腿的顫抖變得非常明顯。後來的許多心電圖顯示他心臟的狀況日漸惡化。
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邱吉爾下榻白宮——他在床上輕微地心臟病發作。日後在一本書裡,威爾遜自豪地講述——而且稍嫌過度自誇了點——他如何為了國家而善盡自己的職責:「在這當口,美國正要介入戰爭,而除了溫斯頓以外,沒有第二人能夠給它提供引導。我感覺到,如果貿然宣布我們的首相心臟病發作,這一定會產生災難性的影響。」十二月二十七日早晨邱吉爾告訴威爾遜,他拉起窗戶時扭傷了胸口一條肌肉。威爾遜很明智地沒讓他明白,他所描述的疼痛——從胸口擴散到手臂——正是心絞痛或者冠狀動脈循環不足的典型症狀。相反地,他讓邱吉爾繼續以為那是拉起窗戶不慎造成的,讓他的身體以自然的方式自己修復這個問題。為了避免驚動任何人,威爾遜故意不找來心電圖的機器。於是邱吉爾在當日早上——躺在床上,還抽著雪茄——就跟喬治.馬歇爾將軍(George Marshall)就軍事指揮權統一的關鍵問題來了一場猛烈的討論。往後幾天裡行程緊密,邱吉爾也都能跟上。十二月二十八日他搭火車前往加拿大,然後返回華盛頓。最後他於一月五日飛往佛羅里達度個假期,在那兒他每天都在海裡游泳;一月十一日他搭火車返回華盛頓。之後,一月十六日,他堅持乘坐水上飛機從百慕達返回英國,在普利茅斯.紹恩德灣(Plymouth Sound)降落。首相出國總共一個多月之久,當中十四天在白宮裡,與美國總統進行過十三次晚餐,與各方幕僚有過八次重要會議。這對任何人都是艱鉅的工作,更不用說是對一位有心絞痛的人而言。
連同他肥胖的毛病,使他成為一個遲緩的人,無法勝任他的工作。於是羅斯福做了一個極不明智的決定,作為第三方,出來與塔虎脫跟民主黨提名人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同台競選。在選戰過程中他遭到槍擊,但是放在胸前口袋裡的鋼製眼鏡盒救了他一命。儘管襯衫染血,子彈固著在他的胸口上,他還是繼續演講,大聲地說:「要殺死一個進步黨黨員(Bull Moose),一顆子彈還不夠!」
當內閣開始討論這個議案時,哈理法克斯背後有強大的支持;他退下首相的位子讓邱吉爾來當,不過是十六天之前的事。他對和談有一個底線,就是和平的條件不能「危及英國的獨立」。哈理法克斯打算在任何談判狀況下都不放棄艦隊或皇家空軍,但是他準備犧牲帝國的某些部分,比如馬爾他、直布羅陀或某些非洲殖民地,「好讓國家免於一場可以避免的災難」。作為外交大臣,他的職責是尋找和平的適當時機,但是他的外交技巧並沒有被政治現實粹鍊過,和平的時機根本不存在。
正當勞合.喬治在販賣官職、擺佈朋友與敵人、縱橫於世界舞台上的時候,復仇女神找上門了,在一場著名的保守黨國會議員會談中——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九日於保守黨總部(Carlton club)——他失勢了,並被迫於當天辭去首相的職務。如果他能認識並接受政治現實的話,事情本來可以完全不是這樣。早在一九二〇年六月下旬的時候,在邱吉爾與查爾斯.馬科迪(Charles McCurdy)的支持之下,他向國會介紹自由黨在政府裡任職的同事,並提出一個計畫,讓聯合內閣的自由與保守兩黨結合起來。當時勞合.喬治正處於政治聲望的顛峰,但是多少有點意外地,這個計畫沒能成功。在那之後他就成為一位沒有政黨的英國首相。當時他本來應該辭去首相一職,改為接受保守黨領袖的領導,或者也可以退居後座議員(backbench)。勞合.喬治遺憾他的自由黨同僚拒絕合併,但是他那對保守黨從來沒有好感的太太,對此卻感到十分高興,與她的先生形成了有趣的對比。
赫伯特.阿斯奎斯
關於希特勒心智的健康狀況學者們進行過冗長的爭論。一九四三年時,中情局的前身策略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tudies),曾經兩度委任專家做過希特勒的心理檔案。第一份是由哈佛大學的人格心理學專家亨利.莫瑞(Henry Muray)博士撰寫,但是直到二〇〇五年才公諸於世;第二份是由頗有聲望的精神分析專家瓦爾特.朗格(Walter Langer)博士完成,但是這份報告也是機密文件,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晚期才被解密,並被移交給美國國家檔案館。一本於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專書即以這份檔案為基礎。
對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如實描述,解釋了很多東西。這些被凸顯出來的議題,將成為本書反覆出現的主題,那就是:大多數政府首腦都有超乎常人、甚至不正常的人格型態。他們面對巨大壓力的辦法,就是把部分壓力轉嫁到他們圈子內部的人身上,無論是同僚或者顧問。而且,他們所展現的力量,常常是他們與疾病對抗的副產品。
二十世紀也是一個醫療技術取得巨大進展的時期。羅納德.羅斯(Ronald Ross)與阿方斯.拉豐朗(Alphonse Laveran)這兩位科學家幫助科學界證明瘧疾(當時世界上危害最大的傳染病)是經蚊子傳染的,為此分別在一九〇二與一九〇七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當邱吉爾一九四三年因為肺炎,醫生開盤尼西林給他服用時,這種藥才剛開始生產不久。醫學診斷在整個世紀裡不斷地進步,微生物技術、血液化學、X光、心電圖與超音波等,使醫學診斷不斷翻新。較晚近的突破,是來自分子生物學與DNA的發現,以及核磁共振成像(MRI)與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PET)掃描等技術所提供的知識。可供採用的療法與用藥的選擇範圍非常大,政治領袖的健康問題有了根本的政變,疾病對決策的影響便也跟著不一樣了。人們活的比以前久,可工作的年歲也變長了。
關於歐洲戰場該如何落幕的大戰略在雅爾達會議就已經決定了。馬歇爾認可這個戰略,布魯克也盡力執行,數量龐大的紅軍此刻正在波蘭與東普魯士展開,其前鋒距離柏林只有四十哩,面對這個嚴酷的事實,邱吉爾與羅斯福也找不到理由來反對。
在邱吉爾生病的所有期間裡,默蘭相都當稱職地把病人的最高利益當作最優先的考量。一九四一年時他對邱吉爾心臟病所做的處置,是對病人最好的作法,也是國家的最大利益。但在一九五三年,他所做判斷對國家是否也同樣最好,就不那麼顯而易見。默蘭提到他在七月六日測試邱吉爾的記憶力,這是腦溢血後的第十四日。他讓邱吉爾背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的詩《西西里的羅伯特國王》(King Robert of Sicily),並對著書本檢查。詩有三百五十字,只有六個字記錯了。然而這不是測試大腦是否還能應付新資訊的最好方式。默蘭引述了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他與邱吉爾的對話,這是首相離開唐寧街之前兩天:
在第一次大戰裡非常嚴苛的時刻,勞合.喬治爬升到政府首腦的位置,大眾輿論感到歡欣鼓舞。德國的潛水艇開始威脅到民船的航運以及英國最要緊的補給航線。戰爭的勝利似乎遙不可及,戰敗的結局卻十分可能。這是個烏雲罩頂的局面,阿斯奎斯的支持者中沒有人願意為勞合.喬治的內閣效力,多數的保守黨人對言詞便給、反應靈活的新首相的穩定性(以及其他許多方面)懷抱疑慮。一九四〇年邱吉爾也是聯合執政內閣,但是不一樣的是,邱吉爾自己是保守黨的一員,他享有黨內國會議員的多數支持,而勞合.喬治的聯合政府得倚賴保守黨國會議員的支持,因為他自己所屬的自由黨,其國會議員中支持他的連一半都不到,愛爾蘭國民黨(Irish National Party)議員支持他的更少。然而勞合.喬治嘗試把這個弱勢轉變成對自己有利:他創立了保守黨議員所希望的東西:一個小單位,一個由五名成員組成的戰時內閣。勞合.喬治在裡面是唯一的自由黨人。另外四人分別是保守黨黨魁安卓.波那爾.拉奧(Andrew Bonar Law),擔任財政大臣與議會議長;工黨領袖亞瑟.漢德森(Arthur Henderson),原本就在內閣裡;以及兩位保守黨的上議院議員,庫爾叢伯爵(Earl George Curzon)與麥訥爾子爵(Viscount Alfred Milner),他們都擔任過殖民地總督,是經驗豐富的帝國管理者,因此被找進來擔任不管部部長(Ministers without Portfolio)。實際上在這種人事組合裡,首相相當自我克制。這個組合之所以能夠運作,是因為勞合.喬治每天在早餐之後,就會走室內通道從唐寧街十號走到十一號,花一個小時跟拉奧一起商討當天該做的事項,也提出他富有想像力的構想,請拉奧以實際與具批判的眼光檢視一番。以這樣的方式,這位可能是世紀最為膽大妄為的英國首相把他充滿魅力與創造力的性格收斂了起來。他接下來兩年的成功,最大的助力是來自這個內閣的組成結構。勞合.喬治的傳記作者約翰.格利格(John Grigg)寫道,他之所以能夠領導這個戰時內閣,「靠的不是首相一職所賦予他的權力,而是靠他的才幹與人格所顯現出來的力量」;而且雖然他是個大膽、正面思考與有決斷力的人,卻沒有獨斷的毛病,「經由調解給其他人極大的尊重,喜歡與人並肩共事」。勞合.喬治兩次重要的調解:一九一六年強力說服海軍部成立護航艦隊;一九一八年堅持從英國新派部隊,以回應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的攻擊行動,並說服美國人同意派兵。
伍德羅.威爾遜在一九一三年成為美國總統之前的許多年,一直患有高血壓;從一八八九年起就有過多次突發神經疾病,可能是由於血管組織方面的問題所引起的。(一個正常人的血壓,收縮壓約在一百二十釐米水銀柱,舒張壓則在八十釐米水銀柱,可表達為一二〇/八〇,收縮指的是心搏週期裡心臟收縮的期間。它通常指的是心室的收縮,持續的時間為零點三秒。舒張壓比較低,因為心室在放鬆當中,並且讓血液重新流入。)
當邱吉爾最後以八十高齡離開職務時,他的女兒瑪莉.索姆斯說,這是她父親的「第一個死亡」,顯見他非常的在意。他的辭職是一拖再拖,而他的繼任者安東尼.艾登爵士已經掩不住遲遲不能就任首相的不耐煩。像要揭發什麼一樣,邱吉爾在離開唐寧街前的最後一個晚上,對他的私人祕書用略帶激憤的口氣說:「我不相信安東尼做的來。」這話讓他說中了。
戰爭期間他憑藉絕妙的謀略與計策拯救英國,他的才智勝過眾位將領、政治人物、上議院貴族、大主教國王與其他人。他現在大膽又技巧地用其才智來挽救自己,免於被下議院議員擊敗。他信心十足,認為自己從前的成就,現在也能再次辦到。為了保住權力的位子,保住施惠恩主的角色,他願意挺身信奉帝國思想,擔任那些人的領袖;或者表現像是開明的宣道者,支持自由貿易與歐洲和平;或者作為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的粉碎者,主張對土耳其與法國宣戰;或者作為英國勞工階級的護民官,為他們擔任崇高的說項人;或者為保守黨的大地主當鬥士來對抗工黨;或者成為愛爾蘭堅決的敵人;或者成為愛爾蘭溫柔的朋友,在鎮壓者的鐵蹄下,伸出保護的羽翼到另外一塊塞爾提克族的土地。這些是勞合.喬治在那悲劇性的一九二一與一九二二年裡先後採取過的政治立場,有時候他甚至在同一時間內採取自相矛盾的主張。他什麼都敢衝,看上去令人驚嘆。但是對那些一直記得他在巔峰時期偉大身影的人來說,這些鬧劇越來越顯無趣,而且不久就形同慘劇。
威爾遜本來毫無疑問地應該於一九一九年下台,或者至少暫時解除職務,以確定他是否能夠恢復健康。他沒能做到這一點,其實這會產生後續政治效應。比如說——如果威爾遜下台了,職務由副總統湯馬士.馬歇爾(Thomas Marshall)接手擔任,他也許可以說服國會正式批准創建國際聯盟的條約。當時所需要做的事,是協助國聯問題爭論中的兩位核心人物達成共識,反對國聯的是參議員亨利.卡博特.羅哲(Henry Cabot Lodge),支持國聯的是參議員吉爾博特.希區考克(Gilbert M. Hitchcock)。如果當時雙方能妥協,那麼國美國就可以在國際聯盟擔任領導角色,使其成為更為有影響力的組織,也就有可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
在為自己進行一些遊說之後,他於一八八七年四月十九日被任命為美國海軍助理次長(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Navy)和*圖*書。他很快就闖出了名聲,幾乎為海軍完成了作戰準備。整整一年之後美國國會表決通過支持古巴獨立,次日麥金萊總統簽署國會決議,決議中做出承諾:一旦解放完成,就把政府組織與統治權力留給古巴人民。四月二十三日,總統號召十二萬五千人志願從軍,因為正規軍的兵力當時只有二萬八千人。幾天之內,羅斯福的由拓荒者組成的義勇騎兵團(Rough Riders)就成軍了,而這位「牙齒多」(Teethadore)——當時紐約時報這麼稱呼他,因為他的門牙向前突出——也就此踏上了成為美國知名度最高的人的旅程。在這場美西戰爭裡,一八八年七月一日的聖黃安山(San Juan Hill)戰役中,羅斯福領導他的部下在騎兵團攻擊中取得勝利時,他的身分是泰迪.羅斯福上校。之後他以旋風之勢當上了紐約州州長,接著又被提名為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邱吉爾的私人醫生默蘭勛爵(即查爾斯.威爾遜爵士),宣稱從一九五一年起,他的主要職責就是讓邱吉爾能夠以首相身分繼續工作。邱吉爾在一九四九年裡有過兩次腦溢血。後來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三曰又來一次,這次非常嚴重。邱吉爾的私人祕書約翰.柯爾維爾(John Colville)被告知,首相可能週末就會過世。邱吉爾當時說話還沒有困難;他給柯爾維爾下了嚴格的指示,不能讓外界知道他已經失能。默蘭與神經科醫師羅素.布萊恩(Russell Brain)起草了一份病情報告,裡面有提到「腦部血液循環障礙」的字句,但在與兩名保守黨大老,拉博.巴特勒(Rab Butler)與沙里斯布里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討論過後被刪掉了。柯爾維爾還詢問了邱吉爾三位新聞界朋友的意見,分別是約翰.貝瑞(John Berry,後來成為康羅斯子爵〔Viscount Camrose〕),比佛布魯克勛爵(柯爾維爾以舊名馬克思稱呼他),以及布拉肯子爵(Viscount Bracken);他們一起約定嚴守祕密,並且說服了他們在艦隊街(Fleet Street,倫敦著明街道,傳統上英國媒體總部都在此處,現多已搬離)的同事門隻字別提邱吉爾的病情有多嚴重。不過,邱吉爾活下來了,雖然他有幾個星期之久無法正常視事。邱吉爾的女婿克里斯多福.索姆斯(Christopher Soames),一位保守黨下議院議員,代替首相行事甚至多次偽冒他的簽名。反倒是邱吉爾自己在一年之後在下議院裡不經意地才說出他曾經有過一次「中風」。
三叉戟會議(Trident)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於華盛頓召開。聯合參謀長團一共進行了十五次會議,此外還有六次在白宮與邱吉爾與羅斯福進行全員會議。羅伯茲的結論是,從珍珠港事變到三叉戟會議這段期間,羅斯福、邱吉爾與布魯克都各行其是,但是從三叉戟會議之後,羅斯福與馬歇爾「就佔據了支配決策的地位」。他著確信如此論述:
鮑德溫多年來都沒有得過任何嚴重的疾病,偶爾有人會說他是英國首相當中唯一下台時是完全出於自願的。我認為這並不符合真相。他的聽力逐漸退化,幾近耳聾,某些靠近他的人士認為他之所以願意下台並把權位交給納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這是一個主要原因。一九三六年張伯倫時任財政大臣:
希特勒在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短暫曝露在芥子氣中,有一段時間他似乎變得目盲也不能說話。朗格報告集中討論了這一事件。藉由其他類似案例的引申,朗格推測這可能是童年的精神創傷所造成的,希特勒小時候可能撞見過雙親的性|交過程,不過朗格無法提出任何特定事件的紀錄或者事實根據,來證明希特勒小時候真有發生這件事。但是無論如何,在較新的討論裡,哥倫比亞大學精神科學者麥可.史東(Michael Stone)寫道:「希特勒幼年時期曾撞見父母親性行為,當時的學界把這種經驗視為造成心理混亂的重要來源。但這種說法沒有討論價值了,因為心理混亂的因果關係這個理論本身,已經被認為不可信。」他認為,過去五十年裡討論希特勒心理健康的滔滔不絕的論文,當中絕大部分都只是精神囈語而已。
一件比較能為張伯倫辯護的事實是,到了一九三九年他對希特勒的看法轉趨實際,也試著爭取時間讓軍備重整計畫能順利推進,因為他知道英國必須作戰了。不過即便如此,讓新的也較適任的首相入主唐寧街十號,在一九三九年關鍵的那幾個月裡,可能會使局面很不一樣,有可能阻止希特勒擴張領土。但是在那個階段,如果真的要把張伯倫換下來的話,新任人選可能不會是邱吉爾,而幾乎一定會是哈理法克斯勳爵(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 Lord Halifax)。雖然他聰明過人也深具愛國情操——他的外號叫作「聖狐」(Holy Fox)——但是他並沒有完全認清,在一九四〇年敦克爾克大撤退以及法國淪陷以後,英國還必須竭力度過許多危難,才能打敗希特勒。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這一天公告了大選將在一個月後舉行,十二月二十八曰聖誕節之後才開票。聯合內閣打算繼續留在原職位上,推出勞合.喬治與波那爾.拉奧共同來打這場選戰。婦女在這次選舉中首度可以投票,聯合政府在下議院的七百零七席中贏得了四百七十三席。
世界經濟大蕭條於一九二九年從美國開始,紐約證券市場突然崩潰,德國也受到嚴重的打擊,一九三一年時特別嚴重。在這段經濟艱困的時期裡,盟國仍然愚蠢地堅持德國應該繳付戰敗國賠款,讓希特勒看到這當中的政治機會。他的每一步都以非常高明的技巧來利用這個局勢。艾倫.卜洛克(Alan Bullock)在他一本希特勒傳記中寫道:「一九三〇年時,德國民意間有一大塊是彌漫著怨恨的情緒。希特勒呢,他本人的性格就貯存了幾乎取之不盡的怨恨,因此他給怨恨的民眾找出一系列的標的,讓他們為自身不幸的遭遇傾洩心中的不平。」這些標的的名單很長,主要集中在聯軍身上(特別是法國),還有戰敗賠款、積弱的威瑪共和、炒作金融的商人、大企業、共產黨人,以及——最重要地——猶太人。德國境內彌漫著對凡爾賽條約的憎恨,由於條約的限制,三百萬德國人仍然居住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與奧地利,同時奧地利無法與德國統一。
極其特別地,在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生病的時候,在法國也發生著非常相像的情況。法國總統保羅.德沙內爾(Paul Deschanel)的太太替她的先生簽署官方文件,因為她先生的行為變得非常怪異。德沙內爾是他時代裡最出色的文人以及政治家之一,年輕時就被選入法蘭西學院。他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七日被選為法國總統,國會議員全體八百八十八票以佔絕大多數的七百三十四票支持他。然而在他獲選之後,關於他誇張行為的謠言就開始流傳。例如,有一次他當眾狂熱地親吻一位參加過一次大戰士兵的嘴,而那位士兵的臉有著嚴重的傷殘,把群眾嚇了一跳。然後,在五月二十三曰晚間,德沙內爾在從巴黎出發的行程中從他的總統專屬火車消失。他可能是從打開的火車窗戶跌了出來,這樣可以解釋他為何腳上受了輕傷,或者他可能在火車故障問題停靠時走下了火車。他最後是穿著睡衣,臉上有血,到了在平交道附近平交道看守人的家裡。他聲稱他是法國總統,剛才從火車上掉了下來,收容他的人只是好笑,並不相信,直到一位被召來的醫生認出他的身分。德沙內爾表面的說詞是:「我的記憶有一道完整的缺口,從打開我的車廂門一直到在這裡醒來,中間的事情我全不記得。」有人主張德沙內爾所患的是艾爾比諾症候群(Elpenor syndrome),主訴是「一種意識半醒的狀態,伴隨空間迷向以及半自主地行走。發生此症狀之前,患者會飲酒過量或者服用過量安眠藥,接著在不尋常或不習慣的地方入睡,不久就『醒來』進入這種症狀。這種狀態會導致跌倒或者行為不端」。據稱德沙內爾當時服用了五十公毫的安眠藥甲基索佛拿(Trional)。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史達林批准逮捕猶太醫生雅可夫.艾廷格(Yakov Etinger)教授。這是一連串逮捕行動的第一個,整件事情後來成為所謂的「醫生密謀」事件。艾廷格的電話遭到監聽——他在電話中對史達林的批評被錄了下來。他死於刑求偵訊之中。一九五一年二月史達林下令逮捕更多醫生,而在那時候,他的高血壓與動脈硬化造成他數次輕微的中風。他的老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成了敵人,而這個所謂的「密謀」變成了打擊貝利亞跟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的工具。「細節上聽起來也許很荒謬,但是『醫生密謀』在史達林的眾多妄想中堪稱經典,而且跟萬靈藥一樣有副作用,能救命也會致命。」副作用之一就是,當史達林發生那次致命的中風,圍在他身邊的資深政治局成員非常害怕,足足等了十二個小時之久才叫醫生過來救治。
究竟上列這些陳述——「瘋狂的雀躍狀態」、「不是處在浪峰上,就是在波谷底」、「在他的性格組成裡,沒有折衷這回事」以及「展現出爆衝的能量與光彩四射的演出」與「倦怠與憂鬱」的並存——是否提供了足夠的躁鬱症證據,將是精神醫學專家會討論的題目。但是如果邱吉爾真的罹患躁鬱症,也並沒有證據指出這疾病導致戰爭內閣做出非理性的決策。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疾病給了他一種激勵人心的特質來領導國家;這在一九四〇年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
在二戰期間,或甚至可說是整個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政治領袖,是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但是羅斯福的政治生涯對本書特別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政府頂層職位上的全部時間——四年任紐約州州長,十二年擔任美國總統——都是在輪椅上度過的;他在年輕的時候,在三十九歲上,感染到了小兒麻痺。他的兩腿從臀部以下全部癱瘓。當他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擊敗赫爾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此時已經罹患憂鬱症)當選總統時,已經習慣於向大眾隱藏他雙腿的狀況。作為總統,在重要的場合,他努力傳達一種他可以站起來的印象;他甚至設想出一種辦法讓他可以走上幾步,以便向外界暗示只要一點小小的協助他就能夠走路,協助的人通常是他的兒子,或者他的護衛。羅斯福所有這些措施都是合理的行為,因為他並不覺得自己失能,也決心不要以殘障的形象出現在大眾前。羅斯福實質上從來不曾在輪椅上拍過照片。在羅斯福總統紀念館裡三萬五千張他的照片裡,只有兩張他是坐在輪椅上的。
一九三二年年底,興登堡受到工業界與銀行界大老的壓力,他們希望希特勒能擔任總理。興登堡的兒子奧斯卡與希特勒會面,希特勒爭取到他的支持。然後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前總理法蘭茲.馮.帕本(Franz von Papen)與希特勒會面,兩人達成一項協定,帕本並且讓興登堡相信應該支持此一協定:讓希特勒當總理,帕本任副總理,布隆柏格將軍(Werner von Blomberg)當國防部長。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星期一,興登堡邀請希特勒出面組成新政府。希特勒的盤算十分精明,新政府裡他只安排了三個納粹黨的部長。之後,帝國議會解散,重新舉辦大選,這時納粹的衝鋒隊以前所未有的排場走上街頭。共產黨分裂了社會民主黨的票倉,納粹黨贏得總投票裡百分之四十三點九的支持,這使他們在帝國議會中取得勉強多數席次。之後共產黨議員被剝奪公權,一項授予希特勒不受制衡的政治大權的授權法案,因而得到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數的同意。
雖然勞合.喬治下台的話就沒辦法讓自由黨內部的分裂在下次大選之前癒合,但是下台仍然是他原本比較好的選擇;他可以在阿斯奎斯一九二八年過世後找個機會回來當首相,屆時他至少領導下議院中單一最大的政黨。然而他沒有這樣做,而是以首相的身分奮戰下去;掌握權力的慾望把他整個攫住了,他不備讓他自己從棚力的羅網中解脫出來。他這麼做,招來了保守黨的史丹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與工黨的蘭姆塞.麥克當謀(Ramsay MacDonald)的敵意,他們準備政治合作,不管付出任何代價,只要能讓勞合.喬治不再掌握大權。
他完成了戰爭任務,領導他的國家與前所未有的可怕敵人作戰。偉大的艦隊與浩蕩的部隊隨他的命令前進。最極端的危險不能使他氣餒,他的思考總是富饒著靈感與素材。他不只降服了國外的敵人,也令國內的敵人稱臣。他必須與不服從的同事、冥頑不靈的海軍將領、不可靠的陸軍將帥爭執,而這些人不只準備在他背後密謀反對他,甚至打算將國王本人牽扯進他們的詭計裡。他放眼向風暴看去,並且毫不動搖。
一九四五年時,英國不但債台高築,也因為兩次世界大戰而疲憊不堪。選民對邱吉爾的健康沒有多少疑慮,但是對他能否在住房與就業等議題上實現競選承諾則相當懷疑。不過英國在對日戰爭結束之前就選出工黨政府,這還是出乎各國意料之外。新政府的領導者是缺乏領袖魅力但有決斷力的克理門特.阿特烈。英國選民已經看到阿特烈在戰時聯合內閣裡擔任首相副手時表現良好;他們是為未來而投票,認為工黨比保守黨更能夠解決和平時期的問題。當時波茨坦會議才進行到一半,邱吉爾就由阿特烈替換下這更加深了史達林根深蒂固的信念:如果選舉的結果不能事先確保就允許進行,就太危險了。蘇維埃帝國裡也舉行選舉,但在高層操弄之下結果總是壓倒性勝利。
一個有痛風的老政治家,
你問他這戰爭為了什麼,
他就書面回答你說:
我所有同事跟我本人
正在竭盡所能找尋答案。
你問他這戰爭為了什麼,
他就書面回答你說:
我所有同事跟我本人
正在竭盡所能找尋答案。
我們所有人在性格組合裡都有許多人格特點,無論是偏執、衝動、憂鬱、戲劇化或者猜疑妄想。但是只有當其中任何一種或多種佔據了主要地位,而且還頻繁地表現出來,這個人的行為才算是成為異常,像史達林的例子一樣。而且猜疑妄想本身並不構成疾病。只有當伴隨其他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或狂躁症,或者當這猜疑妄想變得嚴重,損害到病人的其他能力,這時才算是病理症狀。在極端的例子裡,猜疑妄想本身就是一種重症精神病。猜疑妄想作為人格特質的一種,不必然會使人失能。在史達林的例子裡,他猜疑妄想症狀並未滲透到思考、精神生活或決策能力等其他面向。然而無處不在的猜忌、經久不消的不信任,是史達林終其一生所擁有的關鍵特質。如果他能控制與收斂這項特質,他可能會是一個更好的領導人;但也有人主張,是他的猜疑妄想才使他得以存活。
我非常反對羅斯福的霸權領導、主戰心態以及軍國主義;反對他全面漠視法律與獨斷性格,他對國會的輕蔑,以及他浮濫地訴諸法庭。我很遺憾他會如此生氣,但是我們的《世界報》會繼續批判他,絲毫不畏懼,就算他強迫我到監獄裡編輯我的報紙也一樣。
一九三八年從事前準備一直到前往慕尼黑會見希特勒的這段期間,張伯倫並沒有找霍爾德勛爵(波那爾.拉奧與張伯倫兩人的醫生)看病的紀錄,也沒有其他跡象顯示張伯倫在這期間內有任何嚴重的疾病。即便一九三九年九月張伯倫對德國宣戰之後的幾個月裡,看起來也沒有任何病狀。他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辭去首相,表面看來健康並非原因之一。但是在這之後很快地,在七月二十日,張伯倫被診斷出罹患癌症末期,x光照片顯示他的腸道有部分窄化。在邱古爾的堅持之下,他仍然留在戰時內閣裡。但是他的病變得很嚴重,一次探查性的手術顯示出他的癌已經無法手術也無從治療。同年十月三日,他辭去內閣職務,十一月九日就過世了。
為了向眾人否認身體出問題,同時也為了展示誰才是大局的掌控者,威爾遜暴躁地撤換了國務卿藍新。威爾遜非常不滿,在他缺席的情況下,內閣會議未經他的批准而自行召開。在此期間,威爾遜的夫人艾笛絲開始著手處理他的工作。一連好幾個月,艾迪絲跟醫生製造出總統仍然在處理事情的假象,她後來因此還被稱為美國的第一位女總統。威爾遜這時候已經不再考慮辭職的事情了。事實上在一九二〇年夏天裡他思考的是出馬競選第三任總統。有人將一些誤導真相的訊息與照片送去給位在舊金山的民主黨黨代表那裡去,希望影響黨代表的投票。所幸他們對同黨總統的支持只是情感上的,在政治卻沒有支持他,而是選出了俄亥俄州州長詹姆士.考克斯(James M. Cox)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為副總統候選人。這兩位民主黨的候選人意外地被共和黨的候選人華倫.哈爾丁(Warren Harding)徹底擊敗。威爾遜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主持了最後一次內閣會議,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三日過世。
另外一個用以解釋希特勒人格與決策的推想來源,是他的單睪症——他只有一顆睪丸。這件事情流傳很廣,甚至是二戰期間一首嘲諷歌曲的主題,戰後也還有人唱。蘇維埃部隊取得他燒毀的屍體進行解剖時,證實了這一點。單睪症跟隱單症的區別在於,單睪症只有一顆睪丸,隱睪症則是睪丸沒有從腹腔降入陰囊。希特勒並沒有任何睪丸激素分泌不足的問題。他的私人醫生,提奧多.莫瑞爾(Theodor Morell),在他生命晚期給他的處方是含有公牛睪丸成分的葡萄糖注射液,但這治療的目的並非替代缺失的睪丸。莫瑞爾開立的藥方組合非常古怪:大劑量的中樞神經興奮劑,甲基安非他命,咖啡因,古柯鹼,巨量的柯斯特醫生抗毒氣藥丸——內含小劑量的番木鼇鹼(strychnine)與顛茄鹼(atropine)毒素。這個藥物組合或許讓希特勒變得比無藥物狀態更為緊繃,但是這是在戰爭大勢已去之後才服用的。他的決策能力可能受這藥物的損害,但是這時戰敗已經無可迴避,他所做的決定也比較不重要。
審視勞合.喬治垮台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他所犯罪行為的過錯與失誤,都是來自狂妄的行動。首先,他為世界舞台完全著迷了。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簽下凡爾賽合約之後——簽約之前他已經在巴黎協商了好幾個月——他繼續參加合約相關是的各項特殊會議,過度耗費時間為種種困難的議題敲定決策。在一九一九與一九二二年之間他參與了這類的會議不下三十三次。幽默嘲諷雜誌《潘趣》(Punch)曾用漫畫把他參加會議的這個習慣一語道盡。第二,他漸漸相信自己是無法取代的。
雖然就健康狀況來說,羅斯福不應該於一九四四年再度參選,但是就算換一個新總統來,美國在這短短幾個月裡——從羅斯福的就職典禮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到他逝世的四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三歲——的實際作戰行動也很難說會有太大的改變。在歐洲,從一九四四年年初開始,馬歇爾將軍與其他美國的參謀長,以及由馬歇爾指定擔任盟軍最高統帥的德維特.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將軍等人就已經負責做出關鍵的軍事決策。實際上掌控攻擊發起日(D-Day)及其事前準備與後續發展的人是馬歇爾——重要的事情已經過羅斯福的同意。在一九四五年初期,馬歇爾與美國軍方毫無意願跟蘇維埃軍隊競爭趕赴柏林。當時,在三月中,艾森豪將此立場以電報告知蘇維埃部隊統帥史達林,保證在他指揮下盟軍將不會試著奪取柏林。英國陸軍元帥亞蘭,布魯克在日記裡透露當時的反應,他對英國的參謀長們說,艾森豪不應該直接跟史達林連絡,應該要透過盟軍聯合參謀本部轉達,「那封電報隱含的訊息完全脫離假定,所有先前的協議似乎將有變數」。部分看來,美國人此舉是想要減少盟軍士兵的傷亡,因為他們判斷希特勒會堅持戰鬥至最後一人,而且史達林已經準備不計任何代價拿下柏林;這想法本身是值得稱讚的。不過即便如此,艾森豪直接與史達林通電,不事先諮詢倫敦方面的軍事與政治當局,仍是令人訝異的事情。也許他之所以不事先諮詢,是因為他已經知道羅斯福與邱吉爾在這問題上看法相左。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檀香一場兩個半小時之久的會議上,正式批准羅斯福與馬歇爾先前在華盛頓商定的重大決策。羅斯福堅持要參加這個會議,即便他必須耗費幾個禮拜的緩慢旅程才能抵達。
二十世紀中葉歐洲獨裁者的罪孽如此深重,以至於許多人會輕易地認定犯行者一定多多少少都瘋了。但事實上,這些罪犯裡最無足輕重的一個,義大利獨裁者——領袖(II Duce)——班尼多.墨索里尼才算是患了嚴重的精神疾病。一九二五年時他的健康曾崩潰一次,咳出血來X光照片顯示他有嚴重的十二指腸潰瘍。從那以後,潰瘍造成的疼痛就沒有消失過。他越來越失去安全感;最後則喪失了現實感。他可能得了重症躁鬱症。
二〇〇六年,三位美國頂尖的精神科醫師發表一篇論文,宣稱羅斯福在總統任內極可能患有躁鬱症第一型(bipolar-I disorder),有些人對此感到驚訝。不過這些醫師的結論是,他的症狀並沒有干擾到他執行總統職務時的效率跟表現。曾經有人認為,羅斯福是住過白宮的總統裡最快樂的一位,其他人則相信他已有幻覺而且心神喪失。一九〇八年羅斯福給國會寫了一份特別的訊息,內容大膽且引發爭議,而且把自己劃為與進步左派同一陣線。《紐約時報》的報導稱他有幻覺的傾向,特別是羅斯福相信有人在密謀推翻他。《紐約太陽報》則稱這是一個「用意浮誇的低級表演」,他最好看看心理醫生。
邱:撐過兩次中風還不死的人,多不多?
後來,默蘭失去了邱吉爾家人的敬重,特別是他的夫人克莉曼(Clementine Churchill)。她在一九六四年七月時聽到他正在寫一本關於她先生疾病的書,就給他去了一封措詞憤怒的信:「我一直以為一位醫生跟他病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要完全守密的……我看不出來你如何能合理解釋你現在所做的事。」(默蘭好一段時間都沒有回信。然後在一九六六年,邱吉爾過世後一年,當他正為書的出版準備時,他寫信給邱士爾夫人,詢問是否可以允許他在書裡使用一張照片。她回信說:「我非常遺憾你打算寫書談邱吉爾。」這次默蘭立刻就回信了,信中援引了著名歷史學家屈維林〔G. M. Trevelyan〕對於醫病關係的看法;屈維林認為,一切事情到最後都會為人所知,也認可並鼓勵他出這本書。陸軍元帥伊揚.史莫茨〔Ian Smuts〕以及布拉肯勛爵也同樣表示支持。邱士爾夫人讀過默蘭的書後〔書於一九六六年出版〕,對女兒瑪莉.索姆斯〔Mary Soames〕說:「這本書看待邱吉爾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索姆斯用一句簡單的話總結了家族對此事的看法:「不論是王子還是窮人,首相或者農夫,每個人都應該能夠在完全信賴他的神父、律師與醫生下安息。」)
分析張伯倫在慕尼黑時的心智狀態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當時他已精疲力竭,他飄飄然回到赫斯頓機場(Heston Airport),史無前例地與國王一同在白金漢宮的露台上露面。次日,他對妹妹承認「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比現在更接近精神崩潰」。他的心情是雀躍的,看起來成功地化解了人民對戰爭爆發的擔憂。在整個過程裡他跟內閣裡的一個小內閣一起行動,邊緣化他的對手。今天為張伯倫辯護的人主張,他為英國的軍備重整爭取了時間。然而這並非他的目標。他應該知道希特勒的承諾不可信賴與他的邪惡野心,他只是在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