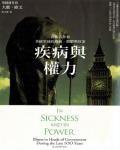第二章 一九五三至二〇〇七年
這個春天我有嚴重的消化不良,三月二十一日我終於倒在床上。到了週末我覺得舒服了,可以旅行,而且杜魯門總統邀請我去使用他在基偉斯特島(Key West)上的別館。我跟史耐德將軍一起南下,在那兒停留到四月十二日。當天他帶我到奧古思塔國家高爾夫俱樂部(Augusta National Golf Club)去,我在那邊一直住到五月十二日。
「我們一定會進行確認的。」發言人回答。
最後一位在一九〇一到二〇〇七年期間患有重病的國家領袖,就是以色列的總理艾里爾.夏隆(I Sharon)。在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七十七歲的夏隆在他的辦公室裡發生過腦血管病變,造成輕微的神智不清,但並未使他喪失意識。就政治來說,這場病發生在一個關鍵的時刻上,因為這正是夏隆離開以色列聯合黨(Likud),創建新政黨以色列前進黨(Kadima)的期間;他打算代表前進黨參加將於二〇〇六年年初舉辦的大選。夏隆體認到,不恰當的保密只會使國內的焦慮感更難平撫,所以當他在接受醫療檢查時,就釋放了一些相關的醫療訊息。這是他第一次對外承認中風。
後來一九八一年時,希思被診斷患有甲狀腺機能減退症;當時他是一位出色的下議院後座議員。醫生給予他甲狀腺素的處方,也許是因為這個處方,他心臟的動脈開始纖維化,並因此發作了被醫生稱為「興奮有力」的心臟衰竭。希思對甲狀腺替代治療有不錯的反應。從他一九七四年不再當首相之後,報紙上就有過一些評論,說他出席下議院院會時常常睡著。到了一九八一年時,以他的甲狀腺功能低下的程度——如他的醫生所確信——他的政治敏銳度已經無法不受損害。沒能解決疑問是,那希思受此病症影響已經多久了呢?不過若要主張希思在甲狀腺機能減退症正式被診斷出來的六年之前,他的病症就已經嚴重到足以損害他認知能力的地步,是完全不可信的。在這個領域中,「佛拉明翰心臟研究計畫」(Framingham Heart Study )所提供的資和是最好的;這個研究的目標是在確認麻薩諸塞州佛拉明翰市住民的心血管疾病風險因素,受測試者後來若被發現患有臨床程度的甲狀腺機能減退症,研究者就會對他們先前提供的血液樣本進行回溯式分析。不過,甲狀腺機能減退症這種不動聲色的疾病帶給我們最主要的教訓是:對位居決策核心的人士來說,一個獨立的醫療評估是很重要的,因為這種疾病常能夠在很長期間裡躲過他們私人醫生的注意。
——愛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
雷根罹患阿茲海默症之事一旦清楚之後,他與夫人南茜決定優雅地,帶著尊嚴地面對這個處境。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五日,雷根親筆寫了一封令人動容的公開信給「我親愛的美國同胞」,告知他是美國一百萬得到阿茲海默症病友的其中之一。他在信上接著寫道:「南茜過去曾經得到乳癌,我則接受過癌症手術。我們發現,透過公開的揭露,我們能夠喚起大家對健康的意識。」信上最後一句是:「我現在要踏上一個旅程,通往我生命的黃昏的旅程。」雷根死於二〇〇四年六月五日,他是備受尊敬的美國卸任總統。南茜說,他有四年之久都沒有張開眼睛。
無論從哪裡看,診斷結果都是相同的:妄想症引發的人格解離(Paranoid Disintegration),也就是長期壓抑的非理性力量爆發。未來的發展是不確定的。人格解離的程度可能繼續進展、維持穩或者消退,端賴詹森抗拒解離的力量,更重要地,要看幾件外在事態的發展:越戰與崩潰中的公眾支持度。這些壓力裂解了詹森的信心,使他懷疑自己還有能力控制這些事態的發展;然而詹森需要這信心,才能抵禦深藏於內心的非理性懷疑與恐懼;他深怕孤單無助地留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裡。
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甘迺迪、魯斯克(Dean Rusk )、詹森、麥克納瑪拉(Robert MacNamara),尼克森,季辛吉與福特(Gerald Ford),所有這些政治人物,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都對美國的重要價值做出貢獻,而這價值卻在越南戰爭中喪失了——芭芭拉.塔克曼用一個字來描述它:美德。美國打越戰的第一個愚昧是「不斷地過度反應:掌權者發明了『危及國家安全』、『核心利益』、『承諾』等話語,不斷在其中過度反應,這些語詞於是有了自己的生命,回過頭來把發明者釘死在符咒裡」;第二個愚味是「幻想自己無所不能」;第三個愚昧是「打死不轉的木頭腦袋,以及『別拿事實來迷惑我』的習慣。」美國政府最大的過錯在於低估了北越達成其目標的能力……同時高估了南越……最後一個愚昧是缺少反省的思考。所有這些愚昧在攻打伊拉克時通通都表現出來了。詹森常常在公開場合為了與越戰相關的抉擇問題表露出痛苦的神情,這是他的風格。不過在他的個人判斷裡,並不存在那種至高無上的信心——患狂妄症的領導者才有的特徵。
之後在五月二十九日,戴高樂踏上了一個奇怪的行程。他決定當天晚上跟他的妻子、兒子、媳婦連同他們的三個小孩搭飛機前往法國在德國的軍事佔領區巴登巴登(Baden-Baden)。對於戴高樂此一古怪的舉動,評論界的意見分歧,有人認為他面對危機方寸已亂,有人則以為這是他應對策略上的一步好棋。最有資格評判這件事的兩個人,龐畢度與法國在德國駐軍的統帥賈克.馬敘將軍(Jacques Massu)相信他是心神混亂了。在動盪的政治局勢中,總統睡眠一直很少,而且,用他的傳記作者瓊安.拉古圖赫(Jean Lacouture)的話來說,他正在經歷一種老年人的「喪膽失志」。當危機結束,戴高樂從德國返回巴黎,也確知軍方對他的擁戴,他給自己的行為提出的解釋是:「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裡,我考慮到了一切的突發狀況。」但是在六月一日他對龐畢度私下卻說:「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完全喪失勇氣了。我真沒辦法為自己感到驕傲。」
葉爾欽很早就有明顯酒醉的紀錄,在一九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曰,當他在柏林出席一項標誌著俄國部隊撤退的儀式時。在那個場合上,他從柏林警察交響樂隊的指揮手上一把搶過指揮棒,自己指揮樂隊,然後唱了一首俄國民謠。一個月後在夏農機場(Shannon Airport)。葉爾欽留在飛機上下不來,雖然愛爾蘭的全體內閣聚在飛機客梯的底端等著迎接他。有一次事件也十分出名,他到美國與柯林頓總統進行一場高峰會議,在返航的途中因為喝太多,酒醉倒後陷入深睡。事後葉爾欽聲稱,是他的隨從不願意叫醒他。然而也有人主張,他在返莫斯科的飛機上其實是發作了嚴重的心臟病。面對公眾輿論,也許讓飲酒過度的傳言不斷流傳,還比讓心臟病發作的消息外露好的多。葉爾欽實際上在總統任內發作過五次心臟病,這是二〇〇四年揭露的訊息。其中兩次,分別在一九九五年七月與十月,情況相當嚴重。到一九九六年一月時,在即將於六月十六日舉行的總統選舉中,只有百分之十的俄羅斯民眾還願意投葉爾欽一票。
一九六三年,幾乎在詹森成為美國總統的同時,英國的首相哈洛德.麥克米蘭(Harold Macmillan)由於健康問題辭去首相一職。麥克米蘭的前任首相是安東尼.艾登,他於一九五七年辭職,表面上也是因為健康問題,不過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必須為蘇伊士運河事件負責。麥克米蘭擔任首相期間,英國經濟呈現一片榮景。然而在一九六三年十月裡的一次內閣會議中,他突然發生尿潴留(Urinary Retention,尿液在膀胱中無法排出)的症狀。這是一種極為疼痛的情況,通常由前列腺增生形成的阻礙導致。外科醫生建議他立即接受手術。
甘迺迪總統遇刺重新燃起了大家對總統患病憲法修正案的興趣;甘迺迪有可能存活下來但是重傷失能,而詹森的健康一向有許多疑慮,既然八年前他有過嚴重的心臟病發作。第二十五條憲法修正案在一九六五年七月獲得共識,並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由三十八州參議員正式通過。
令人驚訝的是白宮的行政官員對於危機狀況缺乏準備的程度。比如說,他們對第二十五修正案的用處僅有模糊的認知。根據第二十五修正案,總統可以簽署一份書函——如果總統的狀況許可的話——把行政的權力暫時移轉給副總統。雷根的白宮醫生丹尼爾.羅格(Daniel Ruge)在槍擊的三月三十日當天整個下午都跟雷根在一起。他相信,雖然總統失血嚴重——雷根在下午三點四十分接受麻醉開始移除子彈之前,失血量超過他全身血液的一半——但還是有能力簽署書函,如果有人把文件準備好遞給他的話。如果雷根簽署了這樣一份書函,老布希就可以暫時擔任總統角色。可是當時的上演的情形是:老布希僅僅被告知總統處在一個嚴重的狀況中,第一次告知是下午二點四十分的一通電話,當時他正搭乘空軍二號前往德州,第二次是三點零四分國務卿亞歷山大.海格給他發的一個電報。海格還把事情弄的更糟糕,因為他在白宮新聞發布廳上一副失去方寸、萬分緊急的模樣,還宣稱他是此刻的內閣部長主管——但根本不是。
夏隆試著消除尷尬的氣氛,說:「我很樂意給你們看,但這真的不是一般我們在這裡做的事。也許你可以問……」談話到此就漸漸結束。
布里茲涅夫死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由時年六十八歲的KGB頭子安德洛波夫接任他的位置。上任三個月後,他就開始需要固定洗腎。兩年不到他也死了,稍早於一九八三年十月才開刀移除一顆腎臟。一九八四年二月我到莫斯科參加安德洛波夫的葬禮,在與新任主席康士坦丁.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握手之後,我在克里姆林宮裡的接待處對一名記者說,我覺得契爾年科很明顯患有肺氣腫。當時他七十三歲。那句隨便說的話很快就傳遍全世界,讓我覺得有些困窘——不是以政治人物的身分,而是從醫生的立場這麼感覺;好幾天我都試著讓自己不要認為那個診斷能有什麼確定性。後來證實他確實罹患肺氣腫,但當時我的觀察不過只建立在聽到了他胸部發出哮喘的聲音。從那時起,我就不再對任何我遇過的政府首腦下任何醫療診斷,尤其因為我的醫學知識越來越跟不上新知。契爾年科死於一九八五年,是三年之內死去的第三位蘇維埃領導人。
艾里爾.夏隆
羅納德.雷根
查爾斯.戴高樂
在選戰中葉爾欽向選民指出,不選他就只能選共產黨領袖格納迪.丘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就此說服了俄羅斯人民。二月十五曰在葉卡捷林堡(Yekaterinburg)一場充滿挑釁的選戰演講中,葉爾欽警告俄羅斯人民,不要選擇回到過去。當他引用索忍尼辛的名言「在紅色的巨輪下毀滅」時,聲音沙啞,還一直咳嗽。在莫斯科,大家用一句古老的諺語來開葉爾欽的玩笑:「你不可能完全失去你的天分,喝再多酒也一樣。」葉爾欽在選戰期間較少飲酒,也接受適當的醫療照顧,這對於他的勝選固然有所幫助,但是真正決勝負關鍵的應該是他作為政治人物的天賦,重新找回了獲勝的意志。他一部分光彩奪目的表現,可能是在醫生的協助下實現的;醫生們發現葉爾欽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於是在夜間讓他使用氧氣,使他能正常入睡,這減輕了他的沮喪症,也大大地增加了他日間的體力。我們明確知道的是,葉爾欽先前睡眠品質極差,在這時得到了改善。
這個焦點窄化帶來的結果是災難性的。在政府內部,理性的論據、相左意見的交換、對根本政策的批判性評估,全都停頓下來了……只有權力才能制衡權力;如果制度的(而非人的)牽制力量被剝除了,那麼民主政治就有滅亡的危險。我跟許多握有大權的人一起工作過。他們無一例外都相信他們的目的是正當的、他們唯一的目標就是公共的福祉;而且他們全都憎恨會阻礙他們意志遂行的人與事。
我非辭職不可嗎?不,並不是非如此不可的,即便當時我感覺這一步無可避免。我嚴肅地擔起了政治責任,而且或許也太不知變通了點……我承認,有個密謀對我造成打擊,而且我的家人因此陷入了失望與痛苦,這如果還不能使我困擾,是非常奇怪的事。
麥可.富萊恩(Michael Frayn)有一部出色的戲劇作品「民主」,描述的是勃朗特擔任總理最後數星期的日子,他把勃朗特呈現為猶豫不決的樣子;不過梅瑟布爾格相信他在重要的政治問題上一般而言都具有決斷力。很有可能勃朗特自己承認的憂鬱症狀影響了他做出辭職的決定。但是在這個時點,他政治生涯的重大挑戰都已經完成,要主張他的辭職對德國的政治發展造成損害是很難成立的。他的繼任者赫爾默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當時是反對勃朗特辭職的——勃朗特更有能力處理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所造成的經濟問題,而且他在外交政策上大多追隨了勃朗特的路線,只有國防例外。在退休生涯裡,勃朗特繼續對德國與第三世界政治做出了顯著的貢獻。因此,有憂鬱症病史並不立刻代表一個人不適合擔任政府首腦,勃朗特就是一個例子。
有意思的是,一九六五年詹森得了急性膽囊炎,他向艾森豪請教該怎麼做。艾森豪建議他開誠布公,點出坦誠會給他帶來好處。本來詹森是執著於保密的人,這次卻接受了艾森豪的建議。他先將此事告知副總統,接著又告訴他的內閣,之後便前往貝特斯達海軍醫院接受外科手術,移除了膽結石與膽囊。他的輸尿管裡也有結石,這次也除去了。手術完成後十二天,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日,他向媒體公布了一張有名的照片,照片裡顯示了他肚皮上一條長長的手術傷疤。
愛德華.希思
毛澤東
一般美國大眾並不期待雷根能掌握一切細節;這一點,後來在伊朗武器禁售醜聞以及事後的遮掩上,讓雷根逃過一劫。雷根先是在總統特別調查武器運送委員會上變更了證詞.然後在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日上寫信給約翰.陶爾(John Tower,擔任調查委員會主席的前參議員)說:「唯一誠實的回答是:再怎麼努力,我也想不起在一九八五年八月前後,我是否批准了一項以色列軍火的補給,連一點點記憶都沒有。因此我的回答以及簡單的事實是——我記不得了。證詞完畢。」大眾對此多半都表示諒解。這個事件就此落幕,雷根承擔了責任,但否認了同謀。他的年紀幫助了他;輿論大眾都了解,大多數人年老以後都有健忘與記憶損失、名字想不起來的經驗。有這種經驗不一定就代表有什麼嚴重的問題,但是也有可能是阿茲海默症的早期徵兆,而且在雷根的案例上就是。不過我們對這種疾病的早期階段的確還不夠了解。與阿茲海默症相關的心智惡化的最早徵候,是很難確定指出來的。
他偶爾看起來心神渙散,回想名字與日期十分費力,想不起來就倚賴顧問們補上。他的雙手有輕微的搖擺。當他談起氣候變遷的議題,是拿準備好的提示紙條來唸稿,紙條上用的字體很大,有黃色與粉紅色的螢光筆畫線。相較之下,在午餐後立刻進行的第二場訪談中,他看起來很有自信,談起相關話題感覺上也非常輕鬆。
手術後詹森罹患了術後憂鬱症,嚴重到他想要寫辭呈辭去總統的職務。這件事外間很少人知道,但消息來源是非常接近詹森家庭的人。少數知道此事者說服了詹森打消此意;即便在四十年之後,這件戲劇性的插曲也仍被遮掩在神祕之中。詹森還有其他由於妄想症而導致的不穩定與不理性,但這是他終於在一九六八年決定下台之前唯一一次嘗試辭職。詹森的家族也有酗酒、債務、過度性行為的紀錄,這更能證明他的躁鬱症病史,因為躁鬱症是可能會遺傳的。照詹森剩餘任期的表現來看,很難否認一件事:如果他在一九六五年就辭職並且讓副總統胡伯特.杭福瑞(Hubert Humphrey)來接手,對於他自己跟對越南問題都會是更好的選擇。
在一九八〇年,威爾遜辭職後第四年,健康狀況變的十分糟糕。該年夏天他罹患了大腸癌,接受了三次手術。一位醫生紀錄臨床診療的細節,提到他對過往歲月的記憶雖然仍然極佳,但卻無法記得自己當天吃了什麼東西當早餐,這就是阿茲海默症典型的先期症狀。雖然威爾遜最後一本書《回憶錄:一位首相的要素,一九一六至一九六四年》出版於一九八六年,但是他的心智功能在那之前好幾年就開始衰退,而且惡化的情況十分嚴重。威爾遜死於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他的經驗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教訓:就一位政府領導人而言,即便是程度輕微的記憶力衰退,只要是持續性的,就應該視為一個思考去留的契機;他的醫療顧問也應該如此看待此事。
柴契爾夫人當天在國會裡過度剽悍的演出,在她黨內的國會議員之間接受度非常低。在我的自傳裡,我對她的描述是:「她處在情緒亢奮的狀態;當她反擊每一個與歐盟相關的提案時,腎上腺素在她全身流竄。」她對自己觀點的絕對確定性,以及表達這觀點時絕無轉圜餘地的說話方式,在在讓人聯想到《太陽報》著名的粗魯頭條標題,那是攻擊當時的歐盟委員會主席賈克.德洛(Jacques Delors ),標題是「去你的吧德洛」(Up Yours Delors )。
二〇〇六年有一份關於美國歷任總統生平的研究,指出老羅斯福總統罹患躁鬱症第一型,判定詹森在任期內罹患了同一病症,此診斷幾乎確定無誤。如果考量詹森多疑的性格,我們找不到任何關於他心智狀態的訊息也就不令人驚訝。他可能指示他的醫生們不要留下任何紙本紀錄,既然有妄想症,他當然害怕自己的健康有任何揭露。詹森在一生中有過臨床上顯著的憂鬱症狀,這一點殆無疑問。在對可取得的文獻進行回顧後,這些精神醫學專家把詹森粗魯與容易反覆的行為詮釋為與憂鬱症狀對反的另外一極——躁狂症狀。詹森習慣把「我的空軍」掛在嘴邊,也不可動搖地相信身為總統他有撒謊的權利。
發展完成的狂妄症在一九九〇年十月三十日這一天顯現出來。柴契爾在羅馬與歐盟各國首長會議之後,返回下議院,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了一連串聲明,說明她不會容忍歐盟所討論的那些事項。當日下議院裡的景象,衛報的政治評論家胡果.楊(Hugo Young)描述的很生動:「回到英國,她還沒冷卻下來。確實,就跟柴契爾政府過去的十年一樣,白廳官員發揮了一定的把關作用。」所以她宣讀的新聞稿還是節制的。然而一到回答問題的時候:
麥克米蘭似乎已經了解他可能患有前列腺癌,也因此他開始思考辭職的問題。他對自己的健康總是傾向做最壞的打算。他的疑病症有長年的病史,這也許跟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裡受過嚴重的傷有關。但是他的醫生約翰.李查森爵士(Sir John Richardson,後來的李查森勛爵,他是我在聖托馬斯醫院的老師,是一位令病人安心、有良心的醫生)一直認為,如果當時他沒有遠行,而是能在那些外科醫生之前先去看首相的話,他應該會給出更樂觀的病情預測,那麼麥https://m•hetubook•com•com克米蘭也許就不會覺得有需要辭職。事實上他並未得到癌症,只是良性的前列腺肥大。完成手術數月之後,他的健康就恢復了。戴高樂比他晚不到一年接受了一樣的手術,也還是留在位子上。
詹森總統在白宮裡最早時期,在社會改革方面的立法,特別是在公民權利方面,表現相當傑出。他把長期在國會裡鍛鍊出來的一切令人敬畏的手腕用來凝聚多數意見,在他之前與之後沒有任何總統達到跟他一樣的號召力。然而隨著他任期的進展,越戰越來越成為主宰性的元素,甚至成為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靨。古德溫解釋:
雷根跟威爾遜一樣都在阿茲海默症出現明顯徵兆之前就退出政治。這跟另一位政府領袖,芬蘭總統烏爾侯.克寇南(Urho Kekkonen)的例子形成對比。克寇南在任內得了一種沒有對外界揭露的病,腦部的功能似乎受了影響。他第一次當選是在一九五六年,而在一九八一年時,在嘗試掩蓋他嚴重的記憶錯亂之後,宣布辭職,雖然他從未真正被診斷出罹患阿茲海默症。他記憶錯亂的問題早在一九七八年就已有跡可循,這一年他最後一次選上總統。
柴契爾當天的演出讓一個人特別的鬱悶,那就是她的副手傑符瑞.郝維爵士(Geoffrey Howe),一位對歐洲懷抱熱情的人。他對她一向推心置腹,曾經出任她的第一任財政大臣,並且在許多面向上是柴契爾主義經濟政策的總設計師。之後他當過外交大臣,然後降級為下議院領袖。柴契爾逐漸對他溫和的行事方式看不上眼,而且隨時能在內閣裡當眾挖苦與羞辱他,讓那些神經最為遲鈍的同事都開始感到難堪。這就是狂妄症最赤|裸的表現型式。郝維是願意在歐盟問題上有所行動的。他在下議院發表了辭職演說,也許由於措詞如此謙虛娓婉,以至於產生了特別的破壞效果——不久之後柴契爾的天罰就到來了;在一個月之內,她被迫辭去了首相職務。
阿諾德.胡屈內克(Arnold Hutschnecker)完成的一份尼克森研究報告十分有趣。他從一九五一年在紐約當一般內科醫生時起就開始治療尼克森,一九五二年尼克森當上副總統後,胡屈內克也繼續治療他。但是在一九五五年時,胡屈內克對他的處置逐漸集中在精神治療方面,而尼克森很擔心影響到大眾形象。在那之後,兩人有過相當次數的祕密會面,但是尼克森在白宮中只見過他兩次。其中一次就在尼克森決定宣布進軍柬埔寨之後。胡屈內克進白宮時由專人帶路,沒有在大門內的訪客登記簿上簽名,過去見尼克森時的熟悉與方便都不復見。兩天之後,季辛吉相信,尼克森事實上「已經在精神崩潰的邊緣」。
他還提到在埃及得了胃痛,回來一直沒好,不得不躺在床上;以及在他辭職的前一個星期,牙醫幫他拔掉兩個臼齒,他感覺疼痛,整個人「暈眩而虛弱」。自傳中勃朗特寫道:「有人謠傳我有自殺的念頭,但這是過度的誇大,事實只是我感到非常的抑鬱。」在寫完被他稱為間諜醜聞的事件之後,勃朗特如此總結:「如果當時我的身體與精神狀況不是處於低潮的話,我是不會辭職的,相反地,我會盡我一切所能地把這整件事情清理乾淨。」
一九七〇年五月,在八日晚間九點二十二分與九日凌晨四點二十二分之間,尼克森打了五十一通電話給他的閣員、幕僚、雜誌編輯、外交部官員與新聞記者,當中還重複撥打給某些人。他在電話中述說他的家庭、祖父母、內戰等等,聽起來像是失眠、做了惡夢後的語言。電話打完,他做了一件讓幕僚驚恐萬分的事:他在清晨跳進座車,開往林肯紀念碑,去跟那些到華盛頓來舉行示威、抗議他入侵柬埔寨的年輕人爭論。年輕人們看到總統來了都嚇一大跳。
尼克森的妄想症狀、他對猶太人的厭惡以及口出穢言,在橢圓形辦公室的錄音帶裡有許多紀錄。他喜歡用錢打通關節、用賄賂干預選舉過程,在錄音帶紀錄裡同樣得到證實。國內稅務署開始調查尼克森從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二年的所得稅申報單。之後一九七三年在佛羅里達與美聯社編輯的一次會談上,尼克森對他們說:「總統到底是不是個騙徒,這一點是一定要讓大家了解。」毫無疑問,他當然是。他的總統任期雖有腐敗,但又奇怪地混合著不少傑出之處。我們似乎可以感覺,儘管有妄想的性情、焦慮性沮喪以及酒精中毒,這個內心有重重衝突的人其實是費了所有力氣來維持他的心智完整。尼克森的私人醫生是瓦爾特.查克(Walter Tkach),他的兒子約翰.查克(John Tkach)博士於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寫信告知羅伯特.達列克(Robert Dallek),他父親的診療紀錄必須在尼克森紀念圖書館裡封存七十五年之後才能公開,又說:「關於尼克森有些事情太過機密了,我永遠也不會揭露。」
在一九九二年九月,無職一身輕的雷根還能夠替老布希做一場助選演說,但是演講當天晚上,他無法認出自己從前的國務卿喬治.舒爾茲(George Schultz ),即使當天稍早他還在家中跟他見過面。一位雷根在白宮的醫生在那天是六個月以來首度再見到他,據他的描述,雷根有點心不在焉,但這對雷根來說是不尋常的,因為一般來說當他跟別人說話時,都是精神集中、完全投入的。談話結束時,雷根問他:「接下來我該做什麼?」臉上的表情是一片空白。這位醫生事後回想,認為這就是雷根得阿茲海默症第一個確定的徵候。
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不管共產主義在西歐民眾的眼中有過多少號召力,都因為蘇維埃於一九五六年入侵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以及東西歐之間(特別是東西德間)的交流日漸頻繁,因而大為失色了。布朗特了解到一件事,這也是他於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四年間擔任總理時極為倡議的,這就是:為了要終結歐洲的分裂狀態,西德不能完全仰賴美國、英國與法國的推動,而必須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策略來。這個在布朗特手中成型的策略,一般稱為東進政策(Ostpolitik),其主要內容,就是勃朗特的首席顧問伊耿.巴爾(Egon Bahr)所說的,「用友好關係來推動改變」,也就是緩慢但持續地將關係正常化。例如在一九六九年,東西德之間電話通訊僅有五十萬通,二十年之後,這個數字變成四千萬。在一九七〇年代,東柏林與西柏林之間電話通話的次數少到可以忽略,但是到一九八八年就達到一千萬通。西德與蘇聯以及對其他東歐國家的關係,也在「東進政策」之下穩定地進步。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戴高樂的健康復原的很好,於是宣布他將繼續競選總統一職。十二月五日他被法蘭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逼到第二回合投票。在些許的遲疑之後,出於受傷與憤怒,他繼續奮戰,並於十二月十九日贏得百分之五十四點六的選票,擊敗密特朗的百分之四十五點四。
然而她在福克蘭戰爭的勝利,以及隨後在一九八三年不費吹灰之力贏得大選,都無疑增強了她的自信心。她開始擺脫那些持反對意見的同僚,而把認同她觀點的人安排在身邊。在長達一年的礦工罷工裡她雖然意志堅決,但並沒有狂妄。面對可能發生罷工,事先她非常細心地做準備,下令提升煤的貯存量,然後才跟礦工領袖亞瑟.夏吉爾(Arthur Schargill)對上。二十世紀裡再沒有第二位英國首相能夠像她那樣不動如山,最後把礦工逼迫到全面潰敗。其他英國首相一定撐不到一年,就早早尋得一個藉口向礦工妥協。但是她正確地認識到,在此事上的完全勝利不只是辦得到,而且還是必要的。礦工是在當時既有的工會法下失敗,而非她所提的新法案。這是她首相風格成型的時刻,可說標誌了二戰之後工會運動在政治與產業界影響力的結束。一九八〇年代英國的經濟衰頹只有透過堅決的領導才有可能逆轉,而柴契爾追求貨幣政策的紀律、工會的改革以及私有化的推動,使英國經濟得以轉型,為後來者留下了可觀的遺產。
戴高樂跟納維爾.張伯倫一樣,直到走下政治舞台後病情才變得十分嚴重。但是我們可以合理地懷疑,他的年紀是否在某些時點上對他的決策判斷構成影響。當罷工與學潮在蘊釀與發展中時,是龐畢度採取了果決的行動,灑錢平撫了罷工者。即便如此,在危機平息之後,戴高樂贏得了六月三十日的國會選舉,他仍然樂於見到龐畢度辭職,並且指派德慕爾維爾(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擔任總理。不過這場與戴高樂的決裂如果有任何效果,一定也只會提高龐畢度的聲望,也讓他能夠清楚地表態,只要時機成熟,他就會競選法國總統。從這時起,戴高樂首度有了一個明顯在等待位置上的接班人。戴高樂接著又做了一個錯誤的判斷,為了地區改革與國會重組的議題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舉辦公投。投票的結果以很小的差距失敗了,支持者佔百分之四十七,反對陣營則為百分之五十三。四月二十八日中午過後不久,發言人代表總統發表了一份簡短的正式宣告:「我將停止行使共和國總統的職權。此一決定自今天中午起生效。」
不過,有一份回顧性質的研究對雷根的兩次選舉辯論會進行了比較:一次是在一九八〇年選戰期間跟總統卡特所做的電視辯論會,第二次是一九八四年雷根以總統身分跟民主黨挑戰者,前副總統瓦爾特.孟岱爾(Walter Mondale),所做的辯論。研究報告指出,一九八〇年辯論時雷根的回應是意思清楚的,所用的語句結構良好也容易理解,但是在一九八四年他的回應帶有許多嚴重的錯誤,有些答話是如此的混亂,到了無法被理解的程度。此外,在卡特辯論上,雷根說話沒有文法錯誤——冠詞、介繫詞與代名詞都使用正確,但是在四年後與孟岱爾辯論時,雷根在第一回合平均每二百二十字有一個文法錯誤,第二回合每二百九十字犯一個錯。在說話停頓上,一九八四年比一九八〇年的次數高出五倍;在說話速度上,一九八四年比一九八〇年慢百分之九。主持這項研究的心理學家布萊恩.巴特沃斯(Brian Butterworth)所做的回顧總結是,雷根此時確實有老年失智的早期症狀。
現在我們很容易忘記,在一九七〇年代末以及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這個世界還處在一個多麼危險的階段。例如說,一九七八年約翰.哈奇特爵士將軍(John Hackett)在轉行進入學術界後,與其思想家合作寫一本書《第三次世界大戰》(The Third World Warr);此書並非危言聳聽之作,而是有很高的可信度。書中指出在北大西洋公約國與華沙公約國之間,一個緊張的小摩擦多麼容易地就在歐洲引發戰爭,而且整個過程都能合理推斷出來。
雷根本人對於萬一無法視事——不是由於子彈,而是因為他的心智退化——所採取的作法是更為直接簡潔的,一如他的風格。一九八七年,雷根的白宮醫生約翰.哈頓問他,假設由於心智退化的問題,他們必須援引第二十五修正案的時候,他希望他們怎麼做?雷根的回答很簡單,「去找喬治跟南茜」,意思是副總統老布希跟雷根的妻子。這適切地表達雷根對此問題的法律立場與務實處置。在最可能的狀況下,這兩個人一個可以代理總統,一個可以私下地勸他,該是下台的時候了。
胡屈內克相信領導人都可以改變,亞伯拉罕.林肯就是一個有所轉變的例子。另一方面,耶魯大學教授巴爾拔(James David Barber)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三日美國政治學會第六十五次大會上主張,年過五十歲的美國總統都不再改變。我不相信巴爾拔這個說法。詹姆斯.卡拉漢在一九七六年當上首相時改變就很大,拋棄了性格中的「小家子氣」,成為一個更洪大的人格以及明智的領袖。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作為首相會不會改變,這一點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然而巴爾拔對尼克森的觀察還是敏銳的:「尼克森的人際關係裡有一點是突出的,就是他有意識地孤立自己,跟他人隔絕開來,獨自做出決策。」他還把尼克森歸類為「積極但負面類型」的總統,而杜魯門是「積極而正面的類型」,艾森豪則是「消極而正面的類型」。美國學界許多年來都在研究政治領袖的人格,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對他們的演說、訪談與文章進行內容分析。大衛.溫特(David winter)是這個領域中的頂尖學者,他在一篇有意思的回顧研究裡有這樣的結語:在這類研究裡,「一定程度的謙卑是必要的,也是應該的」。
早在入侵柬埔寨一事上,尼克森就有明顯的異常行為表現,這比水門事件爆發、他面臨彈劾的威脅時要早的多。比如說,知名的記者詹姆斯.雷斯頓(James Reston)報導過:
在龐畢度與勃朗特掌握大權的同一年,李查.尼克森宣誓就職美國總統。有人描述他是一個「有病態氣質、獨來獨往的傢伙」。沒有人可以確定尼克森在白宮時期裡是否患有重型精神病(Psychotic),但是他顯然非常接近這個狀態。(重症精神病是一個疾病的通稱,包括幾種使患者喪失現實感的疾病,患者可能深陷其中以至於無法意識到自己生病。憂鬱、妄想與酗酒——這些問題尼克森都有——本身並不是重型精神病的構成條件,雖然這些也都可以發展成重症精神病。)
葉爾欽在第一輪投票中贏了丘加諾夫,但是兩人的得票率沒有誰超過百分之五十;得票第三的亞烈斯堪德.烈柏德將軍(Aleskandr Lebed)則在追加投票日之前同意加入了葉爾欽的團隊。儘管葉爾欽這時又發作了一次心臟病,發作形式是胸疼痛以及後續的憂鬱症,但是在七月三日他還是擊敗了丘加諾夫,票數超過他達十五個百分點。不過在八月九日的就職典禮上,葉爾欽幾乎無法走路,說話含糊不清,一望而知是生了重病。
戴高樂將軍(Charles de Gaulle)於一九四〇年從倫敦向法國人民廣播他著名的「六月十八日的呼籲」(L'Appel du 18juin),此時他已經把自己當成法蘭西共和國的政府領導人。次日當他再度廣播時,他稱自己是以法國之名而發言。戰爭開始的前幾年裡,每當他承受重大壓力,就會出現嚴重的憂鬱症狀。在他廣播演說之後才兩星期,英國皇家海軍在墨塞爾克比(Mers-el-Kebir)擊沉了數艘法國船艦,事件中一千二百九十七名法國海軍隨之喪生;在此重大壓力下,戴高樂就出現了一次憂鬱症狀。另外一次憂鬱症發作是在達喀爾(Dakar)大潰敗之後,當時戴高樂無法說服那些效忠於維琪政府的法軍向自由法國投誠。戴高樂事後表示,他甚至考慮過自殺。海軍上將愛彌爾.謬瑟里爾(Emile Muselier)明目張膽地挑戰他的權威,英國方面又拒絕將謬瑟里爾祕密逮捕,這些造成他又一次的發作。另外戴高樂也因罹患惡性瘧疾而病情嚴重,但是這消息並未公開,包括自由法國的將領與政治人物以及英國方面都未被告知。他後來在倫敦的郊區,在妻子的照料之下才恢復了健康。
跟大企業不一樣,在政治領域你幾乎無法規畫接班人。總的來說,政治領導人都緊抓著位子超過太久的時間,變得對較年輕的可能接班者心懷疑慮。蘇聯已經走到一個地步,它年邁的領導班子死困在現況裡,不再是政治智慧的源頭,而是變得抗拒改變。幸運的是,當戈巴契夫繼任契爾年科時,蘇聯選擇了一位年輕又狀況好的領導人——雖然仍然是一位列寧主義者——來擔任第一任總統。相對於蘇聯,東德——與阿爾巴尼亞一起構成未改革的共產主義的最後堡壘的艾瑞克.何內克(Eric Honecker)在一九八九年時是又老又病也不知變通。戈巴契夫拒絕命令蘇維埃軍隊前往東德鎮壓興起的暴動,然後在一九八九年又允許柏林圍牆倒塌,他向前跨出很大的一步。但是戈巴契夫的健康與活力無法阻止蘇聯的死亡,在蘇聯快速地解體之後,俄羅斯尋得一位魅力與勇敢兼具的領導人,然而他惡劣的健康狀況構成一個嚴重的問題。
然而在這次手術得以進行之前,夏隆發生了嚴重的腦內出血,也就是上述治療的併發症。他進行了兩次手術移除血塊並減輕腦內的壓力,之後讓他維持昏迷的狀態。在我書寫此刻的二〇〇七年底,他仍然活著。如果他一開始沒有被給予抗凝血劑,可能還可以恢復過來。由於醫療介入而造成的疾病,是今天疾病種類裡最大類別之一;這是一個難以迴避的事實。夏隆的副手艾胡.歐馬特(Ehud Olmert)成為代理總理,承擔了掌理國家的責任。歐馬特帶領新成立的前進黨在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大選中以最高票數勝出,並且組成了聯合政府,而歐馬特在選後不久便出任總理。歐馬特值得肯定的地方是,他在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公開表示,數日之前他被告知患有初期的前列腺癌。他需要進行一次簡短的手術程序,割除一塊微小的、還沒有擴散的增生組織。他將可以順利任職,不必接受化學或放射線治療。
在法國,在密特朗離職將近十年之後,他當年掩蓋醫療狀況的教訓似乎已經被遺忘。二〇〇五年九月二曰星期五,法國總統賈克.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在開完一整天的會議後,發作了劇烈的頭痛,開始視線不清。艾麗榭宮的醫生被請過來,他本人當晚就住進聖寵谷軍醫院(val-de-Grace)。這次住院治療並未於當天向公眾公布,只在次日發布了一個醫療公告,稱總統「有一點血管相關的狀況,造成輕微的視覺障礙」。公告中沒有解釋問題主要是發生在腦部還是眼部,使得流言四起,說席哈克中風了,部位是在腦部。官方沒有釋出進一步的細節,只除了總理多明尼克.德維勒班(Dominique de Villepin)被告知總統在星期六有走路。各種猜想繼續出現,與席哈克同政黨的政治人物嚴詞批評,認為政府應該給大眾提供相關指引。等到消息傳出,原來星期五當天晚上總統住院的消息連總理也未被告知,媒體上爆出一片的震驚與憤怒。席哈克本人曾經在一九九五年密特朗遮掩事件的餘波中,承諾如果他當上總統,一旦他本人遇到任何醫療事件,一定會提供「透明的消息」。現在相形之下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世界報》放重砲轟擊:「在法國我們拜的這種和_圖_書保密教,會讓前蘇聯的克里姆林宮為我們感到驕傲。」
柯林頓總統在白宮期間沒有重大疾病。從二十一世界初起,人們開始假定政府首長會追隨布希坦誠的例子,比過去時代裡更願意說明他們的實際醫療狀況。令人難過的是,這並沒有發生。我們將在第七章裡看到,東尼.布萊爾以及小布希兩人在醫療問題上,都不打算對他們的選民說實話。
既然在蘇維埃共產黨的統治下,克里姆林宮決策的主旋律就是機密,所以西方民主國家會產生熱切的興趣來研究蘇共不足為奇,那怕是最微小的徵兆,只要能推斷其動向,它們都會積極投入。這樣的興趣也包括研究政治局領導人的健康在內。順著這樣的發展,差不多也就衍生了一門全新的學術專業:克里姆林宮研究(Kremlinology)。一九七七年我任外交大臣,即將按照行程前往莫斯科時,祕密情報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MI6)局長摩利斯.奧德費德(Maurice Oldfield)請我注意觀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的健康狀況,並且在回來後告訴他結果。有傳聞稱布里茲涅夫因為喉癌已經在接受治療。然而當我跟他在克里姆林宮裡會面、進行一段時間的談話之後,我看不出他有任何明顯的異常狀況,雖然我的口譯人員覺得他說話的方式有所改變。我覺得比較清楚的一點是,布里茲涅夫老化的非常快。一九七九年在維也納參加會議時,他幾乎是由兩位高大的KGB軍官給扛進會場的。而同年十二月,當尤里.安德洛波夫(Yury Andropov)、安德烈.葛羅米科(Andrei Gromyko)、波里斯.普諾馬列夫(Boris Ponomarev)與迪米特里.烏斯提諾夫(Dmitry Ustinov)做出重大錯誤決策——入侵阿富汗時,他甚至不克出席,只從自己的辦公室裡簽名同意。這一群衰老領導人統治著的蘇維埃帝國,曾經在大英帝國國力頂峰之時擊敗英國軍隊,如今卻從這個集體決策開始走向衰亡,這件事真具有象徵的意義。
艾森豪的私人醫生霍華德.史耐德(Howard Snyder)稱這次發作是與腸胃有關,而非心血管方面的。後來的診斷結果是迴腸炎,或稱克羅恩氏病。(克羅恩氏病〔Crohn's disease〕是小腸、大腸或所有腸胃道的慢性發炎,最常見於迴腸。這是一種自體免疫性的病症,可能持續數年之久,不斷的復發與緩和。常跟潰瘍性結腸炎混淆,但是結腸炎只影響結腸,而克羅恩氏病可以在腸胃道的任何段落發生。受到影響的腸道會變厚,並且潰瘍,但其他部分維持正常。盛行率有上升趨勢,目前每十萬人裡七人有此病症。表現症狀是腹部疼痛、帶血的腹瀉以及體重下降。近年用抑制免疫力藥物治療法頗有成效。如果患病部位太廣,可能會需要以外科手術切除一部分患病的腸子。嚴重的併發症是腸穿孔,比較常見的併發症是腸阻塞:兩種情況都需要緊急施以手術。)艾森豪在軍中的心臟科醫師托馬斯.馬汀利(Tomas Mattingly)後來成為他白宮的醫療顧問,但這時候並未治療艾森豪。馬汀利相信他在一九四九年遇到的是一次輕微的心臟病發作,而史耐德掩蓋了實情。馬汀利喜歡艾森豪,也很尊重他,但仍認為史耐德的欺瞞是在他的許可與配合下進行的。不管真正的診斷為何,當艾森豪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擊敗阿德萊.史帝文森(Adlai Stevenson)當選總統時,美國選民以為他的身體並無病痛。
部分報告指出,尼克森已瀕臨精神崩潰,並且時常酒醉。他喝酒並不只是由於社交需求;後來有資深的精神醫師把他的狀況判定為酒精中毒。海軍作戰部長艾爾模.祖文德(Elmo Zumwalt)上將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白宮裡會見尼克森總統:
瑪格麗特.柴契爾
勃朗特情感豐富的性格,毫無疑問地,在某些時候會使他無法抵抗抑鬱的情緒。他的憂鬱症狀是週期性的,大約一年兩次,大多出現在秋天,一天中日照開始變短的時節;他會在床上一連躺上兩到三天,任何人都不准連絡他,包括他的妻子。他的貼身幕僚稱這樣的發作為「流行性感冒」。當他返回日常的工作,他並不為自己的缺席表示抱歉,而似乎認為這是十分正常的事。沒有證據顯示他這些「流感」在擔任公職期間對他處理政務有太大的損害。勃朗特著名的傳記作者,彼得.梅瑟布爾格(Peter Merseburger)寫信告訴我,他懷疑勃朗特的憂鬱症可能根本沒有接受治療。
在第二任期間,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當艾森豪坐在桌前工作時,遭遇到他總統任內第三次重大疾病。開始先是暈眩,他的右臂與右手在幾個片刻裡感到虛弱;然後他說話有困難,也找不到正確的字。相關人士一開始以為他的情況是左半腦有暫時性的血液循環不足,但是他的語言能力輕微受損,而且再也沒有恢復,這項事實指出他實際上是腦溢血。(腦溢血,也稱為腦血管病變,關涉到的是腦部突發性的損害,原因是腦部血液的供應由於血栓塞而中斷,或者是腦血管壁破裂後,血液流入腦組織中。後者通常與動脈硬化症——動脈壁被他物覆蓋——有關。)關於這次病情,媒體被告知的訊息要少的多。有一度艾森豪告訴貼身的醫護人員,說他在思考辭職的事。然而他最終還是做滿了任期,擔任總統直到一九六一年一月,之後又活了將近十年。一九六五年夏天他又發生一次嚴重的心臟病,陷入了憂鬱。其他發作接踵而至,在一九六九年三月艾森豪因心臟衰竭過世,得年七十八歲,離他在丹佛心臟病發作隔了幾乎有十四年之久。
詹森的企圖心極其強烈而且不拘手段。克拉克.克利福特(Clark Clifford)認識從杜魯門到卡特每一位美國總統,他形容詹森「是我見過性格最複雜的人;也可能是我遇過最難纏的」。他有時可以「極度的陰險」,是個「駭人的惡棍」。但是他深諳政治權力是怎麼回事。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狄恩.阿契森(Dean Acheson)在給克利福特的信上說,詹森身上「有一種叫人難以相信的組合:他既有敏銳的感受,又極其粗俗,既有良好的理解力,但有些事他又完全遲鈍」。然而克利福特相信,如果不是因為打了越戰的話,詹森「本來可以納入我們最耀眼的總統之列」。
關於越戰,關於詹森,各家觀點之多是數不清的。總統喜愛社交、表現強烈的人格,似乎使得美國國內對他的意見分歧變得更大,而非更小。在一些政治人物的圈子裡有人對他敲定交換條件的能力讚賞有加;在另一些圈子對此則憎恨溢於言表。有人甚至能夠同時又愛又恨。幸運地,詹森最後還是擁有足夠的洞察力,了解到如果他離開這舞台,或可讓他所助長的這個分裂得到癒合。
喬治.龐畢度擔任總統的期間,幾乎跟威利.勃朗特(Willy Brandt)擔任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西德)總理的時間完全重疊。二戰期間勃朗特是在挪威度過的。他與納粹之間沒有最絲毫的關聯,形象從未受到沾染。在一九六一年的柏林危機當中——冷戰的緊張氣氛在柏林是最為強烈的——他作為市長頑強不屈的表現,為他贏得了巨大的個人聲望。在一九六〇年代晚期,勃朗特擔任社會民主黨黨魁,他的政黨與基督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總理是基民黨的庫爾特.基辛格(Kurt Kiesinger)布朗特則擔任外交部長達三年之久。布朗特此時了解到,西德必須改變戰後的長年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的政策,不能繼續在一切形式上都拒絕承認共產主義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東德)。
我知道克發維(Estes Kefauver,一位田納西州的參議員)想這個位子想的要死,而且他比甘迺迪還年長四歲。此外我也寧願更照顧田納西州而不是麻薩諸塞州。但我老是想到一個景象;老喬伊坐在那邊,手握如此的權勢跟財富,卻一輩子覺得要報答我——我多麼喜歡這個景象啊。
由於總是聯合執政,而且生活在持續的戰爭威脅裡,以色列比任何國家都更需要一位能夠以最佳表現運作的總理。以色列的政府首長每天都面對影響到國家安全的決策問題;這些決策當中雖然有些會交給內閣閣員辦理,但是有時候卻需要總理當天在幾分鐘之內拿定主意,而行動或不行動的政治後續效應也唯有總理才能夠正確衡量。因此以色列總理的健康若出了任何問題,在大眾之間總是引起重大關切,也就毫不令人驚訝。以色列以及其他國家需要的是一套強制性的規定,總理必須接受獨立的醫療評估,而當他們因為疾病的緣故無法遂行職務時,也需要一套制度化的安排,讓他們從職位上退下來。
尼克森垮台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是心智失常,飲酒過量,還是狂妄症?毫無疑問地,在連任成功之後,他顯現出許多狂妄症的特徵。也一定有人懷疑尼克森在位的最後十八個月裡,當司法的羅網越來越逼近、他親信的圈子日漸縮小、而他比從前更顯獨行獨斷時,他的心智是否仍然健全。白宮發言人提普.歐尼爾(Tip O'Neill)在一九七三年十月裡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期間見過尼克森,後來他寫道:「總統的行為十分怪異。」十二月時,參議員巴瑞.郭德瓦特(Barry Goldwater)寫道:「我有十足的理由懷疑白宮裡面有人可能精神不正常。這將是我對此事的唯一紀錄,我會把這份紀錄鎖在我的保險箱裡。」國防部長詹姆斯.史列辛格(James Schlesinger)是一位知識豐富的政治家,他在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上說,不要執行總統對軍事方面所做的任何決策,除非他們五人全數同意。而且他們應該首先跟他進行確認。史列辛格對總統精神狀況感到極度的憂慮,他甚至援引《國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要求所有從總統發出的軍事命令,都必須經過他——國防部長——來傳遞。
艾森豪有好一段時間煩惱一個問題:如果總統病的太重,沒辦法正確決策的時候,該怎麼辦?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裡的一次閣員會議上,他提議成立一個特殊的委員會,由該委員會來決定權力移轉的程序問題。同年四月,他的司法部長向參議院提出一個憲法修正案,規定副總統在取得行政權之前必須獲得國會的多數同意。這就是憲法第二十五條修正案的先聲。一九五八年三月三日,在修正案尚未通過之前,艾森豪與尼克森兩人協議達成了一份備忘錄,允許總統可以宣布在某段期間內,將大權轉移給副總統,而總統事後亦得中止這期間。備忘錄也允許副總統在經過適當的諮商會議後,宣布總統失能。這項協議沒有法律效力,但是它凝聚了國會的向心力,讓國會知道有些事非做不可了。甘迺迪政府並不熱衷提高這個議題的優先性,也不想在憲法裡明訂相關程序,而是傾向由參議院提案讓國會決定必要措施,依此來建立這個程序。也許甘迺迪希望讓大眾儘量不要討論總統的健康,因為他自己也在遮掩。
然而槍擊後的次日早晨,梅斯向外宣稱「一切真的照常運作」。貝克也說:「總統完全有能力採取行動。」雷根的新發言人賴瑞.史貝克斯(Lany Speaks)說:「總統會做所有的決定,跟先前一樣。」這是對總統的健康狀態完全不準確的說明,而且是故意的誤導。參議員勃奇.貝合(Birch Bayh),草擬第二十五修正案的關鍵人物,後來談及此事:
當一九八一年一月羅納德.雷根首次踏入白宮時,他已經將近七十歲,但是看起來精神體能非常好。八年後離開總統職務時,他是美國史上最老的總統,但也仍十分受歡迎。雷根總統是個很持別的人,他的良好特質與不足之處常常互相掩蓋。他對於醫療疾病一向直言不諱,讓許多人嚇一跳。一九八〇年總統競選期間,他有一次在飛機上對《紐約時報》醫療版記者羅文斯.阿爾特曼(Laurence K. Altmann)談到他的母親,他說她生前最後幾年有老人痴呆,八十歲時在中風後過世。他欣然接受白宮醫療團隊檢查他的心智狀態,也保證如果在任期內得到老人痴呆的話,一定會主動辭職。他向阿爾特曼請教老人痴呆是怎麼回事,阿爾特曼對他解釋了腦部的澱粉樣積存物以及阿茲海默症,這都是當時尚未被廣泛了解的知識。雷根顯然關心這個問題;他很清楚,以他母親的病史以及他兄長記憶方面的毛病,他自己可能也無法倖免。如果一等親當中有人發病的話,得到阿茲海默症的機率估計是在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如果一等親中無人得此病,那麼得病機率是介於十五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實際患病風險比大多數人想像的都還要低。八十歲以上的族群裡,有大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人患有阿茲海默症。雷根很特別的地方在於,他願意公開地談論他對此病的焦慮,而且還是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總統大選勝利之前。
德懷特.艾森豪
很多白宮官員有個典型的毛病:他們覺得保護自己的權力場子比這個國家的福祉還要重要。如果你有一個不能視事的總統——雷根總統當時幾乎就跟死掉了一樣——不把權力移交給布希是完完全全不負責任的。我認為這違反了憲法的規定。幸運的是,雷根恢復了健康,而我們國家沒有因此遭到損害。
在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初步的檢查裡,夏隆被診斷出在心房壁上有一個小洞,即先天的心房中膈缺損(Atrial Septal Defect)。醫生起先認為是在洞裡或者洞邊形成了一個血塊,干擾了腦部的血液輸送,因此造成了夏隆的中風。於是醫生們做成決定,先讓夏隆恢復一段時間,然後再動手術把洞補起來,方法是在局部麻醉下,用一種器具從食道插入來進行縫補。
雖然說不上『爛醉已極』……但是他的樣子的確讓我覺得不安,像一個腎上腺素衝到了頂、情緒處在崩潰邊緣的人。我感覺他沒有進行理性對話的能力,更遠遠談不上能夠理性領導這個國家——而這個國家正涉入許多複雜的處境,剛開始進行一系列高危險性的行動!
九月二十六日早晨,當艾森豪的病情為大眾所知悉,道瓊股票指數掉了六個百分點,換算帳面的財富損失是一百四十億美金;這是一九二九年大崩盤以來最大的跌幅,幅度甚至超過市場對甘迺迪總統遭到暗殺或者雷根總統遇刺的反應。恐慌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艾森豪的健康表現有很大的幫助。幾個星期後他在醫院的頂樓上拍了一張照片,人坐在輪椅上,襯衫上繡了「好多了,謝謝你」幾個大字。
尼克森在任內的最後幾個月裡,確實試著繼續當好他總統的角色,不過在一次半夜的危機時刻中,令人錯愕地,他卻沒有現身,可能是因為他醉的不省人事。這是指一九七三年蘇聯介入中東戰爭,在十月二十四日晚上,李奧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幾乎要派出蘇維埃的空降部隊到戰區了,美軍因此進入升高的緊急狀態。這次在總統缺席下的危機處理之所以能夠完成,全靠支持尼克森最力的亞歷山大.海格將軍(Alexander Haig)——他返回白宮擔任辦公室主任——以及擔任國務卿的季辛吉;他們給國際媒體製造出一種白宮運作如常的印象。海格稱尼克森任期的最後階段是「美國歷史上最危險的時期之一」,並且說,領導權能不能合法移轉「在那個時候還是一個未知數。」他擔心的不是軍方干政,而是國會可能有不當的行動。
威利.勃朗特
除了一次視網膜剝落,以及影響了小指與無名指的掌肌膜攣縮症(Dupuytres's Contracture)以外——而且都經手術治癒——瑪格麗特.柴契爾在她十一年英國首相任期內,身體健康狀況都很好。然而她的政治歷程,幾乎就是政治領導者陷入狂妄症候群的教科書案例。她一開始上任的階段並沒有狂妄的問題,雖然她習慣把同事二分為「他們跟我們」,還對集體共識不屑一顧,這些行事方式或許算是顯示她有狂妄傾向的蛛絲馬跡。擔任首相的頭兩年裡,她都小心翼翼地讓許多黨內與她不同調派系的反對聲音留在內閣裡;當一九八一年在一個產業爭議上遭到礦工團體挑戰時,因為勝算不高,她也懂得採取退讓的策略——即便只是暫時的,因為一九八四年她又跟礦工對上了。
艾斯屈羅(Aeschylus)跟他同時代的希臘人都相信,神明們吝於讓人類獲得成功,而且會在一個人處於權力頂峰之時給他派來一個「狂妄」的詛咒,讓他失去健全的心智,最終導致他走向毀滅。今天我們不覺得神明們有那麼大的功勞了,我們比較喜歡說這叫自我毀滅。
如果以基本健康為理由,主張雷根總統既然事情已經記不清楚,就不應該決定競選連任,就像哈羅德.威爾遜(後來也得了阿茲海默症)不應該在一九七四年參加那兩次大選一樣,也是言之成理。不過若考慮到政治的因素,這兩人繼續留任是正確的,兩人在後面的任期裡都達成了與他們名聲相應的成就。在連任成功之後,雷根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日內瓦首度與蘇維埃領導人戈巴契夫進行會面。這次會談達成了核武裁減以及後續的核武銷毀。在一九八七年六月,在柏林,儘管國務院反對,但雷根還是做了喊話:「戈巴契夫先生,請拆掉這道牆!」他的反共哲學並不複雜,但卻直截了當、從不動搖,經由他任期上的宣揚,為後來柏林牆倒塌以及蘇維埃帝國的瓦解做出了貢獻。
許多人從雷根總統上任一開始就對他的心智能力產生懷疑。我第一次跟他一對一進行對話是一九七八年在美國外交部,當時他加州州長的任期剛剛結束;第二次是一九八五年六月三日,這次是在白宮裡。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要評估他的心智狀態也很困難,因為他對自己的無知也感覺良好,也因為他自我嘲諷的天分使他充滿魅力。雷根是一位堅持己見的領導者,注意力的持續力也很有限,但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願意專注地把問題用簡單的方式呈現出來,並且把焦點放在少數幾個重大政策的議題上,其餘部分則大範圍地授權給其他人去做。
關於毛澤東身體的健康狀況:一九三四年九月他罹患了腦型瘧疾(Cerebral Malaria),需要使用高劑量的奎寧與咖啡因來治療。一九四六年一月,史達林在毛澤東的請求之下,派了一位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醫生梅尼可夫來給他做檢查;因為當時身邊的人都覺得毛澤東生病了。梅尼可夫檢查的結果,毛澤東只是精神耗損以及神經緊繃(這是當時常用來描述憂鬱症的術語),此外並沒有其他毛病。在一九七〇年代裡,毛澤東病情變得十分嚴重,有阻塞性心臟衰竭(Congestive Heart Failure),肺部與兩腿有積水症狀。一九七一年十月,當季辛吉第二度前來北京,以便為尼克森總統的歷史性拜訪做先期磋商時,毛澤東卻臥床不起,再度陷入了憂鬱症。然而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曰尼克森來訪的日期之前,毛澤東的健康戲劇性的轉好;這次美國總統來訪在中國國內被視為是外交政策的勝利,在後續的幾次會面中,毛澤東的狀況也都很好。其實美國人也不經意地幫助了毛澤東恢復健康:為了預防尼克森病倒,他們事先運了一些氧氣筒與一部呼吸器過來,結果這些器材被送進了毛澤東的房間。
儘管如此,總統辦公室還是譴責報紙刊出了總統反覆的言論,說它們可恥,與美國媒體聯手「有計畫地行動」、「利用各種藉口來攻擊法國」。
威爾避第一任首相任期從一九六四到一九七〇年,並於一九七四年再度獲選首相。他於一九七六年三和圖書月十六日辭職下台。對當時的內閣裡大多數成員,以及對國家全體輿論而言,他決定去職造成全面的衝擊。不過在一九七五年的十二月底,他就已經提醒過兩位可能接替他的人選詹姆斯.卡拉漢以及羅依.詹金斯,他準備要退休了。一九七三年在野時,威爾遜有過一次輕微的心臟病,當時他就下了決定,也向妻子承諾,如果他再度當上英國首相,也不會在那位子上停留太久。他的首要目標是要舉辦公投,決定英國是否留在歐洲經濟共同體(歐盟的前身),而他要盡力確保投票的結果是「要」。他的策略是要重新協商加入共同體的條件,並且宣稱新的條件使得英國加入與否的問題全然改觀。雖然這新條件相對於舊條件實際上究竟有多少改善,是一件值得爭論的事情,但是這個政治策略發揮了很大的效果,威爾遜與卡拉漢(當時擔任外交大臣)成功地讓工黨選民湧向支持加入的一邊。
我所做的,只是一個人類當語言不能表達時,所做的事情。即使二十年過去了,今天我也無法說的比當時一位記者描述的更好;他寫道:「然後他,一位不需要下跪的人,跪了下來,代替那些需要下跪,卻沒有下跪的人——因為那些人或者不敢,或者不能,或者不能也不敢跪。」
不過根據二〇〇六年一月的《紐約時報》,在這次為時不長的住院檢查中,他同時被診斷出大腦類澱粉血管病變(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一種常見的老年人疾病,牽涉到腦部血管脆弱的問題。這造成治療上的兩難:給予抗凝血劑可以阻止血塊的反覆形成,但卻會讓腦部脆弱的動脈出血的風險升高。報導也指出,這位退休的將軍身高約一七〇公分,體重卻達一一八公斤;醫生告訴他,開刀之前他應該先減去四十五公斤的體重。
當然,有虐待狂、手段殘酷以及對他人的性命無動於衷,可是卻沒有精神疾病,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毛澤東的例子上我們有一點精神疾病的證據,雖然所知太少,不允許我們做出可靠的診斷。毛澤東不止有嚴重的妄想症狀,對人心懷妒恨,常想像有人下毒,派人監視他許多同志,他可能也終生都為憂鬱症所苦。根據他的醫生所說,毛澤東每隔一個週期就會因憂慮而病倒,一連數月都躺在床上。然而憂鬱症可能只是實情的一部分,他病情的全貌可能是躁鬱症。因為他能夠忽然從無疑是鬱症的階段裡跳出來,轉而呈現一種差不多也可以視為是躁症階段的旺盛活力。舉例來說,在大躍進如火如荼的展開之後,他似乎陷入一種相對上無所作為的狀態,使自己在一九六〇年左右被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些共黨領導成員給邊緣化。然而毛澤東卻能夠在六年之後跳回來發起文化大革命。週期性地採取猛烈的行動,事後又證明這些行動原來未經深思熟慮,常常就是躁鬱症的伴隨現象。
關於詹森生平的兩本書裡,《孤星升起》(Lone Star Rising)與《不完美的巨人》(Flawed Giant)有很多的故事,但我覺得最能顯露出詹森那種善於算計與權謀本性的,是跟甘迺迪的父親喬伊一段談話。喬伊對詹森說,如果詹森能讓他的兒子傑克(甘迺迪的暱稱)主掌外交關係委員會(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他這輩子將不會忘記詹森的恩惠。詹森事後回憶對此事的反應:
李查.尼克森
劇作家彼得.摩爾根(Peter Morgan)以上述訪談為基礎寫了電影《請問總統先生》(Frost/Nixon)的劇本,在裡面他讓自由派文人詹姆斯.雷斯頓(James Reston)說:
雷根的任期內出現過一次現代史上最緊急的總統健康危機,而且問題不是他的年紀或疾病。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曰下午二點二十五分,約翰.辛克萊(John W. Hinkley)的手槍擊出的第六顆子彈,在從雷根的豪華座車彈開了之後,擊中了雷根;第一顆子彈則打中了白宮發言人詹姆斯.布萊狄(James Brady)的頭部,使他後來終身失能。那顆子彈打進了總統的左邊腋下,被第七根肋骨的上緣改變了方向,進入左肺下方三吋深處,停在一個距離心臟與大動脈只有一吋的地方。
柴契爾的政治生涯之所以這樣以悲劇告終,是因為她跟自己在國會裡的權力來源——保守黨的國會議員——進行對抗。她已經到達一個階段,不只不願意聆聽她國會裡的同事,甚且還一副以嘲笑他們的觀點為樂的模樣。內閣無論在尊嚴還是品質上都大不如前。保守黨國會黨團的多數意見時常遭到她的輕蔑或者操弄。那些有雄厚資產的人,他們並非不清楚內閣政府是憲法的偉大守護者,但還是讓柴契爾如此的行徑橫行多年,讓英國的民主制度受到傷害。當然,內閣對柴契爾一直如此服貼,雖然並不僅僅因為她是位女性,但這也是一個實質的因素。既然內閣太過軟弱沒有出手的能力,就只有留給保守黨國會議員來展現力量了。一位贏過三次大選的政治領袖被剷除了——不是被這個國家的選民,而是在國會民主內規的範圍內,被她同黨的議員們趕下了台。對那些相信代議民主制度以及堅定領導階層的人來說,這個案例完美地展示出,對付一位領導人的狂妄行徑,這民主的控管機制實實在在地發揮了效果。一位民主政體的領導人若陷入狂妄症候群,幾乎避不開的結果就是像柴契爾一樣遭到天罰。她跟她的友人寧願稱此事為背叛,說這是一次政治暗殺。
愛德華.希思在一九七〇年六月獲選首相時,距贏得雪梨-荷巴特(Sydney-Hobart)帆船大賽不過是五個多月前的事,他在唐寧街十號的任期全程裡都健康良好。令人驚訝的是,他決定在一九七四年二月提前大選,當時發生了礦工罷工與電力供應短缺;大選的主題十分奇怪,是「統治英國的到底是誰」。這個決定後來讓一些醫生懷疑,希思在任的最後一年是否已經受到甲狀腺機能減退症早期症狀的影響,雖然真正的確診是六年之後的事情。甲狀腺機能減退症——又稱為黏液水腫(Myxoedema)——從問題開始到完全顯現出來,歷時數年之久也屬平常。患者機能遲緩的徵兆與症狀以緩慢的速度出現,以至於患者周遭的人們在不知不覺中適應了改變,因此沒辦法正確評估患者的遲緩問題。有時患者的醫生也會被這種自動調整而蒙蔽。(甲狀腺機能減退症〔Hypothyroidism〕是甲狀腺作用不足造成的結果。甲狀腺會分泌出兩種荷爾蒙,甲狀腺素〔Thyroxine〕與三碘甲腺原氨酸〔Tri-iodothyronine〕來控制身體的代謝活動,而這代謝活動可以用基礎代謝率來評量。甲狀腺機能減退症的病患,基礎代謝率會下降。發病年齡介於三十歲到六十歲,病症的進程十分緩慢,最後可以使患者發生全面性的遲緩症狀,包括心智運作遲緩,體力減低,體重增加。最常見的病因是自體免疫系統攻擊甲狀腺,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慢性甲狀腺炎〔Chronic Thyroiditis〕,有時也稱為橋本氏病。這種病症相對常見,女性發病率比男性高,女性是每千人有十四人發病,男性則每千人只有一人。早期診斷取決於是否發現血液中的甲狀腺荷爾蒙水平降低,而腦下垂體的甲狀腺刺|激荷爾蒙〔TSH, Thyroid Stimulation Hormone〕濃度增高——這是由於腦下垂體一直試著要提升甲狀腺細胞的活動,以便製造出更多的甲狀腺素,但因為甲狀腺體處於損害狀態不聽使喚,所以腦下垂體只能徒勞地一直分泌TSH。治療方法是給予甲狀腺素,這可以從甲狀腺離析出來,也可以由人工合成。希思的情況是,他血液中的甲狀腺素T 4指數只有三十二,正常範圍介於六十到一百七十之間,也就是非常的低;而他血液中的TSH指數卻高達五十,正常人在五以下。這表示他的甲狀腺活動是低的嚇人。)
然而,艾森豪並非一直對他的身體狀況都如此公開。他距離百分百的健康非常遙遠。一九四三年八月,當他在歐洲擔任聯軍最高統帥時,軍醫發現他血壓過高,而且他從成年以來就一直有腸胃方面的病症,胃部有週期性的痙攣,以及急遽的腹瀉。艾森豪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的日記上寫著:
波利斯.葉爾欽是蘇維埃瓦解後俄羅斯的第一位領導人,而且他雖然來自車臣,卻主導了蘇維埃共產主義和平的轉型過程。不過他掌權的後幾年裡,由於惡劣的健康狀況以及飲酒問題,被他同時代人視為一位嚴重失能的領導者,亟需要被替換下來。關於葉爾欽的醫療狀況以及他極端複雜的治療經過有很高的透明度,這一點,考慮到克里姆林宮在過去歷史裡的機密性格,是很不尋常的。葉爾欽在當上總統之前,於一九九〇年五月在西班牙經歷過一次飛機迫降,這給他留下一條疼痛的腿。讓他從那時起走路有些拖行。他還有下半背部疼痛、心肌缺血或心絞痛,給他帶來心臟部位的疼痛。(心肌缺血〔Cardiac Ischaemia〕是心絞痛的一種,都是由於缺乏適當的血液供應而造成心肌的改變。一樣有疼痛,但程度可以不像心絞痛那樣劇烈。)儘管如此,葉爾欽的健康狀況直到一九九四年起才開始給俄羅斯聯邦政府造成嚴重的問題,因為他為了減輕心臟疼痛一直服用的硝化甘油忽然失去作用了。葉爾欽開始越來越倚賴止痛劑跟酒精。在政治層面上,他也開始縮小能靠近他的圈子,喪失了早年那種富有吸引力的開放態度。
艾森豪是第一位對健康問題不再遮遮掩掩的政府領導。在覺得已經強壯到能走進橢圓型辦公室並處理公務之前,他堅定地拒絕了先返回華盛頓的建議:「沒有人要一個失能的總統。」。他的白宮幕僚長雪曼.亞當斯(Sherman Adams)讓行政部門維持運作,而副總統尼克森很明智地也沒有對掌握權力表現出任何心癢難搔的模樣。十一月十一日上退伍軍人節當天,艾森豪返回華盛頓。他對等待的群眾說:「就算醫生們還沒有完全赦免我,至少也讓我假釋出院了。」而大眾因為他的誠實對他敬愛有加。他先到自己位於蓋茨堡(Gettysburg)的農場,然後再往南到基偉斯特島,從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一月八日在那兒住了十二天。他停留期間的詳細紀錄,顯示了他一面休息養病,同時也處理政府事務。
然而一件決定性的事件改變了她施政的基本特質:那就是一九八二年阿根廷入侵英屬的福克蘭群島。雖然沒有太多英國首相會像她那樣做,派出一支海軍特遣部隊遠赴南大西洋去收復一個不具特別戰略價值的小小群島,但是這項決定本身並不是因為狂妄。根據戰爭期間我跟她所做的交談,我知道她雖然決心十足,但仍然讓人訝異地非常謹慎,而且私下是焦慮大過求戰。當英國部隊在南喬治亞島登陸的消息傳來,她在唐寧街十號門前梯階上說:「太好了,太好了!」這個舉動常常被引用為狂妄症的例證,但是那其實更多是鬆了一口氣,而不是雀躍。真正的狂妄病症狀是她讓倫敦市長安排一場典禮,一群參加福克蘭戰爭的男女軍人以分列式向她敬禮。這個角色,柴契爾知道的很清楚,只有英國女王才合適。
當手術還在進行時,雷根的兩位核心顧問,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與艾德溫.梅斯(Edwin Meese)詢問為雷根開刀的其中一位外科醫生約瑟夫.卓丹諾(Joseph Giordano),他們想知道總統在麻醉結束之後會是什麼狀況。醫生向他們解釋,麻醉結束後雷根還不能做任何重要決定,因為所有麻|醉|葯物對於心智與腦部都有一定的影響,而且他屆時會接受高強度的疼痛治療。他們問醫生這個狀況會維持多久,醫生事後回憶,他記得當時說需要好幾天。四月九日,暗殺事件過了十天,有報導稱雷根在醫院裡一天可以工作兩小時,不過這全屬誇大。四月十一日雷根出院。據他身邊的人說,總統當時是「耗竭地無以復加」。出院以後,雷根一天能夠工作或者維持注意力的時間只有一個小時左右。一直到六月三日他才恢復整日的工作時間,距離槍擊事件已經過了兩個月。
艾森豪在他兩任總統期間內表現相當好。當他卸任總統時,一開始的評價是被低估的。但在那以後他得到越來越高的認可,因為他在任內不讓美國公然涉入任何海外的軍事行動,這一點把他幾位繼任者給比下去了。在總統健康這個議題上,他了解到過去遮掩保密的慣例必須停止,總統若要贏得選民的支持,不一定需要隱瞞健康問題。
尼克森究竟有沒有授意共和黨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Republican Committee to Re-Elect the president)跑去民主黨競選總部裝竊聽器,仍然是個未解的謎團。共和黨的競選委員會一定知道尼克森要取得決定性的勝選不成問題(後來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七日尼克森在全美五十州裡有四十九州獲勝)。更令人難以了解的是尼克森為什麼要涉入遮掩與庇護。尼克森對此事最終的意見,遲至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三日才說出來:在一場電視訪問裡,他回答大衛.弗洛斯特(David Frso)說:「我讓美國人民失望了,在我有生之年,身上都將掛著這個重擔。」
老喬治.布希
夏隆不是以色列第一位在任期中患病的總理:李維.艾施可(Levi Eshkol)、果爾達.梅爾(Golda Meir)以及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也都生病。貝京於一九七九年簽署大衛營協議(David Camp Accords)之後,陷入了嚴重的憂鬱。一部分是因為他同意把西奈半島的每一畝土地都讓給埃及,而引來了對他不公平的批評。他的憂鬱症在一九八二年因為妻子的去世而更形惡化。在一九八三年有一份報告,對他以及當時擔任防衛部長的夏隆做了非常嚴厲的批評,指責他們沒有採取足夠的行動來阻止黎巴嫩境內的夏提拉(Shatila)與薩布拉(Sabra)難民營的屠殺事件。最後當貝京於同年八月辭職的時候,他的憂鬱症已經達到使他失能的程度;直到去世之前,他都過著孤獨而悲傷的生活。
不過這改善是暫時性的,毛澤東的身體再度開始惡化。一九七三年時,他已經說話困難,大多時候都需要氧氣罩。然而他的心智在某些時候仍然是清楚的,在一九七四年十月時,他指定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擔任周恩來的指定接班人。在生命最後一段日子裡毛澤東不得不停止游泳,那是他最喜歡的休閒娛樂。有些人指稱,這是由於運動神經元疾病的早期徵兆所致。他於一九七六年的九月九日死於心臟病發作,一種少見的進行性神經病變使他的喉嚨與呼吸系統陷入癱瘓。
到了一九八九年時,柴契爾對現實的掌握力似乎開始遺棄她了。當十一月柏林圍牆倒塌時,她拒絕面對東西德的統一很快就會被擺上政治的時間表。她骨子裡害怕一個更強大的德國,因此她私下談話時會動情緒地說到「第四帝國」。一次她警告老布希:「如果我們不小心一點,德國人會在和平中達成希特勒在戰爭中沒能達到的目標。」這句斷言是相當不尋常的。一股勢不可擋的政治力量在推動兩德統一,柴契爾卻徹底地誤判了其進展的速度,這顯示她的政治偏見正在損害她的政治判斷力,也表示她的自我信賴正在凌駕她的小心謹慎。到這個時候,柴契爾對外交部的蔑視,使她對一切外交上的建議都置之不理。她毫無疑問地損害了英德兩國的關係,不過幸運的是,她無法說服內閣的許多同事,特別是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胡爾德(Douglas Hurd),於是她就改變了意見。但嚴重的事情是,她與財政大臣羅森日漸隔閡,最後導致他離開了內閣。因為她聽信一位私人經濟顧問的意見,而這位顧問總是公開在媒體上反對財政大臣的政策,這等於柴契爾自己拆財政大臣的台,而柴契爾卻又拒絕承認這是個問題。越來越多人注意到她漸漸無法控制局勢;她無能採取任何行動來挽留羅森不要辭職,同時卻公開地堅稱羅森是「第一流的」、「無懈可擊的」,這坐實了人們懷疑她行政失控。她甚至聲稱自己不知道羅森為什麼要辭職。在她首相任期最後的階段裡,一位支持她的後座議員說,她現在「變得好奇怪」,暗示應該有穿白夾克的壯漢來把她載到精神醫院去治療。她內閣裡的某位部長某次告訴記者,說她已經「瘋了,完完全全的瘋了」。
在波斯灣戰爭即將爆發的背景下,首相的輪替進行地很順利。保守黨的政治順風在繼任者約翰.梅傑(John Major)的領導下迅速地恢復了;在戰爭期間,梅傑的表現也相當好。他在一九九二年繼續贏得了大選。
因此,葉爾欽在一九九六年的選舉中仍然獲勝是令人意外的。他所以能辦到,全靠他採取了「貸款換股權」(Loans for shares)的手段,從未來的金融與工業寡頭們手裡取得了大量的資金。西方的民主國家對俄羅斯民主化過程中的腐敗現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使得葉爾欽受到鼓舞,運用了大量的金錢打了一場非常成功的媒體選戰。葉爾欽簽署了一道命令,允許拍賣國家所擁有的資產;先前俄羅斯首相伊果.蓋達(Yegor Gaidar)與他的副手亞納托利.諸白斯(Anatoly Chubais)為了使國有資產快速私有化,向民眾分發國營事業的股票憑證,現在葉爾欽是直接向大銀行拍賣國家資產,銀行則向政府提供巨額的貸款以為交換。結果是,一隻手數的清的少數幾家金融與工業集團搖身變,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與金屬公司,為此他們僅僅付出了清算拍賣的價格。
記者的報導是:「當時報告的事就這樣打住了。夏隆辦公室沒找到相關規定;後來直到夏隆發生了第一次中風之後,那份檢查報告才被公布,而且只是部分。那是因為他身邊的人想證明他本來是健康的,並且狀況適於服務與連任。」這就是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行之有年的防衛性回應,他們用這種辦法來躲避問題。
尼克森與胡屈內克最後一次見面在一九九三年,場合是在尼克森夫人的葬禮,尼克森請胡屈內克跟他的家庭坐在一起。胡屈內克後來公開主張政治參選人應該要做精神病篩選,不過他也表明他是以一般醫生而非精神科醫生的身分治療尼克森的。他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的《查看》(Look)雜誌寫了一篇文章討論領導類型,文章裡提出了一個具體的觀察,讓我們看到尼克森人格的複雜性。胡屈內克提到,尼克森在一九六二年輸掉加州州長選舉之後,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你們不會再有尼克森可以讓你們隨便踢來踢去了!」這個尼克森應該被歸類於易受刺|激的領導人類型。但是在一九六九年四月時那位宣稱已經冷靜地掌握了北韓飛機事件的尼克森,可能「已經變成一個能自我控制、調整過的人格,能夠憑藉力量在協商交涉裡向和www.hetubook.com•com平前進」。然而關於尼克森對這次事件的反應——四月十四日一架美國的偵察機被北韓擊落,機上三十一名組員全數喪生——有另外一種說法。根據尼克森主要助理郝德曼(H. R. Haldeman)的日記,尼克森一開始要的是做出「強硬的回應」,當他的助手們建議他審慎從事時,才被擋下來。照季辛吉的說法:「把他想要回以致命一擊的本能衝動給強壓了下來。」季辛吉的助理勞倫斯.伊果伯格(Laurence Eagleburger)對尼克森的描述是「咆嘯與抓狂,在危機事件當中爛醉如泥」。另外有一次,據說尼克森喝醉了酒,對季辛吉說:「亨利,我們得給他們來顆原子彈。」
在手術後十個月,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的一場新聞發表會上,一位記者問戴高樂「親愛的將軍,您的身體如何?」戴高樂的回答是:「相當不錯。但是別擔心,有一天我一定死的成。」戴高樂在此以七十五歲高齡選擇繼續競選第二任任期為七年的總統職務,這是不明智的。一九六七年三月,他的首相喬治:龐畢度(Georges Pombidou)在國會選舉裡只以毫釐之差贏得多數票,預示了政治的亂局在前方等待。一九六八年五月,學生運動在法國引發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年邁的戴高樂已經不太能理解學生們釋放出來的是什麼力量。五月二十五日,他覺得自己已經無法控制局勢,於是對他的青少年與體育部長說:「一切都完了。」他的心情處於一種「深沉的黯淡」之中;五月二十七日在主持一次部長會議時「他的心與思維都在別的地方」。他似乎對周遭正在發生的事情已經完全無動於衷,會議上的對話他幾乎都沒聽到。他從前的憂鬱心情回來找他了。
她的語言就轉入冷酷野蠻的單音節字——她在國會最著名的演說方式——她的話在盛怒中跳躍,在大廳中迴響,連那些十一年來熟悉柴契爾會用哪些字眼來說歐盟事務的人,這次還是都給嚇了一跳。「不……不……不……」她在嘶吼,她的眼光彷彿望見那些田野與海洋,那些山丘與前進空軍基地,以及島上那些永不投降的人民。
我對我們自己的力量以及企圖心感到不安。我對我們過度讓別人不安感到不安……我們宣稱不會濫用這駭人的、從所未聞的力量。但是其他每個國家都會認為我們會濫用。這是不可能避免的,或早或晚,當前的局勢一定會產生出一種組合來對抗我們,結局則是我們的毀滅。
毛澤東清算任何反對勢力下手絕不容情,而他從很早就對人命的死傷毫無顧忌,這一點殆無疑問。要打破社會秩序就只能依靠暴力。早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澤東在一篇刊登在共產黨內部刊物的報導裡,帶著虐待狂的快|感,描寫了他親眼目睹一些殘酷場面的經過;文章中稱他「感到一種從未有的狂喜……真是太美妙了……活活打死一兩個人算不了什麼」。
然後在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九曰,總統席哈克在《新觀察者周刊》、《紐約時報》以及《國際前鋒論壇報》聯合訪問中,意指即使伊朗擁有核武,但它不會是多大的危險,這徹底違反了法國先前的政策。第二天,訪問總統的記者們被請進艾麗榭宮,席哈克說他弄錯了。「弄錯的人是我,我不會爭辯這一點。」席哈克同時表示收回他另外一句話「如果伊朗發射核子武器,耶路撒冷會被夷為平地」,並補充了一個多少有點問題的說法:好幾個國家都能夠阻止伊朗的飛彈抵達以色列。法國報界從前有過一個長久奉行的傳統,就是讓艾麗榭宮方面準備一份經過反覆修訂的訪談稿,其中總統任何不恰當的回答都被刪去;但現在的報界已經改變了,記者們在二月一日星期四的《國際前鋒論壇報》上坦率地報導了總統的健康狀況,在他們所做的第一場訪談中: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倍極殘酷,難免有些人也問了那個常常被拿來質疑希特勒的問題:他是不是瘋了?他的毫不容情與草菅人命都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他在一九五八年推動了「大躍進」,把農業部門共產化,把中國農夫以人民公社的制度重新組織,結果導致了據估計高達兩千七百萬人在下放、暴力對待以及飢荒中死亡。這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最殘酷的政治行動之一。而且,即便不看人命的喪失,大躍進造成的經濟損害也是毀滅性的。在一九五八年與一九六二年之間,農業產出下跌了百分之二十八,輕工業與重工業生產下跌的比例分別是百分之二十一與二十三。後來,在一九六六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裡,接連進行的清算與大規模殘殺,大部摧毀了中國豐富的文化與知識子階層。
龐畢度是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五日獲選為總統,接替戴高樂的位置。在任期開始的階段,他是一位非常有效率的總統。他其中一項成就就是撤回戴高樂對於英國加入歐盟成員的否決案,並且與荷蘭首相以及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攜手合作,在一九七三年讓英國加入了歐盟。一九七二年八月時,龐畢度感覺身體衰弱,缺乏精力。他的醫生讓他做了一連串的檢查,包括骨髓檢查與X光照相。檢驗結果證實了他得了與骨髓相關的癌症,而且在惡化當中。這病情的真相,在他死前從未對外界公開過,即便當他因為接受高劑量的類固醇治療而成為月亮臉時——這在一九七四年年初時特別明顯——也沒有絲毫透露。他於同年四月二日死於骨髓性白血病,死前數月都在嚴重的疼痛下度過,尤其是走路時。(骨髓性白血病是一種骨髓的惡性疾病,具有兩種以上下列症狀中:一、骨髓中有過多的與不正常的血漿細胞;二、骨頭在X光照片上顯現有洞;三、血清中有異常的丙種球蛋白,這可能是骨髓瘤球蛋白,班斯.瓊斯蛋白質〔Bence Jones protein〕或者巨球蛋白。漿細胞瘤〔plasmacytotoma〕是骨髓中的單一腫瘤。如果出現一個以上的腫瘤,就稱為多重漿細胞瘤。療程中會運用放射線治療與化學治療,預後的差異相當大,端視哪一類細胞受到腫瘤侵害。)在巴黎,儘管各方也有些猜想,但是只有極少數的官員在艾麗榭宮裡知道龐畢度的狀況。甚至連自己的妻子,也是直到一九七三年走訪中國的行程結束後才被告知。密特朗之所以在競選總統的過程中決定對自己的健康狀況做最大程度的資訊公開,就是受到龐畢度在任期上死亡的影響。但是當後來密特朗總統自己生病的時候,他所做的卻跟此決定完全相反。
兩天之前,戴高樂在全國電視演說裡說,他把法國的命運交付在人民的手裡。然而兩天之後,法國人民不再追隨他了,戴高樂證明了他不是戀佔權位的人。他退隱到位於科龍貝雙教堂的家裡。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正在玩單人紙牌算命時,他感覺到背部一陣突然的疼痛,整個人就倒下了;他的妻子當時陪著他坐在桌旁。他發生的是腹部動脈破裂,可能與動脈粥樣硬化相關。(動脈硬化一詞用於指稱動脈病變的許多狀況,最常見的情況下與動脈粥樣硬化一詞可以互換,指動脈內壁有脂肪斑的形成。當人的身體老化,動脈管壁以及形成管壁的肌肉也隨之衰老,因之有可能在此過程中變得脆弱,發生斷裂或破口。這種狀況會造成生命危險,有時候緊急的外科手術可以挽回性命。)戴高樂的喪禮在當地的教堂舉行,並且按照他明白表示的願望,不邀請共和國總統或其他外國元首出席,也沒有演說、音樂或喧鬧的典禮。如安德烈.馬爾羅(Andre Malraux)所說:「那是一個英勇騎士的喪禮。」不過,跟在他之前的許多騎士一樣,戴高樂最後多打了一場不該打的仗。他在一九六四年年底如果宣布下台,並且以年齡的理由避免再度競選,會是比較明智的選擇。如此一來,他作為法國史上最偉大領導者的歷史地位就不會受到損害。
賈克.席哈克
艾森豪的繼任者甘迺迪,他的疾病問題我們將在第四章中詳細檢視。當他在一九六三年被暗殺身亡時,接替他位置的是副總統林登.詹森,一位充滿爭議性、性格強烈的德州人,其總統任期從一九六三到一九六九年。詹森的健康問題在他當副總統之前就已經引人關注,在他總統任期裡一直都是話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二日星期五,詹森開車前往布朗與魯特建設公司位於維吉尼亞的土地,他跟布朗魯特建設公司有長久的關係;但在路上他忽然心臟病嚴重發作。詹森當時是參議院多數檔的領袖,近來都以狂亂的速度工作著。在那之前已經有過一些預警的訊號,但他忽略了。他一輩子都害怕心臟病發作,但也許正是因為害怕才忽略警訊。他被送往貝特斯達海軍醫院(Bethesda Naval Hospital),手術中麻醉了四十八小時,存活機率只有一半。醫生囑咐他必須中止一切工作。於是在四十六歲上,他被剔除於挑戰總統大位的名單之外。不少人甚至懷疑他能不能保住參議院領袖的位置。詹森墜入了深深的憂鬱,這是心臟病發後常見的伴隨症狀。詹森性格裡本來一直就有強烈的情緒波動,包括截然發作的憂鬱在內。八月七日他出院了,依照醫生的指示,他必須停止抽煙,也不能喝咖啡,還必須減輕體重。沒有尼古丁、咖啡因、性生活或參議院,他沒有任何能滿足自己的事情可做。忽然間他開始讀書,也開始告訴別人——說服力多少有點不足——「有時間能夠,就只是坐著與思索,真是美好的事情」。根據他的傳記作者羅伯特.卡羅(Robert A. Caro)的敘述,當詹森回到他在德州的農場,「他掉進了絕望之中,甚至比在醫院裡還要嚴重」,幾個小時坐在那裡,「眼睛望向空處,什麼話也不說」。關於詹森的憂鬱症在當時以及在擔任總統期間可能是用什麼藥物來治療,最後我們會提到更多一些。
雷根在總統任期內的醫生約翰.哈頓(John Hutton)曾經說:「以他的年紀來看,一切指標絕對都在正常範圍內。」白宮其他醫生也支持這項說法,雖然他們只給雷根做過簡單的心算測驗,要求他計算從一百持續減去七,以及問他一些相當標準(但也粗糙)的問題。
在一九六八年總統選舉之前一段時間,民主黨參議員基尼.麥卡錫(Gene McCarthy)在新罕布夏州初選裡獲得令人矚目的高票,這妨礙了詹森再選一次的機會。四天之後羅伯特.甘迺迪宣布參選,給詹森帶來一個甚至更大的挑戰。數星期後,總統便在電視上宣布他放棄再度競選了。
葉爾欽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辭職下台,他的總理佛拉狄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成為代理總統,並於次年春天的大選中勝選。葉爾欽不但活了下來,還享受著寧靜的退休生活,看著普丁再度在二〇〇四年,在真實的高支持度下,以很大的差距擊敗對手。葉爾欽是一百多年來第一位舉行東正教葬禮的俄羅斯領袖;他於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三曰死於心臟病發作,享年七十六歲。
麥克米蘭起初表示,他對辭職感到後悔。但是在他的回憶錄裡,他承認那是應該離去的時候了。事實上他已經失去了政治的觸感,從該年稍早的普羅夫莫醜聞案打擊到他的內閣時就已經十分明顯,而且麥克米蘭異於平常地在下議院的表現不佳。雖然他有優異的頭腦,但他屬於典型的演員政治家;他有時被稱為「專擺姿態的老頭」並非毫無原因。當他施政順利時,左翼雜誌《新政治家》在一幅嘲諷漫畫裡把他畫成「超級麥克」(Supermac)。之後他一直沒能擺脫這個外號。
哈洛德.麥克米蘭
人們大多都同意,是特勤主任傑瑞.帕爾(Jerry Parr)救了雷根一命。當時他先抱住總統,把他弄上車,叫司機開往白宮,但是當他一看到總統咳嗽嗆出血來,立刻叫司機轉往附近的喬治.華盛頓醫院。這次對雷根的暗殺行動只差一點就取了他的性命,也無疑地減損了他處理繁重總統職務的能力,但是雷根懂得授權辦事,也節約他的體力。
一九六七年詹森接受了一場極度保密的手術,以治療他左腳踝上出現的皮膚癌。海軍上將喬治.柏克萊(George Burkley)曾是白宮裡處理甘迺迪總統疾病問題的主要角色,現在是詹森的醫生,他反駁了一切猜測。一九七七年這場手術才得到證實,那是在詹森於一九七三年死於冠狀動脈栓塞(或心臟病發作)之後好幾年。一九六七年十月時,威理斯.胡斯特(Willis Hurst)醫生對詹森的妻子博德夫人(Lady Bird)做出警示,他極度擔心她先生的健康狀況;雖然她很想告訴他,總統方面已經做成決定,總統將不會再度競選,但她覺得說不出口。這隱含了一點:她覺得有人已經讓她先生下定決心在一九六八年之前辭職。德州選出的國會議員是詹森的好友亨利.剛查列(Henry Gonzales),他說:「他當面告訴我,他不再競選連任的原因是:許多醫生已經告訴他,他不會活過下一任任期結束。」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勃朗特結束在開羅與埃及總統安華.沙達特(Anwar Sadat)的會面,飛返德國;在機場迎接他的內政部長漢斯迪特烈希.甘攝爾(Hans-Dietrich Genscher,當時擔任內政部長)告訴他,總理辦公室裡的一位顧問古恩特.桂勞姆(Gunther Guillaume)已經被逮捕,並且已經承認為東德從事間諜工作。勃朗特在政治上的罩門是顯而易見的。很快地,各種關於他沾染女色的故事就開始出現,雖然這件事情對於在柏林以及波昂時期認識他的人來說並不是新聞。聯邦刑事調查署的一份報告指出,他們擔憂桂勞姆在即將進行的審判過程中,可能會提及一些——報告中娓婉地稱之為——「令人痛苦的細節」。這造成了一個兩難:如果桂勞姆真提到這些細節,將會使聯邦政府出醜,但是如果沒提到,則東德政府就得到一個把柄,以後可以羞辱勃朗特的內閣與社會民主黨。
冷戰期間衰老的蘇維埃領導階層
林登.詹森
在德國以外的人或許沒有充分地認識到,勃朗特個人善感的性情,是推動這「東進政策」重要的助力。這一點,在他以總理身分拜訪華沙時,有清楚的表現。在正式地將花圈放在波蘭無名戰士的墳墓上之後,勃朗特走到猶太紀念碑前,這是紀念華沙猶太隔離區及其死者的。在自傳裡勃朗特描寫了他當時煎熬的情感: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在醫生告訴他身體已經完全恢復後,艾森豪決定競選連任總統。然而從六月六日,他又遇到一次迴腸炎,這次患部在小腸,伴隨著非常疼痛的痙攣。他住進美國陸軍醫學中心(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外科醫師起先有點猶豫,但終究成功地開刀治好他的腸阻塞(克羅恩氏病的併發症)。到八月二十一日時,艾森豪的身體狀況良好,還能搭飛機到舊金山渡個假。儘管他已經六十五歲,但看上去他再度顯出健康的樣子。他先前讓大眾充分掌握他的健康訊息,而且他的醫生所說的也都符合實況,這使他現在很吃香,美國選民從不覺得被欺騙,還要他出來再選一次。
但是,她不顧傳統上被認為較好的作法而在福克蘭戰役以及礦工事件上得到勝利——傳統的看法會要她對這兩件事都妥協——也就表示她對自己的判斷過度的自信,同時蔑視他人的判斷,這是十分危險的;特別是當她於一九八七年第三度贏得大選以後更是如此。她對實施人頭稅(Poll Tax)的堅持,就明明白白地顯示出她的狂妄症候群已經何等嚴重。儘管這項稅被所有人認為不正當,但她堅信沒有這個問題,還是繼續推動這項政策。即便像邱吉爾這樣具有旺盛自信心的領袖,也不至於狂妄到這種程度。在為一九五〇年大選準備保守黨的競選宣言時,保守黨研究部門的一位年輕成員雷吉諾德.默德林(Reginald Maudling)提了異議,認為當中有一項政見是不公平的;但是邱吉爾輕率地否定了他的看法。當默德林斗膽回答邱吉爾,據他的觀察,「英國人民會覺得這是不公平」,邱吉爾沉思了一會兒,然後說:「啊,那這完全是另一回事!」這項政見就被拿下來了。然而對柴契爾來說,光是公眾的意見,份量還不足以改變她前進的方向。不過即使在這個案例上,她也並未顯現出對細部事項的傲慢忽略,那是狂妄症常有的症狀。她的財政大臣尼格.羅森(Nigel Lawson)立場是反對人頭稅,但是在他的回憶錄裡我們可以讀到,柴契爾在提案之前做過詳盡的政策研究,探討實施人頭稅的各項理由,也向同事們做過充分的諮商。不過這一切背後真正的動力,毫無疑問地,是柴契爾的信念,她堅定不移地相信這稅「沒有錯」。在某個較為輕鬆的場合中,我們也可以清楚看見柴契爾開始受到狂妄症候群的影響;她探視剛出生的第一個孫子時,所說的是:「『我們』已經變成一個祖母了!」
把尼克森趕下台的是水門案醜聞。這個事件非常有名,所以我們只做很簡短的陳述。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有五個人因為試圖闖入位於水門大廈裡的民主黨競選總部行竊而遭到逮捕。我們現在知道,尼克森在六月二十日就已經開始討論他們的逮捕問題,而他們第一次在橢圓型辦公室(oval office)討論的錄音帶裡有一個十八分鐘的缺口。要命的是,尼克森開始密切地涉入此案,成為庇護此事的同謀者。一九七四年三月一日,華盛頓的聯邦大陪審團(Federal Grand Jury)對七個人提出控告,當中四人與總統關係緊密,郝德曼與約翰.艾力希曼(John Ehrlichman)更是與總統完全無法切割。約翰.米謝爾(John Mitchell)是總統的老友,曾經出任他的司法部長;查爾斯.柯爾森(Charles Colson)是尼克森重要的白宮助理。最後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一則消息曝光,指出「有適切理由相信尼克森(連同其他多人)參與了蒙騙美國與阻礙司法的密謀」。彈劾程序於七月展開,尼克森在八月辭職。早先在一九七一年時,由於五角大廈文件外洩,尼克森曾批准了闖入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以及精神醫師丹尼爾.艾爾伯格(Daniel Elllberg)的辦公室(因為艾爾伯格被認為是文件洩密的主謀)。
為雷根撰寫官方傳記《荷蘭人》(Dutch)的是愛德蒙.摩利斯(Edmund Morris);這部傳記非常出色,雖然無可否認其立場獨特。摩利斯在書中援引四冊皮面精裝的總統日記,指出雷根的判斷能力並沒有受到任何心智衰退問題的損害。摩利斯形容這些日記「從頭到尾都有一致的風格與可清晰認知的內容。沒有任何地方顯示總統心智惡化,除了偶爾有內容重複以及推論錯誤以外。如果要把這些視為是失智症的初發階段,那會有很多寫日記的人,m.hetubook.com.com包括我在內,都要開始擔心了」。關於一九八五年六月三日跟我會面的事,雷根日記上的記載是精確的,除了幫我的名字多寫了個S。
詹森是不是因為要求兌現這個承諾而當上副總統,我們永遠無從得知。喬伊對甘迺迪有很大的影響力,這比對羅伯特大的多。喬伊可能會覺得把詹森放上候選人名單很值得考慮,因為他估計要打贏選戰一定得拿下德州,而他也不怕得罪民主黨裡那些討厭詹森的人。
事後看來,威爾遜的退休,是一個開明而進步的決定。英國當時的政治與經濟問題看起來像是無止盡地重複發生,他對於必須一再應付這些問題已經感到疲倦,而他的內閣正是他疲倦的最佳寫照。他不具有克服橫在眼前的金融危機所需的意志,下台的決定,讓他躲過了一九七六年英國跟國際貨幣基金會不得不進行的協商。然而在當時,對於威爾遜為何辭職,人們進行了數不清的政治揣測。當中有些是引人發笑的異想天開,比如有人影射他是因為捲入財務醜聞,甚至有人認為他是蘇維埃的間諜。事實上他辭職的原因很可能要單純的多:他對自己的健康越來越感到憂慮。我在過去九年裡,在下議院或者周邊的許多場合上跟他有過很多非正式交談的機會,我逐漸了解到,他照相式的記憶力對他來說是何等的重要,然而這種能力已經開始棄他而去。他的傳記作者菲利浦.齊格勒(Philip Zielger)描述了記憶力退化對他造成的影響,對威爾遜來說,「變得遲緩、一個詞半天想不起來、或者一個統計數據半天找不到,並不只是令人氣惱而已,而是重重的打擊了他的信心」。儘管如此,威爾遜是在沒有受到自己政黨任何壓力的狀況下自願下台,在歷任英國首相裡,他是唯一的例子。他真正的壓力來自他的妻子與醫生。
如果當時有這麼一條規定,要求雷根在競選第二任總統之前必須先接受一次獨立的醫療評估,那麼雷根跟他的夫人南茜可能會考慮到評估結果為負面的風險,而選擇有尊嚴的退休而非再度競選。他們兩人在關於身體狀況的議題上,如實面對的程度常教人意外。例如說在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雷根讓外界得知他得了結腸癌。照當時醫界的看法,他的癌細胞有一半的機會還沒有擴散到瘜肉之外;如果是這個情況,以今日的醫療水平他有百分之七十的機率可以再存活五年。然後在一九八七年白宮方面發出公告,雷根進行了一次程度極其輕微的侵入性手術,割除了前列腺的良性增生。這是經尿道前列腺切除術(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the Prostate),是雷根這個年齡的男性常見的手術;法國的密特朗總統也做過類似手術,不過他的狀況是惡性的前列腺癌。
美國社會為越戰陷入拉扯與痛苦,這意味著詹森承受了長期的壓力,而且在一九六五到六七年期間,他的舉止明顯地變了。他最好的一位傳記作者羅伯特.達列克(Robert Dallek)寫道:「詹森的妄想症讓人質疑;他的判斷與能力是否仍能理性地做出極重大的決策?」但他也承認:「決定一個人是否達到心理失能恐怕並不容易。」他接著提出疑問:「那麼誰能夠宣布一個總統已經跨出了理性正常心智的邊界?」雖然如此,達列克的結論是:「在詹森的案例裡,儘管他對他的敵人採取的言行十分荒唐,但他絕大多數情形下都能掌控他的能力,非常能夠適任總統職權。」確實,越南戰爭對任何總統都是極端棘手的挑戰。他必須具備的能力至少包括能夠理性與平靜地考慮撤回美國部隊;詹森沒能辦到這一點,他對自己充滿疑惑與猜疑。他選擇逐步提升兵力與加強轟炸,但執行不夠徹底,達不到他將領們的要求,不過卻超過他的批評者所能接受的範圍。
早在一九六五年的春天稍晚,李查.古德溫(Richard Goodwin)——詹森總統主要的演說撰稿人,此時已經跟總統保持密切連繫長達三年——觀察到總統「日漸非理性的行為」,他感到憂慮,就開始研究醫學教科書,也跟專業的精神醫學家祕密的討論。他的朋友比爾.莫耶(Bill Moyers)是詹森總統最信賴的年輕心腹,莫耶在古德溫不知情的狀況下採取了相同的行動,分別與兩位精神科醫師做了討論:
哈羅德.威爾遜
梅約診所(Mayo Clinic)裡有完整的醫療紀錄,讓我們對雷根在一九九〇年夏天時,也就是在他離職一年之後的心智狀況有個概念。他是在一次騎馬意外之後,在那裡進行了腦部手術,移除了一個硬膜下血腫,之後接受了一套完整的精神與心理測驗。(硬膜下血腫〔subdural Haemotoma〕,是當介於腦硬膜與腦膜之間的靜脈破裂〔腦硬膜是襯在顱骨內側的組織,腦膜則是包裹腦部的組織〕,血液緩慢滲出並累積起來所造成的。由於頭骨嚴密的覆蓋,人無法直接感覺到這血腫。然而當顱骨內的壓力升高,腦部就會受到積血的擠壓;如果一個人摔到腦部之後幾小時出現了如頭痛或昏睡這樣的症狀,那麼就很可能是硬膜下血腫。最好的診斷方式是做電腦斷層掃描。外科手術的程序是先在顱骨上鑽一個洞,然後把積血抽掉,問題可以立即得到緩解。如果即時被正確診斷,通常不會帶來持久性的腦傷害。)據稱這些測驗結果顯示雷根並未面臨阿茲海默症的問題,但是一九九三年進行的測驗則確定了此事。
稍早在二〇〇五年四月,兩位《以色列國土報》的記者訪問夏隆的時候,問他健康狀況如何。夏隆立刻回答:「我請你們來看看我健康檢查的報告。這會給別人的健康造成壓力!」記者於是請夏隆把報告拿出來看,卻發現夏隆對這樣的要求感到意外。「事實上這對我並沒有不便之處,」他說:「不過我不知道程序上怎麼做。」記者仍然堅持要看報告,夏隆就躺進他的椅子,轉向他的發言人,說:「嗯,我們怎麼處理這件事?有沒有相關的規定呢?」
戴高樂從一九六四年年初開始罹患前列腺肥大,但試著將手術往後拖延。一位同時是他好友的外科醫生幫他裝了導尿管,並跟他一起對外守密,甚至三月裡前往墨西哥的參訪行程也不受影響。四月十五日,在極少人知情的狀況下,他住進了巴黎的克杭醫院(Hospital Cochin),住院次日接受了一項手術,割除了前列腺腺瘤,一種前列腺腺體的良性增生。他住院的消息傳了出去,於是戴高樂把住院前一天親筆寫下的一份聲明交給了媒體。他事先把這同一份聲明放在密封的信封裡寄給了艾麗榭宮(Elysee Palace)一位資深官員,並且交代他:「只有在我死後才可以打開。但是,如果後天一切都像我預期的那樣順利的話,你要把這信封交還給我。」
麥克米蘭拒絕接受女王授予貴族的爵位或騎士的身分。但是在他九十歲生日時,他同意接受了一個世襲的頭銜,成為史托克頓伯爵(Earl of Stockton);他還做了一場滑稽而幽默的演說,控訴當時的首相柴契爾夫人,說她推行的私有化計畫等於是賤賣家傳的白銀。他死於一九八六年。
一九九六年九月,官方公告葉爾欽將會接受開心手術,而柯林頓總統安排了休斯頓的麥可.德巴奇醫生(Michael DeBakey)來看他。他發現葉爾欽患有甲狀腺機能減退症,這可能助長了他的冠狀動脈疾病,讓他有一張浮腫的臉,以及使他無法代謝過剩的酒精。德巴奇醫師建議他把手術延後,再多做一點準備,所以葉爾欽直到十一月七日才進手術房,接受一場長達七小時的五橋冠狀動脈搭橋手術(quintuple bypass,譯按:同時在五條冠狀動脈上做橋接繞道手術,繞過血管阻塞的部位)。德國總理赫默特.柯爾(Helmut Kohl)一次向美國媒體表示,兩位參加這項手術的德國醫生認為,葉爾欽不會撐到二〇〇〇年的總統大選。
美利堅合眾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一九五三年時是世界上兩個力量最強大的核子武器國家。在往後的四十年時間裡,美國逐漸成為唯一的超級強權;但是在美國國內,一些有見識的評論家開始擔憂美國自己的力量與企圖心。艾森豪總統從一九五三到一九六一年在位的期間,成為美國國力興旺及保守主義的象徵。在他卸任前的某次演說中,艾森豪警告了美國人民,軍火工業集團的強大力量可能構成危險。後來的越戰以及新近的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證明,艾森豪的警告是意義重大的。
當勝利的展望越來越樂觀,戴高樂對自己的信心也就隨之增長;然而他總愛擺出戲劇性的姿態。他第一次的辭職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因為制憲會議剝除了他的個人權力。制憲會議於前一年十一月才把他選為總統,但是戴高樂認為若要復興法國,那些權力是必不可少的。他自願退隱的期間住在科龍貝雙教堂(colombey-les-Deu-Eglises),後來於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以六十七歲之年重新出任法國總統,國會中的票數是三百二十比二百二十四。他仲裁了阿爾及爾的和平,建立了第五共和,不讓法國被納入北約的軍事整合架構,否決了英國加入歐盟的申請。在所有這些事件期間,他的健康狀況都被認為良好。
哈羅德.威爾遜是尼克森上任時的英國首相:尼克森下台時,威爾遜剛好重返首相職位。他是晚近在離職之後被診斷出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兩位政治領袖的其中之一;另外一位是雷根。這兩位政治領袖的案例牽涉到本書一項重要議題:政府領導人的心智能力問題。(阿茲海默症是失智症最常見的型式,特徵是逐漸喪失智力與社會功能。它是以德國醫生阿洛斯.阿茲海默〔Alois Alzheimer,1864-1915〕來命名,他於一九〇六年的一篇文章裡描述了這種病的條件。在早期的病程裡,主要特徵是短期記憶的喪失,牽涉到的主要是腦顳葉與額葉裡腦細胞的退化。偶爾也會有喪失時間與空間感的情況,伴隨智力與行為能力的退化,病程歷時的長短則因人而異。最終病人的行走能力也受到影響,喪失了移動的能力,然後在經過一段床上照料的時間之後死去。醫界做了許多的研究,神經醫學家對於取得重大進展懷抱厚望。許多研究案例證實這種病有遺傳學的基礎,牽涉到三組特定的基因。對病人腦組織的檢查顯示出,在皮質層〔大腦的外層組織〕裡的細胞外表上,有澱粉樣蛋白質〔Amyloid Protein〕構成的斑塊堆積。此外,在神經元或神經細胞內部也有病變發生:神經原纖維進行纏繞並且增厚,形成了神經原纖維的糾結。阿茲海默症是一種老人疾病,六十歲之前罕見發病,而根據統計,八十歲以上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表現出此一疾病的某些症狀。有藥物可以治療,但是多半只宣稱可以減緩發病的速度。在二〇〇六年,有四百五十萬美國人罹患這種病;如果沒有重大的改變發生的話,到二〇五〇年這個數字會成長為三倍。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的經濟學人有一篇文章〈拼湊真相〉〔Puzzling out the Truth〕用通俗的語言完整地介紹目前關於阿茲海默症的醫學研究。)
五月六日,勃朗特決定辭職,承認他「有所疏忽」。在自傳裡他寫道:
喬治.龐畢度
美國核心的國家利益在任何方面並沒有因為尼克森的身心狀況而受過損害。但有些事情確實被損害了,即民眾對政治家與政治的信賴與信念,而且不只在美國國內,而是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受了影響。如果沒有一套彈劾的機制來迫使總統接受審判,尼克森永遠也不會辭職,他對總統權力一貫的濫用也永遠不會被揭穿。危險的地方在於,人們不再記得這些負面事件,相反地,在多位繼任總統的襯托之下,尼克森的名譽反而恢復了,而且被認為是在外交政策上大有創建的總統。特別是關係到重啟美中關係一事,尼克森飛到北京與毛澤東會面,中止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外交中斷。然而我們不該忘記尼克森的權力濫用。酒精中毒對政治領袖也是非常嚴重的健康問題;我們將在第七章談到小布希時討論這個問題。
不過是數天之前,夏隆的兩位私人醫生才對發行甚廣的《以色列新消息報》說過夏隆身體健康,他們為他定期所做的檢查沒有發現任何異狀,只除了體重超重。然而,雖然有樂觀的檢查報告,所有接近夏隆的人都知道,夏隆顯現出健康惡化的狀況至少已有一年之久。他舉步艱難,呼吸變得非常急促。他的顧問設法使他避免爬樓梯,也控制他在不同的會議室之間走路的總步數。他搭乘小電梯進他的辦公室,而即便從電梯口走到電視攝影機之前的書桌也要耗費他相當的力氣。他公開談話避免進入細節,而是謹守事先準備好的談話要點,雖然根據助手的說法他的智性能力並未受到影響。
在這次訪談混亂事件之後,情況已很清楚,這位七十四歲總統的狀況並不適合在二〇〇七年五月第三度參選。雖然有關方面嘗試讓這個選項保持開放,但是在三月十一日的電視演說中,席哈克告知法國民眾,他不會尋求再披戰袍了。事實的真相是,我們再度看到一位政府領導人,即便年紀已經太老,也仍緊抱著權位不放,拒絕面對自己老化的現實,特別是在他二〇〇五年舉辦歐盟新憲法的公投失敗之後。至於在成就方面,席哈克是法國總統當中第一位承認法國在二次大戰德國佔領期間,對遣送猶太人負有責任的。他也讓法國免於涉入從二〇〇三年起的伊拉克之役的大挫敗。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四日,當老菸槍艾森豪在丹佛打高爾夫球時,腹部疼痛起來;他以為是消化不良引起的。史耐德當時也在旁邊;他當時已經七十四歲,是艾森豪家庭長年的朋友,多年來也一直治療艾森豪夫人瑪密的心臟瓣膜問題。他像一個家庭醫生那樣,在一間鄉下小診所裡為艾森豪做診療。當二十五曰凌晨二點四十五分史耐德又被召喚,因為艾森豪的胸口疼痛,史耐德判斷總統是心臟病發作,但卻沒有將他立刻送進醫院,而是讓他聞硝酸戊酯讓他的冠狀動脈得以擴張,給他注射抗凝血劑以阻止血液凝結,還打嗎啡讓他平靜下來、減緩疼痛。(硝酸戊酯是用來治療由於血液供應不足而導致心臟肌肉局部缺血所引起的心絞痛或心臟疼痛。它是一種揮發性的液體,由一氧化氮對戌醇的作用而形成。藥物濫用者用它來取得一種「嗨」的感覺,並且用黑話稱之為「啪」〔popper〕。現在的首要療法是用三硝酸甘油酯,方法是把含有三硝酸甘油酯的藥丸置於患者的舌頭下方。)早上七點時他告訴總統的發言人,總統因消化不良而感到不適;用意在讓發言人以及廣大的民眾感到安心。艾森豪一直到上午十一點才醒來,而史耐德等到過了中午才去電軍方醫院要求送一台心電圖機器過來。檢查結果顯示總統發作過心臟病,冠狀動脈有血栓塞。下午二點,艾森豪才被送進醫院。有人可能會說這種冷淡的處理方式近乎愚蠢也太冒險;也有人認為家庭醫生做到最好也就是這樣而已。再另外一種解釋則可以支持對史耐德先前隱瞞過病情的指控:史耐德在一九四九年就照顧艾森豪捱過一次心臟病發作,因此他無疑地知道這次也是,他不讓艾森豪立刻進醫院或者不立即要求心電圖檢查,為的是希望能把這次心臟病發作再度掩蓋起來。
波利斯.葉爾欽
批評葉爾欽過往紀錄的人會提到車臣的戰爭,以及一九九三年十月,當部分反民主改革的國會成員試圖發動政變時,他下令對莫斯科白宮進行砲擊以及強攻,造成了許多人的喪生。批判者也認為,有如此多的國家資產落入寡頭鉅子手中,葉爾欽要負重大責任。然而可以替辯護葉爾欽的是,只有他,一九九一年八月站在一輛坦克車上,阻止了共產主義的復辟。他引進了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選擇以及市場經濟的改革,這些,到了二〇〇八年時,改善了許多俄羅斯人的生活。葉爾欽總統受到美國總統柯林頓頓的支持與寬容,他也漂亮地做出了回報:他在一九九九年的美俄外交倡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科索沃的戰爭最終得以外交方式解決,使美國與其他北約國家無需投入地面部隊。最重要的是,經過了推翻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和平革命——這是在葉爾欽的督導下進行的俄羅斯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紀的上半葉中發展出一套穩定的民主制度。在普丁治理的階段裡,民主受到較大程度的中央控管與操作,但這是必要的過程。我希望,而且沒人能真正確定,俄羅斯會繼續把握住民主;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葉爾欽——不管他是患病還是健康,清醒還是酒醉——將會贏得歷史家們的肯定。
一九六〇年七月的民主黨大會期間,詹森試著阻止參議員甘迺迪的氣勢;他向《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說甘迺迪「是一個生了佝僂病的瘦皮猴」。印地亞.愛德華(India Edwards,她與詹森在政治上關係緊密)在黨大會的一場記者招待會上,宣稱甘迺迪得了愛迪生氏病(Addison's disease,見第四章)。顯然她有「可靠」的消息來源。此人曾經在一棟政府大樓裡遇到甘迺迪的選戰隊伍,而甘迺迪因為忘記隨身攜帶可體松(cortisone)陷入了昏迷,當天半夜一位州警才弄了一些送到他的床邊。這個消息普遍被視為詹森陣營發動的選舉奧步,不過根據愛德華的說法,詹森本人為了愛德華的指控把他牽連進來而對她大吼大叫。雖然甘迺迪看起來並不把這項對他健康的攻擊算在詹森頭上,但是他的弟弟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則認為是詹森策畫的,後來也一直不原諒他。羅伯特從一開始就怨恨他的哥哥把副總統的位子交給詹森;後來哥哥約翰遇刺後,詹森繼任總統,他也感到難以接受。
艾森豪的總統任期讓兩個與政府首腦疾病相關的核心議題成為矚目的焦點。一個是要公開還是保密,另外一個是:當政府首腦已經病到失能時,這個狀況該如何處理。在第一個問題上,艾森豪的案例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關於總統的病況如果少一點機密、多一點公開,反而能保有公眾的信心。
老喬治.布希於一九八八年成為美國總統,之前他擔任了雷根的副總統長達八年。一九九一年五月,當他外出慢跑時,感覺到異常的疲倦與呼吸困難。他住進了醫院,然後官方對外宣布了診斷結果:他有動脈纖維化的問題。後來,他又被確診患有甲狀腺機能亢進症,但是還能夠繼續擔任總統,雖然他的表現似乎有所降低。在波斯灣戰爭後他得到極高的支持度,但是隨著一九九一年夏天前南斯拉夫戰爭的進展,期間發生殘酷的種族清洗,他的支持度又掉了下來。人們也開始覺得奇怪,薩達姆.海珊在伊拉克是不是應該被趕下台,因為他對庫德族的攻擊明顯違反了聯合國的停火條件。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在一場了無生氣的選戰中,老布希敗給了比爾.柯林頓;在一場電視辯論會中,老布希在攝影機前低頭看手錶,彷彿覺得很無聊。他在處理波灣戰爭時展現過的充沛精力、對細節的關注,這時似乎都消失了。有些人認為這是他的甲狀腺機能亢進症帶來的一個副作用。(甲狀腺機能亢進症,或稱甲狀腺中毒症,可以透過血液檢查檢測出來。患者的血液中有過量的甲狀腺荷爾蒙,一種由甲狀腺合成與分泌出來的含碘物質。甲狀腺荷爾蒙控制身體的基礎代謝率,而甲狀腺荷爾蒙過多時,也就是甲狀腺亢進時,基礎代謝率會提升。甲狀腺亢進症的症狀非常多樣:心跳加速、體重流失、易怒、盜汗、顫抖、焦慮、食慾增加,以及怕體外的熱源,因為患者的身體從內部製造出太多的熱。其他更嚴重的症狀有心律不整,以及時常出現的動脈纖維化。一般來說,患者感覺到健康狀況低於平常水平,如果治療成功的話,會感到幸福,發現自己的健康有非常顯著的改善。在布希的例子上,由於他有些年紀,所以接受放射碘的治療,這是對超過三十五歲的患者給予的療法。目的是在摧毀部分的甲狀腺體,讓其他仍然完好的腺體組織繼續生產甲狀腺荷爾蒙,總分泌量會比原先減少。如果判斷的好,代表患者將無需接受替代治療。但如果治療仍有必要,患者將終身服用甲狀腺素藥片,作為一種替代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