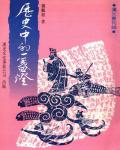二輯
汪榮寶的歷史形相與地位
在這兒,且讓我們止駐奔馳瀏覽他生平與宦途的脚步,仔細探勘這位民初卓越的學者或外交家,他心路的歷程究竟是些什麼!——
在這一季風聲裏,日子過得精緻而慵懶,拂去書架上的木屑煙泥,才發現那一册蜷縮斜傾的詩集。那,是種才人學者永恆的祭儀吧,爲什麼每次掀動它,總要觸惹起我許多的感傷?今夜無事,且讓我細拭歷史的塵埃,爲您講述些久遭遺忘的掌故罷!——
文化的變遷,可分兩類:一是由於內在文化條件改變而產生的,例如春秋戰國時代及西方近代社會之轉變;一是因爲受到其他文化外在的衝擊而激起的,近百年來我國受西方文化的挑戰即爲最典型的例證。這種變遷,事實上是一種社會解體與重建的過程,亦卽奧格本所謂的「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在變遷中,舊社會逐漸解體,而新的社會秩序尚未建立,文化的整體性遂暫時消失,直到社會重建的過程完成後才能恢復。這種整個社會制度及價值等等完全解體的現象,古人稱之爲「滄海橫流」。在清末滄海橫流的大變局大亂局中,智識份子苦澀而悲憤的心靈,卻往往流失在對時勢無可奈何的慨嘆上。因爲:他們洞矚過去與未來,深知在一個文化變遷的社會中,應如何重建社會秩序與社會價值;他們希望能有所作爲,也認爲應有所作爲。但客觀的環境與條件又每每不能與他們配合,甚至形成一種阻力,逼得他們不能或不敢有所作爲。於是,在沉重的使命感的摧折下,他們只能忍受自我内在的煎熬,在沉默的一旁,靜看這個古老而衰敗的大帝國一步步邁向死亡。像夕陽的餘暉一樣,這殘存的光影,只在他們寒澀的心田上,投射下一縷縷凄涼黯淡。這,這就是清末知識份子一種普遍的沉哀,一種「寒蕪落日」的集體意識或象徵!
這闋哀歌,收錄在夏敬觀的「忍古樓詞話」中,記民初這位著名的大使一生心迹事業甚詳,一種才人傷逝之戚,躍然紙上。詞作於日本一再發動侵華時,是以數語悵楚悲涼,寫出一個無可奈何的時代裏,一份無可奈何的沉哀。
有關這些文學與學術上曲曲折折的内容和評價問題,我們不擬多談;在此,我們只是粗陋地勾勒出他的歷史形相,並說明其歷史地位而已。對這樣一位充滿學術內涵的大使,我們有着太多的嘆惋和慶幸,看看他「生亦有涯詩作史」的宣言,再細思趙甌北那沉痛的調吟:「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語便工」,冷然囘眸,橫流滄海,苦難的中國,卻還在幽漆寂寞的角落裏彳亍蹣跚,對它,我們究竟又應有多少悲喜?當此涼夜,請讓一壁礙澀的風聲裹住我沉思的寂寞吧!
事實上,清廷能毁人之書,不能杜人之口、更不能遏阻潰離的人心,維新與立憲相繼失敗後,革命終於成功了。這時汪氏正任民政部右參議,民國成立後卽被選爲國會議員,是「進步黨」領袖之一。口才極佳,論議犀銳。袁世凱忌憚他的鋒芒,調駐比利時公使,帝制時召回,希望他也能勸進,不料他卻向袁氏說:「當爲華盛頓,勿作拿破崙」!兜頭一棍,敲得袁氏大爲不悅,只好再調瑞士,先後在歐洲十二年。民國十三年日本大地震後,又www.hetubook.com.com往日本任駐日公使,至萬寶山事件發生後才回國,折衝樽俎,前後也有八年之久。年五十六,卒於北平,星槎輾轉,半世漂泊至此也可算安息了。
在無數因果緣業中湊砌成長的近代史上,元和汪氏一族頗爲有名。他大伯父、父親和他都是拔貢出身,仲伯父汪鳳藻(芝房)曾任駐日欽差大臣,甲午戰爭時下旗歸國;父親汪鳳瀛(荃台)早年從學於大儒黃以周,通羣經大義,後隨鳳藥出使日本。返國後入湖北蔡毅若(錫勇)觀察幕,撰治文書。張之洞任兩湖總督時,堅請他督署洋務文案,辦理一切外交事宜。當時恰逢庚子之亂,東南自保,他在廣雅幕中獻替甚多。所以張氏返京任宰相時,卽擧薦他做長沙知府;民國成立後袁世凱又命他爲江蘇省省長,不願就;遂改聘爲總統府最高顧問。爲人沉毅、富膽識,平生有兩件事最可以看出他的器度和風節:知長沙府時,遭遇民變,形勢危急,閤府婦幼都已準備上吊他卻力排衆議,效郭子儀事,穿着朝服步行去和暴民商議,亂事也卽因此而平定。其後任袁氏總統府最高顧問時,力阻帝制,曾上書列擧七點理由,反覆勸阻,這就是有名的「七不可」文。原文已佚,僅見於他致籌安會楊度(晳子)一函中,所謂:「今國基甫定,人心粗安,而公等於民主政體下,忽倡君主立憲之異議,召亂速禍,誰爲厲階?」、「公等皆甚愛今之大總統者也,君子愛人以德,不聞以姑息!」……等等,至今誦之,猶覺神情飛動、大義凜然。這篇文章寫上去以後,袁氏敬他名望,並未爲難他,他也樂得鍵戶著書,作「救亡論」十九篇,希望從人心根本處救起,喚醒沉醉在新政體下的人們,認清憂患,齊爲中國而努力,提倡道德,改造社會,用心可謂深苦。由這幾件事看來,他與上位者爭的是公義,對百姓講的是理性與和平,不卑不亢,但也充份表現了一個知識份子身處亂世的氣度與悲哀,他除了寫些文章喚醒人們的良知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
前已說過,他著有揚雄「法言義疏」且早年專力於文字訓詁,造詣湛深,寫過「轉注說」,反對戴震段玉裁四體二用之說,認爲六書皆造字之法,以改字爲造字是轉注,以舊字表新意是假借,前者如老轉爲考、孝、耋、耆、耄、壽,後者如以原來鳥棲爲西的西字代表西方之西——這種講法不但前無古人,也和當時國學大師章太炎迥異,太炎曾與汪氏辯論過古音,他的學生黃侃、錢玄同也和汪氏多次討論商榷。因爲他精通日韓英法梵文,並具有現代語音學知識,利用佛經及各民族語音現象疏釋古音,所以能開創前人所未有的領域,著名的「歌戈魚虞模古讀考」卽是顯例。經歷了清儒三百年來孳孳不倦研究的古音學,要到他手上才開始突破,因爲他除了分部以外,更解決了發音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正是段玉裁等人終身大惑不解的(段氏能分析「支脂之」三韻不同類,但卻不能知道它們的音讀,晚年寫信問江晉三說:「足下能知其所以分乎?僕老老,倘得聞而死,豈非大幸?」汪榮實所作的工作卽是在說明分類的所以然,和段氏等人純粹的語言現象分析不盡相同)。
這些象徵與意識,具體地表現在師夷長和*圖*書技以制夷、中體西用、維新、立憲、革命等一連串行動中;也表現在小說、戲曲、詩歌和論述裏,汪榮寳「清史講義」預測淸室將亡卽是一個實例。所謂「魚爛亡梁君莫嘆,中原堂奧有人窺」「八道河山擅海隅,坐看寒日下平蕪」(三韓),寫的正是這種落日哀感,和梁啓超在光緒廿八年發表的「新中國未來記」意義相同,也和「老殘遊記」裏有關三元甲子和南拳北革這類預言性質相仿。這些知識份子一方面懷抱着滿腔熱血,無奈地看着這個帝國投入死亡的深淵(他們稱之爲「虞淵墜日」);並爲原有文化的失落而眷戀、悲傷。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充滿着悲願爲那含有無窮希望的明天而努力。生活在這樣一個夾隙中,他們爲此而矛盾、而痛苦、而又喜悅異常!呵呵!斜陽黯淡,風物淒其,人世之悲喜,竟如此壯烈而多姿——「上尊賜酒餘酣在,已是虞淵日盡時」(希馬出示先德文公詩集因題)!
汪氏師友中頗多遺老遺少,如鄭海藏陳寳琛等都是,但他也與譚延闓等人時相往還,因此他的整個思想內容必須配合著這整個社會與人物背景來看才有意義,例如他對同治光緒二朝士大夫清流朝議十分不滿:「作史頗傷元祐事」「側聞談紹述,門戶儻休爭」(恭送景皇帝梓宮奉移梁格莊述德抒哀)和黃秋岳「花隨人聖盦隨筆」合看才能深刻地感知其來源、經過與影響;推而遠之,像「老殘遊記」裏痛述誤事之清官這類思想也才能密探其根源。又如他對立憲的看法,常可和汪穰卿的議論合看;書法有一部份與張佩綸相似;文學觀和劉師培相同……等等,都可看出一個大時代中人文活動及人文精神相互烘托影響的實況。然而在這種狀況裏,汪氏最突出的一點是:他對宇宙家國社會有一全盤而系統的認知,這在他「新爾雅」一書裏可以看到。此書體例實仿英法的百科全書,與爾雅原書不同,分成釋政、法、計、教育、羣、名、幾何、天、地、格致、化、生理、動物、植物等十四項,體大思精,推論和定義都很嚴謹,在當時算是難能可貴的了。至於文學方面,理論上他仍依循阮元「文言說」的講法,並與當時常熟嘉興之間競行駢儷的風氣有關,認爲駢文是文章正宗;創作上則效法汪中(容甫)以追六朝,采藻絢爛,極負盛名,例如章太炎就曾稱讚它是當代第一,可以知其造詣。詩更是功力深厚,寄意比興,深得李商隱神髓。玉谿生詩集一册,他可以倒背如流,所以他的集句義山詩也是近代第一,「思玄堂詩」中有「楚雨集」集義山詩七十五首,天孫織錦,精巧渾成,而暗寓清末民國間時事,如「玄武湖中玉漏催,瑤池阿母綺窗開。荔枝盧橘沾恩幸,玉液瓊蘇作壽杯。貝闕夜移鯨失色,星橋橫過鵲飛同。君王曉坐金鑾殿,哀痛天書近已裁」,指太后視事,用榮祿等,下詔捕康梁;「迴望高城落曉河,風光今日兩蹉跎;金鑾不問殘燈事,玉闕猶分下苑波。靑塚路邊南雁盡,碧松根下伏苓多。鄂君悵望舟中夜,一夜將愁向敗荷」,咏光緒被囚於瀛臺……。對於這些詩作,我們不但要注意全詩的眞實性及其文句在歷史背景中的正確意義,更應分析其藝術「形式」(Form)之存在問題,找出其組織結構與內在意義間的關https://m.hetubook.com.com聯,並爲他轉化舊有經驗文句以發展其主題、傳達其意義而喝采。那是種高度語言秩序的重組與創造性想像(Creative imagination)的完成。客觀地說,他的詩固然是第一流的傑作,但決不能超過陳散原鄭海藏;然而集句一體,恐怕眞是冠絕時賢呢!
汪榮寶生長在這樣一個學術與外交世家中,所受的教育和薰染當然很大,所謂「幼承庭誥,長遊大師之門」(初刻法言疏證序),確非虛語。
龍楡生「聞汪袞父下世傷逝木蘭花慢」詞:「未辦埋憂地,愴身世。戀斜陽,算抗疏功名,籌邊帷幄,幾費周章;滄桑,須臾變景,待彎弓誰與射天狼?萬里星槎浩渺,五更塵夢淒涼!徜祥,去國總傷,調苦賞音亡。縱湖山信美,琴書自樂,滿鬢星霜;倉皇,海東雲起,話草玄心事劇荒唐。回首河山易色,可能一瞑同忘!」
帶著自傷與失望,他揮別醜陋的帝制鬧劇,遠赴瑞士,一面養病一面辦外交,並辛勤地箋注揚雄「法言」。他原來煙癮很大,每天要抽五十根,導致肺病吐血,從此煙酒不沾。在此養病時寫下了許多詩篇,從清末海運大通以來,域外詩成了傳統詩裏最新的發展,但康有爲、陳寶琛、黃公度等人的域外詩多以雜懷和遊歷爲内容,他卻頗有些與當地政治情勢有關的作品;赴日以後,則以與當地政教名流唱和者爲多,深入日本政黨之中,因此在他任內辦理外交的成績最爲可觀。——或許這也是一種緣數吧,在他伯父駐日三十年後,他也駐日,再三十年後,哲嗣汪公紀先生又任駐日代表團公使副團長。公紀先生是相信命數的,不知這也有命否?
在清室遜位民國肇興這個當口上,他還捲入一場歷史疑案中:最早,汪精衛謀炸攝政王載灃,榮寶曾勸肅王善耆替其緩頰;辛亥革命成功後,南北議和,他又奉命接待南方使節;後來隆裕太后的退位詔,據說也是出自他的手筆。但此事各家記載頗有異同,梁士詔年譜說:「原文係由南中將稿電來,該稿乃張季直手筆,後經袁左右增加授彼全權一筆而發表。末三語爲天津某鉅公(指徐世昌)所擬」,陳叔通雜憶二十首序則說:「退位詔推張謇起草,武進劉垣代擬,世凱修改,徐世昌、汪榮寶、張一麐參加潤色」。大抵汪氏曾參與修改確是事實,因爲他在民初與袁世凱關係十分密切,與他兒子袁寒雲也頗有交往,但他對袁氏畢竟失望了,就像揚雄對王莽的失望一樣,他自署「思玄堂」思揚雄之太玄,也因此而自傷。
這種預測淸室將亡而又努力爲中國求出路的心態,可用他一首詩來說明:「神州風雨方如晦,帝闕星辰只自高;曾向海天觀日出,盪胸雲海意逾豪!」——在風雨如晦中,他望到了光明,那就是一個新興的民主國:中華民國。
這個汪袞甫,名榮寶,小字夢珊,據說他出生時,母親夢到有人拿一把珊瑚剪刀給他,所以又取此名。不管這個傳說是否可信;他後半生的事業與成就,都奠基於家庭(一個文學外交世家)則無可疑。——這畢竟仍是一種「夙緣」。
據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中說:汪鳳瀛有子八人:榮寳、樂寶、東寳、楚寳、楨寶、椿寶、松寶、相寶。女二,長嫁陳三立子衡恪、次嫁何元翰(記元和汪氏父m.hetubook.com.com子)這點似乎有誤:榮寶只有兄弟三人,但因爲是大排行的關係,他排行第三;那著名的汪東(旭初)雖是三弟,排行卻是第八。汪東是章太炎的得意門生,號稱「東王」是章氏門下五王之一。詩詞書畫無不精擅,任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多年,有「夢秋詞」一卷。汪榮寶則是黃以周的學生,十九歲就被選爲拔貢,朝考籤分兵部,眞是少年意氣、頭角崢嶸。庚子八國聯軍入京後,他南下上海,進了南洋公學,再赴日本修習法律,「新爾雅」一書卽撰於此時。在日本曾多次與 國父及章太炎等人來往,革命學生組抗俄義勇軍,他也參加過。因有革命嫌疑,被清廷強迫返國,任譯學館教席,開始寫「清史講義」。講義裏對清廷的命運極表悲觀,末一章甚至有清亡的預言。這不僅在史學界是個創例,也使清廷大爲惱火,他的哲嗣汪公紀先生在重印講義前記中曾說:此書「痛陳時弊,語觸忌諱,付印成書之際,雖已截去其末,然猶爲間者擧發。清廷禁其書,並將興獄。差幸民國奠定,得免於禍,然刊書已俱毁矣。時……於厨下焚稿未畢,而偵騎已入書齋,其間猶不能容髮」。這具有戲劇性的一幕,展示的是一個學術價值在政治因素下遭到摧殘的實例!
從這種心態和認知出發,他基本情感上雖和一般清末遺老一樣,傾向於德宗皇帝(光緒),但卻和遺老們頑固地擁護已死去的文物制度的態度截然不同。他在戊戌以前即已有了必須改革維新的認識,庚子以後又致力於立憲的推行,民國成立後,他更深入議會,草創中華民國第一次憲法。這些,都可說明他眞正的立場和理想所在。他雖和梁啓超一樣,都希望能在光緒皇帝手上重整中華聲威、完成文化整合的工作;但對舊社會或舊勢力所造成的阻力,他卻有太多的憤懣。因此,他雖有「神州戮力寧無策?何至氾濫學晉賢」(與同舘諸公集陶然亭)的豪情壯語,卻終不免在現實人力之無可奈何中寫下「廊廟卽今多柱石,吾儕過作杞人憂」這類深刻的反諷(irony)。這種反諷除了表示事與願違之外,還蘊含着與文字背反的意義,是種憐恤的痛恨,譬如戊戌政變明明是慈禧要奪回光緒政權的宮闈鬪爭,光緒失敗,慘遭幽閉,最後雙雙以暴斃作結,一齣人間慘劇,造成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無可彌縫的創痕,而他偏要說:「兩宮極慈孝,四海妄驚猜!」(有感戊戌)、「漢家自有家人語,安用春秋治太平!」(重有感之五),什麼是家人語呢?就是黃老之術,他反用三則漢代典故,表達出強烈的痛恨與諷刺,諷刺一般朝臣只想因循苟安爲自己打算,不願也不肯爲天下百姓及國家的前途着想,意存言外,含蓄窈眇。汪榮寶「思玄堂詩」經常用這種手法來表現它的藝術趣味,范肯堂會稱讚這兩組詩:「袞甫眞後輩之奇才也!戊戌之變作者多矣,此八首亦屬辭比事,而有清雋之氣,遂覺情韻不匱,聲音動人」,范氏是被陳散原推譽爲宋代以後第一的大詩人,他的話當然有客觀的評價意義,但有關反諷這點卻還沒有說明。
馬林諾斯基在「科學的文化論」裏說:「文化是由一部份自律的和一部份平列的制度共同組成的整體」,就一般文化通則而言,自律的與平列的(Autonomous and https://m.hetubook.com.comco-ordinated)這兩個形容詞確能說明文化整體中內在協調的眞相。在文化變遷的過程裏,要重新建立新社會秩序,非經由對這些自律的和平列的制度重加研究與建立不可。汪榮寶由訓詁文字之學轉而赴日學習法律,卽是爲了要適應這個需要,收在他手錄的「金薤琳琅齋文存」裏的一些文獻如「修訂法律大臣編纂現行刑律刪除總目議」、「德宗景皇帝升祔禮議」、「論趙啟霖請緩改外省官制摺」、「論都察院不可改爲下議院摺」等等,都可以看出他努力的成績。他曾抨擊當時朝廷:「舍一切法制不談,而漫然以『正本清源』四字爲搪塞之語,試問其所謂正本清源之策果安在耶?」因此,他的改革方法是:從立法與制度入手,法制不立,人事當然無法整全,在一個喪失了秩序與依憑的社會裏,更何效率可言?但制度本身亦不是最終的目的:「釐定官制,不過預備立憲之初步,一切改革之事,方以此始,非謂一切改革之事,遂以此終也。以吏治之弊,不僅在官制,而尤在居官之人。是故廓清積弊之道,亦不僅在改革官制,而尤在改革官人之法」。所謂官人之法包括官吏的選用及官吏的監督兩方面,前者他力斥科擧帖括之學,強調民情和公論;後者則仍從制度之建立來掌握,譬如他所主張的司法獨立和地方自治卽是。他露骨地說:「此而不行,則所謂立憲,所謂預備者,皆虛語耳」!當時清廷命他草憲,他也認爲這正可施展他的抱負,所以有「指掌與誰談赤縣?探懷容我問青冥」(奉詔草憲與李家駒侍郎登泰山宿後石隐七日屬稿而還)的快語,但清廷又何嘗眞心立憲呢?徒然落得一聲「太平妄意堪文致,官禮終須有本原,盡道當時新法誤,誰知新法是陳言」(與仲仁追論舊事)的長嘆而已!
當然,這類技巧的提出和運用,來自實際政治上的顧忌,但和威同以來公羊學派、常州詞學和李義山詩流行的學術趨勢也大有關係,此處不能細談。汪氏詩學義山,神形畢肖,因此他也繼承了義山那種隱辭譎指、環甓託喩的作風,表面上寫的是金雕玉砌、美人香草,事實上卻和國家大事或國際時勢有關。時過境遷之後,至今已不太容易知道他每一首詩眞正的意圖和指喩(聽說周棄子先生每首都能作鄉箋,尚未當面請教),但其流露出的深心熱情卻是每個人都能眞切領受得到的。他在北平時,曾與張鴻(隱南)等人合組詩社,仿宋人楊億「西崑酬唱集」之例,刊行「西博酬唱集」專學義山,序中所謂:「滄海橫流,怨航人之無檝;風雨如晦,懼膠喈之寡儔,於是撰錄某篇,都爲一集,側身天地,應以寫其沉哀!」足可說明這種心境和内容。首二句卽可和「老殘遊記」第一囘「風能鼓浪,到處可危」裏形容中國是一艘風雨中無舵的破船的情形合看,這種「橫流失楫難爲濟」(贈郭春楡宗伯)的悲哀,正是構成他希望從制度本身來拯救中國、爲中國開拓新機運的主要動力。換言之,這是他提供給中國的一個「楫」!
憂樂關天下,興亡繫匹夫;
橫流今在眼,望古獨踟蹰。
——汪榮寶・修禊日集范文正顧亭林祠
橫流今在眼,望古獨踟蹰。
——汪榮寶・修禊日集范文正顧亭林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