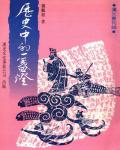二輯
雜記周作人
這還是單就文章上說,若就其内容而言,有些今日看來固屬平常,五六十年前卻是驚天動地的偉論,像弗洛依德的性心理學、傅萊則的神話人類學……,知堂都有推介之功;許多古籍,也靠着他的再評價與介紹,才能喚起注意。他文章之大抄特抄中外著作,不僅作者引爲得意,他的朋友如錢玄同也頗爲贊許,原因或卽在此。他的態度,可以「秉燭談」中論黃公度人境廬詩草的一段話來說:「中國應做的文化研究事業實在太多,都須要切實的資本與才力,關於黃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卽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因爲假如這些事略爲弄得有點頭緒,我們外行人也就早可安份守己,不必多白費氣力來說這些閑話了」。語雖謙退,熱情與焦慮可以想見。其學與其交之雜,不正由於要做的文化研究事業太多了麽?
原因或許有二:一是周作人浪漫的傾向、爲藝術而藝術的主張,頗爲民國十三年以後爲人生而藝術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及創造社等革命文學派所詬病,例如馮乃超便抨擊魯迅「無聊賴地跟着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話」既是非我族類,自將鳴鼓而攻之。但此事尙非主要原因,因爲此時左翼作家對周家兩兄弟,正一律圍剿濫啃,「阿Q正傳」也被指爲嘲笑農民,被罵個半死。不久魯迅受不了了,態度開始轉變,於是迅速被封爲左翼作家聯盟盟主,「阿Q正傳」也就成了普羅文學的代表作,阿Q則是中國普羅階級的代表。如此這般,惹得周作人大爲不滿,而左翼也因爲他頑固不肯轉向而動怒了,二者相激,遂成水火,周乃於廿四年二月寫了一篇「阿Q的舊賬云」:
魯迅
這番宏論,我亦深知,但我之不佩服,也未嘗沒有原因。大抵人對渴望一見,而又不經見的東西,總有點逾份的期望。就像讀「牡丹亭」、聽「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女孩一樣,遙想作者,必是文采風流、翩翩如玉樹之臨風;等到乍然驟見湯顯祖、劉半農,則鮮有不羞憤失望、大嘆「教我如何再想他」的。我們看五四乃至三十年代文學,多有此感,原不僅對苦茶庵主一人爲然。這本是我們自己的過失,怪不得作者。然而,就作者本身造詣來說,一般選集所錄,自是精金美玉全集則不免雜有若干泥沙;讀者若不一味諛美,對這些泥沙便https://www.hetubook.com.com不能視若無覩。何況,周氏以小品散文著名,但其文集卻不止於小品,像「夜讀抄」、「風雨談」、「瓜豆集」……裏許多文字,不是「殆同」書抄,而根本就是抄書。抄書的目的,或者是純在介紹、或者是藉以引申議論,雖有其意義,卻也並非絕詣,這是我所以不很佩服的原因。另外,純就小品文章來看,知堂早年的作品固然簡潔精粹,後期卻不免做作(他在「立春以前」後記中也承認「自己覺得處處還有技巧,這卽是做作」,可見此弊他也未嘗不知)。尤其是一種名士氣,往往夾纏於筆端,刻意表示自己是不求聞達、而語中又若唯恐旁人之不己知,如「藥味集」自序、玄同紀念等,都可算是惡札。不幸我初讀的,就是這些篇,難怪印象不佳。
廿五年,魯迅死後——這眞有趣——周又寫了「關於魯迅」和「魯迅的學問」二文,把左翼之利用魯迅,諡爲「吃烈士」。次日卽接到一封明信片,文曰:「魯迅先生死了!今天看見宇宙風廿八期所載下期新目預告,將有魯迅的學問一文發表。我想魯迅先生的學問,先生是不會完全懂得的,此事可不勞費神,且留待別些年輕人去做。若稿已告成,自可束之高閣,不必發表。此上祝好,武昌田上」。這封信太精采了,以致我們不想多加案語。不過,近來拜讀了一些大陸上的文史研究資料,對於周谷城、商承祚、胡厚宜、唐振常等人「英明領導有誰儔,革命精神貫五州,繼往開來爲黨慶,感恩圖報是吾求」的治學精神,往往因莫名其妙而大惑不解;對於張于、吳文祺等人講文學史小說史都要編扯魯迅嘉言的做法也難以理解。現在翻翻阿Q的舊賬,才得豁然貫通,眞是不亦快哉!
結尾
不過,論語不是也有「觀過知仁」的老話嗎?一位大作家,就算是缺點,也自有其意義、有其好處。拿抄書來說吧,他能在抄書中談文藝理論、談社會風氣、談性、談生活情趣、談西洋新知,乃至無所不談,而不至於枯燥無聊,一般人便很難辦到。既無掉書袋之弊,也覺得較純抒情說理、而腹笥甚儉者有趣。其中最有意思的,則是論學。知堂所學甚雜,對兒童教育、人類學(包括宗教、神話、性)、生物學、民俗學等方面和-圖-書,雖不好說他有多深的造詣,但卻是我所讀過這方面寫得最好的。清言娓娓,在愷悌寬厚中雜有許多詼詭的趣味。這一層,正是一般論知堂的人所不知的。我常恨目前講學問的人,著述必用一種森冷艱澀的文體,讀來幾無生人之趣;而一般作家,又似乎離學問遠了些。知堂便不如此,其文不爭聲色,瀏然而清、淡然而遠,令人在不知不覺中,得着許多知識的啓迪、性情的涵養。當時學者,如朱光潛之論詩、宗白華之談美,也都有此手段,何以如今反不可多得了呢?
我對知堂老人抗戰後的事迹不甚明白,但在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對中日關係的見解,實與乃師無異。所謂逢蒙射羿,日本之欲「進出」中國者久矣,凡有眼睛者皆能見之,周氏自不例外。以小品論,我最喜歡他的「談虎集」,其中便有許多對日本的批評,尤其是諷嘲順天時報。順天時報,是日本在北平所辦的中文報,專以誣蔑中國、宣揚日本德化爲職志。順天者,不知何意,或許是昭識中國人必須順從天皇吧。周氏曰:「日本漢字新聞的主張,無一不與我輩正相反:我們覺得於中國有利的事,他們無不反對;而有害於中國者則鼓吹不遺餘力。我們不怪他這樣想,只是在我們眼前拿漢文來寫給我們看,那是我們所不可忍的。牠明明是寫給我們看的了,報上又聲聲口口很親熱地叫着『吾國』,而其觀點則全是日本人的。牠用了帝國的眼光,故意地來敎化我們,使潛移默化以進於一德同風之域。你在家裏坐着,每天會把那函授奴隸講義似的漢文報送來給你看,眞正巧妙極了。日本人對中國幸災樂禍,歷年來干涉內政、挑撥風潮,已經夠了;現今還要進一步,替中國來維持禮教、整頓風化、厲行文化侵略,這種陰險的手段,實在還在英國之上」。抄了這麼多,一來是說得痛快,二來亦足以表示他對中日關係的批評,偏重在文化方面。然而,周作人畢竟對日本尙有綺念,他仍希望日本會萬一良心發現,自動廢止順天時報;這與今日期待日本自動更正教科書的想法,一樣荒渺無稽。須知日本一向認爲中國是他「失去的領土」,奪回失土的方法,一是軍事、一是文化,而經濟不與焉。文化是與軍事互相配合的,透過教育與文化侵略,牠培植了無數野心家和遍布中國的日本
和*圖*書奴隸,早期的順天時報、現今的教科書,本質殊無二致。行走在臺北街頭,處處讓我們想起一九七六年非洲地區文化憲章草案上所說:在殖民地支配下,非洲社會的人逐漸喪失了個性、竄改非洲歷史,並逐漸以殖民地支配國的語言取代母語。隨着日本經濟而來的,是日本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殖民,才是最具支配力的,牠使我們逐漸忘記了牠吃人的狠相,而與之「親善」、與之「共存共榮」。竄改歷史,便是它要達成此一目的的一個小步驟,雖然做得拙了些,卻無損文化侵略之大業,因爲他將來還有更卑劣的手段。周作人說得好:「二十年來在中國面前現出的日本,全是一副吃人相,不但隋唐時代那種文化的交誼完全絕滅,就是甲午年的一刀一槍廝殺,也還痛快大方,覺得已不可得了。現在所有的幾乎全是卑鄙齷齪的方法,與其說是武士道,還不如說近於上海流氓的拆梢。固然該怨恨,卻尤值得我們輕蔑。——其實就是日本人自己也未嘗不明白這種做法太拙太腌臢了」(瓜豆集.談日本文化書)。甲午之後,即有順天時報;侵華之後,則有教科書修改案。後之視今,亦必猶今之視昔也。對付日本這些齷齪的技倆,從前我們可以抵制日貨、可以抗日,現在呢?我們的妓|女能不接日本淫客嗎?我們的饕餮能不吃日本料理嗎?我們的歌星能不唱中國的日本歌嗎?我們的商人能不走私錄影機嗎?我們的士紳能不說日語嗎?我們……。可見日本固然是愈來愈腌臢,我們也愈來愈窩囊了。周作人是「漢奸」尙能有此見解,我們既連漢奸也不如,只好說是「日奴」吧!苦茶
假如阿Q正傳本來並不是反動的、不是嘲笑農民的,還麼,當初那些批評家們羣起攻擊,何其太沒有眼睛?當初既然沒有眼睛,何以在作者轉變後眼睛忽然亮了?假如正唯是反動的攻擊正是應該,何以在作者轉變後就不攻擊,而且還恭維?——這阿Q一案的結論不外兩種:一是新興批評家之無眼識,一是批評家之不誠實。無眼識不過瞎說;不誠實則是有作用近於欺騙了。唯物史觀的文學批評本亦自成一家,在中國也不妨談談,但我希望大家先把上面所說的這筆爛汚賬算清了再說,前賬未清,免開尊口。
以上雖是幾粒老鼠屎,卻已足夠弄壞一鍋粥了,雖然https://m.hetubook.com.com那鍋粥本是好的。
魯迅與周作人都是章太炎在日本亡命時的學生,雖未名列章門四王,與章氏情份亦自不淺。章太炎是一代宗師,新文化運動中新舊兩派的主要角色,多是他的學生,如黃侃之復古、錢玄同之疑古是也。周氏兄弟與錢玄同交好,周作人甚至自號「疑今」,而其朋友中如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自序中也說對當代學者,「最感謝章太炎先生」,可見章的魅力。新文化運動後,章在上海主講國學,雖引得周作人等不甚愉快,對章的尊敬,其實並未稍減。魯迅曾說他會在東京民報社聽章氏講學,主要是因爲敬仰章的革命精神,但曹聚仁「魯迅評傳」、「文壇五十年」便多次指出魯迅文風及觀念,深受章太炎的影響;周作人對章的尊敬也至老不衰,提及太炎,必稱先生,太炎死後,他記章氏學梵文事,更指出章「博大精進的偉大氣象」。他論日本文化,時引孟子「逢蒙射羿」章,而這也恰好是章太炎最喜歡寫來送給日本人的。
魯迅之孫周令飛奔向自由的消息,在國内引起不小的震撼,巧的是友人不久前贈我一套周作人的文集,大家談周令飛、談魯迅,我倒想一談周令飛的叔公周作人。
日本
周作人文集中可談者甚多,但既講到此處,勢必再無心情談下去了。請讓我用幾句話做個總結:
朋友見我如此,便來勸慰,曰:「周的文章,以冲淡著名,如釅茶、如橄欖,須細細品味,才見眞趣;像你這樣,喏,把卷疾讀,又不寧定,哪能體會人家的好處?須是多讀幾遍,方知此人之享大名,是有道理的。」
或者這種印象,也只是印象而已,就像某些人不喜歡蓄鬍子的男士,未必是大鬍子長得醜。周氏與其兄魯迅,都有一把鬍子,其孫亦不例外,而這位周二鬍子,偏又自稱什麼苦茶庵老,這點是我所最不喜歡的。本來亭軒齋庵之名,皆一意境而已,文人之齋庵,尤多是印章上起造,取什麼庵名,也都無妨,但何苦稱爲苦茶庵呢?一來他未出家;二來他喜歡談性教育,而且談得極好;三則他根本自稱是正宗儒家;四他也不太吃苦茶。一位朋友爲庵名所誑,買了一包苦茶送他,他苦不堪言,只好拉出沈兼士來,說:「端透於今變澄澈,魚摸自古讀歌麻,眼前一例君須記,茶苦原來卽苦茶」。姑不論他取庵名時m•hetubook.com.com,不會有此聲韻學上的考慮(因爲對聲韻學,他是聽之茫然的,見苦茶隨筆頁一三一),卽茶苦爲苦茶之說,也未必可靠。因爲古無舌上音,故古音端透二紐,後來變出澄澈來,但魚模卻不一定古讀歌;廣韻魚模兩韻,古韻只與麻的一部份同部,而廣韻麻韻中差、加、蛇、蝸等字則與歌別爲一部。顏氏家訓書證篇又說:「詩云:『誰謂茶苦』,爾雅、毛詩傳並以荼苦藥也。又禮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卦驗玄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多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荼,乃是苦菜,爾雅釋木篇的「檟苦荼」才是茗茶。周作人曾在夜讀抄裏特地爲我們介紹過顏氏家訓,也在孔德學校講過顏氏家訓,而他對詩經草木,又有特殊深湛的研究,不知何以於此反而懵然,難道他所談,並不一定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嗎?
雜學
友人所贈的周作人文集,卷帙既多,讀來很費了點勁。周是五四時代的健將,也是小品文大家,文名藉甚,集中又有些從前已經拜讀過。但老實說,初看全集,卻不很佩服。「這是什麼散文嘛?」我心裏老這樣嘀咕。
這種態度,當然與其文風頗有關係。許多人都說他的文章冲淡,甚至把他和魯迅比做兩種極端,一亢猛、一歛退,一如匕首投槍、一如釅茶苦茗。其實他也大有憤慨,苦茶隨筆頁二九一說「從來我寫文章就都寫不好,這毛病便在太積極。我們到底是一介中國人,對於本國種種事情未免關心,這原不是壞事,但是沒有實力,奈何不得社會一分毫,結果只好學聖人去寫文章出出鳥氣」、「我不想寫祭器文學,因爲不相信文學是有用的;但是總有憤慨,做文章說話,知道不是畫符唸咒,會有一個霹靂打死妖怪的效果;不過說說也好,聊以出出悶氣」。正是這種心情,所以他的說話便仍是講理、而非罵街。但是,這種態度基本上與魯迅亦無不同,魯迅「狂人日記」中的主人翁,看到中國典籍中字裏行間都是吃人吃人,因而要叫「救救孩子」,不也是周作人人道主義與兒童教育的同調嗎?何以他竟不見容於左翼普羅文學一系呢?
我不諱言,我們有時候也會有點自負之意,但讀古今人文集,卻是沮喪的時候多些。他們的缺點,我也能夠甄別,而他們的好處:學問、氣度、文采、見識,則不是我所能到的。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