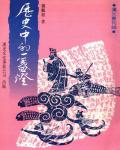二輯
評錢鍾書的「管錐編」
是的,乍讀此書時,我也不免有些失望,在寫給友人的信上我曾提到:「此書義雖精奧,讀之乃有『彼可取而代之』之感;卽論文辭,則僕雖不敏,竊謂過之矣!」——當然有人會笑我是「今之少年喜謗前輩」,但事實上,明白表示失望的不止我一人,王幼華兄師曾向我抱怨:「大陸上許多學者無書可看,而錢鍾書坐擁書城,三十年來居然還只有這種成績,實在……」失望的理由大抵可分幾方面來談:第一、錢氏似乎沒有弄清楚「研究對象」這個問題,當他標明老子王弼注、史記會注考證、楚辭洪興祖補注等等時,他要研究的究竟是什麼呢?須知徐復觀寫「論史記」是以史記爲研究對象、魯實先寫「史記會注考證駁議」則是以瀧川資言的書爲對象。我寫「周易正義研究」研究的就是正義而非易經。其理至明,而錢氏誤混之,既非論史記會注考證,論史記則所讀與所參考的又不僅爲會注考證,豈非進退失據?其次,正如上文所說,他只是藉着經史子書的某些文字,來抒發一些他對文學或人情世態的看法,並未對該書做一完整的了解或認識。有人說這是因爲它本身係一劄記性質,不能以此要求來衡量;然而意識決定形式,劄記的形式,未嘗不可以表達一通盤的認識,例如錢穆的「先秦諸子繫年」,基本上也只是一種劄記,但條辨縷析之中,未嘗不條理秩如,故其決定之因素,乃在乎作者願不願意這樣做或能不能這樣做而已。舉例言之,頁四一三論老子,擧白居易讀老子詩爲證,譏老聃自我矛盾;頁四五七卻又說「白居易嘗學佛參禪,自作讀神經詩解道:『言下忘言一時了』,卻於老子少見多怪,何知二五而不曉一十哉」?論學只在枝枝節節處逞其博辯,而不顧理之安否或全書義理之實然,乃有如是者!像這種地方,難道也要我隨聲喝采嗎?
其他書中可資商榷處也不少,例如頁六十論毛詩正義:「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或色美而材薄、或交惡而質,唯善賈別之。取彼歌謠,播爲音樂,或詞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竟以爲是說言可矯而聲難矯,顯然誤解孔疏文義。頁四〇八以陶淵明「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來解釋黃山谷的「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品)和陸機文賦「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也有問題。其他如頁四一七以佛家中道義解董仲舒陰|道不能獨行和陽主陰輔之說;頁四三六謂韓非六反篇:「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是入室操戈,攻擊老子之學言行不能相符;頁四六〇擧韓偓詩:「圖霸未能知盜道,飾非唯欲害仁人」認爲這卽是「夏竦何曾聳,韓琦未必奇」這類一字雙關的用法;……都不甚恰當。頁九七九論王聖美「右文說」以爲:「祇是王安石字說之推波引緒」,實則右文說與荆公字說迥異,故宜和書譜卷六云:「王子韶字聖美,浙右人」,方王安石以字書行於天下,而子韶亦作字解二十卷,大抵與王安石m.hetubook.com.com之書相違背,故其解藏於家而不傳,張世南「宦遊紀聞」亦貶荆公字說而主右文;同時,右文說非以會意解字,錢氏所謂:「漢人以會意解字之濫,蓋不止讖緯,且已開王聖美類左義右之說」云云,實係誤會。又、頁九四七論好音以悲哀爲主,云:「奏樂以生悲爲善音,聽樂以能悲爲知音……隋書三節尤耐思索;音樂志上陳後主『造黃鹵留及玉樹后|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綺艷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夫佻艷之曲,名曰無愁而功在有淚,是以傷心爲樂趣矣」,按:通鑑唐紀八,太宗貞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卽擧玉樹后|庭花等曲,說它們「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太宗不以爲然,反駁道:「今二曲俱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足證玉樹后|庭花等曲本身並不爲悲。又,頁一一一二論王羲之蘭亭敍句意重複及右軍斥道家而信方士一節,頗恣博辯,然於昭明文選不收此序之故,了無論案,又忽略了一項基本問題,即清代李文田所提出:蘭亭敍「夫人之相與」以下,係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者(汪中舊藏定武蘭亭)此一問題不先解決,則錢氏所論,纍纍三四千言皆戲論而已。……
以上係對這部鉅著作個極簡略的說明,一些校對上的小問題就不多談了。
最後,有個問題值得一提:錢鍾書是來過臺灣再投共返回大陸的人,因此,早先我看到高陽先生論管錐編是刺毛偽政權的文章時,只覺得可笑。但如今我將全書看完,卻被書底流動著的悲哀震忧了。他極端嚮往自由(對大陸崇尙法家,反復鬥爭的現象深致不滿):
事實上博學不須如此炫耀,若眞要旁徵博引,錢氏縱使博學,又哪引得完呢?記得諾曼・福特的話嗎?「不要賣弄你的所知,因爲它常少得可憐」!例如論廣記中「維揚十友」童兒爲千歲人蔘一節,卽漏引西遊記人蔘果故事;論詩經「君子于役」瞑色起愁一節,漏引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小詞有燒殘絳燭淚成痕,街鼓破黃昏之語」、陳世崇隨隱漫錄:「王晉卿云: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劉招山云:一般時節兩消魂,樓上黃昏、馬上黃昏。趙德麟云: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個黃昏」……,我是否也可以笑錢氏「眼前典故,尙且忘卻」呢?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論學原不應如此,文章又豈能這樣寫法?
去年春天,錢鍾書隨中共「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美,轟動一時,此間報章雜誌報導至爲詳盡,尤其夏志清先生的「重會錢鍾書紀實」長文,更透露了三十年來錢氏治學的成績:「管錐編」即將出版的消息,並對此書推崇備至,他說:
除此之外,錢著還有兩個重要的缺陷:一是未利用近年新出土的資料,二是對西方新近學術發展十分陌生。關於前者,中共竊據大陸以來學術上唯一值得炫耀的,就是新出土的祖宗遺產,研究也以這方面最爲豐碩,但錢氏居然完全不曾運用,眞教人詫異。例如他論孫子兵法,依然沿用姚鼐等人的和圖書說法,認爲今本孫子十三篇是戰國時偽書,全不理會山東臨沂銀雀山所出土竹簡孫子兵法及孫臏兵法的考古結果。論唐龍興觀碑子老子,認爲碑本刪去許多語助詞以致語氣迥殊,可以作爲鑑別年代先後之標準;論點很精,但他如稍稍注意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所出的帛書老子,就更可以看出這個特色了。這兩個例子說明了:無論判斷之正訛,不善利用新出資料都會構成顯著的缺陷,而這些缺陷也正顯示了他對這方面的知識十分陌生。其次他對西方近代學術之發展亦不甚瞭解,這可能與他所身處的封閉式社會有關,他所知道的西方哲學思潮,只到黑格爾,馬克斯、恩格斯而止,再下來就比較隔閡了;文學思潮亦然,近代新興的研究法如新批評、神話原型批評,結構主義……等等,在他書中均找不到痕迹。對西方學術,他所做的側重於古典文獻之類比研究(analogy studies),僅止於點出中西某一現象或學理之異同,既無意用西方理論來處理中國問題,用中國理論去闡釋西方現象;也無意從類同的歸納研究中尋出共通性以建立通則。就連「談藝錄」裏論G. M. H. Pkins的Inscape與Tancre'de de Visan的Paysage introspectip(內景)的情形,管錐編都不曾有之,他自己說:
只是在談完古籍上的問題之後,舉一些類似的義理、文例或事件來補助說明而已。善悟者當然可以從他禪家機鋒似的文辭裏,領會到許多中西比較會通的大道理,他本書倒沒有爲此特創局面的野心或意圖。
「於二西之書,聊擧契同,以明流別,匹似辨識草木之羣分而類聚爾。非為調停,亦異攀附。……傾蓋如故,天涯比鄰,切勿須強為撮合;卽撮合乎,亦如宋玉所謂『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也。」(頁四六五)
「管錐編」的寫作方式和他使用的治學方法,與談藝錄相同,許多人未看清這一點,遂以爲談藝錄論唐以後,本書論唐以前,性質與材料完全不同;且既研究易經左傳這類書,則必屬漢學訓詁考據之作,夏志清卽是如此,羅靑「錢著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讀後」也說:「他反對小學家見樹不見林的愚昧,今天竟也寫起文字訓詁的『管錐篇』來」。不但誤編爲篇,甚且對錢著的性質完全懵然。按:錢氏自己說:「說者見經、子古籍,便端肅莊敬,鞠躬屏息,渾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戲三味耳!」(老子王弼注卷第十七則)換言之,他是在研究經史,但其研究方式和着眼點,僅在經史子的文章意味而已。雖然也有一小部份義理,但只是些人情世故的體認和極淺顯的哲學雋語;至於那一點點微不足道的訓詁,更是無關宏旨,不過是藉着訓詁來抒發一下他的文學見解罷了。錢氏一生爲學,均是這種態度,民國三十年刊行的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卽說:「在非文學書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舊衣服,忽然在夾袋裏發現了用剩的鈔票和角子。雖是份內的東西,卻有種意外的喜和_圖_書悅」(釋文盲)!看來他總是在尋找喜悅,所以管錐編裏也一再呼籲「詩須作詩讀」!許多人會因爲他研究易經史記等書,卻大談修辭法而感到不耐,認爲總是在文字的枝枝節節處打轉,但事實上錢氏的興趣也僅在於此,並爲我們找到了不少舊角子。因此,若說「管錐編」卽是續談藝錄,似乎也沒什麼不可以(談藝錄本來就包含有詩、文和一些義理),因爲它們不但在寫作方式和性質上相同,其論點有些也可相互參證,例如論列子卷第六則的心手相應;論周易正義卷第十六則、論全晉文第一〇六則之雪山比象等等均是。三十年來,錢鍾書進步得並不多啊!
當然,由於每個人認知層面的局限,一部百萬言的大書,有些瑕疵實屬難免、也才正常。以一人之力而欲兼通如許多的問題,本無可能,讀其書者,應知其優劣得失,不可矮人看場,爲之妄嘆妄贊才是!以上所論,雖多貶抑,但事實上錢鍾書的洞察力還是很可佩的,我去年參加第一屆古典文學會議時,鄭明娳提出「孫行者與猿猴故事」論文,會中大家對猿猴性淫的問題討論爲踴躍,而簽書頁五四七卽曾論及猿猴故事的演變,論點與鄭文大抵相同,並擧莎士比亞劇本來說明猿猴性淫,可謂不謀而合了。
「管錐編」我只看到三册,包括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史記會注考證、老子王弼注、列子張湛注、焦氏易林、楚辭洪興祖補注、太平廣記及嚴可均所輯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的一部份,共六四四則讀書記(一則有時包含有好幾條相關的見解,其中廣記與嚴輯佔了一半以上)才劇志大、聞見博雜,是近些年來難得一見的大書。夏志清先生之推譽雖不免逾量,但總還是一部相當值得參考的著作。
他一直是位傳奇性人物,在小說、散文之創作和古典文學研究上的成績,有目共覩。民國六十五年,類似蘇東坡海外誤傳死訊的情形,還引發了一場著名的論戰。論戰雖仍是不了了之,但其結果卻使得國內的文學批評在方法上或意識上有了更新的自覺認知;同時,他的大名,也隨之不脛而走。在此之前,國內知道他的人並不很多,三十年來,只有鄒文海在民國五十一年的傳記文學第一卷一期上寫過一篇「憶錢鍾書」。而王禮卿先生在參加論戰時也說他不曾讀過談藝錄。夏志清先生追念錢氏一文刊出當天,李正治兄恰在我家,談及此人此書;我當時雖已遍讀了他父親錢基博的著作,對他卻一無所知。正治回去,卽把談藝錄寄來給我,讀後大爲嘆服;其後又陸續讀完他所有的著作,包括李拔可(宣)「碩果亭重九酬唱集」裏所錄的幾首七律,氣味老蒼、不脫同光體格局。
「言性惡則為政主專制保守,言性善則政主自由進步。」(頁一一六六)
近幾年來,錢鍾書聲望日隆,大有睥睨寰宇之勢,這在當今文化界或學術界上說,都可算是一樁異數。
在這些從經史子籍中掘尋文學趣味的過程裏,他談得最多、最賣力的,是一字多義及比喩之有二柄亦有多邊,他有意借此建立一個有系統的條例,來m.hetubook.com.com處理許多文義上的問題。夏志清先生「紀實」一文中所引到的也正是他這方面的見解。然而,一字數訓或相反爲訓,自始卽爲訓詁學中人所盡知的常識,近人對這方面的研究,也早已超過錢氏太多;看看劉師培「古書疑義舉例補」(錢氏很看不起他)、林尹「訓詁學概要」或龍宇純、陳大齊諸先生的論文,即可知道夏志清先生的贊嘆,實是少所見而多所怪,見駱駝而曰馬腫背!當然,這並不是說錢氏所論毫無價值,至少他藉此通例來解釋一些文學現象和義理,前人就還很少做過同類的工作,例如全漢文卷第廿二論圓喩之多義、全三國文卷第十論字之多義與情之多緒等等,均極精采。因爲他是從語意學的觀點來討論這個問題,與乾嘉樸學一脈取徑不盡相同(我認爲他對這個問題的瞭解,係從黑格爾處得到啓發,而非從訓詁學上來。他向來看不起漢學家,而他自己的樸學根基也很淺,逕以直承鄭玄朱熹譽之,不但他消受不起,恐怕也非他所願哩)然而,所謂一字多義與譬喻之多義,都是語意學上的「一字一義之謬誤」。錢氏釐分爲二,始終未悟二者本爲一理,也是很令人奇怪的!
至於本書的文辭,據夏志清先生轉述錢鍾書語,自謂比「談藝錄」更爲古奧。可是,所謂古奧,不過是故爲詰屈和聒絮而已。刻意賣弄,文體極不雅飭,譬如楚辭卷第一論名詞有時可以顛倒、有時則不可以,理極淺顯,片言可決,他竟耗去了三百多字;書中所謂博學處,大多類此,且雜以戲謔,其實有許多是可以不必賣弄的,他的散文和小說也有這種毛病,在文學藝術上都是無法諱飾的缺點,而運用到文言文上看來則尤爲醜怪。
一字多義之外,互文或兼言等一類修辭學上的問題也談了不少,道理固然都是些老生常談,但早期的修辭學者偏重於從古書中歸納出各種條例,錢氏卻極善於運用這些條例回過頭來從事研究與實際批評,時有創獲(在修詞學上,他未建立新的條例,且運用的範圍很窄)。可是,這種利用修辭學的認知來處理古藉的方法發明處當然也只在文義字句上,因此,全書看起來,就像錢鍾書的一場舞蹈,對易經、史記、詩經、左傳、老子、列子等書,他只是禪家機鋒也似地一次又一次的「觸發」並以此觸發開始,作一番冗長的類比或推衍,並未對易經或史記等書本身進行什麼研究;清儒整理古籍,太苛細地膠滯在該書字句上,錢氏則又太不着題,只在該書某一文句上點一下就盪開了去,二者迥然不同,但其苛細繁碎地夾於文字句義之中則是一樣的。他機警地從一個問題跳到另一個問題,每個問題都是旁徵博引,但又都點到爲止,譬如「天命」是何等大的問題?他卻在論史記中閒閒幾筆帶過;於古人聚訟處,如列子之作者、孫子兵法等問題,卻又游移兩可,作騎牆語。一位普通的讀者當然會震懾於他的博聞彊記,但如果對他書中所提到的問題都有了解的讀者,則恐怕要要失望了呢!
「錢鍾書為古代典籍作訓詁義理方面的整理,直承鄭玄、朱熹諸大儒的傳https://m•hetubook•com•com統;同時他仍旁徵博引西方歷代哲理、文學名著,也給漢學打開了一個比較研究的新局面……今秋『管錐編』出版,雖然在中共大陸不可能有多少讀者,應該是漢學界、比較文學界所未逢的最大盛事。……」
頁六六三有一段文字也很可玩味,他假借「陶尹二君」裏一個想盡辦法逃避秦代苛政而卻無法逃脫的故事,點出生活在虐政之下人民的悲哀,是「躲了點鋼槍,撞見喪門劍」,我們知道毛澤東正以秦始皇自喩的。又、頁三〇六論史記「以暴易暴」,認爲這就是「易君而未革政,執政頻換而下民困苦不異於前,所變易者僅在上者之姓名已耳!」把以暴易暴解成易君而未革政,顯爲誤說,但這並不重要,要緊的是他爲什麼要這樣解釋!對於這些朝更夕改的執權者,他也有一段很精闢很哀傷的議論:詩「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傳云:「一日不見君,憂懼於讒矣」鄭箋則解爲:「獨學無友,故思之甚」。就詩義說,鄭箋解得較好,但錢氏偏偏依據毛傳鬯論了一段權臣不可輕易失權去位的大道理,「一旦去權,禍機不測」;這當是他屢見爲朝當權者,一旦失勢連豬狗都不如而發的感慨。錢鍾書如此直率,我倒擔心中共某些幹部會像亨利.米勒一樣,大叫:「滿腹古典經論的傢伙,是人類的死敵」呢!此書與談藝錄在引證資料方面有一重大差異,也可以爲我們提供這方面的訊息:管錐編引用了大量小說和俗語材料,可見這三十年來錢氏常以小說自遣,排煩解悶,同時共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型態也迫使他注意到那些人民日常生活的俗話,而這兩種情形都是以往錢氏所未有的。讀其書,論其世,他書中對世道人心的體察極爲深刻,且每每感慨繫之,實非無故。這眞是位飽經世變而仍頑強不屈的老頭啊!
文中他直稱錢氏爲「當代第一博學鴻儒」,認爲他在漢學上的造詣,連屈萬里亦不能與之相比。弄得國內人人翹首企盼,不啻大旱之望雲霓。今春,「管錐編」在此處也可以買到了,四五家出版商一窩蜂似地搶印,大家又不辨妍蚩地望招牌搶貨,整個過程,看來幾乎像是一場匆遽的鬧劇,許多人都和夏志清先生一樣,尚未細讀卽知道它是部金庫玉典,並視之爲枕中鴻寶。
與「談藝錄」一樣,本書溶有錢氏許多師友的心血和見解在內,序說:「命筆之時,數請益於周君振甫,小叩輒發大鳴,實歸不負虛往」周振甫是著名學者,曾著有「嚴復思想述評」談藝錄前精雅的目次及校讎也都是他做的,「管錐編」裏引用了一些他的議論,見地很高。錢鍾書論學,喜歡讓善,譬如「談藝錄」中許多見解與同光體詩法相同,他自己做同光體詩、所交往的也多半是同光體詩家(如序裏所提到的李拔可係鄭海藏記室、李證剛係沈寢叟弟子),但他書中卻常諷嘲同光體,「圍城」裏亦是如此,其實彼此詩論本無異同,開卷第一節論詩分唐宋乃風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別,卽與陳石遺弟子黃秋岳「花隨人聖盦摭憶」所持見解相類,其餘可以逆推。攘善如此,而竟對周振甫極爲禮敬,殆可想見其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