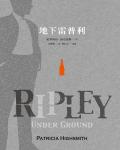十四
「老天!底下有人上吊。」
「混蛋。從奧利他就要收——」湯姆忍下了他要罵的話,連英語都不敢用。湯姆付了車錢。司機沒幫他們拿行李。
他們進了赫綠思的臥室。
「我好喜歡!」赫綠思說,給湯姆一個擁抱,在他臉頰上吻了一記。
湯姆覺得楓丹白露鎮是最好的選擇,楓丹白露宮就在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旁。克里斯看起來就像他實際的身分,一個來度假的高個子美國青年,不窮也不富,湯姆覺得他要找到便車去巴黎,應該不會有任何困難。
星期四上午平靜無事地過去,連一通電話都沒有,不過赫綠思打了電話給巴黎的三、四個人,其中一通是打到她父親在巴黎的辦公室。現在赫綠思穿著褪色的牛仔褲,赤腳在屋子裡活動。安奈特太太的《巴黎人報》裡今天沒有關於莫奇森的消息。下午安奈特太太出門去——表面上是去買東西,但八成是去找她的朋友伊芳太太,告訴她赫綠思回來,還有一個英國警探來訪的事情。湯姆和赫綠思躺在黃色沙發上,昏昏欲睡,他的頭枕在她胸口。早上他們做了愛,棒極了。這應該是件大事。對湯姆來說,做|愛不像前一夜把赫綠思擁在懷裡入眠那麼重要。赫綠思常常說,「跟你睡覺真好,因為你翻身不像地震那樣把床搖晃得好厲害。真的,你翻身時我根本都不知道。」這點讓湯姆很開心。他從來沒問過誰翻身像地震。赫綠思存在,這對湯姆來說很奇怪。他猜不出她人生的目標。她就像牆上的一幅畫。有一天她或許會想要孩子,她說過。同時,她存在。湯姆也無法誇耀說自己有什麼目標,現在他已經擁有目前的生活,但湯姆有種強烈的熱情,想抓住眼前能抓住的愉悅,而赫綠思似乎欠缺這種熱情,或許是因為她生來就要什麼有什麼。跟她做|愛時,湯姆有時會覺得好怪,因為他覺得有一半的時間自己是超然的,好像他是在跟一個沒有生命、不真實、沒有身分的身體在做|愛。或者這是因為他自己的某種羞怯,或是清教徒的拘謹?或者是某種(心理的)恐懼逼他全力以赴,這種恐懼會告訴他,「如果我不擁有赫綠思,如果我失去赫綠思,我就再也不存在了。」湯姆知道自己可以相信這個話,即使是關於赫綠思的部分,但他不喜歡向自己承認,也不容許自己承認,而且他當然沒跟赫綠思說過,因為那是撒謊,就像很多事情一樣。他覺得,完全依賴她的狀況只不過是一種可能性。湯姆覺得,這種依賴跟性|愛其實沒什麼關係。一般來說,赫綠思瞧不起的事物跟他一樣。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她是個同伴,不過是個消極而被動的同伴。如果這同伴是個男孩或男人,湯姆會開心些——或許這就是最大的不同。不過湯姆還記得有回跟她父母在一起,他說,「我很確定義大利黑手黨的每個成員都受洗過,不過又給他們帶來什麼好處?」赫綠思聽了大笑,他父母卻沒笑。她父母不知怎地查出湯姆在美國沒受洗過——這件事湯姆其實不太確定,但反正朵蒂姑媽當然從來沒提過。湯姆年紀還很小的時候,他父母就淹死了,所以他從沒打父母那邊聽說過這方面的事。他無法跟身為天主教徒的皮里松夫婦解釋,在美國,受洗和望彌撒和告解和穿耳洞和地獄和黑手黨,不知怎地,都是屬於天主教而非新教的;而湯姆倒不特定是什麼,但他很確定自己絕對不是天主教徒。
「麻煩和*圖*書你,」克里斯說,「幫我跟貝納德說聲再見,好嗎?他的門關著。我覺得他不想被打擾,但我也不希望他覺得我沒禮貌。」
「老天,你可真忙!」赫綠思用英語說,帶著一點滑稽的醋意。「你想我嗎,湯姆?」
安奈特太太不在廚房,已經回自己臥室了。湯姆敲了門,聽到她應了一聲,於是打開門,安奈特太太斜倚在她床上,身上蓋著一件淡紫色的針織被單,正在閱讀《美麗佳人》雜誌。
然後他們出去到車庫。
「聽我的話!」湯姆用法語說,然後跑出去,下了樓梯。一杯純蘇格蘭威士忌最好,他心想。赫綠思很少喝烈酒,所以應該馬上能幫她鎮靜下來。然後再給她一顆鎮靜劑。湯姆從推車上拿了一個酒瓶和一個杯子,又跑上樓。他倒了半杯,看到赫綠思猶豫沒喝,他就自己先喝了一點,然後把杯子湊到她嘴邊。她的牙齒在打顫。
「待在這裡!」湯姆說。
「可以。」湯姆說。「我打給你吧。路易斯安那飯店,塞納街,對吧?」
是個假人。
對湯姆來說,赫綠思最有活力的時候,就是她發脾氣。她的脾氣大得很。有的湯姆還沒計算在內,比方有時巴黎寄來的貨品遲到而引得赫綠思大發雷霆,她會發誓(不誠實地)說她絕對不會再光顧某某家商店。更嚴重的發脾氣是肇因於無聊,或自尊受到小小攻擊,有可能發生在一個客人在餐桌討論上辯她或反駁她。客人在場時,赫綠思不會當場失控——這點很了不起——但等到客人一走,她就會氣沖沖走來走去,大叫大嚷,把枕頭丟到牆上,吼著,「滾出去!混蛋!」湯姆是在場唯一的觀眾。湯姆會說些安慰她或不相干的話,赫綠思會緩下腳步,一滴淚滾出眼角,過了一會兒她就又笑得出來了。湯姆猜想拉丁民族就是這樣,英國人就絕對不會如此。
湯姆無論如何不希望她去酒窖。他進了廚房,才剛拿了一盒冰塊出來,就聽到一聲尖叫——像是悶住的,因為離得有點遠,但那是赫綠思在尖叫,而且叫得很慘。湯姆往前廳衝。
「不錯呢,你知道嗎?你沒修飾得太過分,我很喜歡。」
然後他們準備去貝特林家。不必穿正式衣服,牛仔褲就行了。凡森也是平常在巴黎工作,週末才回鄉下的房子。
他回到樓下,安奈特太太正在客廳裡和赫綠思談希臘、談那艘遊艇、談希臘的那棟房子(顯然位於一個小漁村),不過湯姆注意到,還沒談到莫奇森。安奈特太太很喜歡赫綠思,因為安奈特太太喜歡服侍人,而赫綠思喜歡被服侍。赫綠思現在什麼都不想要,不過在安奈特太太的堅持下,她答應接受一杯茶。
「我跟一個叫湯瑪斯.莫奇森的人回來。」湯姆說,然後開始告訴她發生的事情。
緩緩地,赫綠思變得憤怒起來,這是復原的徵兆。「這些英國人開什麼蠢玩笑嘛!蠢!低能!」
「我不知道。」
但不是,是赫綠思。她站在那兒沒戴帽子,長長的金髮在微風中飄揚,手裡翻找著皮包。
「事實上——現在我覺得不會了。」湯姆說。
湯姆繼續說:「還有另一件事。貝納德.塔夫茲——我想妳沒見過他——來這邊住了兩天,今天下午看起來他是出門散步了,不過他東西都帶走了。我不曉得他還會不會回來。」
他雙手擁著她。「我想妳——真的好想。」
湯姆被摔上的車門聲嚇了一跳。有人來了。貝納德搭著計程車回來了,湯姆心https://m•hetubook.com.com想。
赫綠思還沒聽說他失蹤了。湯姆解釋了莫奇森懷疑他的《時鐘》是偽造的,湯姆說他相信德瓦特的畫作沒有假貨,所以他和警方一樣,不明白莫奇森為什麼會失蹤。赫綠思不知道整個造假的勾當,也不知道湯姆每年從德瓦特有限公司得到多少收入——其實約一萬兩千美元,大概跟他從狄奇.葛林里那邊所繼承的股票收入一樣。赫綠思對錢有興趣,但對怎麼來的興趣並不大。她知道有關家裡的開銷,她的家庭所出的錢跟湯姆出的一樣多,但她從沒跟湯姆提起過,而且湯姆也知道她根本不在乎,這是他欣賞赫綠思的另一點。湯姆告訴過她,德瓦特有限公司堅持要給他一小部分利潤,因為多年前他還不認識赫綠思時,曾幫忙他們開辦公司。湯姆從德瓦特有限公司得到的收入,都是由德瓦特美術用品公司在紐約的一個批發商轉給他的。其中一些湯姆投資在紐約,剩下的則全數匯到法國。德瓦特美術用品公司的老闆(剛好也是個希臘人)知道德瓦特不存在,也知道假畫的事情。
湯姆攔住她。
「沒有,先生。今天晚上會有幾個人吃晚飯?」
「我去拿吧,」赫綠思說。「你去拿點冰塊。」
「不用起來,夫人!」湯姆說。「我只是想問問貝納德先生在哪裡?」
赫綠思帶回來要放在樓下的東西是一個花瓶,短而結實,有兩個把手,瓶身上頭有兩隻公牛低著頭對峙。這瓶子很有吸引力,湯姆沒問是不是很貴、年代是否久遠,或其他問題,因為此刻他根本不在乎。他放了一張韋瓦第的《四季》唱片。赫綠思在樓上整理行李,還說她想泡個澡。
「你會打電話給警察嗎?」
然後赫綠思告訴她有關她在遊艇「希臘公主號」上的假期——遊艇主人就是那個叫柴波的,這名字老讓湯姆想到喜劇明星馬克斯兄弟。湯姆見過他的照片,露出毛茸茸的胸膛,據湯姆點滴聽來的,這個柴波就像一般希臘船運大亨那樣自負,而柴波只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小房地產商的兒子。根據柴波和赫綠思的說法,柴波的父親被那些法西斯軍閥壓榨,再去壓榨自己的人民,不過還是賺了很多錢,因此他的兒子可以開著遊艇到處遊玩,把魚子醬扔到海裡,把香檳裝進遊艇上的游泳池,然後再把游泳池加熱好在裡面游泳。「柴波不得不藏起那些香檳,所以他就放在泳池裡。」赫綠思解釋。
湯姆也半期待著貝納德憔悴的身影隨時會出現在門口。他緩緩走來走去,每次轉身就朝前門看一眼。「我去了倫敦一趟。」
「是嗎?好玩嗎?」
是的,你可以。或者,也不必他說了,湯姆心想。回家的路上,湯姆開得比平常快。他覺得很擔心,但不曉得到底該擔心什麼。他覺得跟傑夫和艾德失去連絡,而不管他或他們,現在連絡對方都是不聰明的。他想最好是設法說服貝納德留下。可能會有困難。但回倫敦,就表示貝納德又要一再面對德瓦特的展覽,街上到處貼了海報,或許還會看到傑夫和艾德他們自己也陷入恐懼和慌張。湯姆把車開進車庫,直接上樓去貝納德的房間敲門。
「他很高興我回法國了。」
「那是誰?」
告別何等沉重,而我——
湯姆打開門。床已經鋪過了,就像今天上午貝納德坐在上頭時一樣,現在湯姆看得出,床單上貝納德坐過的地方有個模糊的印子。不過
hetubook•com.com貝納德的所有東西都不見了,他的旅行袋,他沒燙的西裝(湯姆已經放進衣櫃裡)。湯姆回自己房裡迅速看了一下。貝納德不在裡面。克呂佐太太正在他房間吸地,湯姆向她說,「妳好。」「不,不要離開我!」
湯姆說,「大概是情侶吧。」他很擔心貝納德不曉得會有什麼反應,但貝納德大概根本沒聽到。
貝納德告退,然後上樓去了。
湯姆把所有東西搬進屋去。
「老天,真遺憾他這麼心煩。」一等貝納德走到聽不到的地方,克里斯就說。「我馬上就會離開了。希望我沒待得太久。」
不然要怎麼辦?呆站在那裡等著她放鬆心情?「沒錯。」他把其他東西拿到她房間。
湯姆放鬆地大笑。「我下去拿香檳!還有冰塊!」
晚餐很棒,有雞肉、米飯、蔬菜沙拉、乳酪,還有賈克琳做的蘋果塔。湯姆的心思在別的事情上頭。不過他很愉快,愉快到一直保持微笑,因為赫綠思的精神很好,談著自己的希臘冒險,最後他們一起品嚐赫綠思帶來的希臘茴香酒。
「貝納德.塔夫茲?英國人嗎?」
湯姆保證他會轉告貝納德。湯姆去把愛快羅密歐開出來。
「別下去,湯姆!那裡好可怕!」
「好可怕的假期!」赫綠思重重坐在沙發上,點了根香菸。她得花幾分鐘才能平靜下來,於是湯姆就開始把她的行李箱往樓上搬。她朝著其中一個箱子尖叫,因為裡頭有東西是要放樓下的,所以湯姆就留下那個箱子,拿了別的東西。「你一定要這麼像美國人,這麼有效率嗎?」
湯姆微笑,然後大笑。他一拍那兩隻腿——只有兩條空蕩的褲管而已,是貝納德.塔夫茲的長褲。「赫綠思!」他大喊,沿著樓梯跑上去,不在乎可能會吵醒安奈特太太。「赫綠思,是個假人!」他用英語說。「不是真人!那是個假人!妳不用怕了!」
那是湯姆畢生最糟糕的午餐之一,簡直比得上他和赫綠思結婚後,兩夫婦跟她爸媽吃的那頓。但至少這回沒持續那麼久。貝納德陷入演員那種無望的沮喪之中,湯姆猜想,他認為自己剛剛的表演很差,所以什麼安慰的話都幫不上忙。湯姆知道,貝納德正遭受到一個演員拼盡全力後那種疲倦的折磨。
湯姆在花園裡工作了大約一小時,然後讀了一點阿根廷作家胡立歐.科塔薩爾(Julio Cortazar)所寫的《秘密武器》。然後他上樓畫完那幅安奈特太太的肖像——今天星期四,她休假。傍晚六點時,湯姆請赫綠思進來,看看這幅畫。
他進了備用廁所,在打開的門前只猶豫了一下——酒窖的燈還亮著——然後開始走下階梯。一看到那片黑暗,懸掛的人影,頭歪著,湯姆感覺到一股震驚竄遍全身。那條吊繩很短。湯姆眨眨眼。那人好像沒有腳。他走近些。
「我得把這個味道沖掉。另外我也想喝點香檳。不曉得的人還會以為貝特林家很窮,他們配餐的酒糟透了。居然只是普通葡萄酒!」她走下樓梯。
「沒在他房裡嗎?或許是出去散步了。」
「好。不行!你絕對不能下去那裡。打電話給警察!」
「你想他今天晚上會回來嗎?」
湯姆衝到門邊打開。「赫綠思!」
「沒錯。我真無法告訴你這一趟對我有多棒——光是能看看一棟法國房子裡面。」
「會!」至少這是自殺,湯姆心想。應該可以證明。不是謀殺。湯姆嘆了口氣,顫抖著,抖得幾乎跟赫綠思一樣厲害。她坐在床的和圖書邊緣。「要不要喝香檳?多喝一點?」
湯姆又下樓。那個假人用一條皮帶懸著,湯姆認出是自己的皮帶。一個衣架撐著那套暗灰色西裝,長褲扣在外套的鉛子上,頭部是一條灰色抹布,用繩子綁在脖子上。湯姆趕緊去廚房搬了一把椅子——很高興安奈特太太沒被這番風波吵醒——回到酒窖,把那個假人拿下來。皮帶從大椽上的一根釘子上垂下。湯姆把那些衣服扔在地板上。然後他趕緊挑了一瓶香檳。他把西裝外套裡的衣架拿出來,同時也拿走了皮帶。他又去廚房拿了冰桶,關了燈,然後上樓去。
「啊,回家真好!」赫綠思說,張開雙臂。她把一個像掛毯的大包包——希臘製品——扔在黃色沙發上。她穿著褐色的皮革涼鞋,粉紅色的喇叭褲,一件美國海軍的雙排釦短大衣。湯姆很好奇她去哪裡、怎麼弄到那件短大衣的?
「啊,基督啊!」湯姆半撐著赫綠思,帶著她走上樓梯。
「任何人。」赫綠思用英語嫌惡地說,噴出了一口煙。
「啊,湯姆!」他們擁抱。啊,湯姆。啊,湯姆!湯姆已經逐漸習慣別人用法國腔喊他的名字,由赫綠思來喊,他更是喜歡。
「一百四十法郎。」
不是赫綠思,湯姆很確定。赫綠思以前有時會挑逗人,但也不常,不過湯姆確定自從他們結婚後,除了他之外,赫綠思就沒再跟其他人上床了。感謝老天,沒跟柴波那隻大猩猩。赫綠思從來不喜歡那一型的。柴波對待女人的方式聽起來很令人反感,但湯姆的態度是——這點他從不敢跟女人說——如果女人從一開始就容忍,好換得鑽石手鍊或法國南部的一棟別墅,那以後還有什麼好抱怨的?激怒赫綠思的,主要似乎是一個名叫諾麗塔的女人,因為遊艇上有某個男人很注意赫綠思。湯姆幾乎沒怎麼聽這段無聊八卦,因為他還在想著該怎麼告訴赫綠思一些自己的近況,而不會讓她心煩。
「好,我會打電話報警的。」
「家裡一切都很好。安奈特太太在她臥室裡休息。」湯姆說,改講法語。
貝特林家雖然相當富裕,鄉下的住宅卻刻意弄得比較粗陋,有個戶外廁所,廚房水槽沒有熱水。熱水是用一個水壺放在燒柴的爐子上。他們的客人還包括一對英國的克雷格夫婦,跟貝特林夫婦都是五十歲左右。凡森.貝特林聊起他兒子,湯姆以前見過,是個二十二歲的深色頭髮年輕人(凡森是在廚房告訴湯姆他的年齡,當時他和湯姆一起喝利加茴香酒,同時凡森在做菜),現在跟女友住在巴黎,同時正想放棄他在美術學院的建築學位,凡森因此很震驚。「那個女孩不值得!」凡森氣沖沖對湯姆說。「都是英國的影響,你知道?」凡森是戴高樂主義者。
沒人應。
「好吧——」湯姆擠出微笑。「那我們就別擔心了。有沒有人打電話來?」
「沒有,先生。」
湯姆不想告訴她說,他看起來是收拾東西離開了。「他沒跟妳說什麼嗎?」
且讓我的雙眼,為無法啟口的嘴說再見。
「我要下去拿一些香檳!」赫綠思大聲說。
他花了一些時間才讓她相信。那是個玩笑,可能是貝納德布置的——說不定甚至是克里斯弄的,湯姆補充道,無論如何,他摸了那兩條腿,很確定是假人。
「我幫妳買了東西。」湯姆爬上樓梯——他的腳踝好多了——拿著那條卡奈比街的長褲下樓。赫綠思在餐室裡穿上,完全合身。
爸爸不太喜歡他,湯姆知道和_圖_書,但爸爸隱隱感覺到赫綠思不會聽他的。湯姆猜想,小資產階級的特點,就是交戰時對人的性格特別敏感。「那諾愛爾呢?」諾愛爾是赫綠思最要好的朋友,住在巴黎。
是貝納德,當然了。湯姆顫抖著扶她走上樓梯,她講法語,他講英語。
「那誰跟柴波上床?我想不會是美國總統的老婆吧?」
「對,我跟他不熟,他是朋友的朋友。是個畫家,最近因為女朋友的事有點心煩。他有可能去了巴黎。我想我該跟妳提一下,說不定他會回來。」湯姆笑了。他愈來愈相信貝納德不會回來了。或許他是搭了計程車,到奧利機場設法盡快搭飛機回倫敦?「還有——另一個消息是,我們明天晚上獲邀到貝特林夫婦家吃晚飯。他們看到妳回來一定很高興!啊,我差點忘了。我還有另一個客人——克里斯.葛林里,狄奇的堂弟。他在這裡住了兩夜。我那封信裡提到他了,妳沒收到嗎?」她並沒收到,因為他星期二才把信寄出的。
湯姆聽了很高興,「別跟安奈特太太說。」他把畫放在角落待乾,面對著牆。
「我去拿。」湯姆匆匆穿上拖鞋。
「妳都烤焦了!」湯姆用英文說,其實他的意思是晒黑。「我來幫妳打發這傢伙。多少錢?」
「噁心的味道,那個希臘茴香酒!比保樂還糟!」赫綠思回家後說,在她浴室的洗手台旁刷著牙。她已經換上了睡衣,是一件藍色的短連身裙。
「答應我你不會下去!打電話報警,湯姆!」
然後又是一聲尖叫,湯姆在備用廁所撞上她。
湯姆回自己臥室,換上他在倫敦買的新睡衣褲。
到了傍晚六點半,貝納德還沒回來。湯姆覺得貝納德應該在巴黎,而非倫敦,但這只是個感覺,他也不敢保證。他和赫綠思吃晚餐時,安奈特太太跟赫綠思聊起早上來詢問有關莫奇森先生的那位英國紳士。赫綠思有興趣,但只是一點點,而且湯姆看得出來,她一點也不擔心。她對貝納德還比較有興趣。
老天,湯姆心想,讀兩首德國詩人歌德的詩來撫慰自己吧。〈告別〉或是類似的,帶來一點德國的堅定感。歌德相信優越性和或許天才吧。這正是他需要的。湯姆從書架上抽出那本《歌德詩集》,不知道是註定還是無意間,他翻到了人〈告別〉。湯姆已經熟記這首詩,但是從來不敢背給任何人聽,怕自己的口音不夠完美。現在一開頭幾句,就讓他難受:
湯姆想查下午的火車,但克里斯有不同的想法。他想在路上搭便車到巴黎。湯姆沒勸阻他。克里斯相信那會是一場冒險。湯姆知道,如果要搭火車的話,就得搭將近五點那班。克里斯帶著行李下樓來,走進廚房跟安奈特太太道別。
「你在哪裡放我下車都行,真的。」克里斯說。
「你知道,昨天夜裡,」克里斯說,喝完了他配餐的那杯牛奶,他另外也喝了葡萄酒,「我看到一輛汽車從那條樹林裡的小徑倒車出來。一定是約一點的時候。我想這事情應該不重要。那輛車倒車時沒開什麼燈,好像不想讓人看到。」
湯姆下樓。「安奈特太太!」
「好吧。」湯姆走下樓梯。
「爸爸說了什麼?」湯姆問。
「我過兩天可以打電話給你嗎?」克里斯問,「我很有興趣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然,我也會看報紙的。」
「我想兩個吧,謝謝,安奈特太太,」湯姆說,想著貝納德可能會回來。他走出房間,把房門關上。
「喔,老樣子。無聊,她說。她向來就不喜歡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