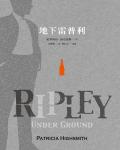二十一
「先生,我想你打錯了。」赫綠思的聲音說,電話掛斷了。
湯姆試著跟赫綠思解釋。莫奇森太太會在一個小時後抵達,想跟他談有關她先生的事情。安奈特太太已經離開客廳了,所以湯姆就可以跟赫綠思講法語,雖然安奈特太太想偷聽也聽得到。莫奇森太太打電話來之前,湯姆想過要告訴赫綠思自己去倫敦的原因,解釋自己曾兩度假扮已故的畫家德瓦特。但現在實在不是講這些的時候。只要他們先順利應付完莫奇森太太的來訪,湯姆只要求赫綠思做到這點。
「她要來這裡嗎?」
「因為——我可能馬上得趕去薩爾斯堡。」
「不,我想去梅朗跟那邊的警察談談。我在奧利機場打過電話給他們了。」
「我要謝謝你。」莫奇森太太說,他們下樓去。
傷口幾乎不痛了。湯姆鬆了口氣,貝納德沒跑來,免得赫綠思擔心。「那位美國女士打過電話來嗎?」
「去找那個瘋子。你看到他了嗎?你的頭怎麼樣了?」她扶著他的肩膀把他轉過去。
「德瓦特那幫人嗎?為什麼?」她開始講法語。「那些人為什麼這麼重要?」
「我想韋布斯特可能想再去拜訪你一次。他趕過去巴黎跟莫奇森太太會合了,所以我才會打電話給你。」
「我說,韋布斯特又問起德瓦特了,問他在哪裡,是不是離開了。」
「給了,」赫綠思說。「一個編出來的號碼。」她還在講法語,而且開始有點生他的氣。
湯姆到樓上的臥房。安奈特太太已經幫他把行李箱的東西拿出來,收好了箱子,但有幾樣東西沒放在平常的位置,所以湯姆把東西擺回他習慣的地方。湯姆沖了個澡後,穿上灰色法蘭絨長褲、襯衫和毛衣,然後從衣櫥裡拿出花呢外套,以備莫奇森太太可能會想到後院走走。
「我先生來訪的時候,妳也在嗎?」
到了樓下,安奈特太太人在廚房裡,湯姆匆匆在前廳說了再見,轉開頭免得被她注意到他頭髮分邊換了。那件很醜,但或許能帶來幸運的雨衣則搭在手臂上。
「我想沖個澡,」湯姆說,同時就聽到赫綠思打開他浴室的蓮蓬頭。湯姆匆忙脫掉衣服,站到蓮蓬頭下,水溫不冷也不熱,剛剛好。
「還需要什麼嗎,湯姆先生?」安奈特太太問。
「我知道妳打算說什麼,妳不希望她在這裡過夜。沒問題。我不會邀她留下來吃晚餐。我們可以說我們有約了,不過我得請她喝杯茶或喝杯酒。我估計——她待在這裡不會超過一小時,我們會非常有禮貌、非常得體地接待她。」
「跑去奧地利?別又是要去找那個瘋子了!接下來你就要去中國了!」
「我可以說你在家嗎?」
湯姆大笑。「赫綠思,妳太瞧得起我了。畫假畫的是那個瘋子貝納德。他想停止。啊,解釋起來太複雜了。」
「這事情跟狄奇有什麼關係?」赫綠思問道。
湯姆看了一下手錶。莫奇森太太的飛機應該再十分鐘就會降落了。
「啊,他有絡腮鬍——人很和氣,但是不健談。」她沒興趣多談德瓦特。「他倒是說過,他不認為有人在偽造他的作品——還說他也這麼告訴湯米的。」
「你知道,湯姆,貝特林夫婦希望我們今天晚上七點過去喝開胃酒。你去一下會有好處的。我跟他們說你晚上可能會在。」
他微笑,很高興她這麼關心。「可以。或許是諾愛爾打來,問她星期二該穿什麼衣服。」
「是的,湯姆先生。我今天早上去看了楓丹白露的那位牙醫,他抽掉了神經。真的拿掉了。我星期一還m.hetubook.com.com得再去。」
莫奇森太太到了。
「沒有關係,」湯姆說。「如果有關的話,我早就告訴妳了。她知道我是狄奇的朋友。妳要不要喝點白葡萄酒?」
「如果他不是自殺——我覺得韋布斯特督察好像不太相信他是自殺的——那麼會是誰殺了他?為什麼?」莫奇森太太問。「或者你對這事情有什麼想法嗎?」
「你可以告訴韋布斯特,說德瓦特似乎很沮喪,可能想一個人靜一靜。」
湯姆沒聽她接下去講的話。他忽然明白自己一定得找到貝納德。他忽然預見到未來的遠景。湯姆拿起行李箱。「再見,我的天使。妳能不能載我到梅朗?要避開警察局,拜託?」
「我們全都可以把神經抽掉了!全都抽光光!這樣就可以保證以後再也不會痛了!」湯姆幾乎不曉得自己在說些什麼。之前他該打電話給韋布斯特嗎?湯姆覺得今天離開倫敦之前,好像不打給他比較好,因為一打了,好像就顯得他太聽從警察的命令。湯姆的判斷是,無辜的人就不會打這個電話。
「沒錯,」湯姆說。「他沒被殺害,是自殺的。我當時認識他大概五個月——或許六個月。」
但他們什麼都不需要,莫奇森太太顯然沒有其他問題要問了。安奈特太太有點不情願地離開客廳。
「湯姆,他要我喊他湯姆,」湯姆說,露出微笑。他站起來。「他看了這兩幅畫。在我右邊的這幅《椅中男子》。還有妳後頭的那幅《紅色椅子》,是早期的作品。」湯姆勇敢地說著,不成功便成仁,管他什麼禮貌、道德、仁慈、真相、法律,或甚至是命運——意味著未來。他要嘛就現在一舉成功,否則就一敗塗地。如果莫奇森太太想參觀這房子一圈,湯姆甚至可以帶她到酒窖。湯姆等著莫奇森太太提問,或許會問起她丈夫認為這兩幅畫是不是真跡。
「希望不會。」湯姆拿起電話。「喂……是的……您好,莫奇森太太。」她想來見他。「這樣很好,當然,不過如果我去巴黎,對您不是比較方便嗎?……是的,是有些距離,比奧利到巴黎要遠……」他沒交上好運。他本來可以故意把路線講得很複雜,好讓她打消念頭;但這個女人已經夠不幸了,他不想再增加她的不便。「那麼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搭計程車。」湯姆告訴她該怎麼走。
湯姆回到客廳時,緩緩走到沙發前,跌坐在上頭。梅朗的警方沒有什麼新消息可以告訴莫奇森太太,否則他們早就告訴他了,湯姆心想。這兩天他不在,赫綠思說他們也沒打電話來過。如果警方發現了莫奇森的屍體在盧萬河或任何——
「妳要不要去樓上看看?」湯姆問莫奇森太太。「或者天黑前去看看院子?」
「隨時歡迎。」湯姆說。他送她出去上了車。
「應該吧。德瓦特好像很誠懇。我們還能怎麼說呢?」她在沙發上往後靠坐。
她和湯姆上樓。莫奇森太太穿了一件淺灰色的羊毛料洋裝。她的體格健美——平常或許騎馬或打高爾夫——但不會有人說她胖。這類結實的體育健將型女人,大家絕對不會說她們胖,但要說她們是什麼呢?赫綠思婉拒和他們同行。湯姆帶著莫奇森太太到客房,敞開房門,開了燈,然後以一種隨意而輕鬆的態度,帶她看了樓上的其他房間,包括赫綠思的臥室,開了門,可是沒開燈,因為莫奇森太太似乎沒興趣看。
「妳好嗎?」赫綠思說。
湯姆當下明白,她知道狄奇的事。赫綠思從來
https://www.hetubook.com.com沒有多說,但她知道。那倒不如索性把事情告訴她,湯姆心想,因為她可能幫得上忙,而且眼前情勢太危急了,如果他賭輸了,或是失了手,一切就都完了,包括他的婚姻。他忽然想到,他不能以湯姆.雷普利的身分到薩爾斯堡嗎?帶著赫綠思同行?儘管他很想,但他不曉得自己在薩爾斯堡必須做些什麼,也不曉得還會去什麼地方。無論如何,他兩本護照都得帶著,他自己的和馬凱的。「我說我們不曉得他是不是離開了。」
「他是什麼樣的人?畫展開幕那天,我差點就見到他了。」
「他的假畫不是你畫的吧?」
「這個嘛——我住在法國這裡,也不會知道。」
湯姆嘆了口氣。「什麼時候?」
「不,我那時候在希臘,」赫綠思回答。「我沒見過妳先生。」
「為什麼?」
諾愛爾.哈斯樂是赫綠思在巴黎最要好的朋友,她的派對總是很愉快。可是湯姆一直在想薩爾斯堡,想著要馬上趕去,因為他判定貝納德可能去了薩爾斯堡。那是另一個早死的藝術家莫札特的故鄉。「親愛的,妳去好了。我不確定我會在家。」
湯姆往前跨了一步。「還要喝點茶嗎?還是來杯蘇格蘭威士忌?」
湯姆猜想,她想私下跟警方談,不希望他在場。
湯姆嘆了口氣。逃避?逃避什麼?或者是追逐什麼?「我不曉得。」他開始流汗了,他想再沖個澡,但又怕耽誤時間。「麻煩也告訴安奈特太太,我有事得趕去巴黎。」
貝特林夫婦住的小鎮離他們家七公里。「我可不可以——」電話鈴聲打斷了湯姆的話。他示意赫綠思去接。
莫奇森太太說好。
莫奇森太太同意喝杯茶。「請原諒我這麼匆忙就不請自來,」她對著湯姆和赫綠思說,「不過因為事情很重要——而且我希望能盡快見到你。」
「你的畫是跟巴克馬斯特畫廊買的嗎?」莫奇森太太問。
「你想我先生發生了什麼事?」莫奇森太太問,看著赫綠思,然後眼神又轉回湯姆身上。
「是啊,我想妳先生也提到過這個。那妳相信德瓦特的說法嗎?」
「我聽懂了。」赫綠思說。
「韋布斯特督察告訴過我,那位在義大利被殺害的狄奇.葛林里,是你的朋友。」莫奇森太太說。
過了一會兒,安奈特太太進入客廳,一臉感興趣的表情,因為莫奇森太太就是那名失蹤男子的妻子。「我最後一次看到他,」安奈特太太說,「是吃午餐的時候,然後他就跟湯姆先生離開了。」
他真希望可以!「親愛的,問題出在護照。我不能以羅柏.馬凱的身分帶著雷普利太太進入法國或奧地利。馬凱,那隻豬!」湯姆淋浴完出來。
「我說我不知道。」
湯姆上樓,從櫃子裡拿出行李箱。他又要穿上那件很醜的新雨衣,把頭髮換邊分,再度變成羅柏.馬凱了。赫綠思進房來幫忙。
「沒有。我想洗個手,先等一下。」湯姆走進樓下的洗手間,洗了手臉。他希望莫奇森太太不會想來麗影,希望她約在巴黎見面就好了,雖然湯姆實在很不想今天還要趕去巴黎。
「我先生也是——除非可能真有人在偽造德瓦特的作品。」
「那個英國督察要來,是為了莫奇森的事情嗎?你殺了他嗎,湯姆?」赫綠思看著他,蹙起眉頭,很焦慮,但湯姆看得出來,她一點也不歇斯底里。
莫奇森太太似乎也很喜歡這幅。
「但你在逃避什麼,湯姆?」
到了巴黎,他發現沒有直飛薩爾斯堡的飛機,而且只有一https://www.hetubook•com•com班白天的航班,中間得在法蘭克福轉機。到法蘭克福的飛機是每天下午兩點四十分起飛.湯姆在里昂火車站附近一家旅館過夜,接近午夜十二點時,他冒險打電話給赫綠思。他一想到她孤單一個人在家就受不了,說不定還要面對韋布斯特,又不知道他人在哪兒。她之前說她不去貝特林家了。
湯姆替她覺得難過,也很遺憾自己殺了她先生。不過,他提醒自己,眼前可不是指責自己的時候:否則那他就跟貝納德沒有兩樣了——貝納德想坦白一切,不惜犧牲其他好幾個人。「妳在倫敦見到德瓦特了嗎?」
「因為德瓦特死了——好幾年前就死了,」湯姆說。「莫奇森打算要——揭穿這件事。」
或許在她自己房裡,或許廚房裡臨時缺了什麼出去買,赫綠思說,湯姆去敲安奈特太太的房門。安奈特太太正在縫什麼東西,湯姆問她能不能來客廳,見一下莫奇森太太。
計程車來了。
安奈特太太顯然忘了,湯姆心想,她其實沒親眼看到莫奇森先生走出屋子。
「啊,打過了。莫奇森太太。她會講一點法語,不過講得很好笑。她今天早上從倫敦打來,說下午三點會到奧利機場,還說想見你。啊,該死,這些人是誰啊?」
現在赫綠思會碰上什麼難關?他告訴她實情,到底是不是比較好呢?
「我不知道,親愛的。不過她來到法國,自然會想找——」湯姆不想說「最後一個見到她丈夫的人」。他又繼續,「她想看看這棟房子,因為她先生最後就是從這裡離開的。我從這裡載她先生到奧利機場。」
「我不能去貝特林家了,」湯姆說,然後大笑起來。貝特林夫婦的問題是他最不必擔心的。「親愛的,我今天晚上得去巴黎,明天到薩爾斯堡。如果有飛機的話,說不定今天晚上就趕到薩爾斯堡。那位英國的韋布斯特今天夜裡可能會打電話來。妳務必說我有事去巴黎,去找我的會計師,或隨便說什麼都行。說妳不知道我住在哪裡。說應該是住飯店,但妳不知道是哪家。」
湯姆又幫她倒了一杯茶。莫奇森太太看著赫綠思。是在打量她嗎?好奇赫綠思對這一切怎麼想?好奇赫綠思知道多少?好奇到底有沒有什麼內情可以知道?或者如果湯姆有什麼罪的話,赫綠思會站在哪一邊?
「喂,是的,日安。」她朝湯姆微笑。「請稍等。」她把話筒遞給他。「一個英國人在講法語。」
湯姆站起來。「重要的是,」他快速地用英文說,因為安奈特太太進來了,「我沒去倫敦。非常重要,親愛的。我只在巴黎。如果見到莫奇森太太的話,千萬別提倫敦。」
「我可以跟你去嗎?」
現在到了法國了,飛機降落,樹頂看起來開始像是繡帷上的墨綠和褐色小團,或者像湯姆家裡那件睡袍上的裝飾青蛙。湯姆穿著他好醜的新雨衣坐著。到了奧利機場,出境人員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下他那本馬凱護照上的照片,但什麼章都沒蓋——他之前離開奧利到倫敦也沒蓋章。好像只有倫敦的出入境才要蓋章。湯姆走過「無申報項目」的通道,跳上計程車回家。
大家好一會兒都沒說話。莫奇森太太正在想著接下來該說什麼或問什麼。湯姆猜想,唯一重要的就是巴克馬斯特畫廊的那些人。但她怎麼好開口跟他打聽他們呢?
「湯姆,你殺了他嗎?就在這兒?」
湯姆答應赫綠思會保持連絡,但說會用別的名字打電報。他們在愛快羅密歐上吻別,然後湯姆離開赫綠思溫暖的懷抱,搭上往
https://www.hetubook.com.com巴黎火車的頭等車廂。「我先生來拜訪的時候,府上還有其他人嗎?」莫奇森太太問。
但傑夫不太好,他又開始結巴了,聲音很小又講得很快。湯姆不得不請他大聲點。
「可是我不認為妳先生的那幅畫是假畫。而且他離開的時候,其實也半信半疑。我跟韋布斯特提到過,我不認為湯米還會想把《時鐘》拿給倫敦的專家看。我不記得問過他,但我有個感覺,他看過我的兩幅畫之後,有了新的想法。說不定是我誤會了。」
「我最喜歡《椅中男子》,」湯姆說。「所以才會掛在壁爐上方。」
湯姆用法語對赫綠思說,「莫奇森太太很想知道,是不是有一幫不誠實的人——在偽造德瓦特的油畫。」
湯姆想著自己敢跟赫綠思解釋多少?「妳告訴他我什麼時候會回家呢?」
「喂,湯姆,我是傑夫。你還好吧?」
「喔,好得很。」
「沒錯,兩幅都是。」湯姆看了赫綠思一眼,她正在抽一根平常不抽的「吉普賽女郎」牌的香菸。「我太太懂英語。」湯姆說。
「他早就死了?」
電話鈴響了。如果是莫奇森太太,那就是從奧利機場打來的。
「好。」
赫綠思對狄奇的事情一直就半信半疑,湯姆知道。但湯姆也知道自己可以仰賴她。赫綠思自己對壞人也有點好奇。但無論如何,在一個陌生人面前,赫綠思對湯姆所說的話絕對不會表現出絲毫懷疑。
湯姆心往下一沉,雙膝發軟,往後坐在旅館的床上。他很自責打電話給她。最好是單獨行動,一向如此。韋布斯特一定明白是他打的,或者很疑心。
「這位是我太太,赫綠思。」湯姆說,「這位是莫奇森太太,從美國來的。」
「我不得不殺了他,為了救其他一堆人。」
赫綠思平靜下來。
湯姆等著她開口,說起她先生認為德瓦特畫作被偽造的理論。但她沒有。她沒有批評兩幅畫中的淺紫色或紫色。莫奇森太太只問了韋布斯特督察問過的那些問題,她先生離開時是否覺得不適,他是不是跟誰有約。
「見到了。」莫奇森太太說,又坐回沙發上,不過坐在相當邊緣。
莫奇森太太站起來,看著那兩幅畫,湯姆又多開了兩盞燈,好讓她看得更清楚。
「他當時好像精神不錯,」湯姆說,「沒提到任何約,這點我也告訴過韋布斯特督察。奇怪的是,妳先生的畫被偷了。當時他把畫帶去奧利機場,包得好好的。」
「可能有個集團,」她看著赫綠思。「希望妳明白我們在講什麼,雷普利太太。」
「親愛的,怎麼了?」
「沒錯,我在倫敦假扮過他兩次。」湯姆說。這話用法語說,聽起來好純真又好歡樂:他在倫敦「表演」過他兩次。「現在他們在找德瓦特——也許暫時還沒找得那麼急。但反正他們根本沒搞清狀況。」
「親愛的,喂。如果韋布斯特在那裡,就說我打錯電話,然後掛斷。」湯姆說。
「如果妳要搭火車去巴黎的話,」湯姆說,「我可以開車載妳去梅朗。」
「我想我要一杯蘇格蘭威士忌,謝謝。」
湯姆緊張地看了電話一眼。莫奇森太太會打電話來。什麼時候?「妳是不是給了莫奇森太太一個巴黎的電話號碼,讓她可以打給我?」
湯姆到廚房拿冰塊。赫綠思跟進來幫他。
他們拿了冰塊和玻璃杯。莫奇森太太想叫一輛計程車到梅朗。她為自己沒先預約好而道歉,但她不知道這回拜訪會要多久。
他們現在都坐下了,莫奇森太太坐在黃色沙發,湯姆跟赫綠思都坐在直背椅上。赫綠思的神態絕佳,一副只
m.hetubook.com.com是為了禮貌而現身,對眼前狀況不太感興趣的模樣。但湯姆知道,她其實很感興趣。
「是的,我知道。」莫奇森太太抽著她的切斯菲德牌香菸。「那幅畫一直沒找到。不過我先生或他的護照也沒找到。」他微笑。她有一張愉快而和善的臉,有點豐|滿,也因此暫時防止了歲月造成的縐褶。
「那你為什麼非得找到那個瘋子貝納德不可?啊,湯姆,別碰這些事情……」
湯姆到前門迎接她,幫忙確認付給計程車司機的車資沒問題。莫奇森太太給了法郎,還給了太多小費,但湯姆也隨她了。
「去四處看看。」湯姆說,滿面微笑。
「諾愛爾在問,我們星期二晚上要不要去參加派對,」赫綠思說,「星期二是她生日。」
「謝謝,雷普利先生,」莫奇森太太說。「還有夫人,等我事情處理完了,或許會再來拜訪兩位——」
「啊,我想我還應付得來。非常謝謝你。」她微微一笑。
「妳好嗎?」
「只有我的管家安奈特太太。赫綠思,安奈特太太人呢?」
「但她先生到底怎麼了?」赫綠思問。
「我先生——」
湯姆已經站起來,兩腳穩穩踩在地上,啜著紅茶。「這事情我沒有什麼想法。狄奇.葛林里自殺了。我想他找不到未來的出路——他想當畫家,而且絕對不想接他父親的造船事業。狄奇有很多朋友,但都不是會害人的。」湯姆暫停一下,其他兩個人也都沒吭聲。「狄奇實在不可能有敵人。」湯姆補充。
赫綠思站起來,身子不耐地扭動著。但她沒蠢到跟湯姆當場大鬧。她不打算失控或失去理智。晚些再來鬧也不遲。
「那我送妳過去好了,」湯姆說。「妳的法文怎麼樣?我的法文不完美,但是——」
「可能是今天。我不曉得他到底打算做什麼……」
「親愛的,你好緊張,」赫綠思說。「喝杯酒吧。」
掛斷電話時,湯姆覺得震驚,同時又氣憤,或者是心煩。為什麼還要面對韋布斯特?湯姆寧可離開這棟房子。
下午快三點時,他抵達麗影。在計程車上,他已經把頭髮分邊梳回原狀,雨衣搭在手上。赫綠思在家。暖氣開著。家具和地板發出打過蠟的光芒。安奈特太太把他的行李提上樓。然後湯姆和赫綠思親吻。
湯姆和赫綠思喝了茶。
安奈特太太下樓時,湯姆剛好走回客廳。「安奈特太太,妳的牙齒怎麼樣了?希望好些了吧?」
「那你怎麼跟他說?」
「好,」湯姆說,倒了一杯。湯姆在飛機上看過倫敦的報紙,都沒提到德瓦特再度出現的消息。英國人顯然認為這消息並不重要。湯姆很高興,因為不論貝納德人在哪裡,湯姆都不希望貝納德知道他已經設法爬出墳墓了。到底為什麼不希望貝納德知道,湯姆也說不清。但這跟湯姆所感覺到貝納德的未來命運有關。
「如果要我猜,」湯姆說,「那就是有人知道他帶著一幅值錢的畫。當然了,不是頂值錢,但那是一幅德瓦特。我猜想他在倫敦跟一些人提到過。如果有人想綁架他,搶走那幅畫,他們可能一時失手殺了他。然後他們得把他的屍體藏起來。或者,他有可能還活著,被關在哪裡。」
「你去希臘做什麼,」她有點焦慮地問道。「然後又跑去倫敦?」
「但聽起來,我丈夫認為《時鐘》是偽作的想法,似乎沒有錯。就像你剛剛說的,那幅畫不是頂值錢,可能因為尺寸並不大。但或許他們想讓他閉嘴,不要讓德瓦特有假畫的說法傳出去。」
「親愛的,要不要喝杯茶?」赫綠思帶著他走向黃色沙發。「你找到這個貝納德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