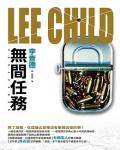9
我何止不太高興。她死得很痛苦,都是我害的。她可能還以為自己幫了我個大忙,讓我的東西不會弄濕,免得生鏽。她只是個來自愛爾蘭的天真女孩,只是想幫我而已。而我竟然害死她,這就跟我在那個現場親自動手屠殺她沒兩樣。
「你看起來不太高興。」他又說了一遍。
不管怎麼說,我仍需要這雙鞋。雖然留著它們很冒險,可是我還沒準備好跟蘇珊切斷聯繫。現在還不是時候。我把自己反鎖在杜克的浴室,然後取出電郵裝置。這麼做感覺很怪。我按下電源鈕,螢幕隨即出現一個新訊息:我們得見個面。我按下回覆:這是一定要的。傳送之後,我便關掉電源,把裝置塞回鞋跟,下樓再回到廚房。
「但是,說不定他們是先搜她的身,發現了她鞋子的機關。」
「所以這是同時來自三方面的惡夢,」他說,「我們可以把多爾跟哈特福那票人連在一起,然後把波士頓的朋友跟聯邦探員連在一起。現在,多爾跟聯邦探員也可以連在一起,因為他把鑰匙給了那個臥底賤人。這就表示哈特福那幫人一定也跟聯邦探員有關係。雖然多爾已經被杜克幹掉,但我還有哈特福、波士頓跟政府這三個大麻煩要處理。我很需要你的幫忙,李奇。」
「我要去廁所,」我說,「馬上就下去。」
為什麼蘇珊突然怕這裡的人接到電話,要中斷訊號四或五個鐘頭?只有一個可能的答案。她怕我出事。
「我一定會告訴你的,」她說,「我當然會告訴你。如果我派了另一位探員進去,就不需要你了,難道你不懂嗎?」
「她到這裡多久了?」我問。
後來,道路突然轉向往西走,我看見二九五號州際公路就在我們左邊不遠處。州際公路後方有條水面呈灰白色的狹長海灣,再往後一點就是波特蘭機場了。一架飛機在大片水花中起飛。飛機從我們頭頂低空呼嘯而過,然後在大西洋上空轉往南方。車子繼續前進,左側路邊出現了一排商店區,商店區正面有個狹長形的停車場。這地方是卡在一號公路與另一條路之間的尷尬地帶,應該算是機場附近利用價值較低的區域,所以會進駐的大概也只有些普通而沒什麼特色的店。停車場裡差不多有二十輛車,全都車頭朝內,跟店門外的人行步道垂直。那輛老紳寶就停在左邊數來第五部。哈雷開過去,停在紳寶正後方。他又開始用拇指敲著方向盤。
「那我想我也不該告訴你。」
蘇珊的臉色又變蒼白了。
「照臥底常用的模式。單身,沒結婚,沒家人,無依無靠。就像你一樣,只是你不用假裝。」 我緩緩點頭。一個貌美的三十歲女人,就算失蹤也沒人知道。這對波利或安傑.多爾這種人來說,可是個很大的誘惑。他們應該無法抵抗吧。這樣就能隨時找樂子了。而他們其他那些同黨可能更糟糕。比如哈雷。他看起來就像不知道文明兩個字怎麼寫的人。
「因為,」她說,「我會覺得彆扭,我的動作不協調。」
我們往回走向屋子,全身已被雨水和海水浸得濕透。貝克躲回廚房,我們跟著他進去。哈雷在角落裡徘徊,彷彿覺得自己不該待在這裡。
「不是信封,」我說,「那個信封是空的。是報紙。藍圖在報紙裡,就在體育版,所以他才沒看棒球賽的比數。信封只是轉移注意力的東西,避免有人監視。他顯然練得很熟了。他用粉筆做完記號之後,就會把報紙丟到另一個垃圾桶裡。也或許是開出停車場的路上弄的。」
「我不知道。反正不是現在。」
「可以打到警衛室。」我說。
「她為什麼會找到我的東西?」
「絕對不會。」她說。
「我想我們只能這麼做。」
我點點頭。「我認為他們想讓她活著。因為他們不知道她是聯邦探員,以為她只是個女人。」
我轉個身。紳寶的車頭面向一間小酒舖。而酒舖兩側的商店,一間專賣汽車音響,另一間外面有扇大型櫥窗,裡頭擺滿假水晶製的枝形吊燈。我不覺得女傭是被派來買新的天花板吊燈,也不是來買裝在紳寶車上的CD播放機。她一定是來買酒。而她當時也一定發現那裡有一夥人在等她。來了四個,也可能五個。至少有這麼多人。一陣驚訝後,她會從手足無措的女傭變成訓練有素的探員,為了自己的生命搏鬥。他們一定料到這點,所以派了一群兇狠的流氓。我上上下下觀察著人行道,接著再看看那間酒舖。酒舖的櫥窗擺滿箱子,從裡面應該看不到外面的情況。不過我還是進去了。
「那就棘手了,」我說,「你想他們為什麼會介紹她?」
蘇珊大概六分鐘後到。她先停在門口,四周張望一下,然後笑著朝我走來。她換了新的牛仔褲跟另一件棉襯衫,不過襯衫是藍色的,不是上次的白色。襯衫外是她那件皮夾克,而最外面還穿著一件尺寸明顯太大的舊風衣。也許是那個老探員的吧。也許是她向他借的。但不是艾略特的,這點很明顯,因為他的體型比她還小。她一定沒料到這裡的天氣會變糟。
我看他,他對著我笑。他的嘴像個凹洞,位在那撮山羊鬍上方,裡頭裝著爛掉的黃色牙齒。我又別過頭。下波潮水進來,這次的浪小多了,不過水消退後,裂縫也被沖洗乾淨,看起來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也沒有任何東西曾出現在那裡。哈雷笨拙地站起來,將空袋子拉鍊拉上。粉紅色的水從袋子裡瀉出,流到岩石上。接著他開始捲起袋子。我轉頭望向屋子。貝克獨自站在廚房門口外,正往我們這裡看。
「我跟波利嗎?」他說。「當然。」
「他們駭進妳的電腦,」我說,「可能是今天早上,或者昨天晚上。」
她看著我。「你覺得是這樣?」
他點頭。「當然。她說她才剛發現這包東西,講得天花亂墜。其實她還推到你身上,說這些都是你的。不過話又說回來,他們這種探員一定會否認的,不是嗎?我猜他們受過這方面的訓練吧。」
我點點頭,沒說話。
我把自己反鎖起來,脫掉鞋子,打開鞋跟。我按下電源鈕,螢幕亮起:無服務。於是我關掉電源,把裝置塞回去。為了裝得像一點,我沖了馬桶,然後坐在蓋子上。我不是什麼通訊專家,我知道電話線路偶爾會出問題,我知道手機訊號有時也會中斷,但是一個地方的電話線路跟距離最近的手機基地台同時故障的機率有多高?我猜很小吧。小到極點了。因此,這一定是有人故意弄的。不過究竟是誰?不會是電話公司。他們不可能選在星期五的通勤時間中斷線路進行維修。如果是星期天一大早還有可能。而且他們也不會同時中斷基地台訊號。這反而只會拖慢兩邊工作的進度。
「維安由我負責,」我說,「我應該早點察覺她有問題。」
「風險很大。」我說。
我沒說話。
「妳為什麼要約我見面?」我問她。
她沉默了一下,然後才開口說話。「你想跳舞嗎?」
「總之我們失敗了,」她說,「你什麼都沒查到。半點線索也沒有。完全沒證據。從頭到尾,這一切都是在浪費時間。」
貝克羞怯地笑了出來。「你真是個冷血的傢伙啊,李奇。」
他看著我。我心想:是波士頓那些人懇求與政府達成認罪協商,然後幫忙安排的。我點點頭。
「看見外頭那輛紳寶了嗎?」我說。
「對方一定是我們的人。」她說,「不是軍人,就是中情局,或者調查局。否則不會這麼專業。」
「那你不會懂的。總之我認為,要是我們將設計圖造假,那個幕後黑手一定會知道。這會讓葛洛斯基陷入危險。或許他的兩個小女兒和其他親人也會有危險。」
她搖搖頭。「我查過了。垃圾車把垃圾擠壓進車內後,就直接載去焚化爐。」
我搖頭。「我看過屍體了。死的不是泰瑞莎。」
波利非常從容地替我開門。他先讓我等了幾分鐘,才笨重地走出警衛室。他還是穿著雨衣。接下來,他又站在原地盯著我看了一分鐘,才開始往門閂方向移動。然而我一點也不在意。我正忙著想事情。蘇珊的聲音出現在我腦海:我要修正任務內容。在我大半軍旅生涯中,有位叫里昂.蓋伯的人或多或少算是我的上司。他會自己編出簡短的語句或格言來解釋身邊遇到的一切狀況,每件事他都能用一句話來說明。他常說:「修正目標是好事,因為這能避免把錢花在不該花的地方。」他的意思指的不是字面上的錢,而是指人力、資源、時間、意志、努力、幹勁等等。有時候他講的話也會相互矛盾,比如他也常說:「工作時絕對不要轉移目標。」當然,很m•hetubook.com.com多諺語也是相互矛盾的,像是人多手雜愈幫愈忙跟人多好辦事,還有英雄所見略同跟傻子想法都一樣。不過大體上來說,在消去那些矛盾的層面後,里昂是贊成修正的,而且非常贊成。主因是修正需要思考,而思考沒什麼壞處。所以我正在思考,而且是絞盡腦汁地思考,因為我感覺得到好像有某件事正緩緩浮出水面,而我只差那麼一點就能想通了。這件事跟蘇珊對我說的話有關聯:你什麼都沒查到。半點線線索也沒有。完全沒證據。
她做了個苦臉。「別太自責了。這不是你的錯。只要他們一侵入電腦系統,要找出臥底就只是遲早的事了。她們兩個都有可能。我的意思是,符合女探員身分的還能有幾個?搞不好只有她跟泰瑞莎而已。那些人一定會查出來的。」
不過我們覺得那時候跳舞還太早,所以先喝了幾瓶啤酒等到晚上。我們去的那家酒吧不大,燈光昏暗,由木頭跟磚塊搭建而成。這地方很不錯,而且還有台點唱機。我們並肩靠在機器前,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決定我們的第一首歌。我們討論得很熱切,到後來我們的第一首歌似乎變得十分重要。她每建議一首歌,我就在心中分析音樂的速度,試著解讀她的想法。我們要抱著對方嗎?是用那種方式跳嗎?還是像平常那樣分開但面對面地跳?最後,我們還是不知該選哪首才好,於是決定直接投下硬幣,閉起眼睛隨機按鈕。結果我們選到了滾石合唱團的〈Brown sugar〉。這首歌很棒。一直都很棒。她舞其實跳得很好,但我就很糟了。
「沒錯。」
我聳聳肩。
「可是我完全沒想到會是她,」我說,「我以為她只是個女傭。」
我一邊往南開,一邊吃完棒棒糖。這輛紳寶不怎麼好開,而且比貝克的凱迪拉克或哈雷的林肯還吵。這是部破舊的老車,車內地毯已變得又薄又鬆,里程表也到了六位數。不過它還是能開,輪胎還不錯,雨刷可以正常擺動,在雨中行進也沒問題,而且還有很棒的大照後鏡。我一路上都注意著鏡子裡的情況。沒人跟蹤我。結果是我先到咖啡廳。我點了中杯濃縮咖啡,藉以洗掉嘴裡巧克力的味道。
大浪隆隆衝來,我們兩人都低頭躲避飛濺的浪花。潮水升到裂縫頂點,還滿了出來,幾乎要流到我們腳邊,但隨即又被拉回去,連裂縫裡的水也沒了。砂礫滾動時發出嘎嘎聲,有些跟著潮水流入海中。海面散佈著灰色泡沫形成的絲線,還被雨水打出一點一點的小凹坑。
「那就這麼辦吧。」我說。
「李奇,到底什麼事?」
「但他只是個商人,對吧?基本上是吧?如果他不認為泰瑞莎會威脅到他的生意,他還會對她做不好的事嗎?」
「等下一波大浪結束再動手。」哈雷說。
我第四次見到三等士官長多明妮.柯爾,是我們一起去酒吧那晚的一星期後。天氣還是很熱,聽說有個熱帶風暴從百慕達方向過來。我桌上的文件堆積成山,各種案件都有。強|暴案、兇殺案、自殺、竊取武器、襲擊……前一晚還發生了場暴動,因為士兵伙食廚房裡的冷藏庫故障,冰淇淋全都融成了水。我剛跟加州爾文堡一個朋友講完電話,他說只要沙漠的熱風吹起,那裡也會發生跟我們差不多的狀況。
「什麼?」
「不是泰瑞莎,」我也再說一次,「是另一位探員,另一個女人。她是以廚房女傭的身分混進去的。」
她繼續玩著杯子,直到它回到原來的位置,轉了整整一圈。杯子粗糙的底面在盤子上發出細微摩擦聲。
「這還是很冒險。」
「真不敢相信。」我說。
也許是蘇珊,而且是私下做的。以她的身分,或許能單獨跟某位電話公司經理見面,要求他就幫她這麼一次忙。只要切斷某個特定區域內的通訊就好。只要中斷一條電話線,然後再關閉九十五號州際公路附近一座基地台的訊號。這或許會造成三十哩範圍的死角,讓開車經過的人都收不到訊號,不過她還是有可能要求對方做到。有可能。而且她會告訴對方,只要持續一段時間就好,不用無限期中斷。也許四、五個鐘頭吧。
「交給你啦,」他說,「鑰匙在門邊。」
我沒回答。
我沒說話。
她點點頭。「八個星期了。我猜廚房女傭應該不方便使用手機充電器吧。」
「底流會把屍體帶走,」他說,「我們還沒看過再被海浪沖回來的,從來沒有。屍體會被帶到一、兩哩外,一路往下沉。我猜接下來就是鯊魚用餐的時候啦。牠們常出現在這附近。另外還有其他各種生物,你也知道,像螃蟹、亞口魚什麼的。」
他臭著一張臉點點頭,同意我的看法。他懂我的意思。接著他拿起放在鑿子旁的那一大串鑰匙。「我想這應該是安傑.多爾的。」他說。
「貝克說她是從波士頓來的。」
我點點頭。貝克家裡的女人還有伊莉莎白跟那位廚師,但她們兩個都不太可能遭受懷疑。伊莉莎白是貝克的老婆,而廚師說不定已經在那裡待了有二十年。
所以是誰?
「垃圾什麼時候收走?」
「這是他第五次來了,」多明妮壓低聲音對我說,「他們完成砲彈軟殼設計後的第三次。」
「什麼另一位?」她又說了一次。「只有泰瑞莎啊!到底怎麼了?你是要告訴我她死了嗎?」
「我學到一件事,」他說,「你可以賭上這條命相信我,那就是我一定要開始檢查大家的鞋子。」
「可惡。」她說。
「不,」她說,「只有泰瑞莎一個人而已。」
她不說話了。過了一分鐘,兩分鐘,接著她抬起頭看我。她想到另一件事了。
還有,她怎麼會找到?為什麼她會到那裡搜查?
我沒說話。
「怎麼了?」她說。
「你餓了嗎?」
「哈雷在車上等。」他說。
「叫他親自畫一份,」我說,「要承擔後果的人是他。」
「八個星期前?」她說。
「注意看了。」多明妮說。
「她是聯邦探員?」我說。
「到目前為止步驟都一樣嗎?」我問。
我注視著那組編號。「她有否認嗎?」
「什麼探員?」
「沒錯。」貝克說。
「大概推測一下,」他說,「你一定看過這種東西。」
我翻身下床,走到窗前。現在已是傍晚,就要天黑了。第十四天,星期五,今天即將結束。我走下樓,心裡一面想著紳寶轎車的事。貝克正好在走廊上。他走得很急,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他走進廚房,拿起話筒聽了一會兒,然後再拿給我。
「好吧。」我說。
「那你的鞋子呢?」她說。
他再拿起葛拉克,轉了個角度,指著滑座右側。
「我猜他們會料到這點,」我說,「最先出狀況的一定都是通訊問題。他們不會因為她一失聯就緊張起來。而且他們也沒別的選擇,只能讓她留在原地。我的意思是,他們也一樣無法聯絡她,叫她回去吧?所以,我認為對方會等一段時間,相信她會盡快再把電池充滿,重新聯絡他們。」我翻轉手中的裝置,指著底部的插孔。「看起來可能要用手機充電器之類的東西。」
我移開眼神,又移回來。現在換我尷尬了。
「那你怎麼知道?」
「行。」我說。他回到走廊上,而我拿起袋子,轉個身再走到屋外,往車庫區圍牆靠海的那面去。我把我那包東西放回原來藏的位置。不要浪費,說不定還能派上用場。而且,我也希望到時能把葛拉克手槍還給蘇珊。她的麻煩已經夠多,別害她另外再加上丟槍這一件了。大部分政府單位都會把丟槍這種事看得很嚴重。
「我們不抓貝克,這已經是我第二次搞砸了。那位女傭是合法派出的探員,但泰瑞莎不是,你也不是。現在女傭死了,他們一定會因為我找泰瑞莎和你私下行動而開除我,另外他們也會放棄貝克這件案子,因為我徹底擾亂了辦案程序,害他們在法庭上根本站不住腳。所以,找回泰瑞莎,然後我們全部回家去。」
我把話筒貼在耳上。什麼聲音都沒有,沒有撥號聲,也沒有短路時的嘶嘶聲。只聽到一片呆滯的沉默,還有我腦袋裡血液的流動,感覺就像透過貝殼聽聲音。
蘇珊沉默了一下。
「決定了嗎?」
「可是你找到了他們藏匿她的房間。」
「沒看過會再被海浪沖回來的。」他又說了一次。
「就靠動能、高密度金屬、貧鈾、高熱這幾樣因素。你是物理學研究生嗎?」
她沒回答,然後開始用食指輕戳杯柄,讓咖啡杯在盤子上緩慢地繞圈。杯子轉動時,裡頭的泡沫跟巧克力粉仍然靜止不動。她正絞盡腦汁思考著。
我hetubook.com.com在想我剛才的感覺。那就像坐雲霄飛車。她是死了,但現在已經不關我的事,而是政府的電腦害死她的。就這點來說,我鬆了口氣。不過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有點生氣。蘇珊到底在搞什麼?她究竟要玩什麼把戲?除非臥底的人都知情,否則絕對別派一位以上的探員到同一個地點,這是絕對無庸置疑的準則。也是最基本的道理。她告訴過我泰瑞莎.丹尼爾的事,為什麼卻不告訴我還有另一位女探員?
「砲彈軟殼得使用金屬材質,」她說,「這是他們的結論。」
「不過她到底是怎麼被查出來的?」她說,「一開始發生了什麼事?我只想知道這個。我的意思是,她才待了兩天就被發現,但他們是在整整九個星期後才侵入電腦系統的啊。」
「沒裝機關的。」
我繼續拿著那張鈔票,等了好一段時間。一百塊,還不用扣稅,應該至少等於他開店一星期淨賺的金額吧。可是他現在連看都不看,這也告訴了我很多事。
我聽見柵門打開的聲音,抬起頭,看見波利正在等我。雨水打在他的雨衣上。他還是沒戴帽子。我本來想小小報復一下,故意等個一分鐘再開進去。反正蘇珊都已經修正目標了。我根本不在乎貝克。不管任務有沒有修正,我一點都不在乎他。可是,我要泰瑞莎,我要找到她。我要昆恩,而且不管蘇珊怎麼說,我也都要找到他。這就是我的目標,不能修正。
「我想是吧。」
「什麼事也不會發生,」她說,「我已經監視過兩次,待了整整兩個星期日,半個人也沒看到。白天沒有,晚上也沒有。」
「你看起來不太高興。」貝克說。
「沒有。」我說。
他把手機遞給我。它的正面有個小螢幕,右邊的長條圖顯示電池滿格,可是信號欄卻完全空著。螢幕上只有幾個大而明顯的黑色字體:無服務。我將手機還給貝克。
「她從第二天就沒消息了。」她顯得很平靜。
我點頭。「我一定得這麼做。我可能是個笨蛋,但還沒笨到極點。這件事已經遠超出控制了。」
他抬起頭,讓一個暗黃色軍用信封從報紙裡滑出來。接著,他伸出左手拍了一下報紙邊緣垂下的部分,像是想把報紙攤好繼續讀。但其實這招是聲東擊西,因為他這麼做的同時,右手也順勢將信封放進他那張長椅邊的垃圾桶。
她搖搖頭。「已經不重要了。我要修正任務內容。我現在不管之前設定的那些目標了,只要把泰瑞莎救回來就好。你一定要趕快找到她,帶她離開,好嗎?」
他作勢向外望。
「不是。」
「我猜她是想控制情況,這是標準程序。對她來說,你不是什麼好人,只是個我行我素的不定時炸彈。你是個殺警兇手,而且還私藏武器。說不定她以為你來自與貝克敵對的組織,還打算出賣你。這樣就可以增加他對她的信任。總之,她要解決你這個問題,以免整件事變得更複雜。她要不就是把你出賣給貝克,要不就是檢舉你,把你這個殺警兇手交給我們。我很訝異她竟然沒這麼做。」
「明天一大早。」
「而對方已經拿到三份真正的藍圖了。」
廚師不在,流理台收拾得整齊又乾淨,而且剛擦洗過。爐子是冷的。這裡只差沒在門上掛休息中的告示牌而已。
「我也是。」
通常立刻回答沒有的人都是在說謊。如果真的沒看見,說沒有當然很正常,可是一般人都會先停下來想想再回答。而且他們還會補上一句抱歉之類的話,說不定還會主動問些問題,這是人性。他們會說抱歉,我沒看見,為什麼問這個,發生什麼事了嗎?我一手伸進口袋,憑感覺從貝克給的那疊鈔票裡抽出一張,然後拿出來。是張一百塊。我將鈔票對摺,用食指跟大拇指夾著舉起來。「現在你看到了嗎?」我說。
我下車走進雨中,才一關門,他就馬上開走。不過他沒回到一號公路上,而是在開到停車場底端時左轉,隨即又右轉。我看到他那輛大車減慢速度,通過一個地面是高低不平混凝土的臨時出口,進了隔壁街區。我拉起衣領,看著他慢慢穿越那區,然後消失在幾棟全新完工的建築後方。那些低層長形棚式建築是以明亮的波狀金屬建造,看來附近應該是某種商業園區。園區內有網狀分佈的狹窄柏油路,雨水淋濕的路面散發出光澤。路緣是混凝土,鋪得很高,看起來很新、很光滑。我又看到林肯轎車出現在那些建築物間的空隙中,慢吞吞地移動著,像是要找停車的地方。接著車子又開到另一棟建築後方,後來我就再也沒看到了。
「妳跟艾略特確認過了嗎?」
「重點來了。」貝克說。
「不。」他說。他拿出一支體積很小的銀色手機。「這個也不通。」
「我知道,」我說,「我太快下結論了,抱歉。」
「電池掛了。」他說。他雙手拿著那個裝置,兩隻大拇指在上面按來按去,很像在打遊戲機。「這不能用了。」
「往北開到薩可,」我說,「現在出發。河中央島上的商場裡,有間叫咖啡咖啡館的地方,我們約在那裡碰面。最後到的人請客。」
「什麼另一位?」
我點點頭。
所以會是誰?也許是某個重量級的政府單位,比如說緝毒署。也許緝毒署是為了那位女傭而來。也許他們的特勤小組已經在倉庫完成取締行動,不想讓貝克知道他們就要來找他了。
「那最好把她房間清乾淨點,」我說,「到處都會有指紋、頭髮跟DNA的。」
那兩個保鑣逃脫了。
她點頭。「第二天後,就沒人見過她了。」
「黑色的林肯橋車呢?」我說,「就是往那個方向開去的?」
「抓好你那邊。」
「我能進行B計畫嗎?」
「妳還是站在葛洛斯基這邊嗎?」
「那她到底是誰?」我問。
「沒有。」
「一模一樣。」她說。
「這不可能。」她說。
「這樣至少比較安全。」
我看到他用右手從褲子口袋拿出一小根粉筆,行經一根路燈柱時,順手在上面打了個勾。這是那根路燈柱上的第五個記號。五個星期,五個記號。前四個記號已經因時間而變淡了。我透過小型望遠鏡看著那些記號時,他已經走進停車場,回到車上,慢慢開走了。接著,我把焦點移回垃圾桶。
「看見了。」他說。
「為什麼問這個?」
「立刻,」她說,「馬上。我一定得這麼做,沒別的選擇。不過我會先上電腦查,找出是誰安排她進去的,再親自告訴對方這個消息,當面賠罪。不這麼做的話,等事情一爆發,我就完全沒機會道歉了。上頭會取消我的所有通行密碼,然後給我個紙箱,叫我三十分鐘內清完自己的桌子。」
我搖搖頭。「同樣的道理,」我說,「他們已經習慣我了,不太可能再懷疑我。」
「我猜,錐鑽是用來撬鎖的。」貝克說。
「她今天早上死了。有人替她做了非常徹底的乳|房切除術,而且沒有麻醉。」
「我們打算否認她來過這裡,否認我們看過這個人。而且這裡也沒有她來過的證據。」
我把錢收進口袋。
「我們要知道她被抓的時候穿什麼鞋。」
他把鞋子遞給我。我接過之後茫然地看著。這只女鞋的尺寸是六號,給小腳穿的,不過鞋頭弄成大大的球形,而為了在視覺上協調,鞋跟也加得又寬又厚。看起來就像想湊流行而製作出的粗陋款式。鞋跟內有個挖空的長方形凹洞。這也跟我鞋子上的一模一樣。要弄出這個洞,需要熟練的技巧,還要有耐心。而且不能用機器來挖。我想像某處的實驗室裡有個人正在幹活,他前方的長椅上放著一排鞋子,空氣中彌漫著新皮革的氣味,一組雕刻工具在他面前擺成小小的弧形,而他四周的地板上積了一堆捲曲的橡膠碎屑。政府人員設計的這種小機關,大多都是以出乎意料的低水平技術製成。不是所有人都在用會爆炸的原子筆,或者嵌進手錶裡的照相機。到大賣場買個商用電子郵件裝置,再買雙樣式普通的鞋子,這樣就算很先進了。
她本來盯著杯子,現在抬起頭看我。「所以你才會問我那件事?」
「你在想什麼?」貝克問。
「這地方安全嗎?」她說。
「這麼做也沒用。她還得把腳上的那雙鞋也丟掉。鞋跟的凹洞不就說明了一切?」
「沒錯,」我說,「她的衣櫃裡留著什麼鞋?」
我沒說話。泰瑞莎很幸運,但那位女傭很倒楣。一件事有好的一面,也會有壞的一面。蘇珊喝了一小口咖啡,做了個鬼臉,彷彿那杯咖啡的味道變壞了,然後她又把杯子放下。
「我藏了包東西,」我說,「裡面有妳的葛拉克手槍跟彈藥,以及其他一些工具。而她發現了這包東西,還藏和*圖*書到她平常開的那部車上。」
「你得忘掉昆恩的事,」她說,「別再想了。」
他拿著報紙在眼前看了大約二十分鐘。我看得出他是真的在讀。他認真讀著每個版面,只略過體育版,而以他身為洋基隊球迷的角度來看,我覺得這點有些奇怪。不過話說回來,我猜身為洋基隊球迷,他應該也不會想看任何關於巴爾的摩金鶯隊的消息。
我突然想起貝克還說了些其他事。
我睜開眼,凝視著海浪,直接把拉鍊帶上,沒再看任何一眼。接著我站起來,走到運屍袋尾端。哈雷已經就位等著了。我們各自抓著袋子四個角,同時抬起來,走上岩石區。他帶我往東南方走,到了岸邊一處有兩塊大花崗岩架交會的地方,它們中間有個陡哨的V字形裂縫。裂縫半滿著流動的水。
「嘿,我還不是,」他說,「杜克也一樣。」
「所以妳想怎麼做?」
我搖搖頭。「不是泰瑞莎,」我說,「是另一位。」
我點點頭。「感覺就像待在一個四面都是鏡子的房間裡,事件接踵而來,每一件感覺都很不真實。」
哈雷利用接下來五次浪潮的浮力,讓袋子一次一點慢慢往外移,直到它整個掛在裂縫中。我抓住的這頭其實已經空了。屍體因為地心引力而擠在運屍袋另一頭。哈雷看著海面,抓準潮水進來的時機,然後低下身子,將拉鍊直接拉到底,再倉卒地趕到我身邊,替我抓住一邊的角落。他抓得很緊。第七道浪進來,濺起的浪花把我們全身都浸濕了。潮水注入裂縫,也填滿袋子,而它消退時,便把袋子裡的屍體直接吸出去。屍體在水面靜止了一下,接著就被底流帶走,沉向深淵。金色長髮在水中飄動,蒼白的皮膚反射出綠色與灰白色光線,然後整具屍體就消失不見了。水流掉時,裂縫中泛起紅色的泡沫。
我回想起海水湧進運屍袋,然後帶走屍體的樣子。我看著水面下流動的頭髮。我看見潮水沖洗著血水,將血稀釋成粉紅色。我一點也不餓。
「處理掉這些沒用的東西吧,」他說,「你拿去丟到海裡,行嗎?」
「我猜這電池應該沒辦法持續八週那麼久。」
「我不知道,」我說,「希望沒事。」
「我是來告訴你,他們已經設計好砲彈軟殼。接下來就要進入重要階段了。」
我放下話筒,望向窗外。「可能是天氣。」
「當家長就是要操心,」我說,「這樣能讓他更集中精神。」
「我不是只拒絕你,」她說,「其實我很想跟你跳舞。謝謝你邀我,我從來沒跟任何人跳過舞。」
「我身上完全沒錢。」
「妳檢查過她的衣櫃嗎?」
我轉回來,看見他從袋裡取出一雙鞋子。黑色的,鞋底很厚,這就是我每次見到她時,她腳上穿的那雙。
我快不能呼吸了。
「是嗎?」
我聳聳肩。「貝克給了我一把貝瑞塔M9,」我說,「所以我會見機行事。要是他彎下腰想看我的鞋,我就朝他額頭中間送顆子彈。」
我第五次見到她,是她開著一輛橄欖綠雪佛蘭載我到馬里蘭州的亞伯丁。我當時正在重新考慮到底要不要讓真正的藍圖外流。這非常冒險,通常我不會擔心這種事,可是我們的進度實在不夠,雖然柯爾已經查出葛洛斯基去的祕密地點,明白他如何置放文件,也清楚他怎麼知會對方東西已送達,但她還是沒看到對方取走文件,也仍然不知道對方的身分。
「這很明顯,」她說,「思考一下時間順序。我們就從今天算回去。十一個星期前,我搞砸了監視照片那件事,所以十個星期前,上頭就不讓我辦這件案子了。不過由於貝克實在是條大魚,我不能就這麼放棄,因此我在九個星期前派泰瑞莎去臥底,沒讓上級知道。不過也正因為貝克是條大魚,所以他們也不想放棄,於是把這件案子交給某個人辦,沒讓我知道,而那個人在八星期前派了這位探員以女傭身分混進去,時間點剛好就接在泰瑞莎後面。結果,泰瑞莎不知道那位女傭到貝克家臥底的事,而女傭也不知道泰瑞莎已經在裡頭了。」
「這裡的激流還真他媽強勁。」哈雷說。
「他們會讓她活著嗎?」
「妳在那裡待多久了?」
「是廚房女傭?」
「貝克怎麼辦?」
她盯著我。「是泰瑞莎?」
「那是你的問題。」他說,「跟我無關。」
「不盡然。」我說。
「八個星期,」貝克說,「傭人在我們這裡都待不久。這裡太偏僻了。而且,你知道波利的為人吧。杜克也不是很好相處。」
我們把沒喝完的咖啡留在桌上,走出門口,穿過賣場內的走道,然後走進外面的雨中。我們的車停得很近。她在我臉頰上吻了一下。接著,她坐進那輛福特金牛座,開往南方,而我則回到紳寶上,開往北方。
我們沉默了好一段時間。然後貝克重新把我那些東西放到抹布上包好,扔進他的袋子。他把沒電的電郵裝置丟回去,再將女傭的鞋子放在最上面。那雙鞋看起來黯淡而空洞,散發出一股淒涼感。
「一對一比較有效,」她說,「就像戒酒治療。」
我瞥了哈雷一眼。他正看著窗外的雨。
「這很合理,」她說,「上頭可能把這案子交給波士頓的分處。從地理位置來看,那裡很適合。而這也正好解釋了我們為什麼沒在華盛頓特區聽到風聲。」
我再看看波利,他還在等,他是個白痴。他在雨中,而我在車上。我放開煞車,讓車子慢慢滑過柵門,再用力踩下油門,直奔屋前。
「我們得找到她。」我說。
「她會沒事嗎?」
「你能在他們檢查她的鞋子前找到她嗎?」
我又別過頭,看著大海。灰色海面起起伏伏。我實在想不透。她找到了東西藏起來?
我別過頭,看著窗外的大海。她為什麼要撿起來?為什麼不留在那裡就好?這算是某種女傭的本能嗎?她不想讓這包東西浸濕?還是有什麼其他原因?
「好吧。」我說。
「他們怎麼發現的?」她問。
「她的鞋子裡有個電郵裝置,」我說,「跟我的一模一樣。鞋跟裡那個凹洞還是同一個人挖的,我認得出那種手法。」
屋裡沒有活動跡象。廚師不在,理察在用餐室裡邊吃三明治邊看著外頭的雨,三明治想必是他自己做的。伊莉莎白還在同一個房間讀著《齊瓦哥醫生》。貝克則是不見蹤影。扣除他可能去的地方後,我猜他一定在那個小房間裡,或許正坐在紅色皮椅上看著自己的機槍收藏品。到處都很安靜。我不明白。蘇珊說看到五個貨櫃,貝克自己也說這個週末有大事要忙,但這裡根本沒人在忙什麼事。
「這很難處理,」她說,「我本來想讓他知情,然後要他提供假情報給對方。這麼一來,我們就能繼續調查,不必冒險讓重要資訊外流。」
「也就是說我們的祕密藍圖被送到市立焚化爐燒掉?」
「妳在八個星期前派了另一位探員進去,」我說,「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上樓回到杜克的房間。內線可以用。波利在第三聲鈴響時接起來,不過我馬上掛掉。外線則毫無反應。我還握著話筒,貝克就出現在門口。
「那好。」我說。
「所以妳想讓真正的藍圖流出去?」
「他說她是他的一些朋友推薦的。」
我當時也的確賭上這條命,因為我還繼續穿著自己的鞋。我上樓回到杜克的房間,打開他的衣櫃。裡面有四雙鞋。這些都不是我在店裡會挑的款式,但看起來還可以,而且尺寸跟我差不多。不過我還是把它們留在原位。這麼快就換另一雙鞋,很容易引起懷疑。再說,如果要丟掉我這雙鞋,也得找個合適的地方丟。沒理由把它們留在我房間讓人發現。我必須把它們弄出屋子,而這麼做並不容易,尤其是剛才在廚房發生了那件事之後。我總不能拿著鞋子就這麼走下樓。該如何解釋?什麼?這個嗎?噢,這是我剛到這裡時穿的鞋子。我現在要出去把它們丟到海裡。或是裝成我突然不喜歡這雙鞋的樣子?所以,我還是繼續穿著。
是報紙,不是信封。十年後,我人在緬因州,躺在一張床上,想起自己跟多明妮.柯爾跳舞,也想起有個叫葛洛斯基的傢伙緩慢仔細地摺好報紙後,盯著水面的上百根帆船桅杆。這似乎跟我現在經歷的事件有某種關聯。是這個,不是那個。接著,我又想到女傭把我那包東西藏在後車廂底層的事。她一定沒在那裡藏其他東西,否則貝克就會發現,然後像在法庭展示證物那樣放在廚房桌上。不過,那輛紳寶的車內地毯已經很舊,也有些鬆脫了。如果我是她,除了把槍藏在備胎的空間裡,可能還會把文件藏在車內地毯下方。我可能會做筆記,留下紀錄。
「我什麼都不知道的話,很難做事。」我說。
我沒說話。
我別過頭。「我認得他的手法。」
hetubook.com.com「查到幕後那個壞蛋的線索了嗎?」
「不知道,」我說,「我沒當過聯邦探員。」
「有編號,」他說,「我們跟奧地利原產公司那裡確認過了。當然,是用電腦確認。我們在這方面有點門路。總之,這把槍大約一年前賣給美國政府。他們訂了一大批,發給執法單位人員,男探員用十七型,女探員用十九型。我們就是從這點知道她的身分。」
「也許我們應該私下練習。」她說。
「因為我們不想這麼做。」我說。
「他們研究的東西本身看起來很不真實。那是種很奇怪的裝置,外觀像是大型飛鏢,但裡面沒有炸藥。」
「你要中止行動嗎?」她說。
我走出屋子,拉起大衣的領子。風變小了,雨也終於不再橫著下。那輛林肯還停在屋子轉角,不過後車廂已經蓋起來了。哈雷正用拇指敲打著方向盤。我坐進乘客座,把椅子往後調,挪出放腳的空間。他發動引擎,啟動雨刷,然後往前開。到柵門時,我們得停下來,等波利解開鏈條。哈雷胡亂撥著暖氣開關將溫度調高。我們的衣服還很濕,因此窗戶開始起霧。波利的動作很慢,哈雷又開始敲方向盤了。
「奇怪。」他說。
「她最後一次聯絡妳是什麼時候?」
「我一定會告訴你的,」她說,「我保證,如果我安排了另一位探員,一定會告訴你的。」
「為什麼?」
我點點頭。「你一定忙得要命,我看得出來。客人這麼多,一個人還應付得來,真是奇蹟。」
「那時候我在店後面,好像在講電話吧。」
「這些東西就在我們給她開的那輛車上。」他說。
「所有電話都不通。」他說。
「妳怎麼安排她的背景資料?」
蘇珊點點頭,沒說話。我腦中又清楚響起貝克的聲音:你可以賭上這條命相信我,那就是我一定要開始檢查大家的鞋子。
「你跟哈雷出去一趟,」貝克對我說,「然後把那輛紳寶開回來。」
「什麼?」
「就跟我的事業一樣。」她說。
「你看到了?」
「也許收垃圾的是中間人。」
我們擱下袋子,讓頭部那側懸空於裂縫中。拉鍊那面朝上,因此屍體是躺著的。我抓著腳部這頭的兩個角落。雨水讓我的頭髮平貼著頭,還流進我的眼睛。感覺十分刺痛。哈雷跨立在袋子上方,然後蹲伏著將頭部那側再拉向外面一點。我配合他的動作,一點點在濕滑的岩石上小步前進。下一波潮水進來,流到袋子下方,使袋子稍微漂浮起來。哈雷利用這短暫的浮力,讓袋子再往外滑一點,我也跟著動。潮水消退,裂縫裡的水又跟著流光,袋子也往下垂。雨水敲打在僵硬的橡膠上,也猛擊著我們的背。冷得要命。
他臉上那個黃色凹洞又對著我笑了。我在想,要是夠用力,我應該能一拳打掉那些爛牙,然後一路塞進他細瘦的喉嚨。不過我沒動手。波利解下鏈條,將柵門打開。但門還沒完全打開,哈雷就踩下油門,車子立刻衝了出去,車身兩側離柵門大概各只有一吋的空隙。慣性使我整個人緊貼著座椅。哈雷打開車頭燈,加速前進,車尾後方濺起很高的水花。我們往西走,因為一開始的十二哩路也只能往這個方向。接著我們往北轉上一號公路,遠離伊莉莎白帶我去的地方,遠離老果樹海灘跟薩可鎮,朝波特蘭走。由於天氣太陰沉,外面什麼也看不見。我只能勉強看到前方車輛的尾燈。哈雷沒說話,只是不斷在座位上前後搖晃身體,還有用拇指邊敲方向盤邊開車。他開車很不穩,不是重踩油門,就是重踩煞車。我們一下加速,一下減速,一下又加速,一下又減速。這二十哩路感覺真漫長。
他點點頭。「就藏在後車廂底層放備胎的空間裡。」他把葛拉克放在桌上,接著再拿出兩個備用彈匣,擺在槍的旁邊,然後取出尖端彎曲的錐鑽跟磨利的鑿子,全部排在一起。還有安傑.多爾的那串鑰匙。
我搖頭。「是昆恩殺的。」
「我們離家很遠,沒人會知道的。」
「可惡,」多明妮說,「我浪費了五個星期。」
「我以前看過死人。我也知道以後還會再看到。」
他把裝置遞給我,於是我放下鞋子,從他手中接過。我按下熟悉的電源鈕,不過螢幕沒反應。
「午餐呢?」我說。
「怎麼說?」
「我們繼續吧。」哈雷說。
我沒說話。
「好,」她說,「所以你認為他們搜了那部車,而你那包東西害了她,對不對?」
「他們比較想用塑膠,不過我認為那只是賣弄之詞。」
我沒說話。
我慢慢將拉鍊往下拉,看到她身體上的毀傷,就跟我十年前見過那次一模一樣。然後我的手停住了。我別過頭,將臉轉進雨中,閉上雙眼。我臉上的水感覺像是眼淚。
「貝克沒告訴你?」
他點點頭。「廚師下班了。你到外面吃,行吧?」
「你看到那位駕駛發生什麼事了嗎?」
亞伯丁是個小地方,位於巴爾的摩東北方二十幾哩處。葛洛斯基會選在星期日開車到大城市裡,然後在內港區將文件放好。當時這地方正大肆整治,是個新興的好去處,不過剛開始還沒什麼人潮,所以大部分時候都是空盪盪的。葛洛斯基有輛私家車,是開了兩年的馬自達,車身是亮紅色。把所有因素都納入考量的話,他開這部車十分合理。這輛車不是新款式,但也不便宜,因為它的車型在當時很受歡迎,所以定價不會打折,而且在二手車市的行情也很好。另外,這輛車是雙人座,要載他小女兒的話不方便。因此他一定會換車。我們知道他太太並不是有錢人。換作別人,我可能還會替他們家擔心,不過這傢伙可是個工程師。他的選擇很聰明。他既不抽菸,又不喝酒,遲早有一天會存夠錢,然後趕快去買輛更棒的後輪傳動手排車。
「有可能。」
後來,我們都跳得喘不過氣了,於是又坐下來,點了更多啤酒。就在這時,我突然想通了葛洛斯基在做什麼。
「你們兩個替同一個人工作嗎?」我問他。
他往左邊瞥了一眼,也就是我的右手邊,朝著商業園區的方向。
我將紳寶開回原來那間車庫停好,然後走到庭院裡。技|師還在第三間車庫,裡面仍然空無一物。我看不出他在做什麼,也許只是在躲雨吧。接著,我跑回屋子。貝克一聽到金屬探測器響起,就到廚房來見我。他指著那個運動提袋。袋子還放在桌上,就在正中央。
但是,這不太可能。緝毒署的特勤小組一定不只一批人馬。他們會同時行動。就算不是這樣,他們只要封鎖離這裡十二哩的那個路口就行了,而且要封鎖多久都行。這段十二哩路程根本無法通往別處。不管電話通不通,貝克都只能坐以待斃。
「沒有。」他又說了一次。
「你這麼認為?」
「她是被推薦來的,」他說,「我們沒在報上或哪裡刊徵人啟事。是我們在波士頓認識的一些人要她跟我們聯絡。」
我凝視著她。
我笑了。那時候,她看起來就像我所見過最沉著的人。她的眼神發亮,表情嚴肅,頭髮撥到耳後,穿著很短的卡其短褲和很小的卡其背心,腳上是襪子和傘兵靴,全身微黑的皮膚都像撲了層粉。
「或者是他的孩子。」
「掛了。」我說。
他拿出一包東西放到桌上,外層裹著一塊跟手巾差不多大、佈滿油漬的濕抹布。他攤開抹布,拿出達菲的葛拉克十九手槍。
接著,我走到花崗岩岸邊緣,揮動袋子,用力投擲出去。袋子在空中轉了幾圈,裡面的鞋子跟電郵裝置都甩了出來。我看見電郵裝置落進水面,立刻往下沉。左鞋以鞋尖先碰到水面,然後也跟著沉了下去。袋子像降落傘一樣,掉得比較慢,隨後輕輕降落在水面上,吸滿水後便翻轉過來,滑行般往海底而去。那隻右鞋則漂浮了一段時間,像艘黑色小船,上下左右顛簸搖晃著,彷彿想駛向東方。它爬上一道浪頭,又從浪的背後滑落,然後開始往側面傾斜,接下來再漂浮了大概十幾秒,就因為進水而沉沒,從此消失無蹤。
她穿著短褲和背心出現,還是沒流汗,皮膚依然像撲了層粉塵。她手裡那個資料夾已經比我第一次拿給她時厚上八倍。
「失蹤的人總會待在某個地方。從我們的角度看,這些女人是失蹤了,但那些抓走她們的男人知道她們在哪裡。」
「接下來呢?」我說。
「他們現在會採取什麼步驟?」他問。
「他們可能永遠不會檢查她的鞋子吧,」我說,「一旦他們以某個角度看她,就不太可能突然改變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你是壓力太大,」她說,「臥底很不容易。」
「你從昨晚才開始負責,」貝克說,「所以就別太自責了。你甚至還沒進入狀況呢。應該揪出hetubook.com•com她的人是杜克才對。」
「你是說女傭的事嗎?」
「她有個跟你一樣的電郵裝置。」
「事情怎麼發生的?」她問。
他手伸進褲子口袋,拿出一疊鈔票,開始先算了幾張,不過馬上又聳聳肩放棄,直接全部交給我。這裡一定有將近一千塊。
我上樓到杜克的房間。我不想把這個房間當成自己的,也希望永遠不用這麼做。我躺在床上,又開始思考,試著想通這整件事。很簡單,里昂.蓋伯一定會這麼說。注意一切跡象。徹底檢視你看過、聽到的每一件事。所以,我打算重新檢視一遍,可是卻不斷想起多明妮.柯爾。
我再點點頭。「把葛洛斯基拖過來,帶到行刑隊面前好好威脅一下。告訴他如果乖乖配合,給對方假的設計圖,我們就對他好一點。」
「我不確定,」我說,「我猜一開始是他們從電腦上知道妳派人臥底,而且是個女人。不過裡頭沒提到名字,也沒有其他細節,於是他們便開始找這個人。我想,他們會查出她的身分,有一部分也是我的錯。」
「女傭是他殺的嗎?」
「當然,」她說,「這個人可不是笨蛋。」
「我沒看到,」他說,「我在忙。」
店裡擺滿箱子,可是半個人也沒有,感覺好像平常大部分時間都是這個樣子。冷冷清清的,到處是灰塵。櫃台後方的店員年約五十,是個一身灰的傢伙。灰頭髮、灰襯衫、灰皮膚。他看起來像是十幾年沒出過店門。我本來想先買點東西再趁機問話,可是一見到他的樣子,我就什麼也不想買,於是乾脆直接上前問他。
「在這裡?」
那個星期日,我們跟蹤他,看著他停在巴爾的摩一處小船塢附近的停車場,下車後坐到一張長椅上。他是個毛髮旺盛的胖子,體型很大,但是不高。他帶著一份當天的報紙。一開始,他注視著水面上的帆船,看了一段時間後,便閉上眼睛,仰頭向著天空。天氣還很好。他就這麼坐著不動五分鐘,像隻蜥蜴一樣曬著太陽。接著,他睜開眼,拿起報紙開始讀。
她點點頭。「如果逮捕他,那會是個悲劇。他是個好人,也是無辜的受害著。而且基本上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對軍隊很有幫助。」
「就當零用錢吧,」他說,「晚點我們再談薪水的事。」
蘇珊與我靜靜喝著剩下的咖啡,我那杯嚐起來又淡又冷又酸。我根本不想喝了。我右腳上那隻鞋很緊,尺寸不對,而且我開始覺得鞋子上好像接了一組鏈條和鐵球。鞋裡的機關一開始還感覺很棒,既時髦又帥氣,很有巧思。我想起三天前,就在我剛到貝克家,就在杜克鎖上我的房門後,第一次打開鞋跟取出裝置時。當時,我覺得自己像電影中的人物。然後,我又想起最近一次打開鞋跟的情景,就在杜克房間的浴室,就在一個半小時前。我打開電源,看到蘇珊的訊息:我們得見個面。
「波持蘭。我們安排她住在一間公寓。她的身分是職員,不是女傭。」
「這些東西怎麼能證明她就是探員?」我問。
「除非對方那個隱形人真的買了艘帆船。」
「就我們兩個?」
我點點頭。他真的很厲害,並沒有馬上起身離開,而是在椅子上又坐了十幾分鐘,繼續看報。接著他才緩慢仔細地摺好報紙,站起來,走向岸邊看看停泊的船。最後,他將報紙夾在左邊腋下,轉身走回車上。
她又點點頭。「他那些朋友一定接受了認罪協商。這是我們最常用的方法。再說,他們也很樂意陷害對方,這些人沒什麼道義的。」
「沒有。」他說。
「好吧。」我說。
「我們一定要找到她。」她說。她又思考了一會兒。「她今天很幸運。他們要找的是個女人,然後剛好又先從女傭身上查起。我們動作得快點,可不能指望她還能這麼幸運。」
「真不錯。」我說。
「我不知道。」我說。
「那輛紳寶?」我得說點話才行。
「由你決定,」她說,「這就是你薪水比較高的原因。」
我開著紳寶在一號公路上往南開了兩百碼,進入第一個遇到的加油站。我到店裡買了瓶水和兩根棒棒糖。如果換算成一加侖的話,我買水付的錢比油價還貴上四倍。結帳後,我走出商店,在門口附近躲雨,然後撕開一根棒棒糖吃,趁這時候察看四周。沒人監視。於是我走到公共電話旁,投下零錢,打給蘇珊。我上次就記住了她的房間號碼。我彎腰躲在公共電話的塑膠罩下,避免讓雨淋濕。她在鈴響第二聲接起電話。
「對方很可能會懷疑。」
她別過頭,沉默了下來。「某個角度,」她重複我的話。「為什麼我們不直接把話說開?」
「行了,放下吧。」哈雷說。他已經喘不過氣了。
那是個無線電子郵件發送器,就跟我的一模一樣。
「它如何發揮作用?」
「妳什麼時候要通知司法部?」
話說完,她對我眨眨眼,然後走出辦公室,在炎熱沉悶的空氣中留下一絲非常細微的香味。
他點點頭。「那是完全分離的線路,」他說,「是我們自己裝的。外線呢?」
「別唬我了。」我說。
「沒有。」
「怎麼了?」她說。
「藏在她鞋子裡?」
「泰瑞莎用什麼方式跟妳聯絡?」我問。
他拿了右腳的鞋,翻到鞋底,用指尖從鞋跟上拔起一根大頭針,然後轉動橡膠鞋跟,像在開扇小門,接著又把鞋子翻回來。搖了幾下。一個矩形的黑色小塑膠製品掉出來,在桌面上發出清脆的撞擊聲。那東西正面朝下。他把它翻了過來。
「什麼時候?」
「只有多爾出賣你嗎?」我問。
「我只是上尉,」我說,「吃飯還得用食物券。」
「妳有自信不會讓對方逃掉?」
我把眼神移開。「希望是這樣。」
「妳去過那間公寓嗎?」
「她的電池沒電了。」
「但是?」
「也許半夜會有人從帆船上偷偷出來。」
「去試試你的。」他說。
「我想,」我說,「最後還是會吧。」
「她會想到把電郵裝置丟掉嗎?」
貝克點點頭。「我從頭到尾徹查過了,我對結果很滿意。只有多爾而已。其他人都沒問題,他們還站在我這邊。他們很遺憾發生這種事。」
「好吧。」我說。然後我把錢放回口袋,直接離開。
「不過她到底是誰?」我說。
「你看。」他說。
我沒回答。
「電腦裡沒有泰瑞莎的紀錄,」她說,「這是私下行動。」
「說不定根本就沒有人。」我說,「或許他們一開始先計畫好這樣的交件方式,而對方後來因為別的事被逮捕了。或是他臨時退縮跑掉了。或者他後來生病死了。也許這個計畫已經沒用了。」
「他們會派人來找她嗎?」
那種眼神鬼鬼祟祟,速度很快,一移過去又馬上回來。
「也許她沒被查到,」我說,「只是失蹤了,妳懂吧。失蹤的女人很多,尤其是年輕、單身又沒家人的。這種事隨時都在發生。光是一年就有好幾千件。」
「不只確認,」她說,「我找過他整顆硬碟,還有他在華盛頓特區總部主要伺服器上的所有檔案。一切可以查的都查過了。我搜尋了泰瑞莎、丹尼爾、傑斯蒂、貝克、緬因州、臥底,什麼都沒查到。他沒在任何地方寫過這些字。」
他的運動提袋放在桌面中央,非常顯眼,像是檢察官在法庭上展示的證物。他拉開拉鍊,在裡頭翻找。「你看這個。」他說。
「很久。我本來還以為自己能當上那裡第一位女主管。」
「開始了。」多明妮低聲說。
「餓死了。」我說。
「替誰?」
我注親著她,眼神很嚴厲,然後又柔和了些。咖啡廳裡的光線似乎有某種力量。從淺色木頭、髮絲紋金屬、玻璃、鉻黃色框架反射綜合起來的光線,就像能透視的X光,也像能讓人人說實話的藥。這種光線讓我看到伊莉莎白.貝克無法控制自己而真正臉紅的樣子。現在,我正等著這道光線也讓蘇珊做出一模一樣的反應。我正等著她因為被我拆穿而羞愧尷尬得臉紅,但我卻只看到一副驚訝不已的表情。一切全寫在她臉上。她突然變得十分蒼白,這是受到打擊才會有的反應。她看起來像是全身的血都流光了。這跟臉紅一樣是不可能裝出來的。
「妳要請客,」我說,「妳比我晚到。我要再點一杯濃縮咖啡,而妳還欠我第一杯咖啡的錢。」她茫然地看著我,然後走向櫃台,回來時替我帶了杯濃縮咖啡,她自己則是喝卡布其諾。她的頭髮有點濕,可見剛才她用手指梳理過頭髮。她一定是把車停在街邊,冒雨走過來,然後在某間店的櫥窗前看著倒影整理儀容。她靜靜數著剛找的紙紗跟硬幣,把我第一杯咖啡的金額拿給我。在緬因州,咖啡是另一樣比汽油貴上許多的東西。不過我想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吧。
「什麼另一位?」
我點頭。
「我從來不跳舞。」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