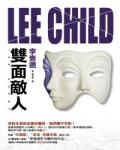1
我點點頭。我相信他。
我盯著看,時鐘停滯的時間似乎好久好久,然後分針又跳動了六度。又過了一分鐘,已是午夜時分,一九八九年變成了一九九〇年。
「這裡死了一個你們的人。」
「他可是一位將軍。」
我頓了一下,還是看不出來。
我又把電話放下。當時我已經進部隊六年多了,陸軍的咖啡是讓我樂意繼續服役的原因之一。無疑的,那是世上最棒的咖啡。陸軍的士官們,同樣也是最棒的。像這位女中士,她的故鄉是北喬治亞州的山區。我才認識她兩天,知道她離營時都住在北卡羅萊納州一處不毛之地的拖車公園裡。她有個小男嬰,她把他的一切都告訴我,但沒提過她有個丈夫。她全身都是骨頭與肌腱,身體就像琢木鳥的嘴一樣堅硬,但是她喜歡我。我看得出來,因為她幫我倒咖啡,如果有人不喜歡你,是不會幫你倒咖啡的。他們只會在背後捅你一刀。她開了我的門走進來,拿著兩個馬克杯,我們一人一杯。
「那是六小時前的事了,因為時差。」
我說:「我就是。」
「那個人是我嗎?」
「很多人帶了大榔頭去。」
我說:「給我看。」
「我的意思是,有些他擺在汽車旅館房裡的東西不見了。像是機票、訂位紀錄、護照以及行程表等等。大體而言,就是一般人會擺在手提箱裡面的那些東西。」
「你們警局曾經辦過在這裡發生的案子嗎?」
蓋伯說,我要控制場面。
蓋伯沒有回話。
「那麼是怎樣發現他的?」
「死人還會亂跑嗎?而且,他們到現在也還沒找到一個清醒的驗屍官。」
他說:「沒幾個人見識過。」他說這句話的樣子就像曾被徵召入伍的人。
「誰打來的?」
「他跑到對面酒吧去找來的嗎?」
「什麼情況?」
我說:「沒問題。」
他說:「有點太寬了,我在城裡開車絕對不會開它。」
他說:「偶爾。相信我,這裡就是那種旅館。」
我等待著。
他說:「二十美金就夠了。在這片被林地包圍的山區裡,沒什麼好貨色。」
他說:「驗屍官剛剛打電話來,他說他至少要再兩個小時才能趕來。沒辦法,今天是跨年夜。」
她把自己的馬克杯拿走後就離開房間了。蓋伯上校是我最上頭的老闆,儘管人還不錯,但他不太可能在跨年夜的午夜零點八分打電話,只是為了跟我說新年快樂,他不是那種人。有些高官會做這種事,一到假日特別來勁,就像自己是個小男孩似的。但是里昂.蓋伯完全沒想過嘗試這種事,對其他人都不可能,對我就更不用說了。即使他知道我在這裡,也不會這麼做。
史達頓說:「嗯。」
「很高興這世界上還有人在某個角落慶祝。」
「我本來以為別人可以去,但今晚在全美國還保持清醒的憲兵裡面,你大概是官階最高的。所以,就是你要去現場。」
他說:「也許可以接受。」
我說:「我沒想到要問。」
我對他說:「我們去看一下死者吧。」
我們倆沉默了一會兒,史達頓看著牆壁。
「柏林圍牆塌了一半,我在電視轉播上看到的,大家瘋狂慶祝著。」
「肯尼斯.勞勃.克拉瑪。」
「什麼時候?」
我說:「當然好。為什麼不喝?」
蓋伯說:「我知道他搭的飛機,我打電話給十二軍團,跟他的幕僚談過了。也告訴他們他的死訊。」
我說:「什麼情況?」
我問:「你待過陸軍嗎?」
三個警察待在車裡,有一個下車跟我碰面。他穿著棕褐色的警褲,短皮夾克的拉鍊拉到下巴,沒有戴帽子。從夾克上的警徽可以看出他姓史達頓,階級是副警長。我不認識他,因為我不曾在那裡服役。他是個一頭灰髮的五十歲男性,中等身高,有一點不結實跟過重,但是看他盯著我外套上徽章的樣子,可能是個退伍軍人,很多警察都是這樣的。
我從軍車調度場開走一輛悍馬車,從大門登記外出。我發現只要五十分鐘就可以開到汽車旅館。它位於博德堡北方三十哩外,我必須先穿過一片我不認識的北卡羅萊納州鄉間區域,沿路一邊是群聚的商店和矮小樹林,另一邊我猜是在冬季停耕的甘薯田。我第一次經過這個區域,以前從沒在那裡的部隊待過。沿路都很安靜,大家還在屋裡面開派對。我希望在他們全都開車踏上歸途之前就可以回到博德堡,避免塞車——不過,如果要我用悍馬車跟老百姓飆車,我倒是很樂意。我穩贏的。
我說:「怎樣?」
「依我的官階,我只能服從命令。」
我說:「問你問題,你就回答。有沒有?」
「鎮上的汽車旅館。」
他沒有回答我。
他說:「客氣一點。離開了部隊,他們才是老大。那是警察的司法管轄區域。」
「那你不也可以探頭出來嗎?」
有人敲門,進來的是車上其中一個警察。
我說:「我們可以幫你們驗屍,地點是在北邊的瓦特.瑞德陸軍醫學中心。」
我說:「好,現在我知道你住在哪裡,我會再回來問你一些問題。如果我在這裡找不到你,我會去你家找你。」
我說:「心臟病發,就這麼簡單。」
我問她:「妳有沙漠迷彩裝嗎?」
那傢伙說:「很有可能是心臟病。」
他又說了一次「媽的」,然後說:「聰明人幹嘛都喜歡做這種蠢事?」
我問:「發現他時就是這樣?」
我問:「怎麼死的?」
蓋伯沉默了好一會兒。
「為什麼?」
他說:「你終究還是決hetubook•com•com定來這裡一趟。你沒說死掉的是個二星中將。」
我說:「我了解警察,我曾經跟一個警察合作過。」
我把鑰匙跟紙條放進口袋,走到對街的酒吧去。每接近一步,就感到音樂變得更大聲,距離酒吧十碼遠時,我開始從通風口聞到啤酒香與菸味。我穿過停在外面的汽車,找到大門——那是一扇結實的木門,它擋住了外面的冷空氣。我一推開門就有一陣音樂和熱氣迎面襲來。裡面人群雜沓,舉目所及,是五百個人待在一堵堵黑牆圍成的空間裡,室內投射著紫色聚光燈,到處都是水晶球燈。我看到後面舞台上有個鋼管女郎,她匍匐在地上,全身只剩一頂牛仔帽。她到處爬著,一邊收取小費。
蓋伯說:「我知道,我和你講完電話後就打給警方那位調度員。他怎麼死的?」
我說:「心臟病發。發作時他正在和一個妓|女進行性|交易。如果哪隻蟑螂比較挑剔,大概死也不會去他待的那家汽車旅館。」
「你不想聲張這件事。」
「等下你就知道。」
我頓了一下,把陸軍的制式桌曆從十二月三十一日翻到一月一日。
我轉身對他說:「我還想得到更慘的死法。」
他問:「這樣會有問題嗎?」
「他在一週內就該回德國去。」
史達頓只是又對著我微笑。
蓋伯說:「我們要謹慎一點。」
「那房間呢?」
我說:「陸軍討厭改變,而且我們永遠不缺敵人。」
我說:「沒有疑點,反正他就是掛了。死因是心臟病發作,可能還有痛風,沒什麼值得我注意的。」
「嗯,然後我們又把他翻回去。」
他全身赤|裸,臉部朝下,是個年近六十的白人,很高,身形就像個身材日漸走樣的職業運動員,很多教練都是這種體型。他依舊有一身不錯的肌肉,但是處理事物的方式開始跟個老傢伙一樣——那些人的體力不管有多好,終究會變樣。他白皙的大腿上沒有腿毛,身上有些舊傷疤,留著灰色平頭,脖子後面的皮膚既粗糙又充滿皺紋。他可以說是典型的軍人:不管幾百個人看到他,一定都會說他是個陸軍軍官。
「他的全名是?」
我點點頭。灰色的皮膚是證據,他臉上的震驚與痛苦,還有他左臂突然出現的疼痛也是。我說:「病情很嚴重。」
「剛剛我在講電話。」
他頓了一下說:「剛剛有人打電話告訴你汽車旅館裡有軍人死掉?」
「在別州嗎?」
電話兩頭沉默了好一會兒。
我說:「病發時,那個女的在他下面。那是確定的,因為她必須用力把他推開才走得掉。」
我說:「他叫做克拉瑪。」
我們倆都沒說話。
我說:「我猜你也知道他的生日,還有出生地。」
他開口跟我打招呼:「少校。」
「你介意讓我看看嗎?」
她說:「新年快樂。」
「他有用過電話嗎?」
第一個疑點是:一個二星上將怎麼會在這裡投宿?我非常確定,如果他住進假日飯店,也不會被國防部質問的。
我點點頭——他是個老兵,沒錯。少校兩肩各有一小片一吋長的金色橡樹葉橫跨在肩章上。這傢伙往上面與兩邊打量我的肩章,這樣的角度其實看不清楚。但我看得出他知道這肩章的意義是什麼,所以他對官階很了解。而且我認出了他的聲音:凌晨零點過五秒打電話給我的人,就是他。他說:「我是瑞克.史達頓副警長。」他很冷靜,他見識過心臟病發死掉的人。
他看著我的車。
「什麼事?」
我說:「那個女人沒有留下任何蹤跡?」
四十分鐘後,一輛軍用救護車和另一輛悍馬車出現了。我告訴手下們把全部東西都拿走,包括租來的那輛車,但是我沒有看著他們辦事,反而是先回基地去。我在大門登記入營後又回到暫借的辦公室,叫中士幫我撥電話給蓋伯。我在桌邊等著,兩分鐘內就接通了。
他說:「真討厭,不是嗎?巴拿馬可能還比較刺|激一點。」
我說:「他搭的是什麼班機?」
致命的心臟病到底給人什麼感覺?沒有人知道,因為病發的人都死了。醫護人員的說法是:細胞壞死、血液凝固、缺氧致死以及堵塞的血管。他們猜想:心臟會迅速跳動,但卻沒有用,或者連心臟都已經動不了了。他們用的字眼通常是心肌梗塞或心室顫動,但這些對我們來講都沒有意義。其實他們只要說一句話就好了:「反正就是癱倒然後死掉。」肯恩.克拉瑪一定是這樣,他剛剛癱倒死去,許多祕密隨他逝去,但是他留下的麻煩幾乎把我害死。
「剛剛有個中士端了一杯咖啡給我。」
他頓了好一會兒,才說:「我還以為你在巴拿馬。」
我說:「你知道嗎?每次我不管到哪裡,我都會帶著一疊東西,像是機票、通行證還有訂位紀錄等等,如果我是從國外飛回來,我還會帶著護照。如果我是去參加會議,我一定會帶著手提箱.裡面會帶著其他拉哩拉雜的東西。」
再六十秒就到了。
我說:「他身上戴著十二軍團的番號臂章,這代表他的基地在德國。他昨天可能是從法蘭克福搭飛機到杜勒斯機場。一定是搭民航機,因為他穿著軍禮服,這樣才能獲得升等。如果坐的是軍機,他應該會穿戰鬥裝。他租了一台爛車,開了兩百九十八哩路,住進一間只要十五塊的汽車旅館房間,花二十塊召妓。」
我把椅子往後推,在桌後站起身來。電話鈴響,我猜是打來祝我新年快樂的。但卻不www.hetubook.com.com是:是個警察打來的,因為在他轄區裡有個軍人死在距離部隊三十哩外的汽車旅館裡。
「所以呢?」
我說:「沒有疑點嗎?」
「你的重點是什麼?」
「那又怎樣?」
蓋伯說:「媽的。他已經結婚了,還發生這種事。」
「那麼他怎麼召妓的?」
我說:「也祝福妳。妳不能起身探頭進來就好了嗎?」
「昨天從法蘭克福飛到杜勒斯機場的美航班機,下午一點抵達。他還有一段需要轉機的航程,是今天早上九點,從專飛國內班機的華盛頓機場到洛杉磯國際機場。他本來打算去爾汶堡去參加一個裝甲兵科會議。他是一位駐歐裝甲兵指揮官,是個重量級人物,這幾年已經在等著當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副主席,因為下一次就該輪到裝甲兵科出身的將領了。現任副主席是步兵科出身的,按照輪替的慣例,他是有機會出線。但是現在看來已經完全不可能了,對吧?」
「再說一次。」
我不需要去。像陸軍這種龐大的組織,人數比達拉斯小一點,比底特律多一點,說到「公事公辦」的精神,則是跟前兩者都一樣。目前軍隊總員額是男女加起來總共九十三萬人,他們的組成可以說就是美國全體國民的縮影。美國國民每年的死亡率大概是千分之八點六五,而在沒有戰事爆發的情況之下,軍人的死亡率並不高於或低於一般民眾。整體而言,他們比一般人口年輕,體能狀況也較好,但是他們抽的菸和喝的酒都較多,吃得較差同時壓力較大,訓練時還必須做各種危險的事,所以他們的壽命跟一般人差不多,死亡率也沒多少差別。就目前的兵力,如果用這種死亡率來計算,一年裡每天會有二十二個軍人死掉,死因包括意外、自殺、心臟病、癌症、中風、肺病以及肝腎衰竭等等,跟底特律或達拉斯的市民沒什麼兩樣。所以我不需要去一趟——我是個憲兵,不是個禮儀師。
電話那頭沉靜了下來。
他在電話那頭還是不發一語。
史達頓點頭說:「他立刻打電話給我們,當時那位女士早就無影無蹤,這是當然的。一開始他還否認她曾經來過,他假裝這裡不是那種旅館。」
我說:「她是個妓|女。這就是為什麼他會被發現,櫃檯那傢伙根本就認識她,看她沒過多久就跑出來,好奇發生了什麼事,所以進房查看。」
我說:「他有個綠色的帆布裝衣袋,棕色皮革滾邊的。我可以用十塊跟你賭一塊,他有一個成套的手提箱。兩者可能都是他老婆挑的,也許是跟LL畢恩郵購的,也許是在十年前買的聖誕禮物。」
「不是。」
「在這裡嫖妓要花多少錢?」
蓋伯說:「這是尊嚴的問題。我們不能任由一個二星上將這樣橫屍在公共場所,卻一點反應也沒有。我們需要有人到場。」
我說:「八分鐘前。我把這件事轉給部隊指揮部。」
「他是在什麼情況下被發現的?他自己打一一九嗎?」
我又點點頭。一點三十二分,克拉瑪在杜勒斯機場的租車停車場。而且依他開的里程數看來,那個數字顯示他是直接開到這裡,不太可能去做其他事——意思是,他抵達這裡是在七點半左右。如果他中途在某處停留吃晚餐,也許是八點半。如果他開車特別小心,也有可能是九點。
我嚐一口咖啡,熱熱的黑咖啡,世間極品。
對面的酒吧繼續傳來音樂聲,史達頓不發一語。
「人可能還沒散呢。」
「你也說了他的死因跟事發地點嗎?」
「去那裡要一個小時。」
「所以呢?」
「派對好玩嗎?」
「這裡不做黑的。」
我問:「你覺得呢?」
我說:「好,打給部隊的指揮部。」我把號碼給了他,我說:「新年快樂。」
我又在桌子後坐下。
「你有駕照嗎?」
他說:「這差事可真慘。」
她跟我一樣都穿著標準的叢林迷彩戰鬥服,袖子平整地往上捲。她的憲兵臂章戴得服服帖帖,我想她在內側用了安全別針固定臂章。靴子也微微發亮。
史達頓問我:「有什麼是我們該擔心的嗎?」
我說:「我可沒見識過死掉的將軍長什麼樣子。」
針動了,它往前跳動六度,這小幅的移動充滿了機械的精準度。它彈了一下,稍稍抖動之後又恢復停滯。
「請便。」
我點點頭。當說到「HMMWV」這個縮寫,都是用「悍馬」兩個字就帶過去了,但其實它的全稱叫做「高機動性多用途輪式車輛」,而且這名稱相當完整地描述了它的性能。在陸軍這種地方當兵差不多就是這麼一回事,他們說會給你什麼,就會給你什麼。
他說:「有必要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但是你要控制場面。如果這案子有問題的話。」
「他們還派你在跨年的時候當值班軍官?」
「我不知道。我十點來的,當時他已經在了。」
我往前跨步,走到床邊,左手往死者腋下的方向往下滑,然後把他翻過來。他的身體僵冷,但是才剛剛變硬。我讓他靠著背部平整躺下,觀察到了四件事:第一點,他的皮膚明顯呈現灰白色;第二點,他臉上還維持著震驚痛苦的表情;第三點,他之前用右手抓住自己的左臂,抓的部位就在靠近二頭肌的部分;第四點,他還戴著保險套。他早就沒有血壓了,因此不可能勃起,所以保險套只是空盪盪地套在身上,就像一片半透明的慘白肌膚。顯然他還沒有達到高潮就死了。
我說:「我自願的,我希望他們hetubook.com.com喜歡我。」
看著軍禮服的外套就像讀一本書,或是像在酒吧裡聽旁邊的傢伙訴說他一生的故事。這件外套的尺寸剛好符合床上那具死屍,上面有寫著「克拉瑪」的名牌,跟兵籍號碼牌相符。上面有用緞帶掛著的紫心勳章,還有在他第二、第三次受傷後加上去的兩枚青銅橡樹葉徽章,這跟他身上的傷痕也吻合。外套肩章上有兩枚銀星,代表他是個少將。他的兩枚兵科領章代表他是裝甲兵科的,從番號臂章看來,他隸屬於第十二軍團。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堆單位發給的獎章、一堆可以追溯到越戰跟韓戰期間的緞帶勳章,有些可能是死命拚來的,有些不是。有些勳章是外國政府發給的,因此他有權佩戴,但並不具強迫性。這是一件標準的長外套,是部隊發給的,不是跟外面裁縫訂製的,看起來雖然老舊,但他保養得很好。整體而言,這件外套告訴我,他只是喜歡炫耀軍功,本身個性倒不算浮誇。
過了一分,還有一分。
「我一跟調度員通完電話就跟他們說了。」
我又說了一次:「新年快樂。」 她把兩杯咖啡都擺在我桌上。
他說:「我要找憲兵執勤軍官。」
我自己待在一個借用的辦公室裡。牆上有鐘,只有時針跟分針,沒有秒針,是個不會滴答作響的電子鐘,它靜得就像這房裡的死寂一樣。我故意看著分針,它並未移動。
我說:「沒什麼事,只是有人沒辦法活到九〇年代。」
「人很多,一大群唱歌跳舞的人。」
「這種死法可真慘。」
我說:「我是李奇。」
「招什麼妓?」
她還是不發一語。我的電話又響起,她趨前幫我接電話,聽了大概十一秒之後才把話筒交給我。
他說:「別惹事。」
「還有他的班機號碼與機位編號,政府會幫他的機票出多少錢。你甚至已經知道他有沒有要求吃素,以及爾汶堡將安排他住進哪一間來訪軍官寢室。」
他說:「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她逃掉了。」
沒有皮夾也沒有零錢。
他說:「悍馬耶!」
他問我:「你喜歡嗎?」
「我沒拿任何東西。」
我問:「你有拿死者的任何東西嗎?」
他問:「怎麼回事?」
他沒有回我話。
我說:「你會拿到檢驗結果,我們的病理師會原原本本的把報告交給你。如果你看到讓你不高興的內容,我們會立刻把案子交回你手上,一句廢話也不會講。」
我長得比他的販賣機還魁梧,身上又都是徽章勳帶,他只好乖乖聽話。當我用這種語氣講話時,有哪個二十歲的瘦排骨敢不從命呢?他把屁股從凳子上翹起,伸手到後面去拿皮夾。打開後我看到他的駕照放在一個乳白色的透明塑膠夾層中,上面有照片、姓名與地址。
我查看口袋。都是空的——只有那輛租來的車的鑰匙。鑰匙套在一個1字形的塑膠鑰匙圈上,還附著一張紙片,上方用黃字印刷著:「赫茲租車公司」,下方則是一個用黑色鋼珠筆寫的車牌號碼。
「我沒見過他。」
裡面除了汽車座椅清潔劑的臭味以及租車合約的副本之外,別無他物。克拉瑪是那天下午一點三十二分在華盛頓附近的杜勒斯機場取車的。他用的是個人的美國運通卡,還因此打折。他拿到車時的里程數是一萬三千兩百一十五英里,現在里程表上面顯示的是一萬三千五百一十三英里,兩者相減後我想他開了兩百九十八英里的車程,這數字大概就是兩地之間的直線距離。
我說:「多少錢?」
我說:「你們曾經翻動他嗎?」
史達頓說:「可能吧,但是要驗屍才能確認。」
「他可能也把皮夾放在裡面,因為他穿著軍禮服,那麼多的勳章與緞帶會把外套的內袋繃得太緊,擺皮夾不太方便。」
「如果軍方高層要花五年才搞定迷彩裝紋路修改的事,那麼裁軍這件事要花他們多久時間?到時候搞不好妳兒子都已經大學畢業了,所以妳就別擔心了。」
「我想說的是,為什麼我沒跟你一樣得到這些訊息?」
她說:「嗯。」但口氣裡還是不相信我。她接著說:「你覺得他是一塊讀大學的料?」
一分鐘了。
我看著床頭擺枕頭的地方,床單跟被子都還很整齊。死者躺在床單上,床單未被掀開,因此枕頭還整齊地擺在上面。但是床上有個頭形的凹痕,還有被手肘與腳跟弄縐與往下陷的痕跡。
他走回外面車上,我則回到悍馬車上,用一〇五的代號呼叫,意思是「請求一輛救護車」。我告訴我的中士,叫她隨車要派兩個可以把克拉瑪所有私人物品列一份清單並且打包的人員,把東西拿回我辦公室。然後我坐在駕駛座,等著史達頓跟他的手下都走掉。我看著他們在霧中加速,又回到屋裡,從克拉瑪的外套裡取出鑰匙,又回到外面把福特轎車打開。
史達頓只是對我笑著。
「我想,在他付錢後,那個妓|女看到他把皮夾擺在哪裡。開始辦事後他就發作了,她看到自己有點小利可圖,於是把手提箱偷走。」
他喀一聲把電話掛斷,我回電給剛剛那位警方的調度員,問到了汽車旅館的名字跟地址。然後我把咖啡留在桌上,告訴中士這是怎麼一回事,回到我的寢室去更衣。我想所謂「去現場」意味著我不能穿著戰鬥服過去,於是換上綠色軍禮服。
我看著他,然後就懂了。一個在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的廉價旅館,旁邊還有個卡車休息站與上空酒吧,地點在軍事基地三十哩以外的地方。
www•hetubook•com•com
他說:「有。」
我說:「將軍也會死,跟任何人一樣。」
我把屍體復原成趴下的姿勢。這可不容易,他至少有兩百磅重。
汽車旅館位於一片漆黑的低矮商區的某個角落,地點在一個大型高速公路交流道旁。商區中央是個卡車休息站,休息站有一個假日才開張的廉價餐館,還有一個連十八輪卡車都停得下的加油站。有間煤渣磚砌成的酒吧,到處都是霓虹燈,沒有窗戶,上頭掛著一個寫著「脫衣舞孃」的粉紅色霓虹招牌。停車場有一個美式足球場大,上面到處是柴油引擎排氣所留下的噴痕,以及沾著五顏六色油漬的污土。酒吧裡傳來嘈雜的音樂,車子在外面七橫八豎地停著。在街燈下,整個區域閃耀著硫黃色的光芒。晚間的空氣很冷,霧氣一層層飄浮著。汽車旅館就在加油站對街,二十個破爛的房間彎曲地排著,屋外的油漆嚴重剝落。旅館看來空無一人,走道左邊底部有間辦公室,同時有個投幣式的入口以及發出嗡嗡聲響的可樂販賣機。
「剛剛我沒看到這則新聞。」
我查看衣櫃,裡面有整套正式的軍禮服,分別掛在三個整齊擺好的衣架上,三個衣架依序擺著摺好的褲子、外套與襯衫,領帶還在襯衫衣領上。擺在衣架上方隔板中間的是一頂校級軍官的軍帽,上面到處是金色的鑲邊。帽子的一邊擺著一件摺好的白色內衣,另一邊則是摺好的白色拳擊短褲。
「兩天前。」
她說:「長官,是蓋伯上校,人在華盛頓。」
「櫃檯那傢伙有看到她嗎?」
他說:「新年快樂!」
「哪裡?」
他帶我走進去,啪一聲按下開關,打開屋內走廊的燈,又按另一個開關把整間屋子的燈打開。我看見一個標準的汽車旅館室內規劃:一個一碼寬的大廳,左邊有個衣櫃、右邊有浴室,然後是一個十二乘二十呎、嵌在牆壁上的長方形櫃檯,跟衣櫃一樣深,床舖則是跟洗手間深度一樣長的雙人寬床。天花板很低,遠處有個寬窗,掛著簾子,窗子下方有個穿過房間牆壁的冷暖兩用空調機。房裡大部分的東西都已經老舊破爛,褪成了棕色,整個地方給人一種黯淡、潮濕與悲慘的感覺。
「嗯,我看到他手上的婚戒,還有他西點軍校的戒指。」
我說:「它的性能就像廣告中講得那麼神。」
「從巴拿馬把你調到博德堡?為什麼?」
「電話壞了。」
房裡很安靜。我只聽得到從外面警車上無線電對講機傳來的對話,還有對街酒吧裡的音樂。我轉身回床邊,看著死者的臉,我不認識他。他在右手戴了一枚西點軍校戒指,左手的老舊婚戒大概有九克拉。我看著他的胸膛,因為他伸手去抓左邊的二頭肌,兵籍號碼牌被右臂擋住。我好不容易把他的手抬起,把號碼牌拉出來,牌子周圍有一圈用來防止碰撞出聲的橡膠。我把牌子拿起來,直到鍊子被他的脖子撐緊才不再移動。他姓克拉瑪,是個血型O型的天主教徒。
衣櫃底層擺的是一雙靠在一起的鞋,旁邊擺的是一個已經褪色的綠色帆布衣袋,整齊地靠在衣櫃後側的板子上。黑色的鞋子被擦到發出微光,捲好的襪子緊緊塞在裡面。這個衣袋是他自購的,每個容易受力的地方還加上了皮革來加強支撐力,但是皮都已經破舊了。袋子不是裝得很滿。
我又說了一次:「好吧。」
他說:「那你就把屍體弄走吧,但是要給我一份報告。」
史達頓不發一語,但我感受不到他有敵意,有些小鎮警察還挺上道的。像博德堡這種大型基地會對它周邊老百姓的世界造成大大小小的許多影響,因此憲兵必須花很多時間跟警察交手,有時他們真是眼中釘,有時卻不是。我感覺得到史達頓不會是大麻煩,他很鬆懈。重要的是,就我的標準而言,他可以說是個懶人,懶人總是樂意把燙手山芋交給別人。
我說:「大概吧,都已經死透了。」
她說:「真的會快樂嗎?」
我說:「我們贏了,那不是好事嗎?」
「那是政府開放的,那半邊是個自由的城市,四十五年來我們一直把它保持在這種狀態。」
我露出微笑。「可以接受」馬上要變成「何樂而不為」了。兩小時後史達頓還有別的事要忙,接下來一堆派對要結束了,路上會一團混亂。兩小時後他會求我把這老傢伙弄走。我不發一語,那警察又回車上去待命,而史達頓則一路走進房裡,面對窗簾拉下的窗戶,背對著屍體。我把掛著大衣的外套拿出衣櫃,把它掛在走廊燈光照射著的浴室門框上。
他說:「海軍陸戰隊,軍階是二等士官長。」
我說:「嗯。他什麼時候住進來的?」
我放下號碼牌,離開床邊,查看了床頭櫃與櫃檯,兩者都空無一物。房間裡沒電——我猜,像這種地方,旅館櫃檯會有付費電話。我走過史達頓身邊去查看浴室,在洗手台旁邊有一個他自購的黑色個人用品皮革包,拉鍊是關著的。包包上有浮印的KRK三個縮寫字母。打開後我發現裡面有牙刷、刮鬍刀以及旅行用的牙膏與刮鬍泡,沒有其他任何東西:沒有藥物、沒有心臟病的處方箋,也沒有保險套。
「看不出來。」
我把外套放回衣櫃裡,查看他的褲子,裡面也是空無一物。鞋子裡也只有襪子。帽子下面也沒有藏東西。我把裝衣袋拿出來,放在地板上打開。裡面有一套戰鬥服、一個M43野戰帽,以及換洗的襪子、內衣各一,還有一雙擦亮的素面黑色戰鬥皮靴。裡面有一m•hetubook.com•com個沒放東西的部分,我猜大概是擺個人用品袋的,除此之外,別無他物。我把它合起來,放回原處。我蹲下看看床底,也沒有任何東西。
床上有個死者。
「很快我們就沒有敵人了。」
「我們的人?」
蓋伯說:「我查過了,他是五二年班的。」
那是一個黯淡的地方,日光燈讓整個空間看來一片慘綠,門口的可樂販賣機不斷傳來噪音。牆上有一具付費電話機,地板上鋪的是老舊油布,及腰的櫃檯裡面空間很狹小,它的材質是人們常在地下室使用的那種假木板。一個旅館員工坐在後面高凳上,他是個大概二十歲的白人,一頭長髮看來沒洗,下巴往後收讓他顯得很沒男子氣概。
「你的意思是……」
「因為死掉的那傢伙是個二星上將。」
她說:「沒待過沙漠。」
「要喝咖啡嗎?」
他沒有對我說些什麼。我轉身推門出去,回到我的悍馬車上去等。
我說:「我是傑克.李奇,今晚的憲兵執勤軍官。」他也認出了我的聲音,於是露出了微笑。
我說:「我接到了命令。」
「棒透了,我女兒也來了。」
「把屍體送去瓦特.瑞德醫院去檢驗。」
我說:「我老爸也是海陸的。」我在跟海軍陸戰隊出身的人講話時,總是把這點講得很清楚,這讓我的血統顯得「純正」一點,他們也不會只是把我當成陸軍大兵。但是我講得很含糊,沒提到他最後官拜上尉。被徵召入伍的人跟軍官不見得就看對方順眼。
他說:「你不需要來一趟嗎?」
門後有個穿著黑色T恤的大塊頭站在收銀機後面,他的臉被陰影擋住,在隱約的聚光燈餘光中我看到他的胸膛跟油桶一樣大。音樂震耳欲聾,大家都擠在一起,連牆邊也都站得滿滿的。我走到外面,讓門甩回去,在冷空氣中靜待片刻,然後走回對街,直接去汽車旅館的櫃檯。
〈這就是心臟病發作嗎?〉當肯恩.克拉瑪停止呼吸、意識陷入一片死寂之際,也許這句話就是他的遺言。在臨終前他心頭浮現的是一陣恐慌。他玩火玩過頭了,不管就哪方面來講都是這樣,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他不該來這是非之地,不該跟這個人在一起,也不該把這原本應該藏好的東西帶在身上。但他本來已經確認自己安全無虞,在這遊戲裡穩操勝券、占盡上風。他臉上可能露出一絲微笑——一直到胸口的重重一擊把他打垮。接下來局勢完全逆轉,原本的勝利變成一場災難,他沒有時間補救任何事情了。
我說:「好像沒什麼值得不快樂的理由。」
「也許十五塊吧。」
史達頓在我身後說:「心臟病發。」
他說:「是個軍人。」
我說:「那就要看他除了機票那些雜物之外,還擺了什麼東西。」
他說:「可能也不會吧。」
她不發一語。
「多得是。」
「手提箱不在房裡?」
「你看過死於心臟病的屍體?」
「如果你是靠美國政府吃飯的人,可不是個好消息。」
「他死的時候正在嫖的那個妓|女。」
我說:「新年快樂。」
我說:「他可能就只是在床上去世而已,很多人都這樣。」
「指揮部又把這件事轉給某人,害我剛剛被人從派對中找出來講這件事,從頭到尾都知道了。」
他說:「好,很好。」頓了一會兒後他又說:「從頭到尾說給我聽,好嗎?」
蓋伯說:「你為什麼會知道?我一直在打電話,而你則是在汽車旅館裡查案子。」
我點頭說:「當然。如果是你,你想讓這件事傳出去嗎?」
我沒回話,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說:「好吧。」
我站起來搖搖頭,騙他說:「沒有。」
那傢伙頓了一下,他說:「你要幹什麼?」
史達頓用帶著微笑的聲音說:「但是,是在性|交之前還是之後?」
「什麼多少錢?」
他搖頭說:「沒有。」
他沒回我話。
「什麼時候?」
第二個疑點是:怎麼會被發現?這傢伙要了一個房間過夜,希望至少一直到第二天女清潔工來打掃以前都不被打擾。那他又怎麼會被發現?
「我只說有可能是心臟病發,完全沒談到細節與地點,現在看來,我的決定是正確的。」
我說:「不需要。」說完就把電話掛掉。
在倒數第二個房間外面,有鎮上的兩輛警方巡邏車隨意停著,中間夾著一輛平凡無奇的小轎車。車子已經冷了,車上到處布滿著霧氣。那是一輛基本款的四汽缸紅色福特汽車,輪胎寬度很窄,輪圈蓋是塑膠的。這一定是租來的。我把悍馬車停在右邊那輛巡邏車旁,下車後感到一陣冷空氣襲來。我聽到對街傳來的音樂更大聲了,倒數第二個房間的燈沒開、門沒關,我猜是因為警方想讓室內保持低溫,否則屋裡那老傢伙的屍體會開始變質。我急著要看他一眼——我可沒見識過死掉的將軍長什麼樣子。
分針又動了,它往前跳動,彈回來後又停滯下來。現在是午夜過了三分。電話又響了,這次是祝我新年快樂的人——我辦公室外面那位中士。
我說:「前面會有坦克幫你開路,我想這就是它規劃中的性能。」
我說:「別擔心,善後工作已經開始了,當地警察允許我把他送去瓦特.瑞德軍醫院。」
「他住這麼裡面,我哪看得到他在搞什麼鬼?」
「上面的紋路被改過了,加了一個個棕色的色塊,花了五年時間研究才改的。步兵那些傢伙說那叫做巧克力條。那紋路不好,以後一定會改回來的。但是他們又要花五年時間才能想通這一 點。」
我說:「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