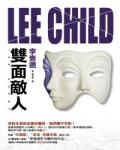16
我沒有回話。他起身後走到牆邊,用指甲去碰觸圖釘,依序查看了華府、史派瑞維爾、綠谷鎮、雷利市、博德堡、恐怖角以及哥倫比亞市等地方。
他點點頭說:「鐵鍬,我覺得起釘器這個名稱叫起來比較不順口。」
我搖頭說:「沒有人會發現我們,永遠不會。」
她說:「你動過地圖。」
「太冷了。」
我不發一語。
「還有四小時回程。」
接待櫃檯後沒有接待人員,房裡有兩個警探,他們都穿著花呢紋輕便外套,兩人都坐著背對我們,其中一個是克拉克。他正在講電話,我搖動門閂,兩人都轉身。克拉克頓了一會兒,看起來有點訝異,然後對我們揮揮手。我們各拉了一把椅子,坐在他的桌邊兩側,他還是繼續打電話,讓我們等他。我用這時間看看房間四周。副隊長辦公室的牆壁從腰部以上都是玻璃,裡面有張大辦公桌,沒有人坐。桌上我可以看到兩個石膏模型,就跟我們的病理醫師做的一樣,我沒有起身過去看,因為這似乎不太禮貌。
「應該會比我們想像得快,這是我們不希望發生的事。」
「他們終於招了。 」
她說:「你該低調點,他會打電話到處找你。」
她說:「好。所以殺卡邦跟布魯貝克的不是同一人。他們之間沒有關聯,我們的時間都算浪費掉了。」
「但它跟你們做的石膏模型相符。」
「你好好想想吧。這是個肥缺,而且陸軍永遠需要憲兵。」
「所以你們現在得靠自己了。我很抱歉。」
我說:「那是假警報。」
我說:「只是路過而已。」
「你那邊有進展嗎?查出誰的名字了嗎?」
「我們想也許你可以把鐵鍬的資料給我們,既然你已經找到你要的東西,也許不需要了。」
他的臉色變白,然後脹紅,那顏色就像崔佛諾夫的柯維特跑車。他怒視著我,好像他真的是個狠角色似的。
他說:「你的臭屁真是讓人難以置信」
「有多少不同款式?」
「好,那我換個方式說吧,我不像某人對自己那話兒的尺寸不滿意,非得從別的地方得到滿足。」
「沒有。」
我說:「太棒了。」
「我知道你想問什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要找支全新的,就只有除夕夜被偷的那支。」
我說:「我要找一款被偷的起釘器,或者說鐵鍬,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稱呼那種東西。」
老人搖搖頭說:「不是。鈦金屬鐵鍬是有專門用途的,我供的其他貨物才是市場的主流。」
我說:「還沒找到嗎?」
我說:「地圖。」
逃學的那種感覺完全不見了。我們往東踏上回程,開始找九十五號州際公路。找到後我們往南朝博德堡行進,回去一定又要面對威拉的電話,面對想把我幹掉的三角洲特遣隊員。就在要穿越北卡的州界前,我們又進入烏雲密布的地區,天色變暗後桑瑪把車頭燈打開。我們經過在另一邊路肩上的州警局,經過克拉瑪的手提箱被發現的地方,一哩後又經過休息區,接著與東西向高速公路支線交會,開下克拉瑪去過的汽車旅館旁的交流道。下交流道又過了三十哩後,我們才抵達博德堡的大門。崗哨的憲兵記下我們是在一九三〇回到基地,我要他們給我一份大門進出紀錄的影本,時段是從元旦當天六點,一直到一月四日的晚上八點為止。我要他們立刻把這八十六小時內的紀錄影本拿到辦公室給我。
「我的意思是,門口的紀錄裡會寫著你在十點半離營,威拉一定會查的。」
我說:「隨便問問,我心裡一直想著海灘。」
我說:「有消息我會告訴你。」
我說:「我自己就是這種人。」
我說:「只是些圖釘而已。」
我說:「這裡,現在。」
「其他店裡也有這種情形嗎?」
「除了剛剛說的這款跟鈦金屬材質的鐵鍬,我只跟一個叫做佛提斯的匹茲堡老牌子進貨。他們幫我開了兩款模具,一款十八吋長,一款三呎長,兩款都是四分之三吋粗。而且都是高碳鉻做的二次鍛造鋼鐵,爪子部分做了表面強化處理,烤漆的品質也很高。」
我們各自回到寢室,我的寢室位於單身軍官專用營舍,它很像汽車旅館。有條街是用某個得過榮譽勳章的傢伙命名的,從那條街上分岔的一個人行道往下走,就可以到我房間。每走二十碼就有一盞街燈,燈下有個衛兵。最靠近我房門的那具燈是熄滅的,因為有人用石頭把它砸爛了,人行道上還有玻璃渣。有三個人站在黑影裡,我經過第一個人:那是留落腮鬍那位皮膚黝黑的三角洲特遣隊士官,他對著我用食指尖敲敲錶面,提醒我時限快到了。第二個傢伙也做了同樣的動作,第三個傢伙只對我微笑。我走進室內把門關上,沒聽到他們走開。這一夜我失眠了。
他說:「我會從歐洲進口一點鈦金屬做的鐵鍬,很貴,但很堅固。更重要的是,很輕,是專門為警方與消防隊設計的。或是可以拿來進行最怕東西腐蝕的水底工作,任何人如果需要小巧、耐用以及容易攜帶的工具也很適合。」
她睜開眼睛,「我們必須回去,再看看出入大門的紀錄,它最快會經過大門的時間是元旦的凌晨六點,因為博德堡距離綠谷鎮有四小時車程。他最晚必須在一月四日晚上八點經過大門,如此一來,這中間就有八十六小時的空窗期。我們必須查一查誰在這時段裡進入大門,因為我們知道鐵鍬在這時段裡進了大門,而我們知道鐵鍬是不會自己走路的。」
他不發一語。
「他為什麼會來當憲兵的頭?」
他說:「那是什麼?」
我看看周遭後跟他說:「因為你要確保商品的品質。」
他也頓了一會兒才說:「你要我說的,難道我不該說嗎?」
她說:「維吉尼亞州的克拉克警探。」
她說:「那太可惜了,這樣你就不知道我穿什麼了。」
「我沒有逮捕他,只是問了他一些問題。」
「怎麼這樣問?」
他把綠谷鎮的圖釘拔掉,「我叫你不要管克拉瑪夫人的案子。」
他做了個表情,好像覺得很有趣,但沒m.hetubook.com.com到興奮的程度。那感覺就像我碰到一個鑑識專家,但我問的卻是關於指紋的問題,而不是DNA。從這點看來,鐵鍬是一種在很久以前就不再繼續發展的工具。
「說真的,你會去哪裡?」
他又點點頭說:「世界上獨一無二。」
克拉克說:「當然。」他往前靠,打開一個抽屜,打開後讓它像展示櫃似的開著,然後移動自己的椅子,以免擋到我。我身子前傾往下看,結果那把彎彎黑黑的東西跟我昨天早上看到的一模一樣。形狀、輪廓、顏色、大小、上面的拔釘爪都一樣,材質也都是八角形的鋼鐵。還有色澤,全都非常準確,它跟我之前留在博德堡太平間那把是完全相同的款式。
他瞪著我。
他說:「抱歉,或許是我自己沒說清楚,這款鐵鍬是他們為我特製的,設計人是我,規格也是我自己訂的,那是訂製的款式。」
「妳可以寄照片給我。」
「所以一個只會計算燃料消耗量的傢伙,在上任第一週就可以吃掉兩個軍人死掉的案子?而且他壓根不想調查。」
我說:「你找到了自己的市場定位。」
「我們還有事要做。」
「他把能用的招式都用在我身上。」
我說:「我們去綠谷鎮找克拉克警探吧。我們可以看看他手上有關鐵鍬的資料。他為我們起了頭,也許我們可以自己結束。反正案情沒有進展,開個四小時車搞不好可以弄到一些資料。」
我坐在桌邊,撥電話到華府找我哥,但他沒接電話。我想打電話給媽,但我怕自己不知道要說些什麼。不管我跟她聊些什麼,她也知道我打電話過去其實是想問:妳還活著嗎?她清楚得很。
「那你投訴我啊,威拉。可以跟你的長官說我傷了你的感情。你可以看看有沒有人相信你。他們會覺得你連這種小事都搞不定,你的紀錄裡也會留下這一筆。一旦被貼上這標籤,你甭想當上一星少將了。」
我說:「威拉這傢伙基本上是個什麼貨色?」
桑瑪問我:「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威拉是個屁,我還沒離開他就先走人了。」
「所以說,佛提斯牌出品、長三十六吋、四分之三吋粗的鐵鍬,市面上很罕見囉?」
我說:「你管不動部下,看你試著解決這個問題,實在很有趣。也許我們可以到體育館用男子漢的方法來解決問題。想試試看嗎?」
他說:「嗯。」
我看看四周,對他說:「我說了什麼嗎?你沒有證人。」
「你還好嗎?」
她又看了我一下,然後轉身面對地圖。我用擴音器把電話的聲音放出來,把話筒擺在桌上,線上傳來喀的一聲,接著就聽到桑切斯的聲音出現。
「明天洞勾洞洞準時在傳真機旁等著,我會用白紙黑字對你下令。」
又過三十分鐘後,桑瑪回來了,我叫她接下來整夜都好好休息,明早在軍官俱樂部會合。我跟她約九點整,就是威拉的命令傳進來的同一時刻。我猜我們可以慢慢享受一頓很悠閒的早餐,吃很多蛋跟培根,到十點十五分再慢慢散步回去。
「我是說在這地區,跟你賣同款佛提斯牌鐵鍬的店。」
「第一點,克拉瑪夫人與卡邦是被同一把兇器殺害。第二點,如果我們要查出兩個案子間的關聯,一定會忙瘋。」
她說:「是個見風轉舵的官僚。」
我說:「好。」
「會有人發現的。」
「召認什麼?」
她說:「三角洲那些傢伙騷動不安,他們知道你逮捕了那個保加利亞人。」
他說:「完全正確。在價格方面我沒辦法跟大型連鎖店競爭,所以我必須提供最棒的商品與服務。」
「那你賣的是什麼貨?」
「所以我打電話來告訴你,我不能繼續查下去了,既然已經找到我們要的東西,就不能繼續幫你了。我沒辦法申報加班費。」
我不發一語。
他陷入沉默,過了一會才說:「你該考慮一下想不想繼續升遷。如果我還在,你覺得自己可以當上中校嗎?」
「所以我從一個貨源拿了一款十二吋長,半吋粗的鐵鍬,儘管這個款式只經過一次鍛造。但就堅硬度而言,這種款式已經讓我很滿意。因為這道槓桿只有十二吋長,一般人的力氣沒辦法把它弄斷。」
「嗯,事實上我必須有所妥協才做了最後決定。我比較喜歡的那家廠商做的產品至少要十八吋長,但我要的東西只需要十二吋。」
「但被偷的不是那款鐵鍬。」
他說:「你怎麼會有安全的電話傳真線路?」
「我們不能待在這裡,所以不能辦卡邦的案子。」
他說:「就像手套一樣跟手吻合。」他又起身走進副隊長辦公室,拿起桌上的模型,一手一個走回自己的辦公桌,把東西擺桌上。那兩個模型跟我們的很像,也是公模、母模各一個。不過克拉瑪夫人的頭部體積比卡邦小很多,因此鐵鍬打在上面留下的傷痕也比較小,長度感覺起來稍短一 點。但鐵鍬一打下去,兩人傷得一樣嚴重,傷口也一樣深。克拉克拿起模型,用指尖滑過上面代表傷口的溝槽。
「他是個危險人物。」
我頓了一會兒才說:「你有提到我找到嫌犯了嗎?」
「誰是嫌犯?」
「真是這樣?」
他說:「這是一個小店,我要小心挑選進貨。這個因素就某些方面來講是負擔,但也同時讓我很愉快,因為我的選擇很自由。定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做,所以在鐵鍬材質方面我顯然應該挑選高碳鉻鋼鐵。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種鋼鐵應該是經過兩次鍛造還是一次鍛造呢?因為我做生意很老實,所以偏好比較堅固的二次鍛造鋼鐵。而且為了實用,爪子的部分要做薄一點,而且為了安全起見,表面必須做硬化處理。在某些情況下,這種東西可以用來救命。想像一下,在屋頂高樑上工作的人如果遇到爪子斷掉,他有可能會跌下來。」
她說:「沒辦法,一定會查出一堆名字。」
這種用來整人的命令非常經典,它會讓人有做不完的事。過去在部隊的整人把戲包括叫人把煤炭漆成白的,或者用湯匙把沙袋裝滿,m.hetubook.com.com還有用牙刷刷地板。威拉的這種命令可說比較現代化一點,像這種不用腦袋的工作,可能要花兩週時間才做得完。我露出微笑。
他說:「威拉來過又走了,不可思議的傢伙。」
電話還在響。
我的表情看起來一定是一片茫然。
我說:「在真實世界裡,辦案就是這麼一回事。」
在我們進門同時,門上有個機械鈴同時響了起來,窗戶裡那種整齊又有組織的風格也延續到店裡。裡面的展示架、壁架與箱子都擺得整整齊齊,地板上鋪的是寬厚的木板,店裡隱隱散發著機油味。店裡沒半個顧客,非常安靜,櫃檯後面站著一個可能有六、七十歲的傢伙,因為門鈴響了,他正看著我們。他的身高只算中等,身材瘦削,有點駝背。他戴著圓框眼鏡,身穿灰色羊毛衫。這樣的外表讓他看起來很聰明,但同時也顯得他的本事只能賣出螺絲起子那樣的小東西。他的外表告訴我,賣東西不是他的第一專長,他應該去大學裡開設有關工具的課程,講授它們的設計、歷史與發展。他問我:「要找什麼嗎?」
當我們往北開時,天氣愈來愈好,我們從一個被低矮烏雲籠罩的區域穿出,開進暖暖冬陽中。因為這是部軍車,所以車內未裝收音機,民間車輛本來裝有調頻、調幅收音機與卡式錄音機的面板部位,在這輛車裡卻是空盪一片。所以我們偶爾會聊聊,其他時候在沉默中前進。自由給我一種奇怪的感覺,我這輩子每天的每一個時刻不管去哪裡,都聽命於陸軍。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個逃學的人,外面的世界跟軍中大不相同,它雜亂無章,沒有紀律可言,可是此刻我卻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我在座椅上躺下,看著這世界的混亂影像在我身邊不斷後退,看來好像投射在流動河面上的陽光,明亮而閃爍。
他說:「還好,你呢?」
他說:「明天就打吧。」
「覺得到八月你還在這裡嗎?」
桑瑪說:「海灘也太冷了。」
「她過得怎樣?」
我們開了十哩車程到史派瑞維爾去。我從克拉克的資料裡找到那家五金行的地址,它就列在第五行,因為跟綠谷鎮很接近。但它的電話號碼旁並沒有做記號,而是用鉛筆註記:沒人接電話。我猜五金行老闆正忙著找人來裝玻璃,還有聯絡保險公司理賠。我想克拉克的手下本來想最後再打一次電話,但還來不及打電話,就已經用國家犯罪資訊中心的資料庫確認了。
「你前妻。」
「第三點,兇手對於史派瑞維爾非常了解。在一個不熟識的城鎮裡,如果匆匆忙忙的,你有辦法在黑暗中找到那家五金行嗎?」
我搖頭說:「還有別的事嗎?」
「第三點呢?」
我說:「我們需要一些背景知識才能了解鐵鍬的市場。」
「早跟你說過了。」
「總之我們只是路過而已。」
我留在人行道上,五分鐘後她開了之前我們用過的那輛綠色雪佛蘭回來。她停車時把輪胎緊靠著人行道的街邊石,我還沒移動她就把車窗搖下。
「他下了什麼命令?」
「資料?」
「你確定嗎?」
「其他有哪些呢?」
「這要感謝上帝。」
我說:「那不是我們的案子。連桑切斯都不能介入,我們就更別說了。」
「有帶武器嗎?」
我往基地外的西南邊看,看到遙遠的地平線上有枯樹冷冷地矗立著。再近一點,一棵高高的松樹正在冬眠,毫無生氣可言。我想它就長在我們發現卡邦的地點附近。
他說:「從傑克森堡到這裡一路都很順,路況不錯。」
桑瑪把眼睛閉上。
「那你在哪裡?」
我說:「如果妳說是他們把手提箱丟出車外,前提是,他們的車必須是往北開。他們沒有朝南開往哥倫比亞。」
我在椅子上動了一下,對她說:「我哥的猜測是,上面在模仿民間企業的做法。他們覺得搞不清楚狀況反而是好的,因為跟現狀沒有牽扯。」
「桑切斯說你發現了嫌犯。」
「你必須在午夜前打電話給威拉上校,否則他要呈報你不假離營。他說他說到做到。」
他說:「這是怎麼回事?」
他說:「我也叫你別去惹他們。」
「千真萬確。」
她說:「這樣好嗎?」
他把那團縐紙丟在地板上,說:「你要我去三角洲特遣隊一趟嗎?」
我把崔佛諾夫的史戴爾手槍還給他,讓他在三角洲特遣隊的大門口下車。他可能會把槍還回去,然後走回房間,又開始從剛才看到的那一頁繼續往下看書。我們繼續往下開,把悍馬車還回汽車調度場,然後走回辦公室。桑瑪直接走到那一頁還貼在牆上地圖旁邊的大門進出紀錄。
我們透過擋風玻璃往前看,巷口很勉強才有視線可言,但接下來我們看到了它,要走出巷子要有足夠的光線。
「真無趣。」
他說:「有進展了,史派瑞維爾那支鐵鍬一定是兇器。我們從那家五金行拿了一支樣本來測試,結果法醫說結果是相符的。」
「我不知道。」
「這些傢伙不需要帶武器。你該把他們關在營區裡,你可以做到這點,因為你是代理憲兵指揮官。」
她面帶微笑繼續開車,從通往綠谷鎮的交流道下去,那速度已經超過速限太多了。
他的臉上露出片刻微笑,說:「你們是陸軍的。政府頒布了戒嚴令嗎?」
他說:「祝你們好運。」
她說:「每天幫她祈禱?」
她說:「瓦索與庫莫,那天只剩他們曾經離開基地。」
我說:「而且,被偷的是三呎長那款。」
我又點點頭。突然間我倒希望天氣不要那麼冷——我很樂意看看桑瑪在海灘上穿比基尼泳衣的模樣,我喜歡布料比較少的。
「你要我扭斷你的脖子嗎?」
他掛斷電話後我坐了一分鐘,然後把話筒托架動一動,把線路整理一下,然後要我的中士幫我打電話給桑切斯。我把話筒夾在耳朵與肩膀間,等待著,桑瑪直視著我。
「你喜歡肌肉車嗎?」
那位老人說:「那是為了壁骨與托樑設計的。如果用得到鐵鍬的那個地方只有十六吋長,十八吋的鐵鍬就派和*圖*書不上用場了吧?」
我說:「幹得好。」
「你們是憲兵囉?」
他說:「我打了電話給媽,她還在強撐著。」
「他如果調查,就變成老掉牙的思維方式了。陸軍需要改變,我們要看的是遠景。」
「資料可能很多,我們不想給你帶來麻煩。」
他說:「該你打給她了。」
我說:「你沒看見我,所以也沒有把命令交到我手上喔 」
我說:「不會。」
我說:「克拉克警探把你借給他的樣品給我們看了。」
我不發一語。
「你把各種五金行都列了出來,我想我們如果從你沒完成的部分繼續往下調查,應該可以省點時間。」
他氣壞了,把頭轉開,我起身把辦公室門關起來。走回桌子後我又坐下,與他面對面。
所以我要桑瑪離開,自己等著威拉。她跟我爭,但最後也同意我們倆總得有個人不被人盯著,這案子才能繼續辦下去。所以她去吃晚餐,我的中士去幫我買個用烤牛肉、瑞士起司與一點美乃滋、芥末做的白麵包三明治。牛肉半熟,三明治很好吃。然後她也幫我倒了咖啡,第二杯喝到一半,威拉就來了。
「啊?」
我拉著話筒的電話線沿著桌子走,然後又坐下。
但這家店卻是深夜裡小偷下手的完美地點。它又安靜又偏僻,大街上的行人都看不到它,二樓也沒人住。五金行的正面是展示櫥窗與入口,分別位於左右,兩者之間只隔了一個門框。窗戶的玻璃上有個月亮形的破洞,暫時用一塊夾板擋住,夾板被切割成跟破洞大小相當。我猜那塊破洞是被一只鞋砸破的,位置靠近門邊,我猜一個高個兒可以把左臂穿進洞裡,輕易用手把門閂打開。但是他必須先把整隻手伸進去,慢慢地、刻意地彎曲手肘,才不會把衣服割破。我想像著他的臉頰要貼在冰冷的玻璃上,他必須在黑暗中氣喘吁吁,慢慢摸索。
「到目前為止,只能說流年不利。」
他直接開門進來,也沒關門。我沒起身,也沒敬禮,甚至連咖啡杯都沒放下。他不敢對我發作,這點我也料到了。因為他知道我有個嫌犯,可以把布魯貝克這案子從哥倫比亞市警方手上拿回來,還可以避免一個菁英部隊的上校跟暗巷裡的藥頭扯上關係,所以他不得不讓我三分。所以他準備好發動客氣與友善的攻勢,也可能是他正想辦法跟下屬建立交情。他坐下後又開始扯褲管,臉上擺出一副「這是男人間的對話」的表情,好像我們剛才一起幹了什麼大事。
「你當過兵的地方裡,哪裡最棒?」
他走回桌邊,打算拿張傳真給我看,電話還是不停響著。但我沒把傳真拿過來,只從下士身後看著那張傳真,上面有兩段文字,段落的距離很近。威拉要我去檢查軍需官接受進貨時所做的庫存紀錄以及出貨時的紀錄,根據這兩項資料,我必須打份報告給他,向他說明這個基地的倉庫裡應該有哪些軍需存貨,然後我要用實際的清查來證實自己所做的估計無誤。如果有短少,我必須列出一張清單,並說明我打算怎麼追回那些東西。我必須立即且準時完成這項任務,當我收到命令時,要馬上向他確認。
我們把車停在右邊停車場,兩輛白色巡邏警車中間,我們走到外面的明亮陽光中,到了前門後指著左邊要我們前往側邊的建築。我們經過一片凌亂的走廊,最後到了一個籃球場大小的房間,那裡可說就是克拉克警探的地盤。一排四張訪客椅被一道木造圍欄圍住,大門旁邊還有個接待櫃檯,走過大門後,遠遠的一個角落有間副隊長辦公室,除此之外基本上只擺了六張兩兩相對的辦公桌,桌上只有電話與紙張。牆邊擺了幾個檔案櫃,髒髒的窗前大部分都有歪斜的百葉窗,很多都已破損。
我走到裡面的辦公桌,拿起電話,桑瑪則是走到地圖邊,依序用她的手指碰觸華府與史派瑞維爾,然後是史派瑞維爾與綠谷鎮,綠谷鎮與博德堡。我則是打電話給喬伊,電話才響第二聲他就接了起來。
他看我的神情好像以為我是個千里眼。
我微笑了一下。不管誰問這問題,我的答案都一樣。我也這樣跟她說。
他點點頭:「這種獨自經營的小店才有的特權。」
「喬伊,她是說自己不久人世,但我們沒必要每天幫她祈禱。」
我說:「混球。」
「他們似乎不能接受這種說法,很多人來找過你。」
「被威拉撕下來,我又把它貼好。」
「但你刀槍不入。」
我帶著桑瑪走出門,回到人行道上,我們已聽不見電話鈴響。
他說:「沒有。而且他們也沒派人手去找,真是不可思議。所以我還是纏著他們。」
「我們還有事要做。」
我說:「我們休息一天吧,找個地方走走。」
我說:「我真的不想升中校。不過,我想你也不會在這裡待太久。」
我問她:「妳穿比基尼還是一件式泳裝?」
他說:「我一直纏著哥倫比亞市警局,要他們把布魯貝克的車找到。」
嚴格來講,陸軍有二十六個官階。菜鳥一進來掛的階級是E1級大兵,一年後如果他沒做任何傻事,會自然被晉升到E2級,再一年後則升為E3初級。如果表現再好一點,可能會升得更快。這條升級之路可以一路延續到五星上將的官階——不過就我所知,好像只有喬治.華盛頓與杜懷特.大衛.艾森豪兩人升到最高一級。拿我當例子,如果我們把E9這個等級分為最小的士官長,還有它上面兩級的一等士官長與特等士官長,然後再把准尉的四個級數都算進來,等於要升十八級才能做到少校,未來我還有七個階級可以讓我繼續往上爬。所以像我這種少校,可以說是夾在中間,常要想辦法對抗上面的命令,但也常遇到下面的人抗命。所以說,在這分為二十六個階級的百萬大軍中,抗命可說是一門繪畫藝術,一個上級與部屬私下會面的場合,可說是一塊表現抗命藝術的畫布。
「我有可能不在。」
「差異很大,我們要找的是大支的。」
所以我離開椅子,把地圖撿起來後又攤開,黏和_圖_書回牆上。我把七個圖釘都撿起,插回原位,然後把名單貼在地圖旁。但我又把名單拿了下來——它根本沒用。於是我把它揉成一團,丟進垃圾桶,只留下地圖。我的中士又拿咖啡進來給我,我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她小孩的父親是誰?他也會家暴嗎?如果是這樣,他大概已經被埋在某個沼地裡了,或者被分屍然後埋在幾個不同的沼地裡。我的電話在此刻響起,她幫我接了,然後把話筒拿給我。
「可是威拉不是盯著你嗎?」
我說:「想找人幫個忙。」
「唉!那是條死胡同。一開始看起來很有可能是他,結果不是。」
克拉克說: 「你們得小心點。有些地方稱那種工具為鐵鍬,有些地方叫起釘器。你必須確認他講的是什麼。」
「我是你的長官。」
他在椅子上又開始像蟲一樣蠕動,身體朝兩邊動來動去,看著四周。最後他把目光擺在桑瑪的地圖上。
他又說了一次:「嗯,鐵鍬的資料。」他把椅子轉過去,起身後走向一個檔案櫃,回來後拿了一個大約半吋厚的綠色檔案夾。他把檔案丟在桌上,發出不小的聲響。
他說:「我懂了。」
桑瑪說:「是。」她把我們的名字與官階告訴他,他也告訴我們他的姓名,從他的姓氏出現在外面招牌上這點看來,他應該是老闆。
我不發一語,她則面帶微笑。
「他正在去你那邊的路上,兩小時前就出發了。那他一定很失望。」
「聽起來很虛弱。」
我搖頭說:「我不打算為了威拉那種混球躲起來。如果他追問我,我會說我需要跨州追查那個亂丟口香糖包裝紙的傢伙。或者跨國,我們可以去一趟大溪地。」
「美東地區的地圖。」
我說:「好。那我們是來找那款被偷的鐵鍬。」
他說:「非常猛烈的一擊。你們要找的人是個右撇子,非常強壯的高個兒。你們在找這樣的人嗎?」
「要去哥倫比亞市一趟嗎?」
「布魯貝克的案子不是我辦的。」
他說:「好幾十種。有六家製造商是我會考慮跟他們做生意的,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家。」
他說:「別接你的電話,是威拉上校打的,他要立刻確認你接到了命令,他氣瘋了。」
我說:「我想是這樣。」
「什麼地圖?」
我瞪著他說:「只有你這家店裡有?」
她說:「傑克森堡的桑切斯留了個一〇一三的訊息代碼給你,還有你哥又打電話來了。」
「會掉漆嗎?」
史派瑞維爾不大,所以找地址時我們只稍微繞了一下。我們在一個狹長的區域找到幾家店,繞了三次後就在一個綠色招牌上找到要去的街道。它帶我們走向一條基本上是死胡同的狹窄巷道,經過那巷道時發現兩邊都是護牆板,接著巷道開始變寬,出現一塊小空地,五金行就在遠方與我們面對面。它像個只有一層的小穀倉,為了讓它看起來較具都市風味,在粉刷上特別下了點工夫。它是個百分之百的家庭式商店,老舊的招牌上漆了老闆的姓氏,完全看不出它是大公司的經銷商。它只是家美式的小公司,位置偏僻,在有時繁榮有時蕭條的景氣中,代代相傳地經營下去。
我又說一次:「還有別的事嗎?」
「什麼忙?」
「然後呢?」
「你上次賣出去是什麼時候?」
我說:「當然。在外面辦公室,你出去時就會經過。你怎麼啦?又蠢又瞎嗎?」
他又點點頭,「品質不好的產品都是中國製造。用生鐵、熟鐵大量製造,或者用熔鐵爐鍛造出來的鋼。那些我都沒興趣。」
我點點頭。卡邦、克拉瑪、布魯貝克。
「她在等著可以把石膏拿下來,她很不習慣。」
二十分鐘後我的電話響起,我發現真實世界更糟糕了:打電話的是我的中士,有個小男嬰那個,她要幫傑克森堡的桑切斯把電話接過來。
她說:「我們把焦點擺在兇器上,其他都先忘掉。想像一下,特製的鐵鍬,全世界獨一無二,它被帶出那條巷子,然後在元旦凌晨兩點又出現在綠谷鎮。然後它在四號那天晚上九點出現在博德堡。這是它的行進路徑,我們知道這條路的起點與終點,儘管我們不確定它在中途去了哪些地方,但它肯定要先經過一個地方,也就是博德堡的基地大門。我們不知道時間,但的確有過那麼一回事。」
「但不見得需要你這種蠢蛋一樣的混球。」
「圖釘代表什麼意義?」
我說:「開個玩笑。他只是個無名小卒,這條路是死胡同。」
我點點頭。我就知道這是他的下一步——對我提出「不假離營」的指控不會影響他身為總指揮官的評價,不會讓他看起來好像沒辦法搞定我。對於一個擅自外出的人進行「不假離營」的指控,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為了進行比較,我們跟克拉克警探一樣跟他借了支樣品。鐵鍬上面沾有機油,握把中間纏著衛生紙。我們把它當獎品一樣擺在雪佛蘭的後座,然後在五金行以北一百碼,一家提供免下車服務的餐廳買了漢堡,在車上用餐。
他說:「我該從哪裡開始?」
我說:「也許是,也許不是。過一陣子就知道了。」
我們把車停在五金行正前方,下車後花了一分鐘看窗戶。裡面有很多展示商品——不過這裡的擺設可不像紐約第五大道薩克斯百貨公司的聖誕節櫥窗,因為這裡的擺設跟藝術毫無關係,不用設計也不必用來刺|激消費,只需要把商品整齊擺在手工釘的架子上,每件都標上價錢。那面窗戶只是用來向客戶傳達一個訊息:我們有這些貨,如果你想買,就進來帶一件回家吧。但是這些東西的品質看來都很棒,有些東西我不知道它們是做什麼用的,因為我對工具不太了解,而且除了刀子之外,我不算真的用過什麼工具。但我很清楚的是,這家店挑選進貨時很嚴格。
「我可以看一下嗎?還是放在你們的證物室裡?」
代表武器形狀的公模做得也比我們那個小,除此之外,兩者看來很像。也同樣是塊石膏,上面布滿小洞,但表面基本上是平滑的,而且看得出這兇器很驚人。
他做了個表情,好hetubook.com•com像有點失望。「那種東西,我一年賣一支,如果運氣好,可以賣個兩支。因為這東西很貴,而且很遺憾的,大家對東西的鑑賞力已大不如前,識貨的人少之又少。」
我說:「沒錯。」
「有人說全陸軍一半的上校都跟她有一腿,她總是這樣,好像是她的嗜好。所以我猜應該包括布魯貝克。我想機率應該是一半一半。」
他又坐下,我對桑瑪點點頭,她把東西拿起來打開。裡面夾滿紙張,她一頁頁翻閱,做了個表情,然後拿給我。那是一份很長很長的清單,裡面包括了從紐澤西到北卡各州的店名,還有地址與電話。前面九十筆資料都打上記號,還有大概四百筆沒做上記號。
她說:「你可以藏在後車廂裡,出了基地大門再出來。」
我說:「嗯。」
我的辦公室很安靜,完全不像早上那樣混亂。有個小男嬰的那位中士又回來值晚班了。她看起來很累,我知道她睡很少,因為整晚工作後還要整天陪小孩玩,這樣的生活真苦。她在煮咖啡,我猜她跟我一樣喜歡咖啡,也許她比我更需要它。
我不發一語。
「寄到哪?」
我上車坐在她身邊,把座椅拉到最後面,又開始幻想她穿比基尼的畫面。她把腳從煞車踏板上移開,加速開往大門。一個憲兵拿出一塊寫字板,他把我們的車牌記下,我們向他出示證件,讓他把名字寫下。他望向車內,看看後座是空的,然後對著站在大門崗哨的夥伴點點頭,柵欄在我們面前緩緩升起。所謂的「柵攔」其實是根夾雜著紅白條紋的桿子,一端裝有平衡錘,桑瑪等到桿子整個升起,與地面垂直,她才讓車子全力衝刺,這輛由公家供應燃料的雪佛蘭從車尾排出藍色煙霧。
我說:「我可以看看那把鐵鍬嗎?」
「我們可以在外面吃中飯,也許還有晚飯。我們可以來個不假離營。」
我說:「有留話嗎?」
他繼續把其他圖釘都拔掉,全部丟在地板上。然後他看到進出大門的紀錄,一 路往下瀏覽,直到他看到瓦索與與庫莫的名字。
我說:「我會打,過幾天就打。」
我說:「我們只有這件事可做了。」
他重複一次我的問題:「其他店裡?」
「跟他說有人在基地指揮官的辦公室外丟了張口香糖包裝紙,跟他說我不許有人這樣毀損陸軍財產。跟他說我整晚都在追查這件事。」
我說:「沒概念,距離八月還有八個月。」
我說:「我想也是這樣。所以你的條件是:正確的鋼材、經過兩次鍛造、爪子部分要堅硬。你挑的是哪幾款?」
我說:「說說看我們查出哪三個新的事實。」
他說:「你們可以要我傳真過去就好。」
他說:「牆上被你釘出一個一個洞,我不容許有人破壞陸軍財產,這真是太不專業了。來你這房間的訪客會怎麼想?」
到了早上他們已經不見了,我順利抵達軍官俱樂部。用餐室在九點鐘可說幾乎是空的,這點是好處。但缺點是剩下的食物都已經在自助餐櫃檯上加熱了一陣子,但整體而言我還是挺喜歡在人少時吃飯,因為我不是饕客。我跟桑瑪挑中用餐室正中央的一張小桌,一人坐一邊,我們差不多把所有剩下的東西都弄上桌。桑瑪吃了大概一磅的玉米粥還有兩磅小麵包,她的身材雖嬌小,食量卻很可觀。我們慢慢喝咖啡,到了十點二十分才回我的辦公室。裡面正忙成一團,每支電話都在響,那位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下士看起來慌慌張張。
他又怒視我最後一次,接著走到外面後把門用力甩上,連牆壁也被他撼動,地上的地圖與名單被推進來的氣流吹動,往上飄了一吋。
他把那張清單從牆上撕下,牆上一部分的漆也跟著膠帶一起剝離,然後他把地圖也撕下來,掉了更多的漆。牆上留下了圖釘插過的一個一個洞,這些洞看起來就像一幅地圖,或者星座圖。
我說:「不,我喜歡搭公車。」
「有大小的差異嗎?」
「大約九個月前。」
克拉克說:「那不是證物。它不是真正的兇器,只是從史派瑞維爾那家五金行借來的同款鐵鍬,不能帶上法庭的。」
克拉克講完電話後,掛上話筒,在一本黃色便條紙上做了筆記。接著呼了口氣,把椅子往後推,這樣才能同時看到我們倆。他沒說什麼,他知道我們不是來做禮貌性拜訪,但同時也不想直接開口問我們有沒有名字可以告訴他。因為如果我們沒辦法告訴他名字,不就顯得他很蠢嗎?
我說:「他們會覺得這面牆上本來有張地圖。是你把它撕下,搞得亂七八糟的。」
綠谷鎮警局在小鎮北邊,那棟樓房的規模比我想像中要大,主要是因為綠谷鎮也比我想像中大。它包括我們之前已經看過的那個美輪美奐的市中心,繼續往北延伸,還有個主要由商店集散區與民生工業區構成的郊區,整個小鎮的範圍幾乎一路延伸到史派瑞維爾。綠谷鎮警局看來可以容納得下二、三十個警員,它的建造方式跟大部分地價便宜的地方一樣,建築物又長又低,涵蓋區域很大,中間的主建築只有一層樓,側邊還有附屬的兩棟建築。側邊樓房與主建築呈直角,所以整個警局是U字型。警局是正面水泥牆面,刻意蓋得像石牆,警局前面有片已經枯黃的草坪,兩邊都有停車場。草坪正中央立了根旗杆,因為沒風,那面經過日曬雨淋而老舊的國旗只是懶洋洋地掛在旗杆上。整個地方看起來有點華麗,也因為陽光而顯得有點慘白。
我說:「當然,這我們早就知道了。」
桑瑪說:「是軍中的案子。」
卡邦。
我露出微笑,心想:兄弟,你就忘了什麼名字吧。你拿什麼跟我交換呢?就算我有名字也不會給你。
「八月就不冷了。」
我站著不動,看看四周,發現那天天氣很冷,天空和營區樓房一樣都是灰色的。
他說:「我剛買了一輛很炫的龐帝克GTO跑車,我在引擎上加裝了又粗又亮的引擎喉管,跑得有夠快。」
他說:「向我報告布魯貝克一案的進度。」
我說:「可能是李文沃斯堡吧,最高戒護的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