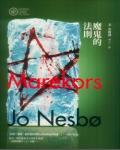第三部
18 五角星
奧莉和依娜一同開懷大笑。奧莉之所以大笑,大部分是因為鬆了口氣。
奧莉仍在撫摸被單。粗糙的羊毛摸起來觸感很好。
尼可萊呵呵大笑,笑聲在四壁裡迴盪。
她走到搖椅旁。
「他說要等到我們訂婚才能打開。」
尼可萊從男子臉上的表情看出他並不明白。
「很像?據我所知,根本就是五角星。」
「對。」依娜輕輕嘆了口氣。
「怎麼回事?」她咕噥說,視線在哈利和安德斯之間來回。
「『mer』是『死亡』的意思,」安德斯垂眼看著他那杯咖啡。「再說得更精確一點,『mer』是『謀殺』的意思。」
尼可萊花了幾秒鐘才明白男子說的是什麼。
「怎樣?」
「然後呢?」
男子問這句話的聲調冷靜而堅定,彷彿很習慣別人給他回答,尼可萊心想。
貝雅特搖了搖頭。「跟其他槍枝一樣,序號被銼掉了,銼痕跟我們沒收的大部分槍枝是一樣的。」
奧納嘆了口氣。
幾分鐘後,奧莉輕敲依娜的房門,驚訝地發現依娜並未回應,耳中卻聽見她房裡傳出輕柔的音樂聲。
哈利暗自竊笑。
尼可萊搖了搖頭。
「嗯,」莫勒說:「又是那個神祕的大型槍枝走私集團。POT密勤局的人很快就會查到他們對不對?」
「可以了解,」哈利說:「可是我把門鎖上了。」
「呃,因為你知道她睡得很沉。」
他走進存放命案現場鑰匙的辦公室,找到他要找的那把鑰匙,然後駕車前往蘇菲街,拿了他的手電筒,往伍立弗路走去。時間將近午夜。一樓鎖著,自助洗衣店已經打烊。墓碑店的展示窗裡一盞聚光燈打亮「長眠安息」這幾個字。
依娜臉上仍留著做夢般的神情。每次奧莉說起她這一生唯一的情人施瓦伯中將,依娜臉上都會出現這種神情。
無人回應。也許依娜睡著了。奧莉走進房內,往床鋪的方向看去。床上沒人。奇怪。她衰老的眼睛逐漸適應黑暗,然後她看見了依娜。依娜坐在窗邊的搖椅上,看起來像是睡著了,眼睛閉著,頭垂向一旁。奧莉仍辨別不出那低低吟唱的音樂是從哪裡傳出來的。
其他人紛紛移動椅子準備離開,但湯姆做個手勢,示意大家先別走。
「想像一下,施瓦伯中將就坐在妳現在坐的地方。」依娜突然說。
她們的互動已經變成有如固定儀式:晚上七點左右,奧莉會泡壺茶,拿個盤子放上餅乾,端著托盤去敲依娜的門。奧莉比較喜歡跟依娜在她的房間裡聊天。說來奇怪,奧莉覺得這個房間最有家的感覺。她們在陽光底下什麼都聊。依娜對二次大戰和弗勒公館發生過的事最感興趣,奧莉也一一告訴她,跟她說施瓦伯中將和蘭迪如何愛著彼此,他們夫婦倆會坐在客廳裡好幾個小時,談天說地,溫柔地撫摸彼此,撥開一縷頭髮,把頭靠在對方肩膀上。奧莉跟依娜說有時她會躲在廚房門後偷看他們。她描述的施瓦伯中將有著挺拔身形、濃密黑髮、高闊額頭,他的眼神可以在玩笑與正經、憤怒與大笑之間變換,他對生命中的大事十分有自信,對瑣碎小事卻如孩子般困惑。不過大多數時候奧莉看的是蘭迪的閃亮紅髮、細長白頸和晶亮雙眼。蘭迪的虹膜是淺藍色的,周圍是一圈深藍色。蘭迪的眼睛是奧莉見過最美麗的眼睛。
「我知道,」依娜說:「所以才很困難。他只是來這裡坐坐而已,我在他離開前對他說我需要時間想一想。他說他了解,畢竟我的年齡小他這麼多。」
「依娜?」
「有趣。」奧納說。
奧莉看著依娜好一會,然後搖了搖頭。
「我是警察,」男子說,像是回應尼可萊的思緒。「我們喜歡問問題。」
「異教徒的符號。人們通常會把它刻在床舖上方或門口,用來驅趕夢魘。」
「你不是這裡的人?」
「你有找到你想找的東西嗎?」
「跟鑽石無關,」哈利說:「而是跟五角星的形狀有關。我知道我在命案現場的某個地方見過這個形狀,可是我記不起來是哪個現場、哪個地方。這聽起來雖然很像胡說八道,可是我覺得很重要。」
「莉絲白是個已婚婦女,據我所知她很忠貞。」
「沒有,我只是在想你剛剛說星星倒過來不合宜是什麼意思。」
眾人沉默了幾秒鐘。哈利知道其他人跟他一樣正在想著同一件事:凶手到底對失蹤的莉絲白做了什麼?「我們在犯罪現場發現的手槍呢?」
「你聽,」他父親曾說:「他們的歌聲那麼美、那麼微小。」
哈利在床上坐下,用指尖觸摸樑上刻痕。這根褐色承重樑年代久遠,上面的刻痕卻十分清晰,一定是最近才刻上的。很明顯,刻痕一氣呵成,數條直線轉折交錯,畫成一個五角星。
「我有管理員的鑰匙,以防萬一。」
「我得承認我的印歐語很破。」
菲畢卡不好意思地瞥了哈利一眼。
「夢魘?」
「謝謝你的幫忙。」男子說,往門口走去。
「報紙上都有寫啊,她們的過去有目共睹。」
哈利的心臟恢復快速跳動,他四處摸索,想找回仍然開著的手電筒。手電筒掉落地面,輕輕發出砰的一聲,在地上滾動畫了一圈。手電筒的光線和那人的影子掠過牆面。
「怎麼了嗎?」
尼可萊在鋼琴椅上旋過身來。他是不是看錯了那個男子?對一個毒蟲或落魄者來說,男子的問題似乎有點尖銳。
哈利在床上躺下。床墊柔軟有彈性。他看著傾斜的天花板,腦子一邊思索。如果床邊樑柱上那個五角星刻痕真的是凶手留下的,它代表什麼意思?
「對,『魘』指的是惡夢。據說有個女魔鬼會趁人睡覺的時候,坐在人的胸部上,把人當馬騎,所以人才會做惡夢。異教徒認為她是精靈。這並不奇怪,因為魘『mare』這個字是從印歐語的『mer』演變來的。」
哈利聽見窸窣的腳步聲,轉過頭去。
安德斯解開腰帶,脫下睡袍,丟給菲畢卡。菲畢卡退了一步,但還是把睡袍接到手上。
「親愛的,我的老故事妳一定都聽得膩了,說說妳吧,妳那個紳士朋友是誰?」
「有趣之處在於這m.hetubook.com.com表示凶手並未性侵被害人,」奧納說:「這對連續殺人犯來說很不尋常。」
「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尼可萊高聲問道。房間裡嚴肅的傳聲效果使他的聲音聽起來比他原本的口氣來得不友善許多。
然後她就來了。她跨坐在他身上,把轡頭塞進他嘴裡,用力拉扯。他的頭給拉得亂轉。她俯身在他身上,把炙熱的氣息吹進他耳朵,宛如一頭噴火的惡龍。答錄機上的無言訊息,嘶嘶聲。她抽打他的脅腹、他的臀部,抽打的疼痛是甜蜜的。她說,遲早她會成為他唯一能愛的女人,他最好一開始就認清楚。
哈利開門走進卡蜜拉的住處。
「好像精神病。」奧納說,打了個哈欠。
「親愛的,這件睡袍是我買來送妳的,還放在行李箱裡,剛才我匆匆忙忙只找到這件衣服。給妳。」
「嗯,那現在魔鬼被消除了?」
奧莉往門上一推,門盪了開來。她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房裡空氣滯悶。窗戶緊閉,窗簾拉上,裡頭幾乎一片漆黑。
這時他面前的電話響起。
他過於疲倦,無法清楚思考。另外有個問題在他腦海裡翻攪。他為什麼沒有注意到五角星?他為什麼沒有把五角星跟鑽石聯想在一起?還是他有?也許因為他動作太快,也許因為他的潛意識把五角星跟別的東西聯想在一起,某樣他在其中一個命案現場看見的東西,可是他無法確切找出那是什麼。
「喔?」
「嗯。你對這些共同點有什麼結論?」
菲畢卡望向安德斯。
「換句話說,調查工作毫無進展。」莫勒說。
「這類型的凶手會表現得像是生死仲裁者,把自己的地位提升到跟上帝一樣。還有,《聖經》〈希伯來書〉第十三章第四節說,上帝將審判姦淫之人。」
莫勒在他的辦公室召開會議,除了奧納之外,還找了主導調查案的湯姆、哈利和貝雅特。
其他人一臉不解的看著哈利。
莫勒問說哪裡有趣?語氣有點沮喪。
「妳懷孕的時候,他太太有沒有發現孩子的父親是他?」
「你們曾一起出去過嗎?」
正當奧莉的茶壺——或說得更精確一點,施瓦伯家族的茶壺跌落地面時,奧納端起了杯子——或說得更精確一點,奧納端起了奧斯陸警局的杯子。
奧莉.希芬森打開通往陽台的落地玻璃門,陽台面對的是碧悠維卡區。她在椅子上坐下,看著紅色火車經過她家。這棟十分平凡的獨棟紅磚屋子建於一八九一年,而它的不凡之處在於它的位置。屋子名叫弗勒公館,以屋子的設計師命名,它獨自矗立在奧斯陸中央火車站旁邊的鐵軌旁,就位在鐵路系統的範圍內,附近鄰居是挪威鐵路公司的小屋和作業廠。弗勒公館是建造給火車站站長、站長的家人和傭僕居住的,牆壁造得特別厚,好讓站長和妻子不會每次有火車經過就從睡夢中被吵醒。此外,站長還要求建築工加強牆壁,這個建築工之所以得到這份工作,是因為他使用一種特殊灰泥,可以讓磚牆更為堅固。倘若火車出軌,撞上弗勒公館,站長希望承受衝擊力道的是列車長而不是他和他的家人。目前為止尚未有火車撞上站長這棟地點又孤單又怪異的優雅屋子,這棟屋子猶如矗立在黑色碎石荒地上的城堡,鐵軌在碎石荒地裡閃爍微光,在陽光下如同蛇一般蜿蜒而行。
「有什麼事?」
「我說笑的時候你們要不要至少擠出一點笑容?」奧納說:「哈利,這聽起來完全就是大腦的正常功能,沒什麼好害怕的。」
哈利到家時,答錄機有一則留言,是蘿凱留的。她問哈利明天可不可以去維格蘭雕塑公園的游泳池陪歐雷克,因為她下午三點到五點得去看牙醫。她說這是歐雷克要求的。
尼可萊回過身,看著鋼琴,集中注意力,輕輕壓下一個琴鍵,讓琴鍵碰觸琴弦,卻不發出聲音。他感覺得到琴鍵抵住琴弦的那種緊繃感,就在此時,他注意到沒聽見關門聲。他轉過頭,看見男子站在門前,手握門把,呆呆看著破窗裡的星星。
「他有地域性,」哈利說:「我們的心理學家也許可以解釋這一點。」
「這些命案現場有一個共同點。」貝雅特說。
尼可萊.洛普溫柔地按下琴鍵,鋼琴的琴音在空蕩的房間裡聽起來細緻飄渺。他彈的是柴可夫斯基降B小調第一號鋼琴協奏曲。許多鋼琴家認為這首協奏曲寫得又怪又不優雅,但從尼可萊的耳中聽來,這是天底下最優美的曲子。他只彈了他會背的幾個小節,心頭就浮現思鄉之情。每當他在老奧克教堂大廳禮堂裡這台未調音的鋼琴前坐下,這首協奏曲的音符總是會自然而然從手指底下流洩而出。
「被害人都是年輕女性,還有呢?」
晚上八點,房門打開。奧莉聽見有人穿上鞋子,步下樓梯,但她還聽見另一種聲音,一種拖著腳走路發出的刮擦聲,像是狗的腳爪發出的聲音。她走進廚房,煮熱水沖茶。
其他三人望向奧納。
「可是你不會?」
「你在幹嘛?」
「怎麼說?」貝雅特問。
「喔?」
「對。」尼可萊驚訝地說。他之所以驚訝是因為挪威人不太算得上是有文化的民族,更何況眼前這個T恤男子看起來如此落魄。
「不客氣。」
奧莉想問他有沒有養狗,但及時打住。她已經窺探得夠多了。她又摸了摸被單,然後站起身來。
但這可能只是奧莉一廂情願的想法。依娜有個紳士朋友。奧莉沒見過依娜這個男性友人,更別說認識了,但奧莉在自己臥房裡聽見依娜的男性友人踏上屋後樓梯的腳步聲;屋後樓梯可以通往依娜的臥房。奧莉不可能禁止男人造訪依娜的房間,不像她自己當女傭的那個時候,只是她也從未有過這個念頭。她只希望不會有人帶走依娜。依娜已經變成她的親密朋友,甚至像她女兒,她不曾有過的女兒。
「剛剛有個目擊者打電話來說,她在卡蜜拉遇害的那個星期五下午,在伍立弗路看見一個單車騎士從救主墓園附近的一間公寓出來。她會記得這件事是因為她看見這個單車騎士臉上戴著白色口罩,心裡覺得很奇怪。那個經過伍立
和-圖-書弗路去聖赫根區喝啤酒的快遞員臉上並沒有戴口罩。」「所以說,」莫勒說,雙手支著下巴。「你記得某件你不太記得的事,可是卻覺得很重要?」
莫勒嘆了口氣。「我知道,比數三比零,對手連球都沒讓我們摸到。沒有人有什麼聰明的想法嗎?」
「你穿的是什麼?」
「恐怕沒有,」湯姆說:「他們把其他解剖工作擺到一旁,優先處理我們的東西,但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發現。沒有精|液、沒有血跡、沒有毛髮,什麼都沒有。凶手留下的具體線索只有彈孔。」
哈利壓低手電筒照向地面,只見木質地板上有薄薄一層灰塵和許多小塵塊。卡蜜拉去世前顯然沒打掃家裡。不過,就在床腳上方,他找到了他來這裡尋找的東西:木屑。
莉絲白在桑納街。芭芭拉在卡爾柏納廣場。卡蜜拉在這間臥房隔壁的浴室。卡蜜拉幾乎全身赤|裸,肌膚濕潤。他碰觸過她的肌膚。熱水讓她感覺起來沒有死那麼久。他碰觸過她的肌膚。貝雅特在一旁觀看。他無法停止觸摸她。那感覺彷彿是用手指滑過溫暖柔順的橡膠。他的視線往上飄移,看見這裡只有他們兩人,沒有別人,這時他才感覺到蓮蓬頭噴出的熱水所產生的溫暖水氣。他的視線往下,看見她正看著他,眼中閃爍著奇異微光。他心頭一驚,把手抽回;她的眼神在關閉的電視螢幕上逐漸褪去。奇怪,他心想,伸手貼上她的臉頰。他等待著,蓮蓬頭噴出的熱水浸濕了他的衣服。微光又逐漸亮起。他把另一隻手放上她的腹部。她的眼神活了起來,他感覺得到她的身體在他的手指底下蠕動。他知道撫觸使她恢復生命力,少了撫觸,她會消失,死去。他把額頭抵在她的額頭上。熱水流進他的衣服,浸濕他的肌膚,彷彿在他們之間形成一層溫暖的隔膜。這時他發現她的眼睛不是藍色的,而是褐色的。她的嘴唇不再蒼白,變得紅潤而富有生命力。蘿凱。他的唇貼上她的唇。他發現她的唇冷冰冰的,立刻縮了回來。
「你在彈柴可夫斯基對不對?第一號協奏曲?」
「我說的不是茶。」
男子身穿粉紅色睡袍,除了那身衣服外,看不出才剛下床的跡象。他的頭髮分線梳理得一絲不苟。他是安德斯.倪格。
「這些鑽石有五個尖角,很像五角星。」
大家提起興趣,望著湯姆。
「小妮子觀察入微,」奧納插口說:「既然我們在討論移動模式,我想再補充一點。反社會型殺人犯通常很有自信,從這件案子來看也是如此。他們有個特點就是會密切留意調查工作的進行,而且會利用每個機會親自靠近調查工作。他們可能會把調查工作看做是他們和警方玩的一場遊戲,很多反社會型殺人犯都說他們看到警察苦惱的樣子覺得很好玩。」
有一晚,就在這種激烈爭吵過後,奧莉已上床就寢,施瓦伯中將敲了敲她的房門,走了進來。施瓦伯中將並未開燈,只是在床邊坐下,跟奧莉說他妻子一怒之下離家出走,跑去飯店過夜。奧莉一聞就知道施瓦伯中將喝了酒,但她還年輕,不知道該如何應付一個大她二十歲的男人。她尊敬、景仰這個男人,甚至有點愛上了他。他請她脫下睡衣,說想看看她裸體的樣子。
莫勒點了點頭,但臉上表情顯示他並沒有因為這句話而受到鼓舞。除了奧納之外,辦公室裡每個人都知道民眾一開始提供的線報最為重要,因為人們都遺忘得很快。
茶壺跌落地毯上,發出咚的一聲輕響。兩根茶匙、一個刻著德意志帝國老鷹徽章的銀糖罐、一個盤子、六塊瑪麗蘭牌餅乾接連跌落在地毯上。
「真是抱歉,」依娜說,吃下最後一片瑪麗蘭牌餅乾。「我沒聽見妳進來。」
哈利避開湯姆的目光。
一想到依娜現在就住在她剛搬來奧斯陸時住的那個房間,奧莉就有種奇怪的感覺,而且依娜的年齡比她剛來時不過大了幾歲而已。依娜半夜醒著躺在床上,心裡可能渴望遠離喧囂的城市生活,回到靜謐的特倫德拉格北方小鎮。
奧納搖了搖頭。「動機一向都是性,沒有例外。」
莫勒在辦公桌上重重拍了一掌。
與其說是孤單,不如說是沒有人需要她。她早上醒來之後,心裡知道就算她躺在床上一整天對其他人也沒有影響,一想到這裡她就十分傷心。
「原來如此,」莫勒說:「可是哈利,我還是不太知道你所說的邏輯是什麼。」
「聖奧麗加是俄國東正教的教堂,」尼可萊又說:「我是牧師兼行政長。你得去教堂辦公室,那裡說不定有人能幫你。」
「太好了。」他說,掛上電話。
「當你走進犯罪現場,你會非常專注,以致於你的大腦吸收到的周邊事物比你可以處理的多很多。這些事物會留在你的大腦裡,直到某些事情發生、某個新線索出現、一塊拼圖拼上另一塊拼圖,可是你已經忘了第一塊拼圖是從哪裡來的。不過你的直覺會告訴你這很重要。這樣解釋聽起來怎麼樣?」
「也就是說現在有一個人正坐在那裡享受這一切囉,」莫勒說,雙手一拍。「今天的會議就開到這邊。」
「該道歉的人是我,」奧莉說:「我就這樣闖了進來,沒看見妳頭上戴著……」
「是啊。」
「不知道。我最近看過這個符號,可是我記不太清楚是在哪裡看過,我也不確定這件事重不重要。是哪個魔鬼使用這個符號?」
「凶手闖進了女人覺得最安全的地方。他闖進她們的家、闖進光天化日下的街道、闖進辦公室的女廁。」
莫勒轉頭望向奧納,奧納正好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少來了,哈利。」
哈利揚起雙眉。
「人手不足的法醫學研究所那邊有消息嗎?」莫勒問:「他們有沒有發現什麼可以幫助我們辨識凶手的身分?」
奧莉又敲了敲門,依然無人回應。
「在妳讓他更進一步之前,妳必須確定他是適合妳的男人。」奧莉說。
「我是莫勒……請等一下。」
此話一問出口,奧莉就後悔了,依娜可能會覺得奧莉在監視她。
「有人放他的專輯給我聽。」
「我的意思是說,說不定凶手不必觸碰被害人也能滿足性和*圖*書慾。」
然後天花板的燈亮了起來。
他脫下衣服,裸著身體躺上床。昨晚他把被單上的被子拿開,只蓋著被單睡覺。他把被單踢來踢去,踢了一陣,逐漸入睡,他的腳卻跑到了外頭,他心頭一慌,在棉布撕裂聲中醒來。外頭的黑夜已染上一層灰色調。他把還留在床上的被子一端丟在地上,面朝牆壁躺了下來。
「那是在她結婚以後,可是她在結婚前是玩樂團的,常常在全國各地的舞廳裡表演。警監先生,你應該沒那麼天真吧?」
「他的年齡是不是比妳大?」奧莉繞了個彎,間接說明她並未逾越界限,偷看依娜那個紳士朋友長什麼樣子。「因為妳說他喜歡老音樂。」
「你有個好母親,她覺得她彈給你聽的曲子對你太難了。」
「調查工作才剛開始不久而已。」湯姆說。
奧莉微微而笑,摸摸依娜的臉頰,替她感到高興。
尼可萊聽見有人清喉嚨的聲音,轉過了身。
「惡夢十字?」
哈利點了點頭,抬起手腕看了看錶。
「他是個好男人。」
星期二
莫勒把電話遞給湯姆,湯姆接過湊到耳邊。
「是她自己說的。」
哈利聳了聳肩。
奧莉點了點頭。「聽起來他很認真。」
「真令人高興,」尼可萊說:「可是我恐怕沒辦法在這裡接受告解。大廳裡有一張表,上面有註明時間,你可以去我們在印可尼多街的禮拜堂。」
「就是研究魔鬼的學問,當人類認為邪惡是因為魔鬼的存在而產生,魔鬼學就誕生了。」
「他給我一樣東西。」依娜說,打開桌子抽屜,拿出一個綁著金色蝴蝶結的小包。
「很棒的切入點,貝雅特。」哈利說,並收到貝雅特的臉紅做為答謝。
「五角星是用一條連續直線互相交叉畫成的。」
「那是個倒過來的五角星不是嗎?」
「有很多意義,」安德斯說:「五是黑魔法最重要的數字。你說的五角星有一個尖角向上還是兩個?」
「妳臉上這個笑容真神祕,」奧莉說:「是不是妳那個紳士朋友啊?」
「我不知道,」奧莉說:「我不敢問。我只是編了許多我自己喜歡的答案,讓我能在夜裡做做好夢,這可能就是我為什麼會那麼愛他的原因。」
「對了,妳怎麼會起來了?」安德斯輕聲問道:「妳沒吃安眠藥嗎?」
「親愛的,我再去泡點茶。」
一九四一年,當年十六歲的她並非如此。那年她離開阿弗羅亞島,沿著鐵軌來到奧斯陸,在弗勒公館當女僕,服侍恩尼斯.施瓦伯中將和他的妻子蘭迪。施瓦伯中將是個高大英俊的男子,妻子蘭迪出身貴族。奧莉剛到弗勒公館的前幾日,心中十分惶恐,但施瓦伯中將和蘭迪待她不錯,也相當尊重她,不久奧莉就明白只要她工作細心準時,符合德國人有時毫無道理可言的著名民族性,就沒什麼好害怕的。
安德斯聳了聳肩。
「就像我剛剛說過的,老闆,只是個直覺而已。」
安德斯看著哈利,點了點頭。
男子不對稱的微笑讓尼可萊感到困惑。他臉上露出的是自我矛盾的微笑,既開朗又沉靜,既友善又憤世嫉俗,笑著且痛苦著。但尼可萊也可能跟往常一樣過度解讀了。
他並未開燈;天際照射進來的月光已然足夠。他直接走進臥房,按亮手電筒,照向床邊的承重樑。他猛然吸了口氣。樑上刻著的果然不是他原本以為的三角形。
菲畢卡身穿睡袍出現在走廊上,睡眼惺忪,紅髮四散。她沒上妝,被廚房的刺眼燈光一照,頓時比之前哈利對她的印象老了好幾歲。她看見哈利在他們家,嚇了一跳。
奧莉在薄暮下瞇起雙眼。太陽散放烈焰一整天.把她窗台花盆箱裡的花朵曬得奄奄一息,這時太陽已然西斜。奧莉微微而笑。天哪,她曾經那麼年輕,沒有人曾經像她那麼年輕。她是否渴望再度年輕?也許不會,但她渴望身旁有人圍繞,充滿生氣。以前聽人家說老人很孤單,她一直無法了解,如今……
「對,她是個好母親,好像聖人一樣。」
哈利用雙手用力抹了抹臉。
「不是,是連續殺人犯,這兩者的差別可大了。」
「他跟其他人都不一樣。他沒有那麼……他很老派。他希望我們等到……才……妳知道的。」
「我想今天這裡的四個大腦已經工作得夠多了。」莫勒說,站了起來。
「我對大量屠殺者不是很了解,這個凶手是不是大量屠殺者?」
男子跨過門檻,走了進來。
「原來如此,不過你為什麼要特別問這個?」
「我們有時候會借用這裡的房間。我在聖奧麗加服務。」
安德斯玩弄著他的咖啡杯。
「不無可能,」奧納說:「一般來說,凶手會希望達到高潮,但他有可能射|精卻不在犯罪現場遺留精|液,也可能他有足夠的自制力,等抵達安全的地方才解決。」
奧莉站起身來,關上陽台的門。快七點了。她朝屋後樓梯的頂端看了一眼,只見一雙時髦男鞋擺在依娜房間外的地墊上。原來依娜有訪客。奧莉在床上坐下,側耳聆聽。
施瓦伯中將是WLTA首長,WLTA是德意志國防軍的運輸部門,他選擇了火車站旁的弗勒公館做為自己的居所。施瓦伯中將的妻子蘭迪可能也在WLTA服務,但奧莉從來沒見過她穿制服。奧莉的房間面向南方,俯瞰庭院和鐵軌。剛住進弗勒公館的前幾週,她晚上常被長長鐵軌發出的噹啷聲、尖銳的鳴笛聲和其他噪音吵得睡不著覺,但日子久了也就逐漸習慣了。在弗勒公館工作一年後,她首次返鄉過節,回到小時候生長的屋子,躺在床上,聆聽著寂靜和空無,卻發現自己渴望聽見熱鬧人聲。
他們在電視和廣播登出了協尋廣告,湯姆剛剛才過濾完民眾提供的線報。警署一共接到二十四通報案電話,其中十三通來自報案常客,這些人不管有沒有看見什麼都會打電話來。至於另外十一通電話,其中七通提供的線索經過清查只是一般快遞員,另外四通電話提供的線報則是警方已經知道的資訊:星期一下午五點左右,卡爾柏納廣場曾經出現一個快遞員。警方接獲的新消息是有人看見那個快遞員騎在特隆赫姆路上。只有一通報案電話令人關注,這通https://www.hetubook.com•com電話是一個計程車司機打來的,司機說他在藝術與科技學院外見過一個單車騎士戴著安全帽和太陽眼鏡,身穿黃黑相間的單車衫,當時計程車司機駕車行駛在伍立弗路上,正好是卡蜜拉遇害時間前後。當天那個時間沒有一家快遞公司在伍立弗路附近區域有件需要收送,但後來第一快遞公司有個快遞員打電話來說,他騎車前往聖赫根區的露台餐廳喝啤酒時,曾稍微經過伍立弗路。
「一個。」
「也許動機不是性。」莫勒說。
「你是說有五個尖角的星星?」
「應該比較像是對犯罪現場的直覺吧,這些犯罪現場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可是我還沒辦法清楚說出來。第一樁槍擊命案發生在伍立弗路的閣樓。第二樁發生在西北方一公里的桑納街。第三樁命案的現場距離第二樁同樣是一公里,這次是在東方,在卡爾柏納廣場的辦公地區。凶手會移動,但我感覺這背後有一個合乎邏輯的脈絡。」
「啊哈!」奧納高聲說:「五角星,以黃金分割比例畫成,形狀很有意思。對了,你們知道有一派理論說克爾特人在維京時代想讓挪威改信基督教,所以他們畫了一個聖五角星,放置在挪威南部,用它來判定城鎮和教堂的位置嗎?」
哈利覺得刺眼萬分,第一個反應是舉起雙臂擋在面前。過了一秒,沒有任何事發生。沒有人開槍,沒有拳頭招呼。哈利放下手臂。
「她通常整個晚上都會睡得很沉。」安德斯說。
直到太陽照到屋頂上最高的屋瓦,她才離去。
他從打開的窗戶向外看,鳥兒正在墓園裡歌唱,令他想起列寧格勒的夏日和他父親。父親曾帶他去城外的老戰場,他的爺爺和叔伯長眠在早已被人遺忘的萬人塚裡。
奧莉聽出這樣說也不對,她問這些問題就好像是個愛嚼舌根的老太婆在探人隱私。她心頭一陣驚慌,彷彿看見依娜已經在心中盤算要搬去別的地方住。
「還有一件小事,」哈利說:「凶手留在被害人身上的鑽石……」
依娜又放聲大笑。那時她一感覺有東西觸碰她的臉頰,下意識地就揮手去撥,於是打翻了盛放茶具的托盤,這時地毯上還留有一層薄薄的白砂糖。
「你到底在幹嘛?」男子問。
「我們可能有點像妳跟施瓦伯中將那樣吧。」
她凝視著他,嘴唇動了動。
「原來如此,可是你沒注意到被害人有共同點嗎?」
奧莉坐在床沿,一手放在喉嚨上,感覺脈搏逐漸慢下來,恢復正常。
「奧納,你有什麼看法?」
「可以這樣說。我找到了五角星。你是做教堂裝潢的,應該知道五角星是什麼吧?」
「也許他跟電影《無為而治》裡的彼得.謝勒(Peter Sellers)一樣,」哈利說:「『我喜歡看。』」
「第一種是固定型殺人犯,他會引誘或強迫被害人到他家,然後下手殺害。第二種是地域型殺人犯,他會在特定地區犯案,比如說開瞠手傑克只在紅燈區殺人,但這個特定地區很可能是整個城鎮。第三種是遊牧型殺人犯,這種殺人犯可能背負最多條人命,美國的奧迪斯.杜爾(Ottis Toole)和亨利.李.盧卡斯(Henry Lee Lucas)這對搭檔就殺害了三百多人。」
「在她床舖旁邊的橫樑上。」
「警監先生,你說得沒錯,我沒睡著,發生那種事以後要睡著不太容易。我醒著躺在床上,腦子裡浮現關於命案的可能推論。」
「她不記得是伍立弗路的哪間公寓了,所以麥努斯載她去看,她指出的那間公寓就是卡蜜拉的公寓。」
「為什麼這樣說?」
「那就不是魔鬼的符號,你說的這個符號可能象徵生命力和熱情。是在哪裡發現的?」
哈利故意打個哈欠,以示證明,完全不明白自己為何要這樣做。
「嗯,謝謝。」
「我打壞了你們門上的星星,我是來賠罪的。」
「她們的性關係都很隨便。」
熱鬧人聲,弗勒公館在二戰期間相當熱鬧。施瓦伯中將喜歡社交,跟他往來的有德國人也有挪威人,人們如果知道有哪些挪威社會的領袖曾是德意志國防軍的座上賓,在弗勒公館吃香喝辣還抽菸,肯定會引起軒然大|波。戰爭結束後,奧莉被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燒燬她藏起來的座位卡。她聽從命令燒了座位卡,不曾對任何人透露半句話。當然了,當她看見報上登出的面孔明明是弗勒公館的熟客,卻大言不慚地說起他們在德國佔領期間過著被德國人擺布驅使的生活,她心裡就會升起違抗命令的衝動。她一直乖乖閉嘴只為了一個原因:和平降臨後,他們威脅說要帶走她的孩子,她在世界上最珍視的寶貝。害怕失去兒子的恐懼一直圍繞著她。
「我的老天,妳這麼年輕,不應該聽死人的音樂。」
奧莉伸手撫摸床上被單。
第一個晚上,他並未碰她,只是看著她,撫摸她的面頰,告訴她說她很美,比她能夠了解的還要美,然後他就站了起來。他離開時,眼淚似乎就要奪眶而出。
「我去卡蜜拉她家查幾件事,」哈利看見菲畢卡以為有壞事發生,便插口說:「我坐在床上閉目養神幾秒鐘,結果就睡著了。安德斯聽見我發出的聲音,上樓把我叫醒。今天真是漫長的一天。」
「妳喜歡他嗎?」
哈利啜飲一口咖啡。「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你的推論?」
奧納做個鬼臉。「呃,這不是伯爵茶。」
男子聳了聳肩。
「黑神,」尼可萊說,輕輕按下三個琴鍵。這三個琴鍵是不和諧音。「又叫做撒旦。」
男子朝尼可萊走來。尼可萊看見男子的眼睛布滿血絲,底下還有深色的黑眼圈,心想他可能已經有好一段時間沒睡覺了。
「他們在一九四五年五月那天離開挪威,後來我再也沒見過他們。到了七月我才發現自己懷孕了。」
「喔,原來如此,可是那不是我負責的,我只看見那個星星鬆掉了,而且倒了過來,」他微微一笑。「說得含蓄一點,那個樣子在教堂裡實在有點不太合宜。」
「喔,原來如此,」安德斯說:「這就簡單了。」
男子卻沒移動。
奧莉閉上眼睛,沐浴在溫暖的陽光中。
他試著在心裡建立命案現場的畫面。
哈利坐了下來,反覆聆聽這則和*圖*書留言,看能不能聽見任何呼吸聲,就像他幾天前接到的那則無語留言,可是卻什麼也沒聽見。
「哇,我看起來一定像扮裝皇后。」
哈利向後一倒,靠上椅背,偷眼朝湯姆瞧去,就這麼一瞧,他驚愕地發現自己心頭對湯姆浮現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欽佩。就好像你發現你的獵物竟然發展出如此完美的生存技能,因而感到欽佩。
「這樣就夠好了,」莫勒:「知道槍枝來源了嗎?」
「我會記下來。」
其他人離去半小時後,哈利看完了住在莉絲白家對面那兩名女子的訊問報告,關掉桌上檯燈,在黑暗中眨眼,這時天啟突然降臨。也許是因為他關掉檯燈就好像上床前關燈那樣,又或許是因為他在關燈後的那個片刻停止思考,無論原因是什麼,他面前彷彿有人塞來一張清晰銳利的照片。
「依娜?」
「對,用連續線條畫成的,你知道這種符號可能代表什麼意義嗎?」
「終於有了!」
「對,比我大一點。」依娜露出促狹的微笑,令奧莉覺得困惑。
然而奧莉發現,一個老太太和依娜這樣的少女發展出的關係,通常是少女提供友情,老太太接受友情。因此奧莉時常留心,不讓自己多管閒事。依娜對她總是很友善,但她心想那可能是因為房租便宜的關係。
「長眠安息。」哈利喃喃地說,閉上眼睛。
莫勒細看胖嘟嘟的心理醫生奧納胖嘟嘟的小指,心想奧納的小指高高翹起,到底有幾分是裝腔作勢,有幾分純粹是因為小指太胖才自然翹起。
門口站著一個身穿T恤牛仔褲的高大男子,一手纏著繃帶。尼可萊首先想到的是,那會不會是教堂有時會出現的毒蟲?
安德斯走到咖啡機前,放回咖啡壺。他的背部和上臂十分蒼白,幾乎是白色的,但他的前手臂卻是古銅色的,宛如夏天貨車司機的手臂。他的膝蓋同樣有如此明顯的膚色分野。
「那跟鑽石有什麼關係?」貝雅特問。
「謝謝。」她說,一臉困惑。
「檢查過了,」貝雅特說:「測試結果顯示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可能性是凶器。」
「有啊。有一次他開車載我去碧戴半島,我們去游泳,我的意思是我游泳,他坐在那邊看。他說我是他一個人的寧芙仙女。」
「也許吧。」依娜說,眼睛閃閃發光。
「那天晚上他流下眼淚,是因為他不能擁有妳嗎?」
奧納伸出手指數算:
「這件案子國際刑警組織已經查了四年,仍然沒有收穫。」湯姆說。
哈利的頭俯向桌面,但他其實正偷偷觀察安德斯的表情。
男子抬頭朝他望來。
奧莉用手拍了拍被單。
「我被噪音吵起來,」安德斯說,把一杯滴濾式咖啡放在哈利面前。「我腦子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有人發現樓上沒人住,闖了進去,所以我就上去查看。」
「有,」男子說:「我是來賠罪的。」
家具和其他物品都沒被移動過,但他的腳步聲依然在屋裡迴盪,彷彿主人死去讓這間屋子留下一個實存的空洞。同時他感覺自己並非孤身一人。哈利相信靈魂的存在。倒不是他對宗教有特別的信仰,而是每當他看見屍體,總是有一種感覺:屍體少了什麼東西,這樣東西跟屍體的物理變化過程無關。屍體看起來像是蜘蛛網上的昆蟲空殼,裡頭的生物不在了,亮光熄滅了,而且不會像早已燃燒殆盡的恆星那樣依然亮著如夢似幻的殘存星光。屍體缺少的是靈魂,就因為屍體少了靈魂之後的那份空洞感,才讓哈利相信靈魂的存在。
「這種五角星我們稱為惡夢十字,或是魔鬼之星。」
眾人像是被遙控器操控似的,同時轉頭朝貝雅特望去。她立刻臉現紅暈,似乎後悔說了這麼一句話,不過她把害羞擺到一旁,繼續說道:
「晚安。」她低聲說,轉身離去。
「五角星是古老的宗教符號,不是只有基督教用它而已。你可以看見那個有五個尖角的星星是由連續的直線組成,直線交叉了好幾次:一些有數千年歷史的墓碑就刻有五角星。不過當五角星倒過來,一個角往下指,兩個角往上指,就代表完全不同的意思,變成了魔鬼學的重要符號。」
「柯爾.波特是個老爵士樂手,早就作古了。」
「魔鬼學?」
她年輕時不喜歡炎熱的天氣,皮膚會發紅發癢,渴望挪威西北部那種涼爽潮濕的夏季。如今她年紀大了,將近八十歲:反而比較喜歡熱,不喜歡冷,比較喜歡亮,不喜歡暗,比較喜歡有人陪伴,不喜歡孤單,比較喜歡有聲音,不喜歡寂靜。
這就是為什麼她把房間租出去的原因。房間租給了一個從特倫德拉格來的開朗少女。
「耳機,」依娜笑道:「可能是音樂開太大聲了,我在聽柯爾.波特(Cole Porter)。」
「莫勒,我是開玩笑的。不過哈利,我知道你的想法,這個凶手對犯案的地理位置有強烈的偏好。以犯案地點來說,我們可以把連續殺人犯大致區分為三種類型。」
哈利的心臟停止跳動,一部分是因為這句話依然迴盪在房間裡,因此他知道這不是夢,另一部分是因為這不是女人的聲音,而最重要的是因為有人站在床邊,俯身望著他。
「我不確定那是不是個想法……」
奧莉看見他們如此恩愛,簡直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有如靈魂伴侶,沒什麼可以拆散他們。不過呢,奧莉告訴依娜說,當弗勒公館的賓客回家後,快樂的派對氣氛有可能變成激烈的爭吵。
「所以只要有人走過樓上地板,就會把你吵醒?」
他認出了站在面前的男子。
「我媽以前常彈給我聽,」男子說:「她說這首曲子很難。」
「妳知道我趕不上潮流,不聽這些現代音樂的。」
安德斯低頭看了看,彷彿這時才發現自己穿的是粉紅色睡袍。
他們四人看起來疲憊不堪,多半是因為原本抱著希望可以找到那個假冒的快遞員,如今這個希望已開始褪色。
「依娜?」
房客依娜依舊沒有回應。奧莉用一手托住托盤,伸出另一隻手輕輕觸碰依娜的臉頰。
「妳嚇死我了。」奧莉低聲說,聲音沙啞難辨。
「說不定殺人行凶和看見屍體對他來說就夠了。」
天啟降臨了。不是奇蹟,只是天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