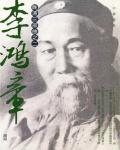第一章 鴉片的宿命
思想和觀念在溝通上的不順,當然會帶來實際運作上的磕磕絆絆。在最初雙方的貿易中,西方對於這個物質需求和慾望並不強烈的東方大國總覺得有點無可奈何,在這個古老的國度裡,似乎人人都有著一種「士」的精神,他們顯得高貴而迂腐,人們普遍不追求物質生活的豐富和奢侈,更注重於精神和面子。尤其是對於技術層面的東西,往往表現得不屑一顧。由於對於西方物質的漠視,在最初西方與中國的貿易中,西方一直出現逆差。在十八世紀之前的所有交往中,西方對於中國絲綢與瓷器的需求量很大,在此基礎上,他們又發展起了對於茶葉的新需求。在整個十八世紀中,以英國為例,它對茶葉的需要幾乎是呈幾何級增長,從一六八四年的五箱增至一七二〇年的四十萬箱,到一八〇〇年則又增長五十倍,這樣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直接的結果就是流入中國的白銀從十八世紀六〇年代的每年三百萬兩,增至十八世紀八〇年代的每年一千六百萬兩。
在鴉片得到中國人的普遍歡迎並且銷售量節節上升之後,英國人終於把鴉片視為取得他們與中國貿易平衡的一種手段了。英國人在征服了印度之後,就在印度大量地生產鴉片並形成對於中國的出口之勢。一七二九年中國進口的鴉片只有二百箱,但到了一七六七年已經超過了一千箱,一八〇〇年則超過了四千五百箱。鴉片似乎與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有效地對應起來了。十九世紀二〇年代,每年有二百萬兩白銀流出中國,而到十九世紀三〇年代初,這個數字上升到每年九百萬兩。
東西方最早的撞擊,是由於彼此精華的互相誘惑導致的。比如絲綢,比如香料,又比如瓷器。這些東西,本身就是帶有強烈神秘色彩的。比如說絲綢,它是由那種軟綿綿的蟲子吐出的絲織成的,這樣的過程本身就有點匪夷所思,像一個童話,或者如一個寓言,或者乾脆像是一種幻變——那種奇特的、牽涉到人類諸多本質疑惑的幻變。瓷器呢,同樣具有的,也是脫胎換骨的意義,那彷彿是泥土的鳳凰涅槃——最骯髒的、最普通的泥土,在經過烈火的焚燒之後,竟有著最潔淨的品質,就像一個最下層的農夫生就了最美麗、最冰清玉潔的公主。至於香料,與絲綢與瓷器所不同的是,它本身就不是一個準確的名詞,它具有混合性,具有模糊性和包容性,它含混不清,卻又無可奈何。它同樣具有謎一般的意義,它所揭示出的世界的神秘意義,它所能給人的啟迪以及迷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絲綢和瓷器。它是那樣的複雜,那樣的生動,同時又具有無限的蠱惑力,讓人們費思量,卻難忘。
一七九三年,在西方與中國的交往中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個龐大的使團從英國來到中國,他們此行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瞭解和掌握這個東方古國。使團由馬戛爾尼勳爵率領,隨團成員中,還有英王的表兄弟、前任駐俄大使馬德拉斯總督。這個大規模的代表團一行竟有一百多人,包括科學家、音樂家、藝術家和翻譯等,他們還帶著大量的輜重行李,在這些行李當中,有大量的禮品,代表著不列顛最先進的科技:望遠鏡、鍍銅榴彈炮、地球儀、自鳴鐘、樂器、兩駕馬車、一個熱氣球,甚至還配備了一名熱氣球駕駛員。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引起中國人對於英國產品的注意。到達中國後,代表團強烈要求拜見乾隆皇帝。謁見乾隆的目的,是想得到乾隆的允許,在各地開設通商口岸。九月十四日,乾隆在熱河避暑山莊一頂馬毛氈搭成的帳篷中漫不經心地接見了他們。來自英國的使者在說明自己的來意之前,就遇到了一個跪拜的問題。在清國看來,這些來自異國他鄉的「夷人」並不是代表一個主權國家向另一個主權國家饋贈禮物,而是來向「中央文明」或者「中央帝國」來朝貢的,既是來朝貢的,自然得向皇上行大m.hetubook•com.com禮。大禮是複雜的,它包括鞠躬、下跪、伏地等一整套程序。馬戛爾尼團長起先同意了,但是,作為當時地球上最驕傲、也最強大的國家的使者,馬戛爾尼也要求皇帝的大臣向他的國王施以同樣的禮節。由於喬治三世不在現場,馬戛爾尼要求皇帝的大臣向他隨身攜帶的一幅國王畫像施以參拜。馬戛爾尼的要求,自然被乾隆那些心高氣傲的大臣拒絕了。
在鴉片進入中國之前,古老的東方帝國已經達到了在農業社會狀態下的自我平衡,從本質上來說,這個國度是缺乏具體的目標和追求的,雖然從表面上看,以儒學為主的文明有著大同世界的目標,但這樣的目標並沒有具體化,也很難實踐化。千年不變的男耕女織,千年不變的春種秋收,千年不變的天朝上國,還有千年不變的之乎者也禮義綱常,使得中國政治和社會制度,在外人眼中,看起來像一尊精巧的瓷器一樣,細膩而迷人:靠灌溉而生產的稻米產量總是很高;鹽的分配和五穀口糧相搭配;大糞便溺足夠用來澆菜;人吃過的泔水可以養豬;堤壩防止水災;政府的糧倉保住了災荒賑恤;保甲制度自動地保障鄰里公安;家族成員之際,各自履行相互周濟安全的義務;農耕以各家各戶為單元進行,每一家,都由一個家長說了算,「三綱五常」的教育使每個人對自己的家庭,每個家庭對國家的義務,都謹守不悖;科舉考試則給所有的才智之士以正統教養,以努力方向;在官吏任用上,實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減少了攀親引故的弊病……這個東方古國就像一架古老的農耕機械一樣,龐大而周密,雖然在運轉過程中並不絕對合理,但是它總是顯得有條不紊,胸有成竹。
歷史進入了十九世紀,或許誰也沒有想到,一個從植物當中提取出來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動。在這裡,鴉片是一個偶然,但同時,它又是一個必然。這樣的鴉片就如同伊甸園的那個蘋果一樣,具有的,是與世界相當的意義。世界並不完全是空間意義上的,它更多體現的,是時間上的。蘋果在必須出現的時間出現,在必須出現的地點出現,並且以一種魔幻的方式,與世界和人類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同樣,鴉片在中國近代發展史上所具有的意義也是如此——這種從最美麗的花朵的果實當中提煉出來的東西,在更大程度上,與那只蘋果一樣,它具有著符號的意義,它所代表的,是那種逃避不了的宿命意義。
從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來看,由於整個制度方式承續著明朝,清朝在性格上也有著明朝的特點。這個國家有著極端的內向性,整個結構缺乏內部以及外部的競爭。在這個制度看來,維持著億萬農民安居就業和上萬官僚寧靜在職,就是一種非常好的平衡了,這種低級的平衡似乎就是他們的全部追求。為保持這樣的平衡,政治制度不會也不願意對財政作更大的變革,並尋求科學發展。與此同時,這種變革和發展所需要的知識儲備以及理想支持也不夠。在這種前提下,整個社會運轉到了一定時期,必然失去一種方向感,社會不可避免地跌入一種停頓和恍惚的狀態。
一八四〇年以後,戰爭並沒有立即使這個緩慢的、腐朽的古老國家醍醐灌頂,對於清朝的刺|激,也遠遠沒有達到讓它發憤圖強的地步;這塊土地上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真正嗅到鴉片嗆人的硝煙。也許,這是因為古老帝國的承受力太強了,人們見得太多,也司空見慣,總是習慣於從容而麻木地對待巨大的變故。從官方的態度來看,鴉片戰爭的失敗,只不過是天朝在一場與西方野蠻人的小衝突中輸了一點顏面。清國不屑在這樣的失利中改變自己的立場、態度以及傳統的生活方式。清政府並未組織相關的調查委員會來研究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追究責任;也沒有派出官員出國考察,更m•hetubook.com•com談不上在組織上作任何更改。一切都是在原地踏步,官方的記載甚至聲稱,海上野蠻人已被趕走。清國不顧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的教訓,一如既往地拒絕把外國人當作平等民族對待,拒絕與他們建立被視為正常交往的外交關係。《南京條約》的很多條款被置之不理,清政府給西方人設置了很多障礙。至於這個國家的民眾,仍然一如既往地重複著先前的生活。東方和西方還沒有心平氣和地進行對話,在中國人和西方人眼中,彼此都是不可理喻的怪物。一位叫汪仲洋的中國文人用文學的筆法描繪了他初次看到的英國士兵:「鷹鼻,貓眼,紅鬍,雙腿不能彎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中午就沒有睜開。」至於在西方人的筆下,中國人一直是麻木、呆滯和無助的形象,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年的英國人麥高溫描繪說:「中國人看起來並不吸引人,他們的皮膚是黃色的,聲音尖利而不悅耳……他們的顴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受傷之後傳下來的。他們的嘴很厚,嘴巴寬大無比——那雙窄窄的黑色杏仁眼神,細小的眼球在眶內轉來轉去,就像是與外部的世界捉迷藏。」
初始,哥倫布的成功在歐洲引起了巨大的驚異,繼而爆發了一陣古老世界從未有過的冒險狂潮,每一個人都湧動因幾個世紀封閉所積蓄的狂熱,人人都想突破自己狹小的生活範圍。在歐洲,那些對自己工作和生活不滿意的人,自感落伍並焦急彷徨的人,還有荷爾蒙旺盛的士兵、失落的軍官、落魄的豪紳、身處底層的黑人,他們全都希望到新世界去沐浴陽光雨露。短短的一百年中,歐洲的航海成就不只是翻了一百倍,而是翻了一千倍。與此同時,地理學、天文學和地圖學在這段時間內也經歷了空前絕後的前進速度。人們終於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星球之上,明白了地球的形狀和範圍,也明白了在廣袤的地球上,還有很多地方是文明的空白。這種對身處世界的茅塞頓開,一下子勾起了歐洲人史無前例的征服慾望。
歷史發展到十八世紀,東方與西方像漂流在大洋中的兩大板塊一樣,不可避免地相撞了。在此之前,世界的力量已經悄悄地向西方聚集,歐洲文藝復興以及稍後的宗教改革,似乎從某種程度上解決了人類所面臨的初級困惑,也指明了人類自身的方向。人類的思想在經過長長的跋涉之後轉而變得深邃起來。這樣的清晰,對於人類自身來說,就像是第二次直立行走,是思想和人格的直立行走。與此同時,由新興思想所產生的動力正在勃發,人們開始了對自身以及自身環境的挑戰,力求把一切不可能變成可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十七世紀的大航海運動興起,人類文明開始邁開大步。大航海所產生的接二連三的效應,使得歐洲墜入集體的狂歡,列強們的胃口像獅子一樣被調動起來。時間也撒開雙蹄,一下子變得突飛猛進起來。
東西方霸主的這一次碰撞就這樣不歡而散。馬戛爾尼從這次與中國最高統治者的會見中洞察到這個文明古國的心思,感覺到他們對於商業知識與理念的匱乏和淺薄。回國後不久,馬戛爾尼撰寫了一份關於中國的考察報告,他在報告中說:中國人根本沒有準備與歐洲列強打仗,因為它到處充斥著貧窮,文人對於物質進步興趣索然;士兵還在使用弓箭……西方看到了這個東方大國的虛弱,他們意識到龐大的中國不足以對他們形成危脅,對於商業觀念落後的中國,開始覬覦了。
乾隆皇帝很快將會見英國使團的事撂在一邊。這個東方皇帝對於西方的經商要求表現得很冷漠。這也難怪,當時清國的人口已經超過了三億,幾乎為包括俄國在內的歐洲的兩倍,同時,清國的國內市場和國內貿易也遠遠超過了歐洲。在這樣的情況下,乾隆當然懶得去搭理地球那邊的歐洲。在馬戛爾尼和他的使團離開中國之
和-圖-書時,乾隆托他們帶給了大英國國王一封生硬的信,這封信絲毫沒表現出外交上的委婉和禮貌,一個成熟自足的帝國的自信和頑固展露無疑:「我們的方式毫無共同之處,你們的公使也無此能力掌握這些禮節,並將其帶到你們的蠻夷之地。那些奇異且昂貴的禮物並不能打動我。你的大使也看到了,我們應有盡有。我認為這些怪誕或精巧的物品毫無價值,你們國家的產品對我來說毫無用處。」
當數百年後,人們在分析這段歷史的時候,可以這樣說:鴉片戰爭打破了這樣的狀態,這樣的戰爭,遲早是要發生的,即使不是發生在一八四〇年,也會發生在不遠的日子裡;它不是由鴉片引起的,必定是由另外一種方式引起的。從這一點上來說,鴉片戰爭的確帶有不可避免的宿命意味。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東方的香料促使了歐洲中世紀的迷幻,也促使了歐洲中世紀的覺醒。在此之前,歐洲在很長時間裡一直用海吃海喝的肉食方式來掩飾生活的單調和無聊。因為嚴謹和刻板,以及對於自身慾望的忽略,他們的生活遠不像東方人那樣富有詩情畫意;他們的生活,包括口味和方式都單調而缺乏情趣,也離自然很遠。這時候來自東方的胡椒、桂皮、乾肉豆蔻花的進入,使得歐洲中世紀粗劣不堪的習慣遭受到新鮮的刺|激,彷彿突然打開一個窗口,有一束光劃破漫漫的黑夜。香料的主要功能是為儲藏,而另一些功能,比如咖啡,比如罌粟,以及能激盪起色|欲和迷幻的麝香、龍涎香、樟腦、珍貴的樹膠脂,等等,對歐洲人所引起的誘惑幾乎是致命的,它們改變了歐洲人的日常生活,也改變了歐洲人的習性。歐洲人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這些極富有魅力的物品都產自於東方,而留給歐洲的,都是些平常與平庸的東西,比如土豆,比如牛羊。這樣的方式如同神奇的天方夜譚故事,激起歐洲一片春意。當然,這些都是早先的事情。那時在西方人的眼中,東方的一切都因其偏遠、稀有、富有異國情調,也許還因其昂貴,而在歐洲贏得了一種影響強烈的、催眠的魅力。沒有任何商品能像香料那樣受到人們如此強烈的貪求,東方的這些花、香以魔幻的方式把歐洲的靈魂給熏倒了。
李鴻章時代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應運而生。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曆一八二三年二月十五日,李鴻章出生於安徽省的廬州府合肥縣磨店鄉。鴉片戰爭爆發的一八四〇年,李鴻章十七歲,那一年,李鴻章按部就班地參加了科舉,考取了秀才。
西方大航海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西方商人乘船來到了中國的沿海地區,開始貿易,也開始掠奪。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佔據著與中國進行貿易的主流;到了十七世紀,新興的荷蘭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成為海上霸主,在亞洲,他們佔據了台灣和雅加達進行貿易;而到了十八世紀,英國人取代了荷蘭人,張開了更貪婪的大嘴。
接下來的事情便是眾人皆知了。因鴉片引起的貿易戰發展為軍事上的戰爭。這場戰爭最大的表現,在於反映了東西方在很多方面的差異:比如說對商業的認識,對軍事的認識,對外交的認識,對民眾的認識……而這場戰爭算是徹底暴露了這個看起來很強大的東方帝國的虛弱。在整個戰爭過程中,大清帝國表現得幾乎不堪一擊,「天朝」的威嚴頓時坍塌。幾百年後的今天,人們在總結這場戰爭時得出的結論是:這場戰爭從本質上來說是實力對比的結果,是軍事上的失敗,更是經濟實力、組織方式、制度方式以及認識和思維方式的失敗。最重要的,還是組織上的重負以及文化傳統本身的脆弱。當時的中國是由無數農村組成的一個大集團,在這樣的集團中所形成的呆板、效率低下、運轉緩慢,以及所形成的不能精確管理的弊端要遠遠大過於貪污的後果。雖然從表面上來看,這個國家有著近乎完全的精神和信仰,但在本質上,由https://m.hetubook.com.com於缺乏科學性而帶來組織上的根本缺陷,制約和限制了社會向精細以及合理的方向過渡。這使得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以及很多相關的制度和措施,不可避免地進入了一個死胡同。
相比於乾坤挪移的自然之勢,一個人的力量總是微不足道的,那種竭盡全力的努力就像紙人在風雨中的飄搖。一切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什麼也不能改變,什麼也談不上改變。
西方很快找到了一個突破的工具,那就是鴉片。鴉片的出現,可以說是集中暴露了中國人的軟肋,那種看起來已成為一種堅強習慣的道德操守和淡泊民風,在這黑黑的藥丸面前,不堪一擊。最初,鴉片主要是作為一種鎮痛劑在醫療上使用,吸食鴉片,容易導致便秘,這樣能夠治療因痢疾所產生的腹瀉。而在中國南方,痢疾非常普遍。但很快,吸食鴉片的中國人開始對鴉片產生了一種依賴,他們抵禦不了鴉片的誘惑,開始大規模地吸食。這種可以舒緩身體與精神上的痛苦和緊張、使乏味而繁重的體力勞動可以變得比較輕鬆的藥物,使古老的國度原形畢露。這樣的狀態正好說明,這個龐大的王朝雖然在道德和世界觀體系上看似緊密,但仍存在明顯縫隙。鴉片在清國的興起,不僅僅給西方列強帶來貿易和經濟上的好處,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找到了這個東方大國的軟肋,讓他們信心爆棚。一個難以抵禦鴉片的民族,最起碼在思想上與意志上是有著很多不成熟之處的。
看起來,所有的緣起似乎都是因為鴉片。
西方勢力就這樣在不經意中向東方積極地滲透。在這種格局下,東方處於明處,西方處於暗處。西方慢慢熟悉東方的一切,熟悉東方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實力、科技水平等,而對東方人來說,由於自給自足的經濟以及對於物質生活的淡泊,包括自我封閉的文化,使得他們始終對於世界那邊的國家引不起興趣。那些處在明處的東方官僚們,漫不經心地,甚至漠視西方勢力的潛伏,他們的注意力仍然在自己的遊戲方式中,沒有因沿海的喧嘩而絲毫改變。他們一直懶得睜大眼睛去注視煙波浩渺之外的地方,自始至終表現得懵懵懂懂、心不在焉,在他們看來,這樣的喧嘩與騷動於事無補,因為時間和生命方式的無法改變,人類所處的狀態同樣無需改變。
這個龐大的農耕機械看起來穩固無比,但在它的內部,並不是天衣無縫的。最切實的危機,是社會生機勃勃的成長和呆板笨重的結構體制之間的摩擦。這樣的內在牴觸,形成了中國社會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啞謎。對於統治者來說,絕對的王權才是國家政權的真正目標,至於其他的,包括社會的發展、物質的豐富以及精神的解脫,都屬於混沌狀態。這樣的混沌,在很長時間裡造成了社會發展以及智力創造上的停滯和靜止。在這個時候,鴉片的出現,使得這個國家的薄弱之處充分地暴露出來。這個精巧的制度和社會在遭受到西方毫無道理的衝擊之後,就像一個瓷器一樣摔在地上……鴉片的出現完全是一種機緣,那是所有的因緣發展到一定階段,或者生命運行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的產物,就如同我們現時的電腦信息的興起。直到今天,仍有人固執地認為,所有的東西都不是發明的,而是風生水起,應運而生的。
在鴉片戰爭起始的那一刻,從沒有人意識到,一場從古到今為止最大的變化就將來臨。即使是在鴉片戰爭爆發後,一切看起來都是緩慢無比。中國人仍在悠閒地享受慢的樂趣,優哉樂哉地按照一種無形的、非物質化的速度,游手漫遊於鄉間小道、林間空地,以及線裝的古書中,仍舊把那些斷章絕句像野花一樣,撒得遍地都是。西方列強對中國的這一次重重撞擊,國人的反應仍是緩慢的,緩慢得像幾乎沒有人察覺。
雙方所描寫的,只是在相貌以及感官上的隔膜。實際上雙方在思想、認識、習俗和文化上的差距更大。這樣的差距,使得從此之後雙方
和*圖*書之間越來越頻繁的磨合風生水起。這也注定,今後的一百年,是一個並不平靜的一百年。
而在東方,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生活仍舊是按照原來的節奏不緊不慢地踱著方步。從對於時間的認識上,就可以看出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區別。在東方人眼中,時間一直是一個圓,循環往復,週而復始,速度並沒有實質性的意義,只會增加輪迴的次數。東方人從不會產生時間上的緊迫感,並且,對於時間,也缺乏認知的精確性。在中國,一天分為十二段,每段之中,是比較模糊的,就像一個圓被分成了十二部分。而在西方看來,時間是直線的,也應該是精確的,它可以精確到時、分、秒。因為對時間的模糊和漠然,在東方人看來,自己生活的地方有著充足的陽光、雨水以及糧食,就已經足夠,他們一直沒有貪婪的慾望,一直滿足,一直自得,他們就像植物一樣,平穩地按照自己的傳統和習慣生長著。按照西方歷史學家的說法,直到一七〇〇年,當時的東方大國,它的物質生活在世界上還是最好的,從東方流向西方的各種發明,要比從西方流向中國的各種發明多得多,所以在馬可.波羅等人的眼中,東方是一個遍地黃金的地方。但從明朝中期以後,西方商業興盛,城市發展領先,在科技、商業、文化、制度等方面後來居上,尤其是航海業的突飛猛進,不僅僅帶動了商業的發展,更使得人們在科技、文化、世界觀以及自信心上突飛猛進。對於此時的西方來說,在很多層面上已經與溫柔敦厚的東方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馬戛爾尼收回了對乾隆行跪拜禮的初衷。八十二歲的乾隆顯然不太高興,但還是有禮貌地克制住了。馬戛爾尼向乾隆贈送了禮物,乾隆看起來並不是很感興趣。後來,這些禮物被堆在宮中的一個廁所裡。乾隆還與一個隨馬戛爾尼來的十二歲的叫喬治的小孩交談了幾句,小喬治已經會說漢語了。乾隆聽著這個金髮小孩怪怪地說著漢語,很是開心。馬戛爾尼對乾隆的印象不錯,他後來說:「在接待我們的時候,乾隆非常親切有禮,我們十分滿意。他是一位優雅的老人,健康有力,看上去不過六十歲。」
貿易的大規模逆差讓西方開始緊張。他們加大了對這個東方大國的研究和評估,讓他們感到困惑的是,為什麼這個文明古國的人要如此克制自己的慾望,有著如此多的與人性相悖的東西。當他們慢慢地深入瞭解這個國度之後,西方人對於中國以及中國文化的評估逐漸降低。與最初傳教士以及伏爾泰們對於中國的讚美和歌頌相比,他們瞭解之後的報告無疑顯得具有理性和真實性。大多數報告都表明中國是一個不富庶的、只是具有古代文明的國度,他們一直處於長長的、蒙昧的中世紀;除了官僚和商人階層之外,大多數人都比較貧窮;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近代化尚未啟動。在這樣大量而清晰的調研報告面前,西方形成了對於中國的相對比較清晰的看法,那就是,中國並不是一個可怕的國家,它的文明,包括物質生活狀態以及對於自然與社會的理解與掌握的狀態尚落後於西方。在中國,由於在世界觀上的普遍模糊,在主體意識上並沒有明確的自由與進步的標準。同時,他們的弱點還在於,缺少一種最隱秘的思想,只是有著一些框框似的道德體系,這種道德體系更多的是為了內心的安寧以及社會的穩定而設立的一些框框。慢慢地,越來越多的西方智者對於中國都持有這樣的觀點。這當中也包括孟德斯鳩、盧梭、黑格爾等。正是基於認識和思想上的優勢,當時的西方對於他們突破中國還是抱有很大信心的。他們形成的一致看法是:古老的農業經濟——官僚政治的中華帝國,遠遠不是正在進行擴張的、推行國際貿易和炮艦政策的英帝國和其他帝國的對手。西方列強在擴張中唯一所需要的,就是尋找一個突破點。就像尋找一個蘋果一樣,使得東方就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