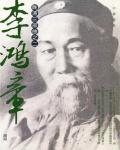第二章 塵歸塵,土歸土
桑於河上白雲橫,惟冀雙親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課讀,負心今尚未成名。
不久,李鴻章的淮軍在上海與太平軍打響了第一仗。對於此仗,李鴻章做了精心的準備,雖然他一直對於自己的子弟兵有足夠的信心,但進入上海的第一仗關係到自己的聲望,關係到這支部隊是否能在上海站住腳,甚至關係到整個戰局的發展。這一場遭遇戰打得慘烈無比,太平軍在忠王李秀成的率領下,共有數萬人進攻上海,交戰的地點就在現在西郊一帶。據說,在戰鬥呈膠著狀態之時,李鴻章搬來一把椅子往虹橋橋頭一坐,親自督戰。太平軍用上了火炮,火力非常猛。淮軍「春」字營的張遇春部上去沒多久,就頂不住了,隊伍漸漸退卻下來。張遇春剛跑到橋邊,正好撞到李鴻章,李鴻章厲聲說道:「拿把刀來,把他的頭砍了!」嚇得張遇春趕忙率眾掉轉方向又跟太平軍去拚命。戰局如火如荼之時,神奇徵兆降臨——淮軍大炮齊發,隨著炮響,上海上空突然烏雲密佈,一場大雨傾盆而下。一向迷信的太平軍心理突變,倉皇撤軍,慌不擇路,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李鴻章大獲全勝。首戰告捷,淮軍信心爆漲,李鴻章更是躊躇滿志。
接下來的戰鬥很快變得殘酷無比。不久,與李鴻章一同來安徽作戰的呂賢基在舒城戰敗後投水自殺。第三年,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這個一直聲稱自己平庸無能,但卻能培養出好幾個傑出兒子的老實官吏在戰局僵持中抑鬱而死,臨終時留下了「吾父子世受國恩,此賊不滅,何以為家」的遺囑。李鴻章又接二連三地打了好幾個勝仗,先是攻克含山,然後又參與攻克了廬州。朝廷為了嘉獎李鴻章,將他的官位一下子提升至四品。
一八四三年,李鴻章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時任京官的父親李文安從北京來函,叫李鴻章入都,準備來年的順天府鄉試。收到父親的來信後,李鴻章興奮異常,他意識到自己報效國家,實現抱負的機會終於來到了。從祠堂郢村老家出發,包括在去京城的路上,李鴻章一共提筆寫了十首《入都》詩。這一組詩,一直為後人所傳誦。
壯志不消三尺劍,奇才欲試萬言詩。
後人曾這樣描述這一段血腥的場面:李鴻章在蘇州婁門外軍營會見並宴請郜永寬等人,「甫就席,有軍官自外入,投牒李公,李公就牒出。酒行,旋有武弁八人,各手一冠,皆紅頂花翎,膝席前,請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計也,竟揚揚得甚,起立,自解其額上黃巾,手冠者俟其側,從官盡起,目注之。轉瞬間,八降酋之頭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
元宵節剛過,首批淮軍四營抵達安慶。他們是張樹聲、張樹珊、張樹槐、張樹屏兄弟部;劉銘傳部;潘鼎新部;吳長慶部。依次組成「樹」、「銘」、「鼎」、「慶」字四營。當新組建的淮軍齊刷刷地列隊於曾國藩面前時,曾國藩大喜過望,他召見各營將領加以考察,並親自為淮軍訂立規章制度。因為擔心新建的淮軍兵力單薄,曾國藩還從湘軍各部抽調兵將,慷慨地交給李鴻章。他們分別是:張遇春部「春」字營;李濟元部「濟」字營;程學啟部「開」字兩營;滕嗣林、滕嗣武新勇「林」字兩營;陳飛熊部「熊」字營;馬先槐部「垣」字營。並將韓正國、周良才親兵兩營送給李鴻章作為「贈嫁之資」。其中,以桐城人程學啟部「開」字兩營士卒多系安徽,打起仗來非常剽悍。這樣,李鴻章初建的淮軍,就有了十四個營頭的建制(每營正勇五〇五人,長夫一八〇人,共六八五人)。一八六二年三月四日,曾國藩在李鴻章的陪同下,檢閱了在安慶集結的淮軍各營。隨後,李鴻章又利用了上海士紳的財力,花銀十八萬兩僱用了英國商船七艘,將九千淮軍分批由水陸運往上海。當淮軍分乘七艘船從長江上順江而下,迎迓著長江溫濕的春風的時候,李鴻章知道自己青雲直上的機會真正到了。
陸機入洛才名振,蘇軾來遊壯志堅;多謝咿唔窮達士,殘年兀坐守遺編。
祠堂郢村比於灣略大,有五十多戶人家,大多已不是李姓了。但他們對李家當年的情景,卻代代相傳,知道不少。一個當地居民聽說我們是來看李鴻章故里的,熱心地趕過來給我們介紹:這裡是當年李家祠堂所在地,這裡是當年李家的書屋……據說,前幾年,還有一個老人知道李鴻章出生時胎盤埋的確切位置……與於灣一樣,現在的祠堂郢村也是破落不堪,李家當年的老宅所在地一片荒蕪,祠堂前的放生池,也成為了雜草叢生的野塘。同樣遍佈村落裡的,是當年屋舍的斷壁殘垣。當年,這裡一片繁華堂皇:村裡不僅有著李家老宅、池塘,還有大片的土地和祖墳地。現在,一切都消失了,彷彿一切都沒有存在過,就像曾經的一個夢一樣。
二〇〇六年七月的一天,我來到了現在的合肥市瑤海區磨店鄉祠堂郢村。來這個地方,是因為我想瞭解一個人的來龍去脈,感受一個地方的氣韻和脈搏,並以此來推斷一個人依稀的靈魂。
窮通有命無須卜,富貴何時乃濟貧;角逐名場今已久,依然一幅舊儒巾。
一八六一年九月五日,曾國藩率領湘軍收復軍事重鎮安慶,控制了長江中游的局勢,對太平軍形成了順江而下的局面。與此同時,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部率重兵出擊,打到離南京不遠的地方。從戰略上說,湘軍對太平軍和圖書的戰略形勢已經由防禦、僵持轉入戰略進攻階段。
驪歌緩緩度離筵,正與親朋話別天;此去但教磨鐵硯,再來唯望插金蓮。
李鴻章像一條潛龍一樣終於等來了機會。他知道,這是一飛沖天的時候了。李鴻章立即行動起來,他寫了很多信,首先通過父親李文安當年的舊部張樹聲招募了合肥西鄉三山諸部團練。接著,又通過前來安慶拜訪的廬江進士劉秉璋與駐紮三河的廬江團練頭目潘鼎新、吳長慶建立聯繫。潘、劉自幼同學,又同為李鴻章父親李文安的門生;吳長慶的亡父吳廷香也與李文安有舊交,自然一呼而應。與此同時,李鴻章還命令三弟李鶴章回合肥故鄉招募舊部團練,響應投軍的有內親李勝、張紹棠,昔年好友王學懋等,以及父親李文安的舊部吳毓蘭、吳毓芬等(這些東鄉團練與西鄉周盛波、周盛傳兄弟的「盛」字營,均屬第二批成軍的淮勇,後由陸路陸續開赴上海)。短短幾個月時間裡,李鴻章即招兵買馬數千人。
李鴻章這十首詩雖然有一些矯情的成分,但在這樣的詩中,明顯地能看出一個人鬱積於胸的大志。這十首詩在總體上有著相當才華,也是一代讀書人的心聲。一個行裝寒磣、氣宇軒昂的弱冠書生,懷著報效天下的強烈願望,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去尋夢,其心境,其經歷,都頗能引起那些皓首窮經夢想顯達的士子們的共鳴。這也難怪李鴻章的這十首《入都》詩後來被人們廣為傳誦。曾國藩曾對李鴻章有一句半真半假的評價「只顧拚命做官」。這也算是從本質上一語中的。李鴻章的確是一個有著宏大志向、異常執著於功名的人。
快到磨店鄉政府的時候,我們終於從一個騎摩托車的年輕人那裡得知了李家祠堂的確切方位。我們順著他所指的方向來到了一個村莊。這個名叫於灣的村落同樣荒涼而破落,村子裡的房屋七零八落,一點秩序都沒有。剛進村口,就可以看到散落在地表的破損的旗桿石、石鼓等。我一邊用相機拍攝,一邊想像當年村落的格局。問及村裡人這裡有什麼與李鴻章有關的遺跡時,村裡人說,當年李鴻章的父母曾合葬在這裡,但現在墓已不在了。他們還說,以前這裡有一個李家祠堂,很大,後來全拆了,現在改建成小學。在學校裡,還有幾株李鴻章種下的樹。
西郊大捷使整個上海灘瞠目結舌。接下來的八月和十月,李鴻章帶領淮軍與太平軍又正面交鋒兩次,是由淮軍中驍勇善戰的劉銘傳部和程學啟部對太平軍的譚紹光部,地點分別是上海西區的北新涇和更外圍一點的四江口。劉銘傳和程學啟都是淮軍中有名的猛將,他們打起仗來有一股不要命的勁頭。這時候,劉銘傳部已在李鴻章的授意下,有了自己的洋槍隊了,這更讓劉銘傳如虎添翼。這兩場戰鬥都獲得了大勝。半年之內,三戰三捷,不僅使李鴻章在上海站穩了腳跟,也為淮軍贏得了相當好的口碑,中外人士不由得對李鴻章和淮軍刮目相看。淮軍的實力不斷壯大,半年之內就迅速擴展至五十個營,部隊增至二萬人。此後,淮軍更是急劇膨脹,至攻打天京前夕,總兵力已達七萬餘人。
一個人的氣質總是與他的生長環境有關。安徽設省是在康熙年間。對於新設立的行省安徽來說,位於江淮之間的廬州並不有名,也一直受著冷落。它只是一個小地方,商業不發達,讀書的風氣也不是太濃。但這塊不顯山不露水的地方絕對讓人不敢小覷,在歷史上,這一帶就是中原文化與楚文化、吳越文化的交際地帶。在安徽文化發展過程中,始終具有一種通變的精神。這種通變即司馬遷所說的「通古今之變」,它包括「批判、會通、創新」等環節,即膽識兼備的批判精神、兼容並包的會通精神和超越前人的創新精神。李鴻章之前,這一帶在歷史上就出過很多雄才大略,比如說春秋時期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一的管仲,秦末項羽大帳中羽扇綸巾、料事如神的范增,漢末三國紛爭時的梟雄曹操,以及東吳大將周瑜、魯肅等。除此之外,廬州本身就在宋朝出了一代名臣包拯。而離李鴻章在時間和地域上最近的,是明朝開國皇帝、鳳陽人朱元璋。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當然給這塊土地積蓄了足夠的底氣,也決定了這一帶經常出沒臥龍鳳雛般的人物。
輾轉一番之後,我們來到了離於灣村數公里的祠堂郢村。這裡,算是李鴻章的出生地。李鴻章位居直隸總督之後,曾有一個在當時極負盛名的風水先生來此地勘察,當他步行到離祠堂郢村五里路左右的「少荃湖」一帶,向祠堂郢村那邊一看,當時就說不出話來——只見不遠處一脈長長的山丘,看過去一條完整的龍脈清晰可見,而祠堂郢村,正好在龍頭,一個山坡的左邊,像一個張開的龍爪。風水先生一下驚呆了。後來,他逢人便說,難怪李鴻章成為國家的重臣,成為皇帝和太后的左膀右臂,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我們一直問著路尋覓而去。令我們感到奇怪的是,竟有許多人不知道李鴻章。他們對我們的問話頻頻搖著頭,他們根本不知道李鴻章的老家究竟在哪裡,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與一百多年前那個大人物的關係。一個老者在聽到我們的詢問後,竟然反問道:李鴻章我怎麼不知道,是那個財主吧?讓我們哭笑不得。當年,這個名字曾經如雷貫耳,然而在歲月懵懵懂懂地向前挨過一百多年之後,卻一下子就變得無足輕重https://www.hetubook.com•com了。人類最以為是的榮光和功名,是經不起時間的腐蝕的,時間能將一切都濯洗得乾乾淨淨,就像海水沖刷沙灘,能將所有的一切蕩滌抹平。
太平軍的失勢,與其說是敗於湘軍,不如說是敗於自身的內亂。由於太平天國本身的宗教觀支離破碎、一知半解,有著濃郁的迷信色彩,缺乏正確的濟世理想和組織理念,這樣的集團在經過短暫的成功之後,很容易將重心轉移到對內部利益和權力的爭奪上。攻下南京後不久,太平天國內部爆發了著名的「天京事變」,太平軍產生內訌,韋昌輝刺殺了楊秀清,石達開拉起大隊人馬離開了天京,太平天國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大大削弱。在這樣的情況下,太平天國無奈放棄北上的進攻目標,由戰略進攻轉向戰略防禦。安慶失守後,太平天國更是陷入恐慌,他們一方面固守天京,另外一方面把進攻方向轉向了富庶的上海一帶。這樣的行為,很明顯不是以取得政權為目的,而是退而求次,準備與清廷各霸一方。一八六〇年,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前鋒直指上海。
殺了「八大王」之後,程學啟立即派兵洶湧地闖進蘇州,「無門不破,無處不搜,無人不魄飛天外」,據說,僅在城內雙塔寺庭院內,就殺死太平軍三萬人。
侷促真如虱處褌,思乘春浪到龍門;許多同輩矜科第,已過年華付水源。
一肩行李又吟囊,檢點詩書喜欲狂;帆影波痕淮浦月,馬蹄草色薊門霜。
一枕邯鄲夢醒遲,蓬瀛雖遠系人思;出山志在登鰲頂,何日身才入鳳池?
李鴻章回故鄉組織民團還有個故事:李鴻章在京時,經常去一個名叫呂賢基的安徽老鄉處,呂賢基時任工部左侍郎,旌德人。一八五三年二月,太平軍從武昌順江東下,攻佔安徽省城安慶,殺死安徽巡撫。消息傳到北京時,李鴻章正在琉璃廠的海王村書肆買書,聽到這則消息後,李鴻章連忙找到呂賢基,慫恿他上書朝廷,調派人馬奪回江淮戰略要地。呂賢基認為李鴻章很有戰略眼光,文筆也好,便讓李鴻章代為執筆奏折。結果奏折送上之後,咸豐帝命呂賢基擔任安徽團練大臣。呂賢基沒想到自己竟被直接派到前線,全家人一時如喪考妣。呂賢基情急之下對李鴻章說:「君禍我,上命我往;我亦禍君,奏調偕行。」於是李鴻章與呂賢基一同回到安徽。
一入都門便到家,徵人北上日西斜;槐廳謬赴明經選,桂苑猶虛及第花。
在滬的江南士紳、買辦慌了,他們緊急籌備「中外會防局」,希望西方列強出面干涉,同時選派曾是李文安、曾國藩「同年進士」的錢寶琛之子錢鼎銘,攜馮桂芬起草的書信抵達安慶,泣請曾國藩發兵救援。曾國藩大為動容,一連幾天與李鴻章商量發兵之事。洞察力驚人的李鴻章向曾國藩提議,應該派重兵深入到上海地區,從東面對南京形成包夾之勢。
昔日兒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為?
曾國藩聽從了李鴻章的意見。最初,曾國藩是準備讓九弟曾國荃領兵東援的,但曾國荃以為攻克天京首功在即,不願前往上海。曾國藩又考慮著起用湘軍名將陳士傑,但陳士傑以母親老邁力辭,不肯出山。經過反覆考慮之後,也因為湘軍招募兵士跟不上,曾國藩決定給李鴻章一個機會,他一方面親擬片稿,力挺李鴻章擔任江蘇巡撫;另外一方面,曾國藩派李鴻章火速就近在合肥一帶招募人馬,組建淮軍,準備挺進富庶的長江三角洲。
丈夫事業最當時,一誤流光悔後遲。
——李鴻章《二十自述》
少年的李鴻章就一直生活在祠堂郢村,間或,他也會到附近的於灣等地走走親戚。李鴻章從小就天資過人,志向高遠,內心也極為敏銳。他先後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了紮實的學問基礎。與此同時,少年的鄉野生活也給李鴻章的成長積累了非常好的草根經驗,積蓄了李鴻章出人頭地的願望,也使李鴻章在本質上成了一個實際而不迂腐的書生。這種草根經驗為李鴻章後來在亂世之中崛起提供了寶貴的財富。李鴻章成年之後,身材頎長,一表人才,極具方巾之氣,擁有宏大的抱負和志向。這可以從李鴻章二十歲時所寫的一首詩中看出:
頻年伏櫪困紅塵,悔煞駒光二十春;馬足出群休戀棧,燕辭故壘更圖新。
世路恩仇收短劍,人情冷暖驗籠紗;倘無駟馬高車日,誓不重回故里車。
李鴻章和淮軍初到上海之時,由於這群來自鄉下的兵勇衣裳襤褸,自由散漫,粗話連篇,當地的士紳很是頹唐失望。李鴻章卻胸有成竹,他知道這支隊伍的戰鬥力,對這支隊伍充滿信心。淮軍抵達上海之後,李鴻章一方面整肅軍隊,去除軍隊的散漫習氣;另一方面,由於在上海見識了洋人軍紀和武器的厲害,李鴻章很想借鑒和學習洋人軍隊的一些做法。為瞭解洋人軍隊的情況,李鴻章甚至化裝溜上了洋人的軍艦。這一看真是讓李鴻章感到震驚,李鴻章頓時明白泱泱華夏之所以敗給西洋小國的原因了,那是因為洋人部隊紀律嚴明,訓練有序,整體化和科技化程度高。這一次見識讓李鴻章感受頗多,他暗下決心,要學習西洋人軍隊的戰爭方式,和-圖-書購買洋人的武器來對付太平天國。李鴻章說學就學,他立即動手聘請了洋人擔任自己部隊的教官,並通過大哥李瀚章,向洋人火速購買了三千桿洋槍,充實自己的淮軍。
詩酒未除名士習,公卿須稱少年時;碧雞金馬尋常事,總要生來福命宜。
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李鴻章的這十首《入都》詩中,還隱藏著強烈的宿命意味。這一組詩有著濃郁的預見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有著偈語的意味。有很多今後的宿命,李鴻章似乎都覺察到了,也寫到了。其中的一些詩句,出人意料地與李鴻章的人生軌跡相吻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首:「回頭往事竟成塵,我是東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夢,青山淪落十年人。」這樣的詩,哪像是一個二十一歲青年所寫的呢?分明像臨終之人的絕筆。正因如此,這組詩更有幽秘色彩,散發著凜凜的極地之光。
回頭往事竟成塵,我是東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夢,青山淪落十年人。
李鴻章和他龐大的家族從這一塊土地上獲取的東西太多了,也正是由於這樣的透支太多,似乎自李家發跡的那一天起,這塊土地就耗盡了它的所有,變得窮困而麻木了。當年有著「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說法,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那麼,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鴻章的老家了。也許,對於這塊土地,李鴻章的確負債纍纍。不只是過去,還包括現在和將來。
李鴻章蘇州殺降事件在當時引起了很大風波。人們紛紛議論李鴻章心狠手辣,將他與歷史上的白起和項羽相比。洋槍隊「常勝軍」統領戈登也非常不滿,認為此事污辱了自己的名聲,提著手槍到處尋找李鴻章,要殺李鴻章洩憤。李鴻章一度非常尷尬,他在給母親的書信當中說:這件事情雖太不仁義,但因為攸關大局,確實是不得已而為之。曾國藩接到李鴻章的報告後,雖然在內心當中也認為李鴻章心狠手辣,但還是寫了一封信,對李鴻章安撫了一番。好在朝廷很快降旨,宣稱李鴻章所做的不僅無不妥,而且還做得很好,這才把事件平息。
因為是暑假時間,於灣小學的大門已鎖上了。我們找到了保管鑰匙的人家,一個風燭殘年的老婦人見我們想看李家祠堂的遺址,便帶著她的兒子為我們開門。一進大門,便見到操場的右邊有兩株茁壯的樹。據介紹,它們正是當年李家祠堂門口的眾多樹中的兩株。在學校的後院,我們還見到了一株老樹,這株老樹葉子翠綠,樹幹粗壯挺拔,非常漂亮。這種樹叫望春樹,來自日本,一般都是種在神社當中的。據說,這株樹是李鴻章七十歲那一年,夫人趙小蓮死後,時任清國駐日大使的李經方回故里守孝,當時的日本首相伊籐博文特意送李氏父子四株名貴的望春樹,以示哀悼。這四株名貴的望春樹,兩株種在大興集的趙小蓮墓地,兩株種在李家大祠堂中。李家大祠堂中的兩株望春樹,後來死了一株,現在只剩一株了。由於時間久遠,這株倖存的望春樹,樹幹的一部分已經朽爛,只好用水泥糊上。在離望春樹不遠,還有兩株異常茂盛的臘梅樹,樹葉密不透風,綠得發亮,像長瘋了似的。這兩株樹都有一百多年了,這麼長時間的臘梅樹,居然如此蔥蘢,這著實是一件奇妙之事。據介紹,李鴻章母親逝世後,李鴻章陪伴著靈柩回歸到故里,在將母親安葬在於灣附近之後,李鴻章曾經在這裡守孝三個月,有一段時間,就住在李家祠堂。那段時間,李鴻章無事時就來到這兩株臘梅前,靜靜地凝視著這兩株樹,若有所思。大約,李鴻章是想起一八六〇年去世的侍妾冬梅了吧。一八六〇年左右,正是李鴻章生命中最嚴峻的時刻,在不長的時間裡,李鴻章接連失去了自己的侍妾和夫人周氏。國運不明,前途不順,自己又屢失親人,那段時間,李鴻章進入了他的人生低谷,心情灰涼無比。現在,這兩株臘梅仍鬱鬱蔥蔥,每到冬天,樹上總結滿梅花,香氣撲鼻。與人相比,樹的生命力似乎更強,人已乘鶴西去,地方物是人非,但樹卻如此的茂盛蔥蘢,這個地方的精靈之氣,大約躲藏在樹中了吧。
袖攜淮海新詩卷,歸訪煙波舊釣徒。
一八六四年,曾國藩的湘軍攻下天京,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失敗。朝廷封李鴻章一等肅毅伯,賞戴雙眼花翎。這一年,李鴻章四十一歲,開始步入他人生的高峰期。此後,李鴻章一直青雲直上,幾乎每隔一兩年,他都能加官晉爵——一八六五年,李鴻章被任命為兩江總督;一年之後,他又接替曾國藩任欽差大臣,督辦剿捻事務;一八六七年,剿捻即將結束,李鴻章被任命為湖廣總督;一八六八年,李鴻章加太子太保銜,並升授協辦大學士,入京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見,允其在紫禁城騎馬,以示恩寵;一八七〇年,李鴻章接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八七三年,李鴻章被授武英殿大學士;一八七四年,李鴻章被改授文華殿大學士。清廷不設丞相,以文華殿大學士為首輔。在榮升文華殿大學士後,李鴻章曾得意地自撰楹聯「已無朝士稱前輩,尚有慈親喚小名」。在當時朝中要臣中,李鴻章算是最為年輕的了。維新變法失敗後,慈禧對「四朝元老」李鴻章特加恩遇,賞賜他「方龍補服」,即其穿著的官服允許有龍的圖案,如此殊榮,何等顯赫!當年李鴻章十首《入都》詩當中和-圖-書有一首:「世路恩仇收短劍,人情冷暖驗籠紗;倘無駟馬高車日,誓不重回故里車。」到了四十歲這一年,李鴻章少年時的志向完全實現了,他完全可以放心裘馬錦衣,榮歸故里了。
一八六二年,李鴻章四十虛歲,在這一年中,李鴻章終於揚起了他人生的風帆,真正地起航了。
李鴻章的祖先們一直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即使到了第六代也即李鴻章祖父李殿華時,家境依然窮困。到了年終,上門討債的人如過江之鯽。從第七代李文安開始,李家開始發跡,三代中竟有四人考取了進士,還有很多人考上了舉人、拔貢、秀才……據說,這是因從李文安開始,李家搬到了熊磚井邊,天天喝著這口井裡的水,沾染了井的神奇。現在,這口井仍然在用,從井口往下看,井中的水似乎很深,也很清。但大理石的井欄已殘敗不堪了,這麼多年村民們一直扯著繩子從裡面汲水,井欄上已明顯鐫出了幾十道深深的痕印,而且明顯地缺了一塊,遠遠看去,就像一件破敗的玉器。據說,李鴻章發跡後,有一位廬州知府為了沾上李家的「官氣」,偷偷地鑿下了井欄上的一塊石頭,回去雕刻成官印。現在,井的周圍,居住著的都是與當年的李家毫不相干的農民,年輕人平時在城裡打工,村裡的婦孺老少,則仍在這裡種田,養著雞鴨魚豚,說著同樣口音的合肥話。不遠處,有一片樹林。據說,當年李鴻章的祖父李殿華就葬在熊磚井以北的那片樹林裡。但現在,當年的墳墓已蹤跡全無了。
在村落正中,我們看到了那口非常著名的古井。這口井在明清時的《合肥縣志》以及後來的李氏家族的碑刻文獻中,都有明確的記載。有許多文章在寫到李家時,都提及這口井給李家帶來的好運。這口井始於明朝,是一個姓熊的官員組織挖鑿的,所以一直稱為熊磚井。據說,正是這口井給李家帶來了鴻運——從李鴻章的家世來看,先世本姓許,祖居地在現在鄱陽湖湖口一帶,而後才遷居合肥東鄉的。到了李鴻章八世祖許迎溪這一代,許迎溪與同莊李心莊既是姻親,又是好友。李心莊無子,便請求收養許迎溪的次子慎所為嗣。由此,許慎所便改姓李了。直到現在,當地民俗仍有「許李不通婚」的規矩,那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一家人。
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即此可求文字益,胡為抑鬱老吾身!
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是李家發跡過程中一個關鍵性的人物。李家到了李鴻章誕生那一年,在當地,已是富庶人家了。李文安在中年之後中舉,這在當地來說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了。李文安共有六子,分別為瀚章、鴻章、鶴章、蘊章、鳳章、昭慶。這個舊式的知識分子雖然資質平平,但卻有著相當好的大局觀,而且在教育子女上有著獨到之處。長子李瀚章一直跟隨曾國藩,李鴻章發跡之後,李瀚章也曾官至兩廣總督;李鳳章棄官從商後,生意做得非常之大,在全國各地,有無數地產和財產;至於鶴章和昭慶,後來的人生道路也是一個從商,一個從官,也算是好的結果。李文安雖然沒有等到這一天,但他在地下有知,對這一切,也該是釋懷於胸了吧。
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八千里外覓封侯。
一八六二年李鴻章的「殺降事件」曾經引起軒然大|波。這一年,李鴻章在與太平軍的交戰中節節勝利,到了年底,李鴻章率淮軍發起收復甦州、常州戰役,與太平軍經過反覆激戰後,淮軍攻克常熟、太倉、昆山等地。在初步掃清蘇州外圍的障礙後,李鴻章制訂了三路進軍的計劃,中路程學啟統率,由昆山直逼蘇州;北路李鶴章、劉銘傳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南路則下攻吳江、平望,切斷浙江太平軍增援的道路。一八六三年七月,程學啟部兵臨蘇州城下,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從天京趕來救援,與北路淮軍大戰於無錫大橋角,太平軍失利。這個時候,蘇州太平軍守將納王郜永寬等發生動搖,與程學啟部秘密接洽,準備投降。程學啟將此情況報告給李鴻章,李鴻章承諾對郜永寬等加官封爵,不解散他們的部隊,整體劃歸淮軍。李鴻章為了消除郜永寬等「八大王」的疑慮,還讓洋槍隊統領戈登出面,對承諾作了保證。不久,郜永寬等殺死守城主將慕王譚紹光,開城投降。淮軍入城後,太平軍八降王仍心存疑慮,率部屯居半城,要求李鴻章兌現承諾,不願剃髮解除武裝,索要官銜及編制。李鴻章當機立斷,採納程學啟的建議,先下手為強,誘殺了八降將。
不久,李鴻章乾脆攜帶家眷出逃,離開了安徽,來到了江西,投奔大哥李瀚章。曾國藩得知李鴻章的去向後,連寫幾封信給李瀚章,讓李鴻章來湘軍大營。在這樣的情況下,李鴻章來到了曾國藩身邊。可以說,這是李鴻章在萬般無奈中走出了最為幸運的一步。這樣的行為是他走上人生顯赫道路的開始。李鴻章在曾國藩身前左右觀察和感悟到的,可以說,恰如其分地採了這位大儒的「氣」彌補了自己的軟肋。李鴻章的性格和氣質得到了根本性的昇華,為日後成就一番事業,奠定了基礎。
這是夏天,烈日灼人。滿目望去,陽光下一片蔥蘢。風熱烘烘,知了在高高的楊樹幹上不停地鳴叫,空氣中一直瀰漫著泥土的腥味和牛糞的臊味。
黃河泰岱勢連天,俯看中流一點煙;此地盡能開眼界,遠行不為好山川。
這個生長在祠堂郢村的合
hetubook.com.com肥東鄉人自小便有著很強烈的功名抱負。等到李鴻章二十四歲的那一年,他考中了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這也是安徽當時最年輕的翰林。李鴻章在翰林院當了一段時間編修之後,對於那種機械八股無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厭倦極了,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正在此時,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朝廷的「國家軍隊」綠營兵腐朽日甚,不堪一擊。朝廷無奈只好借助於民間的力量來「平亂」。曾國藩被派回湖南後不久,辦團練、組建湘軍,在阻擊太平天國的戰鬥中屢建奇功。朝廷見這條路的勢頭不錯,於是又派了一些京官回鄉「練勇」,李鴻章與他的父親李文安也被先後派回安徽,組織民團與太平天國打仗。正因為這種地域文化的影響,在李鴻章身上,集中體現了很多江淮之間人的特點。具體說來,那就是在為人處世上,李鴻章既有中原人行為大氣、敢作敢為、有機智有心計、懂勾心鬥角的一面;同時也有南方人比較務實、精明能幹的特點。從總體上來說,李鴻章仁慈、開朗、詼諧、喜權力、愛面子、重義氣、狡猾、精明、不迂腐,在為人處世上比較平民化,幽默、和藹、直接,有時候帶有很濃的痞氣。
有了舞台之後,李鴻章的才幹充分顯露出來。初步站穩腳跟後,李鴻章從「察吏、整軍、籌餉、輯夷」各事入手,積極招攬人才,鞏固自己的地位,李鴻章起用了郭嵩燾、丁日昌等一批務實肯幹的洋務派官員,建立了以務實幹練、通曉洋務為基準的淮軍幕府。在軍事上,李鴻章正式確立向西方軍隊學習的目標,在淮軍中大規模裝備洋槍洋炮,僱請外國教練指導訓練,將西洋陣法、號角、口令引入淮軍。一開始,那些土裡土氣、缺乏文化的農民兵並不懂得如何使用洋槍洋炮,李鴻章就讓外國教官手把手地輔導。有一次,還發生了在演練中走火引爆彈藥炸死二十多人的事故。但李鴻章對於學習和改變堅定不移,他說,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價,等練到射擊百發百中時,便會無堅不摧。
沒有想到的是,這個離市區並不遠的地方竟是如此破敗荒涼。從合肥市中心向東,小車一直在坑坑窪窪的路上行駛,公路的兩邊,都是破舊的屋舍。雖然這一帶離市區只有十幾公里,但恍惚間,彷彿相差好幾個世紀。我們來之前,剛剛下了一場雨,村級公路更顯泥濘不堪。車子在這樣的地方行駛,我們的心情一下變得沉重起來。
定將捷足隨途驥,那有閒情逐水鷗!笑指瀘溝橋畔月,幾人從此到瀛洲?
一個人的成功總會引起一連串的忌妒。現在,該輪到官運亨通的李鴻章了,一些讒言開始流傳,更有人悄悄打報告給上司,說李鴻章的那些功勞都是偷天陷阱。更讓人惱怒的是,來安徽的滿族欽差大臣勝保也參了李鴻章一本,說李鴻章貪生怕死,兵敗後混雜在土匪中潰逃。類似的小報告因為明顯缺乏證據,很快就不了了之。安徽巡撫福濟卻乘機奪走了李鴻章的兵權。不久,廬州城再次被太平軍佔領。一八五七年底,陳玉成率太平軍在合肥東鄉三河鎮,殲滅湘軍李續賓部六千餘人,李續賓戰死,隨軍的曾國華失蹤。李鴻章賦閒在鄉,都未得參與。在此期間寫了《明光村鎮旅店題壁》,抒發胸中的怨氣:
我是無家失群雁,誰能有屋穩棲烏。
六年宦海持清節,千里家書促遠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間烏鳥慰私情。
可以說,從一個鄉下的布衣青年,最後成為朝廷的重臣,李鴻章完全是靠江淮之間這塊地方發家的,李鴻章也深知這一點。在發達之後,李鴻章一直捨不得這個地方,李氏家族不僅在合肥一帶大量購田置產,連死後,也要將屍骨埋葬在這裡。李鴻章的母親,也即李文安的夫人在北京去世之後,也專門將靈柩從北京經過大運河輾轉運回,與李文安合葬在於灣村。在這一帶安葬的,除了李鴻章外,還有李鴻章的兄弟李瀚章、李鶴章等。
巢湖看盡又洪湖,樂土東南此一隅。
故人共贈王祥劍,荊女同持陸賈裝;自愧長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聞雞不覺身先舞,對鏡方知頰有髭。
遍地槁苗待霖雨,閒雲欲去又踟躇。
兩字功名添熱血,半生知己有殊恩;壯懷棖觸聞雞夜,記取秋風拭淚痕。
即今館閣需才日,是我文章報國年;覽鏡蒼蒼猶未改,不應身世久迍邅。
李鴻章的回鄉之路並不平坦。當李鴻章回到廬州時,這片土地已是滿目瘡痍,昔日的詩情畫意早已消失殆盡,有的,只是戰爭的殘酷和硝煙:廬州失守,安徽巡撫被殺,李鴻章的家鄉磨店也被太平軍佔領。李鴻章一到廬州,即忙著招兵買馬,籌備與太平軍的戰鬥。有點出乎意料的是,李鴻章的開局相當好,他很快組織了一支千餘人的民團隊伍,並且在巢湖一帶首戰告捷,這一次勝利據說還是清軍在皖的首場勝仗。為此,李鴻章受到了朝廷的藍翎賞賜,官位從七品升至六品。第二年,吏部左侍郎王茂蔭保奏李文安回鄉「勸勉鄉人,團練自衛」,李鴻章的弟弟李鶴章也從家鄉來輔佐父親。在此之後,李鴻章先後隨周天爵、李嘉端、呂賢基、福濟等清廷大員在皖中與太平軍、捻軍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