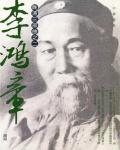第三章 曾門弟子
曾國藩與李鴻章在處理洋務時的不同方法,與他們的學養和性格有關。當然,如果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來說,在曾國藩和李鴻章身上,還體現著中國文化所隱藏著的很多內在特質。中國文化不是完全的儒文化,它實際上是儒釋道的一體化,「溫良恭儉讓」只是表面的價值觀,在暗地裡,陰謀與心計無孔不入;當功名利祿受挫之後,往往又會潔身自好,甚至產生空的感受,偏向於出世——這就是道家和佛家的教義了。
在當時,就淮軍的裝備和實力而言,攻堅能力已遠勝湘軍。李鴻章哪裡不想爭這個頭功呢?但在這種情形之下,李鴻章權衡再三,還是選擇了迴避,想把頭功讓給恩師。在朝廷下旨令淮軍會攻金陵後,李鴻章致函曾國藩,稱自己的隊伍疲勞,想休整一段時間。實際上,李鴻章是想給曾國荃預留充足的時間。朝廷見淮軍遲遲未動,連降諭旨,敦促李鴻章火速調兵。李鴻章只好採取拖延戰術,他先是借口生病回蘇州,不久又提出部隊要休整兩個月才能再戰,最後李鴻章實在拖不過去了,便靈機一動,出兵浙江,謊稱要從湖州對南京形成包圍。誰料此舉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宗棠急忙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由此開始,左、李兩人成了一輩子冤家。李鴻章一拖再拖,實在是用心良苦,後來,連淮軍將領都看不過去了,紛紛表達對李鴻章的不滿。李鴻章只好再次給曾國荃寫信,催促湘軍加快攻城動作。到了夏天,朝廷又降諭旨,嚴令李鴻章派劉銘傳等先鋒火速馳往金陵。李鴻章無奈,只好派劉銘傳、王永勝、劉士奇各率一萬五千人前往,自己大隊人馬仍按兵不動。此時,曾國荃接到李鴻章調兵前來的消息後,幾近瘋狂,他將李鴻章告知的信件遍示諸將,說:「他人將要來了,難道我們苦苦攻了兩年的艱辛將要拱手相讓嗎?」手下的將領堅決表示:「願盡死力。」當晚,通向金陵城內的地道已經完畢,次日,曾國荃部由地道炸塌太平門城垣二十餘丈,攻下金陵。
六年宦海持清節,千里家書促遠行;
一個人的命運總是因一些人或者一些事而改變。人與事,在冥冥之中,都可以互相充當背景的。李鴻章也不例外。就事物來說,太平天國運動、甲午戰爭、庚子戰爭以及晚清諸多事件都可以充當他的人生背景;就人而言,有一個人可以成為他一生的背景,在他命運的航行中充當風帆的作用。這個人是一個湖南人,他的名字叫曾國藩。
儘管李鴻章這種極其實用的處世方式給他帶來成功,也帶來功名,但縱觀李鴻章一生,他同樣因為這種方式使自己的人生重重地打了折扣。就李鴻章的一生而言,可以說一直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如果說我們還可以從曾國藩迂腐和執著的處世原則上看出曾國藩的人格來,那麼,從李鴻章的聰明和實用上,我們就很難看出李鴻章真實的思想,以及真正的追求。與曾國藩相比,李鴻章在整體意義上缺乏真正的人文思想和宗教情懷,並且他也絕不如曾國藩那樣執著,也不如曾國藩那樣真實。在我們的感覺中,這個高個子的合肥人講著一口合肥話,出入各種場所,說著一些不痛不癢的話,王顧左右而言他,或者說一些自鳴得意的俏皮話。有時,這些行為因為缺乏底氣、缺乏視野、缺乏原則,使人起雞皮疙瘩。我們所見到的,一直是那個冷靜平穩、不苟言笑、城府極深的李鴻章;或者是,一個故作幽默、自以為是的李鴻章。至於真實的李鴻章,卻一直煙籠霧繞,更談不上他真實的內心世界浮出水面了。
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二日,曾國藩中風卒於南京,消息傳來,李鴻章不勝哀痛,他感歎說:「吾師果以死穎!不可復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哉!……鴻章從游幾三十年,嘗謂在諸門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親切。」並親筆題寫了輓聯:「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這樣的輓聯,寄托了對恩師的綿綿哀思,也是對兩人終生之緣的一個總結。李鴻章以後對曾氏之子紀澤、紀鴻多方照拂,又協助長兄李瀚章編校《曾文正公全集》一百五十六卷,也許,李鴻章是想用這樣的方式,來補報曾氏一生的恩情。
也許,對於這個晚清最為顯赫的漢臣來說,李鴻章最大的悲劇是:不在於時局的多舛,也不在於個人命運的坎坷,而在於他作為一個個體,無法、也沒有意識去表達自己真正的內心。他無法使自己成為獨立的個體,無法「人之為人」,也無法面對自己。
李鴻章接信後,頗為感動。當周氏病稍有好轉,便收拾行裝趕到東流大營。李鴻章的重回幕府,讓曾國藩如虎添翼。積壓如山的公文得以清理,軍事大計也有人商議了。這一對師徒之間經常徹夜長談,無話不說。
很多年後,當李鴻章閒暇之時回憶起對抗太平軍的這一段歷史時,總是顯得神情凝重。除了慶幸命運對於自己的垂青之外,他還慶幸著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遭遇了曾國藩這樣一個亦師亦友的關鍵人物,這使得他在人生的幾次大轉折中總有貴人相助。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李鴻章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不僅僅體現在地位的增高、氣度沉穩等外部因素上,更多的,還是內心深處的悄然改變。從少年時意氣風發,聰明異常,一直到後來的洞察細微,隱忍無限,李鴻章的人生和性格,從那時起,經歷了一個巨大的U形彎。
曾國藩在經過周密的調查之後,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了,所謂的洋人教士殺嬰兒等事完全是子虛烏有。在談判之中,曾國藩首先自認錯誤,當即決定把天津道、天津府、天津縣的官員全部撤換。誰知洋人得寸進尺,他們進一步提出來,要把這些官員殺了償命。這樣的過分要求把曾國藩逼到了牆角,曾國藩一時變得非常被動。在曾國藩處理事務時,他的兒子曾紀澤看得就很清楚,曾紀澤就告誡父親,對於洋人,不能太講誠信,不能隨便承諾。李鴻章也三番五次給曾國藩寫信,給曾紀澤寫信,說曾國藩辦外交太老實,讓他提醒一下曾國藩。跟洋人打交道,李鴻章還是有經驗的,當年李鴻章在上海灘的時候,為了「常勝軍」的事情,沒少跟英國人鬥智鬥勇。洋槍隊當時的隊長白齊文毆打上海道台,李鴻章大怒之下,要拿白齊文正法,嚇得白齊文躲在英國軍隊中不敢出來。後來,李鴻章硬是不顧英國政府的反對,強行解散了「m.hetubook.com.com常勝軍」。對於洋人的本性,李鴻章要比曾國藩瞭解多得多。
有一種評價幾乎已成公認了,那就是說李鴻章之於曾國藩,就像管仲之於鮑叔牙,韓信之於蕭何。曾國藩與李鴻章都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梟雄。他們亦師亦友,相濡以沫。論學問人格,當時無出曾國藩其右者;論人情練達,處事敏銳,李鴻章又可算是首屈一指。曾國藩應該說是對李鴻章一輩子影響最大的一個人。曾國藩逝世時,李鴻章接受了替曾國藩撰寫碑文的任務,他在與友人的信中說:「謀國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牘私函,無一欺飾語……中流失柱,滔滔如何?……一朝仙去,不復歸來,為公為私,肝腸寸裂!兄本為擬文哭之,無如一字落墨,淚寄千行……」又從千里之外送來輓聯:「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這樣的評價,對曾國藩來說,是非常合適的;而對李鴻章來說,也是說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曾國藩與李鴻章在聯手鎮壓太平軍這段時間裡,他們並駕齊驅,屠殺了成千上萬的太平軍將士,染紅了自己的官袍。也正是在鎮壓太平軍的腥風血雨中,李鴻章變得成熟起來,由一個才高八斗的書生,成為一個封建王朝的所謂能臣。李鴻章後期性格中的忍辱負重、克己復禮,都可以說與這段戎馬倥傯的經歷有關。這段殘酷無比的歲月,讓李鴻章真正見識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曾求學於曾國藩、後來成為李鴻章幕僚的吳汝綸評價說,李氏「生平嚴事曾文正公,出治軍,持國事,於曾公相首尾。其忠謀英斷,能使國重,是非成敗,不毫髮動心,一秉曾氏學」(吳汝綸《李公神道碑銘》)。可見,李鴻章深得曾國藩的嫡傳,在李鴻章身上,還是能見到很多曾國藩的精神的。如果拿李鴻章與左宗棠相比,兩人雖同為經世、洋務一派,但李鴻章在為人上,卻與左宗棠大相逕庭。這就是「忍」、「挺」二字的絕妙所在。
桑於河上白雲橫,惟冀雙親旅舍平;
可以公認的一點是,李鴻章在曾國藩部任幕僚的那些年,應該是李鴻章受益和改變最多的幾年。李鴻章在曾國藩的大營裡那幾年,也是他冶煉自己性格的幾年。對李鴻章來說,曾國藩是過來人,過來人當然清楚曾經的張揚、傲氣、才情和弱點。在曾國藩看來,安徽的團練辦得一團糟,李鴻章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能帶到湘軍中來,必須先在他的身邊學習一段時間再說。出於這樣的考慮,曾國藩沒有讓李鴻章獨當一面,而是讓李鴻章一直跟隨他的左右。對於李鴻章,曾國藩深知他年輕氣盛,急功近利,常常給他潑點冷水。曾國藩常常告誡李鴻章,高官厚祿乃是天命所定,並非人力所能強求。曾國藩還想用日常生活的一些準則來約束李鴻章的言行。曾國藩每天黎明即起,招呼全體幕僚一起吃早飯,邊吃飯邊議論形勢,把一天的工作部署掉,這是他多年的習慣了。李鴻章的習慣正好相反,他是一個典型的夜貓子,每到晚上,便生龍活虎;早晨則睡懶覺不起床。每一次早會李鴻章總是懵懵懂懂,甚至經常找理由不參加這樣的會議。
在李鴻章的《入都》組詩中,有一首詩,用來闡述後來與曾國藩的情誼與緣分倒頗貼切:
一八六四年,淮軍力克常州,蘇南戰局基本平定。這時,曾氏兄弟正順江而下形成對天京的包圍。對於曾氏兄弟而言,他們特別忌諱兵強馬壯的淮軍助攻天京,如果那樣,曾氏十數年苦戰的果實將被別人摘得,這是曾氏兄弟極不願看到的。尤其是曾國荃,自尊心特別強,對於淮軍的節節勝利,倔強的他幾近憂鬱成疾。曾國藩當然心疼弟弟,多次寫信給曾國荃,勸慰他要寬心,如果李鴻章要來合攻天京的話,千萬不要多心,「獨克固佳,會克亦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總以保全身體,莫生肝病為要」。
有一天,李鴻章誑稱頭疼,不想參加早會,可曾國藩不依不饒,一次次派人來叫,說是「人不到齊不開飯」。李鴻章見老師真的生氣了,慌忙披上衣服一路踉蹌跑過去。坐下之後,曾國藩鐵青著臉一句話都沒說,直到吃完後,才衝著李鴻章扔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耳!」說完拔腿就走,李鴻章呆呆地站立在那兒,尷尬了好一陣子。
李鴻章在當幕僚期間還幫曾國藩作出一個重要的決斷——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攻入圓明園,咸豐倉皇逃亡。在此期間,咸豐降旨,要曾國藩速派鮑超部霆軍保衛京師。接到旨意後,曾國藩和胡林翼感到進退兩難,派鮑超去吧,這邊與太平軍力量均衡的格局將被打破,太平軍極可能乘虛進攻。不派部隊去吧,又會背一個「抗旨」的罪名。曾國藩趕忙召集幕僚商議。多數幕僚主張「入衛」;李鴻章力排他議,分析形勢說:洋人入京,只不過是為了金帛議和,並不想推翻大清統治,不會有其他事情。不如按兵請旨,靜觀一段時間再說;對於湘軍來說,與太平軍的決戰才是有關天下安危的大事,所以對待調兵之事,一定要慎重。曾國藩和胡林翼採納了李鴻章的意見,一面按兵不動,一面拖時間,派人送信給朝廷,堂皇地建議: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進京,這一招,明顯的是給朝廷出難題,因為朝廷最忌諱手握重兵的「節度使」進京。朝廷當然不同意。這樣的拖延戰術,贏得了時間。很快,曾國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與八國聯軍已議和,鮑超軍不用北上。
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間烏鳥慰私情。
師徒之間的衝突讓曾國藩的心情壞到了極點。曾國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日內因徽州之敗,深惡次青,而又見同人多不明大義,不達事理,抑鬱不平,遂不能作一事。」在曾氏原先的手稿中,在「而」與「又見」之間,圈掉了「少荃」二字,可見其原文是寫「少荃不明大義,不達事理」的。這一場風波使得師徒間變得生疏尷尬了。到了年底,李鴻章找了個理由要去看望在江西南昌的老母,離開了湘軍大營,回到了南昌的哥哥李瀚章處。
對於「天津教案」處理手段的不一樣,也充分體現了李鴻章與曾國藩在諸多方面的不同。也正是「天津教案
m.hetubook•com.com」的處理結果,導致了李鴻章取代曾國藩成為清廷「第一漢臣」。
到底李鴻章的真實思想是什麼呢?也許,所有關於他的判斷都顯得有點武斷,顯得有點臆度。在絕大多數時間裡,李鴻章總顯得雲裡霧裡,該謙卑的時候謙卑,該倨傲的時候倨傲,該出手的時候出手,該隱藏的時候隱藏。他的一手「迷蹤拳」似乎打得太好了,不僅別人看不出他要幹什麼,甚至,有時候連他自己也有點迷糊了,情不自禁地沉耽於自己的幻象之中。聰明人本身就難得偏執和執著的,對於李鴻章來說同樣也是如此。李鴻章就是這樣一邊打著「迷蹤拳」,一邊從事著自己的改良事業。當然,這樣的行為本身,並不算是高妙的舉動,李鴻章的所作所為決定了他只是一個二流的政客,而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像一個演員,而不是一個成功的導演。偉大的政治家總是有著自己明晰的思想體系以及自己強硬的態度,並且有著一種為著思想和主義獻身的情懷。李鴻章似乎不是這樣。在他一輩子當中,李鴻章總是有意無意地給自己量身定做了一襲華美的錦袍,在大多數時間裡,李鴻章就像一個變色龍一樣,披著各式華美的錦袍拋頭露面,而他的身體,一直隱藏在這襲華美的衣服裡面。
閣下久不來營,頗不可解。以公事論,業與淮揚水師各營官有堂屬之名,豈能無故棄去,起滅不測?以私情論,去冬出幕時,並無不來之約。今春祁門危難,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間東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熱毒,內外交病,諸事廢擱,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台旆速來相助為理。
與曾國藩相比,李鴻章明顯地更適應晚清那個亂世。他既有士大夫的高貴,也帶有草根的刁滑,那是一種弱者的智慧,務勞務實,精明狡詐。李鴻章借此以應付亂世,要比曾國藩那種一成不變的正統有效得多。李鴻章是從底層上來的一個農村小知識分子,這樣的草根經驗,使得他對於一些非正常的手腕和方式非常熟悉,在實踐中也能親身感受到這種方法所帶來的好處。從李鴻章與淮軍的關係中就可以看出,李鴻章才不像曾國藩那樣無限忠誠地主動解散淮軍呢,他一直把淮軍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讓這支部隊有著極強的私人性和專屬性。淮軍一直忠於李鴻章,雖經中法、中日戰爭,一再受創。一直到一九〇〇年庚子事變,聶士成壯烈戰死,淮軍徹底覆滅,李鴻章算是輸得精光。一個人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擁有一支強大的部隊,這一點,足見李鴻章功力之深。不僅如此,李鴻章還自覺不自覺地在政治、外交以及很多方面運用這種手段,這種手段讓李鴻章屢試不爽。
但李鴻章的才幹得到了包括曾國藩在內的湘軍將領的一致公認。在為曾國藩當謀士並掌管文案的那段時間裡,無論是奏稿還是批示,李鴻章都寫得條理清晰,嚴絲合縫,讓曾國藩省了不少心。不僅如此,李鴻章還彌補了曾國藩的很多不足——曾氏生性「懦緩」,沉穩厚重,而李的作風則明快果斷,反應快捷,每有大計,往往得李在旁數言而決。李鴻章在此期間為曾國藩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國藩幾次戰敗後,給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給自己請罪,說自己「屢戰屢敗」。寫完之後,交給李鴻章看,李鴻章改「屢戰屢敗」為「屢敗屢戰」,結果,朝廷不僅沒有怪罪曾國藩,而且還大大地表彰了曾國藩一番。曾國藩曾經考慮將湘軍轉移到四川,以避開太平軍鋒芒。李鴻章就不贊成,李鴻章在分析形勢之後,主張曾國藩堅守長江一帶,決不退卻,耗去太平軍銳氣之後,給予打擊。從後來的情況看,李鴻章的這些謀略都堪稱正確。曾國藩感歎李鴻章有過人之處:「將來建樹非凡,或青出於藍,亦未可知。」在湘軍大營,曾國藩有彭玉麟的忠貞,有楊載福的樸直,有鮑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劃,有曾國荃的頑強,但像這樣洞察全局,並且有著清醒和機巧應變手腕的人才,李鴻章可謂是首屈一指。
回首昔曾勤課讀,負心今尚未成名。
氣味相投的人必定是惺惺相惜的。曾國藩與李鴻章即是如此。在北京,當曾國藩第一眼見到李鴻章時,慣於察人的曾國藩見李鴻章身材修長、五官俊美,言談儒雅、舉止倜儻,更兼有一般人不具備的乖覺和過目不忘的記憶力,心中很是喜歡。在讀到李鴻章遞上來的詩文後,曾國藩更是「大愛之」,料定李鴻章今後必定是一個經天緯地之才。自此之後,李鴻章就經常來曾國藩所居的報國寺走動了。一八四五年,李鴻章參加乙未恩科會試,恰巧是曾國藩出任本科會試的考官之一。雖然李鴻章此次會試落第未果,但其詩文和才學卻博得了曾國藩的青睞。曾國藩後來曾對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說:「你的弟弟少荃,乙未那一年,我就知道其才可以大用了。」隨後,李鴻章在初次會試落榜後的「乙丙之際」(即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國藩門下。在此後的日子裡,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史百家雜鈔》。李鴻章在這一時期受曾國藩的影響,一在於詩文詞章,兼及治學方法;二是講求經世義理之學。兩年後,李鴻章如願以償考中了進士,位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試後授翰林院庶吉士。捷報傳來,曾國藩非常高興,他將李鴻章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帥遠鐸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是科的主考官為潘世恩,副主考為杜受田、朱鳳標、福濟,房師(相當於今天的班主任)為孫鏘鳴。潘世恩出身徽商,是蘇南世家,也算是李鴻章的老鄉。這些鄉情師徒關係,對於李鴻章日後勢力的增強,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李鴻章到達天津後,還真將「痞子腔」派上了用場。與曾國藩的「以誠相待」不一樣,李鴻章的「痞子腔」就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就是「說話不算話」,就是偷梁換柱、暗渡陳倉。這是典型的弱國外交手段,正面交戰不敵,只好虛與委蛇,以謊言對謊言,以欺騙對欺騙,以喬裝好客對虛偽的友誼。當然,這樣的手段對於李鴻章來說,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洋人勢力太強大了,李鴻章沒有其他辦法,只好「搗糨糊」,能「蒙」則「蒙」,能「糊」則「糊」,在不明時局hetubook.com.com的情形下,只好以「打太極拳」應付。李鴻章畢竟是草根出生,這一套對他來說並不陌生,李鴻章一方面與洋人討價還價,另一方面,暗地裡與俄國進行了溝通,因俄國只要求經濟賠償,並不要求人抵命,李鴻章便趁機在原先的判決上進行改動,將原來二十名死刑改為十六名死刑、四名緩刑。雖然改變並不大,但畢竟多保了幾個中國人的性命,算是有效緩解了尖銳的矛盾,也緩和了朝廷的面子。不僅如此,李鴻章還讓丁日昌從監獄裡找來十六個死刑犯,頂替了這十六個,矇混過關,斬殺了事。將流犯的官員,一段時間風波平息之後,又招回原地。李鴻章的「痞子腔」贏得了國人的叫好,「天津教案」所引起的風波,終於在李鴻章手上平息下來。而處理「天津教案」一事欠妥,對曾國藩的影響是巨大的,曾國藩傷心地說自己是「內疚神明,外慚清議」,變得心情抑鬱、衰頹日甚,終於在一年後鬱鬱而終。
曾國藩是一個讀書人,他身上攜帶的寬厚、智慧、誠實的人格特徵,是「仁」的集中體現,曾國藩可以說是中國精英文化的一個集大成者,一個謙謙君子。在他身上,充分體現了儒家的王道,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的孜孜追求。於儒學來說,曾國藩是幾近完美的——於家庭,於同僚,於君主,在立德、立行、立言上,曾國藩都臻於極致。於家庭,曾國藩出身寒門,即使後來官位顯赫,但他一直簡樸務實,保留了耕讀之家的本色。曾國藩一生身體力行,嚴以律己。在對子女和親屬的教育上,曾國藩雖然戎馬倥傯,西征北討,但他一直不放鬆對子女的教育,堅持言傳身教。優良的家風,良好的教育,使得曾氏一門人才輩出:其長子紀澤精通詩文書畫,是晚清出色的外交官;其次子紀鴻喜愛自然科學,在數學研究上造詣較深,可惜英年早逝;其孫輩曾寶蓀、曾約農後來都成為著名的教育家和學者。
於君主,曾國藩一直很忠誠。曾國藩從京城回湖南組織湘軍,正是為了響應《論語》中的一句話:禮失而求諸野。曾國藩含辛茹苦十數載,出生入死,終於完成了替朝廷分憂的初衷。鎮壓太平天國之後,曾國藩手握重兵,權力巨大。但曾國藩一直很清醒,他深知「功高蓋主」的隱患,主動急流勇退,不僅解散了湘軍,而且多次陳明心跡,傾心於老莊。曾國藩正是以他過人的智慧和洞察力,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自己的名節。
李鴻章用軟磨硬抗的辦法,拖延會攻金陵長達數月之久,算是成全了曾氏兄弟獨得「首功」的心願。這樣的「義舉」,真難為心高氣傲的李鴻章了。對此,曾國藩極為感激,攻克南京城不久,李鴻章趕到,曾國藩親至城外下關迎接,拉著李鴻章的手連聲說:「我兄弟倆的一點面子,全是你給的。」曾、李之間在軍政大計上的互諒互助,也是湘淮兩系能夠長期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曾國藩的確算是中國傳統文化冶煉出的典型人物。無論從哪方面說,曾國藩都可謂是晚清第一人。曾國藩巨大的內心力量支撐著他的人格和境界,在這種浩然之氣的支撐下,曾國藩對於人生有大徹大悟的看法: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萬事萬物不勉強為之,但自己又必須在人生中盡最大的努力。在曾國藩的晚年,雖然他目睹了太多的醜惡,也被迫做過許多妥協來獲取來之不易的勝利,但曾國藩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即不道德的社會歸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來糾正,樹立正確的道德準則和態度必須成為首要的目標,經世致用之術不管多麼重要,必須處於從屬地位。曾國藩是用心良苦的,也是值得讚頌的,但曾國藩的完美舊人格在清末的亂世中,不免「虎落平川」了。誠實變成了迂腐,信用招致欺凌,一切都是陰差陽錯。以曾國藩的知識結構,當他面對歐洲寬廣、陌生、富有侵略性的強勢文化時,便有點力不從心了。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亂世之中,曾國藩顯得「緩慢呆板」,一點也不如李鴻章「如魚得水」。
曾國藩奉命回鄉組織民團抗擊太平軍,曾國藩和李鴻章算是暫別了數年。曾、李二人,此時雖然天各一方,但曾國藩一直忘不了關照這位愛徒。李鴻章隨呂賢基剛到安徽,曾氏就致信其兄李瀚章,詢問李鴻章的情況。不久,曾國藩幾次致函呂賢基以及安徽巡撫江忠源,推薦李鴻章的才幹,並讓他們多多關照李鴻章。曾國藩還給李鴻章寫過一封很重要的親筆信,傳授自己帶兵的心得,提出兵家注意的大忌就是「敗不相救」。咸豐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太平軍再克廬州,李鴻章無處容身,於是攜家眷輾轉流離,打了幾場浪仗之後,南下江西南昌,投奔為湘軍辦理糧草的胞兄李瀚章。廬州失守的當天,李鴻章還給恩師曾國藩寫了一封信,對自己辦團練六年、一無所成而深感慚愧,也表達了自己投奔湘軍的意願。
「天津教案」發生之時,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正在家中生重病,曾國藩感覺自己難逃大限了,他讓時任兩江總督的李鴻章幫他運來建昌花板木材,準備後事之用。按常規,曾國藩完全可以以生病為由推掉這份「燙手的山芋」。皇帝知道曾國藩正在生重病,也不好直接讓曾國藩去,只是在諭旨中詢問曾國藩:最近身體怎麼樣,這個事件你能處理嗎?曾國藩接旨之後的回答是:「我身為直隸總督,天津發生鬧事,我能不管嗎?」他還引用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的悲壯詩句自勉,決心向林則徐學習。曾國藩接受任務之後,專門寫了一封兩千多字的遺書,告訴長子曾紀澤在他死後如何處理喪事和遺物等。在一生奉行「忠誠篤信」的曾國藩看來,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一樣,應該以誠為本,以信立言,雖然大清是弱國,但也是大國,不應失去固有的君子風範。
一支軍隊的氣質往往體現著領頭人的氣質。團隊與幫派也是這樣。就隊伍結構而言,曾國藩的湘軍主要將領都是讀書人,其中有科名的達卅多人。而且,曾國藩本人也不太欣賞那些只會打「肉搏戰」的「莽夫」。所以他把沒有文化不識幾個大字的太平軍舊將程學啟轉給了李鴻章。曾國藩曾經洋洋自得地說:「我的這些手下,可以白天打仗,晚上講學。」而在李鴻章的「淮軍」中,十三營淮軍的十一位將領中,只有舉人、廩生各一人,主要將領都出身低微:劉銘傳是鹽販子,張樹聲兄弟、周盛波兄弟介於土匪和刁民之間,吳長慶則興於行和-圖-書伍……太平軍叛將、原湘軍舊部程學啟到了李鴻章那裡後,也是如魚得水。曾國藩對部下,常常是跟他們講道理,講忠孝節義。李鴻章在這一點上跟曾國藩有所不同,李鴻章更多的是講義氣,講利益,他就像劉邦一樣,捨得將利益饋贈給部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樣的做法一直被李鴻章奉為圭臬。在李鴻章看來,像曾國藩那樣重用文人、學者的行為是不妥的,因為這些文人學者具有一定的思想,步調很難一致,還不如重用講江湖義氣、頭腦相對簡單、肯於賣命的「武夫」更實在,這些人有一往無前的精神,也能死心塌地追隨主子,只要捨得給他們利益,他們便會全力效忠。李鴻章不太喜歡迂腐的讀書人,在他看來,只有下層的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腳踏實地做事。正因為主帥的判斷標準不一,湘軍和淮軍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氣質,到了太平時期,雙方氣質上的差異表現得更為明顯——太平天國失敗後,由於湘軍中的中堅力量都具備較高的文化知識,有著比較全面的能力,他們有很多躍上了高層,比如說左宗棠、劉坤一等;而江淮人的精明靈活使得「淮軍」雖然普遍吃得開,能辦事,但其中的骨幹力量卻不具備全面能力,文化知識不夠,很少能真正地進入要員之列。在這方面,湘軍與淮軍,同樣也是「一張一弛」。
曾國藩與李鴻章在性格上還是有很大差異的。曾國藩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耿」而倔強,在生活習性上卻很土氣;讀書太多,凡事總有自己的原則,往往在智慧的同時,總殘留著一絲迂腐氣,為人清高,不合群,愛較真。而李鴻章則不一樣,李鴻章總體上極具有江淮人的性格,富有草根經驗,愛面子,散漫,有著濃重的「痞」氣,為人處世比較靈活,講究實效,也比較世故油滑。這樣相對實用的性格使得李鴻章在官場上要比曾國藩適應得多,一方面可以拉幫結派,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大打「迷蹤拳」。所以在太平天國平定之後,李鴻章很快就在職位上超越了他的老師曾國藩,並且比曾國藩更得朝廷的信任。
於同僚,曾國藩一直寬厚為上,以仁待人。比如說,對於左宗棠,曾國藩有著知遇之恩,但左宗棠一直恃才自傲,出語尖刻。每到此時,曾國藩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淡化處理,在把握住大局的基礎上,有時也做必要的妥協。曾國藩善於發現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僚中,許多都是原先科場和官場不得志者,經他的發現、調|教、保舉,不少人都出將入相,官至總督、巡撫、尚書、侍郎等。他的手下湧現出一批經天緯地之才幹,比如說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沈葆楨、丁日昌、曾國荃、彭玉麟、楊岳斌、劉蓉、李瀚章、李續賓、劉坤一、李宗羲、錢應溥、梅啟照、倪文蔚等。此外,在曾國藩的幕府中,還有一批才高八斗的學人,比如薛福成、吳汝綸、李善蘭、徐壽、華蘅芳、黎庶昌、俞樾、趙烈文、容閎、陳蘭彬等。這些人才的和睦相處,與曾國藩妥善處理各式各樣的人際關係有關。有容乃大,這是湘軍集團在軍事、政治上獲得成功至關重要的原因。
還有一次,李鴻章與湘籍俊傑彭玉麟打了起來。原來事情是這樣的,曾氏主持會議之餘,一群幕僚在一起吃飯閒聊,話題轉到安徽人身上。由於彭玉麟的父親曾在合肥一帶做過小吏,期間頗不得志,一幫湖南人在言語之中對安徽人有些譏笑的成分。李鴻章雖奮力辯白,但孤掌難鳴,一直處於劣勢。李鴻章忍無可忍,惱羞成怒,便一拳打向彭玉麟。火暴脾氣的彭玉麟也忍不住還擊,兩人摟在一起,直到摔在地上,還是你一拳我一拳。大家拚命拉架,才沒有引起大事端。這一次事件雖然沒有擴大,但在李鴻章心目中,還是頗有不快,在湘軍大營,畢竟有「寄人籬下」之感,李鴻章開始考慮自己領頭單飛了。
李鴻章年輕氣盛,經常性地仗義執言。一八六〇年曾國藩當上了兩江總督,把大本營設在安徽祁門,李鴻章對此很不以為然,認為祁門在地理上是一個盆地,對兵家來說是個凶險之地,必須趕緊離開,否則一旦被包圍,將會陷入孤立無援的地步。李鴻章把他的想法跟曾國藩說了,曾國藩只是淡然一笑,並不表示什麼。曾國藩何嘗不知呢,他當時考慮的是拿下安慶後再進攻南京,但朝廷卻讓他直接進攻南京。曾國藩於是屯兵祁門,擺出個姿態準備起兵東進,他還是在打安慶的算盤。李鴻章不明白這一點,見曾國藩不聽自己的意見,很不高興,據理力爭了幾句。曾國藩也懶得向他解釋,不冷不熱地來了一句:「你要是害怕這裡,你走好了!」弄得不歡而散。
也正因此,李鴻章一直感激著曾國藩,也圖謀回報。機會很快就到來了,不久,李鴻章即以「滯攻金陵」的行動,算是回報了曾國藩的恩情。
曾國藩一八一一年生,比李鴻章大十二歲,同屬羊。曾國藩與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是同一年的進士,也是朋友。在輩分上,曾國藩算是李的長輩。李文安雖然資質平平忠厚老實,但他卻慧眼識人,他知道曾國藩是一個雄才大略之人,在京時便有意跟曾國藩交好。李鴻章到了京城順利考中舉人後,時任刑部郎中的李文安便有意識地帶李鴻章拜見一些在京城的安徽籍顯赫,比如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這種經歷,在李鴻章的《入都》詩當中,同樣有提及:「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李鴻章果然應驗了他的初衷。然後,李文安又帶著李鴻章去拜見曾國藩,讓曾對李鴻章進行教誨和照顧。當時,曾國藩正患肺病,暫居城南報國寺養病,閒暇之餘常與經學家劉傳瑩等坐而論道。這座又名慈仁寺的著名寺院,曾是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的棲居所,住在這裡,曾國藩有意感覺一下顧炎武曾經的氣場。曾國藩一直有著大儒之風,面對內憂外患,他常常以顧亭林自喻。曾國藩畢生所考慮的,是在亂世之中,在西方文化與科技的強烈衝擊下,如何推動有著千年歷史的儒學向前發展。後來,曾國藩曾經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義理、辭章、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旗幟鮮明地增加了「經濟」一學,亦即經世致用之學一條。
李鴻章到了南昌之後,又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投奔的願望。曾國藩收到這封信後,立即「奉上菲資三百金」,給李氏兄弟作為安家之資,同時回了一信,讓李鴻章速來建昌湘軍大營。於是,李鴻章在南昌稍稍安頓後,便去了曾國藩處,當了曾國藩的幕僚。這也意味著,李鴻章的和-圖-書人生道路真正起步。
有一個笑話似乎很能說明李鴻章的性格,也能說明李鴻章與下屬之間那種親密的關係。有一次,李鴻章問一個下屬什麼叫拋物線,下屬講了一大通後,李鴻章仍是不懂。那個下屬急了,說:「李中堂,你撒不撒尿,撒尿就是拋物線啊!」李鴻章一下子大笑明白了,幽默地說:「各位明白了吧,莊子說『道在夭溺』就是說的這個道理啊!」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教會利用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特權,大量湧入中國。由於背靠本國政府,在中國享受治外法權,教會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權勢力。這種狀況,引起了中國底層民眾的憤怒。從十九世紀六〇年代開始,隨著西方教會勢力由沿海向內地的滲透,外來宗教與中國文化在底層引起的摩擦越來越多,尤其表現為西方宗教教義、組織結構與中國宗族精神以及組織結構之間的尖銳矛盾。正是這種深層次的矛盾,導致了民間不斷掀起反對教會勢力的所謂教案。一八七〇年,天津的百姓燒燬望海樓教堂,先後打死外國人廿人。
作為皖人,在湖南人林立的湘軍大營,李鴻章不免會感到孤單,感到受排擠。李鴻章當時最怕面對的一個人就是左宗棠了。左宗棠為人狂傲,在曾國藩幕府中目空一切,稱呼他人從來都是直呼其名,即使是對曾國藩,也以「滌生」稱呼。有一次,曾國藩與左宗棠在一起玩一種文字遊戲,將各人的姓名列入詩中,自得其樂。曾國藩先出上聯:「季子自鳴高,與吾意見常相左」,巧妙地將「左季高」三字嵌入聯中。誰想左宗棠對出的下聯卻是:「藩臣身許國,問君經濟有何曾?」左宗棠是直接將「曾國藩」大名三字納入了。以字相稱,本是尊敬,而左宗棠卻直呼其名,就有點不恭了。因為是遊戲,曾國藩也不好說什麼。左宗棠對曾國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新來的後生李鴻章在這樣的局面中,肯定會受很多窩囊氣。這也難怪李、左在以後的歲月中一直不和。這兩人的個性,是不太相融的。
不久,形勢的發展證明了李鴻章的戰略預見是對的。太平軍李世賢部攻佔景德鎮,祁門再度被圍困,情急之下,曾國藩分別給二子立下遺囑,準備在祁門坐以待斃。形勢稍緩之後,在胡林翼和曾國荃的勸說下,曾國藩終於同意移營長江邊的東流。當曾國藩向李鴻章函告這一決定時,得到的反應是熱烈的,李鴻章數次來函獻計獻策。師生間由於戰略分歧所造成的隔閡煙消雲散。在此之後,曾國藩幾次函招李鴻章回營,李因忙於照顧病重的妻子周氏,遲遲未歸。曾氏無法再等,又給李鴻章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
「天津教案」的辦理結果,在國內掀起軒然大|波,人們對曾國藩一片譴責,咒罵他出賣國權,堪為民族敗類。曾國藩沒料到風波竟如此巨大,他自己也變得憂心忡忡,健康更是每況愈下。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派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複查「天津教案」。這是李鴻章第二次為曾國藩收拾殘局了。第一次,是平定捻軍的時候,那時,曾國藩就因為調度不靈,平定捻軍進展不順,最後朝廷不得不派李鴻章接替了曾國藩的職務。李鴻章奉命接手「天津教案」之後,專門拜會了曾國藩。看到曾國藩長吁短歎,心理負擔很重,不由勸慰一番。曾國藩問李鴻章:「你準備如何與洋人交涉?」李鴻章說:「與洋人打交道,我首先要同其打『痞子腔』。」曾國藩怒道:「『痞子腔』怎麼打法,你倒打給我看看。」李鴻章一笑:「我只是隨便說說。」
但李鴻章這一段時間與曾國藩的矛盾並沒有通常所描繪的那樣決絕。到了南昌之後,曾、李二人一直有著書信來往。不過李鴻章心中的確有點梗阻,他曾向丁未同年沈葆楨去信詢問福建的情況,有意去補閩任道員之缺。沈葆楨回信勸阻了他。另一個丁未同年郭嵩燾也來信勸他回到曾國藩身邊去。那段時間李鴻章的夫人周氏生病,李鴻章一直忙於照顧。周氏是李鴻章老師周菊初的侄孫女,李鴻章少年時,周菊初對他就十分欣賞,也經常接濟李家。李鴻章趕考前,周菊初把自己的侄孫女許配給了李鴻章。周氏比李鴻章大兩歲,是一雙大腳。李鴻章跟她的感情一直很好。李鴻章中進士當上翰林後,周氏並沒有跟李鴻章來京城,一直在老家照顧李鴻章的母親。李鴻章回鄉辦團練,夫妻才算得到團圓,在李鴻章戎馬倥傯期間,周氏一直跟著李鴻章東奔西走。
不久,「刺頭」李鴻章又為彈劾李元度之事跟曾國藩再度發生爭吵。李元度是功勳卓越的湘軍元老。在皖南戰役中,李元度沒聽從曾國藩的勸告,失守戰略要地徽州府。曾國藩一氣之下決定彈劾他,要李鴻章寫奏折。但李鴻章不僅不願擬稿,反而率一班人去了曾國藩那裡替李元度據理力爭,指出李元度「其血性足以幹事,而知人則不甚明;其才識足以謀事,而帶勇則非所長」。認為曾國藩既然瞭解李元度的長處和短處,卻捨長取短,這個責任不應由李元度來負。同時,李元度勞苦功高,一直追隨曾氏身邊左右,如果一兵敗就嚴辭彈劾,會讓部下們唇亡齒寒。李鴻章一番激烈的言辭讓曾國藩大為光火,堅持不更改決定。李鴻章倔脾氣上來了,怎麼也不肯起草那個奏折,又以離開為要挾。曾國藩索性揮揮手:「隨你便!」
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結果是:判死刑廿人,流放廿五人,天津知府、知縣革職並流放黑龍江「效力贖罪」;支付撫恤費和賠償財產損失銀四十九萬兩;派崇厚作為中國特使到法國賠禮道歉。
說到李鴻章的中進士,還有一則故事:李鴻章在丁未科考中進士同年中,與沈葆楨同門同房,關係最為親近。兩人經歷各不相同,交情卻絕非一般。李鴻章考試時的房師孫鏘鳴,也是當時的名士。丁未科雖然人才濟濟,但他這一房只考中了李鴻章和沈葆楨兩人,不由得牢騷滿腹。孫鏘鳴鄉試中舉時的恩師是大學士翁心存,也就是翁同龢的父親。孫鏘鳴鬱悶地跟翁心存談起自己的心事,翁心存對孫鏘鳴說:「你先不要發牢騷,把這兩個學生帶來讓我看看。」於是李、沈二人在孫鏘鳴的帶領下,前往拜見了這位太老師。翁心存非常善於「風鑒之術」,他首先上上下下打量了李鴻章幾眼,就大驚失色地說道:「此人將來的功業在我輩以上。」接著又看了看沈葆楨,又說:「這將來也是一個名臣。你這一房考中的人雖少,但有了這兩個,還有什麼可遺憾的!」這是夏敬觀在《學山詩話》裡繪聲繪色描述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