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到古代玩機械/ 古代機械 /
一樣的穿越,不一樣的精彩。
一個因意外而回到古代的工人,抱著不放棄的信念,運用自己的學識和后社會的先進經驗,在扶助國家富強的同時,也令到自己飛黃騰達。
本文是一部理性的穿越小說,以情節取勝。整個故事用機械為連線,穿插美食、武俠、商戰、改革、戰爭、皇室等情節,文中還加入了張三丰、洪七公兩位不同朝代的老頑童,增添故事的可讀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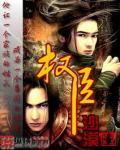
權臣/ 沙漠 /
他讓一個家族的姓氏,成為一個帝國的旗號!
踏過時空的界限,拋卻身份的束縛,引領著一個曾經輝煌的家族走上又一個輝煌的頂點,做一件骨子裡想實現的事情。
怒目揚眉,憑藉未知的三根金指,在動亂的四國、勾心鬥角的九大世家以及名貫。
天下的十方名將之間謀得他應有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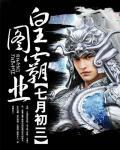
皇圖霸業/ 七月初三 /
一名質子回國,開啟了隱藏在暗流之下的八王奪嫡。一場經歷了三年的戰爭,徹底的暴露了大燕帝國的外強中乾。這時,六國戰亂已起,天下陷入紛爭。大爭之世,且看九皇子姬輕塵如何通過自己的努力,北定邊疆,變法強國,又娶得心愛的女人,再問鼎天下。

醉卧江山/ 離人望左岸 /
這是一個最好的年代,這也是一個最壞的年代。
有人活在笙歌醉太平,十里紅袖招的秦淮河畔,隔江唱著後庭花。
有人活在胡虜夜叩關,風雪滿弓刀的烽煙戰場,生死相依挽殘袍。
蘇牧來了,看見了,經歷了。
於是,他想著,或許能做一些事情,無論好的壞的,總要留下些什麼。
任風月亂了刀槍,唯我醉卧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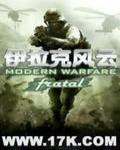
伊拉克風雲/ fratal /
古老的巴比倫文明,桀驁的巴別通天塔,神秘的空中花園,伊拉克——你的歷史如此光輝燦爛!但今天你卻為何被戰火籠罩?你的財富為何被他人掠奪?你的人民為何在爆炸和死亡中掙扎?誰能來拯救他們——
真主說:通道的人們啊,我將降下天神來援助你們!
如果我是庫賽·海珊,如果我曾經執掌大權,如果我回到了20世紀80年代的伊拉克,那麼——會發生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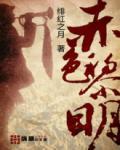
赤色黎明/ 緋紅之月 /
1905年,黎明前的黑暗,魑魅魍魎、百鬼夜行。前方有無數的岔道,前方也只有唯一的生路。
砸碎奴役者們所鑄造的一切枷鎖,我們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有鎖鏈,獲得的則是整個世界。
黎明前的天際必將赤紅如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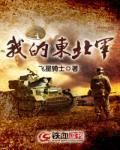
我的東北軍/ 飛星騎士 /
這部小說講的還是一個穿越回到過去的老故事:一個普通當代大學生的意識穿越時空陰差陽錯附身到了1928年的張學良身上。在歷史的分叉口,他拒絕執行「不抵抗」命令,率領東北 軍浴血奮戰保家衛國,促進中華民族統一;大力發展農工商學諸業,創建現代化的中國陸海空軍隊;在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聯合納粹德國,出兵東南亞和太平洋,擊潰日蘇美等世界列強,為中華民族開疆拓土,重寫中國近代史;向著億萬中國人心中的「中華帝國盛世」夢想奮鬥不休。

靈旗/ 喬良 /
《靈旗》是軍旅作家喬良著的一部中篇小說。寫的是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時奪路而逃、在慘烈的湘江之役中再次潰敗、其中一隊傷員藏匿於鄉間的故事。這部作品是八十年代軍事文學的代表作,當時《小說選刊》的主編李國文親自為這篇作品寫了編後記。
小說以極為深沉內斂的筆觸,描寫了紅軍湘江一戰八萬人死傷過半的極度悲壯的戰鬥,其間還穿插了紅軍內部血腥清洗的內幕,以《靈旗》為題,是作者為那些革命先烈所譜的一曲悲壯淒涼的輓歌。

海軍航空戰(1939-1945)/ Nathan Miller /
本書描述二次大戰期間各國海軍航空隊(主要是英美)的作戰,時間從1939年開戰至最後1945年日本投降。作為基本戰史入門書還不錯,要再進一步則需找深入的專著。此書從簡體電子版改製,其中有些名詞稍微不同。原書有些敘述比較簡略,簡體版譯者加了一些補充,放在括弧中。另外原書有些說法並不正確,我就個人所知加按語指正,也在括弧中。

異域烽火/ 卓元相 /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國民政府最後的據點-盧漢叛變後,李彌、余萬程將軍即率領著國山越嶺,衝開險阻,越過邊境,到達荒蠻的森林地-中緬未定界。這支由雲南進入中緬未定界的游擊隊,在荒蠻之中,餐風露宿,在苦不堪言的環境中,面對自然環境與共黨奮戰,用血淚爭取生存的機會,為的就是收拾舊山河,鞏固東南亞反共堡壘,延續大中華錦繡河山。
柏楊先生在1961年根據自立晚報記者馬俊良訪問從泰北撤退到臺灣的孤軍口述資料,以筆名鄧克保發表了戰爭小說《異域》,引起了一陣對泰緬孤軍的風潮,後來出版了七八種有關泰緬邊區孤軍的書籍。
本書即為其中之一,描述國軍反共游擊隊在中緬邊區的奮鬥血淚史,從民國四十二年敘述至五十年的第二次撤退為止。後來作者又出版續集,描述從民國五十年至六十四年間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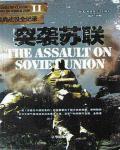
突襲蘇聯/ 葉皮凡.馬卡列夫 /
本書是比較少見的,從蘇聯的角度來看德蘇之戰的爆發。
大戰即將來臨之際,蘇聯為了給自己換來一點準備的時間,選擇了和最危險的對手希特勒簽訂條約。這是國際外交史上最為複雜也最富戲劇性的事件之一。但希特勒卻是一個根本無法與之做交易的人,何況這個陰謀家時刻沒有忘記他進軍東方的「理想」。因此,雖然史達林作出了當時看來唯一明智的選擇,卻還是沒能改變歷史的進程。希特勒的戰爭機器開動了,他會選擇一個他認為最合適的時間,將所有的條約扔進紙簍,然後用斯拉夫民族的鮮血來擦拭他的刀鋒。
史達林應該知道,希特勒是一個根本無法與之做交易的人,然而他卻被《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迷霧蒙住了眼睛。希特勒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百萬納粹軍隊氣勢洶洶地向蘇聯逼來——蘇軍猝不及防,一時間全線潰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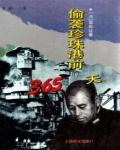
偷襲珍珠港前的三百六十五天/ 實松讓 /
本書《偷襲珍珠港前的三百六十五天》(日文原名:真珠灣までの365日─歴史の裏側の偉大な物語り)出版於一九六九年,實松讓根據日美雙方的資料,對於一九四一年內日美之間的談判、對作戰的準備,以及日本高層對美開戰的決策過程,有相當清楚的描述——也僅限於描述,實松讓身為日本海軍人員,對於政治上的折衝、以及最後如何引致開戰決定的種種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因素,可能也無法深入分析。不過,就跟他的《情報戰》一書一樣,本書也提供了對日本高層決策流程的一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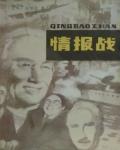
情報戰/ 實松讓 /
《情報戰》本書從戰略與情報機構的角度,回顧日美兩國之間從日俄戰爭到太平洋戰爭結束為止,約半個世紀的軍事對抗的經過;試圖通過一些彰明昭著的偶發事件,列述兩國情報戰的開展狀況,以及它對戰爭,作戰乃至外交鬥爭的影響。除此之外,他還回憶了整個珍珠港前後以及太平洋戰爭中日本海軍情報工作,並且與美國的情報工作進行了比較,是比較少見的題材。
一般讀者如我自己,總是有個疑問,美國因為破解了日本海軍密碼,對於日軍的動向比較容易瞭解,但是日軍方面又如何呢?基本上日本海軍在戰爭期間未能破譯美軍密碼,又缺乏有效的間諜網,不曉得他們如何進行情報蒐集與研判?實松讓提供了非常詳盡的解答。
實松讓身為日本海軍情報部門之一,當然不免要替自己及同仁辯護,不過他所描繪的,也應該是日本海軍的現實。只不過從他的敘述裡,真讓人懷疑當初日本在開戰時到底怎麼想的,難道日本海軍模仿英國洋化太過,連原來自己文化中從中國汲取的部分都忘了嗎?孫子「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無算乎?」的至理名言,顯然日本海軍是聽不入耳,否則怎麼會像實松讓抱怨的這樣忽視情報的蒐集、處理、與運用?
另外這本書有個特點,在書的第一章把日本二十世紀前半的美日國防政策與作戰綱領做了相當好的總結,讓讀者能夠瞭解雙方為何逐步進入對抗。雖然不是剖析真正衝突原因,至少條列了雙方的對應措施。對於要進一步瞭解二戰期間美日國家戰略的人,是有所裨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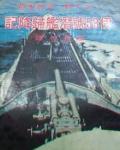
伊五十八號潛艦歸降記/ 橋本以行 /
作者是前日本潛艇艇長。他在本書中,根據親身經歷、某些日本潛艇軍官的回憶以及日本軍令部的一些官方資料和文件,通俗地敘述了日本潛艇在 1941-1945年期間的戰鬥活動情況。書中列舉了很多事實,來說明日本潛艇的戰鬥行動使美國海軍遭到的損失。美國人在出版本書時所寫的長篇前言中,肯定了其中的大多數事實,同時也否定或訂正了某些事實。
美國版前言的作者寫道:「戰爭開始時,日本海軍共有六十艘潛艇;戰爭期間損失了一百三十艘;到戰爭結束時,只剩下一打左右。美國在戰爭初期擁有的潛艇數量與日本大致相等;戰爭期間損失了五十二艘:但到戰爭結束時,卻增加到二百多艘。」
本書的某些章節敘述了珍珠港戰役,潛艇在東太平洋的活動,潛艇對敵岸的炮擊,潛艇在海洋交通線上的活動,潛艇在溝通日德兩國聯繫上的作用。中途島海戰,瓜達卡納爾島爭奪戰,潛艇在吉爾伯特群島、塞班島、菲律賓群島和硫磺島附近的活動,潛艇在北方海區的活動,雷達的作用,有人魚雷的使用,「印第安納波利斯號」巡洋艦的沉沒以及其它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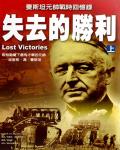
失去的勝利/ 曼施坦因 /
二次世界大戰,一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它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影響極之深遠。今天,無論是世界強權的分佈、軍事概念、科技發展、以至世界經濟格局,都是它的延續;對這樣一場影響深遠的戰爭,實在是有必要去了解的。
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第一手資料,即文獻、檔案、報告和回憶錄等,是所有歷史書的基礎,沒有史料支持的說法,都是沒有說服力的。曼施旦因的《失去的勝利》就是一本很有價值的回憶錄。
英國著名軍事學家李德哈特,在戰後詢問過很多德國將領,他們一至識為,曼施坦因,是他們之中,最有能力的將領。
曼施坦因最膾炙人口的,是他制定了對法國的作戰計劃,這計劃最後亦以他的名字命名,即所謂的「曼施坦因計劃」。這場戰役,對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展,影響最深;沒有對法國的徹底勝利,就沒有「海獅作戰」,也不會有「巴巴羅薩」,「世界大戰」可能也不會發展成「世界大戰」。正因為對法國的大勝,一下子就打破了歐洲、以至世界政治與軍事的平衡,才使得其它世界強權,不得不投入到對納粹德國的作戰,因而使戰爭不斷升級‧‧‧
有人說,希特勒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人,但不要忘記,沒有德軍強而有力的實力作為後盾,軍事勝利又從何說起?而曼施坦因,正是德軍將領的表表者。
馮.曼斯坦——德國陸軍元帥,軍事家、戰略家,與隆美爾和古德林被後人並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三大名將。他是世界公認的偉大戰略家 ,他不僅擅長運籌帷幄,對於衝鋒陷陣、攻城掠地,同樣表現得出類拔萃,可以說是一個天生的軍事奇才。
在本書中,馮.曼斯坦以其親身經驗,紀錄二次大戰中幾場重要戰役的現場實況。根據其私人日記和其他資料,介紹了德國進行侵略戰爭的經過,詳細敘述事前佈局、戰爭過程及戰後影響。

海權論/ 馬漢 /
《海權論》以戰略家的理性與史學家的智慧,總結研究了有史以來的海上戰爭及其影響,提出了制海權決定一個國家國運興衰的思想,直接促成了德、日、俄、美諸國海軍的崛起,從而以海軍的「聖經」之譽,躋身於影響人類進程的十六部經典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