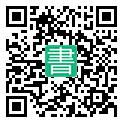第二部
10 聖誕節慘案
「我剛說了,亨利爵士,我很篤定。桑德斯身材魁梧,英俊,臉色紅潤,精神飽滿,和藹可親,人緣很好,對妻子體貼得不得了。但我就是知道他打定主意要除掉她。」
珍娜.賀麗爾晃動著她漂亮的腦袋問:
「不,不是猜測,絕對不是!是實踐與經驗的問題。我聽說,有一個古埃及文物研究者,只要你給他一隻奇妙的小甲蟲飾物,一摸、一看,他就能告訴你它是屬於公元前哪一年的產物,或者是伯明罕的仿製品。他從來也說不清這裏面有什麼規律可循,但他就是能識別,因為他的一生都與這些東西打交道。
每個人都盯著這位老小姐。
「得了,亞瑟,」班崔太太溫和地說,「你知道那地方對你身體很有益。」
「這句格言說得好極了。」亨利爵士嚴肅地說。
「他逗留了一會兒,打打趣,隨後離開了。我說過,我一直很擔心,於是我劈頭就問:
「『那麼我們能認定屍體就在它原先的位置?』他說。
「但事實就是如此,班崔上校,我想跟大家講的也正是您剛才所言。讓我理理思緒……是的,如您所說,說人是非,嗯,這種事很常見。大家都看不起這種行為,特別是年輕人。我侄子——那個寫書的,我認為他寫的很精采——曾經嚴厲指責這種行為,說無憑無據地道人長短實在要不得,簡直太惡劣了,如此等等。但我想說的是,沒有一個年輕人肯停下來思考,他們並未審視事實。其實整件事的關鍵在於:這些您所謂的東家長西家短,有多少比例是真的!我認為如果他們認真審視這部份的話,他們會發現,這些流言斐語十有八九是真的!讓人真正惱火的正是這點。」
「特洛普太太說她去她朋友毛蒂默家打牌去了,我因此暫時放了心。但我仍感到憂心忡忡,而且不知所措。大約半小時後,我回到我的房間,碰到我的醫生柯爾,我上樓時他剛好下樓。我正想跟他談談我的風濕病,於是我請他到我的房間。他跟我提到了(是秘密,他說)女服務生瑪莉小姐死亡的內情。他說經理不希望這消息張揚出去,所以要我也別說出去。我當然沒告訴他,打從那個可憐的女孩一斷氣,大家的話題就不離這件事。這種事一定立刻就傳出去,一個像他那樣有經驗的人應該明白這一點,但柯爾醫生是個單純、毫無疑心而且死心眼的人。也正因為如此,一分鐘後,他的一番不加思考的話,引起了我的警覺。他說他正要走的時候,桑德斯先生請他去看看他太太,好像她最近有些不舒服,消化不良之類的。
「抗議?」她低聲說道。
「那都是憑靈感得來的猜測。」亨利爵士說。
「『我同意您的看法,夫人。那麼,我前面說過,他一定折回來過。真是非常冷血的傢伙。』
「活見鬼了,」班崔上校說,「不可能隨便就找到屍體的。他們怎麼處理……處理第一具屍體呢?」
「『桑德斯先生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他說。
「警官機警地抬起頭來。
「不管怎麼說,那可能是您的想像,瑪波小姐,東拼西湊的想像。」亨利爵士說。
「親愛的女士,您別嚇我了。」
「他把她搬回去,」瑪波小姐說,「這是個很邪惡的點子,但確實絕妙透頂,我們在交誼廳的談話使他萌生了這個計劃。那個女服務生瑪麗的屍體,為什麼不利用呢?還記得桑德斯夫婦的房間在頂樓,與僕人們的房間在一起嗎?瑪麗的房間離他們的房間只隔了兩間。殯儀館的人要到天黑以後才能到,他把時間都計算好了。他沿著陽台把屍體搬過來(五點的時候,天已經黑了),給她穿上她妻子的衣服,在外面再套上那件對她來說太大的紅外套。之後,他發現他太太裝帽子的櫃子竟然鎖著!他唯一能做的是找一頂瑪麗自己的帽子——沒有人會注意到這些細節的,他把沙袋放在她身邊,然後離開房間,出去的時候,故意讓我們都看見,以證明案發時他不在現場。
「桑德斯太太倒在地上,臉朝下,命歸黃泉。
「或者是你朋友的。」亨利爵士修正了說法。
「『除了帽子外。』我答道。
「我跟他解釋說,我阻止桑德斯移動屍體,他點頭表示我做得對。
「現在我迫不及待想把接下來發生的事講個一清二楚。六點四十五分桑德斯先生回來時,我人還在交誼廳裏。有兩位男士與他一起,三個人看起來神情很愉快。桑德斯撇下他的朋友,向我和特洛普太太坐的地方走來,說他給他太太買了件聖誕禮物,想聽聽我們的意見。他買了一個晚宴用的皮包。
「你是說水上飛機嗎?」珍娜睜大了雙眼問。
「我認為我沒有強調『看起來』這幾個字,但警官目光犀利地看著我。
「他笑容可掬地走進來。
「而就在當天,桑德斯太太還對我說,她的消化系統很好,還說謝天謝地呢。
「『是的。』
「我想您說的沒錯,」瑪波小姐說,「我自己……」
「桑德斯被處以絞刑。」瑪波小姐說得很乾脆,「案子破得很漂亮,我從不後悔我參與了讓這男人受到正義制裁的行動。我可沒有耐心像今天的人道主義者那樣顧慮死刑的問https://m.hetubook•com.com題哩。」她嚴厲的表情緩和下來。「我經常為了未能挽救那女孩的生命深感內疚。但誰會願意聽一位老太太匆匆做出的結論呢?哎,哎,誰知道呢?也許在活得開心的時候死去,還勝過在突然變得天昏地暗的世界裏抑鬱寡歡,也強過在幻象破滅中虛度時光。她愛那惡棍,信任他,從來沒看清他的真面目。」
「這真有點難以置信。」羅伊德醫生說,「他這樣做實在冒險,警方有可能很快就到達的。」
「是的,我知道,我侄子雷蒙.衛司也會這麼說,他會說我是捕風捉影。但我記得華特.洪斯,『格林曼』的老闆。一天晚上,他在與太太回家的路上,太太掉進了河裏,而他領了保險金!另外還有一兩個人至今仍逍遙法外,有一個與我同一個社交圈。他準備夏天與太太一起到瑞士登山,我警告那位太太不要去,這個可憐的女人沒有像平時那樣衝我大喊大叫,只是笑笑,她認為像我這樣的老怪物會對她丈夫哈利產生這種想法,真是可笑。哎,哎,結果,出了意外,哈利現在娶了另一個女人。然而我能怎麼辦?我知道是怎麼回事,可是沒有證據。」
「你呢,賀麗爾小姐?」班崔上校問,「你必定有些特別的經歷。」
「我一向不善猜謎,」班崔太太說,「有那麼充份的證據證明桑德斯不在現場,真是可惜,只不過既然你都相信了,那就沒什麼可懷疑的了。」
「『記住我的話,』她說,『這還沒完沒呢,你們聽過這句俗話沒——「福無雙全,禍不單行」。我不只一次地驗證過。還會有人死去的,你們不用懷疑,而且過不久就會發生。禍不單行嚇!』
「恐怕你搞錯了,親愛的。」班崔太太說,並向她解釋這詞的兩種含義。這時她丈夫插話進來說:
「我想,現在大家都想聽聽真相,對吧?桑德斯太太,你們也知道,她整個下午都與她的朋友毛蒂默夫婦一起打橋牌。大約在六點一刻左右,她離開了他們。從她朋友的家到水療院大約十五分鐘的路程,如果走得快的話還不用那麼久。她六點半一定回得來。由於沒人看見她進來,所她可能是從側門直奔回她房間的。她在房裏換了衣服(她穿去打橋牌的那件淺黃褐外套、裙子就掛在衣櫥裏),顯然正準備踏出房門時,便遭人重擊。他們說,很有可能她根本不知道是誰把她擊倒的。我想,那沙袋確實是一件很有效的兇器。由此看來,兇手好像就藏在房間裏,也許是在那個她沒打開的衣櫥裏。
「是的,但那是後來的事了。在我們給警察打電話的時候,格拉蒂.桑德斯還活得好好的。」
「我知道,親愛的,我開始講這故事的時候,你並沒想到結果會是這樣,這也不是我所預期的。但事實就是事實,如果事實證明某人錯了,那他就得承認,並從頭開始。在我心裏,兇手就是桑德斯,無論什麼事也動搖不了我的看法。
班崔太太發出一聲驚詫的喘息,瑪波小姐轉向她說:
「我並沒有特別指定要講什麼血案,」亨利爵士說,「但我知道你們三位女士中一定有人知道什麼精采的案子。好了,瑪波小姐,這次是講『清潔婦的奇遇』還是『母親聯誼會之謎』呢?別讓我對聖瑪莉米德失望。」
「真是個絕妙的藉口,」亨利爵士說,「但說不通。《一千零一夜》就是一個很好的先例!好了,說吧,莎赫札德。」
「我抗議。」亨利.克什林爵士輕輕地眨動雙眼,看著在座的人。
「還記得電話線路壞了這回事嗎?」瑪波小姐說,「那是他計劃中的一部份。他不能讓警方馬上就趕到現場;而且警方來了之後,先到經理辦公室去談了一會兒,然後才到樓上去的,這是他計劃中最弱的一部份,也許有人會覺察到一具死了兩小時的屍體與一具剛死半小時的屍體,是有差別的。然而,他算準第一個發現這命案的人沒有專業知識。」
瑪波小姐別過頭平靜地看著他。
「我告訴他,那帽子原本是在格拉蒂頭上的,但現在落在她頭髗的旁邊。當然,我原為是警方放的,然而警官斷然表示不是他們放的,他們沒動過任何東西。他皺著眉,低頭看著俯臥的屍體。格拉蒂穿著外出服,一件深紅色毛領花呢外套,那頂紅色的廉價氈帽就放在她頭旁邊。
「我與特洛普小姐和卡本特老太太坐在交誼廳裏,卡本特太太信神又信鬼的,對此津津樂道。
「『什麼也不許碰,』我說,『桑德斯先生,請鎮靜點。特洛普小姐,請到樓下把經理找來。』
「我花了兩天都沒弄明白這一點,」瑪波小姐說,「我想呀想的,忽然一切豁然開朗。我立即去找警官,請他做個試驗,他也同意了。」
「有一個小插曲要提出來講一下,那就是在玩橋牌的過程中,有通電話找桑德斯太太,一和*圖*書位李德華先生想跟她說話。聽完電話之後,她看起來很開心,興奮不已,打牌時出了一兩次嚴重的錯誤。她還提早離開了,他們原本計劃多玩幾局的。
「我想說的正是這種感覺(說得很糟,我知道)。這些我侄子所謂的『多餘的女人』,大都有充裕的時間,她們最感興趣的是人。所以,你們知道,她們幾可視為人性專家了。現在的年輕人不像我們年輕時受到眾多的限制,他們可以自由地談論任何話題,但他們的頭腦單純得可怕。他們輕信任何人事物,如果有人告誡他們,即便是輕言細語,他們也會對你說,你的頭腦還停留在維多利亞時代,說那就像洗水槽。」
「但願我能完整地講述這個故事。」她焦慮地說,「我擔心我會語無倫次,人常會不自覺地離題,而且很難記清每一個事件的先後順序。如果我講得很亂的話,請大家包涵,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說了,這場悲劇和聖瑪莉米德無關,事實上,和一所水療院——」
「我最先向她奔過去,跪下,拿起她的手摸了摸她的脈搏,但已經沒用了,她的手臂已冰冷僵硬。緊挨著她頭部的地方,有一隻填滿了沙子的長襪——那是把她擊倒的兇器,特洛普小姐,蠢蛋一個,只知道在門口抱著頭哀叫個不停。桑德斯大叫『我的太太,我的太太』後衝向她。我不讓他碰她,你們知道,當時我就很肯定是他下手的,他可能想把什麼東西拿走或者藏起來。
瑪波小姐有些臉紅,以一個很小的手勢止住了他:
「我說是的,並描述了當時的情景。我想這可憐的人在跟桑德斯以及艾蜜莉.特洛普談過之後,總算找到了一位可有條有理回答他問題的人,這下他可放心了。我想,特洛普當時完全嚇癱了,一定是的,蠢蛋一個!我母親曾教導我說,一個有教養的女人,管何時都必須在公眾場合控制住自己的情緒,無論她暗中有多麼失控。」
「『但經理鎖上了門,而且拿走了鑰匙!』
「你是指我嗎?」班崔太太說,「但我真的沒什麼好講的,我周圍從未發生過血腥事件或神秘懸案。」
「我親自跟他的這兩位朋友談過。我不喜歡他們,他們舉止粗魯、缺乏教養,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說的全是真話,他們說那天桑德斯一直和他們在一起。
「這一定是意外。」
「但他的那種口氣讓我覺得有些寬慰。我覺得他還沒有把桑德斯認真當作喪妻的鰥夫。
瑪波小姐看著這位赫赫有名、美麗、成功的珍娜.賀麗爾,輕輕地點了點頭。
「親愛的瑪波小姐……」
「當然是意外,沒有比這看上去更像意外的了!桑德斯曾跟我說過,他跑過船,一個在顛簸起伏的船上都不會失去平衡的人,會在連我這老太婆都站得穩的電車上倒斜?騙誰呢!」
「『您能肯定是小偷所為嗎?』我說。
「『有人知道桑德斯太太在哪兒嗎?』
「我在陳述這些看法的時候,警官不住地點頭。
「咦,」亨利爵士說,「洗水槽有什麼不妥嗎?」
「但帽子戴不上去,瑪麗的頭髮很短,而格拉蒂,我前面說過,頭髮很多。他不得不把帽子放在屍體旁邊,希望不會有人注意到這一點。然後,再把瑪麗的屍體搬回她自己的房裏去,再次把一切佈置妥當。」
「『我聽說,屍體被發現的時候,您在現場。』
「不管怎麼說,這是個問題。究竟是竊盜殺人案——這似乎不大可能——還是桑德斯太太準備外出去會某個人?那個人是不是從太平梯進了她的房間?他們是不是吵了架?或是他無情無義地將她殺害了?」
「是具死屍,這沒有錯。」瑪波小姐平靜地說。
他一副洗耳恭聽的態度,瑪波小姐因此泛起紅暈。
「嗯,那麼,」珍娜.賀麗爾說,「她畢竟沒有白活,沒有白活,我希望……」她沒往下說。
「那是因為,像大多數的人一樣,您不願面對現實。您寧願認為它不可能,但我知道,事實就是如此。人就是無能為力,真可悲!譬如說,我就不能到警察局去報案,而且去警告那女人也沒用,這點我明白,她對那個男人很癡情。我只能盡量去打聽他們倆的事情。在火爐旁做針線活的時候,有很多機會可以打聽。桑德斯太太(她叫格拉蒂),巴不得能一直聊下去。當時他們好像剛結婚不久,她丈夫以後會繼承一筆遺產,但他們的生活過得很拮据,實際上,他們是靠她那點微薄的工資度日。這種事不稀奇。她抱怨她根本改善不了家裏的經濟,好像什麼地方有個人在控制著一切似的。我後來發現,那些屬於她的錢,她已用遺囑的形式留給了別人——兩人結婚後立刻分別立了份對對方有利的遺囑,非常感人。當然了,一談到錢就頭痛,那是每天的重擔。他們真的很缺錢,事實上他們住在頂樓,與僕人的房間連在一起,一旦失火是很危險的,雖然要真有火災發生的話,和圖書太平梯就在他們窗戶外面。我很小心地問她,房間外是否有陽台,可真危險喲,那些陽台,輕輕一推即可——你們知道!
「『看起來是如此,是的。』我答道。
「哦!」珍娜含糊地說,「我想我沒有什麼親身經歷,我是說,沒碰過那種事。鮮花,當然有囉,還有好多奇怪的留言,但那些都只是男人們的花招,不是嗎?我不認為——」她停住,陷入了沉思。
「他與他的朋友一起回到水療院,設計讓我和特洛普小姐與他一起發現謀殺案,他甚至假裝要把屍體翻過來,而我阻攔了他!然後大家派人去找警方,他則搖搖晃晃地向水療院的花園走去。
「哦!」班崔太太憤怒地說道,「我們已經做了該做的事。我們帶著至高至絕的智慧傾聽,展現了成熟|女性的態度——不巴望自己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
「沒有人問他屍體被發現後他有沒有不在場證明。他在花園裏與妻子碰了頭,帶她走上太平梯,一起回到房間。也許他跟她提過屋裏有具屍體的事,她俯下身去,想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他立即拾起沙袋向她猛擊下去……噢,天啊!即使是現在想起來,也讓我萬分噁心!然後他飛快地把她的衣服和裙子脫下來,掛在衣櫥裏,再從另一具屍體上脫下衣服,給她穿上。
「那個令人生厭的地方,糟透了!早上得早早起床,喝些新鮮的水。然後一大堆老女人坐在一起,東家長西家短地說個沒完。天啊,我一想到……」
「『夫人,不曉得您是否記得死者耳朵上有沒有耳環,或者死者生前有戴耳環的習慣?』
「當然,我們告訴他說我們樂意效勞。他問能否勞駕我們上樓去,他怕他把東西拿下來的話,他太太有可能會撞見。於是,我們就跟他上了樓。隨後發生的事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現在我還能感覺我的手指隱隱作痛。
「呃?」亨利爵士說著,向前傾了傾身子。
「我承認,我就像我們的鄰居法國人所說的那樣『固執己見』。
「不曉得你們當中有誰猜得到。」
「我知道這個叫桑德斯的男人要想他太太的命,而我失算的是,我沒顧及到『巧合』這個怪異的東西。我相信我對桑德斯的判斷絕對不會錯,那人是個惡棍,雖然他裝出來的假悲傷一刻也騙不了我,我清清楚楚記得當時他吃驚、迷惑的表情著實逼真,好像真情流露,如果你們明白我的意思。老實說,與警官交談之後,我心底產生了奇怪的疑惑。因為如果這可怕的事是桑德斯幹的,我想不出為什麼他要從太平梯偷偷摸摸地溜回來取走他妻子的耳環?這可不是明智之舉,而桑德斯是個理智的人,也正因此,我才覺得他危險。」
瑪波小姐停下來,深深地吸了口氣,然後繼續道:
「並不在她頭上……」
「『你們也知道,女士們,』他說,『我只是個粗魯的水手,這些東西我怎麼懂?我讓他們送三個來供我挑選,我想聽聽你們這些專家的意見。』
「哦!」珍娜說,「那麼,這就沒什麼意思了。」
「這讓我有些失望,」亨利爵士說,「但我會盡量接受的。我們都知道您靠得住。」
「也許,你們都猜得出我的結論是什麼。世界上發生的事情經常出人意料。我是如此地相信我的判斷,我想,正是這種固執,讓我產生了盲點。結局讓我相當震驚。事實證明桑德斯根本不可能做案……」
「『各位女士,要我幫你們買聖誕用品回來嗎?』他問,『我馬上要去凱斯頓。』
「我認為您發現的東西已經夠多了,瑪波小姐。」亨利爵士說,「這案子是在我在任之前的事了,我甚至不記得是否聽說過。後來怎樣了?」
「『那沒什麼,陽台和太平梯是小偷出入的捷徑。很可能你們中斷了他的行動,他從窗戶溜出去,等你們都離開之後,他又重新返回來繼續他的行動。』
「但一開始的時候是戴在她頭上的,對吧?」
「為什麼那個裝帽子的櫃子是鎖上的呢?」
「他冷冷地說:『嗯,看來如此,不是嗎?』
「他給他太太打電話,稱自己是李德華,我不知道他跟她說了些什麼。我前面說過,她很容易相信別人。他讓她提早離開牌桌,但沒要她直接回到水療院,而是約她七點鐘在太平梯附近的花園與他見面。他也許跟她說,他想給她一個意外的驚喜。
瑪波小姐搖搖頭說:
「了解了嗎?我對這個男人的懷疑頓時增加了一百倍。他正在鋪路,為了什麼而鋪?在我還沒決定好是否要跟醫生講出我的想法時,他就離開了我的房間。當然,就算要說,我也不知道從何說起。我剛跨出房門時,這個桑德斯正好從樓上下來,一副外出的打扮,再度問我是否需要他從城裏給我帶點什麼回來。我努力和他客套了一番,然後逕直走到交誼廳,要了杯茶。我記得當時正好五點半。
「親愛的,你真聰明。」瑪波小姐高興地說,「我也感到納悶,但答案很簡單,裏面是一雙繡花拖鞋和一盒手帕,是那可憐的女孩給她丈夫的聖誕禮物,那是她親手繡的,這就是她把櫃子鎖起來的原因。我們在她的皮包裏找到了鑰匙。」
「您已經教會我重視人www.hetubook.com.com性了。」亨利爵士很認真地說。
瑪波小姐的眼光逐一掃過她的聽眾。
「桑德斯先生打開臥室的門,開了燈,不知道誰先看見了……
「是的,一定有。」羅伊德醫生說。
眾人都驚訝得倒吸了口氣,瑪波小姐點了點頭,緊閉雙唇。
「我留在房間裏,跪在屍體旁,我不能留下桑德斯單獨與她在一起,但我不得不承認,如果他是在表演的話,他確實演得好極了。他看上去是那樣的茫然、迷惑,完全給嚇傻了似的。
「親愛的,這種事很平常,時有所聞。男士們是很容易受到誘惑的,儘管他們身體強壯多了。把事情弄得看上去像是意外,不是很簡單?我前面說過,第一眼看到桑德斯,我就知道他的企圖。事情發生在電車上,車內很擠,我不得不到上層去,我們三個人都站起來正準備下車時,桑德斯先生沒站穩,正好倒向他太太,她頭朝下地倒向樓梯,幸虧售票員年輕力壯及時抓住了她。」
「現在來看看桑德斯的行動。如我前面所說,他是五點半或稍晚後出去的,然後在幾家商店買了些東西。大約六點左右,他進了『格蘭Spa』旅館,在那兒他碰到兩個朋友,就是後來與他一起回到水療院的那兩個人。他們一起玩了撞球,我想,還喝了威士忌加蘇打。這兩個人(一個叫希區考克,另一個叫史賓德)從那天下午六點後就一直和他在一起,他們一起回到水療院。之後,他撇下他們走過來向我和特洛普小姐打招呼,那時是六點四十五分,這時候,她妻子一定已經死了。
「哦!這才有意思哩,」瑪波小姐說,「這是唯一一件奇怪的事,正是這一點讓兇手露出了馬腳。」
「『您是什麼意思?那帽子怎麼了?』
這位老太太點點頭:
「正是如此,」瑪波小姐有些激動。「在任何房子裏,它都是不可或缺的東西,可是,當然囉,它並不浪漫。現在我得承認,我也有情緒,和其他人一樣,有時候那些不加思索、脫口而出的言論會深深地傷害到我。我知道男士們對家務事毫無興趣,但我還是得說說我那位女佣愛瑟,一位外貌姣好,相當熱心的女孩。我一見到她,就知道她與安妮.韋布以及可憐的布魯特太太的女兒是同一類型——一有機會便順手牽羊。所以當月我就把她辭退了。我給她寫了封推薦信,說她誠實、莊重,但我私下卻警告愛德華老太太不要僱用她。我侄子雷蒙為此感到極大的憤慨,說他從來沒有聽說過如此『可惡』的事,是的,可惡。後來,她又找到艾希登小姐那兒去,我覺得我沒有義務提醒這位小姐,結果發生了什麼事?她所有的內衣蕾絲都被剪了下來,兩枚鑽石胸針被拿走,女佣連夜潛逃,從此消失無蹤!」
「我相信自己的判斷。這之後有一天,在過馬路時發生的一次意外,使我對此更加深信不疑,有一位心滿意足,快樂的已婚少婦馬上就會被謀殺。現在,我問您,我該怎麼做,亨利爵士?」
「親愛的瑪波小姐,」上校叫道,一副慌亂的表情,「我絕對不是指……」
「哦!瑪波小姐。」班崔太太叫道,「你該不會說……」
羅伊德醫生點了點頭說:
「那麼,」亨利爵士說,「答案是什麼呢?」
「問到桑德斯先生是否知道他太太有個叫李德華的朋友時,他說他從來沒聽過這個名字。在我看來,這點可從他太太的態度上得到證實,她似乎也不知道這個叫李德華的人是誰。然而聽完電話之後,她的臉微微泛紅,充滿笑意。因此,不管是誰打的電話,看來他沒有說出真實姓名,這事很可疑,不是嗎?
「我要她保證不到陽台上去,我說這是夢的啟示,她牢牢地記住了,有時候迷信的說法很能發揮作用。她是位漂亮的女孩,臉色有些蒼白,一頭蓬鬆的齊肩捲髮。她耳根子很軟,把我的話原封不動地告訴了她丈夫。有一兩次,我發現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他可不是那種容易哄騙的人,他知道那天我也在電車上。
「我懂,親愛的,」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溫柔,「我懂。」
「我嗎?」珍娜說,「你們的意思是,要我告訴你們我的親身經歷?」
「那裏沒有您感興趣的東西,亨利爵士。當然,我們是會發生一些小小的案子,例如零點二五品脫的上選好蝦莫名其妙地不見了,可是您不會感興趣的,因為結局微不足道,儘管這件事讓人更加了解人性。」
「幸虧我有仔細觀察事物的習慣,我記得有一對珍珠耳環在帽沿下面熠熠閃光,我當時雖然沒有特別注意這對耳環,但他的第一個問題我能肯定的答覆。
「不一會兒,經理就來到了現場。他迅速地把房間查了一遍,然後把我們都趕了出來,鎖上門,拿走了鑰匙。然後,他去給警察打電話。我們好像等了一個世紀,警察都沒來,(後來我們才知道是電話線路出了問題),經理不得不派人去警察局。水療院離鎮上很遠,它是在荒野邊緣。卡本特太太讓我們很受不了,『禍不單行』的預言這麼快就應驗,令她相當得意。有人說桑德斯漫無目的地向水療院的花園走去,雙手抱著頭呻|吟著,展示著他的悲痛。
「一和圖書個很嚴正的抗議。我們一共六個人,男女各佔一半,我要代表在座這幾位受欺壓的男性提出抗議。今晚我們共講了三個故事——全都是我們三個男人講的!我抗議女士們沒有分攤工作。」
「警官一聲不坑地在那兒站了好一會兒,眉頭緊蹙,突然他想起了什麼。
班崔太太睜圓了雙眼。
「當時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怪異陰森的氣氛,像是有什麼東西壓在我們身上,一種不祥的感覺。先是喬治,那個門房,出了事。他在水療院待了好多年,認識每一個人。他開始是得了氣管炎,後來發展成肺炎,最後在得病的第四天死了。這事震驚了所有人。當時離聖誕節只有四天。接著是一位女服務生,一位好女孩,手指化膿,二十四小時後就死了。
「我請他把地上的帽子戴到死者的頭上看看是否能戴上——當然戴不上去,那不是她的帽子。」
「您真愛說笑,亨利爵士,蝦子什麼的只是我信口說說而已,但我倒是因此想起了一件往事——其實不是件小事,是場悲劇,我本人在某種程度上也捲了進去。我對自己做的事從不後悔,不,一點兒也不後悔,只可惜這件事不是發生在聖瑪莉米德。」
「我想,命案被認為是在七點差一刻左右發生的,但實際上是七點或者是七點過幾分時才發生的。警官檢查屍體時最早也要點半,那麼他也許就無法察覺屍體的差異了。」
「我應該想到,」瑪波小姐說,「我在摸那女孩的手時,感覺它是冰冷的,但之後當警官說兇案就發生在我們來之前不久時,我竟然沒反應過來!」
班崔上校雙腿伸得直直的,對著壁爐台皺著雙眉,彷彿盯著一位遊行隊伍中踢錯正步的士兵;他太太則偷偷摸摸地掃視著剛寄來的一份球莖植物目錄;羅伊德醫生盯著珍娜.賀麗爾,眼神充滿了愛慕之意;而這位年輕貌美的女演員則若有所思地注視著自己擦了粉紅色指甲油的指甲。只有那位年長的老處女瑪波小姐筆直地坐著,一雙淺藍色的眼睛對著亨利爵士眨了眨。
「我們一直都認為躺在那兒的那具屍體就是格拉蒂.桑德斯,但誰都沒去看她的臉——她臉朝下,還記得嗎?那帽子又把頭和臉都蓋住了。」
「我不同意他下的這種結論,我跟他解釋說,我親自查看過床底下,經理也打開衣櫥看過,除了這兩處外,這房間裏再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藏身。衣櫥中間裝帽子的小櫃子倒是鎖著的,但那只是一些淺淺的隔板,是沒辦法藏人的。
「『這就對了。這位女士的珠寶盒被翻遍了,我知道她沒有什麼太值錢的東西,只有手指上戴的戒指被摘了下來。兇手一定是忘了耳環,所以在案發後又返回來取走了耳環,冷血的傢伙!或者也許……』他環顧四周,然後緩緩地說:『他也許就藏在這個房間裏,一直都在。』
瑪波小姐停了下來。
「我把我知道的都說完之後。警官說:『謝謝您,夫人,恐怕現在我得請您再看看屍體。您進門的時候她是否就躺在那兒?是否被動過了?』
「恐怕我講得有些突然。我現在試著詳詳細細告訴你們發生了什麼事。對此我一直深感痛心,我本來可以阻止它發生的。上帝應該知道,我盡了力。
「最後,警察終於來了,與經理、桑德斯先生一起上了樓。稍後,他們也找我上去。我上了樓,警官正坐在桌子旁邊寫著什麼。他看起來很聰明,我喜歡他。
「別急,我是找到了一個好辦法。」瑪波小姐說,「但那男人比我想像的要聰明得多。他不再等了。他認為我可能已經起疑心,因此先下手為強。他知道弄成意外會受到我的懷疑。因此,他把計劃改成了謀殺。」
「反正是一堆老女人坐在一起說人是非。」班崔上校咕噥道。
「您是說,有人假扮成她嗎?但當您碰她的時候……」
「我看我們還是聽聽蝦子的傳奇吧!」亨利爵士說,「請吧,瑪波小姐。」
「你們會說,這與發生在凱斯頓水療院的事毫不相干,但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係的。這正好能說明,為什麼從我第一眼看到桑德斯,就很篤定他想除掉她。」
「她一邊點頭一邊說完最後一句話,並把棒針弄得卡喀卡喀直響。我一抬頭剛好看見桑德斯就站在門口,有那麼一會兒他有些出神,我清清楚楚看到他臉上的表情,我認為是卡本特太太那些話讓他興起了殺人的念頭——這到死我也不會改變說法——我看得出他的大腦正在計劃。
瑪波小姐稍做停頓,讓其他的人對她的話加深印象,然後繼續說:
「我很擔心,非常地擔心,因為我不知道怎樣才能阻止他。在水療院我可以防止任何事故發生,只消暗示對方我對他有所懷疑即可,但那最多也只能拖延他的計劃而已。不對,我開始相信唯一的辦法便是大膽地設下圈套,讓他自投羅網。如果我能設計誘使他動手取她性命的話,哼,他的真面目便會露出來,那麼她就不得不面對現實,儘管這對她來說是一項很大的打擊。」
「您讓他試什麼呢?」
「您真讓我驚訝,」羅伊德醫生說,「您能有什麼妙計可施?」
「但她的確被殺了呀!」
「『您是珍.瑪波小姐嗎?』他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