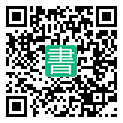三、寂寞休止符
「過了不久,也——幾個月了。」他望著靜文。「我們感情極好,他去了我也不想活,事實上我也有了那個病,我只在等再見他的那一天,我在等。」
靜文唯有照辦。
孩子好像在哭,怎麼她聽不到聲音,就好像只有畫面的靜寂時刻。然後,孩子被送去嬰兒房,手上綁上條藍絲帶,樣子粉|嫩可愛,他像誰呢?完全看不清楚——
應酬。這是每個商人不能拒絕的事,靜文苦笑。信哲多少個夜晚沒出現在晚餐枱上了?
信哲有應酬,做生意的人時間是控制不準的。靜文獨自坐在餐抬上,全無食欲。
「不錯,不錯,有進步!」玉明總是鼓勵。「你快講簡單的話了。」
靜文沉默無言。
淚眼模糊中,靜文走下木樓梯,走到小巴站,坐小巴回市區處。
「他沒說在哪裏養病?」
「不要講話。」依然是對流淚眼。「你剛剛醒,不要講話。」
「好。」靜文不言不語地走開。
樓下的廳裏有兩個七、八歲的孩子在玩耍。
她活在絕望、傷心、痛苦的黑暗中。
她又多收了一個男孩子學生。大熱天在全屋冷氣開放中給學生上課,倒是輕鬆舒服。
「你一定會好,聲音一定會回來,」她說:「現代醫學那麼昌明,一定能醫好的。」
「他們常去旅行?」
「那麼——我能為你們做什麼?」
「顯志出了事?」靜文一針見血。
「還不睡?」他望著靜文。
「只是——到此為止。」靜文沙啞地說。
是不懂。兩個男人的愛情。
她一直在黑暗中飄飄浮浮的,身子很輕,能看見手術牀上的自己。意識又回來,啊,生孩子,醫生護士正滿頭大汗地工作著。
小女孩搖搖頭,「沒有人跟他同住,他一直是一個人。」
但是,此刻的他卻像一隻鬥敗的公雞,頹然垂下頭。
「但是我——」她指著自己的喉嚨,仍是那種嘶嘶啞啞的怪聲,聽不見正常的字句。
在管理處借電話,電話久響無人接聽。
「靜文,不能這樣,他不想跟你談。」
這天信哲又有應酬,靜文覺得今夜特別累,於是早早上牀休息。
「我發誓,我保證,我會找人穩妥地做這件事——在我去了之後,一定能做到,直到不需要。我發誓。」
她不懂這種感情,也不想批判。沒來之前她曾覺得不光彩、惡心,然而聽張先剛的話——他的談吐、他的氣質不俗,他講的話也沒什麼不對,愛情的事有什麼道理可說呢?
「不、不、不,不要錯怪阿志,他很愛伯母,只是怕別人知道我們的關係。而且我自私,我希望他常常陪著我,我不要他被女人搶去,所以我對女人特別兇惡,特別沒禮貌。」
「媽媽——」靜文臉無人色。
「還好。」淑華有點遲疑。「他總講那些話,說好些了,但人又不回來,又不許我問話,說長途電話貴哦。」
她以為信哲會驚醒幫她,然而信哲不在牀上,快三點了他還沒回來?
靜文只能耐心等候。孩子在肚子裏過了預產期還不出生的話有沒有危險?又拖了兩天,她心中愈來愈不安,卻不敢出聲,信哲到底問過醫生沒有?她可不可以先進醫院呢?信哲沒說,她也不好意思問。信哲這兩天忙得不可開交,一筆大生意在談,最好別煩他。
「啊……沒有,不是。」淑華有點慌亂。「我是說……以前工廠同事打來的。」
但聽著自己喉嚨發出的怪聲,靜文連覺也睡不著。
「他剛開車出去。」
顯志到底是自己至親的哥哥。
「他、他、他——進了醫院。」
「哪有這種人,小孩子還不懂人性。」靜文搖搖頭。「你覺得身體有什麼不妥嗎?」
「我不懂。他看來只是瘦弱,但他一直都是這樣啊。他要被觀察一段時間。」
這話——有什麼不妥?是嗎?
「下次我要自己接聽。」淑華大聲說。她很少對靜文用這種態度,這表示了她心中極之不滿。顯志在她心中最重要,自丈夫去世。她的全部希望、所有精神都放在兒子身上。
信哲、淑華和醫生的話又漸漸變得很遠,好像在說「危險期沒過,不能打擾。」之類的話,什麼危險期?她又沒生病,只是生孩子而已。很長的一段時間,身不由己地昏昏迷迷,四周彷彿有聲音,又與她全無關係似的。然後,突然間,她醒過來。有一種不知置身何處的感覺。
木樓梯上的天地和樓下完全不同,現代化的高級傢俬,精緻的布置,二房二廳整齊得一塵不染。張先剛讓她坐。
「很嚴重?」
「請——跟我來。」他放下食物,轉身出去。
「是,一定。」信哲頑皮。「沒有嫂嫂就沒有你,就沒有我們的婚姻,也沒有就來的孩子。」
「哦——」管理員帶絲懷疑地上下打量她,看得她渾身不自在,只好退出。回到家裏,完全不敢提這件事,怕淑華擔心和傷心。她自己不停在想,顯志為什麼通知了淑華之後又匆匆避開?是不是其中還有什麼隱瞞?不安只能放在心中,獨自承擔。她一定想辦法把顯志找出來,否則怎麼對淑華交待?很奇怪,淑華自此之後從來沒再提起顯志,而且看來很平靜安詳,和初知顯志入院時完全不同。
「很快。他去超級市場買食物,」一個小男孩搶著說:「他每次也都帶些給我們。」
「一直以來是你在騙媽媽?」她啞著聲音。「是阿志臨去時吩咐的,」他垂著頭,幽幽地說著。和以前那惡狠狠的樣子簡直不是同一個人。「他要我做。」
靜文於是找第二個醫生、第三個、第四個,幾乎找遍了港九的耳鼻喉專家,大家的話都差不多,她的靭帶全被破壞,失去彈性,變得僵硬,再也不能唱歌。
「他去的情形怎樣?」
「他的脾氣愈來愈怪了。」淑華嘆息。
「要慢慢調理,或要看耳鼻喉專科醫生,」醫生嚴肅地對她說:「開刀的時候你昏迷,要在喉嚨裏插喉管,可能喉管碰傷你聲帶上的靭帶,令靱帶失去彈力。以後可能會好。」
死者已矣。顯志從小不快樂,與人沒有交通,他去了——或是解脫。
面對小小的巧儀,她簡直又恨又愛,原是這麼可愛美麗的小女孩,但是——因她來臨而破壞了靜文的一切和_圖_書,靜文無法不怨不恨。
「啊——顯志,」淑華像吃了一驚。「沒有,我不知道他在哪裏,怎麼樣?只是很久以前他告訴我,他在安心養病。」
「癩痢頭的孩子是自己的好。」靜文笑。
她略懂一些急救知識,忙把小巧儀放在一邊,替淑華用力按人中,又用白花油讓她聞,幾十秒後,淑華悠悠轉醒。
努力撐起身子,亮了燈,她預備去叫醒淑華。她知道孩子將出世,該立刻去醫院。
「上次他對你說什麼?」靜文不答反問。
「他們人呢?」
「別哭、別哭,醫生說你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你知道,再拖五分鐘你不開刀的話,孩子和你都會沒命。」她竟經過了大難不死的時刻而毫不知情。
原來如此,靜文點點頭,安靜下來。
「她是我的堂妹玉珊,從美國學聲樂回來,她聽過你演唱,很讚賞你。」玉明熱心地說。「你們是行家,她希望認識你。」
玉珊在旁邊淡淡地笑一下,靜文竟看見她笑容中的揶揄,是嗎?玉珊。心中如被巨物撞擊,痛得不得了。
也許就是這絲揶揄重新激起她心中的鬥志,突然間她坐起來,她不能放棄,她還要試,哪怕只有半絲希望。
她竟經歷了一個大難大劫。
淑華不再言語。哪有不想見兒子的母親?顯志的電話又來了,靜文立刻接起。
是她在生孩子嗎?怎麼她好像是置身事外似的一點感覺也沒有。
「如果我只生一個孩子呢?你要男還是要女?」
信哲很認真地想一下。
下午下課,她立刻趕到淑華說的醫院,她急切地想要更多顯志的資料。
「請——保重。」她推門外出。
「沒有理由不相信,」她輕嘆。「他跟你一起很快樂,所以連家都不想回,母親也不想見。」
「不得不應酬,」信哲揮一揮手,臉上滿是酒精刺|激的紅霞。「不陪他們喝一點是不禮貌。」
信哲認為小巧義有病,醫生卻說一切正常,有些嬰兒是天生這麼反叛的。
並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信哲,她下意識覺得這並不光彩。萬萬想不到,顯志竟是個同性戀者。從小的種種蛛絲馬迹,他孤僻,不合群,不與女同學說話以及長大後的種種怪異行動,她應該早有所覺,然而誰會想像得到他竟真是——唉!
「我要見顯志。」她堅決地站在那兒。
未來的嬰兒帶給這家庭更多的希望。
「我不要你花錢讓我去夏威夷,你自己花那麼多錢看醫生,我只是說說。我自己一個人也不敢去,我不懂說話。」
「記住。我們是兩夫妻,最親密的人,有什麼事一定要告訴我,讓我替你分擔。」他誠心誠意。「一生一世都這樣。」
靜文立刻想到顯志,心中莫名地掠過一絲不安,心情立刻沉重起來。
她嘶啞的聲音連單音字都發不出,她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思。
她還沒來得及說「喂」,顯志已開始說話。
「不可能。毅力很重要!」玉明正色。「我始終覺得你必然會復原,上天不會如此待你。」
二十四歲的年輕歲月裏,她的心已像七老八十,比淑華還灰,還無望。
靜文也不敢問,怕帶來後患。
「媽媽,什麼事?」她的心往下沉。
「他一定極聰明美麗。」
「我會盡量替你醫,但——」他謙然而笑。「我不能保證什麼。」
「無論什麼,你告訴我。」她的聲音顫抖。
「記住,星期六中午老師一家移民,我們一定要去送行。」靜文說。
淑華為什麼再也不流淚、不掛念、不擔心?
這更增加靜文的不安,什麼事要這樣神神秘秘?她甚至沒回來晚餐。
淑華卻興奮地迎上來。
「在醫院。醫生不准出院。」
「多——久?」靜文帶著惶恐,語不成聲。
「已驗過血,已證實。」淑華說。
顯志又說在夏威夷?根本扯謊。
「我看得出,你有事瞞著我,」信哲說:「好幾次我看見你對著鏡子發呆。」
她的內心還是最惦念著顯志,自丈夫去世後唯一的精神寄托。
再提顯志,這個大男人竟低下頭嗚嗚地哭泣起來,好傷心好傷心,像死了親人。
「張先生開旅行社的——啊!」管理員警覺。「你是什麼人?」
「你們的大哥?」
「顯志才是媽媽的兒子,媽媽不會要別人的錢。」她正色說。
「長途電話當然貴,他在養病沒有收入。」靜文心中難過。
「不放心也不行,他在那麼遠?」淑華茫然無助。「我也去不到。」
靜文下午沒課,中午就從中大趕回家,意外地看見淑華在臥室垂淚。
靜文站起來,無言地盯著他看。這一刻她十分勇敢,因為她知道他是個惡狠狠的人。
好在救護車十五分鐘就趕到。十五分鐘不算長,但對陣陣劇痛又流血不止的靜文來說,彷彿過了一輩子。
靜文一眼認出他是消瘦了的張先剛。不只消瘦,整個人還顯得亂,頭髮、鬍鬚、衣服都沒整理好,神色消沉黯然。
「我們沒見過。」
靜文四下張望一下,快步走上木樓梯。
「萬一他生氣,他不再打來怎麼辦?」
「各人帶小姐買鐘出街了,我當然立刻打道回府,陪老婆。」
淑華什麼都不問,她心中最盼望的事,就是每星期三下午顯志的電話。
「你終於找來了。」他低墼說。
「靜文,我們總要有信心,並保持希望,」玉明堅持。「我不相信現代的醫學醫不好你。」
玉珊笑得燦爛,靜文心中卻流過一抹憂愁,她有疑問:她的聲帶真可以復原?
他不答,只傷心地哭泣,很久很久。
「沒有。目前的我非常滿足,極幸福,怎麼會有心事?」
「什麼時候?」靜文強抑悲痛。
早晨起來,靜文覺得不舒服,頭昏身熱又作嘔,她想,糟了,生病了。她沒有生病的時間,中大的工作和新收的學生都令她十分忙碌。
靜文嘆息,淑華並不懂愛滋病的一切。
「我——走了。」她轉身欲離開。
靜文只請了李玉明老師和她的朋友陳蓓華,她不想太多人知道她現在的情形。
「媽媽,有顯志的消息嗎?」她無意中問。
「下次還是讓我聽,我要聽他的聲音。」淑華顯和_圖_書得不滿。
「不、不,沒有事。」淑華嚇了一跳,連忙掩飾地抹乾眼淚。「我沒事。」
「他打電話來。」淑華漲紅了臉。
那居然是一處很高級的大廈。門口管理員問清了她要找誰之後才肯讓她上樓。
小女孩一再搖頭。
張先剛從屋後駛出一輛汽車,根本沒注音四周就揚長而去。他看來士氣消沉。
「放心。我隨傳隨到。」他拍拍她,翻身睡去。
怪聲是她發出來的?她駭然。
生孩子是喜事,為什麼流淚?發生了什麼事?她怎麼完全不知道?
靜文心一痛,淚又流下來。
但靜文怎能告訴她真相呢?那太殘酷,那會毀了她,她受不住。
「我不懂。但他們說——他……他是——愛滋病帶菌者。」淑華大哭出聲。
「等你,我們彷彿好久沒聊過天了。」
「請——等一等。」他囁嚅著跟出來。「我很想給伯母一筆錢,又怕唐突,不知道——」
「不、不,還有一個可能生病的年輕男人,」靜文強按下心中不安。「很瘦很蒼白的。」
「靜文——」信哲也叫,也有淚意。
「我是他妹妹。」
「不能去。醫生不准他隨便見人,」淑華立刻說:「顯志連我都不許再去。」靜文不語,她已有打算。
她從臥室出來,看見淑華正把電話掛上。
「他屋子裏好整齊漂亮,」小女孩笑起來。「沒有男人會那樣整理屋子。」
「怎麼樣?美女如雲?」
「我是安仔的妹妹。」
「還早,十一月才是預產期。」
「我不知道。」她誠懇地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覺、愛情,別人不能說什麼。我不知道,但——謝謝你令顯志過了快樂的七年。」
「陪客戶吃晚飯?」
經她再三懇求,終於得到地址。
「顯志呢?」她單刀直入。
她一身一頭冷汗,是痛出來的。才一下牀,感覺到溫暖又潮濕的液體從大腿內壁流下。一低頭她看見大量的血,一陣頭昏加上一陣劇痛,她尖叫起來。淑華聞聲衝進來,一看這情形也嚇傻了。
「不要講話。」淑華立刻制止她。「你動手術時候插氧氣管,傷了喉嚨,過一陣就好。」
「啊——有點頭昏,別擔心,只是有點累,我沒事。」她立刻又去抱巧義。
靜文淚水簌簌而流。
「為什麼不早告訴我?」靜文埋怨。「害我白白擔心這麼久。」
信哲出來,水已沖掉他的微醉,他看來已完全清醒。
不知道什麼時候,她被一陣又一陣劇烈的陣痛痛醒,那種痛是屬於不可忍受的,她忍不住呻|吟起來。
「很好,沒有不妥,完全沒有。」
「怎麼辦?信哲不在?怎麼辦?」她叫。
「你流血太多,身體弱,要多休息,醫生每天替你打安眠針,你終於渡過危險期。好了,好了,母女平安。」
玉珊熱烈地打招呼,靜文卻無言以對。
淑華說要留醫觀察的?顯然是顯志與那個姓張的男人驅騙淑華。好在靜文還有個地址,以前顯志留下的。
李玉明帶玉珊來訪。
愛滋病帶菌者,那表示——表示顯志是個同性戀者?一剎那間往事全湧上來,顯志那沒禮貌的房東,顯志那惡狠狠運動員般的朋友,顯志的怪異陰沉,顯志的陰陽怪氣,顯志——那怎麼可能呢?
開學了,她不能再去中大教書,更無法教學生,她那種難聽、不能成句的聲音,學生們都會嚇一跳。
「哪有這種事。」她打著哈哈。
母女間的親情是那樣神奇,小小的嬰兒居然展開笑容。
「媽媽,」靜文疑心更重。「讓我聽電話只有好沒有壞,你想不想見到他?」
他應酬極多,一星期起碼五天不回來晚餐,起碼有一半是凌晨四五點才歸家。靜文並不計較,有什麼好計較的?她已全無鬥志,全無希望。
她是聲樂家,一生事業就在聲帶上。
「你要保持身體好,你是我最親的人。」習慣了靜文嘶啞的聲音,也猜到她講什麼。
「怎麼這樣說?孩子怎麼會癩痢?」
「讓我來,」靜文抱起孩子,很奇妙,巧儀的哭聲立刻停止。
「媽媽——」她狂奔過去。那聲「媽媽」簡直不像人類的聲音,沙啞淒厲,令人毛骨聳然。
靜文這才看見她兩臂都是針筒,大概在輸出營養劑和其他藥物。
何況,靜文自己還有揮之不去的困擾和痛苦。
「繼續打電話、放錄音帶,」她想一想,淚水從眼角緩緩流下。「如果你不能再做,請找人代做。媽媽——不能承受顯志比她更早去的打擊,電話對她極重要。」
「我看——復原的機會不是很大,也許可以講一些話,但唱歌大概不可能了。」醫生好像在法庭作最後宣判。「好的靭帶全僵硬了。」
「顯志今天意外地又打電話來,他說夏威夷的天氣和醫生的悉心治療,他有很大的進步,啊!他可能快回來了。」
靜文找到一個陰涼的樹下耐心地等著,她在等一個機會。
第二天早晨,靜文出去了大半天,她必定是去辦什麼事,她很慎重,為外出還推了一個學生的課。
那天靜文去電話公司請求查每星期三的電話來源,電話公司原本沒有這項服務,後經靜文解釋原因並加懇求,才有今天這封信。
可惜的只是他們倆俱是男兒身。
她敲著唯一的一扇木門。
靜文重複一次顯志的話。
靜文沒出聲,她看見張先剛正推開鐵門走進來。
「安顯志,今晨出院了。」詢問台的女孩告訴她。「他的資料?那是保密的。」
她再開始找醫生,只要聽見有哪個好醫生,她不辭勞苦,山長水遠地必定趕去。即使半絲希望,她也不放棄。
中午回來,她卻什麼都沒說。但神色是安詳中帶著慎重。
讓她說什麼呢?也許是大家眼中的悲劇:卻是當事人最美最甜的夢。
現在一切都好,都美滿,還有什麼事令母親流淚?
靜文聽見這樣的話還是覺得不自在,他們是不同世界的人,究竟是她或他們是另類人呢?她分不清。
「你相信我的話?」他驚喜。
她看四周,全是白濛濛的一片,有極重的藥水味道,有白衣人在走動——醫院。是、是,她來生孩子的,孩子怎樣?
星期三下午m.hetubook.com.com,顯志的電話依時來到,淑華緊張地早早守在電話旁邊,生怕靜文會搶她的電話。接聽電話時,臉都因興奮而發紅。
醫生很仔細地替她檢驗,很慎重地研究了半天,然後說得有些歉意。
「靜文——」是淑華疲倦極了的哭聲。
「他真的一個人住?」
雖然第二天有早課,靜文還是等到深夜。一點半,信哲才微帶醉意地回家。
中午,她打電話去公司找信哲。
就在她全力尋訪醫生之際,有一夜她突然驚覺,她有多少天沒見過信哲了?信哲沒回過家,即使有,也在她睡夢中,換下髒衣物然後匆匆外出。為了她的傷,她忽略了家,忽略了丈夫、女兒、母親,她內疚得心都絞痛起來。
白天,她開始照顧巧儀,做一切淑華做的事,晚上才把巧儀交給母親,很奇怪,巧儀在靜文懷裏乖得不得了,不哭不鬧也不發脾氣,晚上一回到淑華房裏,就開始哭鬧,就開始不聽話。
玉珊為什麼要如此對她?
「庸脂俗粉,」信哲揮揮手。「她們眼中只有錢,但大陸佬喜歡,沒辦法。」
靜文也大概忘記了電話的事,她每天替學生上課,日子過得正常而平靜。
「顯志——還好嗎?」靜文故意問。
她被無情的現實從天堂打進地獄。
「你——不罵我、恨我?」他極之意外。「你——沒有話說?」
靜文努力收攝心神替十六歲的女孩子上課,兩小時中她心中隱隱覺得有什麼不妥,以致她變得有些煩矂。下課後送走小女孩,她在屋子裏找不到淑華。在牀邊留著她的拖鞋,她外出了。
顯志在裏面?她抱著一絲希望大步走進去,但是——她看見一個靈位,上面有顯志的照片,有長生牌,有一個小瓷瓶,看來是載骨灰什麼的。
「我——」她說不出話。不該不安,沒理由不安,是不是?信哲是負責的好丈夫。
「阿志通知伯母去醫院見他時,其實那時已不行了,他錄了許多話,很多錄音帶,讓我定期打給伯母,說他去了夏威夷。」
她拒絕抱巧儀。
立刻有人來到牀前,那是淑華。
女兒取名巧儀,很漂亮的一個孩子,只是脾氣暴躁,夜晚吵得很厲害,為了不使靜文和信哲煩惱,淑華深夜就常常抱著她在客廳直到天亮。
「陳先生一早去了深圳,傍晚才回。」那個相當能幹的秘書說。
「不會的事學學就會了,很容易。」他走進浴室,嘩啦嘩啦地洗起澡來。靜文有點不安,卻又說不出什麼所以然。喝一點酒當然不是大事,而且——信哲變得有點陌生,是,就是這樣。孩子還沒有出世,丈夫怎能變得陌生?
「我——我——我——」她紅了眼眶。
「你根本不會喝酒。」
回到家裏,淑華一定要靜文「坐月子」,她是古老的人,不准靜文洗澡洗頭,不許她吃生冷的東西,不許外出走動,弄得她煩躁極了。目前她最急要做的事是看耳鼻喉醫生。
眼看著淑華瘦了、憔悴了,但靜文幫不上忙。她的傷口未合,不能抱孩子,怕破裂。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意識回來得更多,人也有絲清醒,然而,她感覺到痛,不知從哪兒來的痛,彷彿全身每一個關節、每一個細胞都痛,像火燒也像撕裂,她忍不住呻|吟,她聽見一聲聲「撕嘶」的怪聲,她聽不見自己的聲音。
「最近你看來有心事。」信哲很細心。
駭然見到淑華抱著小巧儀兩人一起跌在地上,淑華——彷彿昏倒。
「他又大方又好人,」多話的小男孩又搶著說:「他還送大哥一張免費機票去泰國玩。」
「顯——志?!」靜文倒退一步,全身劇震。張先剛無言站在那兒,臉如死灰。
「是啊。他明天才回來。」小女孩說:「他答應以後也給我們。」
「是啊。我們到他屋子裏玩過。」小男孩說。
「好多天沒見過張先生和安仔了,」管理員笑得有點曖昧。「去旅行了吧?」
「還是要女兒。」他說:「女兒比較貼心,長大後還會多得回一個兒子。如果只生一個兒子,將來就是別人的。」
「誰的電話?」她隨口問。
許多醫生已婉轉地對她說:「你別再來,浪費金錢時間,我們無法幫你更多。」
這段時間,靜文覺得幾個世紀都過去了,她原本溫暖的心變得冰冷,不祥的感覺完完全全包圍著她,她無法支持,只得坐在沙發上。
「還有巧儀。」淑華抱緊了巧義。「我們是直系血緣。」
「信哲來電話說他不回來晚餐,要談生意。」淑華把話題移開。
她敲了很久,很久,確定了屋裏沒有人才頹然下樓。
「真把我嚇死,送進醫院你就昏迷,醫生說難產,嬰兒的臍帶繞住了脖子,流了好多血,最後信哲來了,決定開刀。這中間的時候你完全昏迷不醒,醫生只能對你作一般急救,開刀的事非等信哲簽字不可,拖了很久——」信哲到哪裏去了?她記得很清楚,她痛醒時已清晨三點,還拖到多久他才回來?天亮?心中太多疑問,偏偏全身無力,又說不出話,情急之下眼淚也流下來。
「也許回,也許不回,看時間。」秘書的聲音很甜。「晚上他有應酬,不過我一定通知陳先生打電話回家。」
彷若晴天霹靂,嚇得靜文魂魄四散。
「不、不,那個張先生,他說顯志病得很厲害,在醫院,讓我去看看。」淑華想到傷心處又流下眼淚。「就是他長年住在外,沒有人照顧,可憐,啊,靜文,愛滋病會怎樣?」
靜文忍著無邊無際的剗痛,顫聲說:「打九九九叫救護車。」
靜文強烈地感覺到淑華在說謊,她不想拆穿,每個人都有一點自己的秘密。
「他——他很含糊,」她終於說:「其實他一個星期打一次來,只是他說,不許我問問題。上次——就是他打來的,我沒說出來。」
「為什麼不通知我們?我們有權知道。」
「X月X日下午二點半九龍XXXXX號打出,電話登記者張先剛。」
「哦,差點忘了,信哲今夜又有應酬。」
「明早我再打電話給醫生,」信哲彷彿有少少不耐煩。他太忙,這點點小事不該打擾他。「他答應會送你入院。」
「你們——和張先生很熟?」
淑華無言搖hetubook•com•com頭,眼淚又掉下來。
「人呢?」
淑華起初有點茫然,然後慢慢爬起身。
「女人不坐月子身體不好,那是一輩子的事,聽話。一個月很快過。」
「媽媽,你是媽媽,他永遠會找你。他是你的兒子,根本逃不掉,你怕什麼?」
「請問張先生在嗎?」她明知故問。
他嗚咽著。
「怎知孩子的興趣是什麼?不能強求。」
屋裏沒有反應,一絲回應都沒有。
「是他不許我告訴你,他說——他的事只讓我知道。」
「媽媽——」淚意一直往上湧。
「孩子。」靜文又作口形。
她黑了,瘦了,眼眸失去光芒,面容憔悴,失去俏麗,也許是種下意識的錯覺,她看來臉額上彷彿有層黑氣,就是別人說的霉運當頭的那種。
「信哲呢?」她用口形表示。
「我只怕臨時作動起來找不到人送。」
「哪個人?」淑華茫然不知。
上學下課、教學生、等待孩子出世,她的日子是一成不變的,生孩子之後明年她又預備開大型的演唱會,雖然大著肚子,每天她也勤練聲音,人的身體就是件大型樂器,久疏練習會生銹的。
「啊——」靜文驚呆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事清竟然這樣,太出乎意料之外,太不可能了。
「什麼時候——去的?」
「稚氣!」他深情地撫摸她的頭髮。「我做生意忙是為了你,為了這個家,為我們以後能過更好的生活。我和你是一輩子的事,記住,嗯。」
「媽媽,為了證明一點事,為了他好,你讓我接聽。」靜文臉色凝重。
看見靜文,他像遭到雷殛般呆住了。
「這是好消息。」靜文強忍淚水。「晚上帶你出去吃飯慶祝。」
一滿月,靜文立刻找專科醫生。
「身體很痛,有各種併發症。但是——我可以保證他很快樂,很滿足。不、不,我是說我們都快樂滿足,我們找到了對方。我們在一起七年,那是段最美好的日子,美好得如今我們要承擔後果,然而無悔。」說到後來,他嘴角泛出沉醉的甜蜜微笑,臉上泛出動人的光輝,真如他所說,是無悔。「你知道,顯志愛靜愛乾淨,我替他布置了這兒,我知道他一定滿意。我去之後已吩咐人替我們把骨灰放在一起,我們共用一個瓷瓶,我們永永遠遠在一起,不分他和我。我們是快樂的,阿志和我此生不渝,真的快樂,只可惜——你們不懂。」
「我叫他們送來給你看,可惜你現在全身插管,不能自己餵人奶。」淑華走出房門。
回到家裏,她強顏歡笑,她不能讓淑華看出什麼不妥。
她知道張先剛依約按時打電話來,淑華看來平靜而快樂,這就行了,顯志在世時也疏於見面,淑華完全沒有懷疑。
「你喝酒了?」她吃驚。
靜文下意識地把身體縮在樹後。
「不、不!」淑華看來極度不安、害怕,這是無論怎麼掩飾也掩飾不了的。「真的沒事。」
「阿志的意思。他不要伯母傷心,他說伯母身體不好,眼睛差,能瞞到幾時就幾時,至少在我去見他之前我可以打電話放錄音帶,沒有惡意。」
她的敲門聲引來了樓下玩耍的兩個孩子和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他們都睜大了好奇的眼睛盯著她。
她躲在家中以淚洗面。
「媽媽,我還在夏威夷養病,張先剛照顧我,我很好。這邊的海風很舒服,天氣怡人,早晚我都在海灘散步。媽媽,請放心,病情沒有惡化,一切如常。如果好一些,我會回來看你們,還有靜文,靜文的孩子就快出世了吧?她很好,很幸福,她是好人,我知道她一定會好好照顧你。代我問候她。」他略停一停。「很想念香港,還有香港的各種食物,我會盡快回來。」說完,立刻收線。
「如果是女的,我們培養她學聲樂,她一定有你這麼好,如果是男孩,我要他像我。」信哲無限憧憬。
靜文不得不相信他們的話,卻仍然焦慮。
「這孩子跟我大概沒緣分。」淑華說。
靜文慢慢垂下頭。
「有沒有朋友在醫院陪他?」
淑華全身震動,她顯然招架不了。
找一個沒有學生上課的上午,她拿著洋傘找到那個地方去。
靜文握著話筒,心中的懷疑一圈圈擴大。
預產期前一天,她覺察不到有任何動靜,醫生告訴她:「作動時才到醫院。」但她很擔心,是不是該早到醫院催生呢?日子到了呢。
她覺得靜文沒理由搶顯志電話聽。
「傻信哲。」她輕輕拍打他,相擁人夢。
她被判了死刑。
「吃晚飯了嗎?」靜文問。
「媽媽——」靜文不滿,淑華的一切她了解,一定有什麼她解決不了的事才會流淚。「連我都不講,還有誰能幫你?」
淑華想一想,說了一些話,竟然跟顯志今天說的差不多。
「孩子——」她想問是男是女、健康嗎、像誰呢之類的話,卻又聽見「嘶嘶」的怪聲。
「他到底說什麼?」淑華催促。
不是她敏感,真的,她看見了那絲揶揄。
她被送進了急症室,只見護士醫生手忙腳亂地檢驗探測她的一切,立刻,她被抬上有輪子的病牀,幾個護士飛奔著推她人產房。剛開始她還有意識,但那永不休止、一陣比一陣厲害、一陣比一陣更頻密的劇痛令她痛不欲生,她昏迷過去。
「顯志在哪裏?」她駭然問。
十天之後,靜文開刀的傷口好了,孩子也正常,醫生簽字讓她出院。
「怎麼怪?」
「玉珊會留在香港發展,她唱得不錯。」玉明愉快地說:「以後香港聲樂界將有兩顆閃亮的明星。」
「無能為力。」那女孩沒有表情地望著她。
玉明帶來一個女孩子,看來比靜文彷彿還要大一兩歲。
老天,這是什麼?懲罰?她做錯了什麼?難道她這麼多年的苦學苦練,一輩子的前途就這麼完蛋?她不甘心,絕對不甘心。
「我現在希望第一胎是個女的,可以將來照顧弟弟。」
「姐姐要不要在我們家等他?」小女孩相當乖巧伶俐。
「有人照顧他的,你放心。」靜文想起那張先剛。
昏迷是很奇妙的一件事,腦子裏突然間變得空靈,m.hetubook.com.com現實中的一切愈距愈離,終於消失,劇痛也彷彿離她而去。
是清水灣一間村屋。
她失去了唯一的哥哥,淑華失去了唯一的兒子,就這樣無辜的。
但是,並沒有地址。這個電話號碼也沒有印在電話簿上。
她友善親切又美麗的笑容令小女孩的戒懼消失。
「上大富豪,」信哲壓低了聲音。「你知道,我是生平第一次踏進這種地方。」
「休息吧,明天還有工作。」他熄燈,擁著她很快入睡。
但是她沒有講,什麼都不講。顯志的事無論如何她講不出口。
「你想一想,最好可以講給我聽,我可以幫你,」靜文說:「學生要來上課,上完課我們再聊。」
她失去了一切。
「那個人呢?」她突然想起。
「他說汁麼?」淑華急切地問。
但是,所有的醫生都幫不了什麼大忙,她是有些進步,只限於能講一些普通的單字,聲音依然沙啞難聽。
「他若再來電話,請讓我聽。」靜文正色說:「我懷疑一些事,我要問他。」
坐的士直奔而去。
她心中很快掠過那次在酒店咖啡座遇見他們的情形,顯志穿得極時髦高級,顯志看來十分快樂——快樂,是真的。
靜文點頭。她奇怪,信哲打電話來為什麼不找她說話!明知她在家的。
九點鐘,淑華眼睛紅紅地回來,疲累得彷彿一下子老了十年。
「她終於醒了。」有人在說。
「信哲——」她很感動。
「媽媽,我帶你看醫生。」她勉強地說。
「是女兒,很好,很健康。」淑華一邊說一邊抹淚。「只是——辛苦了你。」
「希望能快點見到他。」淑華眼睛紅了。「他一個人在夏威夷也真可憐。」
淑華在背後咕嚕一句:「你到底懷疑什麼?為什麼不給我聽」之類的話,回到房裏。
打電話回中大請假,立刻去看醫生,醫生含笑對她說:「你沒有病,去驗驗尿,看看是否懷孕。」一言驚醒夢中人,檢驗的結果,真的,她有了孩子。
「很難說,我不是專科。」
「請問——跟他同住的人呢?」
「我知道你喉嚨靭帶受傷,不能講話,」玉珊是乖巧靈活而顯得有點圓滑的人。「等你好了我們慢慢談。」
「張先生什麼時候會回來?」
「出意外?生病?到底是怎麼回事?你總要告訴我才行。」
他們的住處重門深鎖,根本沒有人。
「回公司嗎?」她用沙啞的聲音困難地說著。
她的脾氣變得急躁無常,喜怒無定,弄得整個家庭裏的氣氛壞極了。信哲很有耐心,安慰並鼓勵他深愛的妻子,然而時間拖久,也會變得不耐煩。
「好。謝謝。」靜文一邊抹著冒出來的汗,一邊撐著因久站而疲累的腰。
她也閉上眼睛,一點點小事不該胡思亂想,商場該是這樣的,是她沒見過世面。
「你見過他?」
暑假來臨,靜文可以輕鬆些,不回中大教課,她不必舟車勞動那麼辛苦,她的肚子已微微突出,小小的嬰兒已漸漸在長大。
兩天之後,靜文收一封電話公司的信,信上簡單地寫著幾行字:
醫生像普通病人般檢查淑華,一切正常,除了眼睛不好,有青光眼之外,並沒有什麼不妥,他對靜文說:「讓她多休息,多吃點營養食品。」
她又回到生活的正軌上。
靜文根本在教學生,沒有出來。
「信哲去上班,他忙。下了班他會來看你,」淑華了解女兒的心理。「我去打電話給他。」
晚上,他微帶酒意地回來,相當興奮。「這筆生意做定了,」他輕吻妻子。「明天若簽約,我們可以有很大的利潤。」
靜文眉心深鎖。
靜文皺眉。對這種世紀絕症她一無所知,那只是報章雜誌上的名詞罷了,離他們很遠很遠的永不會與他們有關。但顯志——
「怎麼——發現有這種病的?」
滿月的那天,信哲請了兩桌酒,有朋友及公司裏的職員。短短一年多,公司已由兩個人增至六個,信哲很有本事。
「謝謝。」
「阿志是個可愛的大好人,卻沒有人了解他,包括他的家人,」他繼續說:「是我們互相令對方的生命完整,請相信我,乾乾淨淨,光明正大,像所有人們眼中正常的夫妻。只是為法所不容,我們被人們的觀念和眼光判罪,其實兩個人的感情,何罪之有?」
她坐在電話旁發呆。突然間聽見小巧儀驚駭的哭聲,嚇了一跳,連忙衝到淑華的房裏。為了方便照頓,小巧儀與淑華同房。
靜文被安置在一張木椅上,能坐下來,她已舒服多了,小女孩還給她一杯冰水。
「我也不太清楚。」靜文避不作答。「明天下午下課後我去看他。」
信哲也說:「花多少錢我都要醫好你,香港只有你的聲音最美。」
家,像一個凝固的大冰窖。
淑華把一切看在眼裏,痛在心裏,除了抱巧儀及餵奶,陪她睡覺外,淑華愈來愈沉默,沉默到整天可以不說一句話。
「我不知道。他——痛。」
快十一點時,木樓梯出現一個人。
村屋有兩層高,彷彿住著兩家人。樓下的鐵門關著,但廳裏的情形一目了然。右邊的牆上有道木樓梯,顯然讓二樓住客自出自入,不經過一樓的屋裏。
「我——」仍是不成語調。
怎麼會這樣?簡直晴天霹靂。
「顯志通知你的?」
這是唯一的辦法,她總不能下樓叫的士。
生孩子為什麼要開刀,是,她躺在手術抬上,腹部從肚臍以下開了個大洞,孩子從那兒取出來的。別的女人也像她這樣嗎?她完全不懂,不明白。又看見醫生替她縫針,孩子被護士抱在一邊洗澡清潔。
她想叫——又聽見一陣「嘶嘶」的怪聲,誰在這兒整蠱作怪?
「好像不許我在電話發問。說完了他要說的話立刻收線,什麼都不肯多講一句。」淑華搖頭。「我不想失去他。」
有些不對勁,是不是?
「啊!那個屋主,」淑華點點頭。「那人樣貌不怎麼樣,但對顯志極好極好,是他一直在服侍他的。」
張先剛慢慢抬起頭,緩緩轉身推開一扇房門,並示意靜文過去。
這消息在晚餐桌上宣布後,引起興奮的巨浪,信哲高興得又叫又跳,自己活像個孩子。淑華抹著淚微笑,接著又流出更多的淚。
「下次他什麼時候打來?」靜文突然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