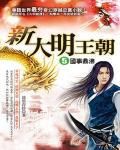第五章 昏君庸臣
「那麼呂宋怎麼辦?萬一那西班牙與葡萄牙聯軍攻打過來,那又該當如何?」
崇禎臉色已是很難聽,覺得很難再聽這老頭子嘮叨。他知這何喬遠是泉州人士,而泉州則是明朝每年出海船隻最多,出外謀生僑民最多的港口城市,是以何喬遠為家鄉說話,圖個老來虛名,回鄉之後也得些現實好處罷了。他想來想去,便認定了何喬遠目的在此,因冷冷道:「朕知道了。不過海禁一事是祖制所定,有大誥在前,朕不敢胡亂更改。你且退下!」
不顧皇帝和群臣的反感,他皺著雙眉,仍站在大殿中心,向著皇帝陳辭道:
何施二人知他說得雖是狂放,卻也並無誇大之辭,他當初與何斌施琅赴臺創業,除了十幾條小商船,百餘名手下之外,再無他物。縱是連住的地方,也是臨時搭建的茅舍。現下不過六七年光景,臺灣已有百多萬人,十餘萬軍隊,可用來縱橫四海的無敵水師艦隊,襲遼東,伐倭國、戰呂宋、奪瓊州,皆是無往而不利。地盤越來越大,手下文臣武將無數。除了行事手斷稍顯霸道,治臺方略皆以法理而行,不以那些儒生所云的王道教化之外,當真是全無缺點,當真是千百年來少有的大英雄,大豪傑。
施琅知道此番召他回來,必有大事。此時何斌有拿話試探之意,便忍不住哂然一笑,向何斌道:「廷斌兄,你何時也學得這麼狡猾!」又看一眼張偉,又笑道:「難不成是近墨者黑麼!」
張偉聽他連珠炮似的問完,一時卻不急著作答,向著何斌點頭道:「尊侯這些年獨當一面,確是長進了!」
「復甫的才幹機智,還有對天下大勢的眼光,絕不在我之下。此番攻明之事非同小可,我哪能不與他商量!僅是他給我出的『靖難』的大義名分,以用來說服那些頑固不化的老古董們,便是絕頂的好主意。」
說罷目視施琅,待他說話。
王都不顧皇帝反應,他身為工科的給事中,有建言直諫之權,再加上身為清流,犯顏直諫方顯風骨。是以不顧皇帝臉色,繼續沉聲道:「此時北方已亂,江南負擔大明財賦大半,張偉手下有這樣的強鎮雄兵,再加上其人也算得上雄材大略,陛下認為他不敢窺探江南麼?若是江南有警,則明朝危矣!臣以為,現下賊兵雖是勢大,到底是烏合之眾,陛下該當命熊文燦駐節襄陽之後,一定要南防張偉,可以不必入川。南京為大明陪都,陛下可詔命南京兵部尚書並南直隸的各總兵、指揮使司清軍釐兵,整頓軍伍,隨時關注臺海動向,一旦那張偉有甚異動,便可與熊文燦成犄角之勢。再命福建、廣東沿海督、撫遷沿海的商人百姓入內,禁絕中外貿易,禁絕洋人入境,禁絕臺灣貨船停靠,斷了張偉的財路。如此這般,方可保江南半壁。」
論起富庶,江南無一城市可與泉州相比。待他聽說張偉在臺灣大力發展貿易之事,親自攜了門生子弟,乘船出海,至臺灣參觀一番。回鄉之後,綜合其對北方及江南、泉州各處為官的瞭解,苦思良久之後,終下定決心要上疏皇帝,要令大明如同張偉那般的對外貿易,依他的想法,若是以明朝來做張偉那個彈丸小島所做的事,定然是事半功倍。到得十幾二十年後,整個南方定然富庶非常,那建州和賊兵起事,自然也會輕鬆被敉平。
何喬遠出班奏事之後,卻不說話。顫微微從懷中掏出一封奏疏,遞呈上去,崇禎打眼一看,卻見是《開海禁流疏》。
張偉點頭答道:「正是。咱們現下每年得的金銀不少,不過百姓到底不能日入斗金,有些物什,用金銀交易也是不便。比如那燒餅油條,總不能讓人用銀子結算。現下咱們用的是大明鑄的銅錢,銀賤銅貴,吃虧甚大!待我正式舉兵起事時,便開始由呂宋鑄銅,銅四鉛六,鑄成大漢通寶。內地銅銀比價是一千二百文兌一兩銀,咱們的成本比內地小得多,估計實價是九百多文便可抵一兩銀。依著一千文兌一兩的官價,仍是可以佔不小的便宜。」
他擠擠眼,向施琅笑道:「志華他近來總算是有了後嗣,心情大好之下,卻是比前陣子變了許多。若是半年之前,只怕喚了你過來,草草交代了便是。哪有閒心同你說笑!」
「那倒也不必,咱們就要對江南動手了!」
施琅點頭道:「全數都看過了。這煙廠也罷了,我不吸煙,對這些東西殊無興趣。這絲廠和布廠當真了不得!也虧志華兄想得出來!依
hetubook.com.com我看,若是朝廷不禁海運,咱們三年內,就能把江南的幾千家絲布作坊打垮,整個大明南方都得穿用咱們的絲布!」何斌卻向施琅問道:「你來臺之後,可去那些煙廠和絲廠、布廠看過了?」
只是張偉脾氣倒也是怪,屬下無論是何人拿這一番話來誇讚奉迎,皆被他罵得狗血淋頭。他常道:「我算的什麼!只不過是運氣好罷了。漫說不能與前賢相比,縱是袁督師的才略,也是遠過於我!」
施琅待張偉話音一落,便急問道:「此事非同小可!你們可考慮過整個南方明軍實力?北方明軍動向如何?關寧鐵騎若是被調過來又將如何?明軍水師雖弱,不過要是荷蘭和英國被大明說服,與他們勾結起來對付我們,又該當如何?還有,最令我擔心的便是關外的皇太極,若是他趁著這個機會,毅然入關趁火打劫,咱們不是為他人做嫁衣?縱是守住南方,可是北方也必將不保,必將成為南北對峙之勢!」
他沉吟一下,覺得此時觸怒張偉到底不妥,又道:「那張偉公忠體國,還算得是勤謹事上。賜其都指揮使司的世職,好生撫慰著,不使其滋事生亂。至於江南兵備一事,著南京兵部尚書切實整頓,著左都御史劉宗周巡按檢視,務要確保江南無事!」
他不但資歷在這朝堂之上最老,論起在清流的地位名氣,亦是遠遠超過後學晚生劉宗周等人甚多。是以此時別人皆不敢開口說話,唯有他凜然而出,直接指斥王都所言不對,開口反駁。若是別人,只怕這些言官們立時便會群起而攻,而這位德高望重的境山先生一出,那王都等人面面相覷,卻也是無法可想,只得呆立一旁,聽他說話。
見何喬遠仍想說話,崇禎忙向劉宗周道:「你來說說!」
施琅見張偉與何斌說的熟絡,由呂宋撤兵一事又扯出長篇大論來。他是純粹的武夫,對這些事絕不關心,因向張偉急道:「咱們還是說出兵的事,可成?既然那呂宋依兄弟的意思可以撤兵回來,那麼我的水師,想來也是可以回來?」
張偉皺眉道:「我只覺其中有些不對,定然是被那西班牙人尋到了我的破綻,只是我想來想去,卻是百思不得其解,也只索罷了。漢軍撤回六千來,其實也不甚緊要。留著一萬多漢軍,原本是因呂宋局勢不穩,用來彈壓當地土著。現下呂唯風幹得不錯,聽說他在當地招募了不少漢人軍人,以大刀長矛加少量的鳥槍土炮,組成了靖安軍,又拉攏了不少土人首領,分而化之來統治。再加上全呂宋島上星羅密佈的漢軍堡壘炮臺,全呂的局勢已是穩定,比之當年西人統治還更勝一籌。」
何斌見張偉神色,知道他要與施琅交代大事,因起身向四周圍侍的下人揮手道:「都下去,沒有傳喚不要進來!」
待他說完,崇禎已是覺其說得很對,正欲開口讚許其見,依其言而行。卻又見奉召來京的南京工部左待郎何喬遠出班奏道:「陛下,臣以為,王都之言雖是有理,卻只是因噎廢食之舉。」
見下人皆魚貫而退,房中再無外人,張偉乃向施琅正容道:「你說得對,雖說咱們不怕,到底還是有諸多不便。從朝議來看,現下的這些所謂的君子正人對咱們都是一肚皮的成見。想拉攏,是很難了!」
在封建社會,能控制清流輿論,就等若是在皇帝和百姓心中有了良好的口碑。張偉之所以要盡量拉攏官紳儒士,也是因為這些人雖是文弱之極,手不能提四兩,但若是在鄉里振臂一呼,卻比任何人都有用,千載之下,儒家雖不是宗教,實則已經有了比宗教更禁錮操控人的力量。此番在朝堂之上,這些清流們一致行動,所陳奏的又多是商量好的對策,比之往日空言無物強上許多,是以連崇禎亦被他們說服,那些閣臣中如錢龍錫收受過張偉大筆的賄賂,原本是要為他說話,當此之時,卻是半個字也不敢說出口,唯恐被這些抱成團的言官們當堂指斥。此時這何喬遠突然站出來說話,那些與張偉交好,又或是受過他拉攏好處的官兒們立時精神一振,一時間各人均是眉開眼笑,心道:「嘿嘿,看你們這些後學末進,如何與這何喬遠抗辯。」
崇禎早就不耐煩。若不是看他三朝老臣,年事已高,滿頭白髮仍是勤勞國事,自己也曾親下諭旨,誇讚他「老成體國」,又將他召來北京咨問國策,早便將他喝斥退下了。因皺眉向他www.hetubook.com.com道:「國家以農桑為國本,斷乎不能以工商為重。先生退下!」
張偉見他添脣咂嘴吃得香甜,卻又凝神皺眉的想著朝議的事,因大笑起身道:「尊侯莫急,這點子小事還難不倒咱們!」
各人商量之餘,都道當前明朝兩大患,一者就是滿清女真,二者便是臺灣張偉。至於農民軍,各人都是士大夫出身,現下農民起義雖然鬧得沸沸揚揚,各人卻都對官兵剿滅這場農民大起義充滿信心。
張偉嘿然一笑,道:「我管他!這些老夫子,士農工商中他們最大。除了念上幾本死書,對政治軍事,乃至人情世故,工商貿易一概不懂,偏生又以救天下而自詡,當真笑話。比如那劉宗周等人,論起品行來一等一的好,卻偏生好心辦壞事的人就是他們。那孫承宗和熊廷弼是何等的人才?鎮守關外時,偏是這些文官起勁攻擊,什麼勞師費餉,畏敵不前,硬是逼得皇帝撤換,當真混帳!我雖不能斷然將他們如宗族那般剷除,想我事事聽從他們的計較,卻也是休想了。我便是不放人,能將我怎樣?不過是背地裡嘀咕幾聲罷了!」
何喬遠見殿上諸人全然不解其意,皇帝及諸臣皆是一頭霧水,心中當真氣急。他原本亦是一呆書生,辭官回鄉之後,倒是對民生有了更直觀的瞭解,知道明廷的財賦大半來自江南田賦,而難得的一些礦山和工廠卻已在萬曆年間被神宗派出搜括的宦官黃門打擊的奄奄一息,此時雖然略有恢復,卻已是不復當年盛況。
他此語一出,不但皇帝頗是意外,便是那王都等人,亦都驚詫不已。適才王都所言,正是劉宗周與門生弟子,並各科的給事中,都御史等清流儒士商討出來的方略。各人都對明朝的現狀憂心不已,明末讀書人風氣尚佳,雖然愚腐,卻亦有東林黨這樣關心時事的政治組織,比之清朝萬馬齊喑卻又好了許多。
「正是。留下些近岸的炮船,防著走私和哨探敵情就是。水師主力回臺,準備隨時策應南方戰事!」
施琅鄭重點頭,答道:「這是自然!」又詫道:「怎地連復甫兄也知道此事?」
「陛下,臣以為南方之事,海禁為禍甚大,唯有開禁之事,弭盜安民,莫先此舉。」
卻又納悶道:「怎地你們現下涵養城府這麼深了?這才多久沒見,二位就歷練得如同宰相一般了。朝議的事,竟似全不理會,這倒真教人佩服。」
施琅聞言大悟,亦是微笑道:「原如此事,廷斌兄此語甚是有理,今朝踏破旁門,方見此間真意啊!」
說到此處,他伏下身子,向皇帝叩首道:「臣的話說完了,伏惟陛下明鑒決斷。」
他將手中摺扇搖上一搖,扇起一陣涼風,向著何施二人笑道:「做生意久了,什麼事都打算盤。其實若是攻下江南,整個南方都是我的地盤,那時候用銅錢搜括百姓的銀子,實則還是在搜羅我自己。這銅銀比價如此之高,還是因大明的銅礦開採的不好,流通時又被雁過拔毛,成本太高!」
他向一頭霧水的施琅解釋道:「漫說從朝議有結果到派出大員出巡地方,到知會地方官員準備,到真正實行,以大明官僚習氣,拖杳無能的辦事能力,你道真能將咱們逼死麼?」
他擺手道:「比若那些布廠作坊什麼的都破了產,那些失業的工人怎麼辦?」
「西葡兩國的動靜,我已聽英荷兩國的駐臺使節說了。那西人國王聽說呂宋被咱們攻下來,人也殺個乾淨,自然是暴怒異常。當即便要出兵過來攻打咱們。只是知道咱們的陸軍實力後,卻一時又犯了躊躇。海軍的實力,他雖仍在我之上,不過想在南洋同我打,還需調動本土與南美的力量,組成聯合艦隊,再加上最少三萬人以上的陸軍,方可與我一戰。失去呂宋後,那西班牙的收入降了一大截,正是財政緊張的時候,哪有錢去擴軍,哪來的錢同我打消耗戰!加之那葡萄牙人原是被西人兼併,並不心服。在南洋和澳門又有大把的利益,哪肯為別人賣力拼命?是以他們吵了個把月,卻是全無結果。以最新的消息看來,他們多半是要再想別的法子,直接和我火拼的主意,卻是想也別想了。」
何喬遠自少奇偉不凡,好學不綴,萬曆十四年二十來歲年紀便中了進士,歷任刑部主事,禮部員外,廣西布政使司,在戶部右侍郎任時辭官回鄉,身上只餘一兩白銀,為官清廉自守如此,為當時士林稱道不已。回鄉之後,整個www.hetubook.com.com福建省的官紳皆上門來拜,又著書授徒,與東林黨最早的領袖鄒元標等人被人稱為「四君子」。
三人一齊笑了一回,施琅方正色道:「自天啟四年起,我的性命便交託給志華兄了。蒙兄不棄,一直視我為腹心,施琅不是不知好歹之人。臺灣有才有德之人甚多,唯我從當年的鎮遠軍統領到現下的水師總管,一直這麼做將下來,可不都是志華兄信重於我,方能如此?兩位大哥有什麼話,只管說來。便是現下讓我帶著水師去炮轟北京,我也只管遵命去做就是。」
他嘿然一笑,指著張偉笑道:「這定然是你的計謀。讓這毛頭小子出頭,借他父親的聲望來行此事。可憐那黃尊素一世道學,兒子卻被你拐得不務正業,成日裡只顧著忙這些。舉業經書都拋到一邊。他老子來尋我幾次,只說要舉家回南京,求我通融,我也只得敷衍罷了,卻是被他攪得頭疼!」
「這倒也是。不過當真施行起來,於咱們還是大有不便就是了。」
他將心情放鬆,張偉卻已是慢慢斂了笑容,向施琅正容道:「攻打大明的事,現下除了你,便是陳復甫與江文瑨、張載文、王煊、卓豫川等人知道。今日與你商量之後,萬萬不可令他人知曉,若是現下就洩了密,其禍非小,你要仔細!」
那王都更是慷慨激昂,在朝堂上力陳道:「張偉梟雄之心,以未生之子大脯全臺軍民,便是那呂宋,因有其部駐軍,亦是鬧得沸沸揚揚,如此聲張滋擾,卻是為何?陛下今日再對其進行額外恩賞,看似能撫其心,實則壯其膽矣。唐明皇恩寵安祿山,竟以貴妃以其為子,口稱『胡兒』,明皇又以四鎮與其節度,不可不謂深恩厚德,後事如何?祿山竟反,鐵騎狂衝而至潼關,唐室一夕之間失卻半壁江山,唐皇徒為人笑耳。今陛下與寧南侯恩義不立,君臣間亦不相得。張偉海外歸來,與當年胡兒一般,遲早必反!今陛下欲以高官厚祿籠絡其心,臣恐徒為後世笑耳。」
錢謙益知劉宗周固執,不易說服。他雖是對張偉略有好感,卻也不值當為他與劉宗周爭拗。況且大學士溫體仁新得帝寵,因其「孤立、無黨」備受皇帝讚譽,溫體仁要對付張偉,想來是與大學士錢龍錫爭位,此時摻合此事,斷無好處。是以與劉宗周敷衍幾句,當即便告辭而出。
崇禎打開略略一看,見是恭楷的蠅頭小字,密密麻麻寫了滿紙,因不耐煩細看,便又張口向何喬遠道:「奏疏朕回宮再細看,你且先來說說看!」
海禁一事,自明太祖以來以然略有爭論,卻從來沒有人敢在朝堂上公然反對,若不是何喬遠身分超然,只怕立時就有人上前與他理論。饒是如此,這太和大殿上仍是議論紛紛,各人均想:「這何老頭子從南京趕來,怕是熱得暈了頭了。」
張偉嘆一口氣,黯然道:「從周王定鼎,始有華夏,有漢秦之威烈,有唐宋之富強。哪一朝的開國帝君不是勵精圖治,希圖讓百姓過上好日子?唐太宗貞觀之治時,斗米不過三四文錢,一年的列刑犯人不過二十九人,行遍大江南北不需持刃,這是何等的恢宏氣度!左右不過六七十年,天下又復大亂。如此周而復始,中國每三百年必大亂,兵凶戰危,多少典籍被焚,宮室被毀。我聽那些個夷人說起故國,竟有千多年的建築保存至今,而中國的秦漢唐宋,又有哪一朝的宮室留存下來?是以我一則絕不會盤剝百姓以自娛,亦不會自詡為聖君而不行改革之事。前一陣子我令人在《太學報》上商討興亡之事,雖然爭來辯去的沒個結果,到底大家暢所欲言,將來終歸有個制度出來,不使興亡更替的老路在我張偉手中繼續下去。」
張何二人見他著急,不禁相視一笑。那何斌笑瞇瞇開口道:「若論些陰謀詭詐的事,志華倒是與我商量。那事情我與他已經辦妥,現下只待時機一到,便可發動。你所說的起兵藉口,已是全無問題。至於軍事上的安排與打算,志華想必是與漢軍的那幾個參軍,甚至與江文瑨書信往來商量,其中的奧妙,卻是我也不懂,倒不是故意與志華一起來捉弄你。」
這次廷議過後不到半月,張偉於臺灣已是知道經過。與何斌閒談說笑時提起,渾當是笑話,倒是從呂宋回臺述職的施琅聽了之後大驚失色。見張偉與何斌二人神色自若,渾然不把此事放在眼裡,施琅急道:
施琅詫道:「這可是朝廷頭疼的事了。他們不是和_圖_書說什麼大明以農桑產國,不以工商為重,不與小民爭利麼。這些人,正好可以回去種地。」
以劉宗周為首,這群言官御史及各科的給事中,無疑是朝中清流的代表,這些人大半廉潔自愛,操守過人,很得同僚的敬重。除非是魏忠賢那樣的閹人,先天就被這些嚴峻峭刻的士大夫所拒絕之外,哪怕是朝中大佬,那錢龍錫、溫體仁、周廷儒之流,對這些清流儒生也是敬重有加,分外拉攏。
事實也確是如此,只要皇太極與張偉不出來搗亂,不管張獻忠與李自成如何蹦躂,到底還是打不過明朝的正規軍。各人商量良久,最後便決定趁著此次朝議發難,不但要令皇帝打消撫慰張偉的意思,還要施行各種辦法進行限制,縱是現在就逼反張偉,也比他在海島上好生經營,日後實力越發壯大來得更好。他們書生議政,雖然也算得上頗有見識,卻只是低估了張偉軍力的實力和張偉一統天下,重振大漢聲威的決心罷了。
何斌見張偉叉腰四顧,一副豪氣干雲模樣,因失笑道:「志華,這會兒又不是在桃園兵營校閱,何必如此。」又笑道:「初識志華時,覺得不過爾爾。不料倒當真與他幹出一番事業來!此人別的長處也罷了,唯有這眼光見識,當世無人可及。是以不論是做什麼,我何斌終歸押他這一注就是了。」
看著他青衣小帽神色匆匆而出,劉宗周輕輕一撇嘴,斥罵道:「利令智昏!」他對錢謙益當真是失望之極,原以為他貪污一事定是被人汙陷,現下想來,倒也是五五之間了。
待第二日朝會,劉宗周與禮科給事中盧兆龍、工科給事中王都等人極力反對皇帝優撫張偉,各人都道:「張偉雖未露反跡,到底是擁兵自重的藩鎮,朝廷若不早圖,反而加以祿位,卻是向張偉這樣的武夫示弱,這萬萬要不得。」
張偉從鼻孔中哼將一聲,向施琅道:「誰說江南是朝廷頭疼?那麼大一塊富庶之極的地方,留給朝廷去破壞浪費麼?當初我若不是在臺灣一手一腳的苦拼苦熬的,而是把江南那幾個省給我治理,五年內,我能蕩平南洋,二十年內,能教大明疆土擴大十倍!四十年內,我能教有太陽照射的地方,都有漢人的疆土!」
何斌聽他感嘆,卻是想起一事,向張偉問道:「聽說那黃宗羲要寫一本書,叫什麼《明夷待訪錄》,說的是君王以天下奉一人,最是無情殘暴之人,需要以文臣遏制帝權,尊士權、開言路、不以帝王一人為尊,而是與士人共治天下。這可是出於你的授意?」
他略一遲疑,又道:「只是此人很是囂張跋扈,在臺灣時就有些恃才傲物的模樣,在呂宋更是了不得。簡直就是一言九鼎,有時連全斌也要吃他的虧。還好對兄長的交代卻是從不敢駁回,比若那尋金礦一事,雖然幾個月來只尋到一個小礦,卻是一日也未曾停過。至於銅礦,已是開始鑄成銅器,並在呂宋發行銅錢了。我還聽說,兄長你打算在臺灣也發行呂宋的鑄錢?」
「陛下,臣意與陛下同。國家當以農桑之業為本,我朝立國兩百餘年,未曾與百姓爭利,也不是一樣致天下太平?現今國事紛擾,首要還在教化人心,刷新史治,撫流民,治軍備,徐圖更改之。何大人所言雖是有理,到底是劑猛藥,需天下太平,諸事順諧之時,再議不遲。」
「陛下,想來陛下還不明臣的意思。臣是說,有海禁百餘年後,海上有警竟致不能抵敵,那麼海禁何用?閣臣夏原吉原意是要節省用度,方裁撤船廠,大明不造大船,那麼倭人入侵之後,我明朝受的損失,失去的財物金銀,豈不是遠遠超過幾個寶船廠的浪費麼?」
「廷斌兄,現在臺灣便有過萬的絲布工人,每年出產的數量已足夠往內地銷售了。這絲布不比他物,只要家裡還有點餘錢的就得買來穿用。江南絲布都是幾十幾百人的小作坊,出產的辦法也不如咱們,成本比咱們高出許多。咱們的布運將過去,立時就能把全南方的坊絲織布業打垮!到那時,銀子還不是想怎麼賺就怎麼賺。」
他說到此時,崇禎皇帝已是神色難看之極,只是聽他說得有理,卻也不好發作。
張偉搖頭微笑不語,何斌卻先啃一口西瓜,向著施琅讓道:「尊侯,不必著急。這是從冰窖裡剛起來出來的,汁多沙甜,是咱們臺灣出產的上好西瓜。你在那呂宋椰子吃得多,這玩意是好久沒吃到了吧?」
崇禎帝見是何喬遠,便點頭道:「你有話,儘管講來。m.hetubook•com•com」
施琅面色凝重,勉強吃上一口,向何斌答道:「是,那邊甚少這麼好的西瓜。我已命人帶了種子過去,呂宋天氣比臺灣還熱,估計也能生出不錯的來。待長了出來,自然要命人送給兩位兄長品嘗的。」
「陛下,自太祖皇帝列十五不征之國,因倭國屢犯海禁,又由我天朝子民出海而去,成為異國之民,成了背棄祖宗的刁民,是以太祖頒海禁之令,除了留下泉州等港口開放之外,本朝制度就與那南宋絕然不同,寸板不准入海。官司也不抽稅,海關亦無釐金收入。再有鄭和下西洋後,宣宗皇帝因大學士夏原吉奏說寶船一事勞民傷財,其弊甚大。宣宗皇帝准奏,燒了南京寶船廠,就是連造船的圖紙,亦是一張不留。自此之後,我大明沒了官師,沒有能戰的水師,致有嘉靖、萬曆年間倭人入寇,四處燒殺搶掠,海上竟無半個大明的水師官兵抵擋!」
何斌笑道:「銅價高,百姓花一千二百文的銅子才能兌換一兩白銀,官府卻是只收銀子,比價卻是依著官價,生生的就盤剝了兩百多銅錢。內地百姓生活甚是艱難,辛苦從土裡刨食,就這麼著進了官府的腰包。這樣的朝廷,不亡才是沒有天理!志華能想到搜括百姓就是跟自個兒過不去,將來就是稱王稱帝的,想來也是惠澤天下,斷不至有鼎革一事了。」
「臣意以為,海禁一事好比治水。禁不如導,國家不准寸板出海,實則海上商船不絕,大半是那些敢死之徒拼命出海,販賣貨物至南洋。因暴利誘人,無法禁絕,從世宗年間的汪直,到現下的鄭芝龍、張偉,哪一個不是從這海外貿易裡得了暴利,成為富甲天下的巨富?國家與其仍是持禁,倒不如放開海禁,公開貿易,設立有司收取稅賦,則利潤不歸走私商人所有,而歸國家矣!以個人的實力,又如何同國家相抗?只要陛下開放海禁,則貿易暢通,諸事順諧,天下金銀源源不斷入我大明府庫,則可以足財賦,備軍餉,平亂民,抗外夷,其利甚大!」
崇禎聽他說到此處,仍然是不得要領,卻因這位老臣德高望重,倒也不能喝斥,只得勉強一點頭,道:「說得甚是,朕知道了。」
「不錯,若是給咱們多來幾十萬工人,多造幾千家水力工廠,漫說是中國,就是全南洋,那些白種夷人的地盤歐洲,都得穿咱們的製造的絲布了!」
見施琅納悶,張口想問。張偉擺手道:「這些你且不管。你現下要做的,便是將呂宋島上的一萬二千名漢軍,運回六千人來,以充實漢軍的實力。」
「這事情可非同小可!若是朝議之後當真遷海民,毀船廠,禁絕商人出海,咱們在臺灣的工廠雖然還能賺南洋貿易的銀子,不過內地出產的商品出不來,咱們這裡造出來的布匹、煙捲、火柴入不得內地,再加上人員來往斷絕,別說賺錢,咱們簡直就成了睜眼瞎子啦!」
張偉聽他二人說得熟絡,卻忍不住打斷兩人話頭,向何斌笑道:「廷斌,賬不是這樣算的。若咱們真的那麼做了,不給別人留條活路,只怕不是賺錢子,是大把的賠錢啊。」
「朕意亦是如此!即刻著有司商議海禁一事,勿使滋擾百姓為要。」
「這話不錯。那呂唯風確實是能力超卓,又是難得的踏實肯幹。再加上兄長派去的官學子弟和臺灣精幹官吏輔佐,還有當地漢人協助,呂宋那邊已是固若金湯了。他徵集了幾十萬民夫,在宿務和馬尼拉港修了大量的炮臺長壘,西班牙人就是來了,也最多打打海戰罷了,想要登陸作戰,我看非得有五萬人以上。隔著幾萬里海路,想也別想!」
施琅聽他顧左右而言他,不禁急道:「到底如何,你們商討的到底是何計謀,此事該當如何進行,又如何考慮我適才說的那些?志華兄,你倒是說明白些可好?」又拍腿埋怨何斌道:「廷斌兄,我一直說你老成厚道,怎地今日也來與弟調笑!」
別人不知道張偉自覺是因來自未來,知道歷史發展的方向,佔了先手方無往而不利,是以不喜人誇,各人被罵之餘,反到又誇讚張偉謙遜,不肯比肩前賢,張偉縱是聽到,卻也是無可奈何了。
「何以見得?」
輕蔑一笑,向何施二人道:「書生見識!當真是可笑之極,世宗時倭人犯境,一直到萬曆年間,朝廷何嘗停過海禁?汪直那會子,大明國力還是強盛之時,都管不了走私商人。這麼大的國家,辦起事來有那麼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