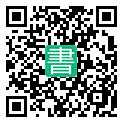第二章
二
雖然房中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拴柱的臉還是紅了。
「老鄉,把行李擱這,炕上坐(左口右背),上頭暖和。」同時很勤快的伸手接住拴柱子的行李。
「不,」老站工笑了笑:「我是滄州人,冀、魯、晉在關東算是大同鄉。」他一面談著,一面向候車室外望了望:「要投親靠友,早些走吧,天晚了人生地不熟的難找啊,請你再想想看,那家煎餅舖是什麼字號。」
郭爾羅斯前旗,只有十字型的兩條主街,由車站到十字路口,顯得燈火很暗淡。過了十字路口,一直走下去,便是警察署、旗公署、稅捐處、郵局等各種機關。出了市區,再走四十多分鐘,是去扶餘縣松花江邊的渡口。
「拴柱子。」
這是個奇異的小城,沒有城牆和寨子,沿著鐵路一長條的橫躺在松花江畔的大草原上。
「嗯。」
「小兄弟,你是剛從山東來?」
馬路似乎比兩旁的房屋地基低了一尺多,走進每家商店的時候,都得先爬上三五級台階。
「拴柱,」表舅親切的喊他的名字,把「子」字給省略了:「現店裡正忙,你先上炕坐一坐,一定還餓著肚子吧,我先給你弄吃的,等忙過這陣子再『拉』。」
現在拴柱子已經習慣店中的氣氛,炕上矮几及地上方桌,有不少的客人。
「大妮啊,」還是趙大嬸先嚷:「見見拴柱,拴柱你今年十幾啦?」
現在這個陌生的小城,整個呈現在拴柱子面前。
「先填飽肚皮。」
拴柱子似乎聽清楚了,重新捎起行李,臨走時臉紅脖子粗的:
他鼓起勇氣,用力拉開風門,剛伸進腳,一大團暖氣撲來,與外面成為兩個世界。
但他仍舊不放心,捎了行李走到車廂門口,向一位老頭兒客客氣氣的問:
「老大爺,這是郭爾羅斯前旗嗎?」
「拴柱,」對方一皺濃濃的眉頭:「我就是你表舅。」
拴柱子想這可能是老招牌,招牌越老,生意越好。
拴柱子聽從的在木椅子上坐下,停了一會兒才感到有絲暖意。
「你叫啥?」
「你是那個莊上的?」店夥扯起圍布擦油膩膩的手。
「咱要是不在站上值班,定規送你到地頭。」
他忙拾起帽子和字條,遞給老站工:
家住山東,在山東,和圖書
「唉!真是人老啦,看字橫豎都不分辨啦,咳咳,」他咳嗽著走到行李房,遞給另一個年輕小站工,小站工低聲唸了一遍,他哈哈大笑著回來:
「來啦!來啦!」
「別靠爐子太近,小心著涼。」
拴柱子看見薄暮籠罩下的車站對面,有著上下粗中間細的大煙囪,還有發電廠後面那座被雪所裝飾的土堆。
拴柱子怕他摔倒,過去扶他。對方又把手一揮:
拴柱子看到這位喝醉的陌生同鄉,產生一種說不出的感覺。他有些胸口發悶,眼睛發澀,他想不透辛辛苦苦賺來幾個錢為啥喝酒呢?怕冷嘛,喝一兩盅燒刀子暖暖身子就行了,為啥要喝得當街大吐特吐,如果是留在老家的爺娘知道了,不知有多傷心。
他不由自主的搖搖頭,表示為同鄉難過。然後進了市場大門。在右手看見有一排低矮的小瓦房,第二家門口同樣也掛了一個半圓型的小木牌,只有半張煎餅那麼大。木牌可能經過長期的風吹霜打,早已失去油漆的光澤,幾乎連上面的字都看不清楚。尤其那兩片布條,只剩寸許,風再吹也飄蕩不起來了。
「小五十啦?」
拴柱子這時才看清腮邊那顆痣和三根長毛,表舅找到了,高興得差點掉下眼淚,正要張嘴,訴說自己來逃荒闖關東投奔之意,突然裡面傳來拍擊木板的聲音。
「俺家住九孔橋,姓李,俺姥姥家是劉家寨,俺表舅叫趙——趙宗之……」拴柱子語無倫次說了一大堆。
趙大嬸有副好嗓門,一個勁的嚷,大妮卻立在那裡像塊門板,動也不動,趙大嬸伸手一拉扯:
「老大爺……」後半句卻接不上辭兒。
「是不是腮上有個大黑痣,黑痣上面有三根長毛,」老站工又滔滔不絕的說下去:「他是趙大嬸的堂弟,趙大嬸三年前開春死了當家的,便把『老趙頭』找來幫忙,準沒錯,你是找『老趙頭』。」
「唉!不碰上大賤年,誰肯離開那一畝三分地和老祖塋。拴柱,你來了,儘管放心住在這裡,別說是親戚,就是同鄉,有一盌稀的,也分給你半盌。」那口吻同王老太太見面時一樣。
「啊,大妮正月十八,是表姐。」
殺人放火,逞英雄噢……和圖書
「小兄弟,你怎麼忘了呢?啊,你找的是鴻記煎餅舖,那是咱老去的地方,咧,你是趙大嬸的什麼人?」
拴柱子讓他把行李接過去,放在長條凳上,有些激動顫著聲兒問:
「睏吧,有話明天說,」趙宗之看拴柱終於脫得赤條條的進了被窩,低聲說:「明格我著你表姐給你縫個褲叉(即內褲)。」
他從月台上爬起來,得向候車室奔去。郭爾羅斯前旗車站也是一棟灰色尖頂哥特式建築。拴柱子進了候車室,發現當中生了一個大「蹩烈器」,大塊的無煙煤,把生鐵鑄成的爐身和半截煙囪,燒成暗紅色。
拴柱子再度道謝,一出候車室,又陷於寒陣裡。沒走多遠便感到一雙腳雖然能抬起來,踏下去卻木木的,似乎不為自己所有。但他還沒有忘記站上的老站工,由老站工連想到從天津到錦州途中遇到的那位在長春經商的大掌櫃。同樣的都很和氣和樂於助人。
拴柱第一次同娘們炕對著炕睡,有些不習慣,怔在那裡。
店舖都是紅磚砌成,突出的磚柱超過房子的平頂。在房頂上面又沿著磚柱砌了一個連一個的半圓型矮牆,在每個半圓型矮牆上鑲嵌了圖案和商店字號。
趙宗之收拾盌筷,拴柱子想幫忙時,從木隔扇後面走出來一位高大健壯的女人。挽著巴巴頭,插了銀簪子,一雙改組派又尖又大的一雙腳,黃黃的大臉滿臉的笑,望著拴柱子。
在老頭兒催促間,火車又開始蠕動。拴柱子忙推開車門,慌慌張張拖了行李向車外擠。一腳沒踏在梯子上,摔了下來,幸喜月台上也有一層積雪。
「老大爺,你看看這條子上寫些啥?」
「『老趙頭?』」拴柱子從沒聽見有人用這種稱謂,他的臉覺得發燒:「不瞞老大爺,我從沒見過表舅的面。」
拴柱現在是一塊石頭落了地,並不慌張找工作。也知道乾著急沒有用,只是對新環境不太習慣。
在郭爾羅斯前旗下車的人並不多,候車的人也很少,站工很悠閒的樣兒,一雙略呈黃灰色的老眼,打量拴柱子一大陣子。然後用手理了理兩角上翹的灰白色鬍子:
「我——我是來找俺表舅的。」
拴柱子按照老站工的指示,到了十字路口便向左拐,走了一小段路,便看見一座像牌坊似的大木門https://www•hetubook.com.com,當中寫了四個一尺見方的黑字,拴柱子也不認識,他停下凍得麻木的雙腳,站在那裡東張西望。
「老大爺,謝謝你啊!」這次他把客氣詞兒學會了。
這時一陣風撲過來,如同一盆新從深井中打上來的涼水,潑在赤|裸裸的身上,那份寒意穿骨入髓。自恃年輕火力強不怕冷的拴柱子,第一次覺得那身棉衣如同單褂子,毫不抵寒,上下牙齒不由自主的發出「得得」聲音。
「老趙頭,老趙頭!……」
「你表舅姓啥?」對方望著四周正在大吃大喝的客人,想從客人當中找到拴柱子會尋的表舅。
「這是我大嫂,」趙宗之說:「拴柱,是你大表妗子。」
「大叔,鴻記煎餅舖在那裡?」
「老太爺,你也是山東人吧?」
「甭謝。」老站工接上話頭兒,看他臨出候車室門時,特別叮囑:「小兄弟,『後尾』(尾發『仁兒』音),再勸告你一句,關東可比不得山東。冷得夠受,一進屋頭件大事先脫外面衣服,別把寒氣逼進去。還有在屋外凍過了頭,不能先在旺火上烤手腳,不是嚇唬你,手指腳趾都會烤化了,變成殘廢。」
「好,」拴柱一想說好不對:「就是年頭子差。」
拴柱子挖空心思,怎麼也記不起來,表舅那家煎餅舖是啥字號,似乎老娘沒說。王家二表叔也沒有叮囑清楚,他急得伸手抓頭髮,破舊的毡帽頭被抓下來了,跌在地上,他看見帽頭裡有張紙條,突然記起,暗罵自己:「真笨的像條老草驢,把表叔寫的字條兒給忘得屌蛋淨光了。」
「大表妗子。」拴柱又紅了臉。
「他姓趙,就在這店裡。」
拴柱子顧不得一切,放下行李便向「蹩烈器」邊偎,誰知越偎越冷,這時一位年老的站工過來說:
「老疙瘩,快下車吧!」
「六月廿三。」
他走到門前,門上的玻璃同樣被暖霧所遮,看不清裡面情形。不像那家大飯莊,一個小夥計專擦玻璃大門,亮堂堂的。
「準沒錯兒,」老站工熱情洋溢的:「我記起來了,二十多家煎餅舖,只有他家姓趙,你看,」老頭兒向外一指:「就是這條大街,一直走,到了十字路口,向左拐,再一直走,看到商場,進了商場大門,第二家便是山東鴻記煎餅舖,準沒錯兒和圖書。」
首先望到牌坊旁邊,有一家店舖燈火特別明亮,門口掛了兩個像家鄉娶親挑的綢質綵燈,說它是燈又不是方型,而是個圓筒筒,下面飄著紅布條兒裁成的流蘇。
拴柱子感到餓了,便張嘴吃起來。他看見店中只有趙宗之一個人,送煎餅、送菜、送粥、燙酒,忙得團團轉,仍舊供不應求,到處聽喊:
客人們活像蝗蟲,來一波又一波,他們吃得又多又快,喝酒的也不少。漸漸散去了,店中只剩下一個醉鬼伏在矮几上,呼呼大睡,沒有許久進來了兩個人,打了個招呼便把他連抱加拖弄走了。
「俺——俺——沒喝醉,還差幾——幾盅。」他又用扭動的步伐走著,邊走邊扯起粗啞的嗓門,直腔直調的吼:
大玻璃門內有著窄窄的屏風,屏風後生著大火爐。兩面一拉溜的大炕,炕上擺了矮几,許多人正在大吃大喝。
拴柱子領教過這一帶的冷,比起長春冷得多,至於烤化手指腳趾卻將信將疑。他又想起娘常說的「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忙說:
另一條橫路,一邊商店林立,加上市場,比較熱鬧,另一邊通往糧棧區,大青磚圍子,四角有碉樓,代表了財富的堆積站。
在炕的盡頭,第二間屋子都是小房間,經過許多城市的拴柱子看出門道,那是一家大飯莊。在飯莊對面同樣也有一家店,門口不是燈籠而是半月型的大木牌,漆成古銅色,木牌下面兩角拴了紅布條兒,也在寒風中搖擺招展,不過木牌上寫的不是方型中國字。而是像春犂翻出來的一大團彎彎曲曲的蚯蚓。
「表姐表弟,今後天天碰頭,有啥臊的,叫表弟,叫表姐。」
老站工遲遲的接過去,拉著架子,瞇縫起眼,端詳了一陣子:
「既然來了關東,就向前闖,現在是冬天,就待在店裡,不缺你吃的用的,等來年開春,再給你找個路道。」
拴柱子望了一陣子,附近的這份勁熱鬧,如同集場,大概是啥「市場」了。正巧從裡走出一位幹勞力活的,扭動著兩隻腳,東倒西歪的過來,老遠便嗅到一股酒氣,拴柱子只好上去問:
「這裡並不大,算起來也有二十多家煎餅舖。別看煎餅舖是小買賣,還都有個字號,小兄弟你是找那一家啊?」
「家裡都好吧?」
火車站附近街面上的店舖並不太多,店舖和圖書門面上除了鑲好的字號之外,還掛了幌子。藥店門口有一長串木製白底黑巴巴的大膏藥,帽店、靴店,同樣掛了各型木製帽子和鞋、靴。
「十七。」
火車緩緩的停下來。
趙宗之跑到木隔扇前面,從小窗洞中,端了兩大盌熱氣騰騰高粱米粥,給一位趕車的大掌鞭,然後匆匆忙忙到小窗洞又講了幾句話,立即又拿了一大捲煎餅,一盤黃豆芽,一盌苞米粥,放在拴柱子面前。
拴柱子在家聽母親講,表舅沒有娶老婆,是個老光桿,他怕老站工弄錯了,忙加說明:
「山東煎餅舖。」
「你們同歲,幾月生?」
趙宗之移去炕上的桌子,又從對面炕上搬來行李,要拴柱和他舖在一起。這時趙大嬸,在對面炕上拉起一條藍布被單,又熄了電燈,娘兩個摸摸索索,脫衣服。
「嗯,」對方用手向牌坊內一指:「進——進市場內右——右——右手第二家,哇!」大嘴一張活像噴泉,吐了一堆,把雪溶化了,如同新出籠的年糕,還冒熱氣兒。
大妮回轉身子,拴柱子卻沒有敢抬頭,只看見大妮藍布棉袍下面,露出一截著了衛生褲,褲外套了紅毛線襪子,繡花棉鞋,可能天天圍著鍋台轉,繡花棉鞋上一層油垢,那雙腳沒有纏過,任意發展,夠大的。
老站工很熱情也很健談,拴柱子覺得出門在外,難得遇見這種好人,他突然也裝著很在行的說:
趙大嬸一說,拴柱子更加放了心,雖然笨手笨腳,也跟著收拾盌筷,隨在趙宗之身後,把碗筷送到木隔扇後面鍋台時,看見一個女人,紮了兩條長長的辮子,穿了藍布棉袍,外面罩了件大紅毛衣,臉朝著牆角,裝著沒有看見拴柱。
「我是來投奔表舅,表舅不是女的。」
店內燈火不夠亮,蒸氣和食客的廉價煙葉噴霧,使人一時看不清楚,還薰得眼睛發澀發痛。他一怔,後面的門「啪!」的一聲關上,碰痛了腳後跟。原來門上拴了一條強有力的粗彈簧。這時一位身材粗矮,腰中圍了青色圍布的男人過來。
「哇!哇!」一面走一面吐著走遠了。
「嗷,」老站工的眉頭縐起來,一副沉思的樣兒:「你表舅有多大歲數?」
「投奔誰?」對方很關切的樣兒又問。
兩人誰也沒喊誰,等於相識了。接下去便忙了一大陣子,總算把店內清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