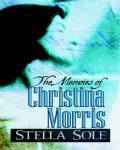十九
厭惡和憤怒在我的胸中沸騰著:「你胡說八道,英國人絕對不會像你這樣的對待婦女,他們是真正的人,舉止端莊的人,不像你這麼卑鄙無恥。」
「這並不像你想像中的那麼卑劣,這和現實生活的情景完全相同。」
我猶豫地看著他。
「是的,我沒有看見你,你從哪裡來?」
「那只是表皮上的擦傷,」那個德國人說,「我們會給你敷藥包紮,使傷口迅速痊癒,我讓你休息三天,熟悉一下新的環境。」
時間為什麼這樣無情地和我作對,幾個小時飛速而逝,去橋邊的時間來得太快。我不得不按時走出家門,開著車惶恐地上了路,遇到塞車時,我停下來,反而覺得鎮定。當車子開到橋邊時,我馬上又堅強起來。
「不要告訴任何人你在為我們工作,連你最親近的人也不能告訴。」
「不要激動,莫里斯太太!雖然你現在認為你不可能為我們工作,但是我和你可以做好朋友,你可以向我索要被你剛才拒絕了的香菸。」他怪模怪樣地嬉笑著。「你甚至可以讓我為你服務,請相信我,不會讓你失望的。可能你想知道德國人是怎樣做|愛的,我會盡力施展雄威,令你難忘,納粹是強壯而奇特的人。」
我很快離開這個寒酸的套房,走下樓梯來到公寓的門口。門口警衛不像疤瘌臉那麼粗野,他眨著眼睛微笑地看著我。我乘坐公共汽車返回到橋邊,找到了自己的車。我疲憊不堪、神志萎靡地坐在駕駛椅上,發動了汽車緩緩向著自己的家門駛去。
我沒有回答。
「請坐。」
無人吱聲。
「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我心裡問著自己,覺得活著不如死了好。
劉易斯在他父親身旁工作,對各種事態的進展瞭如指掌,難道他背叛了自己的父親和祖國嗎?我感到一種撕心裂肺的痛苦,這比知道哥哥是叛徒對我的打擊更嚴重。
「我請求你們立刻讓我出去。」我狂怒地說。
「我是被迫的,如果僅僅是為了使自己活下去,我會斷然拒絕的。」
「我們將會贏得戰爭,因為我們是強大的。」他傲然地笑著。
「你敢肯定嗎?」
我嗅到了烈性酒和黑色菸草的混合氣味,這種氣味濃郁,長時間地充斥著我的鼻孔。我用手摸了摸身子下面的草墊,又見到近處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房門被帷幕遮擋著……我漸漸明白自己現在是待在一個不通風的小臥室裡。
「莫里斯太太!請注意我說的話。」
我無奈地從床上起來,感到倦怠、沮喪、悲傷。十一點鐘時,我必須去到橋邊,別無選擇,因為好多人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穿在一條鏈索上,都會因為自己的舉止不當而陷於危險的境地……
「是,」我有氣無力地低聲說。
「抽支菸!」他遞給我一支菸。
「你沒聽見嗎?」
「別指望讓我跟你們工作,那是憑空妄想。」
「我讓你看一看這簽名的筆跡。」他接著說。
「是的,」我回答。
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屁股坐到了底,彈簧露出布面扎著了屁股,我也一動沒動。
我仰起頭,沉思著說:「哥哥如果陷了進去,他為什麼還使用我?」
「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反正我不能幫你們做,我絕對不背叛自己的祖國,我願意先死。我雖然為你們工作過,但那是違背自己意願的,是毫不知情的,我不了解我是在做什麼。」
「你想看證據嗎?」
「沒有關係,不|穿鞋我也可以走。」我氣得發喘。
「我不知道,但是偽裝很重要,你不認為偽裝是對你的一種保護嗎?」我們走進花園來到樓房,客廳比較一般化。
「你還不了解,我們並沒有遇到麻煩,遇到麻煩的是你;我們是自由的,你不自由;我是個男人,你是個女人;我是勇敢的,而你卻是軟弱的。我和你有很多差異。」
「當然。」
「好!」我點了點頭。
「是的,人們之所以稱呼我們是特工人員,就是我們不能用自己的真名字。你稱呼別人時也只能用他們的假名字,記住『萊普.惠特。』」
「聽不見我說話嗎?」我扯著嗓子喊道,「你們是什麼人?」
「你注意聽我的話,按照我所說的每句話去做,別想愚弄我們,你所說所做的每件事都逃不過我們的眼睛,我們的密探經常在你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出現在你的身邊,你不知道密探是怎麼活動的,密探可能就在你的家裡。」
我聽到身後有好幾個人的腳步聲,便本能地脫下鞋子往前跑,這裡離住房很遠,所以我不敢呼喊,但用盡全身力氣也似乎跑不快。我心裡怦怦直跳,跑得兩腿發酸,襪子也脫落了,如果摔倒了就更糟糕。
「我不抽,謝謝!」
「你說得對,然而,我覺得現在我在這裡比你在這裡更安全,雖然這裡是你自己的國家……你很天真,莫里斯太太!你想嚇唬我,以為www.hetubook.com.com我是小孩子嗎,告訴你,我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我們可以將你毀滅,」他接著譏諷地說,「我們是戰場上的人。」
每當我出去時,都感覺到身後有人跟蹤,彷彿每個人都用懷疑的目光看著我。我神經緊張,整夜翻來覆去睡不著覺。
我丈夫不贊同地搖著頭,說道:「你說你很好,可是你被戰爭所困擾,整日裡胡思亂想。」
昨天一直下著雨,今天卻放晴了。我準備吃過午飯去他家。
「我不知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沒有公寓。」
「不,你對我們很重要,我們很需要你,這就是為什麼請你為我們工作的原因。」
這時候,我想把那些駭人聽聞的事全講出來,可是我想起了那張紙條上所說的話,想起了哥哥所說的話,沒有敢張口。
「別想,絕對不可能!」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她的特工代號是三,當別人和你們在一起時,你可以稱呼她羅斯。」
「是的,但那是有原因的,那是因為你已經瀕臨死亡的邊緣,可是現在我卻不同,我身體健壯,精力充沛。」
「人們知道講出來得越多,挽救自己生命的可能性越大。面對生存與死亡,人們會失去控制的,」我明白,但是我哥哥絕對不會牽連別人的,「然而,他不願意讓你再受第二次牽連,要知道你是受到他的牽連才來到我們這裡的。你和別人講了,別人就可能被你牽連。」我再次點點頭。
「我控制不住,彷彿覺得災難即將來臨似的,我不能確定是什麼災難,只能是憑直覺。」
「我的鞋子呢?」我艱難地吸了口氣。
「因為我們有力量做。」他盲目自信說。
「好的。但是有些事我不明白,我怎麼像這樣裝扮離開家呢?」
他笑了。「雖然你血管裡流淌著英國人的血液,但不久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德國人。莫里斯太太!你現在拒絕我的香菸,到時候你會向我乞求的。」他繃起了臉。「怎麼樣?你接受我的建議嗎?願意和我們一起工作嗎?」
「誰不知道莫里斯上尉的妻子,莫里斯上校的兒媳?」
我害怕了,心想,這男人看來是說得出做得到的。我眼睛盯著他,向後倒退著,渾然不知所在,彷彿見到了劉易斯,我正待在他身邊,偎倚在他的懷裡……忽然,我又從夢魘中醒來,那個疤瘌臉的男人連笑帶嚇唬地咣嘰一下子將門關上。我一拐一拐地倒退到床邊,看見那個英俊的德國人正躺在床上,抽著菸,衝著天花板吐煙圈兒。他似乎很喜歡這場遊戲,見到我回來時,便從床上起來,似笑非笑地說:「我以為你不會回來了,這是你的地方,請坐!我們最好不要繼續耽誤時間了。」
「那家公寓裡的人知道我叫萊普.惠特嗎?」
「你不要胡思亂想,要設法控制住自己。」他規勸我。
「不要怕,莫里斯太太!你丈夫和莫里斯上校不在家裡。他們要在國防部待上一整夜,我們安排得很周詳,他們的進進出出不會受到阻攔。」
不久,他們都去了國防部。我到樓上換好衣服,走出了家門。
「每一個特工人員都有一個代號或者是名字,這名字不是你的真名字,是你的密碼名字,從現在開始你必須增強自己的記憶力。」
我不禁憤慨地說:「你對英國人並不了解,他們不僅勇敢,而且是正人君子。」
我按時到達橋邊,驚奇的是沒見到有人在那裡等候。我從車裡走出來以後,才發現那個疤瘌臉的男人,我被嚇了一跳。他取笑地說:「我嚇著你了嗎?」
「我抽菸你介意嗎?」
「事實很快會使你相信。」
幾分鐘過後,是那麼漫長的幾分鐘,我聽到了更多的腳步和說話聲,這些人是幹什麼的?我向著帷幕望去,帷幕敞開了,走進來兩個人,一個四十來歲,高個子,肌肉發達,看著比較英俊,像是一個重要人物。陪同他的是那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臉上有疤的男人。
「你該去看醫生。」我丈夫堅持著。
我懷疑地看著他,那個臉上帶疤的男人也站起來走了,當他走近帷幕時回過頭來嘲弄地向我說:「如果有事你叫我,我就守候在房門旁邊。」
「我可以喚起你的記憶,你是克莉絲蒂娜.莫里斯,愛德華上尉的妹妹。你哥哥病了幾天,準確說是病了十八天。在這段時間裡,你哥哥不能離開家,你代替他做了他應該做的工作,值得佩服呀!」
「進去!」他說。
「不,不總是這樣。」我為自己辯護。
我絕對沒有像恨他這樣恨過別人,我感覺自己是在和一隻野獸搏鬥,是赤手空拳地面對敵人,我懷著一種挫敗感無奈地將憤恨嚥進肚子裡。
我來的時候將車子停在了橋邊,從錢德爾家到橋邊有一段路面沒有鋪好,到處散布著碎石子兒很硌腳,心想:「我不應該穿高跟鞋。」
「我會到那裡的。」
和圖書「懷曼上尉可能是其中的一個。」
「我丈夫絕不會屈膝去幹這些勾當,我的公公或者我丈夫的哥哥他們也絕對不會去幹的。」
他們根本不予理睬,我繼續唱獨角戲:「你們想要錢嗎?」
這套房間有一個臥室,一個餐廳,一個客廳,一個廚房和一個浴室。臥室的壁櫥裡黏貼著廉價的低級的粗布,手提包和鞋子如同我女傭用舊了的一般……這就是我未來的新家。
我焦急和恐懼,再加上跑步,不覺汗水濕透了衣服。本來走在石子路上就夠艱難的了,何況赤著腳跑路。我顧不得腳掌疼痛,拼命地向前猛跑,後面的腳步聲愈來愈近,彷彿他們隨時都能將我抓住。
「莫里斯太太!你如果告訴別人反而會給你帶來麻煩。」
我讀著:「上校,社會安全局,莫里斯。」我閉上了眼睛,然後又睜開,心想,文件上怎麼會有我公公的簽名呢?他在我心目中是一個忠誠的可敬的人呀!這可能是德國人偷來的文件吧?是的,一定是,正是這樣。
我照他說的讀下去,眉頭蹙了起來,果然讀成了:「劉易斯」。
這時,我聽到了那個德國人的話音:「這些是什麼東西?」
「你忘記了你已經是在為我們工作了嗎?」
「把它戴上!」
我聽著他的話,真想扇他一記耳光。他們讓我經歷了如此痛苦的磨難,還假惺惺地說感謝我。這些人是什麼貨色?實在令人可恨。
我駭然地看著他。
「我明白了。」
「我是不是在床上的動靜太大了?」
「你現在明白了吧?!如果你不為我們工作,其他人的生命就有危險。你的手和腳都被捆著,已經失去了自由,你是在『元首』的手掌之中,他下達命令,你只能服從,你明白嗎?」
我覺得無望、迷惘、崩潰,我想死,最好在這個世界上消失得無影無蹤,不幸的是,自己依然活著。我可以想像出即將呈現在面前的一切,那走向背叛道路的艱辛、羞慚、悲愴。我絕望地問自己:「怎麼辦?上帝!親愛的上帝!怎麼辦?」我必須被迫地走上這條路,好像是被扔進了河裡只能隨著激流前進。
「你經常是……」
「這是你神經太緊張的緣故,記得嗎?我們住在維亞雷焦的時候,我不是對什麼事都害怕嗎?」
「首先,我們要感謝你給我們的很有價值的幫助。」
「你現在不是在你自己的國家裡。」
「那是一家小公寓,祕書不可能住公館。但是那裡應有盡有,特工代號六可以做你的男朋友,當然這只是為了體面,只是逢場作戲。」
「我認為這已經是順理成章的事了,莫里斯太太!我剛才對你說過,你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那,你走吧!」
「你真的想知道嗎?那好,我可以告訴你,所有的人都是從他媽媽的肚子那裡來的,我則不同,我是來自地球裡面,走吧!別耽誤時間了。」
「我還要讓你看一些東西。」
星期六早晨醒來時,我渾身直發抖。我想逃跑,往哪裡跑?不打仗該有多好。
我看了看自己的腳。
「一旦我離開這裡,我就告發你。」我虛張聲勢地恫嚇著說,其實內心是慌亂的。「除非你們想殺死一個毫無自衛能力的女人,納粹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我覺得我即使拒絕,他也是要抽的。他拿出一個金菸嘴,裝上一支菸,點燃後吸了一口又吐出來,說道:「我很高興你決定參加我們所做的工作,你必須注意我說的話,我們的工作是高度精確的,你明白嗎?」
「我怎麼對丈夫說呢?」我驚恐地大聲說。
「幹什麼?你們幹什麼?」我大聲吼叫。
「不介意。」
「我們希望你能同我們合作。」那人脫口而出地說道。
我將垂落至眉梢的頭髮塞進一個廉價的假髮裡。
「你不知道愛德華上尉是在為誰工作嗎?你想問我你是在為誰工作嗎?」
忽然,我好像聽到了收音機的聲音,留神仔細一聽,又覺像是有人在談話,可能是兩個人,這種粗野刺耳的聲音預示著大難即將來臨。我的心臟收縮著,渾身打著哆嗦。
我慢慢地走著,尋找著好走的路面,好不容易走到了橋頭,輕鬆地吁了口氣。這時,我突然發現有一輛不認識的小汽車停在我的車旁,那輛車是黑色的比我的大,我不知道該向前走還是該向後退,頓覺六神無主。
我驚恐地看著絲帶,沒想到這竟然是我丈夫的筆跡。
我站起來艱難地走向帷幕,他毫無表情地動也不動,我掀開帷幕,邁出一步,拉開了房門,那個臉上有疤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我知道你會找到我,你要抽菸嗎?」
「可能!但是我絕對不接受納粹的東西。」
「你可以在你的公寓裡換衣服。」
那人抽完了一支菸,將菸頭丟進菸灰缸裡,接著又點燃了另一支。他繼續說:「你應該知道,這也是基本的常識,你從這裡出去到公寓時,不能就這麼和_圖_書簡簡單單直截了當地走進去,而且你要記住自己不是莫里斯太太。」
他們迅速用又涼又濕的不知道什麼東西塞進我的嘴裡。我無法喊出聲來,不知道頭部受到猛擊還是怎麼啦,兩隻耳朵呼隆隆地炸響,然後就失去知覺,什麼也不知道了。
仍然無人答話。如果他們不是互相說話,我真的會以為他們是啞巴。我只能安靜地等待。他們中間有兩個年輕人,三個大約五十多歲。他們穿戴很普通,有一個人牙咬著上唇蔑視地看著我,他那色迷迷的樣子使我覺得噁心。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但是我知道他們不是平常人,可能是奉命來審問我的。那麼,究竟是誰下達的命令呢?我輕輕移動了下腳,看到腳上還穿著襪子,襪子磨出了窟窿,染有斑斑的血跡。我從那張還稱得上是床的鋪上坐起來,試圖將兩隻腳放在地板上,但是那難忍的疼痛使我禁不住尖叫了一聲。
「如果不只是你一個人處於危難之中呢?」他譏笑地問。
雖然我很不喜歡他,但我對他的離去感到不安。我緊張地坐在一張高背沙發椅子的邊緣上,待了大約兩分鐘的樣子,房門打開了,一個人從裡面走了出來,這人說話時我看了看他,這人不是德國人,好像是一個英國人,也是一個叛徒。
「明天你的新美髮師就會到你家裡去。」
薄暮時分,我向錢德爾太太告別離開她家。街上空無一人,因為天氣涼爽,人們都待在家裡。我幫了別人的忙心裡十分高興。
「你們究竟是想幹什麼?」
女僕走進來向我說:「早安!夫人!你睡得好嗎?」
他們包紮了我腳上的傷口,這時,我驚奇地接到了一雙新長筒襪以及我自己的那雙高跟鞋。那個疤瘌臉的男人將我送回停放汽車的橋邊。雖然他離開了我,但我仍然覺得身後有人跟蹤。回到家裡時,沒有見到一個人,所以用不著向誰解釋我去了哪裡。我沒吃晚飯就立刻躺到床上,絕望地哭了一夜。劉易斯直到天亮才回到家裡。
「他們不是叛徒。」我高聲說。
「讓我們把這事說清楚。」這個男人又說道。
「肯定不是。」
終於,我無法再跑了,大衣扣子開了,鞋子和手提包丟了,襪子也褪了下來,我喊著,叫著,覺得好像掉進水裡即將淹死,忽然,一隻手,接著又是另一隻手,緊緊地將我抓住。
「你為什麼那麼緊張?」
恐懼忽然又向我襲來,我想起了當我要求在書房裡陪伴劉易斯工作時他說的話,「好吧!但是有一個條件,不要讓任何人知道,包括爸爸在內。」現在看起來,他這話說明他也在為納粹做諜報工作,說不定那天夜裡他書寫在絲絹上的情報是從父親那裡偷來的文件上抄錄下來的咧!這太可怕了!哥哥是叛徒,丈夫也是叛徒。
「出去吧!」他的夥伴敦促地說。
「因為我不相信你說的每一句話。」
我醒來時,首先看到的是頭頂上晃動著的一個燈泡,燈泡由一根電線吊在天花板上,電線的顏色看不大清楚,燈泡的亮光十分耀眼。這時,我身上雖然疼痛,但兩隻腳反而沒有感覺。我扭轉了一下面頰,看到了一個廉價、骯髒、破爛的帷幕,帷幕上的印花兒縫隙間露出一雙眼睛,瞳孔黑而發亮像個甲蟲。
「你認識你丈夫的筆跡嗎?」他問我。
他又向我講述了很多應該做和不應該做的事,然後才讓我離開,並將公寓的地址、鑰匙以及證明我是薩拉.哈維的文件交給了我。他試圖給我一口袋錢,但被我拒絕了。
沉重的腳步聲逼近我,嚇得我上牙磕打著下牙,就在這時候,帷幕打開了,一個人走了進來,接著是第二個,第三個,總共是五個人,我一個也不認識。他們圍攏桌子坐著,一眼也不看我,好像我不存在似的。他們講著帶有口音的英語。
在飯桌上我對丈夫說:「今天我想去看看錢德爾的小孩兒。」
這天晚上我們沒有做|愛,我吃了安眠藥睡得很好。
幾乎每個人都抽菸,小屋裡彌漫著煙霧。我感到窒息,感到頭暈。猛然間,他們都站了起來,準備要走。我害怕地問:「你們想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裡嗎?」
「同誰合作?」
「那是一個將要滅亡的國家。」審問我的德國人宣告。
我打斷他們的話,問道:「你們為什麼把我帶到這裡?」
「那麼,你想殺死我嗎?」
「我會記住的。」
「我不願意聽你那些廢話了,你讓我馬上出去。」我要求著。
「是的。可是沒有人願意死,面對死亡和恐懼的人會把許多事都講出來的。」
「我明白。」
「沒有人可以強迫我,我會立即死去。」
那人昂首大笑道:「有人告訴過你嗎!是的,他們沒說錯,我是魔鬼,莫里斯太太!我可以讓你從哪裡來再回到哪裡去,你看到我的兩隻手了嗎?」他將雙手伸m.hetubook.com•com向我面前,活動著手指。「這兩隻手很結實,和別人的手不一樣,摸起來像天鵝絨般的柔軟,但當某人使我發怒時,這兩隻手就會變成鉗子,將某人的脖子緊緊鉗住,讓他來不及為自己的靈魂祈禱就立即死去,這很有意思吧!嗯哼!你想試一試嗎?」
「那麼,我是一個英國人。」
我試圖站起來,雙腿劇痛迫使我坐了下來。
「你是誰?你不是英國人?」
我沒有回答。
「現在我派人把你送回家裡。」德國人的話音打斷了我的思緒。
「我不明白。」
「走吧!我不阻攔你。」
「如果強迫你做,你怎麼辦呢?」
「我女傭瑪麗的新降生的侄子。」我解釋著。
我用疑問的目光看著他。
「我害怕戰爭和戰爭帶來的後果,我心神不定,憂慮不安。」
「你以為我知道嗎?」他嘲弄地回答。
「他們會將他處死。」
「今天晚上先吃點安眠藥,觀察一下再說。」
「代號三需要和你連繫時,是在上午十點鐘,要記住是上午十點鐘。代號三沒去你家的那一天,你就要像今天一樣喬裝改扮到我這裡來,到時候別人會給你衣服的。在外人面前,你充當我的祕書。」
我由於不能相信任何人,便轉而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會知道我的遭遇和苦衷。每次我擔驚害怕地完成一項違背良心的任務時,都覺得後悔,心想,下次絕不能再幹,可是我又繼續幹了,又經受一次新的折磨。這折磨變得越來越沉重,幾乎將我軋成齏粉。
「我等著,」我說。
「你現在相信了吧!」
我聽著這個德國人說的話。
「你的確夠天真的。」德國人斬釘截鐵地說。
我讓他繼續說下去。
「將這個眼鏡戴上,這看起來像墨鏡,但不是墨鏡。」他又遞給我一件兔皮外衣。「這不是你平常穿的那種外衣,你現在不是莫里斯太太了。」
我沒有回答,假裝著不舒服的樣子。
「獅子終究是凶猛的野獸,牠是叢林之王。你知道是為什麼嗎?因為牠是叢林中最厲害的野獸。」
他和氣地看著我,說道:「我是德國人。」
接下來的三天,我度日如年,哪裡都不想去,什麼事也做不下去。
自從納粹讓我看了劉易斯叛變的鐵證之後,我不能不以叛徒來看待他。當他向他父親說「我們將贏得戰爭」或者「我們將粉碎第三帝國」時,我禁不住這樣想,他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偽君子。
「你很迷人。」
我恨撒謊,但是我不能不撒謊,我必須裝模作樣。
「這個孩子是誰?」公公問。
「這人是誰?我需要耐心!」我叮囑著自己。「現在我要的就是耐心!」
「證據?」
「我給你解釋,比如,英國人知道愛德華上尉在為我們工作,那將會產生什麼後果?」
「我認為我是在為英國工作。」
「不要緊張,這無補於事,何況我不是跟你談話的那個人。」
「你有什麼心事嗎?」我的丈夫問我。
「你不懂密碼,但是你可以看看簽名。」
我不能說話,感到頭昏腦脹。
「現在我們可以走了,你穿得很體面,連你丈夫也認不出是你了。」他坐在方向盤後面發動了車子,一路上他無話找話,盡扯些閒篇。不一會兒,我驚奇地發現我們的車子已經停靠在一個豪宅的門前。他遞給我一個黑色的小皮包,我們從車裡走出來。
他搬來一把椅子,向我說:「請坐在這裡,莫里斯太太!這把椅子更舒服些。」
「我留下來,我和你談話。」那個英俊的男人說。
忽然,我意識到現在是夜裡十點鐘了,離開家裡的時候是剛過中午。
「是的,跟我來!」
「萊普.惠特?」我詫異地問。
房間只剩下我們兩個人,那個英俊的男人看了我幾眼,然後,搬了把椅子靠近床邊坐了下來。
錢德爾的孩子已經生下來三天了,我還沒去看望。今天,我帶上小孩衣服和一些錢準備去他家。他們住在倫敦北部工人區域,我的女傭瑪麗說她每月都從自己的薪水裡拿出錢幫助他們,但他們仍然過得很窮。
我從皮包裡取出手絹擦拭眼淚,用手向上推了推他們給我的墨鏡。
我乘坐公共汽車來到被指定的公寓,走進房間後,立即將假髮和墨鏡摘下來,然後把有關薩拉.哈維的所有文件放進梳妝臺的抽屜裡。
他站起來又拿來一些文件。
「不要照他寫的讀,將每隔三個字母的頭一字母放在一起然後再讀。」
「你們可恨。」
「有人告訴我,你就是魔鬼。」我嚷道。
我倒臥在床上,兩腳疼痛難以站立,只覺得筋骨斷裂,渾身無力。我想到,哥哥是不會為納粹工作的,他是一個英國人,是一個愛國者,不是一個傻瓜,是個受過教育的軍官,這些事怎麼會出在他身上?他不會接受金錢的,那是為什麼?是什麼導致的?我哥哥變得很殘酷而不像他自己了,在遇見那個奧地利女人以後變了……我想到的事又立即被否定https://www.hetubook.com.com了,可能是約翰為納粹工作,不,不可能是約翰,我絕對不會認為他可能是……
「莫里斯上校,他的兒子,還有別人。」
「當然,」我開始緊張起來。
我跟隨他來到被灌木叢半掩著的車子面前。
「你們需要對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價,你們會後悔的。」
「我想這會兒你是真的明白了,」納粹接著說,「你會很快知道我們會成為好朋友的。」
坐公共汽車到倫敦北部很方便,下了車就是錢德爾家。但是我害怕有人跟蹤,所以還是自己開車前去。
「從今天開始,你不要再用克莉絲蒂娜.莫里斯這個名字了,你現在的名字是萊普.惠特」。
沒有人回答。
我嚥了口唾沫,變換了一下姿勢,聽到他說這些話覺得非常厭惡。
這男人蹺起二郎腿,兩眼緊盯著我,問道:「你想抽菸嗎?抽菸可以使你的神經鎮定。」
「還好,瑪麗!」我說。
雖說如此,但我覺得這對我說來是一種災難。現在,我必須聽下去,對我來說,他所講的都好像是發生在電影和小說裡的事。我不敢相信自己在他們的迫使下能演好這場戲。
「你認為我發瘋了嗎?你會背叛你的國家嗎?」我氣呼呼地問。
「我忘不了。」
他嘴角掛著挖苦的微笑:「誰?你?不要使我發笑,你現在是在我們的手心裡,我們說什麼你就得做什麼。」
「你說的是我哥哥嗎?」
我點了點頭,知道自己已經掉進了陷阱,愛德華說得對,沒有走出去的路。
「今天是星期二,」他接著說,「星期六上午十一點鐘,你要到達你停放汽車的橋邊,你要是不到,你會知道發生什麼樣的後果。」
我的周身在抖動,吃驚地問:「其他的人是誰?」
「很好,你到這裡來是接受我的指令的,我會告訴你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他停了停又說:「開始,你會覺得有困難,不過你會逐漸熟悉的。你在執行任務的時候一定要裝作無事人的樣子,不能流露出一星半點驚慌神色。你知道自己是個特工,可別人只知道你是個普通人。別的特工和你連繫時只是知道你是萊普.惠特。你工作時必須忘記真實的自我,時刻想到自己是一個祕書,向和你接頭的特工表明你是一個牢記自己角色的女演員。」
我一拐一拐地跟著他走出房間,那個像惡棍似的疤瘌臉仍然站在那裡。我跟著那個英俊的男人來到一個有柵欄的房間,裡面放著一張桌子,四把彈簧椅子,兩個櫥櫃,桌子上放著一個錄音機和一盞檯燈。
「你明白我不是在撒謊了吧?」
好幾天我都沒能和哥哥說上話。我知道他在倫敦,是故意想躲開我。約翰也是想躲開我。我覺得他們的舉止行為不正當,但是又無可奈何。
「克莉絲蒂娜.莫里斯沒有,但是,萊普.惠特有。」
「你胡說!」我大聲嚷道。
疤瘌臉的男人走了出去。
別人都恭維地向那個英俊的人打著招呼,可是他卻表現得漫不經心。
「你們顯然不認識我。」
「那麼,你是不是接受了我們的建議?」
我往我的車裡鑽,他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說:「不,不是坐你的車,把你的車停在這裡,坐我的車,請吧!」
「我看你有些不耐煩。」
「我是一個德國人。」
「我是否需要一直偽裝下去?」
我坐進了後車坐。在他坐進駕駛椅之前,他從後背箱裡取出一個包裹,將包裹打開。
他走向櫥櫃,打開倒數第二個抽屜,拿出一個刻花木盒子,拉過一把椅子靠近我坐下來,然後,將木盒子放在桌子上,掀開盒蓋,取出一捲黑絲綢。這使我想起那天夜裡劉易斯趴在桌子上在黑綢子上寫字的事,愛德華也讓我送過黑綢子。
他臉上掛著嬉笑向我走過來,手裡拿著一架帶有燈泡的小機器,打開了燈,將綢帶放在鏡子上,慢慢拉動著綢帶。
我怒火中燒,厲聲說道:「你不知道我可以把你抓起來嗎?」
因為椅子不夠,那個帶傷疤的男人就坐在床沿上,兩隻眼睛盯著我說:「我喜歡見到你,莫里斯太太!」
「德國人,一個納粹。」我驚恐地說。
頓時鴉雀無聲。
「不知道,你在那裡使用的名字是薩拉.哈維。」
「你看這是不是莫里斯上尉的筆跡?」他的話音裡夾帶著勝利者的傲氣。
「我遺憾地告訴你,莫里斯太太!你已經是我們的人了,是元首希特勒手中鏈條的一環。」
我坐在他搬來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對面。
「這不是我丈夫的名字。」我鬆了口氣說。
「你不了解情況。」
當我離開這座豪宅時,一個可怕的稱呼在我的腦海裡連連衝撞:「你現在變成了一個間諜……一個間諜……」我意識到我背叛了自己的祖國,眼淚像湧泉般地流淌出來。
「好!」我丈夫說。
「我期待著你能向我解釋清楚。」我竭力掩飾著內心的恐懼。
「你有一個美髮師是很正常的。」
「我會牢牢記在心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