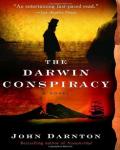第十二章
「道理也很明顯,你擋了他的路。你是他實現自己苦心追求的目標道路上的一個障礙。」
「給我再買一杯麥芽酒,我會把你的建議放在心上。」他說。
過了好幾個星期,小獵犬號才結束在附近的勘測工作回來。它繼續朝南行駛。船上的人非常悲痛,因為有三個水手在逆江捕獵田鷸的途中病死了。查理有他自己沮喪的理由,但相形之下太微不足道了,他也很難說出口:當他在碼頭等船的時候,他看見麥考密克的行李堆在那裡準備登船,外加一個鸚鵡籠。
「我看到你帶走了所有的行李,」查理說,「你原是想在岸上住很久吧?」
事也湊巧,幾天後,兩人與皇家海軍艦艇薩馬朗號——與他們共用一個停泊區——的一位叫佩吉特的船長一起進餐。而這位客人正好幾乎不會談其他的,就會講他聽說過的種種奴隸制駭人聽聞的暴行。他講了一個又一個——什麼有的奴隸被打得只剩一口氣,什麼家人分散被賣給不同的主人,以及逃跑的人被像狗一樣追捕等等。
他站起身,把杯子砸在牆上。
菲茨洛伊返身退到主桅影子下,他的臉上籠罩著憤怒的陰雲。
查理忍不住露出滿臉的沮喪。菲茨洛伊俯身過來拍了一下他的胳膊。
「很好」,他對盧姆伯說,「請別再煩心那事了。回到英國後,我們會把它們全部理出來。」
說完,他怒沖沖地走了出去,扔下查理目瞪口呆地坐在那裡。他馬上跟著出去了。弄成這樣的場面,他難以再留在那人的房裡。他剛一出去,就看到菲茨洛伊在莫須有地痛罵可憐的惠格姆。這位首席高級軍官只得克制住自己,滿臉通紅地盯著甲板。
他雇了一個叫西姆斯.柯文頓的船艙服務員幫他打理他的獵物和剝製標本。既然有了一個同伴和密友見證他的英勇業績,他再也閒不住了。他激|情澎湃,心中充滿了二十四歲的信念:偉大的功績和發現在等著他。
「如果你頑固不化,還這樣看周圍的人,那我就覺得我們沒有理由繼續一起進餐了。」
「誰知道呢?也許是名聲、社會地位之類的人們所企求的虛榮和無價值的東西。」
查理迫不及待地上了岸。當他從小帆船跨上碼頭,他的雙腿在堅實的地面上直搖晃。他在狹窄的街道上閒逛,然後朝中央廣場的大教堂走去。在密集的人群中,他感到悵然若失。他仔細地看著那些人群:有戴著錐形帽子的牧師、乞丐、大搖大擺的英國水手和背上披著長長的黑髮的漂亮女人。
「你指的是我們的船長?」
對照而言,查理感到高興的是,自己不必為社會地位而操心。他能純粹出於認識論的目的,專心一意地投身於科學研究之中。他告訴自己說自己不是個勢利的人——他為自己善於和各行各業的人打交道而自豪——但他覺得很不可思議的是,在和傑米.巴頓這樣的野蠻人在一起時反倒比與自己的同胞在一起更要舒坦。
查理抑制不住心中的高興。
菲茨洛伊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講起一次去拜訪一個大莊園主的事。為了證明自己的奴隸並非過得不幸,莊園主一個一個地把他們叫來,問他們是否願意獲得自由。
查理盯著他,覺得很好玩。他已經習慣了他的抨擊。
說罷,船長吃完自己的最後一片羊肉,喝光酒,扔下餐巾,似乎是要終止對那一問題的所有討論。不久,佩吉特也回到了自己的船上。而查理正在怒火中燒,他不能讓這個話題就此作罷。藉著白蘭地的酒興,他問船長是不是不能理解自己對一種制度——把人降格為動物——的極大憤慨。
「沒問題。」
但沒過多久,他看到的景象讓他覺得自己撞進了一個比船上的一切都更讓人難以忍受的地獄:非洲奴隸,黑如鍋底,被人肆意驅使。他們赤|裸上體,在港口的勞工船上,上身匍匐在船槳上拼命划著,頭上是皮鞭在飛舞。靠了岸,他們用頭頂起大包的貨物,急匆匆地上岸去追上他們走了老遠的主人。
「記住,你得設法自己掌權。這是在這條沒有王法的船上唯一的生存之道——否則船長們會像磨石一樣把你磨成粉,然後把你灑在風中。」
「是這樣的,先生。影印文件上要求只寫一個名字,因此我就寫了你的名字。我在想這樣好不好。」
查理沒了反駁的話。
「不,不,不。證明你的價值,展現你的才華。」
「我還遠夠不上為奴隸制和*圖*書辯護」,船長說,「但我所不能贊同的是你堅信奴隸必然過得不幸,是對上帝賜予他們的命運的踐踏。在我們家的莊園上,我看到佃農們因為有人為他們的安康操心而無比感恩戴德。在我看來,一個善良的主人對於一個生活無有著落的人來講,應是一大福祉。這一點,他們很多人都會承認。」
「是因為你和你那該死的標本,與船長發生了爭吵。他指責船長偏護你,你在船頭掛什麼網都可以,而他作為船上的高級醫生,卻不讓他執行自己的搜集職責。事情鬧僵是在兩個星期前,當時你讓船上的木工幫你郵寄那些瓶子和盒子。我聽說爭吵得相當激烈。」
他讀了一遍日記,皺了皺眉,把它撕下來扔進了廢紙簍。他給姐姐卡瑟琳寫了一封信,講了一大堆東西,並告訴了她麥考密克下船的事。他只簡單地說了一句:「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損失。」
查理花了整整一週時間把他的標本進行打包和裝箱,並託運給英國的亨斯洛。接著,他又急於去內陸地區考察。查理在那裡正好遇到一個叫帕特里克.倫農的愛爾蘭人,於是便與他一道騎馬北行,到他大約一百英里外的咖啡種植園去。
「絕對。事實上我曾聽他說,他難以忍受與意見相左的人為伍。實際上他說簡直不願與一個道德觀念和他差距如此大的人共同進餐。」
「見你的鬼去吧」,他衝口說道,「你幾乎掩飾不了你的想法,覺得自己比周圍任何人都要高尚。你這種輕視態度不適合你的身分。」
軍艦剛剛離開,當地的警察局長就十萬火急地划船過來。他攀登上船,請求菲茨洛伊援助。黑人士兵奪取了軍火庫,全造反了。查理站在船長旁邊,感到血液沸騰:終於有了一個戰鬥機會!
「是的。上週他去了站上的海軍部,獲准乘船回他在泰恩河岸的家去。今天一早,他就提著背包下船去了,肩上還托著一隻鸚鵡。」
第二天早上,查理與幾乎和自己同樣興奮的麥考密克又回到那裡,同去的還有扛著鶴嘴鋤的柯文頓和一幫船員。他們工作了一整天,只停下來吃了些鹹牛肉和餅乾——要是其他人願意,查理會樂得那也不用吃。黃昏時分,兩位科學家討論著擺在沙灘上的二十根骨骼。兩人一致認為:它們是已經滅絕了的史前動物。雖然它們和現在的動物有相似之處——比如普通的野生羊駝,但是它們卻是野生羊駝的二到三倍大。查理認為,有一個——是花了好幾個小時才挖出來的一個顱骨——屬於大地獺屬期的動物。他曾在一次課堂上聽到講過。但麥考密克卻認為它可能屬於巨爪類動物時期的動物。他們都絞盡腦汁去回憶在愛丁堡學過的每一點知識。他們筋疲力盡地坐在沙灘上,臉上是一道道的泥痕,鬍子上糊著泥漿。他們先是微笑,接著放聲大笑。查理像一隻巨大的樹懶一樣跳上跳下;麥考密克則拿起一塊沉重的顱骨,把它架在頭上,蹣跚地走來走去。船員們哄然大笑。在返回的途中,查理望著他的同伴,心裡想:他還不是那麼壞嘛。
「不知道。」海軍上尉副官回答說。
「真見鬼。」他自言自語道,「我原以為擺脫了那個可恨的東西了。」
「我見過。」
查理舉杯慶賀自己的好運。
「有道理。但怎樣做?」
「是什麼原因?」他問道。
「美妙之極。但我們沒有姊妹船啊。」
晚上,查理在日記本上傾吐了自己輕快的心情。「我覺得去掉了肩上的一塊重壓,」他寫道。「那人的爭辯也有些道理——按習慣講,隨船醫生就是船上的標本搜集者。但他自己定位為我的競爭對手。我常覺得他總想破壞我和船長的關係。而且我也的確讓他把標本和我的一起寄了回去,他幾乎對我沒一點感激之情。總之一句話,一個令人很不愉快的傢伙。」
兩週後,菲茨洛伊發令停止發掘。小獵犬號啟航的時間到了。他急於要繼續他的勘測工作和他自己早有安排的項目——把兩個雅馬納印第安人送回到他們的出生地,並在世界的那片凋敝的土地上播下基督教的種子。
當他迎面站在這充滿著無數新奇和異域風貌的大自然面前,他想,我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天地。他瞧見蝴蝶順著地面飛行,蜘蛛在空中結出像船帆一樣的網,蟻群幾分鐘時間就把蜥蜴和其他動物消解成一具具骨架。他沿路睡的是當和*圖*書地人的草蓆——伴著知了和蟋蟀的奏鳴入睡,聽著猿猴的嗥叫和綠鸚鵡與眼睛晶亮如珠的紅喙巨嘴鳥的尖聲鳴叫醒來。他驚異於成百上千的蜂鳥,下馬那會兒工夫就能打洞鑽入地下的犰狳,無心而靈巧地把自己裝扮成蠍子的飛蛾,以及螢火蟲求偶的信號。
「如果你當了船長,我希望你會給我所有隨船醫生應得的禮遇,包括獨立負責標本搜集工作,並公費郵寄回國。」
聽到這話,菲茨洛伊勃然大怒。
不知怎的,傑米.巴頓看到這些骨頭特別興奮。他在周圍走來走去,一有機會就去摸一下。據有人講,他曾說自己以前也見過這樣的東西,就在他們村莊附近。查理很驚訝。他覺得這個野蠻人非常聰明,很善於吸引別人的注意。
他在叢林中劈路而行,看見從枯朽的樹幹上發芽的蘭花、西班牙地衣和像繩子樣懸掛在樹枝上的藤本植物。他在濃密不見天日的樹葉下穿行,猛烈的陣雨也濕不了他的衣服。他肌肉發達,頭腦清醒,身體健壯而黝黑。
查理感到一驚:這樣說來那些化石只是以他一個人的名義寄給亨斯洛的。他心裡一陣興奮,接著又感到一陣愧疚。他不能獨享這一榮譽,必須是兩人共有的。麥考密克畢竟是第一個看到那個地點的人,儘管查理確信自己也很容易就會看見那個地方。不過現在沒什麼辦法了——所有權和功勞問題得在以後再解決了。同時,這些化石已經運往劍橋安全保存——那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且毫無疑問,以後還會有更多的化石。
「麥考密克?」
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發顯得匆忙而又繁複。查理急著要把所有需要寄回去的骨骼運上一艘將起程去英國的輪船。而同一天,小獵犬號則要到河的對岸去補給物資,包括瓶子、保存標本用的酒精和他自己訂購的靴子。因此,他安排在當地居住時間較長的一個英國人愛德華.盧姆伯幫忙處理這些郵寄工作。兩天後,查理回來付錢給他時,得知運送的東西已經按期出發了,終於放了心。
查理幾乎難以自抑。他問菲茨洛伊難道不覺得,當一個奴隸當著他主人的面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他很可能會尋找他認為主人喜歡聽的話說嗎。
年輕的金轉身朝向牆壁,擺成一個見過世間太多險惡的人沉思的睡姿,最後說了一句:「總之,我贊同拜倫的觀點。我要說讓所有的人都見鬼去吧。」
「那人總跟我作對,我也說不清為什麼。他是個蠢驢,喜歡恪守細枝末節,簡直不配叫做自然科學家。而且他很庸俗。一句話——儘管我非常不喜歡那樣的字眼——他純粹是個下賤胚子。」
當查理遞過去一疊鈔票時,盧姆伯問了一個問題:「順便說一句,先生,貨物運走之前我就該問你的,我注意到你們有兩個人——你們稱自己什麼?——博物學家。你和另外那個人——他叫什麼鬼名字呢?」
「現在他還是嗎?」
「我贊同這一觀點,但恐怕達爾文先生不會同意的。在這一問題上,他是個狂熱分子。」
「還有一件事。」
「哈,那就是你得動腦子的地方。你和菲茨洛伊很熟——讓他買一艘。想法說服他,告訴他為了勘探的成功,必須要有一艘姐妹船。告訴他沒有它,我們完成不了測探工作。他準備了那筆錢,也有那個想法。你要掮開的只是一扇沒上鎖的門而已。」
就在同一天晚上,麥考密克與沙利文——船上唯一沒有拋棄他的人——坐在泰布爾霍特酒店的酒吧喝酒。這個前隨船醫生一臉的疲憊——四隻偌大的罐子空空地放在面前——他不確定酒店老板會不會同意給他一個房間過夜。那隻鸚鵡在旁邊桌子上啄著麵包屑。
「當然了。還得考慮到另外一點,」麥考密克陰沉地說。
「是什麼?」沙利文問道。
沙利文承認:這人說得有道理。
「明擺著的。」
查理沒有回答。他想起他曾認識的一些博物學家,他們借助自己的研究攀上社會地位的階梯。如果一個人搜集了數量可觀的標本,博得一個專家的名聲,他完全有可能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甚至獲得爵位也未必不可能。
沙利文沉默了一會兒。這個計策可能有效,而且不管怎麼說,也不會有害處。就算是請求被否定,這也可表明自己對這項任務的熱情。
「但要m.hetubook•com•com怎樣才行呢?」他追問道,「位子已經被上尉們占滿了。不知要等到啥時候了。」
佩吉特船長承認,有的主人對待奴隸還算仁慈,但即使是他們也對奴隸們的慘狀視而不見。他想起一個奴隸曾說過的一句話:「若是我能再見到我的父親和兩個姐妹,我會感到非常幸福。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們。」
沙利文在迷濛的煙霧中點了點頭。「自己掌權」那幾個字激起了他的興趣。
「哦。」
「但如果隔著一些距離的海水,事情會好辦得多。」
「一點不假」,他回答說,「誰也不知道標在航海圖上的考察會要多久,是吧?」
查理想,馱運貨物的動物也比他們強。他驚愕地發現,那些奴隸驚惶地急忙給他讓開道,眼睛看著地面,不敢與他對視。剎那間,所有那些他曾在喬斯舅舅的餐桌上看到過的對奴隸制的抨擊,他曾聽到過的那些激烈的言論,所有那些狂熱的召喚,都如洪水般湧了上來,讓他血液沸騰。他想起了約翰.埃德蒙斯通。那個獲得自由的奴隸非常友善,好幾年前就在愛丁堡教會了他剝製標本。他是如此地憤慨,這種正義的情感充滿了他的全身。
小獵犬號從英國出發兩個月後,在二月份一個潮濕悶熱的上午九時到達了南美。它沿著滿是茂盛的香蕉樹和椰子樹的海岸駛過一片平靜的水域,靜靜地進入巴伊亞的古老城鎮薩爾瓦多腳下的萬聖灣。
他們環顧四周。周圍全是巨人的骨骼、象牙和磨圓了的背甲骨。它們從土裡伸出來,好像是一次滑坡時埋在了那裡。這些屍骨葬在一個天然墳場中,變成了骨骼化石。它們很可能是上古時代的動物骨骼,因為它們遠比現今地球上的動物骨骼大。整個下午,他們都在這個墳場上忙碌。他們挖出巨大的遺骸,把它們堆放在狹窄的海灘上,然後回到船上。
「喂,搭個手幫我搬一下我的戰利品行不?」
「哈,不過他們可能勸我回去,尤其是如果天邊再有一艘船的話。另一艘船意味著另一個醫生鋪位。」
沙利文盯著桌子對面。「那於你又有什麼好處呢?你都不在船上了。」
「我的天。你們猜是什麼?」他叫道,「像一根龐大的腿骨吧?你們覺得可能嗎——會是化石嗎?」
「也許是吧」,查理回答說,「不過大自然只向她所青睞的人微笑。」
「實際上,韋奇伍德家在反奴隸制協會中非常活躍。他和他們有直接交往,而且通過他妻子,他也與他們有連繫。他們設計了一種陶瓷的奴隸小男孩,套著鎖鏈,跪在一排字下面:
查理不得不承認菲茨洛伊的話不無道理。
他與粗獷的加烏喬牧人——他們非常羨慕他的槍法——一道騎馬,並向他們學習扔流星錘——用生牛皮連接三塊石頭做成。一天,他用那倒楣的武器把自己的馬給絆倒了。那天夜裡,他抽著當地捲菸給他姐姐寫信:「那些加烏喬牧人放聲大笑。他們叫道,他們見過各種動物被擊中,卻從未見有人把自己打倒過。」
金跳下陽臺,舉起一個木箱,給他講了個好消息。
儘管有些喜劇色彩,但這次冒險經歷卻激發了查理的豪情。船南行四百英里到達布蘭卡港,他們便開始對那裡的海岸線進行認真的勘測。他則白天都待在陸地上。少年時的遊樂給他帶來了不少益處。他縱馬在潘帕斯河流域多風的平原上,射擊鴕鳥、鹿子、豚鼠和野生羊駝。他給船長的飯桌帶回新鮮的肉食,也贏得了船員們的感激——不再是乾牛肉與餅乾,而是沒有去殼的烤犰狳。他熱愛戶外生活,甚至冒險到內陸地區去——據說那裡野蠻的印第安人會折磨和殺死外來的旅行者。
「哪裡,只需學學菲茨洛伊船長就行了。」
那天晚上,查理談的全是下午的發現。他推測著那是些什麼骨骼。他查遍了動物學、生物學和古人類學書籍,先提出一種理論,隨後放棄了,又提出另一種理論,接著又回到原來的理論上去。最後,吃過晚飯,菲茨洛伊看著他朋友那狂熱勁,覺得很有趣,於是把他推出房門說道:「看你這著迷的樣子,今晚很可能整個夜裡都要走來走去反覆琢磨這個問題了。我要求歇口氣。要是那些骨頭活過來和-圖-書了的話,可得叫醒我。」
「麥考密克先生。怎麼啦?」
幾分鐘後,醫生本人出現了。他臉上掛著愉快的笑容,那樣子好像什麼事也不曾發生過似的。
「難道我不是一個人、一個兄弟嗎?」
「肯定嘛,那麼有名。」
他們聊了一些時間。突然麥考密克用心不良地放低聲音。
那天晚上,查理遊玩回來。他發現菲茨洛伊話特別少,整個晚餐兩人都沒說話。他又一次覺得自己成了船長陰沉的目光審評的對象。
「要是他們不投降的話……」他懊悔地對麥考密克說。麥考密克腰帶上掛著一把短彎刀,看上去比查理預想的還勇猛。他們一起喝了些朗姆酒。
「而且我怎麼也搞不明白他為什麼那樣不喜歡我。」
回來的時候,他遇到正悠閒地把腳擱在陽臺欄杆上休息的金。這位見習船員遞給他一杯朗姆酒,興高采烈地看著查理那些壓得倒一頭運貨騾子的標本。
「你不知道嗎,」麥考密克說,「我們的達爾文先生一家人是站在廢奴運動最前線的?」
「喂!」金繼續說道,「他的不滿也有一點兒道理吧?」
船進港後,查理信守誓言,在科爾科瓦杜山腳下的博托福古城郊租了一個農舍。他與金和奧古斯塔斯.厄爾住在一起。厄爾是輪船上的美術家,對這個城市非常了解。他領著他們在城市中心區域硬結的低窪地帶進行了一次庫克式的探險之行。
他們沒再說什麼,只是默然地把杯子一碰:滴酒不濺。
的確如此。一個九月的下午,當查理、菲茨洛伊、麥考密克(仍是那麼的友善)和另外兩個人乘著汽艇在考察岸邊的泥灘時,他們有了一個重要的發現。當他們正繞過一個叫彭塔阿爾塔的海岬時,獨自面朝海岸的麥考密克指著一個約二十英尺高的土堤突然叫道:「喂,那邊是什麼?」那座土堤高聳在一大片蘆葦後面,裡面嵌著一些奇怪的白色物體。開始時,那看上去像一個純色的大理石露天礦場,自個兒坍塌裸|露出來,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但當汽艇靠得更近時,他們發現是些更為有趣的東西——是些骨頭牢牢地嵌在硬結的泥沙層裡。
前一天晚上,躺在輕輕搖晃的吊床上,他向室友菲利普.吉德利.金講了自己對麥考密克的反感。
一個星期後,小獵犬號的主甲板上到處都堆滿了化石,要從船頭走到船尾都很不方便。第一海軍上尉惠格姆抱怨說他的船「被搞得一團糟」——「簡直把它變成了一個博物館」——不過他只是裝出一副驚愕的樣子而已。大多數船員都為這一事業興奮不已,他們聚精會神地傾聽達爾文滔滔不絕地分析這些動物被趕上滅絕之路的原因。他談到生存環境的改變,山體的上升以及南北美洲間的地峽中大陸橋的出現。菲茨洛伊則完全不贊同:他在星期天的一次船上布道中堅稱,牠們的滅絕是因為沒能上得了諾亞方舟。
幾週後,他們進入了阿根廷海域。他們很快便發現,那裡比他們見過的任何地方都要崎嶇不平和荒蕪。當小獵犬號靠近布宜諾斯艾利斯港口時,一艘阿根廷檢疫船從船頭發射了一枚炮彈,極不友好地要求他們隔離。菲茨洛伊簡直氣暈了。他從那艘船旁邊駛過,威脅要把它炸上天。然後他繼續前行到蒙特維多,並說服那裡的一艘英國軍艦開回布宜諾斯艾利斯去向英國國旗的受辱討回公道。
「別那樣擔心,阿哲——你仍然是小獵犬號上唯一的博物學家。你的標本堆滿了我的甲板,並一直在用陛下的開銷寄回國去。我說話沒算話嗎——啊?多年後,當你作某一場著名講座時,難道不配你提一下我的名字嗎?」
「順便說一下,量你也猜不出誰被廢了,」他用的是一個水手術語,指人因意見嚴重分歧而放棄航行。查理立即知道了是誰,但沒等他開口,金脫口把那名字說了出來。
沙利文吃了一驚。
「奴隸制度是最麻煩也是最複雜的問題,」沙利文說,「規定販賣奴隸為非法是一回事,而要在海外領土上廢除蓄奴制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你這個英國佬,」他說——把自己排除了在外,「對顯微鏡下的蟲子如此著迷,如此喜歡和圖書搜集骨頭。相比之下,你對大是大非的成見真是太微不足道了。」
「就在剛才你還提到過。我敢肯定,誰都會覺得菲茨洛伊船長不太像一個心理健康的最佳標本。你見過他的情緒變化——一丁點的刺|激就可能使他陷入極度沮喪的泥潭。萬一他有什麼事——且不說其他的,整個船上這副牌就要重洗了。」
對於查理來說,這一天可是等得太久了。他已經體會到海上生活的單調乏味——也就是說,一艘今天可以用作軍艦的雙桅橫帆船明天就可能變成自己一個可怕的牢籠——如果一個人有個總跟他過不去的仇敵。他和麥考密克的關係已經嚴重惡化,不再僅僅是粗魯,而是近乎一種略為掩飾的仇視。
金揶揄地看著他,說道:「拜倫本人說得再好不過了。」
「什麼?——施計讓那個指揮官把他的腦袋崩開花?」
菲茨洛伊派出了大約五十個武裝到牙齒的船員。查理跳上一隻船去加入他們的行列。他把兩支手槍別在皮帶裡,迫不及待地想登上岸。他們穿過塵土飛揚的街道。許多商人衝到門前和從窗口探身出來向他們歡呼。查理笑開了懷,他感覺到一種與船友們間的溫暖的同志情誼。他回頭看見麥考密克。他驚訝地發現這種親近感甚至也延伸到了他的身上。兩人相視一笑。查理舉起一支手槍朝向空中,模仿了一個開槍的動作。
「也許惠格姆會掌管那艘姊妹船——他是二號人物。」
「結果沒有一個人不是說:不,他們不願意。哈,相比於他們自己謀生忍饑挨餓,他們在他手下要過得好得多。」他宣布說。
而就在這一刻,在小獵犬號船上,麥考密克與巴塞洛繆.詹姆斯.沙利文也在談論著同一個話題。醫生在下層甲板上,說的話菲茨洛伊能聽到,但他假裝不知道他在那裡。
「像菲茨洛伊船長那樣——給他的指揮官一個好印象。掌管一艘姊妹船,表現出你的指揮能力。進入權力層,然後充分表現自己,讓每個人都為你喝采。要像海軍上將從不離身的軍服那樣牢牢抓住你的權力。」
「麥考密克。」
達爾文跳下船,用短棍撥開蘆葦,蹚水朝岸上走去,使得螃蟹紛紛往兩邊逃竄。待其他人趕上來時,他已經在堤岸上掘開了。岸上有一層疏鬆的沉積層,由沙礫和淤泥構成。他一下下地往外掏,掘到肘部深時,他最後奮力一扳,一根三尺長的大骨頭鬆落出來。他像獎品一樣把它舉了起來。
但真可惜,造反很快就夭折了,暴亂者立即投降了。當船員們到達軍火庫時,除收羅俘虜和在堡壘四周搜尋那些負隅頑抗者外,已沒什麼事可做。接近傍晚時,他們已經在院子裡的熊熊大火上燒烤起牛排了。狼吞虎嚥地吃著嘶嘶冒著熱氣的紅彤彤的牛肉,查理還在品味著那難得的一會兒興奮。
後來,惠格姆提出讓查理到餐廳和其他軍官一起用餐。但沒過一會兒,菲茨洛伊——情緒又是突然變化——派人送去一封言詞懇切的致歉信。查理考慮到船上的安寧,決定不再計較這次冒犯。然而,他對菲茨洛伊的看法不再像從前了——他放棄了近乎幼稚的偶像崇拜——並發誓當小獵犬號到達里約熱內盧並利用那裡作為基地對沿岸上下的近海水深進行探測的時候,他將到岸上去。
「你將還得和阿哲競爭。」
船起航的那天晚上,他又開始反胃了。在與菲茨洛伊吃晚飯的時候,他提到麥考密克走了又回來的事。開始時,船長似乎一心在想著別的事情,沒有回答。他含糊地揮了一下手,然後突然清醒過來,說道:「啊,是啊。他要求回來,實際上是他求我的。我想:幹嘛呢,有什麼害處嘛。就這樣,你瞧,他就在這裡了。」
「那樣你最起碼也會是小獵犬號上的二號人物。不可能會是降級。」
「你與那些高貴的羅馬人、博學的希臘人,甚至——我猜想——這個洲那些高貴的野蠻人到底有哪些相近?」金繼續說道,「僅僅是因為你精通了蒸汽機——一小片推動其他金屬運動的金屬——你以為你就獲取了統帥整個世界的權力。你相信自己坐在了那該死的金字塔頂上。而你卻對它的建造者以及建造的原由一無所知。」
「會是什麼呢?」
「一點不假。讓達爾文先生最惱怒的,是菲茨洛伊船長不同意小獵犬號應為根除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販奴貿易而戰鬥。我覺得在這點上他這樣說船長實在是太放肆無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