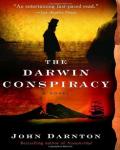第十三章
「不可否認的是,他對宗教更加狂熱了。他成了一個嚴格的《聖經》文字論者。我丈夫常說,命運的轉變使得小獵犬號船變成了一個人信仰的搖籃和另一個人信仰的墳墓。」
「傑米.巴頓」,他叫道,「不是傑米.巴頓幹的!他們想把他釘在十字架上……像釘我那樣!」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一日
他斷斷續續地說完這最後的話,那憤怒的樣子嚇得我跳了起來。但他扯住我的手臂不放。他一下站起來,俯身靠在我近前,嘴裡還不斷地念叨著。我感覺到他的唾沫濺在我的額頭上。我的心怦怦直跳。
在哈利街二樓的辦公室,他極為熱情地接待了我,侍候我坐下,並說與「達爾文教授的女兒」晤面是他的榮幸。我立即聲明說我父親絕不是什麼教授,而只是一個業餘的博物學者。他回答說:「要是所有的業餘愛好者都能像他那樣,我們就太幸運了。」
從我讀的那數頁手稿中可以看出,他把整段整段描寫旅行過程中所發生事件的內容都刪去了,尤其是他本人與羅伯特.麥考密克的幾次談話內容。如果沒記錯的話,這人是船上的隨船醫生。我把這些手稿與發表在雜誌上的文章進行了對照。我發現他們之間大部分的對話——有的帶有爭論性——從來沒有在書裡出現過。我還特別注意到,有些被刪除部分講的是麥考密克先生非常妒忌菲茨洛伊船長對爸爸特別的善待。其中有一則說的是船長帶著爸爸,而沒有帶他,到某個島上去玩。麥考密克先生非常生氣,因此當爸爸跟他說話時,他轉身就走了。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刪去這些內容,卻又偏偏把旅途中其他所有的事情記述得那麼仔細。也許是因為這些章節有損麥考密克的形象吧——事實上,他給人的感覺是個最讓人討厭、壞點子最多的人。
我忍不住看了一眼赫胥黎先生。他打量著整個場面,帶著幾分滿意,像一個將軍看到自己的部隊擊潰了敵軍一樣。當他看到菲茨洛伊船長時,頓時面白如蠟。他立即轉身對一個年輕人小聲說了些什麼。那個年輕人擠過人群,走到菲茨洛伊船長面前。精疲力竭的船長這時已跌坐在座位上。年輕人一把將他扶起來,推著他走了下來,從一個側門出去了——到底是出於惱怒還是友善,我不清楚。
可憐的菲茨洛伊船長。上帝如何能讓世間有如此的不幸?我們人類又如何承受得了那樣的不幸啊?
我謝過她,並緊緊地擁抱了她一下。她警告我說,她聽說菲茨洛伊因悲傷和不幸已精神失常。她講了一些他的不幸遭遇——實在是太多了。他的雄心壯志每每受到挫折。他在小獵犬號上進行的勘測工作沒有給他帶來預想的名望,於是轉向了政治。他在達勒姆贏得了一個空缺位置,卻與托利黨的另一候選人捲入了一場惡意的對抗,最後在美爾大街他的俱樂部外面拉扯了起來。這一醜聞使他做起工作來很不順心。於是,他接受了紐西蘭總督的職位,殊不知又陷入移民與當地毛利人激烈的土地紛爭中。這事情證明了他的無能,於是被召回。經過艱苦的旅途勞頓,回國後他的妻子瑪麗死了,留下四個沒了娘的孩子。接著他的大女兒又死了。他的財產被一點點地銷蝕一空。
我對菲茨洛伊船長的拜訪糟透了。我簡直被嚇破了膽,而且我擔心那次拜訪對船長也幾乎沒有任何益處——恰恰相反,恐怕是使他本已不好的健康狀況更加惡化了。這在現在看來是一點不假。
我正若有所思地望著這亂糟糟的屋子,突然聽見從大廳樓梯上傳來的沉重腳步聲。船長突然進了房間,樣子極為怪異。他已然失去了軍人的威儀,身子佝僂得厲害,頭微微向一旁偏著,雙眼睜得圓圓的,像是要凸了出來。他頭髮凌亂,鬍子也是亂蓬蓬的,就像是當年指揮皇家艦艇長途勞頓歸來的模樣。我的出現讓他感到很迷惑。但他仍還有些禮儀意識,突然伸手過來,微微鞠了一下躬,然後咕嚕著說:「羅伯特.菲茨洛伊船長……我很榮幸……您……有何貴幹……呣」如此等等——難以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他身上似乎憋著一股勁,像小孩子擰緊發條的玩具,手不停地忽上忽下的,雙腿左右直晃。他焦躁地不住地動來動去,讓人思維很難集中。我鼓足勇氣扶他到椅子前,使他坐了下來。m.hetubook•com•com我自己坐在他旁邊。別無它途,只好開門見山了。
一八六五年四月三十日
好一段時間船長的話都在我的耳裡迴響:「事實就是那樣的,嗯,達爾文先生?」他是什麼意思呢?我想,那句話可能會是因傷心和痛苦而神經錯亂的胡言亂語。實際上,從他那蒼白的面容和狂亂的樣子來看,他的確太令人同情了——悲傷而不安寧。而且我得承認,他還帶有威脅的味道。但不管怎樣,我還是覺得非找他談談並找出一個原因來不可!讓人迷惑不解的問題一個疊一個,我瘋了似的想把它弄個水落石出。
是拉斯舅舅告訴我的。他一點不體諒我的感受,興奮地向我描繪起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那事經菲茨洛伊可憐的妻子傳出來後,就成了科學俱樂部的熱門話題。在菲茨洛伊死的前一天,他坐臥不寧,不時從椅子上跳起身,走來走去,嘴裡還念叨著什麼,然後停住又坐下來。他堅持要到辦公室去,但剛出去又倒了回來,然後下午去了倫敦。晚上回來時,他顯得極度的不安。他堅持一定還要見見莫里,雖然第二天就是星期天,他們也已經道過別了。
但這些刪節的內容仍讓我很納悶,於是我決心去看看還有沒有其他被刪掉的東西。趁弟弟們在專心畫畫和爸爸在外面沙道作保健散步的時間,我偷偷溜進他的書房。在他的木書桌上方的一個書架上,我發現了在航海途中作的一些筆記。它們都是編了號的,因此我一眼就能看出裡面缺了一些——但上面沒有標明它們的去向。我看了一下其他的,把它們小心翼翼地抽下來,以便能準確地放回去而不被發現。當我翻看這些筆記本時,我吃驚地發現爸爸把有些事件和條目都改了。我之所以能分辨出來,是因為這些墨跡的色澤與原先條目的顏色明顯不同,而且前後完全一致,而在旅途中寫的各個條目每一週都不一樣。另外,有的記錄是硬插|進去的——有時潦草地寫在邊上,讓人明顯看得出來是後來補上的。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早先的條目被整條給劃掉了。
看到他一貧如洗的處境,他的同事——「包括你自己的爸爸,」弗朗西絲說——設法讓他進了皇家協會。協會又推薦他去貿易委員會,並任命他作天氣統計員。這個職位沒有什麼迷人之處,但對愛好科學的人還是很有趣的。他又結了婚,並想盡量在新的崗位上幹出一番成績來。他把一種叫氣壓計的儀器視若寶貝,並盡量收集到各種觀察資料——不僅僅為了記錄已經發生的天氣情況,而且還試圖對未來的天氣情況進行預測。他把它叫做「天氣預報」,並認為這有利於保護海上的船隻。但雖然開始時有一些成效,它卻沒有成功。他那些錯誤的預測遭到人們普遍的嘲笑——《泰晤士報》最近也停刊了他的「天氣預報」欄目。
「你們英哥人——沒有一點生氣,」他尖聲大叫。他那口音聽起來就像是那個印第安男孩。
「傑米被送回到火地島後,失蹤了數年。我在一八五五年十一月找到他。他的變化之大,令我非常吃驚。我們從狹窄的河道進入亞加沙加,看到一個小島上有煙火。我升起艦旗。有兩條獨木舟駛過來,其中一隻上有一個很胖的印第安人,沒穿衣服,身上很髒。他站起來叫道:『舷梯在什麼地方?』我們把他拉上船,發現正是傑米.巴頓——真是難以置信。他似乎又完全回到了原始的狀態,不過他還會講英語。而且還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他拒絕被叫做傑米,他說他想被叫做奧隆利科。我不明白那到底是怎樣回事。
我住在拉斯舅舅家裡。看到我對爸爸的過去感興趣,他覺得很有趣。他非常好,同意安排我一個星期後與菲茨洛伊見面,並答應這事只能是「我們自己的小祕密」。他也警告我說,菲茨洛伊正被他自己稱之為「藍色惡魔」所困擾。
恐怖的事一個接著一個!我剛聽說菲茨洛伊船長自盡了。真難以置信!只在兩天前我還見過他。
菲茨洛伊船長可能會是幫我澄清疑惑的羅塞塔石碑,但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接近他。說實話,我一想到要去見他心裡就發慌。從人們在唐豪斯的閒談中,我聽說過他相當多的事情。我知道很多人都認為他大腦有問題。他還對爸爸抱有很深的敵意,斥責他試圖推翻基督教世界的所有信仰。同時,他肯定也責怪自己作為輪船的統帥,不應該讓他那樣做。hetubook.com.com
我是直接了解到這事的,因為我親眼目睹了在牛津的英國科學進步協會上,赫胥黎先生與蘇比.薩姆.威爾伯福斯間的那場現已廣為人知的衝突。當時,菲茨洛伊船長還當眾出了醜。那場景在我腦海裡至今還栩栩如生——儘管當時我才十四歲——我真難相信那竟然是五年前發生的事了。拉斯舅舅把我偷偷帶了進去。我躲在他的椅子後面——盡量不讓人注意我——目睹了那整個過程。
也許大火之夜是在後來的旅途中發生的事——非常可怕,很多船員都捲了進去;或者是與傑米.巴頓有關的什麼事情。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他這個人對基督教文化極其排斥。他可能幹出最殘暴的行為。
那天晚上,他睡得很不好。早上妻子驚醒時,他已經睜開了眼睛。他問她僕人為什麼不叫醒他們,她告訴他說是星期天。他在她身邊又躺了半個小時,便悄悄起來,到隔壁的房間吻了他的女兒勞拉。然後他來到更衣室,鎖上門。一分鐘後,她聽到他身體倒地的聲音。她尖聲叫喊僕人。僕人們砸開房門,發現他已躺在血泊中。他從修面工具包裡取出一把折疊式刮鬍刀,只一下——也許還對著鏡子——刮鬍刀猛地抹過喉嚨,結束了自己不幸的生命。
我決定馬上離開這裡。我掙脫他的手。
根據拉斯舅舅的建議,我去國家氣象局的候見廳見他。我沒有預約就去了,因為我知道他要在那裡會見莫里先生。一位助理聽了我的請求,斜挑著一個眉頭,一副得意地傻笑的樣子,讓人窘迫之極。那樣子似乎是說我什麼都不懂。他好像在掂量著是否要通報船長我的到來。他左手拿著一把直尺,不停地敲打著另一隻手的掌心,讓我站在那兒等著他思考。我懷疑這輩子從來沒人對我這樣無禮過。他最後終於同意了,出了房間,並明確表示他不會回來的。而想到要和一個頭腦可能不正常的人單獨待在一起,我著實有些懼怕。
為了打發時間,我決定多了解一些關於火地島大屠殺的事情。於是,我去拜訪了威廉.帕克.斯諾。在菲茨洛伊把傑米.巴頓送回到那個蠻荒之地的二十二年後,這位船長又找到了他。那時,斯諾先生受雇於巴塔哥尼亞傳教會。不過,他現在卻成了它的主要對手。他以傑米在那次大屠殺中所犯的報復罪以及其他一些證據為由,欲將這個協會置之死地。
「菲茨洛伊船長」,我開始道,「很對不起我這樣冒昧。希望您不會認為我太失禮。我非常想請教您幾個有關小獵犬號和那次航海的事情。」
「我知道,儘管傑米點頭哈腰,笑臉迎奉,但他並不真正尊重輝煌的西方文化。就是在船上的第一天晚上——我剛從他隱退多年的原始地找到他,他說了一些讓我永遠不能忘記的話。他說:『英哥人的窺穴是魔鬼的。』我過了一些時間才領悟到他的意思——我們的科學全不是他預想的樣子。他說話的樣子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鄙視。」
我不由得點頭表示贊同。
「而且不出我的所料,印第安人的結局非常慘。上次的報告說,他們因疾病死了不少的人。還有,看看這個……」
一八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日
那天夜裡,我怎麼也難以入睡。他那古怪的話在我的腦中不斷迴響,尤其是最後那句毫無意義的話:「你們英哥人——沒有一點生氣。」
「你也應明白,他可不是你父親的什麼朋友,」弗朗西絲說。
我們到外面花園裡去散步。天氣出奇的暖和。我們互相推心置腹。她告訴我說,爸爸沒有參加她父親的葬禮,讓她非常不高興。她指出,小獵犬號上的床位是通過她父親的努力才弄到的,而且爸爸那一箱箱著名的標本也是她父親收的。我有責任給他找托詞,當然都是圍繞他的身體做文章。然後我突然脫口說道,我覺得也非常奇怪,爸爸總是避免參加葬禮,連他自己父親的葬禮也沒有參加。我說那是一個極其嚴重的缺點。接著,我又不自覺地列出了他的其他種種缺點。能把這些向人吐露出來,讓人覺得好不輕鬆。
https://m.hetubook.com.com說著,他遞給我一份傳教會時事通訊——《悲憐之聲》。我看到上面有篇報導,叫《令人萬分悲慟的消息》——講的是傑米.巴頓的去世。斯諾先生等我看完,才又開口。
那是我聽到他說的最後一些連貫的話。我問他大火之夜指的什麼。他直直地盯著我,幾次開口都說到半截就停住了,全是一堆沒有意義的話。他的頭不住地搖,很不贊同的樣子,嘴裡說道:「不對……不對……不是火地島,是在加拉巴哥……那些著魔的島嶼——啊!……那一切就發生在那……」然後他樣子嚇人地盯著我,用單調而令人恐怖的腔調說道:「事實就是那樣的,嗯——達爾文先生。」說完,他笑了起來,笑聲低沉而邪惡。
輪船在波浪輕柔的港灣停靠了幾天。船員們在海岸上邊一塊安靜的地方草建起一所傳教會所。幾百印第安人乘著獨木舟從四面八方趕來。星期天,傳教團準備在會所舉辦一次禮拜儀式。船員們穿戴整齊,划船上岸,從成群的印第安人中擠過。船上只留了廚師一個人。他在輪船上看到,船長和船員們剛一進去,那些印第安人便搶過他們的大艇,把它們推進水裡。會所裡響起讚美詩的歌聲,接著便是驚叫聲和尖叫聲。白人們跌跌撞撞地跑出來,印第安人在後面用木棒和石頭追打。其他人提著長矛趕來。一個水手逃到齊腰深的水裡,被一塊石頭擊中太陽穴,倒在海裡。沙灘上血流成河。驚駭的廚師放下一艘小划艇,拼命地划上岸,消失在樹林中。幾個月後,一隻派去調查的船把他救起時,他已被嚇得半瘋。他赤|裸的身體長滿了癤,眉毛和鬍鬚都被印第安人拔了。他講述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件。輪船把他送回福克蘭群島時,同時還帶上了傑米.巴頓。
「讓人覺得尷尬的是,他一點也不友好。他要衣服穿。於是我把自己的一條褲子和一件襯衣給了他。但他太胖了,穿不了。他想吃肉。但當我們把他帶到甲板下面給他肉吃時,他又太激動了,吃不下去。我問他是否想到福克蘭群島的新傳教所去,他斷然拒絕了。我給了他一些禮物,包括一個音樂盒。他非常高興。我於是叫他第二天再來拿一些。
弗朗西絲說,在所有打擊和挫折中,對菲茨洛伊造成傷害最深的是關於艾倫─加德納號的船員遭屠殺和傑米.巴頓本人被控領導了那次暴行的消息。我們於是開始討論起那場令人震驚的事件。但這時花園裡其他人加入了我們的行列,所以我們沒再談下去。
我最近遇到一些最為奇怪的事情。爸爸長期以來一直有個習慣。他常常在樓梯的櫥櫃裡放一疊紙,給年幼的孩子寫寫畫畫用。但他極為節約,紙的正面往往是他寫過的草稿。兩天前,在給霍勒斯和倫納德拿紙時,我開始閱讀上面的內容。它們是他的《乘小獵犬號環球航行》較早的幾個手稿版本。我無意中發現版本間有些不一致的地方。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他已打算對書的內容進行多處修改。
我不知道這些被修改的內容是否是對原稿的進一步思考或者闡述,就像審閱草稿那樣。但它們似乎不太像是那種情況,因為只須粗略一看,你就能發現它的目的是在於對原來的記述本身進行改動。有的修改內容涉及菲茨洛伊船長,有得是關於傑米.巴頓的——這個無恥的野蠻人簡直不知道什麼叫背信棄義,還有一些是有關前面提到的麥考密克先生的。
太嚇人了!可憐的人。我禁不住想,是否有我的一點原因——甚或是大部分原因——使他如此失卻理智。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的良心可就難得安寧了——但我永遠也不會明白自己到底處於哪一端。我一想到它就發抖!夠了,這些窺探,這些幼稚的調查遊戲!我再也不會幹那事了。我要立即停下來,迫使自己改變。我要重新做人,要成為一個更善良的人,而不再是多年來那個多疑、狂妄的莉齊。
斯諾先生嘆了一口氣,說:「我想其餘的你從報紙上都知道了。」我的確知道。他們進行了一次正式問訊。混亂的證詞加之不利於巴塔哥尼亞傳教會的政見,傑米被判無罪——儘管那位廚師同時還聲稱,大屠殺後,巴頓先生還爬上船,在船長的房間睡了一個晚上。
斯諾先生看著我的眼睛,又說:「真有點奇怪,居然是在給達爾文的女兒講這些東西。」
斯諾先生又講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一位叫格.帕肯漢姆.德斯帕德的https://www.hetubook.com.com新牧師來了。他一心以為可以以傑米為先導,吸引大眾皈依教會。他新雇了一個船長。這個船長回到火地島,設法把傑米和他家人帶到了在福克蘭群島的克佩爾的教會所在地。他們既不學習,也不做事,在那兒只待了四個月。為了回家,他們答應讓其他人來頂替他們的位置。因此,第二次回去時,他們作了一個交換——傑米回他原來的島上,另外九個印第安人過來。他們在那裡似乎很適應——誦唱讚美詩,並接受洗禮。但他們起程回去時卻很不順利。德斯帕德認為他們偷了教會人員的東西,並下令搜尋。他們把包裹扔在甲板上,對被指責偷盜非常生氣。而當那些物件被搜出來和沒收之後,他們甚至更加憤怒了。
那個房間本身就讓人覺得非常壓抑。我們的狄更斯先生已有過那樣的描述。屋裡窗簾很厚,光線非常暗,只在屋的中央有一盞煤氣燈。靠牆四周是舊的木櫥櫃,有半牆高。櫥櫃上方掛著一幅幅發黃的航海圖和水漬斑斑的輪船圖片。畫框斜掛在牆上,角度很是怪異。屋裡滿是灰塵,甚至破舊的辦公桌氈面上的墨水池裡和褪色的綠天鵝絨椅子上也覆蓋著一層厚厚的塵埃。那樣子看上去不像是一間政府辦公室,倒像是一個太平間。
於是,我兩手抓住裙子,頭也沒回地衝出門去。我聽見背後一連串的痛罵聲,一些更讓人聽不懂的話,以及那恐怖而刺耳的笑聲。
船在洶湧的大海上的一路顛簸並沒有使他們的怒火減弱。當艾倫─加德納號靠岸時,其他的印第安人向輪船划過來,船上的印第安人也吵鬧起來。傑米被請來調停事端,但他偏向他的族人,提出要更多的禮物作為補償。但已經沒有了。這時一個水手告訴船長他的私人物品有些不見了。接著又是一道搜索命令——東西找到了——那些印第安人狂怒地扯下衣服,扔掉《聖經》以及一切文明社會的物什,然後赤身裸體地登上他們的獨木船。直到夜幕降臨,他們的尖叫聲一直在海岸上迴蕩。一堆堆的篝火在岸上生起,滾滾的濃煙在黑暗的夜空裡升騰。
我得想法見見菲茨洛伊船長。我必須和他談談,懇請他給我解釋一下,因為這一切都讓人太難以理解了!太多的問題攪得我頭暈目眩。我必須弄清楚小獵犬號航海過程中發生了些什麼事。通過讀爸爸的日記——沒有刪改的日記,我敢說——很明顯,在航海過程中發生過某些事情,某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這些事件未曾有充分的記錄。我對那些事情一無所知。但我確信,他們對航海考察的結果卻是至關重要的。
「儘管問……儘管問……」
「天亮時,有更多的小船圍著我們。傑米和他的兄弟們,以及其他一些人來到船上。氣氛顯得很不好。我給了傑米很多禮物,他手裡都拿不了。他們一遍遍地叫著『雅莫蘇勒』,就是『給我』的意思。真的,你聽了之後永遠都忘不了的。其他一些人推著我說:『英哥人來了——英哥人給東西——英哥人很富。』傑米不肯幫我們,於是我就叫把船帆鬆開。他們以為我們要走了,怕我們綁架他們,便搶著翻下船。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傑米。當我們的船開走時,他和他的妻子坐在一艘獨木舟裡護著他們的禮物,不讓其他人奪去。」
「我知道,」我答道,「爸爸說他一直用塞內克斯那個名字在刊物上攻擊他。他過去就熟悉了他的論點。」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五日
船在南美時發生過一件事,具體是什麼我不清楚。爸爸寫得非常隱晦,讓人心裡乾著急。他把它叫做大火之夜。他指的是什麼,讓人一點也看不明白。但那幾個字卻暗示了某次暴亂,也許是英國人與野蠻的印第安人相遇時發生的事。那些印第安人的外表被描繪得特別嚇人。爸爸對他們作了非常生動的描寫:他們如何地像野獸一樣站在岸上流口水,他們的頭髮纏結在臉上,他們臉上塗著一道道紅白相間的顏色,他們身體上塗著油脂,全身赤|裸,只在肩上披一件野羊駝皮做的斗篷。
但我不敢在那裡逗留太久。說實話,我感到有種強烈的內疚感,因為我知道,自己讀的東西不是自己該看的——而且就此而言,也不可能讓任何人看。我聽見前門臺階上響起爸爸手杖的聲音,我迅速放回筆記本,關上書房。相隔僅幾秒鐘,他便進了中央走廊。當我寫下這些時,我想,也許明天趁爸爸又到沙道散步時,我還能找到機會繼續查看他寫的東西。
我的運氣真不錯!這週末胡克夫婦——基尤的植物學家約瑟夫和m•hetubook.com.com他的妻子弗朗西絲——到我們家來做客。弗朗西絲也是爸爸摯愛的老師、已經離去四年的親愛的老亨斯洛的女兒。她最聰明了,提出了一個見到菲茨洛伊船長的辦法。
「求您讓我走,」我叫道。
我正要打算離開,他突然拉住我的手臂,把我按下來,急切地說道:「七處傷口,他們看到的。七處傷口……像我們的救世主……基督的聖痕……事情就那樣,當船長……那孤獨……我好心痛……我所有的錢都沒了……花在探險號上了……海軍部的敵人和忘恩負義的東西。他們曾警告過我……小心,他們說……沙利文,我自己的二把手海軍上尉,封騎士了,封騎士了……而我……我如何呢?」
在那個新博物館悶熱的演講大廳裡擠了大約有五百人。主教從各個方面對爸爸的理論進行了攻擊,然後提了一個著名的嘲諷性問題:赫胥黎先生是在他父親那方呢還是他母親那方與猿猴有親緣關係?赫胥黎先生一下跳起來,他以慣有的激|情為爸爸的作品辯護,並用了一句很快就傳播開來的反詰的話作了一個總結:如果他必須作出選擇——是以猿猴為祖先還是以得到大自然的賜予、具備理性卻將其理性之力用於嘲諷嚴肅的科學討論的人為祖先,「那麼,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猿猴。」這句話造成了臺下一片哄亂。人們高聲歡呼和打口哨。有的把他們的程序單扔向空中。我從拉斯舅舅的椅子後面望出去。就在我們前面,一群學生嘶聲反覆叫道:「猿猴,猿猴!」不到兩排遠的一個孕婦站起來,突然暈倒在地板上。
簡短的寒暄後,我請他講一下那次大屠殺的事。他皺了皺眉頭,然後粗略地給我講了些人們早已熟知的東西。
「達爾文是個異教徒,是個不信仰宗教的東西……是魔鬼的女僕……海灘上的石頭就是證據。他們磨圓了……被大洪水……就是《聖經》裡記載的那次大洪水。我告訴你……諾亞方舟的門太小了,乳齒象進去不了……異端邪說是一種罪過,違反摩西十誡也一樣,嗯——達爾文先生?事實就是那樣的,嗯?」
一八六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太讓人傷心了,」斯諾先生說,「但我當時就覺得肯定會發生這樣的事。它是從第一個英國人和第一個印第安人見面後開始的一連串事件的結果,從菲茨洛伊船長從制服上扯下那顆紐扣買下那個小孩時就已註定了的。」
這時,我看見了菲茨洛伊。他穿著一件破爛得不成樣子的舊海軍少將制服,看上去像《舊約》裡的一個先知。他像著了魔一樣走過人群,一隻顫抖的手裡高高揮舞著《聖經》,嘴角上還沾著一星唾沫,頭髮也凌亂不堪。他稱爸爸是一個「褻瀆者」。他說他後悔同意帶「那個人」上船,並說他的忘恩負義「比毒蛇的牙齒還要狠毒」。他稱他是「魔鬼自己的花衣魔笛手,將引領輕信的人們墮入地獄,萬劫不復」。一度,他氣急敗壞地看著樓座上歡呼的人群宣布說:「但這一切都是錯誤的——那個人是個惡棍。」他繼續這樣罵著。但我幾乎都沒聽清楚——除了他轉頭朝著我這邊方向說的那一句。那句話是:「事實就是那樣的,嗯,達爾文先生?」他把這句毫無意義的話重複了幾遍。那怨毒單調的聲音使我不寒而慄。
我沒有講我在做的調查或者我內心深處的懷疑,而只是說我需要和菲茨洛伊船長談談。她說會很麻煩,因為他最近從南肯辛頓搬到倫敦以南的上諾伍德去了。她提醒說,我是肯定不會被邀請到那裡去的。但接著她又有了一個主意。她確知現在在國家氣象局工作的菲茨洛伊最近要與美國海軍中的對應人物馬修.莫里會面。我的拉斯舅舅肯定能弄到他們的日程安排,並能安排一次假裝偶然相遇的見面。
我衝出前門,跑下臺階。我揮手叫住一輛敞篷馬車——牠們幾乎從不停,但我想是駕車人看到我這衣衫不整的樣子,動了惻隱之心——我直奔拉斯舅舅的家。我喝了好幾杯熱茶都還沒恢復過來。
於是我提到南美洲、火地島和那個似乎讓他神志混亂的名字。「……火之地……火之地」,他的話奔湧而出,快得讓我幾乎聽不清楚。我明白他說的是早期的探險家給它的命名。當地人在岸上點起大火,水手們以為自己看到的就是地獄,於是就給它起了那個名字——事實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他低聲恨恨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