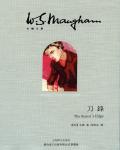第三章
二
「『你遲疑做什麼?不要因為我的緣故,我希望。我是個哲學家,我懂得此處不著那處著。我不怪她。你年輕,我也年輕過來。青春是稍縱即逝的。』
「『這聽上去不錯,』我說。
「『住口,你這狗材,』他說。『你要知道這些無聊的事兒做什麼?來,讓我們學德文。』
「『這有什麼關係?你只管追她,老弟,我不會礙你的事。她可能不那麼年輕,但是身體長得很不錯。』
「『別胡說八道,』我跟他說。『她大可以做我的母親。』
「你怎麼辦呢?」
「我們一點不著忙,因為我們至少要等到莊稼可以收割的時候才能找到一處農場做工作,所以,兩個人懶懶散散地由那慕爾和列日穿過法國和比利時,然後經由亞琛進入德國境內。每天頂多走十英里或十二英里路;遇到一個村子看上去不錯,就住了下來。總有一個客棧之類的地方可以過夜,總有一家酒店可以吃到飯,喝到啤酒。整個說來,天氣都很好。在煤礦裡幹了好幾個月的活之後,能夠跑到野外來,的確開心。敢說我從來就沒有體會到一片綠茵看上去有這樣好看,一棵樹還沒有長出葉子,但是樹枝籠罩著一層淡綠色薄霧有多麼的美好。考斯第開始教起我德語來,而且我相信他的德語和法語講得一樣好。我們一路行來,他就會告訴我經過我們面前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東西德文叫什麼,一頭牛,一匹馬,一個人等等,後來又叫我複述簡單的德文句子;就這樣把時間消磨掉。等到我們進入德國境內時,我至少已經能夠跟人家要我要的東西了。
他害羞地笑一下,甚至臉有點紅起來。
「有,」拉里點頭微笑著。
我不由得笑起來。我可以想像得出拉里當時的模樣,穿著補過的襯衫和短褲,臉和脖子被萊茵河的太陽曬得黝黑,靈活而瘦削的身體,一雙深色眼睛嵌在凹進的眼窩裡。我可以有把握說,他這副相貌會使貝克爾太太這樣白皙、這樣胸部豐|滿的主婦欲火中燒起來。
「現在你回想一下當時的情景,是不是認為這件事情有點滑稽味道?」
「我從來沒有這樣痛快過。天氣仍舊很好,我們漫步穿過小鎮和村落;碰到有什麼可看的,就停下來看看。只要有地方可以過夜,就住下來;有一兩次,睡在稻草堆上。吃飯在路旁的客店裡吃,等到我們到達釀葡萄酒的鄉間時,就不喝啤酒,喝起葡萄酒來;在客店喝酒時,就跟店裡那些人交朋友。考斯第有一種粗野的快活派頭,使那些人對他很信任;他會跟他們打司卡特,那是一種德國的牌戲。玩牌時,他會偷牌,可是人脾氣好,而且講些他們欣賞得了的下流笑話,所以那些人輸給他那幾個大錢也不介意。我和他們練習講德語;在科隆時我買了一小本英德會話語法,進步得很快。到了晚上,考斯第喝了兩大盅白葡萄酒之後,就會以一種古怪的病態方式談論從逃避孤獨而找到孤獨,談靈魂的黑夜,談造物和主宰合為一體的極樂境界。可是到了清早,當我們穿行在明媚的鄉野,草上還沾著露水時,我想要他再告訴我一點,他卻變得非常生氣,幾乎要動手打我。
「可憐的老貝克爾為了使她們不要吵嘴,只好把農事擱下來。」
「她身體緊緊抵著我,用又熱又豐|滿的嘴唇吻我,兩隻手不住摸我的身體,兩條大腿夾在我大腿中間。」
「愛麗——就是那個媳婦的名字——是個又高又壯的年輕女人,只有二十來www.hetubook.com.com歲,黑眼睛,黑頭髮,一張長方的陰沉沉的臉。她仍舊替自己在凡爾登陣亡的丈夫戴著孝。是個虔誠教徒,每逢星期天早晨,都要步行到村子裡去做早彌撒,下午又要跑去做晚禱。她有三個孩子,其中一個是遺腹子;吃飯時除掉罵孩子外,從不開口。她在農場上只做少量的工作,多數的時間都花在帶孩子上,晚上總是一個人坐在客廳裡開門看小說,這樣哪個孩子哭她就能聽到。兩個女人感情很壞。愛麗看不起貝克爾太太,因為她是個棄兒,做過傭人,而且對於她是一家的主婦,能夠發號施令痛恨之至。
「『你上哪兒去?』我問。
「考斯第這一向一直都在設法勾引貝克爾太太,但是沒有進展。她是一個快活的、嘻嘻哈哈的女人,很隨便地和他一起揶揄說笑,考斯第對女人很有他的一套。我猜她知道考斯第的用心,而且敢說自己感到得意,但是,當考斯第開始擰她時,她卻教他放規矩些,並且摑了他耳光。我敢打賭,那一記打得很重。」
「哦,他們當作我是從美國軍隊裡逃出來的,弄得回不了美國,回去就得坐牢。我不願意跟貝克爾和考斯第上酒店去喝酒,他們認為就是這個緣故。他們覺得我不願引起人們注意,弄得村警來盤問我。當愛麗得知我打算學德文時,她就把自己的舊課本拿出來,說要教我。因此,晚飯後,她就和我走進客廳,把貝克爾太太丟在廚房裡;我讀給她聽,她改正我的讀音,並設法使我懂得那些我不認識的單詞。我猜想她這樣做與其說是幫助我,還不如說是擺點顏色給貝克爾太太看。
「我們沿萊茵河步行時在那裡耽擱過,我很中意那個城市。我喜歡陽光照在屋頂上和河上面的那種情調,那些小街,那些別墅、花園、栗子樹的大道和大學的洛可可式建築。當時,我就想到在那兒待一個時候倒不壞。可是,我覺得在到達那裡之前,該把外表收拾得像樣一點。我的樣子就像個流浪漢,敢說我如果找到一處供應膳宿的人家,要租賃一間房,人家不會信得過我,所以我坐了火車上法蘭克福,去買了一個皮包和一些衣服。我在波昂斷斷續續住了有一年光景。」
「我時常恨考斯第不容易叫醒。在煤礦上時,我總要死扯活拉把他叫起來,使他不至於遲到。可是,現在我倒很感謝他睡得這樣沉了。我點燈穿上衣服,把衣物打在背包裡——我的東西不多,所以一會兒就打好了——把胳臂套在背帶裡。只穿襪子穿過閣樓,一直到樓梯下面才穿鞋,把手裡的燈吹熄。夜很黑,沒有月亮,可是,我識得大路,到了大路上就向村子的方向走去。我走得很快,因為我打算在有人走動之前穿過村子。這兒離斯溫根堡只有十二英里,我到達時,剛開始有人走動。這次夜路我永遠不會忘記。路上除了我的腳步聲外,一點聲音也沒有,只偶爾從農場那邊傳來一聲雞叫。後來天上露出一點既不是亮又不是黑的魚肚白,接著,是晨曦微露,太陽出來,鳥兒全開始歌唱起來。還有那綠油油的田野、草地和樹林,田裡的小麥,被清晨的寧靜光線照得金裡泛銀。我在斯溫根堡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個小麵包,然後上郵www.hetubook.com.com局打了一個電報給美國旅行社,叫他們把我的衣服和書寄到波昂去。」
「我毫不遲疑就決定了。
「後來春天來了。在那片平坦而荒涼的鄉間,春天來得很晚,仍舊是陰雨和寒冷;可是,有時候,也會有一天晴暖,使人不想離開地面,坐著搖搖晃晃的電梯鑽到一百英尺下面的地球肚裡去,裡面擠滿了穿著煤汙工人褲的礦工。春天固然是春天,但是,在那片汙濁的原野上,春天來得很羞澀,就像拿不準會不會受到人們歡迎似的。它像朵黃水仙,或者百合花,開在貧民區住房窗沿上的一隻盆子裡,使你弄不懂它在那兒做什麼。星期天早晨,我們躺在床上——因為我們星期天早上總是起身很晚——我在看書,考斯第望著外面藍天,對我說:
「為什麼到波昂?」我打斷他。
可是,他沒有告訴我是哪些收獲,而且那時候我已經很熟悉他的為人,他願意告訴你時,就告訴你,他不願意告訴你時,就會半開玩笑地把你的問題支開,再問他也是白費。我得提醒讀者,這一切都是在十年之後他才告訴我的。在這以前,也就是我和他重又碰面之前,我一直就不知道他的行蹤,或者他在幹什麼。拿我來說,他等於死了一樣。如果不是由於我和艾略特的交往,經常使我得悉伊莎貝兒的生活經過、從而想起拉里,我肯定早已忘掉有這個人了。
「一個拳頭就像汽錘而且說打就打的人,你跟他有什麼爭辯頭。我曾經看見他發過火。我知道他可以把我打昏過去,把我丟在水溝裡,而且用不著我提,他就會在我昏倒時把我的口袋掏光。我對他這個人簡直摸不透。當葡萄酒打開他的話匣子,他談到至高無上的主宰時,他會避開平時講的那些粗野下流話,猶如脫掉在煤礦裡穿的煤汙工人褲一樣;他會談得很文雅,甚至很有口才。我敢肯定他並沒有弄虛作假。不知道我是怎樣會想起的,但是,我多少有種想法,好像他從事煤礦上那種辛苦的非人勞動是為了折磨自己的血肉之軀。好像他憎恨自己那個巨大的臃腫不靈的身體,要給他罪受;他的詐欺行為,他的仇恨,他的殘酷,都是他的意志對——唉,我不知道你會稱它做什麼——他的意志對一種根深蒂固的神聖本能的反抗,對自己渴求上帝的欲望的反抗,那個使他害怕同時又使他困惑的上帝。
「『不是一個農夫的妻子。只是一個農夫的寡婦,一個把生命獻給國家的英雄的寡婦。』
「後來她溜下我的床,輕手輕腳下了閣樓。我可以告訴你,我深深嘆了口氣,心放了下來。你知道,我嚇壞了。『天哪,』我說,『真險!』我想貝克爾很可能吃得大醉回來,昏昏沉沉睡了,可是,他們睡一個床,說不定他會醒來,看見自己老婆不在床上。還有愛麗。她總是說睡得不好。如果她醒著,她就會聽見貝克爾太太下樓走出屋子。接著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貝克爾太太和我睡在一起時,我覺得有塊銅片碰到我的身體。當時我沒有注意到,你知道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一般都不注意這些事情的,而且我一直沒有盤算到他媽的這是什麼。現在我想起來了。當時我坐在床沿上,正在盤算這一切事情的後果而且發愁時,忽然嚇了一大跳,人站了起來。那個銅片是愛麗丈夫的身分牌,被愛麗一直纏在手腕上的,所以和我睡在一起的並不是貝克爾太太,而是愛麗。」
「我從來不是hetubook.com.com那種認為女人在追我的人,可是,我感到——嗯,貝克爾太太看中了我。這使我很不舒服。單拿一點說,她比我大得多,而且老貝克爾一直對我們很尊重。吃飯時,貝克爾太太管分菜,我沒法不感到她給我的菜總比給別人的多一點。我總覺得,她在找機會同我單獨在一起。她會以一種我想你會稱做的挑戰姿態向我微笑,曾經問我可有女朋友,並且說一個年輕人在這種鄉下,一定因為找不到女朋友而感到苦悶。這類事情你是懂得的。我只有三件襯衫,而且都穿得很破了。有一次,她說我穿得這樣破爛真丟臉,要我把襯衫拿來讓她給我縫縫補補。愛麗聽到了,因此,下一次她和我單獨在一起時,就說我如果有什麼東西要補的,讓她來補。我說沒有關係。可是,一兩天後,我發覺我的襪子洞全補好了,襯衫也打上補釘,放在閣樓上我放東西的長凳上,但是,不知道是她們哪一個做的。當然,我並不把貝克爾太太放在心上;她是個忠厚女人,我覺得這可能只是她的母性表現;但是,有一天,考斯第跟我說:
「可是,他們對你怎樣看法呢?」我打斷拉里的話。
我哈哈大笑,笑得不可開交。
「『不要響,』她低聲說。
「農場上的活不重。牛要餵食,還有豬也要餵食;機器很不靈,我們得好好收拾一下;但是,我還是有點空閒。我喜歡那些芳香的草坪,傍晚時常常到處閒逛,覺得日子過得很不錯。
「我有什麼辦法?我能夠聽見考斯第在我旁邊的床上鼾聲很大。這是約瑟的處境,而且我過去一直覺得有點可笑。我只有二十三歲。我不能鬧出來,把她趕走。我也不想使她傷心;只好依她。
「愛麗是個富庶農夫的女兒,嫁過來時帶了一大筆奩資。她並沒有在村裡上學,而是上的最鄰近的斯溫根堡鎮的一個女子體育學校,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憐的貝克爾太太十四歲就到了農場,能夠看書寫字在她已經很不錯了。兩個女人關係搞不好,這是另一個原因。愛麗一有機會就賣弄她的知識,貝克爾太太氣得滿臉通紅,就問有知識對於一個農夫的妻子有什麼用。於是,愛麗就會看著自己用鋼鏈繞在手腕上的死去丈夫的身分牌,對著貝克爾太太慍怒的臉惡狠狠地說:
「『不要胡說。』
「但是,我們總算時來運轉了。我們剛穿過一處坐落在低谷中的村子,就望見一幢單獨的村舍,外表還不錯。我們敲敲門,一個女人來開門。我們像平時一樣問她可要幫工的,說我們不要工錢,只要有飯吃,有地方住就行,想不到她並沒有請我們吃閉門羹,而是叫我們等一下。她向屋子裡面叫人,不久就出來一個男人。這人把我們仔細打量一下,問我們從哪兒來的。他要我們把證件給他看,看到我是美國人時,把我又瞪了一眼。他好像不大高興這一點,但仍舊請我們進去,並且喝杯葡萄酒;他把我們帶到廚房,三個人一同坐下。那女人端來一大盅酒和幾隻杯子。他告訴我們,他雇的幫工被公牛抵傷了,現在在醫院裡,要等到莊稼收割之後才能復工。戰爭裡死了那麼多人,餘下的人又都進了萊茵河沿岸興起的那些工廠做工去了,現在找幫工他媽的可真不容易。這個我們知道,而且早已算計到了。總而言之,他說他可和圖書以雇用我們。房子裡地方很大,可是,我想他大約不願意我們住在家裡;不管怎樣,他告訴我們稻草棚上面有兩張床,我們就在那裡睡。
拉里停下來,我吃吃笑了。
「我知道有許多波蘭人夏天都回波蘭參加割麥子,不過,時令還早,而考斯第波蘭是回不去的。
「你這番經歷使你有什麼收獲呢?我的意思是說在煤礦上和在農場上。」
「這家人家姓貝克爾,有老貝克爾,他的妻子,他的寡媳和孫兒女。貝克爾年近五十,肥碩的身軀,花白頭髮;他在大戰時參過軍,腿上受了傷,現在走起路來還是一拐一拐的。腿上的傷使他很痛苦,只能靠喝酒解痛;睡覺前總是喝得醉醺醺的。考斯第和他相處得很好,晚飯後,時常一起上酒店,打司卡特,大喝其酒。貝克爾太太原是婢女。他們把她從孤兒院裡領出來,貝克爾在妻子死後不久就娶了她。她比貝克爾年紀小一大截,也還有點姿色,長得豐|滿,兩腮紅紅的,淺色的頭髮,有股風騷勁兒。考斯第不久就看出這裡面有點花頭的結論。我告訴他不要當傻瓜。我們有個好工作,可不願意丟掉。他只是嘲笑我;說貝克爾滿足不了她,而且是她自己在要。我知道叫他規規矩矩是白說,但還是關照他當心點;貝克爾可能看不出他的企圖,但是還有他的媳婦。你逃不脫她的眼睛。
「你可能覺得好笑,」拉里說。「我可不覺得。」
「科隆並不完全是順路,可是考斯第堅決要去那裡,他說是為了那一萬一千殉道修女。等我們到了科隆時,他去酗酒胡鬧。我有三天沒見到他;等他回到那有點像工人宿舍的房間時,臉色非常陰沉,原來他和人家打了架,眼睛打青了,嘴唇也劃了一道口子。那相貌可不怎麼好看,我可以告訴你,他睡了二十四小時,後來我們就沿著萊茵河流域向達姆施塔特出發;他說那一帶鄉間很好,我們很有機會找到工作。
「有一天夜裡,我被弄醒了。開頭我弄不清是怎麼回事;我半睡半醒,我感到一隻熱呼呼的手捂著我的嘴,這才發覺有人和我睡在一起。我把手挪開,接著就有一張嘴撫著我的嘴,兩隻胳臂抱著我,我感到貝克爾太太的兩隻大奶|子抵著我的身體。
「也許。可是這事情弄得非常尷尬。我不知道這會引起什麼後果。我不喜歡愛麗。我覺得她是個頂討厭的女人。」
「考斯第這樣把穩,我並不高興,我不願意相信有這種事情。我不知道怎樣對付這種局面是好,後來,我追溯了當時曾經觸動我的許多事情,愛麗講的那些我沒有怎樣留意的話。可是,現在我懂了,我有把握說愛麗也知道是怎麼回事。貝克爾太太和我單獨在廚房裡時,愛麗會突然跑進來。我有個印象好像她在監視我們。我很不喜歡,覺得她想要當場捉著我們。我知道她恨貝克爾太太,只要有點風吹草動,她就鬧出來。當然我知道她沒法子抓到我們的把柄,但是,這個女人的心眼兒很壞,說不定會編出一套謊話來灌輸給老貝克爾。我不懂得怎樣對付,只好假裝我是個大傻瓜,一點領會不了這個女人的用心所在。我在農場上過得很快活,做工作也幹得很開心,不想在收割之前就離開。」
「『流浪。穿過比利時到德國,再沿萊茵河走。我們可以在農場上找www•hetubook.com•com到工作,把一個夏天混掉。』
「第二天,我們就去告訴工頭我們不幹了。我找到一個人願意拿一隻背包和我換皮包。我把不需要的和背不動的衣服送給杜克婁克太太的小兒子,因為他的身材和我差不多。考斯第留下一隻口袋,把些要用的東西打一隻背包,就在第二天老太婆給我們喝了咖啡之後出發了。
「可是,你怎麼會把她當作另外一個呢?」
「是啊,夏天一天天過去。我們像牛馬一樣幹著活。割掉麥子,堆起麥子。後來櫻桃熟了。考斯第和我爬梯子摘櫻桃,兩個女人把櫻桃裝進大籮筐,由老貝克爾送到斯溫根堡鎮上賣掉。後來我們又割裸麥。當然始終還要照顧牲口。我們總是天沒亮就起來,一直做到天黑才歇手。我想貝克爾太太已經看出我這人沒有指望,把我放棄了;我總是保持和她若即若離,但是,盡量不得罪她。晚上,我已經非常瞌睡,談不上讀什麼德文;吃完晚飯就回到閣樓上去,往床上一倒。貝克爾和考斯第大都上村裡的酒店,可是考斯第回來時,我已經酣呼大睡了。閣樓上很熱,我睡覺時總脫得赤條條的。
「那時屋子裡漆黑。她除了叫我不要作聲外,一句話也沒說。她們兩個身材都高大。我認為貝克爾太太看上了我。從沒有想到愛麗會把我放在心上。她總是想念自己的丈夫。我點起一支香菸盤算當時的情形,越想越不高興。看來最好的辦法是離開這兒。
「『我要離開這兒。你可要跟我一起走?』
「我們並不趕時間,春天差不多快過去了,樹木全長得青枝綠葉的。葡萄園裡的葡萄開始灌漿。我們總盡量沿土路走,現在路上的灰塵大了起來。我們已到了達姆施達特附近,考斯第說我們還是找個工作做吧。我們的錢快用光了。我口袋裡還有半打旅行支票,可是,我拿定主意只要能夠不用,還是不用。當我們看見一家看去還不錯的村舍時,我們就停下來,問他們要不要兩個幫工。我要說我們的外表並不怎樣討人喜歡;身上又是灰塵,又是汗,又是骯髒。考斯第樣子像個大流氓,我的樣子想來也好不了多少。我們幾次三番被人拒絕了。有一個地方的農夫說,他願意雇用考斯第,但是不能用我;考斯第說我們是好朋友,不能分開。我叫他去,可是他不肯。我很詫異。我知道考斯第喜歡我,雖則我想不出是什麼緣故,因為我現在已經對他沒有用處了,但是,我決計沒有想到他喜歡我到這種地步,會為我而拒絕工作。當我們走開後,我感到有點良心責備,因為我並不真正喜歡他,事實上,我覺得他相當可厭,但是,當我想要說幾句話,表示我對他這樣做感到高興時,他把我臭罵了一頓。
「『你聽著,她要的不是我而是你。我一點指望也沒有。』
拉里嘴邊勉強露出微笑。
拉里有點遲疑,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那麼,後來怎樣呢?」我問。
為了使讀者休息一下,我在這裡另起一節,但是,這樣做只是為了讀者的方便;拉里的談話並沒有中斷過。我不妨借這個機會說,拉里談得很從容,時常小心選擇他的字眼。雖則我並不自命把這些談話記錄得完全無誤,可是,我不但竭力重述了他的談話內容,而且也複製了他的談話風度。他的聲音清脆,具有一種音樂美,聽上去很受用;他談話時,不作任何手勢,只抽著菸斗,有時停下來把菸斗重新點一下,盯著你望,深色的眼睛裡帶有一種討喜的,往往是古怪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