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整頓内務與精神動員
三、經略西南、西北為後方
不久,王瓚緒被蔣介石收買過去,同康澤勾結,向蔣介石密報四川地方軍人反蔣活動的材料。被激怒的川地軍人聯合起來揭露王的種種罪狀,還調遣一部分軍隊集結成都,劍拔弩張,形勢嚴峻。蔣介石又不得不罷免了王瓚緒,由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行轅主任賀國光兼省府秘書長,代行主席職務。
二劉大戰(劉文輝、劉湘爭奪四川的戰爭)後,劉文輝退居康定、雅安地區。一九三八年,南京國民政府遷渝後,蔣介石對屢屢反對自己的劉文輝採取了拉攏政策,以打擊劉湘的勢力。劉湘死後,蔣介石同意劉文輝在西康建省。王瓚緒在謀取四川省主席職位過程中,為獲得劉文輝的支持,也答應將川邊廿一縣劃歸西康建省。
西南包括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四省。抗戰期間,貴州幾乎完全為蔣介石所控制,西康在四川軍閥劉文輝的統治下,雲南則在龍雲的控制下。所以,西南問題的中心在於四川、雲南兩省。蔣介石想乘抗戰之機,使中央勢力深入川、滇,結束這些地區多年來的半獨立狀態。
蔣介石成功地控制了有天府之國美稱的成都平原,但是繼續向西前進的時候,卻遇到了麻煩,「芝麻開門」的咒語在西康這道門前失靈了。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蔣介石乘飛機從重慶飛往蘭州,這是抗戰全面爆發後,蔣介石對西北地方進行的首次巡視。一個月左右的西北之行,他先視察了甘肅,後又視察了青海、寧夏、陝西等地,並對上述各個問題進行了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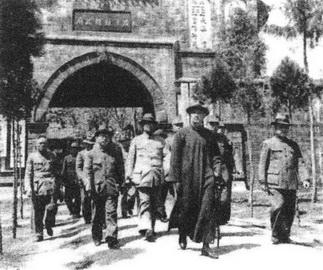
一九三九年十月,蔣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
七月初,川康整軍會議由何應欽主持在重慶召開。矛頭主要指向劉湘,對其他軍閥(二十軍楊森、二十四軍劉文輝、二十八軍鄧錫侯、廿九軍孫震及四川邊防軍李家鈺)是能吃則吃,能削則削。當時劉湘是省主席兼四川善後督辦(後改為川康綏靖主任)各派軍閥對他獨攬大權都十分不滿,但懾於劉湘的實力,表面不得不唯唯諾諾以示遵從,而思想深處則有強烈的反感。蔣介石就利用這一點,縱橫捭闔,終於使會議通過了有關川軍的三項決議:各軍縮減五分之一;團長以上軍官由中央直接委派;軍餉每月由軍政部派員點名發放。至此,川軍的人事權和財政權都被收歸中央統一掌管。
蔣介石的努力並未白費,八年中,數十萬川軍壯士轉戰祖國的大江南北、黃河内外,為民族抗戰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據不完全統計,在八年抗戰中,川軍將士共傷亡六十餘萬人。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劉湘在漢口病逝,國民政府為劉舉行了隆重的「國葬」,以安撫川軍,這對其他雜牌軍也有穩定作用。蔣介石的寬容態度和處置辦法,確實有利於鞏固抗日陣線。
隨著天津、北平、上海相繼淪陷,國防最高會議決定國民政府遷移重慶,十一月二十日發表遷都宣言。蔣介石及國民政府重心機構並沒有馬上入川,而是遷移到武漢。他還有顧慮:一是以韓復榘、宋哲元為首的一批北方將領能否利用黃河天險,在中原組織有效的抵抗,確保後方及華中側翼的安全問題;二是以劉湘為首的一批川軍將領能否保證中央機關安全入川。
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雲南省政府徵調數十萬民工,經過九個月苦戰,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底,滇緬公路中國段全程九五九點四公里全線通車。共完成土方一千一百二十三萬立方米,石方一百一十萬立方米,當時缺乏築路機械,主要靠人力挖山開路,勞動十分艱苦。工地沒有住房,風餐露宿;冬天高山區,以烤火熬過難眠之夜;夏天在河谷地區,汗流浹背,瘴瘧流行。在整個修路過程中,民工傷亡在萬人以上。為了補充勞力,婦女也走上了艱苦的築路工地。
九月十四日,蔣介石離陝返回重慶。事實上,蔣介石此行並不像他在公開場合所說的那樣,是例行視察,而是緬甸戰役失敗後,為國民黨政權從西南退往西北做準備。
西安事變後,輿論普遍認為蔣介石是屈於民意被迫抗戰,這實在是缺乏對他的深入瞭解。當許多人認為蔣介石被迫放棄了「攘安」之論的時候,他卻作了「以退為進」的規劃。在蔣介石的思考中,抗日實際上已經把「安內」與「攘外」統一起來,事實也表明聯合抗戰的方針比「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更靈活,因為以深得人心的抗日為旗號,「安內」的措施實施得更順利,就連排除異己也能名正言順地進行。
為解決西藏問題,蔣介石於廿六日由蘭州飛抵西寧。為了解除馬氏兄弟的戒備心理,他在青海省政府下榻,除了錢大鈞、朱紹良、顧祝同、胡宗南、戴笠等心腹大員外,只帶貼身保鏢四人。在召見馬步芳、馬步青時,蔣介石大加讚賞馬家軍,鼓勵他們「精忠報國」,並犒賞他們十萬元。蔣介石青海之行有著十分明顯的目的,即要借馬家軍的力量對西藏造成壓力。馬步芳對西藏早存非分之想,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同西藏軍隊在玉樹進行過青藏戰爭。
全面抗戰爆發以後,為了阻止其他國家援華物資進入中國,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宣布封鎖中國沿海。由於海運受阻,加上桂越公路及滇越鐵路也已受到威脅,新闢對外通道就成為當時中國的當務之急。所以,八月的國防會議期間,蔣介石接受了龍雲的建議,通知交通部協助雲南方面加緊修築滇緬公路。龍雲回到昆明後,立即抓緊籌辦。
調滇軍抗日,派中央軍戍邊,蔣介石「一出一進」順利蠶食「雲南王」備受排擠,政見迥異,龍雲最終走上反蔣道路。
徐州會戰時,六和*圖*書十軍開赴魯南戰場,在禹王山之戰中打得英勇頑強,苦戰近月,全軍官兵傷亡過半,其中旅、團長陣亡五人,負傷四人。徐州會戰以後,滇軍雖然損失很大,但名聲大振。此時的蔣介石沒有採用削弱雜牌軍的慣用手段,他在武漢召見龍雲和盧漢,對滇軍英勇作戰大加讚揚,保證部隊不縮編,可速請本省補充兵員,武器不足由中央補充。當然,他還要求龍雲再派一個軍出師抗日,於是孫渡率領第五十八軍奔赴湖南第九戰區參加抗戰。為了避免分化瓦解滇軍的嫌疑,蔣介石任命盧漢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統一指揮五十八軍和六十軍。
劉文輝的「政治上半開門」即是堅持省府人選由他確定,雖然在省府中曾安排過一些蔣介石的人,卻始終以川籍人員為主。在經濟上,蔣介石花了很多錢養西康,但是一直沒能奪走西康的軍政大權。
西安事變後,龍雲確定的方針是「抗日防蔣」。首先是加強軍事力量,四萬多人的滇軍是龍雲的衛隊,採取法式武器裝備,戰鬥力甚強,且唯龍雲馬首是瞻,似乎不知道中國最高武裝長官是蔣介石。其次是穩定雲南經濟,繼續阻止法幣在滇境流通,大量儲備糧食。雲南的糧食不能自給,歷來要從越南進口。龍雲早就意識到中日之間的戰爭將是持久戰,所以從「九一八」事變後就大力積累糧食。另外是加強同各方面的聯繫,以比較開明的政治態度對待中共、進步文人,支持抗日民主運動。此外,他同汪派的人也有暗中聯繫。
美國駐華大使詹森考察這條路線後,向美國總統羅斯福報告說:「這條公路選線適當,工程艱苦浩大,沒有機械施工而全憑人力修成,實屬不易,可同巴拿馬運河工程媲美。」
這一階段,劉湘對蔣介石還是比較強硬的,劉湘說過這樣的話:「我如果要幹的話(指川軍要反蔣)就是天也要打它一個洞。」不過,劉湘終於沒有行動,在民族危機加重的關頭,一切以民族大義為重,任何私怨都可以也應該捐棄。
日本利用中國内部紛爭之機,加緊「蠶食」中國。「攘安」論調,終於被中共「求同存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口號擊退。居於中國最高統治地位的蔣介石對日本「蠶食」中國的舉動早有顧慮,隨著日本亡華意圖日漸明顯,對於「攘外」和「安內」他也作了新的思考。一九三五年,他開始更多地考慮對日作戰的問題,雖然不乏悲觀陳辭,對內對外的態度確實已經發生了變化。
在軍事上,劉文輝堅持不讓蔣介石的一兵一卒進入西康。蔣介石曾派人收買土匪武裝,委以官職,就地組織反劉文輝的武裝力量,被劉文輝以違反兵役法為由強迫解散,國民政府的兵役法是不允許收編土匪的。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衛以「赴滇講學」為名飛往昆明,十九日下午,由昆明飛往越南河內,開始了他的「曲線救國」之旅。據汪派人士說,汪精衛已將全部「和平運動」的計畫告訴了龍雲,還得到龍的贊同。汪精衛在發表「豔電」投敵之後,其爪牙們也不斷宣稱,龍雲是可能「回應」的重要人物。
蔣介石對此還不是很放心,決定親自到西北去巡視。為什麼選擇這個時間去巡視西北呢?其目的主要有三:
龍雲,字志舟,出生於雲南昭通燕山的黑彝家族,彝名納吉烏梯,自幼習武,在彝民中以械鬥英勇著稱。辛亥革命時期與表弟盧漢離鄉投軍反清,後入雲南陸軍講武堂學習,接受了正規的軍事訓練,深得唐繼堯的信任。大革命時期,雲南爆發反對滇系軍閥唐繼堯的群眾鬥爭,龍雲深受影響。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他與胡若愚、張汝驥等滇軍將領聯合發動政變,推翻了唐繼堯對雲南的十四年統治。在隨後的將近三年內,他們之間又展開了軍事混戰,一九二九年下半年,龍雲擊敗胡、張聯軍,統一了雲南,確立了自己對雲南的統治。此後,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蔣介石指使杜聿明在昆明發動政變,龍雲被迫離開雲南為止,龍雲統治雲南十八年之久,是民國時期任職雲南主要領導職務時間最長的一位。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中國東部和南部的國際通道被完全截斷,緬甸的失守又使西南面臨被日軍攻擊的危險,這樣,蔣介石更感西北戰略地位的重要。他認為「今後我國局勢,西北重於西南,對內重於對外,整軍重於作戰」,因而計畫「從事於西北之建設,並將新疆與青海之全部鐵路一一氣呵成。蓋戰後二十年內,如有外患,則我必取守勢,仍欲引敵至我内地決戰」。他甚至有遷都西安的打算。他認為「南京與北平皆近海,最初三十年必不能建立強大之海軍為之掩護。故首都地點不能不在西安。以其地位適中,介於東北與西北之間,足以控制全國」。
蔣介石排斥異己的做法,促使龍雲政治思想發生轉變,在抗戰中,龍雲暗中支持抗日民主運動,促進了昆明民主堡壘的形成。蔣介石把龍雲趕出了雲南,不僅沒有解決雲南問題,反而是促使雲南及其他省分的地方實力派背蔣而去,加劇了蔣介石政權的離心力。
一九四二年,西藏地方政府與英印當局相勾結,圖謀脫離中央搞獨立,蔣介石使出一箭雙雕之計,命劉文輝率二十四軍進藏,另派兩個師的中央軍入康接防。劉文輝將計就計,向蔣介石索要軍械、裝備、經費和物資,還要求擴大編制,並派參謀長伍培英長駐重慶催促。經過半年糾纏,蔣介石以「暫緩實行」收場。一九四四年初,蔣介石派中央軍一個旅入康,被劉文輝擊退。
一九三九年元旦,西康省正式成立,省府設在康定,劉文輝任省主席。同年二月一日蔣介石撤銷重慶行營,分設成都、西昌委員長行轅,試圖控制西康。而劉文輝則利用西康地處抗戰後方、動輒牽涉大局的有利條件,實行了「經濟上開門,政治上半開門,軍事上關門」的較為強硬的對蔣方針。
劉湘死後,四川已是群龍無首,蔣介石https://m.hetubook•com.com認為控制四川的機會到了。劉湘死後三天,蔣介石連下幾道命令,撤銷劉湘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川康綏靖主任和四川省主席等職務,同時任命張群為四川省主席,撤銷川康綏靖公署。此舉遭到川康實力派的強烈反對,率軍留守四川的十七名旅長聯名致電蔣介石,反對張群主川。劉的部下認為:劉湘剛死,蔣介石既不派員來蓉慰言,又不與有關各方商洽,即命張群主川,實屬「趁火動劫,意圖宰割」。因而群情激昂,決定反對張群來川,在成都全城張貼標語,並舉行遊行示威。
武漢失守以後,國民政府各機關全部遷移重慶,四川的重要性進一步增強。蔣介石為安定抗戰大後方,千方百計分化劉湘嫡系將領,封官許願,收買川康實力派,為張群主川鋪平道路。張群也進一步拉攏川康各方人士。在組織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川康興業公司,開發川康的活動中,張群日漸取得了四川地方軍閥的支持。蔣介石認為張群的佈置已告完成,於是電轉川軍將領,說明自己實難再兼川省主席,擬任命張群繼任,希望他們協助張群。川康實力派得到了經濟實惠,認為此時再反對張群主川已不可能,遂表示贊同。
一九四四年冬,蔣介石想以通敵叛國的罪名武力解決劉文輝。中央又不好出兵,蔣介石把希望寄託在楊森、潘文華身上。楊森對蔣言聽計從,潘文華卻認為中央既已掌握劉文輝確鑿罪證,最好公諸國人裁判,不必興師動眾,更不宜加以襲取。由於潘文華不從命,只好作罷。
西北有著遼闊的地域和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不過,多年以來,中央政府在這裏的統治卻又是最薄弱的。同時,在這片土地上,民族、宗教問題又錯綜複雜。蔣介石非常重視西北,抗戰以前就派遣胡宗南率中央軍主力鎮守西北。全面抗戰爆發以後,西北有著雙重的意義——國際通道和西南地區門戶。正因如此,自一九四〇年以後,蔣介石不斷加強西北的軍事力量。

一九三九年冬,日本入侵桂南接著侵入越南,中國經越南的交通線被截斷。為了保衛雲南大後方及緬甸這條國際交通線,一九四〇年九月,蔣介石下令抽調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盧漢率原第六十軍的一八二、一八四兩個師及第九集團軍司令關麟征率領第五十二軍開入滇南,沿滇越邊境佈防。這是蔣介石的中央軍首次進入雲南,這是他為吃掉龍雲而下的第一步棋。蔣介石為了消除龍雲的顧慮,任命龍雲為軍委會昆明行營主任,並允許龍雲新成立一個軍(第九十三軍)。
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才開始對西南各省進行實際控制。西南各省原不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一九三五年追擊中共工農紅軍時,蔣介石雖然已極力把中央勢力滲透進去,但仍沒有根本消除地方的割據狀態。這時,他利用抗戰的時機,在西南地區再度大張旗鼓地統一軍政,力圖完全控制西南各省。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蔣介石明令張群為成都行轅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調賀國光為憲兵司令兼重慶衛戍總司令。四川「中央化」在經過了一段艱難的歷程後,終於實現。
從西康建省到一九四九年西康起義,劉文輝始終沒讓「中央軍」勢力進入西康,劉文輝的二十四軍沒有一兵一卒被蔣介石調出,沒有一兵一卒參加抗日,他雖然保住了自己的實力,但也在客觀上不利於抗戰的大局。
事實證明,蔣介石努力實現四川「中央化」是對的,也是堅持抗戰所必須的,不過他用王瓚緒來挑撥四川實力派之間的矛盾,從而實現控制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這也為以後鄧錫侯、劉文輝的投誠埋下伏筆。

四川在抗戰時期是國民黨統治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當時四川有六千多萬人口,是兵源的基地;重慶又是國民政府的陪都;抗戰爆發後,沿海許多企業內遷四川,又建了不少新的小型工廠;四川每年糧食產量又居西南各省之首。所以,四川自然是西南問題的重中之重。
早在南京國防會議期間,龍雲三番五次地表示,現在國難當頭,大家都應「少說廢話,多負責任。身為地方行政負責者,當盡以地方所有之人力財力,貢獻國家,犧牲一切,奮鬥到底,俾期挽救危亡」。現在,他奉命派滇軍出征,大部分裝備、給養均由地方自籌,滇軍在前線也忠勇奮戰。但是龍雲的抗戰熱情並沒有抵消蔣介石對他的顧慮,一個突發事件反而增加了蔣對他的疑心。
首先是為解決新疆問題。蘇德戰爭爆發以後,善於見風使舵的盛世才以為蘇聯和共產黨不可靠了,便積極投向蔣介石。恰在此時,原駐哈密的蘇聯紅軍第八團主力被調回參加衛國戰爭,盛世才見時機到來,便派人向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輸誠。蔣介石也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從而確定了解決新疆問題的幾項原則:向新疆派兵;將新疆劃歸第八戰區,以盛世才為副司令長官;新疆與蘇聯間的政治、經濟問題,其交涉權由中央行使。但盛世才又為中央軍入新後其地位無保障而顧慮重重。朱紹良為穩住盛世才向蔣介石提議,由蔣派親信大員攜其親筆信函前往迪化,承諾不危及盛世才在新疆的權力和地位,以解除其反蘇反共的後顧之憂。
其次,處理西藏問題。西和圖書藏此時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危機,國民政府同西藏的關係此時存在危機。關係惡化的主要根源是西藏地方政府阻止中央政府修築中印公路。雖然,蔣介石採取了軟硬兼施的政策,但西藏地方當局以英印為靠山,堅決拒絕康印公路經過西藏,尤為嚴重的是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六日成立專理漢藏間一切事情的「外交局」,儼然以獨立國自居。因此,蔣介石計畫乘巡視西北之際,決定對西藏問題的解決方針。
一九四一年,中英達成共保滇緬國際交通線的協議後,蔣介石調集大量部隊到雲南邊境,出於抗戰大局的需要,龍雲再次同意中央軍入滇。當時,駐紮在雲南的蔣介石部隊主要有三個部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滇參謀團(以林蔚為參謀團長)的部隊,昆明防守司令(初為宋希濂,後為杜聿明)的部隊,準備入緬的遠征軍。一九四三年四月,蔣介石又成立了以陳誠為首的遠征軍司令長官部,設在滇西楚雄,把楚雄以西的軍隊指揮權從昆明行營(原行營主任為龍雲)劃分出來,削弱了龍雲的實力,並且楚雄在昆明附近,可以就近監視龍雲。
最後就是督促胡宗南加強封鎖陝甘寧邊區的目的。
對劉湘積極支持抗戰的表現,蔣介石是十分讚賞的,但劉對韓復榘的暧昧態度不得不使蔣介石有所顧慮。在獲悉韓復榘的陰謀之後,蔣介石不動聲色。隨戰勢變化,他任命劉湘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無法抗拒,帶病親自率領主力部隊到南京前線。川軍大量外調為中央政府各部門順利遷入重慶鋪平了道路。後來,韓復榘戰場上擅自撤退,蔣雖以臨陣脫逃罪將韓處決,並沒有公佈其想擁川獨立的陰謀。
抗戰爆發前,劉湘在蔣介石的卵翼下成功打擊了四川其他軍閥,成了四川的統治者。蔣介石在追擊紅軍時,不斷向四川擴張。在四川統治權問題上,劉湘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兩廣事變時,劉湘密令所部軍隊在夜間向成都、重慶兩地集結,準備策應李宗仁。西安事變時,劉又有同樣的舉動,甚至直到蔣被扣的第五天都沒有發表聲明支持蔣。不但如此,他甚至還勸張學良要毫不猶豫地把蔣幹掉。當時,劉湘還想乘機恢復四川行政和財政的獨立。但時局變化太快,就在劉湘準備大顯身手的時候,西安事變就和平解決了。此時,蔣介石的部隊正大舉進攻陝西楊虎城部隊。為自衛計,川軍在重慶一帶佈防,阻止蔣介石部隊的進犯。但是,劉湘的一切活動,都瞞不過蔣介石的耳目。

蔣介石(右)孔祥熙(左)陪同林森(中)步出國民政府禮堂
蔣介石利用中央軍入滇來解決龍雲的用心是十分明顯的。他常常向在滇的親信面授機宜,要求他們秘密監視龍雲的動向。他曾對宋希濂(當時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說:「你到昆明後,首先要瞭解雲南的情況,搞清楚昆明附近的地形,對各重要據點要確實控制,隨時提高警惕,並與王叔銘(時任昆明空軍司令兼空軍學校教育長)密切關係。」中央軍進入的同時,許多軍統特務也開進雲南活動。
在此期間,蔣介石曾先後派遣李烈鈞、唐生智來雲南考察,實際上是監視龍雲。不過,考察後,唐生智給蔣介石的報告認為,龍雲抗戰態度是堅決的,「擁護鈞座,始終不渝」,與汪精衛叛逃事件並無牽連。唐生智的報告並不足以使蔣消除疑心,何況,削弱龍雲勢力、解除雲南半獨立的割據狀態是蔣介石素來的願望。汪精衛經由昆明出逃的事件,不過是加速了蔣介石控制雲南的步伐。
雖然龍雲在汪出走當日就電告了蔣介石,後來又就此事做專門報告,但在外敵緊逼,內部分裂,流言四起的環境下,蔣介石是不可能不懷疑龍雲的真實態度的。
在迪化,盛世才盛情款待宋美齡一行。經過一夜洽談,盛世才在宋美齡一再保證其在新疆地位不變的條件下,同意了蔣介石的要求,並當即覆函表示按蔣的要求去做。九月五日,在蔣介石返回西安不久,盛世才便命令蘇聯撤走所有駐新疆專家、顧問以及駐甘新邊界星星峽的蘇軍。九月十七日,盛世才在新疆掀起清共浪潮,中共駐新疆領導人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被逮捕。蔣介石在新疆反蘇反共的陰謀得以實現。
成都的激烈反應使蔣介石大為震驚,也使他清楚地意識到川事不能操之過急。但是,考慮到四川已成為抗戰的大後方,若是動盪不發,國民政府就無法在四川立足,而當時的形勢又不允許他對川用兵。蔣介石於是改變策略,覆電安撫四川各將領,同時,一面保留川康綏靖公署,任命鍾體乾為主任,另一方面則任命張群為重慶行營主任,並擬委派曾任重慶行營主任的顧祝同代替張群主持川政。代理全川保安司令王陵基得消息後,聲稱「顧祝同如敢飛成都,當以大炮在機場歡迎」。蔣介石無奈,只好滿足四川軍閥的要求,任命王瓚緒代理川省主席。

「東禦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蘇俄、內懾回馬」,蔣介石調集胡宗南精銳坐鎮西北;親巡西北,與軍閥握手言和,蔣介石為退向西北做準備。
在軍事問題上,他先後巡視了河西走廊的肅州(酒泉)嘉峪關、甘州(張掖)、涼州(武威)等地,視察了第廿九集團軍各部隊和寧夏馬鴻https://m•hetubook.com.com逵部隊,為中央軍進入新疆做準備。同時,先後在蘭州興隆山、寧夏謝家寨召集西北高級將領召開軍事會議,並對西北的軍事問題進行部署。防範共產黨,是他強調的重點,他要求加強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
為此,蔣介石付出了一定代價。因蔣韓之間積怨較深,處死韓復榘曾引起世人對蔣介石「公報私仇」的猜疑和議論。如果披露韓復榘的分裂陰謀,這種議論便會煙消雲散,但蔣介石寧可承受輿論不明真相的壓力,也未披露韓、劉陰謀真相,其目的在於繼續團結川軍和韓復榘舊部及宋哲元部抗日。

蔣介石將胡宗南的第十七軍團擴編為第三十四集團軍,他給胡宗南制定了「東禦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蘇俄、內懾回馬」的十六字戰略方針。為了加強空中防禦,蔣介石同時下令在河西之玉門、張掖,青海之居延海等地修建重型轟炸機機場。另外,蔣介石還親自兼任「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四團」、「西北幹部訓練團」團長和「西北游擊幹部訓練班」班主任,以培養國民黨在西北的政治、軍事骨幹。

蔣介石巡視西北與蒙旗各族王公合影
於是,蔣介石進一步增兵西北,使這一地區中央軍多達十三個軍。一九四二年三月,他將胡宗南任命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並將其所率部隊擴充成三個集團其中,陝南、豫西、隴東、關中一帶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七集團軍駐用於防共和禦日;在蘭州、平涼及河西走廊一帶的第三十八集團軍防範盛世才,牽懾回馬。
蔣介石未能把西康的軍政大權收回,除了劉文輝的強硬態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劉文輝和當地少數民族關係十分好,而蔣介石要奪取西康,就不能不考慮少數民族的態度。並且西康是扼守西藏的要道,在少數民族地區,蔣介石不得不慎重行事。
在張學良、楊虎城的兵諫下,蔣介石已經同意聯共抗日,一場大規模對日作戰即將到來。從兩次事變中,蔣介石看清了劉湘並不真心擁護自己。為了有一個安定的大後方,他越發覺得必須一勞永逸地解決四川問題,即使引起武裝對抗也在所不惜。
這次,蔣介石設想在青海與西康之間單獨設立一個單獨的省,把玉樹作為省會,以加強對青藏康邊的控制。他乘飛機巡視了青藏邊地區後,決定「對藏暫時隱忍,以冀其自覺」,解決西藏問題以政治手段為主,軍事手段為輔,只要西藏承認中央政府只有一個,即重慶政府就可以了。蔣介石認為,只要西康和青海控制在手中,川康和青藏公路打通,「藏事自然解決」
在西北的巡視中,蔣介石發現西北軍隊軍心渙散,戰鬥力低下。各將領也普遍反映後勤補給困難,士兵經常吃不飽肚子,部隊藥品缺乏,疾病流行,從而怨聲載道,要求中央給予解決。蔣介石對此十分惱怒,他訓斥各級長官事事依賴中央,並要西北駐軍體諒中央的困難,力行「勤勞儉約」,凡事「自動自理,來解決一切補給困難」。他指示西北駐軍除了軍事訓練以外,更重要的是開展建設西北的活動,即屯墾、畜牧、興辦水利、植樹造林、發展交通運輸五大任務。他告誡胡宗南等人,「必須認清西北目前的形勢與其在國際上的重要性」「一致努力來建設西北,鞏固西北」,「不可視為邊疆而言辛苦」。
抗戰一爆發,蔣介石就以抗戰統帥的權力,將龍雲經過多年訓練的雲南精銳部隊的主力抽調出境。一九三七年九月,以盧漢任軍長的第六十軍,轄三個師,奉命出滇保衛南京外圍。當時,蔣介石十分注重對非嫡系將領施以恩惠,加以籠絡。六十軍到武漢時,蔣介石待之禮遇有加,允許盧漢增編三個補充團,撥給汽車二十多輛以及德造手槍八百支,子彈十多萬發,還專門為該軍配備後方醫院。此外,他還令六十軍全副武裝,列隊行軍經過武漢鬧市區,以宣示國軍仍有精良部隊未投入戰鬥,藉以鼓舞後方民心,同時也振奮了六十軍軍威。滇軍在武漢遊行時,蔣介石的德國顧問看到後,驚異地對蔣介石說:「盧漢率領的滇軍是你們中國的驕傲,是最有力的部隊。」
「攘外」亦可「安內」,利用抗戰時機統一西南軍政,蔣介石早有準備;民國政府遷都、川康軍事會議多效並舉,蔣介石坐收天府之國卻難取西康大權。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劉湘赴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最高國防會議,在會上竭力主戰,提出「抗戰四川可以出兵三十萬,提供壯丁五百萬,供給糧食若干萬石」劉湘慷慨激昂的發言得到全場的讚許,高漲的民族主義終於開始驅散擁兵割據的落後觀念。九月一日,川軍分東、北兩路開始出川抗日。
蔣介石的擔心並非空穴來風。據宋哲元的密報,韓復榘曾派人遊說宋部,提出由劉湘令川軍封閉入川之路,韓本人率部撤居南陽、襄樊、漢中一帶,勸宋部撤守潼關以西,然後聯名通電倒蔣。蔣介石嚇出了一身冷汗。劉湘、韓復榘、宋哲元三部有數十萬大軍,在外有日軍步步緊逼的形勢下,如果聯合行動,真的是能「把天打一個洞」的。
「芝麻開門」的神話故事在蔣介石身上發生了,蔣介石打開的是煥發勃勃生機的天府之國。抗戰八年,四川除派數十萬軍隊出川抗戰外,還向和圖書國家貢獻了二百五十多萬壯丁,補充了南北戰場上的國民黨軍隊,以致當時前線有「無川不成軍」之說,有六十餘萬將士傷亡。另外還有幾百萬民工服務國防。抗戰時期軍糧的相當一部分靠四川提供,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年的時間內,共向政府交糧八千二百多萬市石,占同期全國徵糧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一點六三,為抗戰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在龍雲領導下的雲南為抗日作出了巨大貢獻。滇軍先後在魯南、武漢、湘北、贛北及滇南作戰,「均能忠勇奮發,一往無前,彈雨槍林,傷亡枕藉」。據統計,在抗日戰爭期間,雲南派出滇軍支援前線抗戰約近四十萬人,傷亡約十萬人。龍雲自己也曾表示:「滇省原為貧瘠之區,但國事如此,誓以將政府歷年所蓄,及民間所有公私力量,悉數準備貢獻國家」,而無怨言。
雲南,簡稱滇,位於中國的西南邊陲,與緬甸、越南接壤。唐、宋時分屬大理國和南詔,元代置省,因地處雲嶺以南得省名。雖然自辛亥革命開始,雲南就宣布接受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領導,但是不管是在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時期,還是在國民黨執政的南京政府時期,雲南事實上都處在滇系地方力量割據狀態中,儼然是個獨立的小王國。蔣介石早就有心控制雲南,卻總是找不到扳倒「雲南王」龍雲的機會。
一九三七年春,蔣介石提出要縮編四川軍隊,又提出要軍民分治,劉湘主軍,由蔣介石派人任四川省主席,劉湘堅決抵制。但在中央政府的優勢兵力面前,劉湘最終屈服,同意將所有軍隊都轉歸國民政府軍委會直接指揮,川軍的財政開支轉歸蔣的重慶行營負責,一切軍事設施也由國民政府接管。同時蔣決定召開整軍會議改編川軍。
蔣介石採取了三步法,即調出、派進和解決。
隨著戰爭形勢的變化,中國對外交通斷絕,滇緬公路幾乎成為抗戰時期中國唯一的對外陸上交通線,成了抗戰的輸血管、生命線。這樣,雲南成了重要的工業基地和唯一的外貿集散地;清華、北大、南開等高校遷入昆明後,雲南又成了抗日的文化中心之一,雲南的地位更加重要。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龍雲還利用他所控制的滇緬公路,向各省來往貨物徵收過路費,雲南的分割獨立狀態已經成為全國抗戰的阻礙。蔣介石為了抗戰考慮,也為了其統治地位考慮,一心想控制雲南。但龍雲也不想輕易地把自己的地盤轉手讓人,圍繞著雲南的控制權,蔣介石與龍雲展開了一系列鬥爭。
在新疆問題上,他於八月廿九日派宋美齡、吳忠信、朱紹良等攜帶他的親筆信飛往迪化,撫慰盛世才。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中央軍由蘭州開進安西、玉門,控制哈密的蘇軍;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員,收回外交權,歸中央政府,使蘇聯在新疆的外交步入正軌;肅清在新疆的共產黨;下令蘇聯軍隊撤離新疆;收回迪化的飛機製造廠。與此同時,對新疆省黨務特派員、教育廳長與省政府秘書長等人選作出規定,要求均由重慶任命。
龍雲也在防備著蔣介石。滇軍主力部隊被調往抗戰前線後,滇中軍力空虛,為了加強雲南防護,龍雲不顧蔣介石「國防歸中央」的規定,又組編了七個步兵旅,但是這並不能阻止中央軍開進雲南。
但是,這並沒有贏得蔣介石的信任。相反,蔣介石不斷排擠龍雲的力量,在雲南安插自己的親信,密佈特務,監視龍雲的舉動。雲南「中央化」的過程中,蔣介石並沒有獲取地方實力派的人心。
消除地方割據,增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是歷代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標。在頻頻遭受外敵侵略,備受喪權辱國之煎熬的近代中國,統一與集中的願望和要求更顯迫切。蔣介石在三十年代初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就是以這種歷史願望和要求為背景的。他的失誤在於固守黨派之爭、信仰之別,在「安內」方面採取了僵化的排除、消滅異己的力量的態度。
就是通過這樣一步一步行動,蔣介石把他的勢力逐步滲透到雲南的各個領域,龍雲的力量不斷受到排擠。但蔣介石想解決龍雲,徹底控制雲南的圖謀一直未能得逞。但抗戰一勝利,蔣介石就利用機會用武力把龍雲請到重慶任軍事委員會參議院院長,從而在表面上了控制了雲南。但滇系的幾十萬大軍和地方勢力依然存在,一番波折後,只好任命滇系第二號人物盧漢繼任雲南省政府主席,雲南政權仍然落在滇系手中。
九月三日,蔣介石從寧夏飛抵西安,於六日在西安召集長江以北各戰區(第一、二、五、八戰區)高級將領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李宗仁、蔣鼎文、孫蔚如、湯恩伯、胡宗南等。會議持續了五天,蔣介石聽取了各軍、師長的彙報,並針對逃兵、兵役、軍糧、軍隊編制、軍隊的教育與訓練、軍紀、對敵戰略與戰術等問題,作了兩天的講評。
龍雲統治雲南之初,繼承了唐繼堯軍閥統治的衣缽,一面追隨蔣介石鎮壓共產黨,一面建設「半獨立」式的「新雲南」雲南大小官吏設置任選都由龍雲一手操縱,蔣介石根本無法插手。雲南經濟政策和金融系統也自成體系,龍雲搞了一個雲南人民企業公司,經營和管理雲南各項企業,原始積累都歸雲南地方所有,一直到一九四一年,雲南仍使用地方發行的滇幣,蔣介石的「法幣」在雲南一度被視為廢紙。
因此,他在青海對馬步芳百般籠絡,要其在軍事上給西藏加強壓力,並修築西寧至玉樹長達一千四百餘公里的青藏公路,修建飛機場,儼然使青海成為解決西藏問題的前沿陣地。蔣介石還部署馬步芳派軍隊兩個團進駐青藏邊境,配合西康劉文輝的軍事行動,該支部隊不久便進入西藏境內。蔣介石在青海期間巡視並佈施於塔爾寺和東關清真大寺,並於廿七日召見藏教活佛、回教阿訇、藏滿蒙回漢各王公、千戶、百戶、士紳等於西寧,大談民族團結。他稱漢、藏、蒙、回、滿是五大宗族,均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